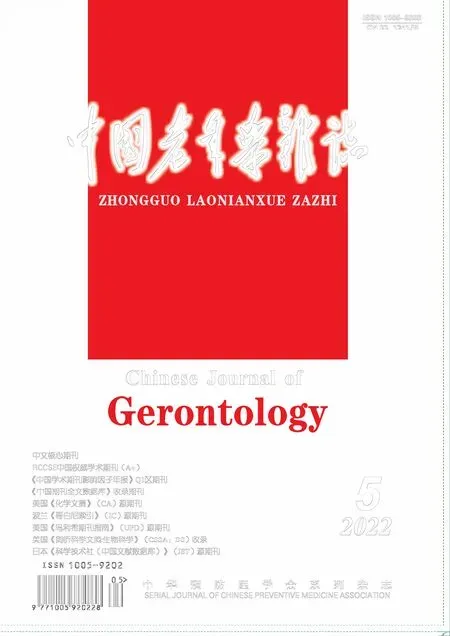積極老齡化理論的國內外研究進展
李宏潔 張艷 杜燦燦 趙敬 李思思 田雨同 劉珍
(鄭州大學護理與健康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預計到2025年,全球6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12億〔1〕,如何有效緩解老齡化負擔、提升老年人口的生活質量成為全球范圍內的重要議題。積極老齡化理論提倡老年人擺脫“貧窮、多病、無價值”等消極刻板印象,充分發揮自身潛能與優勢、作為家庭與社會的重要資源參與社會生活中,在體現自身價值的同時,也為社會做出有益貢獻,從而緩解老齡化問題負擔。自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正式提出積極老齡化理論框架之后〔2〕,該理論已成為全球各國應對老齡化問題的新思路并被廣泛應用,如對積極老齡化理論內涵的解讀、相關測評工具的研制、積極老齡化影響因素的研究及對積極老齡化促進措施的探索等。目前,積極老齡化理論在中國也已得到逐步探索和應用,研究內容集中于理論解讀和現狀分析。本文對積極老齡化理論的國內外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1 理論概述
傳統老齡觀念多將老化理解為不可逆的衰退過程,將老年人定義為“衰弱、無價值”的消極形象,而忽視了老年人的潛在能動性和社會價值〔3〕。直到20世紀末,積極心理學的浪潮推動老齡問題研究向“積極老齡化”方向發展。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在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上正式提出“積極老齡化”理論框架,將積極老齡化定義為:老年人能夠充分發揮自身體力、精神及社會潛能,并按照自己的需求、愿望和能力去參與社會,以實現生活質量的提升,同時也能在需要幫助時獲得充分的保障和照料。該理論以“獨立、參與、尊嚴、照料、自我實現”為基本原則,包含3個支柱要素——“健康”“參與”和“保障”〔2〕,其中“健康”指老年人能夠維持良好的身體、心理及社會交往狀態,是積極老齡化的先決條件;“參與”是老年人能根據自己的能力和興趣、參與到文化、娛樂、經濟等社會生活中,實現老有所為,是積極老齡化的核心內涵;“保障”指老年人在部分或全部喪失自理能力時,能夠得到足夠的照護支持,以滿足其身心、經濟及社會支持等層面的需求,是積極老齡化的必要條件。此外,世界衛生組織還在“健康、參與、保障”的基礎上,提出了積極老齡化六項組成要素,即健康和社會服務因素、個人行為因素、個人身心因素、物理環境因素、社會環境因素及經濟因素〔2〕。
2 積極老齡化相關測評工具
積極老齡化理念提出早期,社會建構理論家Gergen就從社會建構觀點出發,提出了積極老齡化的三大測量維度,即自我、人際關系和社會參與〔3〕,盧曉琳〔4〕根據這3個維度設計了13個條目的《積極老齡化量表》用于測評積極老齡化程度,但該量表內容側重于對“參與”的測評,未涉及“健康”和“保障”兩方面。2007年,Barker等〔5〕開發了《老化認知問卷》,該問卷包含8個分問卷,主要用于評估老年人對老化的認知情況,目前已由胡蘊琦〔6〕漢化修訂。2009年,詹明娟〔7〕通過文獻回顧編制了《活躍老化量表》,該量表包含“心理健康”“生活調試”和“社會互動”3個維度共24個條目,并成為中國部分研究者實施積極老齡化干預的評價工具之一。2012年,胡敏〔8〕通過文獻回顧結合質性訪談,編制了《老年人積極老齡化測評問卷》,包含身體活力、生活滿意、家庭支持、積極參與等4個維度共32個條目。2014年,Thanakwang等〔9〕指出,以往積極老齡化測評工具的理論基礎不一致,并結合質性訪談,在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積極老齡化理論框架的基礎上構建了《積極老齡化量表》,該量表包括自理能力、積極參與社會、開發心靈智慧、建立經濟保障、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積極學習、加強家庭關系確保晚年得到照顧等7個維度共36個條目,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014年該量表由張建閣等〔10〕引進并漢化。
3 積極老齡化相關因素
3.1個人因素
3.1.1身心健康 在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積極老齡化理論框架中,身心健康是積極老齡化的先決條件,也是老年人社會參與的前提。Paúl等〔11〕對葡萄牙1 322名社區老年人進行訪談發現,身心健康與積極老齡化高度相關,包括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認知、幸福感、孤獨感等在內的身體和心理因素均會影響積極老齡化的實現。該研究也表明,心理因素在老年人適應老化的過程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步入老年期之前就應該采取措施預防健康問題、著重提升其適應能力和心理彈性,以提升晚年生活質量。我國有關研究結論也顯示,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是老年人實現積極老齡化的必要因素〔12〕。
3.1.2老齡觀念 積極老齡觀是老年人對于自身參與社會發展、社會保障所持的積極樂觀態度〔13〕。促進老年人維持健康、參與社會,還需從認知層面入手,幫助老年人樹立積極老齡觀。積極的老齡觀可降低消極刻板印象對老年人行為和認知功能的影響,還有助于減輕因共患病而造成的老年人生活質量降低〔14,15〕。有關研究也表明,積極的態度可提高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幫助其主動參與社會活動,提升積極老齡化水平〔16〕。一項關于老年癡呆的隊列研究也發現,積極的老齡觀念可降低老年癡呆的發生率,即使是對于攜帶癡呆基因的高風險人群,積極老齡觀也同樣是預防老年癡呆的重要保護因素〔17〕。
3.1.3人口學因素 除身心健康、老齡觀念等因素外,人口學資料的不同也可能造成積極老齡化水平的差異。巴西的一項研究對2 052名老年人進行訪談,結果表明老年男性和女性的積極老齡化水平存在差異〔18〕。歐洲的一項研究對非機構化老年人進行的橫斷面調查顯示,老年男性比女性的積極老齡化程度更高,且已婚或同居者的積極老齡化水平比喪偶或離婚者高,而不同居住地的老年人積極老齡化水平亦有所差異〔19〕。此外,文化程度也是影響積極老齡化水平的重要因素,馮春梅等〔20〕研究顯示,在積極老齡化各項影響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對積極老齡化水平影響較大。
3.2物理環境 物理環境也是積極老齡化的重要影響因素。Chrysikou等〔21〕分析認為,城市規劃、建筑設計等環境因素與積極老齡化密切相關,完善基礎生活設施有助于促進積極和健康的老化,并指出應將積極老齡化理念融入建筑、設計等學科教育中,以求創建年齡友好型的生存空間。世界衛生組織還與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35個城市合作,編制了“全球年齡友好型城市指南”及“年齡友好城市基本特征清單”,確定了8個年齡友好型城市的特征:室外空間和建筑、交通、住房、社會參與、尊重和社會包容、公民參與和就業、溝通和信息、社區支持和健康服務,為積極老齡化社區建設的自評提供參考標準〔22〕。
3.3社會因素
3.3.1經濟水平 經濟條件會影響老年人對養老方式的選擇及晚年的生活質量。Perales等〔19〕研究顯示,老年人收入水平越高,其積極老齡化水平越高。日本學者通過隊列研究發現,經濟狀況是影響積極老齡化的決定性社會因素之一,與高收入者相比,收入較低者更可能具有較低的健康壽命〔23〕。中國相關研究也證實了經濟實力是影響積極老齡化的重要因素〔20〕。
3.3.2社會活動 眾多研究均證實了活動參與對積極老齡化的重要作用。一項針對歐洲四國(丹麥、法國、意大利和英國)的縱向數據分析表明,參加有償活動的老年人更不易患抑郁或報告較差的健康狀況,提示有償活動可能有助于老年人的晚年健康〔24〕。也有研究顯示,志愿服務活動同樣與積極老齡化密切相關,且老年志愿者比年輕志愿者的服務時間更長,提示可在老年人群中倡導志愿者服務活動〔25〕。此外,Malderen等〔26〕對居住于長期照護機構的老年人進行焦點小組訪談后發現,除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因素外,有意義的休閑活動也是積極老齡化的重要決定因素。我國基于老年人口健康調查數據的分析也顯示,參與社會活動對老年人有積極影響,且能顯著預防老年人失能的發生〔27〕。
3.3.3社會保障 盡管積極老齡化的關鍵在于老年人自身的主動參與,但外部保障仍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因素,無論是身心健康、物質環境還是社會參與,都必須依托有力的社會保障才能實現。León等〔28〕研究指出,有效的社會支持有助于降低老年人抑郁水平、改善其認知功能和生活質量,是積極老齡化的關鍵因素,應從改善社會資源入手,為老年人提供有力的外部保障。李春斌等〔29〕也指出,保障老年人合法權益是促進老年人社會參與、實現積極老齡化的必要條件,倡導相關機構積極完善老齡人口閑暇權、文化權、福利權等保障,做到社會資源“不分年齡、人人共享”。
4 積極老齡化促進措施
常見的積極老齡化促進措施有互助養老、老年大學、“互聯網+養老”等模式,其共同特點是通過引導老年人參與自尊、自立、有益的社會行為,為老年人賦能,幫助其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學”等目標。
4.1互助養老 互助養老強調以積極合作和相互照料來實現老年人的增能與發展,并通過引導非正式社會支持來緩解養老照護人員短缺與龐大的養老服務需求間的矛盾,從個人和社會兩個層面實現積極老齡化。
4.1.1同輩支持 同輩支持是互助養老的重要形式,如起源于美國的會員制養老組織“Villages”,就是以“自治、自我支持”為理念。通過老年會員之間相互服務來滿足其就地老化的需求〔30〕。類似的還有以“泛家庭”為理念的荷蘭生命公寓,以老年婦女互助為主的法國芭芭雅嘉公寓等。2008年,我國農村地區也率先興起了同輩互助形式——“互助幸福院”,通過低齡老人照顧高齡老人、健康老人照顧失能老人,滿足老年人的照護需求,幫助老人從依賴家庭走向自主互助〔31〕。同輩支持不僅能幫助老年人依靠自身力量實現就地老化,也是鼓勵老年人社會參與的重要精神支持。Janet等〔32〕研究也表明,同輩支持有助于提升不愛外出活動的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活力、增強他們外出活動的自信心和感知社會支持,對促進積極老齡化有很大幫助。
4.1.2代際支持 代際支持包括代際學習和同住支持。代際學習是指年長者和年輕者在知識、技能、觀念等方面進行交換和學習。研究顯示,代際學習能填補代際鴻溝、打破代際間刻板印象,且“經驗傳播者”的身份使老年人獲得價值感和使命感,促使老年人重新融入社會〔33〕。此外,代際學習對保持老年人身心健康、實現老有所學也具有重要意義,如我國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借鑒國外代際閱讀模式開展“樂齡學堂”,通過組織年輕志愿者為老年人讀書讀報、知識講座,幫助老年人拓寬視野、增長見識,維持身心健康〔34〕。 而同住支持主要是通過不同年齡組的共居和互助交流實現積極老齡化目標,如德國的多代屋、日本的老少合居房屋等,美國西雅圖的代際學習中心還嘗試“將幼兒園建在養老院”。近年來我國多地也開始嘗試開展此類模式,通過代際同住使老年人得到陪伴,年輕人獲得鍛煉、收獲智慧與經驗,達到積極老齡化“雙贏”目標〔35〕。
4.1.3時間銀行 時間銀行是互助養老逐步發展形成的新模式,這種模式將代際、同輩間的互助服務進行量化,其理念是“服務今天,享受明天”,即由低齡或健康的老年人利用空閑時間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服務、積累服務時長,并在自身需要照護時兌換相應時長的服務,是引導老年人進行積極老齡化社會參與的重要方式〔36〕。該模式由美國學者提出,并發展成為促進積極老齡化發展的新型社區養老模式,在多個國家地區得到認可和應用〔37〕。Valek等〔38〕認為,時間銀行不僅實現了互助養老,還是一種非正式的社會學習,能促進不同年齡群體的跨文化理解與尊重。由于該模式合作互惠的理念與我國傳統文化中“守望相助”的特性相吻合,近些年我國部分地區也開展了時間銀行并取得成效,盧曉琳〔4〕調查發現,時間銀行有助于擴大老年人的人際網絡,使老年人進行更加積極的社會參與和自我實現。
4.1.4其他互助形式 除以上外,各個國家和地區還發展了多種無償或有償的互助支持形式。Dizon等〔39〕對不同國家地區積極老齡化政策的分析結果表明,志愿工作被認為是老年人進行社會參與、對社區做出貢獻的重要的積極老齡化促進方式。如中國香港的“左鄰右里計劃”,培訓老年人成為社區義工進行鄰里關懷和走訪,識別需要幫助的老年人、并鼓勵隱居的老人外出參與活動,通過鄰里支持、為社區安全做貢獻來提升老年人的價值感〔40〕。此外,中國河南省駐馬店市在全國范圍內率先建立起由政府支持的殘疾人托養中心,其中照護者與被照護者均為建檔立卡的貧困戶,通過這種托養形式,貧困失能人群能夠獲得良好的托養照護,貧困健康人群也可通過提供照護獲取津貼,緩解經濟負擔,實現“自立、互助”雙贏〔41〕。
4.2老年大學 老年大學旨在通過教育促進積極老齡化,實現老年人終身和全面發展。國外老年大學多具有較完善的政策支持,部分還由高等院校創辦,并鼓勵老年人主動參與課程設置,通過知識傳遞、體育活動等多方面教育內容鼓勵老年人積極健康迎接老化〔42〕。研究表明,參與老年大學不僅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43〕,還能增加老年人對互聯網新興技術的接觸和使用,提升其在信息時代的社會參與水平〔44〕。中國老年大學較發達國家起步稍晚,目前尚未形成統一的課程設置標準,但亦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完善,并取得一定的積極效果,如金陵老年大學、杭州老干部大學等。中國老年大學協會鏈接各地老年大學為會員單位,并定期舉辦各種積極老齡化主題教育和文藝活動,以促進積極老齡觀念的宣傳普及。
4.3互聯網+養老 近年來,互聯網、新媒體的普及催生出“互聯網+養老”新模式,旨在通過信息技術為老年人的健康、安全賦能,并拓寬其社交網絡,從而實現積極老齡化。健康是實現積極老齡化的先決條件。Nam等〔45〕調查發現,基于互聯網的健康信息有助于老年人主動實施預防性健康行為(如癌癥篩查、疫苗注射)。Camp等〔46〕研究也表明,基于ipad的新媒體教育有助于增強糖尿病老人自我健康管理的效能感。還有針對癡呆老人的智能家居,通過自動提醒裝置幫助老人獨立完成日常活動,提高癡呆老人的功能獨立性,減輕其對照護者的被動依賴〔47〕。此外,互聯網對于促進老年人社會參與也具有重要意義,Czaja等〔48〕開發了用于老年人社交、查詢的軟件系統PRISM(個性化提醒信息和社會管理系統),并證明了其在減少老年人社交隔離和孤獨感、增加老年人社會參與效能感方面的作用。Szabo等〔49〕研究也表明,互聯網社交工具改善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健康狀況,使老年人能夠更加廣泛地參與社會活動。
綜上,積極老齡化理論強調老年人的自立和自我實現,鼓勵老年人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用,從社會負擔轉變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資源。目前國內外有關積極老齡化的研究涉及測評工具、影響因素、干預措施等各個方面,但多以城市社區老年人為研究對象,測評工具的研發也多以城市老年人為樣本,較少涉及農村地區老年人。相較于城市老年人,農村老年人沒有“退休金”作為穩定充足的經濟來源,養老條件低于城市水平,此外,中國農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且易受傳統家庭觀念的影響,因而在步入老年后,將多數時間用于家務勞動、照顧孫輩等,以上因素綜合導致農村老年人對于較高層次社會活動缺乏參與條件和參與意識,其積極老齡化現狀不容樂觀。因此,未來研究可關注農村老年人積極老齡化水平的提升,在農村特色文化背景下繼續探討積極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促進措施。此外,由于年齡、生活背景、文化水平、經濟條件等均可能影響積極老齡化水平,因此未來可嘗試建立積極老齡化預測模型,并以中年人群為對象,探討其積極老齡化準備度,從而設計針對性干預措施,幫助其積極應對角色過渡,協助推動積極老齡化實踐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