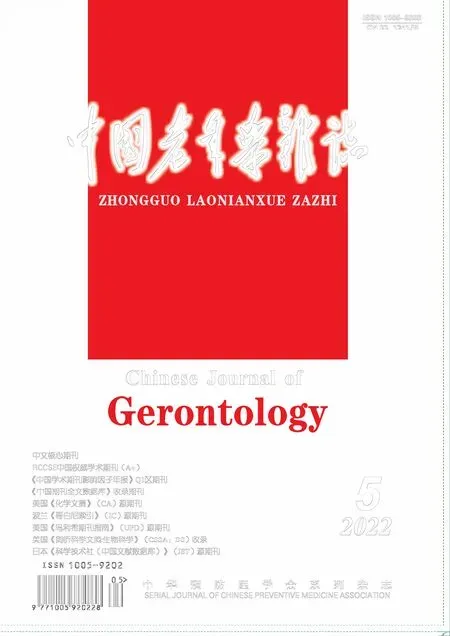肌萎縮側索硬化致病蛋白與自噬相關研究進展
劉玥 朱瑜 江建香 江師師 徐仁伵
(1江西省人民醫院神經內科,江西 南昌 330006;2南昌大學醫學部研究生院)
肌萎縮側索硬化(ALS)是以上下運動神經元損傷為特點的神經系統變性病中的一種,其預后較差,一般平均生存期為3~5年。目前僅有利魯唑及依達拉奉用于臨床治療〔1〕。現今流行的致病學說較多,諸如蛋白質的異常積聚及毒性作用,星形膠質細胞激活小膠質細胞引起的炎癥反應損傷神經元,神經元內質網應激及運動神經元的軸突運輸損害等〔2〕,其中較為主流的致病學說為蛋白質的異常積聚及毒性作用,由于眾多異常蛋白的累積,細胞離不開自噬與泛素蛋白酶體降解途徑。泛素蛋白酶體系統主要是對于短壽命蛋白質的降解,而自噬則優先用于選擇性降解長壽命的蛋白質和損傷的細胞器。自噬是高度保守的分解代謝細胞通路,用于降解基礎水平的蛋白質和細胞器及病理條件下的病原體和蛋白質聚集體〔3〕。本文對自噬過程及其與ALS相關致病蛋白的相互作用進行綜述。
1 自噬概述
自噬的定義為在所有真核生物中保守的分解代謝過程。從調節細胞內的基本代謝功能到各種疾病,如衰老、癌癥、神經退行性疾病和溶酶體病等,自噬已經成為控制人體內穩態的中心調節點〔4〕。自噬的神經保護作用源于其消除諸如α-突觸核蛋白或tau蛋白等致病蛋白的能力。然而,不同的致病蛋白可能影響自噬過程的不同類型和步驟。自噬功能紊亂已在多種疾病中被報道,包括神經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病(PD)、阿爾茨海默病(AD)及ALS等〔5~8〕。自噬是一種有效的神經保護機制,可積極促進致病蛋白清除,但在某些情況下,其會成為這些蛋白質毒性作用的靶點。當致病蛋白直接干擾自噬細胞內維持細胞功能的組成成分時,或當自噬過程受到間接干擾時,這種對自噬系統的毒性可能是導致疾病的主要原因。因此,了解自噬的分子機制及過程對疾病發生發展及治療都有一定作用。根據到溶酶體的物質,自噬途徑在哺乳動物中有3種類型的自噬。在巨自噬中,細胞胞質內底物首先被困在雙膜囊泡(自噬體)中,然后與溶酶體融合,使底物完全降解。參與這一過程的基因和蛋白質被稱為自噬相關基因和自噬相關蛋白〔9,10〕,在伴侶介導的自噬中,蛋白質被胞質中協同作用的伴侶蛋白識別,該伴侶蛋白將底物帶到溶酶體表面,使其在溶酶體表面進行轉運。最后,在微自噬和內質體微自噬中,底物通過溶酶體和內質體膜內陷而內化〔11〕。因此,了解自噬過程及相關蛋白與自噬的關系,有助于通過干預或誘導自噬等手段,緩解疾病發生發展過程,以達到一定的治療目的。
2 ALS中致病蛋白與自噬
ALS中存在多種蛋白異常積聚,如 Cu/Zn超氧化物歧化酶(SOD)1、Tar DNA結合蛋白(TDP)-43、肉瘤融合/脂肪肉瘤轉運蛋白(FUS/TLS)、9號染色體開放閱讀框72編碼蛋白(C9orf72)、囊泡相關蛋白(VAP)B等〔12,13〕。這些相關蛋白的基因突變或蛋白積聚在ALS的發病過程中均參與一定作用。
2.1Cu/Zn SOD1 SOD1基因突變是經典的ALS致病模型。被損害抗氧化功能的SOD1突變可導致超氧化物的毒性積累〔14〕。目前Perera等〔15〕發現在ALS相關的SOD1或TDP-43突變體的運動神經細胞中進行強烈自噬誘導,如對SOD1G93A小鼠施用Rilmenidine(一種抗高血壓劑,與咪唑啉-1受體激動劑可誘導自噬)可上調脊髓中的自噬和線粒體自噬,從而導致可溶性mtSOD1水平降低。同時,Rudnick等〔16〕研究發現在表達突變型SOD1的ALS小鼠模型中,發現運動神經元在疾病進展早期形成含有泛素聚集體的大自噬體。研究者為了研究這種反應是保護性的還是有害的,在小鼠體內通過敲除Atg7(關鍵的自噬基因),即Atg7cKO小鼠,發現敲除后的小鼠表現出神經肌肉連接的結構與功能缺陷。通過將Atg7cKO小鼠與mtSOD1小鼠模型雜交,發現自噬抑制加速了脛前肌早期神經肌肉失神經和后肢震顫的發生。然而,也發現Atg7cKO SOD1G93A雙突變小鼠的壽命延長了。自噬抑制并不能阻止運動神經元細胞的死亡,但它能減輕脊髓神經間質的膠質炎癥,阻斷應激相關轉錄因子c-Jun的激活。因此運動神經元自噬在疾病早期維持神經肌肉的神經支配,但最終以非細胞自主的方式促進疾病的進展〔16〕。
2.2TDP-43 TDP-43是一種核RNA結合蛋白,參與RNA加工的幾個方面,主動在細胞核和細胞質之間穿梭工作〔17,18〕。在ALS與額顳葉癡呆(FTD)中,TDP-43被排除在細胞核之外,但這種細胞質錯誤定位在神經元損傷或應激中很常見〔19,20〕,TDP-43陽性包涵體可能是諸如AD等神經退行性病變的繼發病理特征〔21〕。Barmada等〔22〕開發并驗證了一種單細胞光學方法,發現致病突變可縮短TDP-43的半衰期。刺激自噬可改善TDP-43清除和定位,并可提高攜帶TDP-43突變的小鼠原代神經元、人類干細胞衍生神經元和星形膠質細胞的存活率。其次,該團隊發現TDP-43的水平和定位能決定神經毒性,并表明自噬誘導通過直接作用于TDP-43清除來減輕神經變性〔22〕。Wang等〔23〕研究發現雷帕霉素(一種依賴mTOR的自噬激活劑)在TDP-43陽性泛素化包涵體(UBIs)為特征的FTLD-U小鼠模型的早期病理階段給藥,可挽救學習記憶障礙、腦缺血再灌注損傷及小鼠的運動功能異常,同樣伴隨著caspase-3水平降低和小鼠前額神經元丟失減少。此外,病理后期的自噬激活也能改善運動功能,并伴有TDP-43陽性UBIs的降低。該研究為自噬激活劑治療神經退行性疾病奠定了基礎。
2.3FUS/TLS 有5%~10%ALS病例是家族性的,而SOD1、TDP-43、FUS突變占家族性ALS的30%左右〔24〕。FUS是一種廣泛表達的526氨基酸組成蛋白,由15個外顯子編碼,屬于多功能DNA/RNA結合蛋白的FET/TET家族,最初被發現作為人類癌癥融合癌基因的組成部分〔25,26〕。ALS與核RNA結合蛋白(RBP)的聚集相關,包括FUS。如何在健康的運動神經元中預防FUS聚集和神經變性仍是無法回答的問題。有研究通過使用ALS患者尸檢組織和誘導多功能干細胞衍生神經元的組合來研究FUS突變對RBP穩態的影響,結果顯示FUS的聚集傾向通常通過相互作用的RBP緩解,但當FUS由于ALS突變而錯誤定位于細胞質時,這種緩沖會消失〔27〕。細胞質中存在易聚集的FUS導致RBP穩態失衡,加劇神經變性。然而,使用小分子增強自噬減少細胞質FUS,可恢復RBP穩態并在體內挽救神經細胞運動功能。因此RBP穩態的破壞在FUS-ALS中起關鍵作用,并可通過刺激自噬來治療。
2.4C9orf72 C9orf72中的GGGGCC(G4C2)重復擴增是ALS和FTD常見的遺傳原因〔28,29〕。C9orf72 的核苷酸重復擴增(NRE)導致這些疾病的致病機制包括C9orf72功能的喪失和由NRE編碼的毒性RNA和蛋白質驅動的C9orf72功能機制的獲得。這些機制與在患者和動物模型中觀察到的幾種細胞缺陷(包括核質運輸缺陷和核應激)有關〔30〕。Liu等〔31〕研究發現C9orf72是溶酶體靶向和降解CARM1所必需的,而精氨酸甲基轉移酶(CARM)1是巨自噬/自噬和脂質代謝的重要表觀遺傳調節因子。在C9orf72缺乏的細胞中,包括來自ALS-FTD患者的細胞,CARM1異常積累,特別是在糖剝奪應激下,可導致自噬和脂質代謝失調。這些結果表明,C9orf72是營養應激反應中負反饋調控自噬溶酶體途徑的關鍵調節因子。有研究表明在C9orf72突變的 ALS/ FTD患者中,發現了p62在小腦、海馬和新皮質中積聚,表明自噬受損〔32,33〕。p62與C9orf72相互作用,在C9orf72突變的患者衍生的成纖維細胞中檢測到p62水平升高。此外,在神經元中C9orf72敲低后,自噬受損并且p62和TDP-43在聚集體中累積〔34,35〕。
2.5VAPB VAP蛋白是具有氨基末端主要精子蛋白(MSP)結構域和跨膜結構域的同源蛋白。其中VAPB是一種多功能蛋白,參與內質網至高爾基體之間的蛋白轉運、神經肌肉接頭發育及神經元軸突延伸。其中,VAPB突變可致家族性ALS。Lin等〔36〕、Wu等〔37〕研究表明VAPB的敲除誘導自噬蛋白Beclin1表達上調,促進微管相關蛋白1輕鏈(LC)3轉化和LC3斑片形成,而VAPB的過表達抑制了這些過程。VAPB對Beclin1的調控處于轉錄水平。此外,敲除VAPB可增加自噬通量,并促進自噬底物p62和神經退行性疾病蛋白的降解。Sentürk等〔38〕發現自噬-溶酶體降解需要有如VAPB等引起ALS的蛋白,VAP蛋白的喪失會導致酸度異常的溶酶體積累。其中VAP33突變體顯示出自噬小泡,尤其是自噬溶酶體的大量積累。由于VAP蛋白位于內質網膜、內質網-高爾基體系膜,并直接與脂質轉移蛋白相互作用。這種束縛促進高爾基體向內質網的4-磷脂酰肌醇4-磷酸(PtdIns4P)的轉移,因此,VAP的丟失導致高爾基體中PtdIns4P的積累,從而強烈促進自噬體的產生,這些自噬體沒有被適當地酸化而成為功能性溶酶體,從而損害了自身溶酶體的降解能力。
3 總 結
運動神經元是哺乳動物最極化的細胞,其細胞活性高度依賴于有效的能量供應、軸突小泡長距離逆行運輸及受損細胞器和異常蛋白聚集體的適當清除等的協作。而在導致ALS及其相關疾病如FTD中的近40個遺傳因素中,包含了幾個基因編碼與自噬有關的蛋白質,包括TBK1、泛素結合蛋白(SQSTM)1/p62、視神經蛋白(OPTN)、泛醌蛋白(UBQLN)2、VCP和C9orf72的突變〔39〕。自噬過程無疑是中樞系統調節分解代謝及循環過程的重要機制之一。大量研究已經證明了異常蛋白積聚于神經元細胞的過程,因此,對于自噬的研究也成為治療ALS等相關疾病重要靶點。
目前,針對ALS的自噬研究機制表明,在實驗性ALS背景下,由于干預措施及所采用的動物模型不同,自噬水平的藥理學和遺傳學調節可能導致與小鼠存活和疾病進展不同甚至相反的后果。如利用雷帕霉素或觸發mTOR獨立自噬的藥物(即亞精胺和卡馬西平)治療TDP-43突變小鼠可防止疾病發展〔23,39〕。而在有些研究中表明對突變的SOD1轉基因小鼠施用雷帕霉素會因細胞凋亡增強而加劇疾病進展,或可能根本沒有影響〔40,41〕。通過給予海藻糖(該途徑的mTOR非依賴性誘導物)激活自噬可防止SOD1轉基因小鼠發病〔42~44〕。在運動神經元特異性Atg7條件敲除小鼠(Atg7cKO)中,Atg7的丟失不足以引起這些小鼠的神經變性。然而,運動神經元的靶向自噬導致影響選擇性肌肉連接的自發表型。Atg7cKO小鼠出現了與脛骨前肌早期ALS退化的運動神經元支配的神經肌肉連接形態紊亂相關的電生理改變,這些結果揭示了自噬和蛋白質穩定連接在運動神經元肌肉維持中的生理作用〔16,39〕。同時,已有研究報道了通過使用Atg7單倍體不足小鼠對重要自噬調節因子Becn1/Beclin1基因進行基因消融,盡管會增加蛋白質積聚,但仍能延長ALS小鼠的壽命〔45〕。而另一項研究發現相反的結果,與對照組相比,SOD1G127X和SOD1G93A小鼠的Becn1雜合子,發展出更具攻擊性的表型〔46〕。盡管出現了神經肌肉連接受損,但上述的兩種實驗小鼠均發現比相應單倍體不足小鼠壽命有所延長。在分子水平上發現,Atg7cKO SOD1 G93A小鼠顯示出預期的電生理和肌肉連接改變〔16〕,證實自噬是維持神經肌肉連接完整性的關鍵過程。該研究證明,早期自噬是維持脆弱運動神經元肌肉連接的生理機制。相反,在晚期,運動神經元自噬作為一種有害的機制發揮作用,可能通過細胞非自主機制加速ALS的進展。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與所用動物模型的差異、受試藥物的非特異性、治療開始的疾病進展階段及該途徑在神經元和神經膠質細胞中可能的不同作用有關。提示自噬活性可能影響ALS的進展及靶向通路的特異性效應應該以一種時間和細胞特異性的方式進行更詳細的研究,并盡可能與多種疾病參數進行比較。
綜上,包括SOD1、TDP-43、FUS、C9orf72及VAPB等在內的相關基因及蛋白均在一定程度上與自噬產生相互促進或抑制作用,而ALS中自噬激活與抑制會因疾病不同階段甚至所屬實驗動物的不同而產生不同作用。因此,在某些特定條件下研究促進或抑制自噬或許會減緩疾病進展,對ALS患者是一個較有效的保守治療方案。但目前自噬在ALS中的相關機制尚未完全明了,應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