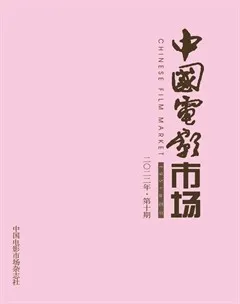主旋律電影的流變與反思
【摘要】主旋律電影承擔著主流價值觀的傳播,在國產電影中占據較大比重。本文將從宏觀上梳理中國香港導演“北上”執導的主旋律電影作品,來分析主旋律電影的創作流變。從題材的選擇到類型的拓展等方面探討主旋律電影流變的成因與時代背景,以及香港導演在從主旋律電影向新主流大片流變中的成功經驗與創作傾向,同時總結香港導演群體北上創作的利弊與得失,以期為主旋律電影的發展提供一些啟示。
【關鍵詞】主旋律電影 香港導演 新主流電影 電影工業化
2003年,《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的簽訂,使中國大陸電影與中國香港電影的合作進入新局面。面對大陸莊重、理性、嚴肅的主旋律電影,中國香港影人從市場、觀眾等方面出發,對主旋律電影進行市場化運作的嘗試。以重大革命歷史題材、英雄人物題材和重大工程建設題材為內容,融入港片中的市場元素,從形式和風格上讓主旋律電影更加豐富與多樣,促進國產電影呈現出商業電影主流化、主旋律電影商業化、主旋律電影藝術化的局面。在創作上沿襲了類型片創作的傳統,結合主流意識形態表達作為影片的特點;在敘事層面將個體人物與家國情懷融合,構建無地域差別的特點,實現了“以國為家”的身份重建和敘事轉變,更加注重主流意識形態和價值導向,將中國香港的人文理念與大陸對接,創作出《湄公河行動》《中國機長》《攀登者》《紅海行動》等一大批口碑與票房并重的作品。
一、創作主題從革命歷史到貼合時代
早期主旋律電影的創作主要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主旋律的時代性,影片創作強調與時俱進,與時代發展的脈絡基本相一致;二是主旋律電影朝著類型化的方向發展。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已存在香港導演北上創作。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香港電影式微,電影票房大幅下滑,電影作品產量逐年減少,加之市面上充斥著粗制濫造的作品以及盜版盛行,香港本土電影市場持續低迷,部分香港導演開始北上尋求出路。合拍片也從最初的內地取景轉向直接創作迎合大陸受眾觀影趣味的影片,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合拍。
隨著CEPA的逐步實施,大批香港導演北上拍片,經過十多年的磨合與探索,《十月圍城》《中國合伙人》《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長津湖》等票房和口碑均有不俗成績的大片,掀起了主旋律電影的熱潮。這些影片在意識形態表達和影像技巧上的創新,有效實現了核心價值觀的正向傳達,香港導演憑借其尊重市場、尊重觀眾的創作傾向,在主旋律電影莊重、嚴肅、理性的特點上,又多了趣味性。工業化制作和類型化的敘事,以及視覺奇觀的嵌入輔之以高投入、重營銷的商業化運作模式,使香港導演執導的多部主旋律電影贏得了票房與口碑。
早期的主旋律電影聚焦于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歷史英雄人物題材、重大工程建設題材進行宏大敘事,專注于對歷史事件、英雄人物的還原。在政策導向和市場的影響下,主旋律電影創作開始把社會現實與觀眾的觀影感受聯系在一起,獻禮片更是把這種聯系推向高潮,如根據湄公河大案改編的電影《湄公河行動》,以及以抗美援朝為背景的電影《金剛川》《長津湖》等,都體現出這種主旋律電影創作的新傾向,并且都取得口碑和票房的雙豐收。又如劉偉強導演的根據川航3U8633事件改編的電影《中國機長》,塑造了從機長到乘務員的英雄群像,一改之前此類電影中聚焦于英雄個體塑造。這些影片在主題選擇上符合中華民族自立自強的現實情緒,在敘事上也著力突出不同人物為實現民族大義而自我犧牲、奮斗不息的行為,激發了觀眾強烈的情感認同和家國情懷,使觀眾在再現的歷史情節中獲得現實認同。
二、敘事視角以受眾為導向
之前許多主旋律電影通常對歷史人物、英雄人物采取謳歌的表達方式,鮮有對人性的探討、對社會深層問題展開討論,也不太考慮市場的因素,沒能與受眾產生積極互動。中國香港導演在研究兩地文化差異和受眾心理后,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將類型元素、電影工業化、娛樂精神、人物理念等運用到主旋律電影的創作中,找到了一種融入大陸電影市場、契合大陸主流院線觀眾的敘事策略。
CEPA的簽訂后,在新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下,中國香港導演一是以小切口展現大主題,通過敘事主體的真情流露來呈現大的主題思想。如陳可辛導演的《中國合伙人》以主人公成東青、孟曉駿和王陽三人的關系走向為主線,從相知、相識到創立“新夢想”最終實現“中國式夢想”的故事,闡釋了一代人在友情、愛情、事業和東西方文化交融下的迷惘,引起大眾的強烈共鳴;二是以英雄人物為題材的主旋律電影,開始轉向平民化的視角,更具類型特征。如徐克導演的《智取威虎山》,將楊子榮智取威虎山的歷史時間嵌入到海歸姜磊回家過年的現代故事中,以現代京劇唱段《打虎上山》與小栓子的手繪本作為兩條敘事明線,小栓子與姜磊的祖孫關系作為暗線在片尾揭曉,明線作為歷史文化、民族精神的展現,暗線展示敘述者的身份,增強文本的可信性與說服力;三是以重大革命歷史為題材的主旋律電影,在保證故事完整性和真實性的基礎上,進行合理化的藝術改編,增加戲劇沖突,在觀眾已知情節中設置懸念。如林超賢導演的《湄公河行動》塑造的方新武形象,在面臨家仇國恨時,方新武展現了英雄人物的“缺陷”面,塑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立體人物形象;劉偉強導演的《建軍大業》,宏觀全景展現建軍歷史,大跨度的時間圍繞“建軍”的主題,講述南昌起義之前,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困難。在傳達主流價值觀的前提下,融合了中國香港電影的類型化元素,年輕態的美學追求和趨于成熟的工業化制作。香港導演的大膽嘗試為主旋律電影創作的拓展提供了新經驗。
被稱為“東方好萊塢”的中國香港電影業,有著成熟的類型電影創作模式與工業化生產經驗。在香港導演北上創作的主旋律電影中,雖然娛樂元素不多,但這種娛樂元素卻為主旋律電影創作提供了更多選擇。如徐克導演的《智取威虎山》中,“老八”的人物形象設置,從人物臺詞到戲劇動作都顯得十分夸張,在觀眾精神緊繃時,“老八”的出場給予觀眾一定的放松;《長津湖》中的“雷爹”,除了承擔“精神支柱”的形象外,還附帶一定的娛樂形象。娛樂精神作為香港導演長期堅持的美學傳統,為主旋律電影的發展提供了創新動力。同時,隨著市場經濟發展,主旋律電影開始重新面對和思考市場問題,更加重視市場因素。
三、從本土文化到多元文化的有效融合
中國香港導演北上之后創作的影片在敘事上體現著香港與內地不同文化的交融。香港導演在不斷磨合與嘗試后能夠將自身的敘事手法與主旋律電影的特點很好地結合,使得主旋律電影在表達方式上更豐富,也使主旋律電影更具市場吸引力,既表達了主流價值,也獲得了觀眾的認可。
(一)中西方文化交融下的類型化敘事
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得香港具有顯著的本土文化特點,隸屬于嶺南地區的香港繼承了粵港地區的市井文化,在香港回歸之前形成了特有的中西方文化交融下的香港文化,即“當代香港文化是中西文化和傳統與現代文化交融的多元混合體,目前以商業性流行文化為主流”[1]。根植于這種文化背景下的香港電影,自然成為香港文化的縮影,也體現出具有香港特色的類型化美學特征。2003年CEPA簽訂之后,伴隨著北上進程,香港導演開始注重中華傳統文化,追隨內地文化的表達訴求,越來越注重體現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對國家情感的認同。
(二)主流價值與時代文化的交融
香港電影特色敘事手法給主旋律電影融入了類型化的元素,主流價值對香港導演創作的影響使我們看到香港導演執導的電影作品中對當下中國主流文化的認同與建構,從早期對以動作功夫片展現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侵略者的個人英雄主義電影,變成了全民族共同對抗外敵的民族英雄。革命歷史題材影片如《建黨偉業》《建國大業》等既再現了歷史,又傳遞出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主流價值觀;聚焦于國際背景下的《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愛國主義大片,既表現了國家保衛公民生命安全的決心,又凸顯了愛國主義情懷,更彰顯了國家自信。這些作品體現出鮮明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英雄主義等主流精神,是主流價值與時代文化交融的典型作品
四、從主旋律電影到新主流電影
主流電影的概念最早由學者馬寧提出:“主流電影理論并不是那種體系嚴密的理論,它實際只是一群年輕導演和策劃人企圖改變現狀和發現中國電影生機而發出的良好愿望。”[2]所謂的“新”必須被主流市場所接受和認可,既要反映主流價值觀,又要完成市場與價值觀的有效融合。學者尹鴻、梁君健認為,“新主流電影就是未來中國的主流電影,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載體,也是國家意志和民眾需求的精神匯聚。”[3]縱觀香港導演北上的創作主要可分為兩類———革命軍事題材和現實題材。筆者對現有的新主流電影進行文本分析,認為香港導演在長期創作中形成的美學觀和電影創作理念影響著新主流電影的風貌。例如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聯合執導的電影《長津湖》,登頂中國電影票房之冠。博納影業于冬認為《長津湖》把中國電影工業推向了新高度,其在繼承主旋律電影傳統的敘事模式基礎上,借鑒了好萊塢類型片的制作經驗與宣發模式,以受眾為基礎的創作導向,滿足了受眾的期待視野。
(一)受眾本位下的工業化產物
明星制是好萊塢電影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經濟和文化的雙重屬性。一方面,明星具有強大的票房號召力;另一方面,明星本身就是一種符號。2009年上映的獻禮片《建國大業》對明星制的運用使電影回歸視覺奇觀本性,滿足了大眾的視覺愉快,明星制的運用打破了青少年群體與歷史題材之間的觀賞障礙和時代隔閡,明星成為能否捕獲年輕受眾的重要因素之一。2011年由劉偉強執導的獻禮片《建黨偉業》精選了一大批與革命先輩們參加革命時的年齡相仿的年輕演員,同時這批年輕演員作為“90后”“00后”的“偶像”,使影片收獲了大量年輕受眾的關注。2021年的電影《金剛川》《長津湖》等都運用明星制使得這些作品成功出圈。從根本上說,明星參演就是一種視覺奇觀,相對比CG制作,作為真人的明星更具可看性。
電影工業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制片人中心制,認為制片人在電影創作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制片人是電影制作中的核心。中國大陸的電影制作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實行“導演中心制”,但是隨著電影產業化的發展,這一制度已經不能勝任市場的需要。于冬在《湄公河行動》上映后接受采訪時表示,在對大陸導演的選擇中發現,對于主旋律電影的拍攝普遍具有“紅頭文件”情結。“制片人中心制”的運用使得于冬選擇了中國香港導演林超賢,事實證明,林超賢執導的《湄公河行動》成為觀眾喜聞樂見的作品,實現了主流價值與商業性、藝術性的統一。
(二)類型加強的本土化實踐
類型片是衡量電影工業是否成熟的標志,類型化也是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中國香港電影有著成熟的電影工業體系,這也使得香港導演具有豐富的類型片拍攝經驗與技法。在進行主旋律電影創作時,出于對市場的考量和對觀眾喜好的尊重,在創作中會挖掘題材中的類型片元素。
以《中國機長》為例,首先在人物塑造方面,打破了以往許多主旋律電影聚焦于熱血英雄人物之上,而是選擇了機長和空服人員這一平民群體,塑造了一群普通人在災難面前恪盡職守的平民英雄形象。《中國機長》對人物形象實現了立體化塑造,把飛機內的工作人員作為一個共同體,從機長到空姐,從地服到指揮人員甚至到整個民航業。因為大家的共同努力,在災難面前各司其職,最終化解了危機。陳旭光、張明浩認為:“該片把中國慣常的“舍生取義”“大公無私”等“求義舍生”式價值觀模式悄悄置換升級成了‘英雄也是普通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共同體價值觀。”[4]在敘事層面,類型化的敘事使得香港電影具有標準的敘事范式,在創作中為充分調動觀眾情緒,趨向于使用“最后一分鐘”的強推動敘事模式,在特定的時間內要完成特定任務,如《紅海行動》特定時間內找出黃餅,《長津湖》特定時間給志愿軍總部運送電臺等這樣扣人心弦的情節,故事張力十足,并引起觀眾強烈共情。香港導演北上在創作上拓展了主旋律電影的類型和題材,也推動了新主流電影的發展,為新主流電影的創新提供更多思路。并從題材選擇、敘事范式、人物形象塑造、電影工業化等多重維度,為新主流電影的創作提供了可行性模式。
五、“港式”主旋律電影的創作得失
“北上”的香港導演執導的主旋律電影體現出以敘事為先、以人為本的核心創作理念,深度挖掘題材內涵并超類型化方向發展,同時以平民化敘事視角和不斷創新的鏡頭語言展開敘述,重視凸顯人物弧光,合理塑造人物性格,以及電影中熟練運用工業化的生產制作模式,這些經驗都值得大陸導演借鑒。
香港導演給主旋律電影創作帶來新氣象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一方面同質化嚴重,主旋律電影在類型化的道路上,并不能如懸疑片、災難片等類型化特點明顯,主旋律電影必須考慮主流價值的影像化表達,在受眾上必須做到老少皆宜等。香港導演執導的主旋律電影在敘事手法上也多有重復,比如,許多影片慣用“最后一分鐘營救”的強推動敘事模式。另一方面中國香港和大陸在文化和審美上存在較大差異,一些人只看到《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長津湖》等影片的成功,卻忽略了《太平輪》等片在口碑和票房均差強人意的情況。部分香港導演過于迎合市場偏好,而從事本身不擅長的宏大敘事,放棄了對小人物命運的關懷,導致其不能更好地發揮創作經驗。
六、總結
2003年CEPA簽訂之后,中國香港導演創作的主旋律電影在不斷的實踐中探索出一條既符合主流文化和價值觀又融合娛樂化和商業化的創作之路,為主旋律電影商業化、商業電影主流化、藝術電影主流化提供了范本。當下,如何讓主旋律電影在國內市場獲得認可的同時走出國門,也是主旋律電影創作者面臨的問題。在積極推進電影工業化、產業化的進程中,電影創作者要樹立全球市場意識,重視商業化營銷和運作,為主旋律電影走出去打下堅實基礎。
注釋
[1]周毅之,從香港文化的發展歷程看香港文化與內地文化的關系[J].廣東社會科學, 1997 (02): 20.
[2]馬寧. 2000年:新主流電影真正的起點[J].當代電影, 2000 (01): 16-18.
[3]尹鴻,梁君健.新主流電影論:主流價值與主流市場的合流[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2018, 40 (07): 82-87.
[4]陳旭光,張明浩.電影工業美學視域下的《中國機長》:災難片的本土化與“新主流”的新拓展[J].電影評介, 2020 (01): 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