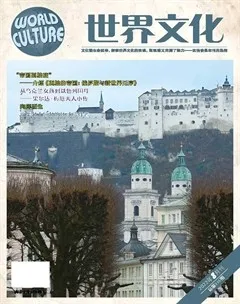最早將紅十字會介紹到中國的人
5月8日是世界紅十字日,這是為紀(jì)念紅十字會創(chuàng)始人亨利·杜南(其生日為5月8日)而設(shè)立。習(xí)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紅十字組織是全世界影響范圍最廣、認(rèn)同程度最高的國際組織;紅十字是一種精神,更是一面旗幟,跨越國界、種族、信仰,引領(lǐng)著世界范圍內(nèi)的人道主義運(yùn)動。目前,紅十字會是與聯(lián)合國、國際奧委會并稱的世界三大國際組織之一。100多年來,紅十字會高舉人道主義旗幟,為保護(hù)人類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類的尊嚴(yán),促進(jìn)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友誼和合作,促進(jìn)人類持久和平做出了卓越的貢獻(xiàn)。
中國紅十字會成立于1904年,是國內(nèi)歷史最悠久的人道組織。對于中國紅十字會的歷史研究,有一定的理論成果,包括中國紅十字總會編著的《中國紅十字會的九十年》,還有近年致力于紅十字會研究的池子華所編《中國紅十字會百年往事》《中國紅十字運(yùn)動史散論》等。然而,是誰最早將紅十字會介紹到中國的呢?相關(guān)著述均語焉不詳。
在中文文獻(xiàn)中,最早使用“紅十字”并提及在瑞士日內(nèi)瓦建立“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一事的是美國傳教士、同文館總教習(xí)丁韙良(1827—1916),他在《西學(xué)考略》光緒七年(1881年)八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寫道:

紅字會救濟(jì)被傷兵丁之事,本由同仁會而出,咸豐九年( 1859年)奧、法相戰(zhàn),有瑞國醫(yī)士杜南者歸自戰(zhàn)場,將目睹情形向會中述之曰:被傷兵丁數(shù)萬,軍營醫(yī)士照料不及,臥地被露所浸以致潰爛而死。會友聞之,莫不感傷,于是議設(shè)另會,專為救濟(jì)被傷之事,以紅十字為記,名為紅字會,轉(zhuǎn)告各國,各遣使會議章程。
(丁韙良《西學(xué)考略》,岳麓書社2016年版)
上文有幾層含義:一、“同仁會”(今譯“日內(nèi)瓦公共福利協(xié)會”)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前身;二、紅十字會創(chuàng)始人是杜南,之所以要創(chuàng)立,是因為杜南親眼見到了奧地利和法國交戰(zhàn)時傷兵的慘狀,因為軍營醫(yī)生少,許多傷兵沒有得到及時救治而死;三、這一國際組織的標(biāo)記是以“紅十字為記”,職責(zé)是救護(hù)傷兵;四、為了使這一設(shè)想落到實(shí)處,他們倡議召開國際性會議,討論章程。“轉(zhuǎn)告各國,各遣使會議章程”可能是指1863年10月26日—29日在日內(nèi)瓦召開的有16個國家的36位代表出席的籌備會議,會議確定了一些基本原則,規(guī)定每個國家成立救護(hù)委員會、開展訓(xùn)練男護(hù)士的工作、救護(hù)車和醫(yī)院中立化,以及采取統(tǒng)一識別的紅十字臂章等,而名稱就確定為“國際紅十字會”。
丁韙良的日記雖然沒有使用“紅十字會”這一名稱,但是用了“紅字會”的名稱,并且指出“以紅十字為記”;還介紹了紅十字會的創(chuàng)始人杜南及成立的由來。只是丁韙良把杜南的職業(yè)搞錯了,杜南并非醫(yī)生,而是一個銀行家的兒子,后來一直忙于紅十字會和其他人道救助事業(yè),乃至貧病交加而死,1901年杜南獲得了首屆諾貝爾和平獎。
丁韙良同一天的日記接著寫道:
同治四年( 1865年)諸國公使會于冉城(今譯日內(nèi)瓦)以定戰(zhàn)時料理病傷士卒之新例,其在事之戰(zhàn)國一體保護(hù),蓋拯命之事決不意存畛域,但知救其病傷而已,即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義(此舉由友人穆尼耶鼓舞而成,故伊現(xiàn)為會中董事),冉城議事宮已泐石而志其事。
(《西學(xué)考略》)
這應(yīng)該是指1864年8月22日(可能丁韙良記憶有誤)在瑞士日內(nèi)瓦召開的國際會議,會上正式簽訂了國際紅十字公約,即《改善戰(zhàn)地陸軍傷者境遇之日內(nèi)瓦公約》,規(guī)定戰(zhàn)場上進(jìn)行救護(hù)的醫(yī)院和人員處中立地位,應(yīng)受到保護(hù);應(yīng)對傷病員不分?jǐn)秤丫o予救護(hù)。這一天,就成為國際紅十字會的誕生日。“此舉由友人穆尼耶鼓舞而成”,是指1862年杜南的《索爾弗利諾回憶錄》出版后在歐洲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反響,在書中他突出描述了戰(zhàn)場上傷員們不可名狀的痛苦,并向世界呼吁:制定一項國際性的法律,以人道主義態(tài)度對待戰(zhàn)俘,保證傷員中立化;在各國成立一個志愿救護(hù)者協(xié)會,召集一批訓(xùn)練有素的醫(yī)護(hù)人士,一旦戰(zhàn)爭爆發(fā),他們自愿開赴前線,不分種族、國籍、宗教信仰和政治信念,救助傷病員,以彌補(bǔ)軍隊中醫(yī)療工作的不足。杜南還建議,立即召開一次國際性會議,討論這個協(xié)會的基本原則。1863年,慈善團(tuán)體“同仁會”創(chuàng)立了一個“五人委員會”,開始研究如何實(shí)現(xiàn)杜南的設(shè)想,穆尼耶(今譯古斯塔夫·穆瓦尼耶,1826—1910)為其中之一。丁韙良贊揚(yáng)穆尼耶“仁愛宅心,以救人為己責(zé),家稱素封而能不辭勞瘁以興義舉,因而諸大國深感其德,獎以寶星焉”。
《西學(xué)考略》有光緒九年(1883年)同文館印本。2016年,筆者在點(diǎn)校整理的《西學(xué)考略》的長篇序論中指出:“這可能是中文文獻(xiàn)中對紅十字會的最早記載。尤其是他指明了紅十字會之成立,與瑞士早已存在的同仁會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值得研究國際組織和慈善機(jī)構(gòu)的學(xué)者們注意。”

丁韙良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xué)者。他在1864年翻譯出版《萬國公法》是國際法正式傳入中國的標(biāo)志,此后他又翻譯出版了《星軺指掌》《公法便覽》《公法會通》《陸地戰(zhàn)役新選》等。他是當(dāng)時在華外國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國通”,中文非常出色,是最早向西方特別是美國介紹中國文學(xué)和文化的學(xué)者之一。其代表作《漢學(xué)菁華——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響力》分為五卷,分別從中國古代的科技、文學(xué)、宗教、哲學(xué)、教育、外交等幾個領(lǐng)域,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進(jìn)行了闡述。1880—1882年,丁韙良利用請假回美國探親機(jī)會,作了一次環(huán)球?qū)W術(shù)考察,遍游日、美、法、德、英、意和瑞士等國,回來后用中文寫就一部《西學(xué)考略》,向總理衙門匯報。其間丁韙良曾在巴黎和倫敦多次見過曾紀(jì)澤并與之深入交談。因此,他最早將紅十字會介紹到中國是順理成章的。
最近研讀晚清第二任駐英法公使曾紀(jì)澤的出使日記《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又有新的發(fā)現(xiàn)。該書中光緒六年(1880年)四月初五日記載:
是日有軍械局送制造圖來觀,末幅繪藍(lán)輿一具,所以舁臨陣受傷之將士者。輿旁繪十字架,蓋以紅布。剪十字之式綴于輿上,舁夫亦剪十字綴于衣襟,則雖經(jīng)歷敵軍不加害焉,此西洋公例也。治傷之醫(yī),自治本國將士,亦治敵軍將士。其醫(yī)亦綴十字于衣襟以為識,雖干戈擾攘之際,可以全身而遠(yuǎn)害。無論何等狡詐之國,皆不肯違背此例。其言曰:將士之臨陣,非其本心也,君與帥之命。殺已傷不足以示武,吾殺敵軍將士之受傷者,敵軍亦將效吾之所為以報怨焉,是吾自戕吾之受傷將士,例敗而受累者多矣。又兩軍相當(dāng),擒獲將士,若被獲者自誓不再預(yù)此次戰(zhàn)事,即可縱之使歸,如其歸而復(fù)求出戰(zhàn),則其本國官長罪而斥之,亦謂其輕敗公例則受累者多也。此西洋之良法美意,風(fēng)氣之未澆者,與清臣談及,書而記之。
(曾紀(jì)澤《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岳麓書社2008年版)
這段話的要點(diǎn)是:一、戰(zhàn)場上救護(hù)傷兵的擔(dān)架(“輿”本指轎子)、醫(yī)護(hù)以及抬擔(dān)架的人都以紅十字為標(biāo)記,敵軍不能加害,“此西洋公例也”,哪怕是最狡詐的國家也不敢違背;二、戰(zhàn)場上的醫(yī)生,不僅治本國的傷兵,也治敵國的傷兵;三、其理念是殺死傷兵不足以顯示自身的威武,何況你殺死對方的傷兵,對方也會報復(fù),這樣就會陷于冤冤相報,等于殘殺我方的受傷將士;四、曾紀(jì)澤高度評價這一做法為“西洋之良法美意”,并與使館翻譯、英國人馬格里談及。曾紀(jì)澤雖然沒有明確提到紅十字會這一組織,但指出了這一組織的獨(dú)特標(biāo)記,并提及其理念,尤其難得的是非常鮮明地表達(dá)了贊同立場。
曾紀(jì)澤是晚清首位通曉英語的著名外交官,出國之前就常讀英文報紙,和京城眾多外國名流有廣泛而深入的交往。出國之后,在英法使館分別聘請了英國人和法國人擔(dān)任翻譯。他與報紙主筆、政要交往頗多,信息渠道通暢。曾紀(jì)澤也非常重視國際公法,認(rèn)為公法對于維護(hù)國際的和平與穩(wěn)定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對于紅十字會理念能夠理解并贊同。他和丁韙良是至交,出國之前因怕攜夫人在外國參加活動不便,還專門寫信向丁韙良請教。《出使英法俄國日記》及曾紀(jì)澤《使西日記》出版多年,點(diǎn)校者在邊批中也提醒讀者這段內(nèi)容是關(guān)于紅十字會的記述,不知為何沒有引起紅十字會研究者的注意。
回頭再說中國紅十字會成立于1904年之事。1904年,正在倫敦的駐英公使張德彝受命補(bǔ)畫紅十字會原約,并將光緒皇帝批準(zhǔn)加入國際紅十字會的敕諭翻譯成法文,親交瑞士駐英公使。張德彝《八述奇》中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月十八日的日記云:

本年三月初十日,外務(wù)部具奏補(bǔ)畫瑞士紅十字會原約,謹(jǐn)擬頒給駐英使臣全權(quán)敕諭,并請批準(zhǔn)保和公會畫押各款一折。奉朱批“依議欽此”。前于十五日奉到敕諭,敬謹(jǐn)譯成法文,并各件備妥,于今午親捧面交瑞士駐英公使,請其轉(zhuǎn)交瑞廷。
光緒皇帝的敕諭原文是:
皇帝敕諭記名副都統(tǒng)出使英國大臣張德彝:朕惟大瑞士國紅十字總會為環(huán)球善舉,實(shí)深嘉許。各國公議保和會內(nèi)紅十字會推廣水戰(zhàn)條約,已派前駐俄使臣楊儒畫押,其陸戰(zhàn)條約,亦應(yīng)一體允認(rèn)。茲特命爾為全權(quán)大臣辦理入會事宜,會商大瑞士國駐英使臣,知照總會,補(bǔ)行畫押。爾其敬謹(jǐn)將事,毋負(fù)委任。特諭。
“保和公會”(或“保和會”)即世界和平會議,1899年5月在荷蘭海牙舉行,清政府派原駐俄公使楊儒赴會。大會于7月29日通過《推廣日來弗原議行之于水戰(zhàn)條約》(即《關(guān)于日內(nèi)瓦公約原則推行于海戰(zhàn)的海牙公約》)。“日來弗原議”是指1864年8月22日通過的《改善戰(zhàn)地陸軍傷者境遇之日內(nèi)瓦公約》,該公約又稱《紅十字公約》,也即上文所說的《陸戰(zhàn)條約》。盡管楊儒在《水戰(zhàn)條約》上畫了押,但還沒有在《陸戰(zhàn)條約》上簽字,必須與瑞士政府進(jìn)行交涉,補(bǔ)行畫押。《東方雜志》1904年第4期《外務(wù)部奏補(bǔ)畫瑞士紅十字會原約謹(jǐn)擬頒給駐英使臣全權(quán)敕諭并請批準(zhǔn)保和公會畫押各款折》說:
現(xiàn)值日俄事亟,戰(zhàn)地居民流難可憫。本年二月十二日,御史夏敦復(fù)奏請查照西例設(shè)紅十字會等語,奉旨外務(wù)部知道欽此……適接瑞士總會來函,以中國應(yīng)補(bǔ)畫陸戰(zhàn)條約為請,臣等以瑞士為未經(jīng)訂約之國,擬由駐英使臣張德彝照會瑞士駐英公使,作為入會之據(jù)。茲據(jù)張德彝電稱瑞士政府以該大臣辦理此事務(wù)須奉有補(bǔ)畫該約之全權(quán)敕諭,方能照辦等語。臣等查中國與各國訂約頒給使臣全權(quán)字樣,歷經(jīng)遵辦在案,此次補(bǔ)畫瑞士紅十字會原約自應(yīng)奏請頒給,以昭慎重,謹(jǐn)擬敕諭一道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伏候命下,臣等即行恭繕,請用御覽,發(fā)交駐英使臣張德彝遵照辦理。

可與張德彝《八述奇》相印證。由上可知,1904年的日俄戰(zhàn)爭,導(dǎo)致清朝加快了加入國際紅十字會的步伐;為慎重起見,授予駐英公使張德彝全權(quán);張德彝是直接和瑞士駐英公使交涉,而并未到瑞士簽字畫押,眾多書刊稱張德彝前往瑞士簽字畫押,不知依據(jù)何在,查詢張德彝此段時間日記,并未有到瑞士的記載;光緒皇帝對于紅十字會的評價是“環(huán)球善舉,實(shí)深嘉許”。
順便說說紅十字會網(wǎng)站,中國香港紅十字會是做得很好的,表現(xiàn)在突出了紅十字會的理念及使命、期盼公眾積極參與以及沒有官方網(wǎng)站那種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網(wǎng)站首頁是“暗處有光,全賴有你”八個醒目的大字,下面闡述了香港紅十字會的理念:“我們力求世上人人都能尊重及保護(hù)人的生命和尊嚴(yán),并能自愿地以一視同仁的態(tài)度施以援手,改善弱勢社群的境況。”并告知公眾如何投身于紅十字會運(yùn)動。在關(guān)于國際紅十字及紅新月運(yùn)動使命中是這樣介紹的:防止和減輕人類在任何地方遭受的痛苦;保護(hù)生命和健康,并確保對人類的尊重,尤其是在武裝沖突和其他緊急情況期間;為預(yù)防疾病和促進(jìn)健康和社會福利而工作;鼓勵該運(yùn)動成員提供志愿服務(wù)并隨時提供幫助,對需要保護(hù)和幫助的人表示一種普遍的團(tuán)結(jié)精神。此外摘錄了紅十字會始創(chuàng)人亨利·杜南(1828—1910)的名言:“永不言棄,坐言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