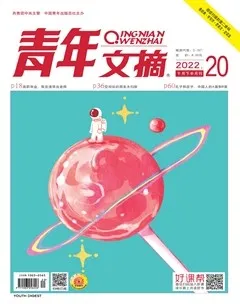孔子和莊子,中國人的A面和B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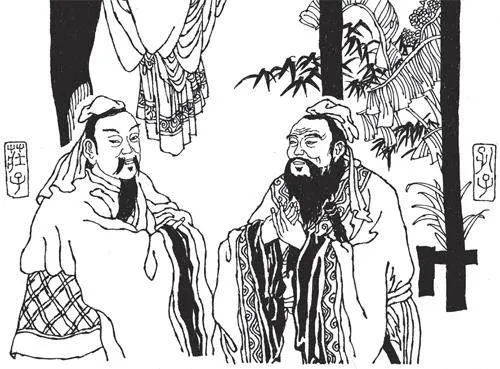
如果從人類人口總數、從影響人類歷史的時間長度來看,孔子、莊子作為思想家,在世界范圍內排名進入前10,沒有一點問題。莊子和老子是道家人物,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人物。儒家講孔孟之道,道家講老莊哲學。
儒家和道家,對中國人的影響有多大?我曾經在《風流去》里寫道:“孔孟之道是朝廷的,老莊哲學是民間的。”在中國古代,孔孟之道也許靠了國家的力量而有后來的地位,科舉考試時,儒家著作是士子應考的必讀書,而莊子,憑的是他個人和一本《莊子》的魅力,靠的是讀書人對莊子的喜愛。
那些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們,桌子上擺著儒家的“四書五經”,你要是去翻翻他們的枕頭底下,大都放著一本道家的《莊子》,那是他們的心靈慰藉。考中的,去治國平天下,做儒家;落榜的,回家做一回化蝶之夢,醒來后,眼前又無處不是四通八達的康莊大道。看上去,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最核心的部分,這沒錯。但翻到道家這一面來看,也許,我們更能夠看明白中國人。道家對中國人的影響,遠超我們的想象。
孟子講過:“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孟子·盡心上》)其中,達則兼濟天下,是儒家思想;而窮則獨善其身,是道家思想。從整體上看,孔子是儒家,這沒有任何問題,他一生弘道,一心要拯救世界,但是看孔子本人的氣質,他更像道家,“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當孔子講這句話時,你說他是儒家還是道家?
子路、冉有、公西華、曾皙侍坐,孔子要四個弟子“各言其志”,來談談各自想怎樣改變世界。這個話題的開始,是儒家的。但最后呢,曾皙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有人把這段意譯如下:“二月過,三月三,穿上新縫的大布衫。大的大,小的小,一同到南河洗個澡。洗罷澡,乘晚涼,回來唱個《山坡羊》。”這是儒家拯救世道、大濟蒼生的生活嗎?不是。是道家那種獨善其身、逍遙自在的生活。曾皙說完了,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本來,孔子作為一個主題討論會的主持人,給出了一個儒家題目。結果,當有道家風范的曾皙說出那句話后,孔子感嘆說,我贊成曾點啊!
孔子最喜歡的學生顏回,骨子里也有道家的氣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孔子對顏回還說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之則行,用我們就去干;舍之則藏,不用我們就去隱居——如此灑脫,如此有堅持但又能隨時放下,是儒家嗎?是,但難道不也是道家嗎?這是很高的境界。孔子說,只有你顏回和我兩個人能做到這樣啊!
關于什么是儒家,什么是道家,林語堂講:譬如小孩打架,拳頭硬的是儒家,拳頭軟的是道家。當你打得過別人時,勇猛精進,是儒家;打不過別人時,退讓一步,并給自己找很多理由,然后以弱勝強,是道家。所以中國人能在儒家和道家之間很容易地實現轉換。有了這種轉換,中國人做事就不會執著于一點。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古代中國讀書人很少有自殺的。而西方讀書人自殺的比例遠遠超過一般人,因為他們遇到形而上的問題解決不了,人生沒有出路了,怎么辦?只好自殺。但中國古代讀書人就很容易給自己找到出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思路很容易就轉換過來了。
今天的中國人,即便沒讀過莊子,身上也有道家精神。舉個例子,你競選班長。寫競選詞的時候,志在必得的時候,你是儒家,儒家勇猛精進。然后,你落選了,心里很難過,但轉念一想,沒選上也沒啥大不了,選上了還浪費我時間耽誤我學習呢。一轉身,你就成了道家,道家不鉆牛角尖。這種思維,就是中國式的。儒道兩家的存在,是我們中國人的福祉,它們讓我們的思想不固執于一端,讓我們的精神享有更多自由。
為什么我們喜歡莊子?因為我們人人有弱點,有內心的脆弱,在痛苦的時候,是莊子給我們安慰,給我們溫暖;為什么我們尊敬孔子?因為我們人人有優點,有內心的勇氣,希望有精進的人生,希望對世界有所貢獻。所以,孔子、莊子,都是中國不可缺少的偉大人物。
其實,不論莊子還是孔孟,他們討論的是同一個問題——作為個體的人自身的尊嚴。區別在于,儒家強調的是一個人的道德屬性,而道家強調的是一個人的自然屬性;儒家強調的是一個人的倫理責任,而道家強調的是一個人的個性自由。若把儒、道結合在一起,我們可以成為怎樣的人呢?既能承擔倫理責任,又能享受個體自由;既有心靈自由,又是有規矩的——是不是有點耳熟?對,正是孔子說的那句,“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從心所欲,是道家的境界;不逾矩,是儒家的境界。兩者結合起來,就是人的主體性的完美的建設。
(本刊原創稿,洪鐘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