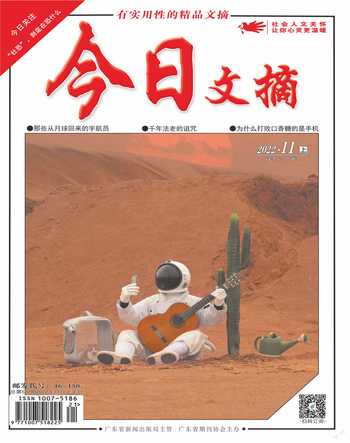他們為何把已故親人制成干尸?


不久前,中國臺灣屏東縣的一起事件讓人感到既震驚又心酸。
2021年12月初,有人報警稱,鄰居一姓葉的老婦人和女兒已經多日沒有露面,擔心她們發生意外,希望警察能派人前來查看。聯系其次子后,警察打開了葉姓婦人的家門,卻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老婦人已于2月去世,現在變成了一具干尸。
這并不是一起兇殺案。原來,82歲的葉婆婆去世后,其50歲的女兒因為不舍,沒為媽媽辦理后事。她將遺體放在躺椅上,每日都精心清潔和擦拭。屏東天氣本就干熱,外加老人體脂率低等因素,遺體竟然慢慢變成了“木乃伊”。
當然,從任何角度講,我們都不提倡將死者做成干尸以對抗喪親之痛,但葉家人確實為大家打開了思路:親人去世后,除了悲傷,我們還可以做些什么讓家人一直陪伴在身邊(比如一些西方人會把已故親人的骨灰做成茶壺)。
葉家女兒的行為雖然令人大跌眼鏡,但并非絕無僅有。在距離臺灣島約3000公里的印度尼西亞南蘇拉威西省塔納托拉查縣,人們死后,都會被家人做成干尸放置在房間一隅,和生者繼續“生活”。
按托拉查人的說法,如果立即將死者火化、填埋,人們一定會感受到無法承受的悲傷。如果做成干尸,那么死者好像只是生病了而已,親人就有更多時間來調節自己的痛苦。
從小就在死人身邊長大
一個塔納托拉查縣的普通午后,90歲的阿爾弗里達·蘭通筆直地躺在“床上”。透過積滿塵土的老花鏡,她凝視著天花板,對前來送午飯的兒子充耳不聞,對圍在身邊的孫輩也視而不見。
沒人會責備其態度冷漠,畢竟,她早在7年前就去世了。沒錯,像在這邊生活過的每個人一樣,阿爾弗里達被家人做成了干尸。
干尸的制作也分“古法”及現代手段,在一篇記載托拉查最后一代國王于2003年去世的文章中,人們可以一瞥傳統的干尸制作方法。
首先,殯葬人會把肥皂切成碎屑,再混以草藥和熱水擦拭死者身體。體內也要消毒,具體方法是用小勺,將三大瓶食醋一點點從死者喉嚨處灌入。清潔完畢,尸體將被長達290米的布料裹成“木乃伊”。
最后一步有些“玄學”。殯葬人通常在存放尸體的房間架起一口黑色石鍋,還特意囑咐任何人都不要觸碰,否則會影響到靈魂,破壞尸體。數天過后,干尸便會成形。從科學角度講,學者認為這口石鍋主要是給制作干尸提供所需的干燥環境。
遺憾的是,隨著最后一位接受過傳統訓練的殯葬人去世,干尸制作“古法”已經基本滅絕。今天,托拉查人會給尸體注射福爾馬林來留住親人。過程確實簡化了不少,但總感覺缺少了點靈魂。
盡管事實上已經死亡,但在當地人眼里,逝者僅僅是病了而已。像阿爾弗里達的兒子梅薩科,每天仍會定時為母親送上一日三餐(放在地上),時不時,他還會坐在棺材邊,同媽媽說說心里話。
“如果母親不住在家里,我們會十分想念她。”年近半百的梅薩科一臉笑容,“她照顧了我們一生,現在我們也必須好好照料她。”
在梅薩科所在的鎮子上,7年的干尸并不算罕見,在他不遠處,就有一位躺了12年的“父親”保羅·西林達。雖然因為年代久遠,保羅的面部已經變成土黃色并泛起一層層類似中式點心的酥皮,但畢竟是家人,每次看望時,他女兒的眼中還是充滿愛意。
更令外人驚異的是,這里的孩童也一點都不畏懼尸體——畢竟,托拉查人從小就在死人身邊長大。
為死而生
對梅薩科們來說,將已故親人的遺體做成干尸并非都源自不舍,更重要的一點是,他們還沒有為舉辦葬禮做好準備。
準備這么久,不是窮,而是由于托拉查式葬禮過于昂貴。要知道,在他們的文化中,死亡可是高于出生、成年和結婚的頭等人生大事。
一場平均規模的托拉查葬禮通常要舉辦3至5天,逝者家屬則應宴請至少5000名賓客以彰顯排面。如何協調這么多人的時間、怎么將數天之長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以及提前準備葬禮上祭祀用的牲畜,每一項都既耗財又費力。
以祭祀用的黑水牛為例,每頭價錢約為7900萬印尼盧比(約合人民幣3.5萬元)。有人的地方就有攀比,為體現家族實力,葬禮上使用水牛的數量也在不斷突破新高。
曾有媒體統計發現,當今一場托拉查葬禮的平均花費大概在2.5億印尼盧比(約合人民幣11.5萬元),這個數字是印尼人均年收入的5倍有余,對于以種植水稻為生的托拉查人來說,無疑是筆天文數字。
由于葬禮過于昂貴,不少塔納托拉查縣的年輕人都選擇到大城市,甚至諸如馬來西亞等鄰國討生活。然而,這些人離開村莊的原因并不是想在外面生根發芽,而是看中了那里可觀的薪水,這樣才好在親人去世之時,奉上一場對得起死亡的葬禮。
正因此,外人總稱托拉查人是“為死而生”。
2008年,在經過長達5年的準備后,托拉查末代國王的葬禮終于成功舉辦。
當時,被宴請到場的嘉賓多達10萬人,祭品包括80頭水牛(至少1頭為稀有品種)和數不清的豬仔。男男女女在葬禮儀式上歌唱跳舞,尖刀劃過一只只豬和牛的喉嚨,土地頃刻間變成紅色。
托拉查歷史上最后一場皇家葬禮,在宏大和震撼中畫下句點。
國王的葬禮尚且籌備了5年,出現10多年的高齡干尸,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死亡經濟
在塔納托拉查縣,死亡是繼農業之后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每家每戶都在為葬禮存錢;祭祀用的牲畜養活了一整條畜牧業鏈條;為逝者制作的木制雕像“tau-tau”,其產業規模也在日益壯大……
由于對外界極具噱頭和吸引力,越來越多的國內外游客慕名前來參觀。在不少村子,酒店、民宿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當地人最終賺起了旅游業的錢。
死亡還是當地財富再平衡的重要調節手段之一。比如,葬禮上祭祀用的牲畜需要繳稅——水牛每頭22萬印尼盧比(約合人民幣101元)、豬每只12萬印尼盧比(約合人民幣57元)。村長會把這筆錢收集起來,再用于修建教堂、道路等公共設施。
可以說,托拉查人不僅是“為死而生”,這一整個民族的社會活動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死”進行的。
和死亡有關的習俗還有很多。
在一些部落,人們每隔幾年就將逝者從墳墓中挖出來,換上嶄新的衣服和墨鏡,然后在村子里游行一圈。嗯,入土不為安,葬禮都不是一個人的終點。
如果有嬰兒不幸夭折,當地人會在樹干上挖出一個洞穴,把尸體放在里面,這樣孩童就可以與樹木“合為一體”,繼續陪在父母身邊。
2017年,出于好奇,BBC記者薩哈爾·贊德帶領攝制組來到了塔納托拉查。
薩哈爾的父親于2014年去世,她和家人只用了兩天就將尸體火化并下葬,雖然已經過去3年,她仍然沒有完全適應父親的離開。借此機會,薩哈爾想從托拉查人的死亡觀中學點什么。
拍攝期間,薩哈爾發現,托拉查人并不是不哀悼家人,他們的痛苦只不過是被看似永無止境的儀式所稀釋了。雖然她不確定自己是否能接受把父親做成干尸放在家中,但也希望擁有一個這樣逐漸適應親人離開的過程。
一次,在參觀完一場“manene”(開棺儀式)后,薩哈爾因為想到了自己的父親而略感悲傷——她有些羨慕托拉查人能與已故的親人重逢。
“你怎么紀念父親?”一位當地老者看到她心情低落而問道。
“我會時不時到墓邊看望他。”薩哈爾回答。
“那你其實也在做‘manene’。”老者一臉慈祥,“你去墓邊是因為還記得他是你父親,你們之間還有情感聯結,不是嗎?你對他的愛永遠也不會消失,這才是‘manene’的真諦。”
(秦巧薦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