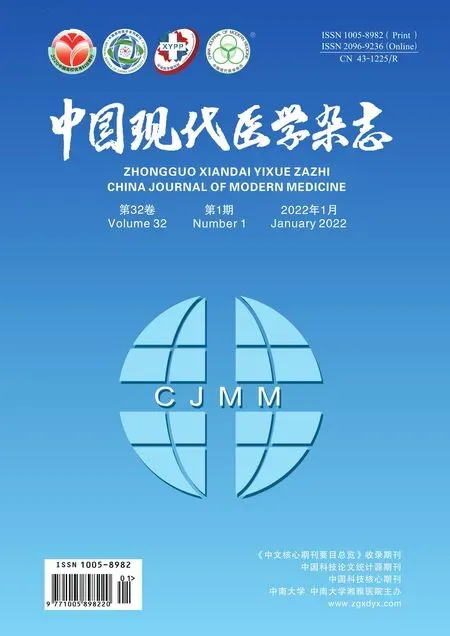帕金森病與炎癥相關的研究進展
趙秀鑫,任惠
(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老年神經內科,云南 昆明650032)
帕金森病是一種進展性的中樞神經系統變性疾病,常見于中老年人[1],目前其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我國的患病率隨著年齡增長而升高[2],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在≥80 歲人群中,帕金森病最高發病為1 663/10 萬[3]。該病呈進行性加重,尚無特效治療方案,患者生活質量顯著下降,給患者、家庭及社會帶來沉重負擔。帕金森病的主要病理特征是黑質多巴胺能神經元變性死亡和腦干神經元內α 突觸核蛋白積聚形成路易體。腦黑質中多巴胺能神經元丟失及紋狀體內多巴胺濃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時,患者出現相應的臨床癥狀[4],主要表現為靜止性震顫、運動遲緩、肌肉強直等運動癥狀。左旋多巴是治療帕金森病的金標準藥物,雖療效顯著,但長期單一使用易出現嚴重的運動波動和運動障礙。近20年來關于帕金森病的研究發現神經炎癥在其疾病進展中有重要作用。臨床發現了帕金森病與一些炎癥相關的生化指標有關,如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 IL)IL-17、IL-12、IL-6,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等。這些生化指標有望作為診斷和提示帕金森病進展和預后的生物標志物。同時,抗炎治療有望成為早期阻止及延緩疾病進程的有效方法。
1 帕金森病炎癥學說的病理依據
當腦內受到刺激時,機體會產生炎癥來進行防御,而該神經炎癥主要是大腦中存在的神經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和小膠質細胞)引起的,并且是帕金森病病理學的共同特征[5]。其中以小膠質細胞過度激活為特征的神經免疫炎癥反應是該過程的一個重要步驟。小膠質細胞主要由間充質中胚層的巨噬細胞生成,根據其所處狀態不同形狀也各異,未被激活的小膠質細胞呈現分支狀,被激活后呈現阿米巴狀。小膠質細胞活化能通過清除過量神經毒素、消除瀕死細胞和細胞碎片修復腦損傷。然而,過度活化的小膠質細胞也會發揮細胞毒性作用,可產生和釋放過多的神經毒性物質(包括自由基和促炎癥細胞因子)最終引起神經元損傷[6]。炎癥可激活小膠質細胞及其他膠質細胞(星形膠質細胞)通過旁分泌途徑來損傷神經元[7],其中有研究支持反應性小膠質細胞增生是帕金森病神經炎癥關鍵步驟的假說[8]。有動物實驗[9]發現帕金森病小鼠模型的黑質致密部小膠質細胞增生、激活明顯活躍,并且發現有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和IL-1β 分泌,而TNF-α和IL-1β 對神經元有攻擊作用,加速了神經元的變性和死亡,說明小膠質細胞增生是導致帕金森病發病的重要環節之一。被激活的小膠質細胞不斷增生與神經元變性可能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在多巴胺能神經元的變性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可能通過抑制小膠質細胞的激活來延緩疾病進展[10]。此外,張永軍等[11]在6-羥基多巴胺誘導的帕金森病小鼠模型中發現黑質紋狀體系統的小膠質細胞被激活后產生大量IL-12 的亞基之一P40(IL-12P40),而使用納洛酮后IL-12P40 減少,其機制可能是抑制了小膠質細胞的激活而減少了IL-12P40的分泌,阻止了神經元的損害,表明納洛酮對于氧化應激和炎癥介導的中樞神經系統的損害有保護作用。而對小膠質細胞激活的靶向治療可能成為帕金森病治療的一個新靶點。
2 帕金森病的外周血炎癥生物標志物
生物標志物是特定疾病的可測指標,用于評估疾病的進展和治療效果,其可以是物理、化學或生物學參數,一般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異性。目前帕金森病經過驗證的生物標志物有:成像生物標志物——分子成像、經顱超聲檢查、磁共振成像和光學相干斷層掃描,生化生物標志物——腦脊髓液或血液中生化生物標志物[膠質纖維酸性蛋白、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神經絲輕鏈蛋白、谷胱甘肽、輔酶Q10、神經黑色素、血漿同型半胱氨酸],炎癥生物標志物,臨床生物標志物等[12-13]。因為帕金森病與神經炎癥相關,本文進一步介紹炎癥生物標志物。
2.1 白細胞計數
白細胞是主要的血液免疫細胞,可釋放促炎細胞因子,同時也被促炎細胞因子激活。目前普遍認為神經炎癥與多巴胺能神經元變性密切相關。帕金森病患病率隨著衰老逐漸增加[2],慢性炎癥狀態是老化過程的主要特征。不僅在腦脊液中,在患者的外周血中促炎細胞因子水平都與帕金森病疾病進展有關。中性粒細胞占總循環白細胞的1/2~2/3,并在炎癥條件下升高。有研究[14]報道外周血白細胞的成分反映帕金森病的一些臨床癥狀,在這些患者中,外周炎癥可能是臨床癥狀發展的主要表現之一。帕金森病患者中NLR 明顯升高[15];MOGHADDAM 等[16]發現NLR 可作為紋狀體多巴胺能喪失的預測指標。NLR 作為帕金森病的炎癥指標,廉價易得,可用于在非運動癥狀早期對疾病篩查及對抗炎治療效果的評估。
2.2 促炎癥細胞因子
帕金森病患者的與炎癥相關的生物標志物水平明顯升高,促炎癥細胞因子可作為帕金森病的檢測指標。在大腦炎癥介質水平改變的帕金森病患者中,神經炎癥與小膠質細胞異常活化有關。QIN 等[17]的研究結果顯示帕金森病患者的外周血IL-6、TNF、IL-1β、IL-2、IL-10 水平升高,這提示帕金森病伴有炎癥反應。另有研究[18]發現帕金森病患者IL-6 和IL-17A 水平與疾病嚴重程度相關,而與疾病持續時間無關,IL-17A 可能與帕金森病非運動癥狀的潛在病理生理有關。因此,帕金森病患者炎癥因子水平較健康者升高,表明其與炎癥息息相關,炎癥因子有望在未來作為帕金森病診斷的生物標志物。
2.3 CRP
CRP 是系統性炎癥的生物標志物,是機體常見的一種急性期反應蛋白,不論是CRP 還是高敏感C反應蛋白(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都可作為炎癥檢測的指標。AKIL 等[15]發現帕金森病患者的hs-CRP 水平升高。一項關于CRP 和帕金森病風險的研究表明帕金森病與CRP 水平升高有關[19],CRP 可能是帕金森病或帕金森病導致炎癥反應的危險因素。并且有研究[20]也發現CRP 的升高與帕金森病患者嚴重的運動癥狀、不良的心理健康和不良的睡眠亞型相關。有研究[21]表明帕金森病患者經免疫測定法檢測hs-CRP 水平與凍結步態有關。另有研究[22]使用永久性雙側頸總動脈結扎的嚙齒動物模型來評估慢性腦灌注不足期間的CRP 表達,發現用IL-1β、IL-6 分別或結合處理小膠質細胞時CRP 的表達增加,這也提示CRP 是體內炎癥水平的一個重要標志物。一項針對帕金森病和血管性帕金森病中國患者的橫斷面研究[23]檢測了患者的同型半胱氨酸和CRP 水平,發現同型半胱氨酸和CRP 在帕金森病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可將同型半胱氨酸和CRP 用于評估帕金森病和血管性帕金森病的進展。另一項橫斷面研究[15]發現帕金森病患者的hs-CRP 水平更高,且帕金森病患者血清hs-CRP、CEA 及NLR 3 者之間呈正相關。一項納入313 例帕金森病患者的回顧性分析探討了CRP 與帕金森病的關系[24],該研究平均觀察了1 753 d,結果發現基線CRP 水平與帕金森病患者的死亡風險和預測生命預后相關。因而,帕金森病患者CRP 水平升高可能與帕金森病持續緩慢發展、多巴胺能神經元受損有關,將CRP 應用于帕金森病疾病發展的監測具有良好的前景。
2.4 CEA
CEA 是正常胚胎組織所產生的成分,出生后逐漸消失,或僅存極微量。當細胞癌變時,此類抗原表達可明顯增多,是一種被廣泛使用的腫瘤標志物,特別是在結腸區域。血清CEA 水平在腸道疾病、衰老、心臟代謝疾病、動脈粥樣硬化及急慢性炎癥中都有所升高。血清CEA 水平可能與炎癥有關,早在1986年NOWAK 等[25]研究發現帕金森病患者血清CEA 升高。近期AKIL 等[15]研究發現帕金森病患者的CEA、hs-CRP 和NLR 水平升高。CEA 可能成為帕金森病新的候選生物標志物,但是,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證實二者之間的關系。
3 抗炎藥物在帕金森病治療中的應用進展
3.1 非甾體抗炎藥
非甾體抗炎藥(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NSAID)是最著名的環氧合酶抑制劑,是由細胞因子或炎癥刺激物誘導的,并在炎癥反應中產生的重要介質。炎癥與帕金森病的發病機制有關,NSAID 在預防和治療帕金森病方面也逐漸引起研究人員的關注。CHEN 等[26]記錄了415 例帕金森病患者定期使用非阿司匹林NSAID,在隨訪過程中發生帕金森病的危險性低于非常規使用者,表明使用NSAID 可能延遲或預防帕金森病發作。然而進一步研究[27-28]并未發現阿司匹林、對乙酰氨基酚或其他NSAID 的使用與帕金森病風險之間存在關聯。而一項納入15 項研究的薈萃分析支持NSAID 的使用及使用的劑量與帕金森病的風險無關[29]。然而,也有學者指出帕金森病的風險可能與NSAID 的種類有關。在帕金森病的炎癥和氧化應激模型中,布洛芬可以顯示出阿司匹林或其他NSAID 沒有的保護特性,布洛芬使用者的帕金森病風險要比非使用者低約30%,這可能和布洛芬可以保護多巴胺能神經元和其他神經元免受谷氨酸毒性有關[30]。布洛芬有神經保護的潛力,但其具有較高的首過代謝,跨血腦屏障的能力有限,難以達到克服和逆轉神經炎癥所必需的血藥濃度,并且口服后有嚴重的胃黏膜損害、腎和心臟毒性,限制了其實用性。有研究[31]提出將布洛芬通過黏膜黏附微乳劑鼻內給藥來發揮其神經保護作用并避免副作用,結果證實布洛芬通過黏膜黏附微乳劑鼻內給藥對1-甲基-4-苯基-1,2,3,6-四氫吡啶誘導的小鼠模型具有神經保護作用,其機制可能是黏膜黏附微乳劑可以增強腦部攝取,還可以保護多巴胺能神經元免受神經炎癥的影響,顯示出較好的神經保護作用。氟比洛芬衍生物HCT1026 是一種NSAID,口服具有安全性。有研究[32]表明HCT1026 在不改變抗炎效果的情況下極大地降低了副作用,在1-甲基-4-苯基-1,2,3,6-四氫吡啶誘導的衰老小鼠模型中,HCT1026 具有對抗多巴胺能神經毒性、運動障礙和小膠質細胞活化的顯著作用。因此,NSAID 劑型的改進、新抗炎藥物的開發可能為帕金森病的治療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3.2 丁苯酞膠囊
丁苯酞是我國自主研制的一類新藥,有效成分提取于芹菜種子,所以又稱為芹菜甲素,對改善急性缺血性腦卒中患者神經功能的缺損十分有效,具有抑制炎癥反應、保護線粒體功能、抑制自由基生成及減少細胞凋亡等功能。近期有學者發現丁苯酞軟膠囊可有效減輕帕金森癡呆患者的炎癥反應,保護神經功能,改善認知功能,且安全性高[33]。劉丹榮等[34]研究發現丁苯酞能明顯改善帕金森癡呆患者的認知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提高臨床治療效果,同時丁苯酞軟膠囊還能降低帕金森癡呆患者血清CRP 水平。丁苯酞治療帕金森病的機制可能是其具有多靶點治療作用,能有效改善線粒體功能,抑制氧自由基生成,保護神經細胞抑制多巴胺釋放從而改善患者神經功能。宋麗倩等[35]研究表明丁苯酞軟膠囊可通過調節病變部位的CRP、重組人帕金森病蛋白7、神經營養因子3 水平從而對神經系統產生保護作用,促進神經損傷恢復,改善患者認知功能。有研究[36]發現在1-甲基4-苯基吡啶離子誘導的大鼠腎上腺嗜鉻細胞瘤12 細胞模型中丁苯酞可以激活自噬,并加快自噬體的聚積,促進突觸核蛋白降解,從而保護腎上腺嗜鉻細胞瘤12 細胞免受神經毒性,且丁苯酞可保護模型大鼠的線粒體功能,并通過抑制氧自由基的產生和阻止線粒體轉換,降低1-甲基4-苯基吡啶離子的細胞毒性并增加細胞內谷胱甘肽的含量,從而減少氧化應激。然而,丁苯酞治療帕金森病的有效性還需要大量臨床和基礎實驗進一步證實。
綜上所述,帕金森病的發生與神經炎癥有關,并將NLR、CRP、CEA 及相關炎癥因子作為帕金森病的炎癥指標,目前抗炎藥物在治療帕金森病方面已取得很大進展,抗炎治療可以延緩慢性疾病的進展,有效改善帕金森病的癥狀,提高帕金森病患者的生活質量,但目前帕金森病神經炎癥的機制、有效治療帕金森病抗炎藥物的開發仍缺乏臨床循證醫學證據,需要進一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