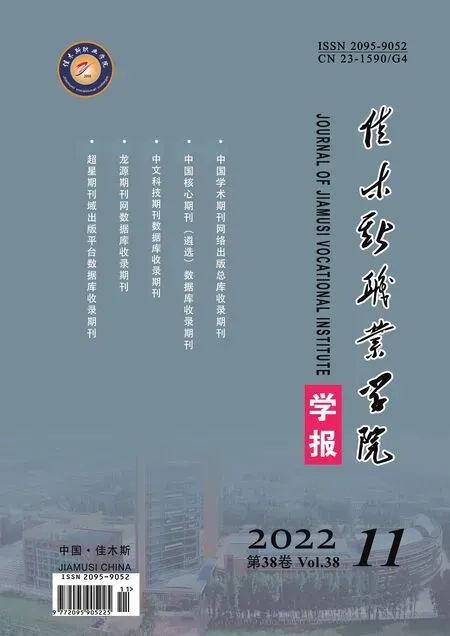未成年人網絡游戲監管制度改良的探討
——基于未成年人游戲現狀的調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修訂
劉安之,李金虎,王依婷
(西南民族大學 法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根據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在京聯合發布的《2020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未成年網民規模達到1.83億,互聯網普及率為94.9%[1]。保障未成年人在網絡游戲領域的合法權益刻不容緩。本文將通過調研分析未成年人網絡游戲目前的情況,并結合現行法律提出對未成年人網絡游戲監管制度的改良建議。
一、法律規制的必要性
(一)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新增網絡保護章節,要求各大主體在實踐中建立行之有效的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絡的制度。未成年人網絡游戲防沉迷制度是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的重要制度。網絡游戲作為網絡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網絡游戲防沉迷制度的建立對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有著積極意義。
(二)理論依據
根據飛利浦·津巴多的環境—人性交互作用模型理論,環境對人的行為具有重要影響。環境好會使人積極向善,環境差會啟動人性之惡。簡而言之,人的行為會和所處環境的性質趨于一致。未成年人網絡游戲防沉迷制度,是通過技術手段對未成年人的網絡游戲時長進行控制的制度。通過技術手段控制未成年人的網絡游戲時長可以給未成年人提供不易沉迷的網絡游戲服務,從而達到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的目的[2]。
(三)現實依據
未成年人群體的心智不夠成熟,辨別是非的能力較弱,三觀仍在塑造時期,更容易受到不良風氣與不良信息的影響。為保障未成年人在網絡游戲領域的合法權益,國家頒布了多部相關政策性文件。通過在國務院官方網站、中國政府網等網站上閱讀并分析這些網絡游戲監管政策,可發現以下幾點缺陷:一是網絡游戲領域未成年人保護的權力責任主體不明確。二是該領域政策缺乏頂層設計。三是該領域政策制定過程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四是該領域政策多為通知類、呼吁類文件,缺少明確的實踐指導性政策,對受約束主體的規制作用較弱。
二、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機制建設情況
(一)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概述
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是中國相關部門提出的旨在解決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的一種技術手段,形式是使用技術手段對未成年人的網絡游戲時間進行控制。2021年8月30日,國家新聞出版署印發《關于進一步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所有網絡游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節假日每日20時至21時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時網絡游戲服務[3],其他時間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游戲服務。《通知》對網絡游戲企業對未成年人提供網絡游戲服務的時間、登錄模式、付費服務等進行了細致規定。為了給未成年人提供符合《未成年人保護法》網絡保護新章節與《通知》規定的網絡游戲服務,網絡游戲企業與網信部門聯動,通過技術手段對未成年人的網游時長等進行了控制。
(二)網信部門與網絡游戲企業聯動建立的防沉迷系統主要手段
《通知》頒布后,在網信部門和國家新聞出版署等相關機關的推動下,2021年5月31日之前,所有游戲企業需要將所有在運營游戲接入國家新聞出版署網絡游戲防沉迷實名驗證系統[4],6月1日還未完成的游戲則需要停止運用。這套防沉迷系統的核心技術手段是要求所有網絡游戲玩家實名制登錄游戲。實名制認證的開啟可以有效辨別出未成年人玩家,便于網信部門、網絡游戲企業對未成年人網絡游戲進行全方面規制。網絡游戲企業較多采取強制下線的方法控制未成年人游戲時長。
目前,相關部門仍未建立統一的未成年人網絡游戲服務標準,對未成年人網絡游戲時長、時間段、內容、充值服務限額等未作出統一的規定。各家網絡游戲企業所具體執行的技術措施也有所不同。
三、未成年人網絡游戲情況及問題
筆者通過發布問卷調查的方式調查了未成年人游戲時長、自控力、充值等情況,在此筆者事先提出以下假設。假設1:未成年人游戲頻次隨著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而有所減少。未成年人游戲頻次的減少與政策的嚴格性成正相關。假設2:游戲公司對未成年人網絡游戲的監管強度隨著政策的出臺而增強。
對調查得到的數據進行分析,從而得出一些未成年人網絡游戲的現狀。
據《通知》《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關于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加強通知》)出臺后筆者對未成年人游戲情況所做的統計,未成年人將網絡游戲作為娛樂休閑方式的情況依舊十分普遍,可見《通知》并未對未成年人進行網絡游戲起到足夠的效果,可見假設1是偽命題。按照假設1背后的邏輯,隨著政策的出臺和加強,未成年人網絡游戲的頻率應當有明顯下降,但是根據兩次數據的對比,從不進行和偶爾進行網絡游戲的未成年人占比有所下降,而一般、偶爾、經常、沉迷網絡游戲的未成年人占比有所上升。對假設1的證偽看似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隨著相關措施的出臺和治理的加強,未成年人的叛逆心理反而受到刺激,促使其進行網絡游戲,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國目前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并不能取得成效的關鍵性因素。
《加強通知》發布后,未成年人登錄網絡游戲的時段主要集中在周末和節假日,平均每周游戲時長大多不超過3小時,但同時還存在27.54%的未成年人通過各種途徑幾乎每天都登錄網絡游戲。結合調查得出的數據可知,未成年人大多需要遵循學校的日常作息規律以及家庭作業的控制因素,在《通知》等沒有頒布前其主要游戲時間就分布于周末和節假日,因其參加的興趣班和家長的監督,能留給自己支配的時間本就不多,用于網絡游戲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與三小時大致相符。
據問卷數據反饋,超過九成的受訪者不認為未成年人對網絡游戲具有自控力。調查人群存在家長與未成年人兩種身份,其中32.63%的受訪者認為針對網絡游戲未成年人或多或少有自控力的數據大多來自未成年人群體,幾乎全部家長都認為未成年人對網絡游戲沒有自控力,需要家長提醒等外界方式進行有效他控。這一現象是符合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這一特性的,而家長處于監護人這一特殊身份毫無疑問應當承擔他控的職責,但完全依賴家長這一力量來對抗紛繁的游戲其效率顯然微乎其微。當家長破壞他控與家庭和睦的平衡時,網絡游戲帶來的傷害會被放大,從而突破文首提到的全部法律法規的法益保護范圍。因此,讓更多主體發揮作用,推動全面建立未成年人網絡游戲防沉迷制度,一方面能改善未成年人的成長生態,將《未成年人保護法》拉入人們的視野,另一方面也能建立《未成年人保護法》與其他法律體系的聯系,從而為和諧社會的建設搭建更為科學合理的路徑。
通過對目前主流的幾家游戲公司最新的針對未成年人用戶的監督策略分析可知,大多采取了實名制審核、面部識別等方式對用戶進行識別。若識別為未成年人則將會對其游戲時間進行嚴格控制,時間累計到達政策規定的標準時,將采取停止提供游戲服務的方式強制未成年人停止游戲,即假設2成立。但假設2與筆者剛剛得出的結論似乎存在著某種矛盾之處。為什么相關政策變得更為嚴格,游戲公司也確實落實了相關要求,而該項政策卻未能奏效?通過走訪調查,筆者證實了上文的結論,發現未成年人存在架空監管的情況。目前大多數識別方法是通過使用者提供的真實姓名及身份證號來驗證用戶年齡,這一做法給心智成熟的未成年人提供了極大的“作弊”空間。其僅需要獲悉成年監護人或近親屬的身份證號即可完成驗證。部分公司采取了另一種較為嚴格的識別方法——面部識別。已有的新聞大量報道了未成年人通過欺騙成年人完成面部識別的案例。人臉識別技術的發達也給未成年人提供了便利,僅僅是成年人的一瞥便可以幫助其完成驗證。
四、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建議及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的未來展望
(一)明確現有制度的漏洞
第一,著力改善未成年人成長環境。此時以立法的視角和改善未成年人網絡游戲情況的目的,筆者認為應當從兩個維度來審視未成年人,從而更清楚地認識到未成年人在網絡游戲時遇到的問題。首先,應當拋棄成年人的偏見,重新認識新時代下的未成年人。如今的未成年人心智成熟的時間已經提前,并且所屬環境的互聯網普及度越高,該地未成年人心智成熟的速度可能就越快,依然單純地用年齡來衡量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可能已經受到了新的挑戰。這背后的邏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十八條第二款承認了以自己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十六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具有完備的民事行為能力相同。其次,雖然筆者通過調查結果否認了在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中叛逆心理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認,在缺乏社會經歷的前提下,未成年人僅通過網絡所形成的人生觀、價值觀是不完善的,面對突如其來與之認識不符的嚴厲政策,難免會采取極端的“報復”方法。因此針對未成年人的問題,既要像成年人一樣去審視,也要像未成年人一樣去引導和保護。在真正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環境和認知邏輯之后,所做的探索才是有意義的。
第二,適當給予未成年人可支配財產(對于有可支配財產的未成年人適當增加按時給予的財產),或由父母提供、安排一些娛樂方式[5]。除了上文提到的疲憊感,未成年人還面對的一大現實問題就是經濟情況一般不如成年人,而選擇其他的休閑娛樂方式,無疑會帶來較大的經濟支出。若獲得放松的結果確定,如果能夠降低獲取結果的條件,無疑更吸引未成年人的注意,這一點同樣也適用于大學生,甚至是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的情況。
(二)明確核心責任機關
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是《未成年人保護法》實踐化的一大重要成果,系統作用的最大化發揮需要學校、家庭、社會、政府、司法和網絡服務提供者六大主體的聯動作用,系統的進一步優化同樣需要六大主體相互配合,需要從立法上確立核心責任主體所在。從原則上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6],國家親權原則得到了長足體現。在國家親權原則的指導下,核心責任主體應當為國家行政機關,即政府主體。從實際應用上看,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的進一步優化需要核心責任主體具備調度其他五大主體相互配合、通力合作的能力,政府主體同樣為最佳選項。確定具體承擔實踐職能的機構,則需要結合實際需要,不同職能的政府機構分別承擔適合本單位職能的實踐任務。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優化的核心責任機關則需要由具有一定技術實力的網絡監管部門承擔。
(三)統一未成年人網絡游戲服務標準
未成年人在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的作用下,游戲時長與游戲時間段受到了嚴格統一的控制。在此之外,各大網絡游戲服務提供者對充值機制、實名制登錄核查等機制沒有適用統一的標準。以實名制登錄核查機制為例,有的網絡游戲企業每次登錄都需要未成年人進行人臉識別,從而避免未成年人通過找成年人代驗證的方式鉆制度的漏洞,獲得更多網絡游戲時長;有的網絡游戲企業則只在初次登錄游戲時需要未成年人進行實名制認證和人臉識別;有的網絡游戲企業甚至并沒有人臉識別系統。
不統一的模糊標準會導致未成年人在接受不同網絡游戲提供者提供的游戲產品時受到的限制程度不同。統一未成年人網絡游戲服務標準,有利于拓寬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的作用邊界,避免未成年人利用系統的漏洞。
五、結語
對現階段未成年人網絡游戲監管制度來說,相關主體需要認識未成年人規避監管的問題。在探索新的治理辦法之前,要看到已有的規制辦法與實際未成年人行為能力狀況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解決這一問題則應當以兩個維度的目光審視互聯網背景下未成年人的真正成熟情況,結合具體的認識情況,發揮家庭在未成年人教育、成長過程中的優勢。對現有的網絡游戲防沉迷制度來說,要進一步提高制度的執行效率,需要相關政府技術部門和網絡游戲服務提供者加強聯動,明確核心責任機關,確定實踐執行流程,完善、細化法律法規對未成年人網絡游戲服務的具體標準。如果政府是未成年人網絡保護中的右手,那么家庭則相當于左手,當雙手共同發揮作用時,可以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健康的網絡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