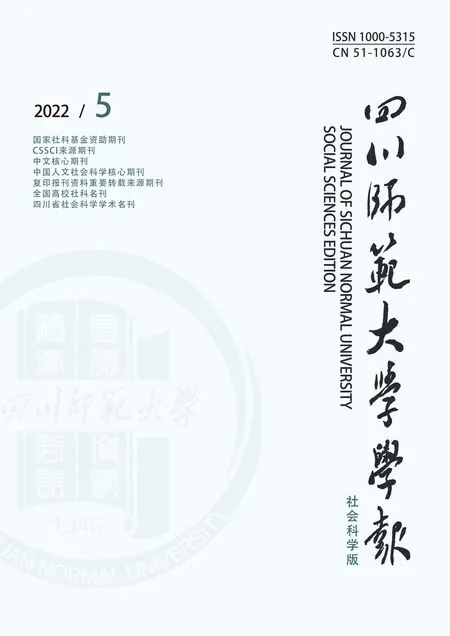四川財政整理與蔣介石、孔祥熙之爭(1934-1935)
蘇騰飛
近代分稅制下,財事權的分配,一直是財稅改革所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近代中央政府集權的重要手段。南京國民政府四次財政改革均以央地財事權的重新分配為基礎,以此調和央地矛盾;而地方整合亦是南京國民政府加強集權的重要一環(huán),除采取軍事途徑外,另有財權讓渡、金融滲透等方式。一定條件下,整合地方與強化財權成為近代國家實現(xiàn)集權過程中的二面一體的矛盾,二者往往顧此失彼。抗戰(zhàn)前夕的川省財政整理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抗戰(zhàn)前夕,民族危機加深,四川戰(zhàn)略地位凸顯,“川劉”成為擁蔣與反蔣集團拉攏的對象,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國民黨中央整理川省財政的價碼,不僅為中央財權與地方政權的互換提供了條件,也為蔣介石和孔祥熙的矛盾升級打開了空間。國民黨中央如何通過讓渡財權實現(xiàn)地方整合?蔣、孔雙方又如何在博弈中維持合作關系?分析回答這兩個問題,不僅能夠透視南京國民政府在中央財權與地方政權上的轉換機制,同時也能把握蔣、孔之間的合作限度以及抗戰(zhàn)前夕國民黨高層的政治生態(tài)走向。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學界關于近代央地財事權分配方面的研究表明,晚近以來,中央財權出現(xiàn)形式上的下移,并與近代分稅制實踐相契合;就民國時期分稅制的實踐目的而言,名為分權,實則集權,宏觀層面上的研究基本理清了近代中央政府加強財權、整合地方的脈絡(1)參見:魏光奇《清代后期中央集權財政體制的瓦解》,《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07-230頁;陳鋒《清代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調整》,《歷史研究》1997年第5期,第100-114頁;鄒進文《民國財政思想史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72-74頁;《北洋財稅制度研究》課題組《北洋時期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研究》,《財政研究》1996年第8期,第59-63頁;杜恂誠《民國時期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第184-195頁;張連紅《整合與互動:民國時期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研究(1927-1937)》,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174頁;焦建華《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集權與分權:南京國民政府分稅制改革再探討(1927-1936)》,《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15年第2期,第67-72頁;潘國旗《從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看國民政府時期的地方公債》,《歷史研究》2016年第3期,第113-132頁;柯偉明《民國時期稅收制度的嬗變》,《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1期,第149-170頁。。在四川財政整理研究方面,黃天華、方勇、石濤等學者的研究表明,蔣介石在實現(xiàn)四川地方財政整理和川政統(tǒng)一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2)黃天華《蔣介石與川政統(tǒng)一》,《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第128-135頁;方勇《蔣介石與四川財政之整理》,《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2期,第113-120頁;石濤《抗戰(zhàn)前南京國民政府對四川幣制的統(tǒng)一:以整理地鈔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4-127頁。。以上研究均側重于央地財政關系,缺乏對國民黨高層對地方整合的不同態(tài)度的關注。有鑒于此,本文擬以整理四川財政期間蔣孔往來密電、《蔣介石日記》、報刊等史料為基礎,以蔣孔分歧為主要線索,討論國民黨中央如何在整合地方和加強財權之間尋找平衡。
一 分歧源起:“四川之錢能否用于四川”
1933年8月,二劉大戰(zhàn)結束后,劉文輝敗退川西,蔣介石有意輔助劉湘統(tǒng)一全川,意圖將成都建設成為國防中心(3)《蔣介石日記》,1933年8月26日、9月7日。。自1934年起,蔣介石更加重視四川的整合,將“川劉問題”與華北問題、粵桂問題、西南軍事問題置于同框(4)1934年的《蔣介石日記》反復將四川問題與倭俄、魯晉、粵桂湘問題放在同一層面考量。參見:《蔣介石日記》,1934年5月10、12、14、15、16、17、19、21、23、24、29日,6月4日,8月10、12、26、27、28、29日等。,并認為安定四川是應對粵桂問題和華北局勢的先決條件(5)《蔣介石日記》,1934年11月23日。。此時,劉湘所屬二十一軍正面臨深刻的財政危機(6)在長期的防區(qū)混戰(zhàn)中,二十一軍形成了以發(fā)債和借墊為主的籌款方式。為應對開支,在準備金不足的前提下,大發(fā)紙鈔,造成地鈔貶值;而債券和地鈔充斥市面,又導致銀行擠兌和金融風潮,四川金融搖搖欲墜。同時,川軍對紅軍的作戰(zhàn),耗費了大量錢糧,進一步加劇了二十一軍的財政危機。據(jù)調查,自1932年蕭克、賀龍所部進入川境始,到1934年10月止,川軍各部圍剿紅軍所耗軍費達到8000萬元以上,大體相當于二十一軍兩年的財政收入。參見:《四川剿匪聲中之財政》,《四川經(jīng)濟月刊》1934年第2卷第5期,第2頁。。為緩解危機,劉湘求助于國民黨中央。1934年3月,劉湘派二十一軍財政處長劉航琛拜謁蔣介石,面陳四川財政狀況,表明了愿意服從中央的意愿,希望中央撥發(fā)川中“剿赤”軍費和善后建設經(jīng)費,蔣隨即表示同意(7)《蔣中正在南昌行營紀念周訓話題為新生活運動之解釋又電何應欽黃郛等剿匪情報另電汪兆銘四川劉湘派劉航琛到贛面陳擬請在中央川省稅收項下酌為指撥基金俾由川發(fā)行公債以濟急需請與相晤妥洽辦法等》(1934年3月26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文物圖書/稿本(一),典藏號:002-060100-00079-008。。9月,蔣介石以劉湘“剿共”失利為由,電令何應欽派胡宗南入川“剿共”,但遭川軍各部的反對,軍事入川就此作罷(8)《蔣中正電何應欽指示川軍劉湘部失利擬請胡宗南入川援助剿匪事因川軍內部意見分歧加上贛亂未定須詳加考慮但可于宜昌鄂北間置部隊以作準備·貴州主席王家烈率部堵剿蕭克股匪》(1934年9月1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文物圖書/稿本(一),典藏號:002-060100-00086-013。。此后,蔣介石逐漸形成依靠劉湘整合四川的既定策略(9)據(jù)劉湘駐北平代表華覺明稱,1934年10月,蔣介石、何應欽等在洛陽商議“川事非倚畀甫公(劉湘)不可”。參見:《華覺明電郭昌明蔣中正何應欽蒞洛似系別有所商對川事非倚劉湘不可》(1934年10月13日),臺北“國史館”藏: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及錄存,典藏號:116-010108-0288-053。。而劉湘方面也積極造勢,召集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等川軍將領召開“剿匪”會議,確立自己的權威(10)《錢大鈞電蔣中正據(jù)葉維電稱四川剿匪會議鄧錫侯等提出統(tǒng)一服從劉湘由其負責統(tǒng)籌撥派餉械及建請中央令陜鄂湘黔會剿赤匪并組織參謀團等案》(1934年10月19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187-093。,后又拉攏楊森,統(tǒng)一川軍各部意見(11)《戴笠電蔣中正成都剿匪會議因楊森未到迄未舉行經(jīng)劉湘派盧作孚往邀楊并派張表方游說各軍將領現(xiàn)將領意見漸趨一致等文電日報表等三則》(1934年10月19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42-162。,川省各路將領遂逐漸形成了由劉湘統(tǒng)一四川軍事財政的主張(12)《賀國光電蔣中正據(jù)王薌庭電稱成都各路總指揮會議結果由劉湘統(tǒng)一軍事財政及其提出精選部隊事宜等》(1934年10月2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188-031。。
國民黨勢力入川前后,中央各派在對如何圍剿紅軍、以何種方式統(tǒng)一全川等問題上各有主張。錢大鈞、丁錦(行營審核處主任)、劉峙等將領,或主張率中央軍直接入川“剿共”,或主張調離劉湘,由中央主川;張群、楊永泰、李仲公等親川勢力,主張利用劉湘,整合川軍各部,圍剿紅軍,實現(xiàn)四川統(tǒng)一;孔祥熙、牟鈞德(財政部視察員)等財政部勢力認為應派財政專員入川,控制四川財政,分化川軍各派,使各部川軍漸趨中央領導(13)分別參見:臺北“國史館”收藏的“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檔案/特交檔案/一般資料”:《錢大鈞電蔣中正據(jù)葉維電稱四川剿匪會議鄧錫侯等提出統(tǒng)一服從劉湘由其負責統(tǒng)籌撥派餉械及建請中央令陜鄂湘黔會剿赤匪并組織參謀團等案》(1934年10月19日),典藏號:002-080200-00187-093;《丁錦呈蔣中正勿予劉湘餉彈援助并飭秦隴豫楚等中央軍協(xié)剿川匪等川局意見》(1934年11月19日),典藏號:002-080200-00193-015;《劉峙電蔣中正補述川省剿匪計畫可調離劉湘由中央軍入川鄂北陜南湘黔邊境諸軍則防匪勢蔓延》(1934年11月19日),典藏號:002-080200-00193-041;《李仲公電毛慶祥轉呈蔣中正請于重慶設置行營并以劉湘為參謀長以為統(tǒng)治川黔初步》(1934年11月16日),典藏號:002-080200-00192-042;《張群電蔣中正經(jīng)分別與劉湘張必果鄧漢祥商定擴大三省剿匪總部組織與改組四川省府等辦法》(1934年11月18日),典藏號:002-080200-00193-008;《孔祥熙函蔣中正據(jù)財政部視察員牟鈞德電稱川局須先簡任廉干大員入川整頓財政后軍權即可統(tǒng)一》(1934年11月28日),典藏號:002-080200-00194-088。。在權衡華北形勢與西南政局,尤其是胡宗南軍事入川失敗后,蔣介石確立了“對川收回財政而不收回軍政”的方針(14)《蔣介石日記》,1934年11月20日。,開始倚重劉湘,重組四川省府,整理四川財政。但在以何種方式整理川省財政、中央與四川的財權應如何分配等問題上,蔣介石與孔祥熙卻存有分歧。
首先,在整理四川財政金融的途徑上,蔣介石與劉湘合議發(fā)行國債,以換回四川舊債和地鈔,但孔祥熙竭力反對。1934年11月19日,劉湘入京,與蔣介石、汪精衛(wèi)、孔祥熙等人商議重組四川省府、整理四川財政事宜(15)《劉湘入京與整理川政》,《大公報》(天津)1934年11月19日,第2版。。在京期間,劉湘與孔祥熙的兩次面商并不順暢。劉湘呈請財政部,希望由四川省府發(fā)行7000萬元公債,以緩解四川財政危機,孔祥熙則以“擔保品一時難覓,發(fā)行巨額公債,實難銷售”為由,拒絕劉湘所請;后劉湘又提出以“川鹽收入”作公債發(fā)行基金,財政部則以“關(鹽)稅用度,已列入國庫為一般的開支,不能專供川省公債擔保”為由,拒絕發(fā)行公債(16)《劉湘訪孔祥熙 續(xù)商川省財政》,《申報》1934年11月29日,第3版。。直至賀國光率領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入川參謀團入川前,財政部與四川省府就如何整理四川財政、如何籌集軍費等問題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但是,劉湘與蔣介石的商談卻極其順利。蔣介石支持劉湘關于“地方債額由中央擔保發(fā)公債數(shù)千萬元,并派中央分行入川救濟金融”的財政整理方案;對此,劉湘十分中意,稱:“此財政最后決定,于我原來希望可謂圓滿無缺,可知此次蔣公必令邊遠將領滿意而去,以圖共負責任也。”(17)《劉湘電郭昌明昨午前謁蔣中正談財政舉兩個方式其一為徹底中央管理》(1934年12月11日),臺北“國史館”藏: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及錄存,典藏號:116-010108-0859-047。1935年1月,在未經(jīng)財政部同意的情況下,劉湘以四川督辦公署的名義,以川省鹽稅和田賦為還本付息基金,發(fā)行1.2億元整理金融公債,換回二十一軍舊債(18)《督署發(fā)行整理四川金融公債》,《四川經(jīng)濟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第175-179頁。。
第二,在“剿共”軍費問題上,蔣介石贊成以國稅作為川軍“剿共”經(jīng)費,孔祥熙則建議以四川省稅充當作戰(zhàn)經(jīng)費。入京期間,劉湘與蔣介石初步達成以川省國稅為“剿共”經(jīng)費的共識,但孔祥熙對此反應強烈。1935年1月22日,孔祥熙向蔣轉達了財政特派員陳紹媯關于“以四川地方稅作為剿匪費用”的建議。陳認為,川省國稅難以應付浩繁的軍費,應由中央統(tǒng)籌辦理川省國地稅收,以調劑軍費開支;所有征收人員由財政部委任,特派員公署試用,川省國地稅款盡數(shù)上繳國庫(19)《孔祥熙電蔣中正轉陳四川財政特派員陳紹媯建議以地方稅撥作軍費應付剿匪并與劉航琛暫管國地兩稅統(tǒng)籌事宜等整理川省財政辦法》(1935年1月2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202-052。。陳紹媯名為財政特派員,實為孔祥熙的駐川私人代表,其建言亦為孔祥熙所授意(20)據(jù)陳紹媯在鹽務稽核所的同事陳況仲稱,陳為宋子文母親的干兒子,與孔宋關系頗深,是孔宋親信。見:陳況仲《鹽務稽核所紀略》,政協(xié)四川省自貢市委員會《自貢文史資料選輯》編輯委員會編《自貢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1984年版,第98-99頁。。該項籌集軍費辦法,立刻招致劉湘的反對。劉稱四川“匪患”未滅,以全省稅收供給軍費,則債務無以為償,市面崩潰,牽動前方軍事(21)《孔祥熙電蔣中正轉陳四川財政特派員陳紹媯建議以地方稅撥作軍費應付剿匪并與劉航琛暫管國地兩稅統(tǒng)籌事宜等整理川省財政辦法》(1935年1月2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202-052。。為督促劉湘“剿共”,蔣介石同意由中央籌集“剿共”軍費(22)“剿共”軍費稱為作戰(zhàn)費,與川軍各部經(jīng)常軍費不同,參謀團入川后,川軍作戰(zhàn)經(jīng)費主要通過賀國光向中央索要。。
第三,在財政整理主導權問題上,孔祥熙并不熱衷于四川財政的整理,這與蔣介石“財政入川”的策略相悖。1934年11月,孔祥熙派財政視察員牟鈞德入川考察。據(jù)牟陳報,四川軍閥“實無一人堪勝全川之任,茲已勢窮力蹙,乃思假中央之力,謀個人卷土重振之圖”,建議中央可簡任財政專員入川整飭四川財政,愿服從中央者“點名發(fā)餉,簡留精銳……補充餉械”,另簡派重兵扼守夔萬酉秀一帶,嚴防“共軍”出川外竄,迫使川軍“剿共”;孔祥熙轉陳蔣介石電,稱牟鈞德“所陳不為無見”(23)《孔祥熙函蔣中正據(jù)財政部視察員牟鈞德電稱川局須先簡任廉干大員入川整頓財政后軍權即可統(tǒng)一》(1934年11月2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194-088。。該電文是在劉湘入京期間所發(fā)。顯然,孔祥熙并不希望中央輔助劉湘整理川省財政,而主張派財政專員控制川省財政,并通過軍餉控制川軍各部。孔祥熙借牟鈞德報告名義,闡發(fā)其對川態(tài)度,意圖影響蔣介石對川政策。但蔣介石并未采納孔祥熙的建言,而是依靠劉湘統(tǒng)馭全川,并在劉湘入京期間與之達成“川省統(tǒng)籌”、“中央輔助”的財政整理方案(24)《劉湘電郭昌明昨午前謁蔣中正談財政舉兩個方式其一為徹底中央管理》(1934年12月11日),臺北“國史館”藏:閻錫山史料/文件/電報/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及錄存,典藏號:116-010108-0859-047。。
以上分歧的關鍵點,在于央地財權分配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四川之錢能否用于四川”。蔣介石欲通過讓渡部分財權實現(xiàn)對四川的整合,支持將川省國稅充當川債發(fā)行基金,由中央籌集川軍“剿共”軍費,并主動參與四川財政整理,以實現(xiàn)四川的整合。孔祥熙則不愿過多插手四川財政整理事務,更不愿以川省國稅作為川債發(fā)行基金和“剿共”軍費。1935年1月,參謀團入川,財政部在川設立財政特派員公署,著手整理川省財政(25)財政特派員制度始于1928年11月,其設立的目的主要是改善地方截留稅款的惡況。參見:《修正財政特派員暫行章程》(1929年1月3日),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政府財政金融稅收檔案史料(1927-1937年)》,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84-85頁;張連紅《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結構的劃分與實施》,《江海學刊》1999年第6期,第150頁。。孔祥熙任命長期從事鹽務工作的陳紹媯為財政特派員,其用意可見一斑。
“四川之錢能否用于四川”,是蔣、孔分歧的關鍵點。孔祥熙認為,川省財政整理和“剿共”軍費,不應以損失川省國稅為代價;蔣介石為達到整合四川的目的,主張將川省國稅用于地方財政的整理,認為中央應該在整理川省財政中負有主要責任,同時認為民初以來四川軍閥截留國稅(鹽稅)已成慣例,驟然收歸中央,勢必引起國地矛盾,增加地方整合難度。這些分歧和矛盾,隨著川省財政整理而逐漸顯現(xiàn)、升級。
二 矛盾升級:謀全局與謀一域之爭
1935年2月,四川省府重組。劉航琛、鄧漢祥代表四川省府提出一套整理四川財政辦法,其中包括軍費墊支、中央?yún)f(xié)濟、舊債換回、川中運現(xiàn)等一系列措施。出于“剿共”軍事和整合四川的考慮,該財政整理辦法得到蔣介石、楊永泰等人的支持。但是,這些辦法大部分是以犧牲國稅和中央銀行的利益為前提,遭到了孔祥熙的反對。蔣、孔矛盾亦因此升級。二人皆認為己方謀全局、彼方謀一域。蔣介石從全國政局出發(fā)認為,穩(wěn)定川局是解決華北、粵桂和西南問題的關鍵,因此勸說孔祥熙舍棄“小利”;孔祥熙則認為,國稅收入和公債發(fā)行牽涉國家財政安全和金融穩(wěn)定,不應以四川“一域”而牽涉全局。因而,雙方圍繞整理舊債和收換地鈔問題展開了博弈。
(一)整理舊債
截至1935年1月,四川省府共欠債款12139.9585萬元,為償還債務,劉湘在1935年1月發(fā)行金融公債1.2億元,其中4600萬元償還地方銀行債務,而劉湘入職四川省府后借入的200萬元則由四川省府獨立籌還,因此實際需整理的負債額共計7339.9585萬元(26)財政部四川財政特派員公署編《四川財政概況》,財政部四川財政特派員公署1936年印行,第157、159頁。。但此項公債由于難以確定發(fā)行準備,導致債信低下。為增強債信,維持四川金融穩(wěn)定,四川省府請求中央換回舊債。1935年3月4日,四川省府委員兼秘書長鄧漢祥代表省府向中央提出換回金融公債辦法:由財政部籌5000萬元現(xiàn)金,立刻將債券折收,后將川省國稅收歸中央;如不能籌集多額現(xiàn)款,可發(fā)行四川金融公債8000萬元,亦可將此項債券收回(27)《鄧漢祥呈蔣中正四川統(tǒng)籌過渡期內籌墊各軍餉項辦法及所發(fā)整理川金融公債款之用途等案》(1935年3月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212-129。。3月10日,劉湘以“朱、毛竄入黔北,川中人心,異常震動”為由,再次呈請中央承認所發(fā)1.2億元公債,要求中央盡快發(fā)行公債、墊發(fā)軍餉、籌集戰(zhàn)費(28)《劉湘陳請整理川省財政辦法及統(tǒng)籌發(fā)放軍餉呈》(1935年3月10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jīng)濟(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259頁。。最終,財政部同意發(fā)行“民國二十四年善后公債”,以換回二十一軍舊債。但在新舊債的兌換折扣、公債的發(fā)行額和發(fā)行范圍等方面,蔣、孔間分歧不斷。
首先,在新舊債的收銷折扣和公債發(fā)行數(shù)額方面,雙方分歧較大。孔祥熙認為,四川金融公債債信薄弱,價格大跌,重慶中國銀行僅以三一折兌現(xiàn),聚興誠銀行公債兌現(xiàn)不足三折;對劉湘未經(jīng)中央核準,私自指定鹽稅為還本基金一事,他表示中央難以承認其債權人債本;他進而主張,可發(fā)行5000萬元善后公債,以2600萬元換回7300萬元舊債(三折一五左右),以2400萬元用于四川善后建設和“剿共”軍費開支(29)《李儻致譚光密電稿》(1935年5月2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jīng)濟(一),第263頁。。此辦法立刻遭到楊永泰的反對,理由是“舊債概以三五折換掉,則川省金融界之資金及存款,立即折耗其半數(shù),不啻宣告其死刑,銀錢兩業(yè)之倒閉者,必相繼不輟”(30)《孔祥熙電蔣中正已定四川省整理地鈔發(fā)行公債及協(xié)助軍事辦法并籌維運現(xiàn)入川以安川局等文電日報表等二則》(1935年6月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2-015。。蔣介石也認為:“中央發(fā)行公債五千萬,決不足分配,三五折掉換尤辦不通。業(yè)經(jīng)迭電詳述,計達尊覽,請即查照謝特派員所擬之第一案,決定發(fā)行七千萬元,于本星期內議決公布為妥。”(31)《蔣介石致孔祥熙密電》(1935年6月4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jīng)濟(一),第265頁。
其次,在善后公債發(fā)行范圍上,孔祥熙堅持公債只能在川省境內發(fā)行,禁止在上海發(fā)售。他認為,川債在上海發(fā)行將影響全國金融市場;中央發(fā)行公債多數(shù)以關稅為基金,收入盡在上海,故公債在上海市面流通;四川善后公債以四川鹽稅為基金,以中央銀行渝行為經(jīng)理機關,本息應由中央渝行償付,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必須設在成都,公債也應在川境發(fā)行(32)《孔祥熙電蔣中正轉陳四川財政特派員陳紹媯建議以地方稅撥作軍費應付剿匪并與劉航琛暫管國地兩稅統(tǒng)籌事宜等整理川省財政辦法》(1935年1月2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202-052。。孔祥熙所慮不無道理。按1935年國民政府發(fā)債總額2.54億元計算,僅四川善后公債一項就占該年國民政府發(fā)債總量的27.56%(33)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1949年)》,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74-375頁。。若發(fā)債基金不穩(wěn),在金融中心上海發(fā)售債券,很容易影響全國公債價格。而楊永泰卻認為,川鹽收入屬國稅,中央銀行渝行不是川省銀行而是全國銀行,將中央銀行發(fā)行的國債強分彼此,且限制發(fā)行范圍,不利于四川的統(tǒng)一;他還指出:“近年以來,無論中央公債或中央核準各省之地方公債,向無此項公債只得于某某省內賣買抵押字樣,如獨對川省創(chuàng)此新例以歧視之,非川省不傾向統(tǒng)一,乃中央無統(tǒng)一川省之誠意矣,則川人對于中央,其將作何感想耶?”況且7000萬債款為分期發(fā)售,不至于影響上海金融市場(34)《孔祥熙電蔣中正四川鹽稅收額攤外債基金及每月善后公債等尚有所缺則九年還清應酌予延長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6月1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2-141。。孔祥熙之所以限制川債的發(fā)行范圍,是顧忌善后公債在上海發(fā)售,會影響其他國債的價格,使國家公債收入縮水。6月11日,孔祥熙向蔣報告稱,由于該年四川善后公債指定鹽稅為償還基金,使得中央發(fā)行的鹽稅庫券在上海證券市場竟跌4元有余,盡管鹽稅庫券基金已改用關余,但因該庫券冠有“鹽稅”二字,遂使其價格受到影響(35)《孔祥熙電蔣中正鹽稅庫券基金現(xiàn)雖改用關余然因傳言四川省公債以鹽稅作抵使得該基金大跌等文電日報表等三則》(1935年6月11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3-003。。但蔣、楊仍堅持在上海和四川范圍內發(fā)售。
再次,在善后公債的償還時間上,蔣、孔亦存在分歧。公債還本付息年限取決于公債基金是否充足。四川善后公債是以川鹽收入為還本付息基金,因此川鹽收入穩(wěn)定與否將直接決定四川善后公債債信狀況。財政特派員謝霖與財政廳長劉航琛商定月?lián)?3萬元,分九年還清,但孔祥熙要求將償還期限延長至十二年。孔稱,據(jù)川省鹽務稽核所報告,四川鹽稅年收入平均在900萬元,除外債攤撥160萬元,年剩余740萬元,現(xiàn)月?lián)?0萬元為善后公債基金仍有缺口,因此公債不可能在九年內還清,故主張十二年還清;楊永泰針鋒相對,根據(jù)四川鹽運使劉樹梅的呈報估計,四川鹽稅歲入至少在1800萬元以上,故每月?lián)芨洞▊?3萬元絕對不成問題,因此堅持九年內還清善后公債的主張(36)《孔祥熙電蔣中正四川鹽稅收額攤外債基金及每月善后公債等尚有所缺則九年還清應酌予延長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6月10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2-141。。實際上,孔祥熙對川鹽收入的估計并不客觀,1933、1934兩年僅二十一軍防區(qū)內鹽稅收入就分別約達886萬元、972萬元(37)張肖梅編著《四川經(jīng)濟參考資料》,中國國民經(jīng)濟研究所1939年版,第三章“財政”第18頁。。盡管二十一軍占據(jù)川南重要鹽場,但1935年川政統(tǒng)一后,川北鹽場納入省府管轄范圍,川鹽年收入應在1200萬元以上(38)根據(jù)1921-1931年四川鹽稅統(tǒng)計,川北、川南鹽場鹽稅共收入12988萬元,平均年收入在1100-1200萬元之間(1180萬元)。參見:財政部四川財政特派員公署編《四川財政概況》,第42頁。。1935年,四川財政廳編訂川鹽預算收入為1500萬元,財監(jiān)處編訂川鹽預算為1020萬元;1936、1937年,財監(jiān)處制定川鹽預算皆為1670萬元(39)張肖梅編著《四川經(jīng)濟參考資料》,第三章“財政”第18頁。。經(jīng)過國民政府和四川省府對鹽場設施和鹽務管理的改進,1936年度(1936年7月-1937年6月),川鹽實際收入達到國幣2272.5萬元(40)財政部鹽務總局統(tǒng)計室《1914年至1948年6月歷年鹽稅收入統(tǒng)計表》,江蘇省中華民國工商稅收史編寫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工商稅收史料選編》第2輯下冊,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5頁。。因此,楊永泰等人對川鹽收入的預估相對準確,1935年的四川善后公債完全能在九年內還清。但由于四川財政危機加重,蔣介石不得不遷就孔祥熙,稱:“兄如確認為有十二年之必要,可即決定為十二年,請即發(fā)表,勿再因此延緩為荷。”(41)《蔣介石致孔祥熙密電》(1935年6月18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jīng)濟(一),第266頁。但孔祥熙最終同意九年還清(42)《孔祥熙致蔣介石密電稿》(1935年6月19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jīng)濟(一),第267頁。,財政部亦在1935年6月30日公布《民國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債條例》(43)《民國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債條例》(1935年6月30日公布),財政部四川財政特派員公署編《四川財政概況》,第158頁。,四川舊債問題得以解決。
綜上可知,孔祥熙之所以降低四川舊債價格、限制川債發(fā)行額和發(fā)行范圍、延長還本付息期限,主要目的是維持中央銀行的國債價格和信譽,減少川省國稅的流失,以最小的代價實現(xiàn)四川舊債的整理;蔣介石、楊永泰則為了避免四川省府及債權人的反對,也為了更好整理川省財政、平衡收支,主張放寬川省發(fā)債條件,以期快速實現(xiàn)四川軍政大權的整合。
(二)整理地鈔
1935年初,四川督辦公署曾以1.2億元金融公債中的4300萬元用于整理地鈔,但由于債信不足,地鈔問題并未得到妥善解決,擠兌風潮不斷(44)財政部四川財政特派員公署編《四川財政概況》,第157頁。。四川擠兌風潮爆發(fā)的根本原因,是四川市面缺乏現(xiàn)金(45)康心之《四川金融之回顧與前瞻》,《四川經(jīng)濟月刊》1935年第4卷第6期,第7-9頁。。川省防區(qū)混戰(zhàn)時期,商業(yè)衰落,商品入超增加,川境現(xiàn)金外流,導致市面現(xiàn)籌減少,紙鈔貶值,申匯大漲。川政統(tǒng)一之初,劉航琛認為,地鈔價值跌落的根本原因是準備不足,因此他要求地方銀行停止發(fā)鈔、封存未發(fā)行鈔票,并建議中央向川中運現(xiàn),補充地鈔準備金,改善幣值(46)《劉航琛談整理四川財政:先整理舊欠平衡收支 再謀統(tǒng)一使?jié)u上軌道》,《大公報》(天津)1935年2月24日,第4版。。1935年3月,重慶銀錢業(yè)再度爆發(fā)擠兌風潮。蔣介石催促孔祥熙向川省運現(xiàn),并稱“統(tǒng)一幣制與統(tǒng)制匯兌為惟一要務”(47)《蔣中正電孔祥熙整理川中金融以統(tǒng)一幣制與統(tǒng)制匯兌為惟一要務》(1935年3月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革命文獻/統(tǒng)一時期,典藏號:002-020200-00033-019。。孔祥熙本人也認為,向川中運現(xiàn)是解決四川地鈔問題的“一勞永逸之法”,而收銷地鈔需要中央銀行渝行存儲準備金700萬元,且每周須運現(xiàn)50萬元前來以備兌換,但問題是現(xiàn)中央銀行現(xiàn)鈔緊缺,無法向川中運現(xiàn),故他建議四川省府每月?lián)?5萬元作基金,發(fā)行有獎儲蓄券,每月抽簽還本,用以收回地鈔;但此一建議立即遭到楊永泰的反對:“發(fā)行獎券,久為中央令禁……且為期甚遠”,“以獎券收回川省債券,理尚可通,如以獎券收回川省十足通用之地鈔,必招川人之反感”(48)《孔祥熙電蔣中正整理四川地鈔辦法擬以省府每月五十五萬基金發(fā)行有獎儲蓄券按月抽簽還本再收回地鈔等文電日報表等三則》(1935年3月19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48-156。。最終,各方商議由中央發(fā)行“整理四川金融庫券”,總額3000萬元,以中央所收川省部分統(tǒng)稅及印花煙酒稅為還本付息基金,月?lián)?5萬元,分64個月還清(49)財政部四川財政特派員公署編《四川財政概況》,第159頁。。但在金融庫券的發(fā)行準備、地鈔與本鈔兌換比率等方面,孔祥熙與蔣介石及四川當局仍矛盾重重。
至1935年4月9日,四川地方銀行共發(fā)行地鈔3307.68417萬元,共有現(xiàn)金準備306.790498萬元,準備不敷3000.89367萬元(50)《財署整理地鈔辦法》,《四川經(jīng)濟月刊》1935年第3卷第6期,第174頁。。5月,四川省府初步形成了收銷地鈔實施辦法,即財政部將3000萬元整理四川金融庫券向中央銀行抵押2300萬元,連同四川省府籌款700萬元,一并交付中央銀行,委托其收銷地鈔,并確定該年6月1日為收銷地鈔期限(51)《孔祥熙電蔣中正中央銀行力量有限請督促四川迅即按原案如期照撥準備金不得短缺或抵免以便屆期實施整理地鈔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6月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2-028。。但四川省府無法在短時間內籌集700萬元現(xiàn)款,于是,四川財政廳廳長劉航琛與財政特派員謝霖商議,先撥300萬元,剩余400萬元,分兩個月,每月各撥200萬元(52)《謝霖致劉航琛密電》(1935年5月23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一編財政經(jīng)濟(一),第262-263頁。。至6月5日,四川地鈔開始收銷,四川省府仍未將300萬元撥交中央銀行。孔祥熙電呈蔣介石,稱中央銀行渝行現(xiàn)金缺乏,請督促四川省府盡快將300萬元撥交中央銀行;但據(jù)劉湘稱,5月底,四川省府已經(jīng)向重慶銀行、錢莊押借300萬元,由各行、莊立出月息1分的地鈔定期存單送交中央銀行渝行,于6、7、8月底每月分別提取地鈔100萬元,并隨付月息,但中央銀行渝行拒不接受,只收取現(xiàn)金(53)《孔祥熙電蔣中正中央銀行力量有限請督促四川迅即按原案如期照撥準備金不得短缺或抵免以便屆期實施整理地鈔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6月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2-028。。孔祥熙拒不接收地鈔,是因為地鈔兌換申鈔須補水,若以地鈔充作準備金,則中央銀行發(fā)行準備必定縮水;若以現(xiàn)金入賬,則可充實中央銀行現(xiàn)金儲備。但是,四川金融瀕于崩潰,四川省府已無法籌足300萬元現(xiàn)金繳存中央銀行。因此,楊永泰認為:“不必于此強求,致成僵局,蓋整理地鈔、統(tǒng)一發(fā)行、統(tǒng)一貨幣乃中央必應擔負之責任也。”(54)《孔祥熙電蔣中正中央銀行力量有限請督促四川迅即按原案如期照撥準備金不得短缺或抵免以便屆期實施整理地鈔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6月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2-028。在蔣介石的催促和嚴令下,四川地鈔開始收回。
三 困境紓解:中央與四川財政關系的確立
在整理舊債和收換地鈔的過程中,蔣介石與孔祥熙的矛盾升級。孔的遷延態(tài)度和對川省財政的干預,阻礙了蔣對川政策的實施和政治、軍事目的的達成。為提高財政整理的效率,蔣介石重新部署人事,任命關吉玉為財政特派員,同時設置行營財監(jiān)處,關吉玉身兼處長,川省財政進入中央統(tǒng)籌階段。財監(jiān)處架空了財政部在川的人事布局,使財政部四川特派員公署成為僅管理川省國稅之機關。財監(jiān)處建立后,在蔣介石的強力干預下,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駐川國有銀行,與川省財政之間形成了穩(wěn)固的借墊關系。
駐川財政人事的更迭,是蔣介石威權的一種表達。早在1935年3月,蔣介石電令孔祥熙,要求撤換四川財政特派員陳紹媯,另派員充任,孔當即照辦(55)《蔣中正電令孔祥熙應即撤換四川財政特派員陳紹媯另覓人接辦》(1935年3月2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籌筆/統(tǒng)一時期,典藏號:002-010200-00131-040。。孔祥熙之所以任陳紹媯為財政特派員,除陳為孔、宋親信外,另與其職歷不無關系。陳長期供職國民政府鹽務系統(tǒng),歷任松江鹽運副使、四岸食鹽濟運總局長、湖北財政特派員等職(56)《財政部設立四岸食鹽濟運局 委陳紹媯為局長 組織簡章已公布》,《申報》1928年2月6日,第8版;《財政部令(第二三七五號,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七日)》,《財政日刊》1929年第445號,第3頁。,后因包庇“裕川土案”而被革職(57)石影《宋子文在漢籌款六百萬元:以鹽稅作抵息借三百萬已簽定合同 責成省市政府籌募關稅庫券三百萬 陳紹媯溺職受撤 另委李基鴻繼任》,《上海報》1930年9月1日,第2版。。孔重新啟用陳紹媯,其用意在于保護川省最重要國稅收入鹽稅(58)陳紹媯任內,禁止川軍強提鹽稅,同時降低川鹽楚岸稅率,鼓勵川鹽輸出,這些都促進了川鹽收入的增加。參見:《陳紹媯請制止川軍人提鹽稅》,《民報》1935年2月8日,第1張第2版;《川鹽稅繳入國庫 陳紹媯已呈請財部轉飭 嗣后不得強提以符功令》,《中央日報》1935年2月8日,第1張第3版;《獎勵川鹽輸出 陳紹媯電陳意見》,《中央日報》1935年2月27日,第1張第2版;《陳紹媯電請核準楚岸專銷川鹽》,《申報》1935年2月27日,第6版。。陳就職后,主張以省稅劃作“剿共”軍費,同時要求四川財政特派員公署掌理全川財務行政、控制全川稅征機構及人事組織(59)《孔祥熙電蔣中正轉陳四川財政特派員陳紹媯建議以地方稅撥作軍費應付剿匪并與劉航琛暫管國地兩稅統(tǒng)籌事宜等整理川省財政辦法》(1935年1月2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202-052。,這些主張遭到四川當局的不滿。陳紹媯被撤換的詳因,檔案中并未明確提及。但據(jù)四川鹽務稽核所陳況仲表述,1935年初,陳紹媯在擔任財政部特派員期間,曾通過內部消息,伙同重慶金融界商人買賣申票獲利,因此獲罪(60)陳況仲《鹽務稽核所紀略》,政協(xié)四川省自貢市委員會《自貢文史資料選輯》編輯委員會編《自貢文史資料選輯》第14輯,第99頁。。從表面看,陳紹媯因非法買賣申票,貪污公款,遭免職。但在1935年初,重慶《工商夜報》因報道陳紹媯處置四川財政不當、行將撤職,被二十一軍部停刊一周(61)王綠萍編著《四川報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四川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14頁。。另據(jù)重慶平民銀行經(jīng)理寧芷邨回憶,劉航琛也曾解決了財政困難(62)寧芷邨、周季悔、衷玉麟等《川康平民商業(yè)銀行與劉航琛》,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29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頁。。通過內部消息買賣申票獲利,在當時是一件極為普通的事情。可見,買賣申票、貪污公款,只是蔣介石撤換陳紹媯的一個理由。陳紹媯作為孔祥熙意志的忠實執(zhí)行者,在整理財政問題上止步不前,是蔣罷免陳的主要原因。
陳紹媯被罷免后,中央銀行秘書長謝霖暫代特派員一職,但四川財政整理的進程并未因人事更迭而有所推進。1935年4月,重慶再度爆發(fā)銀行擠兌風潮,并出現(xiàn)人員傷亡事故。4月23日,楊永泰致電蔣介石,呈請電令孔祥熙,從速整理地鈔,安定四川金融(63)《楊永泰電蔣中正報告地方銀行發(fā)生擠兌原因及處理經(jīng)過并請電孔祥熙速將整理地鈔辦法決定宣布以安定四川省金融》(1935年4月2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文電/領袖事功/國家建設,典藏號:002-090102-00011-262。。緊張的華北局勢,增加了蔣安定川局的急迫感。5月28日,蔣介石致電孔祥熙指明四川的重要性,稱:“日本在華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勢,最近必有舉動,彼之目的在擾亂我經(jīng)濟之發(fā)展與軍事之成功,此時我方軍事與政治重心全在四川,請兄對于四川經(jīng)濟有關之各種問題從速解決,并早定川中金融之根本方策,不致發(fā)生根本之動搖,如能多解現(xiàn)銀入川以備萬一更好,務請急辦為盼。”(64)《蔣中正電孔祥熙我方軍事與政治重心全在四川請早定金融根本方案》(1935年5月2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革命文獻/統(tǒng)一時期,典藏號:002-020200-00033-066。同日,蔣介石又致電宋靄齡,讓其勸說孔祥熙從速解決四川經(jīng)濟的各種問題,多解現(xiàn)銀入川,穩(wěn)定四川金融(65)《蔣中正電宋藹齡轉孔祥熙此時軍事政治重心皆在四川請從速解決四川經(jīng)濟各種問題希能多解現(xiàn)銀入川早定川中金融政策》(1935年5月28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225-068。。5月末,重慶各大銀行收銷地鈔,成渝銀錢業(yè)幾乎無錢可借。6月2日,蔣介石再次函電孔祥熙,催促其先發(fā)行7000萬元的四川善后公債,“先定川局,再圖大局之挽救”(66)《蔣中正電孔祥熙速發(fā)行七千萬四川公債先定川局再挽救大局》(1935年6月2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227-023。。蔣介石的救市心態(tài),可見一斑。
但孔祥熙仍不為所動,對四川公債問題采取拖延戰(zhàn)術,這種消極態(tài)度激怒了蔣介石。6月7日,蔣介石再電孔祥熙,要求盡快辦理四川公債,稱:
如果對于川省不照此原定之案辦理,不惟與四川為難,是直與弟之軍事為難。兄處陳紹媯等不明大體,只報私怨,其在川營私舞弊,確有實據(jù)。望即先行扣押,由中負責證明,以為貪污者炯戒。如果中央徒計目前小利而不為將來整個打算,殊非統(tǒng)一之道,更非中央之福。務希從速照第一案通過,從速公布。否則,四川財政即日崩潰,而軍事不堪設想更可知矣。(67)《蔣中正電孔祥熙盡速依照第一案辦理四川公債并懲治陳紹媯在川營私舞弊》(1935年6月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228-034。
如前所述,早在1935年3月24日,蔣介石曾電令孔祥熙撤換陳紹媯(68)《蔣中正電孔祥熙應即撤換四川財政特派員陳紹媯另覓人接任》(1935年3月24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216-067。,孔當即照辦,并由中央銀行秘書長謝霖暫代。時隔一個多月,蔣介石重提法辦陳紹媯,實為懾孔之舉(69)盡管陳紹媯不再擔任四川財政特派員,但仍是孔對川政策的重要幕僚。參見:《陳紹媯昨午謁孔 請示整理川省財政》,《新聞報》1935年4月26日,第12版。。孔祥熙大為驚恐,并于6月9日函電蔣介石,極力撇清與陳紹媯的關系,申訴苦衷,稱陳紹媯在宋子文任內曾任川事,后因其熟悉川情,故派其充任特派員一職,“謝霖在川原屬暫代弟意,兄如有屬意之人,擬請見示,即當遵派”,并指出上海金融正處崩潰之時,整理川債會牽動全局(70)《孔祥熙電蔣中正關于陳紹媯案非任內之事及請示可否以謝霖暫為處置中央銀行重慶分行與地鈔事件并請加以審查枉法謀利者等》(1935年6月9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228-082。。由于四川善后公債發(fā)行進程緩慢,蔣介石授意孔祥熙召回謝霖,任關吉玉為四川財政特派員(71)《蔣中正電請孔祥熙正式加委關吉玉代理四川財政特派員及令謝霖回部》(1935年6月1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籌筆/統(tǒng)一時期,典藏號:002-010200-00141-044。。7月,蔣介石設立行營駐川財政監(jiān)理處,以關吉玉為處長,劉航琛為副處長(72)參謀團在1935年10月改組為重慶行營,以顧祝同為主任、賀國光為參謀長、楊永泰為秘書長,仍以關吉玉任財監(jiān)處處長、劉航琛為副處長。。財監(jiān)處的設立,稀釋了財政特派員公署對四川財政的控制力,且關吉玉身兼二職,阻斷了孔祥熙直接插手四川財政事務的途徑。
同時,行營財監(jiān)處指定中央銀行重慶分行成立國地兩稅聯(lián)合金庫,并規(guī)定:自1935年7月1日起,四川省一切國省兩稅均解入聯(lián)合金庫;凡屬于四川的國省稅,統(tǒng)由財監(jiān)處監(jiān)理,并在決定一切度支、處理對外事件時,以“委員長”名義行之(73)《行營設駐川財政監(jiān)理處》,《四川經(jīng)濟月刊》1935年第4卷第1期,第126-127頁。。財監(jiān)處下設三組:第一組,掌理文書、印信、庶務及交際等事項;第二組,掌理聯(lián)合金庫,洽辦收交款項票據(jù)等事項;第三組,掌理記賬及填造表報等事項(74)《行營駐川財監(jiān)處之進行狀況》,《四川經(jīng)濟月刊》1935年第4卷第4期,第7頁;《軍委會行營駐川財政監(jiān)理處正式成立》,《四川月報》1935年第7卷第3期,第31-33頁。。從財監(jiān)處的職掌和權力來源看,財監(jiān)處權力直接來源于委員長行營,地位高于財政部四川特派員公署;同時,財監(jiān)處控制四川的國省稅款大權,掌管四川國省兩稅聯(lián)合金庫,指導、監(jiān)督四川省府制定預算,掌理川省財政收支。這樣一來,財監(jiān)處不僅具有支撥川軍餉款權力,而且川省一切重大財政措施都必須經(jīng)過財監(jiān)處的審核方能執(zhí)行。財監(jiān)處成為統(tǒng)籌四川財政的最高機關,而財政特派員公署則淪落到只負責辦理國稅事宜的財稅機關。
財監(jiān)處成立之初,孔祥熙曾要求財監(jiān)處接受財政部監(jiān)督、指揮,收支賬目應報財政部核準,而蔣介石則一面答允孔祥熙所請,一面又稱“應由弟(指蔣介石)直接指揮”(75)《孔祥熙等電蔣中正對于整理四川省財政意見書中關于整理機關擬依來函采用第二種辦法并補充請商同財政部制定監(jiān)理處組織章程等三點意見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7月7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5-106。。財監(jiān)處設立后,孔祥熙仍能通過中央銀行插手整理四川財政事務。在地鈔與中鈔的收兌比率上,四川當局與財政部產(chǎn)生分歧。1935年8月13日,孔祥熙擬定以本鈔1000元換回地鈔1250元(八折),認為四川申匯最高價可達1600余元,平均匯價亦在1200-1300元之間,八折收銷地鈔比較公允(76)《孔祥熙電蔣中正以四川善后公債一千萬元押借七百萬元擬由中央中國兩銀行各三百萬元農(nóng)民銀行一百萬元地鈔與中央本鈔性質不同地鈔收縮本鈔推廣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8月1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6-271。。此辦法遭到劉湘反對,劉申述的理由是:川省“剿匪”各軍二等兵一名每月領伙餉為地鈔5.28元,而中央軍所領為申鈔7元,最近川軍與中央軍同駐一地、共同“剿匪”,川軍兵士因領餉差異已有怨言,但仍以“四川生活低于他省,故原定餉章不同為解”;若再以申地匯價變相八折領餉,川軍二等兵僅得4.2元,斷難維持其最低生活,故“此規(guī)定之地鈔標準匯價之有害于軍事者也”(77)《劉湘電蔣中正川省地鈔變相八折匯價影響軍事財政及擬意見五項之文電日報表》(1935年8月25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7-040。。但是,由于孔祥熙堅持八折收換地鈔,雖經(jīng)蔣介石、楊永泰多次溝通,仍然無果。故楊永泰呈稱:“孔部長文二復電,因其中第三節(jié)之地鈔問題所擬辦法及所持見解,頗不正確,然迭經(jīng)往返討論,擬暫存不復”(78)《孔祥熙電蔣中正以四川善后公債一千萬元押借七百萬元擬由中央中國兩銀行各三百萬元農(nóng)民銀行一百萬元地鈔與中央本鈔性質不同地鈔收縮本鈔推廣等文電日報表》(1935年8月13日),臺北“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tǒng)文物/特交檔案/一般資料,典藏號:002-080200-00456-271。。相持之下,蔣介石最終同意以8折收回地鈔,四川地鈔問題得到解決。
孔祥熙為提高財政部對川話語權,設法提高了財政特派員的職權。1935年9月,財政部公布《修正財政部四川財政特派員公署組織辦法》(79)《修正財政部四川財政特派員公署組織辦法》(1935年9月20日),《財政公報》1935年第92期,第1-3頁。,著重加強財政特派員對于川省地方軍政費支撥方面的權力。重慶行營為了進一步增強財監(jiān)處的權力,于同年11月公布《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財政監(jiān)理處監(jiān)督川省稅務辦法草案》,規(guī)定財監(jiān)處對四川稅務具有“督征”、“稽核”、“考績”之權;加委原省府派遣的各區(qū)財政視察員為稅務督征員,并由督征員負責督征區(qū)內縣長和征收局長的考核之權;由行營派出稽核人員,不分區(qū)域,巡行考察,無論國省稅收機關,均在考察范圍之內;同時,財監(jiān)處對各級征收官吏還具有獎懲權力(80)《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財政監(jiān)理處監(jiān)督川省稅務辦法草案》,《四川月報》1935年第7卷第5期,第243-246頁。。財監(jiān)處統(tǒng)一了川省的稅務人事權,中央與四川財政關系最終確立,川省財政實現(xiàn)整合。
此后,財監(jiān)處多次向渝蓉兩地中央銀行及其他駐川國有銀行借款,財政部與四川財政關系得到疏通,至1938年川省國地收支劃分之前,四川省政府向駐川國有銀行抵押或商借數(shù)額達1820萬元之巨(81)分別為:劉航琛向中央銀行商借款1200萬元;為平衡預算向中、中、交、農(nóng)四行借款100萬元,以建設公債向中央銀行押款60萬元,以二十五年四川善后公債向中、中、農(nóng)三行押款31萬元,以禁煙鹽稅及特貨向中、中兩行借款200萬元,為“剿赤”向中央銀行借款9萬元,以建設公債向中國銀行押款20萬元,以營業(yè)稅向中、中、交、農(nóng)四行借款200萬元,八項合計總數(shù)達到1820萬元。分別參見:《川向中央銀行借款千二百萬 孔祥熙允許》,《益世報》(天津)1935年11月30日,第2版;財政廳長甘績鏞報告《四川省政府財政廳施政報告(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八年六月)》,1939年7月在省參議會報告后校訂,第26頁。,四川財政與駐川國有銀行之間形成了穩(wěn)固的借墊關系。
四 結論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地方財政整理是國民黨中央實現(xiàn)地方整合的關鍵步驟。財權讓渡是調和央地矛盾的重要方法,也是實現(xiàn)中央集權的一種方式。蔣、孔之爭是國民黨中央整合地方過程中發(fā)生的典型案例,是現(xiàn)實政治與法理規(guī)則的博弈。盡管蔣、孔雙方對于集權的實現(xiàn)途徑不同,但二者在維持國債債信、增加國稅收入、增強中央權威方面并無異議,二者均以強化中央權力為最終目的。因此,蔣、孔之爭屬合作框架內分歧,并非派系之爭。基于不同的立場和訴求,以及對政局、時局理解的層級各異,二者在對川問題上存有抵牾,但并不妨礙蔣、孔之間的長期合作。自1933年10月孔祥熙繼任財政部長后,極力配合蔣介石的軍事政治行動,軍費、債務預算顯著增加,且預算對實際支出的約束能力明顯下降(82)阿瑟·恩·楊格《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國財政經(jīng)濟情況》,陳澤憲、陳霞飛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5頁。。這些都是蔣、孔之間合作的基礎和表征。國債債信、國稅收入與四川財政在蔣孔戰(zhàn)略意圖中所處位置不同,為“一域”與“全局”之別。1935年,國民政府共發(fā)行2.54億元公債,其中四川公債券額達1億元,約占40%(83)千家駒編《舊中國公債史資料(1894-1949年)》,第374-375頁。。發(fā)行巨額的四川公債,容易影響全國的國債價格和金融穩(wěn)定,此為孔祥熙所慮;但在當時復雜局勢下,“川劉”成為維系華北、粵桂、西南穩(wěn)定的關鍵,因此蔣介石不惜“多費幾錢”來維持大局。
盡管蔣、孔之爭是以蔣介石多數(shù)提案被通過為最終結果,但蔣、孔交涉多以磋商為主要解決途徑,而非以行政指令方式進行。在關鍵問題上,如在地鈔與中鈔的兌換比率上,孔祥熙寸步不讓,使蔣介石無計可施。財監(jiān)處建立后,孔祥熙和財政部在四川的勢力被削弱,但孔祥熙仍能以財長的身份提高財政特派員公署的權力,以中央銀行總裁的身份協(xié)調中央與四川財政金融關系。這表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盡管形成了以蔣介石和軍事委員會為中心的權力結構,但其權力仍被“法統(tǒng)”約束,蔣介石在四川推行實施的各項財政政策,必須冠以“財政部”名義,方能順乎法理。這是關吉玉身兼財監(jiān)處長和財政特派員的主要原因,也是國民黨弱勢獨裁的重要表征。
合理劃分央地財權與事權,是近代分稅制實踐的關鍵步驟,也是南京國民政府整合地方過程中中央與地方勢力博弈的重要場域。國民黨中央通過讓渡部分財權來實現(xiàn)地方整合。在整理四川財政過程中,蔣介石區(qū)別性對待四川的重要原因,在于穩(wěn)定川局已成為國內外時局、社會情勢的迫切要求。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民族危機加深,國內輿論和國民黨內部逐漸形成了對內“團結”以御外侮的聲音(84)羅敏《走向“團結”——國民黨五全大會前后的蔣介石與西南》,《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28頁。。同時,四川處于西南中心位置,川軍將領手握重兵,成為陳濟棠、李宗仁和韓復榘等反蔣勢力拉攏的對象。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國民黨中央整合四川的價碼,即財政部需讓渡更多利益以維持四川政局穩(wěn)定,此為蔣、孔矛盾的焦點。蔣介石任用“親川派”,力圖實現(xiàn)川局的穩(wěn)定,以拒日本;對川強硬派暫時失勢。維持國內政局的穩(wěn)定,是抗戰(zhàn)前國民黨中央制定各項政策的底色,亦是其政治生態(tài)的直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