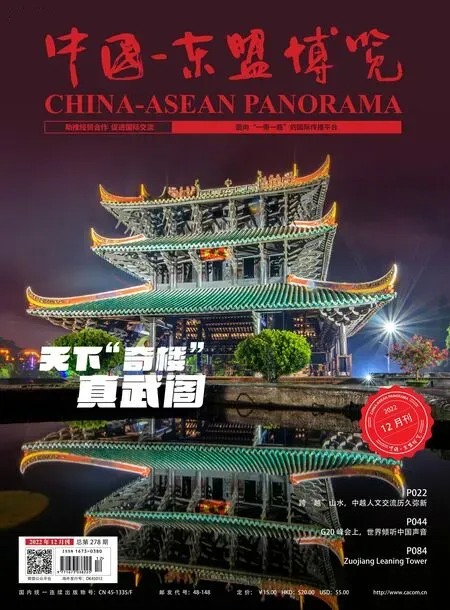“壯刀王”黃冬鵬:笑傲刀劍江湖
●撰文/唐琪

■ 黃冬鵬與他的刀劍人生
是什么讓他放棄穩定的工作,花費9年去“復活”一個幾近失傳的古法技藝?又是什么支撐著他,即使賠上所有積蓄,也不肯放棄在外人看來幾乎是不可能走通的一條路?他又是誰,居然能從一個半路出家的“門外漢”變成明星都追捧的“壯刀王”?接下來,就讓我們走進他的生活,一起見證一場“奇跡”的誕生。

■ 壯刀,將壯族諸多文化元素融為一身
從“門外漢”到“壯刀王”
黃冬鵬出生于廣西南寧的一個書香之家,從小就開始跟著爺爺學習繪畫。家庭環境的耳濡目染,加上本人對美術的癡迷,黃冬鵬很快就熟練掌握國畫、油畫、素描等多種繪畫技法。
后來,由于對美工頗感興趣,黃冬鵬選擇來到廣西電影制片廠,開始從事置景道具的制作。黃冬鵬說:“由于我本身美術功底比較扎實,動手能力也不錯,所以從事這份工作,不僅自己樂在其中,同時也精進了制作道具的水平,這對我后來制作壯刀可以說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一天,還在電影廠工作的黃冬鵬偶然翻到了國外的《刀王》雜志,很快便對書中花紋鋼鍛打的精品刀具心生癡迷。“我當時就被這精美的工藝深深吸引,非常迫切地想了解和學習,可在我翻閱了很多資料后,卻發現鮮有記載,幾近失傳。”黃冬鵬說,他贊嘆之余又心生痛楚,但也正是從那時起,挖掘和繼承傳統鍛造工藝的想法,開始在黃冬鵬的心里萌芽。
不過,當時在電影廠的黃冬鵬有著不錯的收入,工作也很穩定,而要想學習鍛造工藝,必須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在夢想與現實之間掙扎了7 年后,黃冬鵬才最終決定辭職,義無反顧開始他的“刀劍人生”。
黃冬鵬告訴我們,“當時家人朋友都說我是不務正業,甚至覺得我瘋了。因為前期的事業花費很大,自己又沒有鍛打房,所以場地都是租用的,一天的花費很大,700 多塊錢一天,積蓄都賠進去了。”
不光開頭難,黃冬鵬造刀之路更是難上加難。由于古法失傳已久,黃冬鵬便來到了橫縣,與老打鐵匠們一同交流學習,并查閱了大量的古籍資料,才慢慢找回了古法鍛造技藝。然而,掌握了方法,實踐起來卻并不簡單。他嘗試了無數種鋼材,進行了無數次調試,卻屢屢碰壁,夢想中的花紋鋼,一直沒能打造出來。
黃冬鵬回憶說,“當時,不停的失敗讓整個人情緒已經很低落了,就連給我租場地的場主都心疼我了,覺得這件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黃冬鵬終究沒有放棄,經過上千個日夜的打磨,上百斤鋼材的試煉,黃冬鵬終于在2009 年鍛造出了完美的花紋鋼,讓失傳已久的古法鍛打技藝成功“復活”。
自此之后,黃冬鵬不斷精進自己的技藝,鍛制出了自己滿意的花紋鋼。而憑著精深的造詣,黃冬鵬成為了廣西唯一掌握花紋鋼鍛造手藝的工藝大師,實現了“門外漢”到“壯刀王”的驚人蛻變。
刀尖上的壯文化
每次黃冬鵬給我們介紹壯刀時,他眼里似乎總是充滿星光。他告訴我們,“我畢生的夢想就是能把從古至今各個時期的壯刀都全部復原出來,要讓更多人了解我們壯族的刀劍,體悟壯族獨有的民族魅力。”
而壯刀,作為壯族別具一格的文化符號,幾乎是與壯族人民共生共存的。早在2000 多年前的駱越時期,壯族先民就在花山壁畫上刻下豐富完整的壯刀圖案,讓民族迸發的智慧和力量躍然巖壁之上。

■ 《壯刀—盛世華章》復興了駱越民族古刀的輝煌風采
在過去,由于壯族先民主要居住在山林中,灌木叢生,山石巨大,所以曾經作為勞作工具的壯刀,就主要起到開伐的作用。此外,先民還會根據自身體型設計出適合本民族使用的形制,讓壯刀能更好地滿足日常生活的各種所需。
不過,如今黃冬鵬復原的壯刀,在保留原有工藝的基礎上,還融入了更多壯族文化元素。黃冬鵬拿著他的代表作品《無極駱越》向我們介紹說:“你們看,一把小小的壯刀,可是蘊藏了豐富的壯族文化。刀身上的紋理是采用互滲工藝鍛造的布丁紋,源自我們壯錦上的花紋,而且因采用了不同鋼材,受到光線的變化還會呈現出彩虹般的七彩色。”
一把小小的壯刀,拿在手里卻頗有分量,仿佛和其所承載壯文化一般厚重。黃冬鵬說,這都是歷經了數十道極為復雜地鍛造工序才能出品。而如此精美的刀具,在制作上更是精益求精,其核心工藝甚至要以秒來拿捏。
古法鍛造是壯刀文化千年的寶貴工藝,而其中最難以掌握的便是這鍛打技藝。黃冬鵬說:“鍛打,講究時機,除了時刻觀察,還得手疾眼快,因為每種鋼材熔點都不一樣,只有在一個溫度點上面是能夠結合的,這時間只有幾秒,一旦錯過,就失敗了。”
而如此復雜的工藝,黃冬鵬卻能掌握得爐火純青。面對熊熊燃燒的爐火,黃冬鵬僅靠眼睛,且只需1 秒鐘,就能看出溫度。但黃冬鵬說:“只能看出溫度還遠遠不夠,更多時候是需要匠人的熟練度和感覺來拿捏,這也是能掌握鍛造工藝的人寥寥無幾的原因。”
如今,除了把壯刀制作技藝保留下來,黃冬鵬還努力把壯刀制作技藝融入到人們的生活中。在黃冬鵬的壯刀王文創基地,展示了豐富多樣的壯刀文創產品,從餐廚刀具到裝扮飾品,壯刀深受各路收藏家的喜愛,成功開辟出了一條富有現代活力的文化傳承之路。
鍛刀,更是鍛“心”
黃冬鵬語重心長地說,壯刀傳承之路,其實走得很艱難。
壯刀制作技藝,對匠人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黃冬鵬說:“制作壯刀,不僅需要有優秀的動手能力,還得具備審美、美術、雕塑等扎實的藝術基礎,另外,擁有一顆能經得起‘鍛打’的耐心,這更為重要。”
譚云鵬是黃冬鵬的徒弟之一,雖然和黃冬鵬同齡,自己也是高校的教師,但他一直以來都虛心地向黃冬鵬請教學習。“去年開始接觸到黃老師,就發現一把很平常的刀,在他手上做出來很有藝術感,也有民族特色,他手上的刀已經上升到一種藝術品的階段了。”
在壯刀藝術魅力的吸引下,譚云鵬開始向黃冬鵬學習,但卻發現這條路卻并不好走。譚云鵬說:“剛開始的時候,錘到手,燙傷,割手,手起泡,還有體力不夠,還要去拉煤。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受傷,挨縫針,還打了破傷風。你看黃老師的手、我們的手受傷都是家常便飯。”

■ 壯刀王文創基地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與收藏家
而鍛刀之路最難的,還有努力之下卻收獲甚微的挫敗感。譚云鵬感慨道:“火候要不就過了,要不就是沒有夠,成功率現在20% 都達不到。書上寫是多少溫度,并不是說到了那個點它就合適,最難的就在于很多時候它是靠感覺來的,所以說耐心真的很重要。”
雖然傳承之路并不好走,但黃冬鵬卻一直在盡可能多地豐富壯刀的傳承方式。黃冬鵬先后成立了工作室、展示中心、文化基地和研學中心,并借助“大師進校園”等活動,到各個高校講學,開展合作研究,共創實訓基地,開啟了現代師徒傳授模式。
從電影制片廠里做道具置景的小伙子,到刀鋒上孜孜不倦,行走了二十年春秋的非遺手藝人,黃冬鵬在逐夢路上步履不輟的鍛造錘煉,讓中國傳統刀劍技藝和廣西民間的壯刀文化在新時代綻放出一縷復蘇的曙光。

■面對熊熊燃燒的爐火,黃冬鵬只需用眼睛看1秒,就能知道溫度

■ 著名收藏家馬未都到壯刀王工作室參觀交流
TIFS
壯刀制作技藝于2019 年被列入第八批南寧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而黃冬鵬不僅是壯刀制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也是非遺基地負責人、中國少數民族科技史學會理事、南寧市工藝美術協會副會長、廣西工藝美術大師。如今,黃冬鵬創造了“壯刀王”“冬鵬”等文創品牌,其作品歷年多次榮獲中國工藝美術最高獎百鶴金鼎獎、百花獎、金鳳凰獎、廣西“八桂天工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