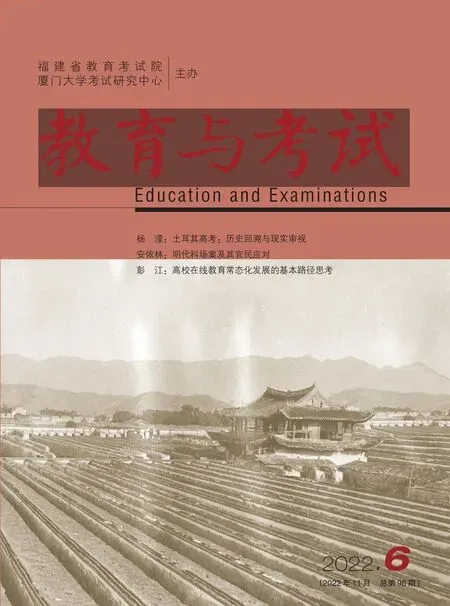進退之間:蔡元培辭職與回任北京大學校長考述
楊衛明 汪秋萍
1916 年9 月,尚在歐洲游歷的蔡元培應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之邀出長北京大學,1917 年1 月正式就任,此后直至1927 年7 月北京大學與北京其他幾所學校合并改設京師大學校,校名一度取消,蔡元培任職北京大學校長前后十年多時間。盡管他自稱在校辦事僅五年有半,卻無妨北京大學發生的舉世矚目變化,不僅成功步上現代大學軌道,在近代中國民族、國家認同上的作為亦令人驚嘆。不過,蔡元培在此期間多番請辭與回任,又頗耐人尋味。①探賾索隱,蔡元培的學術堅守與當時政治紛擾的博弈以及自身秉持的“教育獨立”理念復合而成的景觀,折射出近代中國教育變遷的曲折,也彰顯著先行者堅毅執著的品行。
一、辭職與回任簡歷
據《蔡元培年譜》《蔡元培年譜長編》及研究者的梳理[1],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的請辭及回任情形,簡列如下:

顯而易見,蔡元培在此期間的請辭,與政治紛擾息息相關。不論是因外交而生的學潮刺激,還是因復辟帝制鬧劇、教育總長越權干涉司法獨立、北京大學被迫改組而成,呈現的都是教育直面政治強權的圖景。其中,像第四次圍繞“欠薪”“索薪”而發的請辭,持續時間之久,歷經反復之多,著實令人扼腕(從《蔡元培全集》第三、四卷以及《蔡元培年譜長編》〈中冊〉的收錄與記載可知,此次事件,始于1919 年底,息于1922年9 月,在此期間,甚至包括蔡元培被打發再度外出游歷);即便是因反對講義收費而發的第五次請辭,亦反映著蔡元培對于北京大學學生以類似政治運動方式解決問題的憂慮。因為,這與他對學生,尤其是大學生的期待(首先應專注于學業)相距甚遠。換言之,政治紛擾及其所牽動的波瀾乃是蔡元培請辭北京大學校長的重要起因。
當然,頻頻請辭,又絕非一時意氣所為。蔡元培曾省思:“吾人作事,必先審其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然后定其舉止。”[2]107那么,“可能與不可能”“應為與不應為”的變換,昭示著怎樣的心路糾結呢?
二、“學術堅守”與政治紛擾的博弈
民國初年,蔡元培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身份參加由京師大學堂更名的北京大學校的開學典禮時即明確表示“大學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1917 年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中再度開宗明義:“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2]72此后,就這一話題,按他自己的說法,每一年北京大學的開學典禮上都要“講一次”。深受德國大學傳統影響的蔡元培,極力凸顯大學的學術研究職能于情于理;但在大學“學術研究”職能早已成為學界共識的情形下仍著意為之,則無疑是受刺激于當時北京大學聲名狼藉、實為“官吏養成所”這一現狀(蔡元培稱之為“著名腐敗”[2]709)。為將北京大學真正打造成“研究高深學問”的場所,蔡元培認定,唯有效仿世界各國大學通例,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2]190不論大學校園氛圍營造、系科設置,還是學校管理,都應助益于學術研究的順利開展。延聘積學而熱心的教員,是護翼大學“學術研究”主旨以及提振學術興趣的關鍵。執掌北京大學期間,蔡元培以“學詣”為標準聚集的教師隊伍,僅就“文科”底下,便有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也有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人,他們思想傾向不同,行為舉止各異,甚至相互攻訐,但無一例外均是相應領域的學術大師。一時間,北京大學校園百家爭鳴,學術研究蔚然成風。
因而,面對來自外部的政治紛擾,蔡元培的抗爭不言而喻。1917 年7 月2 日,即因張勛復辟帝制引發第一次請辭,“不意日來北京空氣之惡,達于極點,元培絕不能回北京。謹辭北京大學校長之職。”[3]57不久,又因學生反對“中日軍事協定”事件請辭,“頃本校學生對于‘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多所懷疑,元培平日既疏于訓育,臨時又短于肆應,奉職無狀,謹此辭職。”[3]293自責疏于管教,實乃關愛學生及肯定學生愛國之舉。蔡元培日后坦言:“如果學生的行為懷有良好的愛國主義信念,那么,學生是無可指責的。”[2]491故而,五四運動期間北洋政府試圖以迫使他去職作為瓦解學生表達愛國之舉的籌碼時,蔡元培的憤慨可想而知。他不僅極力營救被捕學生,且以“殺君馬者道旁兒”表達困倦之意,直至發出“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2]220-221的強烈抗議,以示決絕。
盡管如此,各方挽留,友人勸勉,加之身處政潮、學潮中的北洋政府的讓渡,尤其是北京大學全體學生“曠時廢學,惟有痛心。兢兢自守,幸無隕越。此后當益自策勵,求學救國,萬不至逾越軌范,以貽先生憂”[2]225的自省等因素疊加,又令蔡元培再度感知學術堅守的可能,遂“不容堅持初志”[2]225,于1919 年9 月再次回任北京大學校長職。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中,他深情告白:“讀諸君十日三電,均以‘力學報國’為言,勤勤懇懇,實獲我心。自今以后,愿與諸君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仆等,當共負其責焉。”[2]230
不過,這并非意味著蔡元培對于政治紛擾的無端妥協以及對于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的一味認可。
權且不論領銜北京國立八校校長發起“索薪”遭受屈辱而提請的辭呈,單就1923 年1 月17 日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獨立,致使北京大學兼課教師羅文干(時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被非法逮捕一事來看,蔡元培的憤懣可謂達到極點。“元培目擊時艱,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茍安;尤不忍于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2]454兩日之后,又特發聲明,堅辭北京大學校長職。[4]310確實,此番事件之后,蔡元培雖未能真正辭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卻也不再到校任事。胡適言及蔡元培的這一舉動,說道:“他個人因為政治太黑暗了,他的一去,明明是對惡政治的一種奮斗方法。”[5]
事實上,就蔡元培個人的自我定位而言,亦在學人角色。他表示自己在學術研究方面的興趣以及從事學術研究的意愿,強調與擔任行政官員之間的抵牾、沖突:“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愿意見的人,說多少不愿意說的話,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實在痛苦極了。”北洋政府政治上的腐敗與墮落、倒行逆施,令他極度失望,直至深惡痛絕。“這種惡濁的空氣,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2]456盡管蔡元培在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為毋庸置疑。但學術堅守,誠然蔡元培思考大學教育問題的基點。1929 年蔡元培為《北京大學三十一周年紀念刊》所做的序中,仍以“要以學術為惟一之目的,而不要想包辦一切”[2]555勸誡同仁。
由此,也就不難理會因學生反對講義收費而發的請辭。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演說中,蔡元培即諄諄告誡學習者,應當知曉“大學之性質”“為求學而來”。蔡元培后來的回憶表明,由于深受官僚習氣熏染,當時進入北京大學的學生,對于學問本身并沒有多大興趣,他們關注的是畢業及畢業之后的出路。所以,學生們對于學有所長的教員并不見得歡迎,反倒是對前來兼課且有地位的政府官員甚為推崇。“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要性,是于求學上很有妨礙的。”要改革北京大學,“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6]聘請學人,設置研究所,增添圖書資料,成立各學科學術團體以及各類學生社團等,實為應對之舉。因而,當學生再次以政治運動方式謀求問題解決時,無疑觸動了蔡元培的逆鱗。《為北大講義費風潮辭職呈》中的不滿與憂慮可見一斑,因為“此種越軌舉動”,可能“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4]270對于青年學生,蔡元培始終希望他們作為有學識的新型知識分子,尊師重教,專心致力于學術研究。事后,經教育部與北京大學絕大多數學生勸留,并開除鬧事帶頭人馮三省,蔡元培方與全體教職員工到校視事。在當日的演說中,蔡元培仍心緒難平。“爾日所要求的事,甚為微末,很有從容商量的余地,為什么要用這種蠻橫的手段,顯系借端生事,意圖破壞。”[2]444雖然,政治紛擾對于學生思想觀念、行為舉止的影響毋須諱言,但是,“大學的學生,知識比常人為高,應該有自制的力量;作社會的模范,卻不好以受外界暗示作護符。”[2]446
三、“教育獨立”的訴求及困頓
在蔡元培的視域里,學術堅守是大學生個體擴充學識、激發志趣、陶冶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學力,而養成模范人物之資格”,進而具備社會服務本領的根本依托。他列舉道,像五四運動期間那樣表達愛國情感,直接介入政治,喚醒民眾,雖無可厚非,但并非長久之計,不過“一時之喚醒”。“若令為永久之覺醒,則非有以擴充其知識,高尚其志趣,純潔其品性,必能幸致。”而像平民講演、平民夜校等可行措施所需的學識及人格積攢,“推尋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學問為第一責任也。”[2]230在《北大第二十三年開學日演說詞》中,他再次提及,“須知服務社會的能力,仍是以學問作基礎,仍不能不歸宿于切實用功。”[2]272此外,他更是欣慰地表示,五四運動之后北京大學學生觀念上的覺悟之一即是:“因學問不充足,辦事很困難,辦事須從學問上入手,不得不專心求學。”[2]305充分顯示了他對于學術堅守的篤定。
其中,借學術堅守養成的“模范人物之資格”[2]230,據蔡元培所見,尤有非比尋常的價值。“人格完備,而道德亦因之高尚矣。”[2]66蔡元培深信:“社會的各分子都具有健全人格,此外復有何求?”健全人格的標志,即是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的和諧發展。如此,才能有效感觸、接納與形成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與意識。“都能自由平等,都能博愛相助,共和精神亦發展了。”[2]265因此,民主共和時代,養成“健全人格”,實乃國民“愛國”的表征。“至民國成立,改革之目的已達,……則欲副愛國之名稱,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養成完全之人格。蓋國民而無完全人格,欲國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慮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國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謂愛國矣。”[2]75蔡元培甚至以人格陶鑄與社會服務情形反觀學術堅守的質與量,寄望學者“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2]163及端正服務社會的態度。
不唯如此,學術堅守對于民族、國家而言,則是其立足、強盛的支撐。蔡元培說道:“一個民族或國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腳,——而且要光榮地立住,——是要以學術為基礎的。尤其是,在這競爭激烈的二十世紀,更要倚靠學術。所以學術昌明的國家沒有不強盛的;反之,學術幼稚和智識蒙昧的民族,沒有不貧弱的。”[7]他還以“一戰”時期德國“力抗群強”以及戰敗后不下十年重返世界列強之林為例加以佐證。而他自己參與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積極鼓搗“留法勤工儉學”,緣由之一正是法國“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義之正大,與吾國儒先哲理類相契合;而學術明備,足以裨益吾人者尤多”[2]60;為北京大學學生爭取“庚款”留美名額,同樣出于“求國家富強,促學術發達”[2]152之故。總之,“青年們既要負起民族的責任,先得負起學術的責任。”[2]663
顯然,在近代中國“救亡圖存”場景下,蔡元培倡導的學術堅守,不僅是“純粹理性”之舉,更是融合“事功”“致用”之為,或者說,既為了促成學術發達,又指向“學術救國”的“實踐理性”。
作為學術研究重鎮的大學,在學術堅守上自然責無旁貸,任重道遠。蔡元培不厭其煩申論大學的“學術研究”歸屬,反復勸誡學習者,“在大學,則必擇其以終身研究學問者為之師,而希望學生于研究學問以外,別無何等之目的。”[2]137“能在學校里多用一點工夫,即為國家將來能多辦一件事體。”[2]513推而廣之,“一校之學生如是,全國各學校之學生亦如是,那末中國的前途,便自然一天光明一天了。”[2]514這些均是題中應有之義。
何以保障大學的“學術堅守”呢?大學內部(自身)建制自不必言(如大學評議會、教授會、行政會等的建設);外部規則(國家教育行政管理等)更加不容小覷。聯系蔡元培民國初年闡明的民主共和時代教育應恪守的“五育并舉”方針,以及此番已逐漸步上現代大學軌道的北京大學狀貌,使他更有底氣堅信“乃得有超軼政治之教育”[2]1的理路。接到李石岑的《教育獨立建議》一文后同聲相愾的“教育獨立”吶喊,道出了蔡元培的心聲。其中,教育之所以要超然于各派政黨,在蔡元培看來,那是因為二者之間步調并非完全一致。一方面,就目標與宗旨而言,教育旨在造就個性與群性的和諧發展;而政黨追求的是一種“特別”的群性,即政治信仰上的一統,及建基于此的行動一致,不容許過多的個性張揚。另一方面,就周期與時效而言,受制于人的成長規律使然,教育具有較長的周期,即“教育是求遠效的”;而政黨的政策,首先是“求近功的”,政黨更迭時,教育方針也將跟著改變。因此,若把“求長效”的教育交與政黨,教育的成效便要大打折扣。[2]377
可見,蔡元培的認知與經歷里,政治紛擾乃學術堅守之“大敵”之一;“教育獨立”訴求,則構成“學術堅守”的強勁動力。誠如有學者指出:“‘教育獨立’思潮的核心,是仿效西方‘學術自由,學校自治’的模式,力主教育擺脫來自政治的、宗教的各種牽掣,從人類傳承智能、謀求發展、完善身心的終極高度,達到某種獨立運行的狀態。”[8]
“至于強調大學相對于政府的獨立,更是蔡元培‘教育獨立’理想觀念的核心部分。”[9]導言8 蔡元培說,不但自己的興趣聚焦于高等教育領域,就教育與民族、國家的關系來看,大學教育更加涉及根本,所以“當先把大學整頓”。[2]707借鑒德國大學模式,堅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學”“術”分野、“教授治校”等規范,即是維護大學自身邊際的基本操作。由此,當政治強權干擾甚至破壞大學內部運行規范時,蔡元培的抗拒也就不言自明。“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于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么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2]220-221只是,作為政府任命的大學校長,蔡元培又著實難以將政治強權與紛擾隔阻在校門之外(因為,這原本即是教育的外部關系的固有成分)。“索薪”無果而主張的“對于北大及其他北京國立各校之根本救濟,鄙意宜與北京政府劃斷直接關系,而別組董事會以經營之”[2]467“北大校務,以諸教授為中心。大學教授由本校聘請,與北京政府無直接關系,但使經費有著,盡可獨立進行”[2]469等,更像一廂情愿。之后,“大學院”與“大學區”制試驗的曇花一現,再度證明教育不是脫離政治的空中樓閣。換言之,當二者之間變得難以調和,辭職或許也就成了最為妥帖的方式。蔡元培以《易傳》中的“小人知進不知退”反向明志:“退的舉動,并不但是消極的免些糾紛,間接的還有積極的努力”,[2]455形塑了“知退君子”的風格與作為。
四、結語
當初,蔡元培不顧多數友人勸阻,而聽從“既然知道他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算失敗,也算盡了心”[2]625-626的建議,不惜可能的聲名受損,毅然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職,從而開啟了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史的新篇章。在此期間,他奉行的“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舉動,順勢化為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新傳統。誠然,由于自身特殊經歷與特定情懷,“蔡元培心目中的大學,還與一般人眼中的大學不一樣。因為,在蔡氏而言,既有曾為教育行政首長的經歷,就必然會站在國家利益的角度來審視大學,有其通達的官場態度;而從本質上來說,蔡氏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文學者,所以其對學術的濃厚興趣,也必將制約著他對大學的判斷與思考。”[9]導言5 學術堅守的踐履、教育獨立的訴求,無疑閃爍著理想主義的光芒,盡管有著忽略近代中國學術與政治、教育與革命輕重緩急之嫌,卻無妨仁人志士的致力與執著:“國際視野”與“本土情懷”的交織,無非是要尊重教育自身固有的運行規則,極力避免因權力意志或愚昧無知而對之造成的有意無意、或顯或隱的傷害。如此,才有“健全人格”的養成,才有民族、國家的復興與振興。“知退君子”,是蔡元培穿行于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形象與格局向度。進退之間,盡顯先行者堅毅執著的品行。
注釋:
①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期間的辭職,當時即引發學界、社會的注目,胡適、陳獨秀等學人、名流的言談,道出了蔡元培的執著與抗爭;后世學者的相關研究(梁注:《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周天度:《蔡元培傳》等),再度凸顯了蔡元培堅定理想、不畏強權的高尚品格等。傅國涌、王家聲等學人的著述、編纂,還較為完整地概述了蔡元培七辭北京大學校長的史實。而婁岙菲博士從教育史視角對蔡元培1923、1926 年辭職的專題探討(婁岙菲:《蔡元培1923 年辭職原因新探》,載于《教育學報》2008 年第6 期;《蔡元培1926 年辭職事件再解讀》,載于《教育學報》2010 年第4 期),則更具深度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