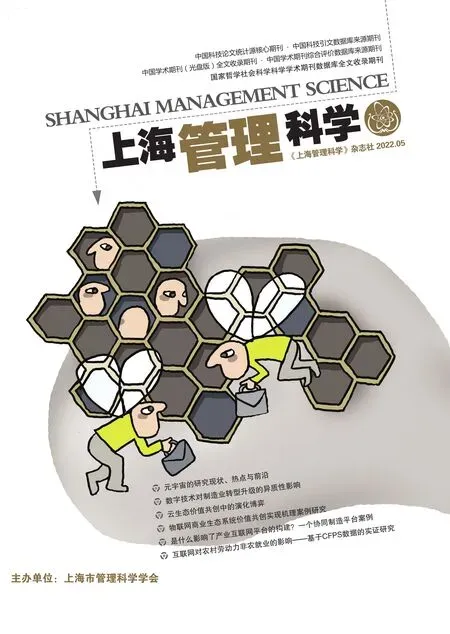環境規制和企業減排:一個文獻綜述
關 瑾 張瀚文 朱啟貴, 3
(1.上海交通大學 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30;2.上海工程技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620;3.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上海 200030)
0 引言
面對嚴峻的環境和氣候變化問題,《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建立健全環境治理體系,推進精準、科學、依法、系統治污,協同推進減污降碳,不斷改善空氣、水環境質量,有效管控土壤污染風險”。2022年1月24日,國務院印發了《“十四五”節能減排綜合工作方案》,要求“到2025年,全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比2020年下降13.5%,能源消費總量得到合理控制,化學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排放總量比2020年分別下降8%、8%、10%以上、10%以上。節能減排政策機制更加健全,重點行業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基本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經濟社會發展綠色轉型取得顯著成效”。囿于環境污染物排放的外部性,實現上述約束性目標關鍵在于政府進行合理的環境規制。但是,在長期以GDP為核心的晉升激勵制度下,我國地方政府間競爭導致公共政策明顯扭曲,其中環境治理通常首當其沖地成為被犧牲的一項地方公共職能,各地為實現經濟增長而忽視環境甚至犧牲環境的盲目做法屢見不鮮。因此,學術界對我國環境規制有效性的質疑聲也一直不絕于耳,并引發了一個充滿爭議的議題:環境規制對企業污染排放的影響是正向倒逼減排效應抑或負向綠色悖論效應?準確回答該問題既要考慮不同類型規制工具的效應差異,也要區分環境規制對企業減排的直接和間接影響。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環境規制對企業污染減排影響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主要圍繞以下三條主線展開:正式環境規制對企業減排的直接影響;正式環境規制通過綠色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和外商直接投資等中間渠道對企業減排的影響;非正式環境規制對企業減排的影響。
1 關于正式環境規制對企業減排的直接影響研究
1.1 倒逼減排效應
早期研究表明,正式環境規制能夠抑制企業污染排放,具有明顯的倒逼減排效應(Hettige et al., 2000)。近年來,隨著全球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正式環境規制能否促進企業減排再次引發關注。Shapiro and Walker(2018)指出在1990—2008年,盡管美國制造業產出大幅增加,但制造業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了近60%,并認為自《美國清潔空氣法案》(1990年修訂版)頒布以來,環境規制逐漸收緊是美國制造業污染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制造業生產率提升和貿易轉移的作用甚微。Greenstone等(2021)聚焦中國“向污染宣戰”后第一個五年(2014—2018年),研究了中國水和空氣質量的變化趨勢。在空氣質量方面,除臭氧以外的主要空氣污染物濃度在2013年達到峰值后均顯著下降,而且經濟發達且人口稠密的地區空氣質量改善幅度更大。在水質方面,除長江流域以外的地表水質量從2008年開始不斷改善,其中黃淮流域水質改善最顯著,但地下水質量在逐漸惡化。Guan等(2022)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并結合中國工業企業二氧化硫排放數據,為綠色政績考核是否加強地方環境治理提供了嚴格且全面的經驗證據。結果表明,綠色政績考核有效抑制了企業在粗放邊際和集約邊際上的二氧化硫排放。
陳詩一和陳登科(2018)采用2004—2013年中國地級市PM2.5濃度數據,考察了霧霾污染對經濟發展質量的影響。結果表明,霧霾污染對大中城市經濟發展質量的負面效應顯著高于其他小城市,而且隨時間推移霧霾污染的負面效應越來越大,并指出政府環境治理能夠有效減少霧霾污染,從而有利于助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王嶺等(2019)利用中國地級市日度空氣質量指數(AQI)以及細微顆粒物濃度數據,檢驗了我國首輪中央環保督察對城市空氣質量的改善效果。結果表明,首輪中央環保督察顯著降低了空氣質量為良和輕度污染城市的AQI和細微顆粒物濃度;與南方城市相比,中央環保督察對北方城市AQI和細微顆粒物濃度的降低效應更顯著。韓超等(2021)發現地方約束性減排目標能夠驅動企業采取清潔生產和末端處理的方式減少污染物排放,并且宏觀層面的減排效應來自存續企業之間的資源再配置而非企業進入退出。
1.2 綠色悖論效應
但是,部分學者認為正式環境規制的倒逼減排效應并不顯著,甚至可能表現為綠色悖論效應。Wang等(2018)采用1998—2007年工業企業產出和排放數據,實證評估了“三河三湖”政策對企業化學需氧量(COD)排放的影響。盡管該政策迫使許多小型污染企業退出市場,但并未對存續企業的COD排放產生實質性影響。黎文靖和鄭曼妮(2016)采用中國地級市AQI和主要經濟指標,探討了城市污染治理的激勵機制及其作用效果。當污染治理相對增長壓力更大時,各城市會迫于環保壓力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增加環境治理投資,但是增加環境污染治理并未顯著改善空氣質量。沈坤榮和金剛(2018)認為河長制提升了水中的溶解氧含量,初步緩解了水體黑臭問題。但是,其他深度污染物未能得到有效治理,反映出地方政府“治標不治本”的粉飾性治污行為。
1.3 異質性環境規制效應
已有文獻表明正式環境規制對企業減排的影響在不同時點、執法強度、產業結構和規制工具之間存在異質性。石慶玲等(2016)發現“兩會”期間城市空氣污染下降了5.7%,其中二氧化硫和細微顆粒物濃度下降最明顯,但城市空氣質量在“兩會”過后急劇惡化,這說明短暫的“政治性藍天”是以事后報復性污染為代價的。包群等(2013)采用倍差法識別地方環境立法的減排效果,并認為單純的環保立法不能顯著抑制污染排放,僅在環境執法較強或污染嚴重的省份,環保立法才能夠產生倒逼減排效應。李虹和鄒慶(2018)認為資源型城市資源、污染密集型行業占比較高,環境規制收緊對產業負面沖擊較大,因此環境規制應考慮當地經濟發展對資源行業的依賴程度。李永友和沈坤榮(2008)認為不同規制工具減排效應存在差異,其中排污收費能夠抑制污染排放,而環保補助的減排效果不佳。
2 關于正式環境規制通過中間渠道對企業減排的影響研究
2.1 正式環境規制、綠色技術創新和企業減排
關于正式環境規制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傳統觀點認為在生產技術和需求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盡管環境規制能夠有效抑制企業污染排放,但不可避免地會增加企業治理投資,擠占生產性和盈利性投資,造成潛在產出和利潤損失,從而削弱企業競爭力(Gray and Shadbegian, 2003)。通過大量案例研究,Porter and van der Linde(1995)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嚴格且設計恰當的環境規制能夠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創新補償收益可以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規制成本,從而使企業獲得更大競爭優勢,這一論斷被稱為“波特假說”。盡管“波特假說”是否成立存在較大爭議,但其首次系統闡述了環保和增長之間存在“雙贏”結果的可能性,從而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研究。國外學者首先從行為經濟學、市場失靈和組織失靈等方面構建了該假說的理論基礎。從行為經濟學角度出發,Ambec and Barla(2006)認為企業理性取決于職業經理人行為,由于創新投資會增加企業成本,現期偏好的職業經理人會延遲創新投資,而環境規制能夠抑制該行為偏好。同時,盡管理性企業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但市場失靈導致企業無法完全實現潛在利潤,其中包括不完全競爭(André et al., 2009)和非對稱信息(Mohr and Saha, 2008)等。此外,Ambec and Barla(2002)認為環境規制有助于克服組織慣性,從而降低企業創新的組織成本。
為了從經驗上驗證“波特假說”的正確性,Jaffe and Palmer(1997)將其細分為“狹義波特假說”“弱波特假說”以及“強波特假說”2。關于“狹義波特假說”,學術界普遍認為市場激勵型比命令控制型的規制工具更具減排靈活性和激勵長效性。Jaffe等(2002)認為以交易許可為代表的市場激勵型環境規制對企業環境友好型發明、創新和技術擴散具有促進作用。齊紹洲等(2018)認為中國排污權交易試點政策誘發了試點地區污染企業的綠色創新活動,并且該試點政策對綠色創新的誘發作用主要體現在綠色發明專利,而非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李青原和肖澤華(2020)認為不同的市場激勵型規制工具也會對企業綠色創新產生截然相反的效果,其中排污收費激勵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而環保補助卻擠出了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相對而言,“弱波特假說”得到了更多經驗支持,已有大量文獻表明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正相關(Popp, 2006; 黃德春和劉志彪, 2006)。但是,目前“強波特假說”仍存在較大爭議。He等(2020)認為國控斷面水質監測站數據僅反映了上游水質,與下游污染企業相比,位于水質監測站上游的污染企業通常面臨更嚴格的環境監管,從而導致上游污染企業生產率下降。涂正革和諶仁俊(2015)認為排污權交易機制有助于緩解我國二氧化硫排污權配置的低效率問題,但在短期和中長期均未產生波特效應。盡管如此,仍有學者發現了環境規制有利于提高企業競爭力的經驗證據(Berman and Bui, 2001; 陳詩一, 2010)。
2.2 正式環境規制、產業結構升級和企業減排
關于正式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眾多學者認為環境規制對產業和企業群體是一種強制性“精洗”,通過優勝劣汰驅動產業結構升級,降低“三高一低”產業比重,促進清潔生產投資和綠色技術創新,從而抑制污染物排放(范慶泉等, 2020)。由于中西部地區的環境規制強度相對東部地區普遍更低,近年來我國污染西進態勢凸顯,甚至超過了世界向中國的污染轉移彈性(Chen et al., 2018; 沈坤榮等, 2017)。童健(2016)認為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在我國東、中和西部地區均呈現J型特征,但J型曲線拐點處對應的規制強度差異較大,其中東部最低、西部最高。高明和陳巧輝(2019)則認為命令控制型、市場激勵型以及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實際效果不同,其中東部地區市場激勵型規制工具的激勵作用最為顯著,中西部地區命令控制型規制工具的激勵效應更明顯,而自愿參與型環境規制在不同地區的激勵效果均較弱。
2.3 正式環境規制、外商直接投資和企業減排
關于正式環境規制對外商直接投資(FDI)的影響,學術界圍繞“污染天堂假說”和“污染光環假說”兩種完全對立觀點展開研究,并且至今仍未得出明確結論。其中,“污染天堂假說”認為跨國公司出于節約環境治理成本等因素,傾向于向環境規制較寬松的發展中國家轉移污染產業或其生產環節,從而加劇了東道國環境污染(Levinson and Taylor, 2008; 張宇和蔣殿春, 2014)。“污染光環假說”認為跨國公司采用的清潔技術或標準會向當地污染企業擴散,從而有利于改善東道國環境質量(Antweiler et al., 2001; 邵朝對, 2021)。但是,二者之間看似針鋒相對的矛盾并非無法調和。Grossman and Krueger(1995)將影響環境污染的因素劃分三類,即生產規模、產業結構與環保技術,這說明“污染天堂假說”側重于FDI的規模效應和結構效應,而“污染光環假說”則強調了FDI的技術效應。因此,FDI與東道國環境污染之間絕非簡單線性關系,可能會呈現倒U型特征(包群等, 2010)。
3 關于非正式環境規制對企業減排的影響研究
近年來,非正式環境規制逐漸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并被認為是繼命令控制型和市場激勵型規制形式之后的第三次規制浪潮。一般而言,正式環境規制在制定、執行和監管過程中存在滯后性(Kathuria, 2007);地方政府可能會競相降低規制強度以吸引經濟要素(Li and Zhou, 2005),正式環境規制也可能會受到腐敗行為和隱性經濟影響(Oliva, 2015; 余長林和高宏建, 2015)。因而,當正式環境規制缺失或執行不力時,應鼓勵公眾參與環境治理以彌補正式環境規制的不足,這樣不僅有利于提高公眾環保意識,還能加強公眾或非政府組織機構對污染企業的監管,從而緩解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同時,Farzin and Bond(2006)則認為引入公眾參與和監督機制有助于提升環境治理效率、改善地區環境質量。早期的非正式環境規制主要是公眾通過信訪、投訴等方式直接向當地或上級政府表達自身環境訴求,政府部門通常會要求企業公開污染信息以接受公眾和市場監督,從而通過影響企業社會聲譽使其產生內在減排激勵(Langpap and Shimshack, 2010)。
在傳統媒體時代,報紙、廣播和電視成為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主要媒介,其對企業污染事件的報道有效抑制了排污行為,并顯著提升了地方環境治理效率(Kathuria, 2007)。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應用和不斷普及,網絡媒體的信息傳播優勢日益顯現,從而成為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前沿陣地。鄭思齊等(2013)分別借助谷歌趨勢和谷歌搜索工具構造公眾環境關注度指標,探究了公眾訴求對城市環境治理的推動機制。結果表明,公眾參與能夠促使地方政府更關注環境治理問題,不僅改善城市環境污染狀況,也有助于城市跨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而邁入增長和環保“雙贏”的發展階段。徐圓(2014)識別了以公眾對污染事件的關注度和新聞媒體對污染報道的透明度為代表的非正式環境規制對中國工業污染的影響,并指出源于社會壓力的非正式環境規制有利于降低工業污染排放強度,但其作用仍遠低于正式環境規制。李欣(2017)則認為以網絡輿論為代表的非正式環境規制有助于緩解霧霾污染,其中環境行政規制和經濟規制是網絡輿論有效發揮霧霾抑制效應的中間機制,而環境污染監管的中介效應并不顯著。
4 結論和啟示
通過回顧國內外相關理論和實證文獻,本文得出以下結論:第一,環境規制在促進企業減排和改善環境質量方面已被大多數研究證明是有效的,部分研究支持綠色悖論效應可能與樣本選擇、模型設定和時間跨度等因素有關;第二,執行是環境規制的關鍵環節,綠色政績考核和中央環保督查已被發現能夠提升環境治理效率;第三,企業通過生產調整、技術創新和位置搬遷等措施來應對環境規制,但企業響應行為在不同規制工具、所有制類型以及規模和行業之間具有異質性;第四,盡管公眾參與等非正式規制措施仍處于早期階段,但有限的證據表明這些措施可以顯著影響企業排放行為;第五,制度支持與環境規制同樣重要,已有研究表明監測、報告和審核等制度漏洞助長了城市和企業對排放數據的操縱行為。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本文提出了未來需要重點關注的研究方向。
4.1 聚焦地下水和土壤污染問題
目前,中國空氣和地表水質量有所改善,但地下水質量在過去十年中不斷下降,有必要對地下水污染的成因、后果和政策選擇進行探討。同時,工農業活動所導致的土壤污染日益加劇,但鮮有經濟學研究關注我國土壤污染問題。
4.2 探索異質性企業對環境規制的應對機制
在空氣污染情形中,企業可能會同時受到空氣、能源和氣候等政策的影響,異質性企業如何應對環境規制有待商榷,未來研究應注重考察不同環境政策之間的協同作用和沖突之處。此外,企業所有制類型(特別是國有屬性)對環境績效的影響尚不明確。
4.3 注重地方環境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
迄今為止,大多數研究僅強調了環境規制的減排效應,但鮮有研究關注地方環境治理的成本收益和效率分析。盡管已有研究表明地方官員已采取大量措施確保達標排放、防范數據操縱,但缺乏對這些行動意愿和成本的正式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