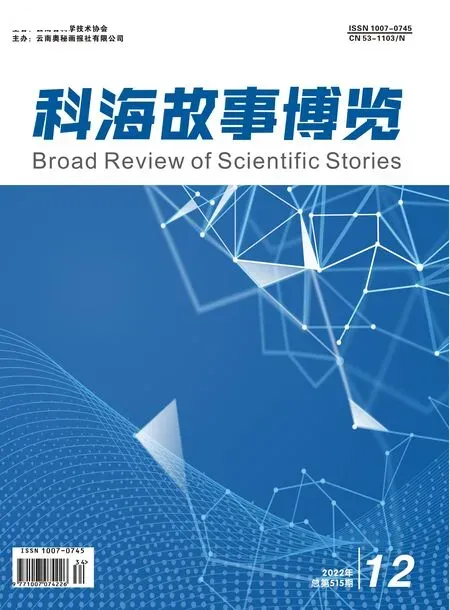一行與埃拉托色尼大地測量比較研究
韓嘉偉 鄧可卉
(東華大學,上海 200051)
在我國唐代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 年—公元741年),我國著名的天文學家一行(公元683 年—公元727 年),本名張遂,組織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大地測量工作。不僅對我國當時歷法工作的修訂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更為有價值的是提供了實測數據,進而否定了我國歷史上流傳將近八百年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錯誤理論,第一次算出了相對精確子午線一弧度弧長的長度。[1]
公元前200 多年,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圖書館管理員的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約前275年—前194年),埃拉托色尼已知同一子午線兩地之間的距離,再計算出這兩地相對地心的夾角,進而第一次推算出地球的周長。由此創立了地理學這一名詞,被西方地理學家們稱為地理學之父。
雖然一行測量的是地球子午線一弧度長度,而埃拉托色尼計算的是地球周長,但二者在測量與計算中其數學邏輯以及天文思想存在著諸多異同。
1 測量的目的及其背景
從當時的歷史背景角度來看,一行之所以成功地發起了這次對天文學進行的測量,主要有下列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為了修訂歷法。根據《舊唐書》的記載,唐玄宗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太史頻奏日食不效”“言《麟德歷》行用既久,晷緯漸差”。[2]一行已經發現,對于不同的觀測地點,不同節氣的日影長度和漏刻晝夜分差也不相同。一行深知這個現象在以前的歷法中并無提及,要想搞清楚其中的原理,必須進行實地測量。
第二,用實測數據否定古人“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錯誤說法。其實在之前劉焯(公元544 年—公元610年)就意識到“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3]我們通過一行主持的測量的方法和地點上,可以大致推斷出一行是采納了劉焯的建議,為了實現劉焯的計劃,實際驗證“日影千里差一寸”說法的謬誤。
而早在西方的古希臘時期,人們對地球是什么樣的形狀眾說紛紜,一部分人們認為大地是平狀,還有一部分人認為大地是球狀,但并沒有很好的證明方法。到了公元前三世紀左右,古希臘著名自然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才正式提出地球是球狀的觀點,并提出了相關的證明方法,激發了埃拉托色尼等諸多學者對地球的探索的興趣。埃拉托色尼是亞歷山大城遠近聞名的學者,據說為埃及君主尤厄格茨(Euergetes)聘請他擔任王子費羅派托(Phllopator)的宮廷教師,之后被任命為亞歷山大城圖書館館長。由于此圖書館匯集了當時最豐富的古埃及、古希臘各個學派的科學著作,使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科學研究中心,埃拉托色尼在此博覽群書,擁有了相當先進的天文學,數學理論,在其著作《地球大小的修正》里介紹了精確測量地球圓周的科學方法。埃拉托色尼在圖書館的古籍中發現,每到夏至的時候,太陽光都會射入這口井中,“這口井有25 尺深,螺旋形的階梯一直延伸入水中。據說在夏至日的中午太陽光會恰好照亮井水,而不在井壁投射一點陰影”。[4]根據陽光照射到井底這一現象,埃拉托色尼得出結論,塞恩城地處北回歸線上,而亞歷山大城很巧合地恰好與塞恩城同處一條子午線,由此埃拉托色尼萌生了測量地球周長的想法。
由于一行與埃拉托色尼對于大地測量的目的與背景的差異性,導致二者產生了不同方向的啟發與影響。一行耗時四年的大地測量,除了否定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錯誤理論,進一步肯定了修改歷法的必要性以外,還為修訂新歷法提供了寶貴的測量數據。一行《大衍歷》較為準確地描述了太陽的運動規律,也使得一行認識到在小范圍空間內所認定的知識,不能盲目地認為可以應用到任意大范圍空間,這與埃拉托色尼剛好相反。
埃拉托色尼推算地球周長實驗是前無古人的,利用已知的數據僅僅利用兩個距離不遠的城市推算出地球的周長,是運用數學、地理計算思想在小范圍空間拓展到大范圍空間的一個成功的實驗。這也使得埃拉托色尼貢獻了另一項重要的科學成就:第一次根據經緯線繪制出了世界地圖,開創了利用經緯線描繪地圖的正確使用方法,讓人們更進一步地認識地球。
2 測量過程
一行的測量過程是十分浩大的。一行帶領的測量隊所勘測跨度極大,北到鐵勒,南達林邑,遍歷朗州武陵、襄州、太原府和蔚州橫野軍等十三處,分別測量了當地冬夏二至、春秋二分的日影長和北極高。同時,據《舊唐書》記載,“自丹穴以暨幽都之地,凡為圖二十四,以考日蝕之分數,知夜漏之短長”,可知當時還把測量結果繪制成圖。[5]
在這次測量中,一行借鑒了劉焯的計劃,以中原平地為中心對四個地點進行多方面的測量,分別用八尺之表同時測出春秋分、冬夏至的日影長度與其北極高。[6]所選取的四個地點分別是上蔡(今河南省駐馬店市上蔡縣)、扶溝(今河南省周口市扶溝縣)、浚儀(今河南省開封市)、白馬(今河南省安陽市滑縣)。[7]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個地點的選取極為巧妙,四個地點幾乎處于同一經度,且地勢相對平坦,海拔也相差不大,使得測量數據的對比起來更加準確,與劉焯的建議完美匹配。最后根據一行的計算,從圭表上看,相差一寸,并不是相差一千里,而是只有二百五十里左右,由此第一次用實證推翻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錯誤理論。
而在公元前200 多年前,埃拉托色尼住在亞歷山大港,在其以南的塞恩城(今阿斯旺),發現一口井,每到夏至的正午時刻,太陽光總能直射入井中。埃拉托色尼的想法與中國傳統的圭表側影相同,此時正值夏至正午時刻,太陽光直射北回歸線上,那么位于北回歸線上的賽恩城則是被太陽光直射,他用一根棍子插在井口旁,棍子并沒有陰影。同一時間,在亞歷山大港進行同樣的操作,棍子出現陰影,運用簡單的幾何學原理測得太陽光與棍子的夾角為7.2°,再利用平行線同位角的原理,7.2°就是亞歷山大港和塞恩城相對于地心的夾角。[8]
當時的埃拉托色尼認為亞歷山大港和塞恩城處于同一條經線上,然而事實上塞恩城在亞歷山大港以東3°的地方,這就造成了一部分的計算誤差。埃拉托色尼最終得到的角度約為7.2°。[9]這兩個城市之間,有一條古代的通商大道,往來的商人駱駝絡繹不絕,長期經驗得知兩地的距離是5000 希臘尺。
由此易得,地球的周長=5000×50=250000 希臘尺=39816 千米。與當今所測得赤道周長40075.13 千米相差無幾。[10]在測量儀器并不精密,測量方法也并不先進的2000 多年前能夠測算出如此接近現代實際的測量數字,相當了不起。
不少學者對埃拉托色尼地球周長測量實驗中的賽恩城與亞歷山大城之間的距離精度提出了質疑,認為在兩千多年前的測量手段和測量工具是不發達的,難以想象單憑來往商人的“道聽途說”就可以獲得如此精確度的數據。實際上,由于尼羅河常年遭受水災,導致了周圍的道路經常遭到破壞,為了保證國家的土地劃分以及邊疆劃分的合理性,進而來避免不必要的沖突,人們需要不定時地進行大地測量工作,所以當時人們已經積累了比較成熟的測量知識,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埃拉托色尼對地球周長計算之精準奠定了基礎。[11]
3 測量計算比較分析
一行組織這次測量更重要的就是為了求出同一時刻北極高差一度的兩地的地面距離,這實際上已經為進一步正確認識地球的大小提供了實測根據。但當時受限于世界觀的認識,中國古代并沒有意識到地球是一個球體,再加上一行在主持這場聲勢浩大的測量的兩年后,年僅44 歲病逝。所以我們不能說一行測算出子午線一弧度弧長,就差一步計算出地球的周長,實際上我國古代對于地球的認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行打破了錯誤的傳統研究方法,并主張需要用實測數據去推斷其原理,“凡日晷之差,冬夏至不同,南北亦異,而先儒一以里數齊之,喪其事實”,[12]一行在此次測量的四個地點都準確地測量北極高度,把工作重心放在北極高一度之差的情況下地面兩點距離的測量,由此可以明顯推斷出一行已經在研究北極高與地面距離之間的關系。
若將一行所測的一弧度弧長351 又80/300 里,即155 千米,再將其乘以360 得到地球周長為55800 千米。若以一千年后法國的讓·巴蒂斯特·約瑟夫·德朗布爾(Jean Baptiste Joseph Delambre,公元1749 年—公元1822 年)較為精確的子午線一弧度來計算,則得到地球的周長為39960 千米,與現代地理學中的地球周長相差不大。
而公元前200 多年的埃拉托色尼,是建立在亞里士多德關于地球是球體的假設下,自然萌生了測量地球周長的想法,從一開始就比一行的目的動機更加純粹。埃拉托色尼的周長求解思路在當時看來是極為正確的,但仍存在著不少漏洞。
首先,埃拉托色尼假定兩地都處于同一子午線上,而事實上,塞恩城與亞歷山大城并不處于同一條子午線上,而是存在著3°左右的偏差。直到17 世紀人們才進一步認識到地球并不是一個完美的球體,那么埃拉托色尼根據有著3°偏差的塞恩城與亞歷山大城所計算而來的周長必定偏大。其次,塞恩城實際上是在北回歸線以北,埃拉托色尼單憑肉眼觀察到太陽光直射入井底就推斷塞恩城位于北回歸線上是不嚴謹的,畢竟人的肉眼始終無法觀測到微小的偏差。最后,埃拉托色尼這次測量的嚴重缺陷就是缺少兩地距離的實測,只是來往商隊的“道聽途說”的經驗主義。盡管所算地球周長在當時較為準確,但缺乏了實測數據,甚至可以說,這樣的數字是缺乏科學上的嚴謹性、精密性。雖說埃拉托色尼地球周長計算實驗存在著不少的漏洞,但毫無疑問,埃拉托色尼是用弧度求解地球周長第一人,是第一個求解出地球周長的科學家,也可以說是測算出子午線一弧度弧長的第一人。
反觀一行并不僅僅停留在“頭腦風暴”,而是一位“實干家”。所經之地連起來相當于一條超過23°的子午線弧,從南至北約2500 千米。測算得出了相對精確的子午線一弧度弧長,直到一千年后才被法國的德朗布爾進一步精確。一行所組織的耗盡四年時間的測量計算,得出了較為精確的子午線一弧度的弧長距離,同時為后世給出了精準的實測數據和測量方法,為《大衍歷》提供了數據支撐。值得一提的是,一行所主持的大地測量工作所選取的四個地點,幾乎在同一經度,這也是我國古代天文學家中第一次蘊含著地理經緯度的思想。[13]就所產生的科學價值而言,一行的影響更加深遠。
4 總結與討論
一行與埃拉托色尼在測量和計算上有諸多的相似之處。二者都是基于子午線的一弧度弧長所展開的跨時空的“較量”,但其背景、目的、方法、意義都大相徑庭,但毫無疑問的是二者都為科學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為天文學、數學、物理計量學、地理學提供了寶貴的數據和思路,讓人們更進一步地認識了地球。
埃拉托色尼對地球周長推算的起因,似乎更像是一種興趣,他敏銳地觀察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通過已知數據巧妙運算出地球周長這么一個龐大的數字,極大地推動了古希臘地理學的發展進程,其蘊含的天文學、數學、地理學思想,啟發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者。但始終缺乏實測數據,被很多人認為其數字之精確充滿了偶然性。
反觀一行,雖然測量子午線一弧度并不是此次聲勢浩大的大地測量任務的根本目的,但無論從測量的方法,測量地的選取,測量的儀器等都相當具有科學性,僅在四年時間里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果,堪稱天文學大地測量工作的典范,并用實證數據否定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錯誤理論,同時為《大衍歷》的制定提供了準確的數據支撐。由于我國古代天文學家直到明末清初在“西學東漸”背景下才逐漸認識到地球是球體,所以一行所測算的子午線一弧度弧長的數據,顯然不能說一行差一步推算出地球周長,中國古代天文學家對地球的認識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行與埃拉托色尼的方法論差異,恰恰也是中西方古代科學思想的差異。西方對待科學的態度往往都是從哲學思辨開始的,很多西方古代的自然哲學家去潛心鉆研大自然的規律往往都是出于興趣使然,埃拉托色尼測算地球周長亦是如此。而中國古代科學思想對待科學理論的態度往往是“經世致用”,所研究的學問一定要有所用,所以中國古代的科學知識大多是經驗的、實際的,一行所主持的浩浩蕩蕩的大地測量是對此的一個很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