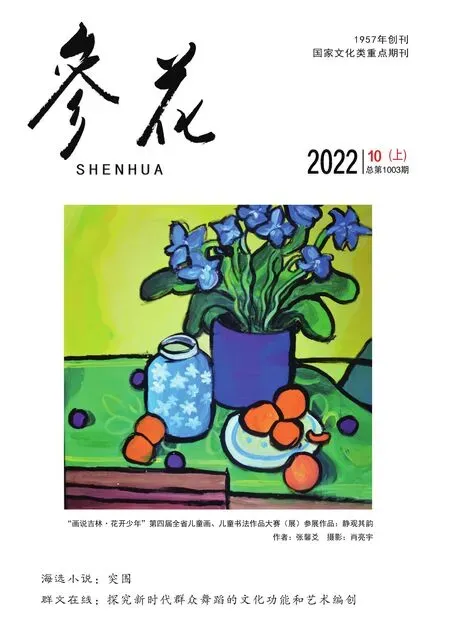手風琴樂曲改編與創作技巧淺析
◎孫藝楠
手風琴自從傳入我國伊始,就以其獨特的音色及演奏技巧引起眾多音樂愛好者的青睞。經歷了百余年的長足發展,手風琴樂曲也同我國的近代歷史與文化相互交融,變得密不可分。在此背景下,結合手風琴的音色特點,將中華民族文化的內涵賦予手風琴樂曲的改編與創作中,實為新的發展路徑。手風琴樂曲的改編與創作通常具有一定的技巧,只有深刻理解手風琴的表現手法,才能夠編創出一部優秀的作品。
一、手風琴的表現手法
(一)展現動態
作曲家只有以樂器為媒介,將自己作曲時的情感波動、所思所想進行藝術化處理,繼而通過音樂語言進行表達,才能夠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充分發揮樂器的價值。以獨奏呈現的手風琴演奏,單聲部旋律優美,而合奏時又能夠利用其模擬性出色的優點,為聽眾帶來豐富的聽覺體驗。不僅如此,手風琴的琴鍵部分與風箱部分的緊密配合,又能提高樂曲的層次感,得以用音樂來展現動態的畫面,使本就飽滿的手風琴演奏更上一層樓,給人以“身臨其境”的體驗。
以作品《牧民歌唱》為例,樂曲要求演奏者以靈活的指法對馬蹄交錯的意象進行展現,局促的旋律兼具節奏感,使人不禁聯想到山陰下廣袤牧場中奔跑的駿馬,演奏者的演奏力度又為樂曲賦予生命力與力量感,以音樂的形式呈現出極為生動的畫面。[1]
(二)塑造人物
如何僅憑有限的聽覺語言,塑造出形象豐滿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是樂器樂曲創作中的難點,感染力與共鳴感是作曲家要把握住的重點。通常情況下,作曲家會使用急促的旋律、較快的節拍來表現作品人物憤怒、激動、緊張或歡快的情緒,使用慢節拍、舒緩的旋律來表現作品人物悲傷、放松等情緒。這些人物情緒的表現手法通過了實踐的檢驗,能夠引起聽眾情感上的共鳴,因此便成了樂曲創作中的重要規則。相較于其他樂器,手風琴琴鍵與風箱的共同作用,能夠更為豐富、多層次地表達出作品人物的情緒,使人物形象更加飽滿,演奏更具畫面感。
以《白毛女組曲》為例,演奏中手風琴抖風箱與裝飾音的協作,提高了樂曲的層次感,既表現出了曲中人物喜兒的悲傷情緒,又表現出了她對仇人的憤怒情緒,一上一下、一左一右的表現方法,為人物賦予了生命,將角色復雜的思緒展露無遺。
(三)描繪自然
自然景觀也是樂曲創作中的優秀素材,相較于其他樂器,手風琴在描繪自然時,具備明顯的優勢。“寓情于景”“寄思于情”是音樂創作的主要手法,對自然場景的表現直接影響了作曲家情緒傳達的有效性,也是決定此樂曲能否引發聽眾共鳴的重要因素。手風琴演奏中,琶音、顫音的應用,能夠模擬出極具自然感覺的音色,使樂曲能夠描繪自然,極富畫面感。
以作品《牧民歌唱》為例,在樂曲前奏中,鍵盤上單音、和弦,主音、屬音之間的相互轉換,加之頓風箱的技巧使用,逐漸加快的節奏暗示著樂曲的高潮即將到來,而后主和弦的轉位將全曲帶向高潮,描繪出太陽升上天空、照耀廣袤草原的壯美畫面。
(四)模仿聲音
手風琴的擬聲能力很強,能夠模仿出多種樂器的聲音。因此,在樂曲中,手風琴的表現風格也多種多樣,不同樂器的不同音色能夠同時出現在手風琴樂曲中,為聽眾帶來豐富的體驗。[2]在樂曲創作中,對自然聲音的模擬能夠提升樂曲的張力,豐富旋律的層次感,取得極佳的表現效果。
二、手風琴樂曲編創的時代背景
手風琴樂曲的改編與創作要結合當下的時代背景,不能脫離現實,只有這樣,才能夠編創出“叫好又叫座”的優秀作品。
(一)我國群眾的需求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民眾對文娛生活的質量也愈發重視,依托信息技術得以發展的各類文化產品數量及種類與日俱增。相較于具備一定上手難度的樂器演奏,民眾似乎更喜歡“快餐化”“碎片化”的文娛形式,這也就意味著本就小眾的手風琴藝術的影響力也在不斷降低,人們對手風琴樂曲的認知范圍也在不斷縮小。在部分影響力較大的手風琴樂曲中,相較于俄羅斯風格的樂曲、法國的華爾茲、拉美的探戈,具備民族風格的手風琴樂曲則愈發稀少。
(二)當下的時代思想
脫離時代內涵的藝術作品注定難以滿足大眾對文娛的需求,因此,如何創作出滿足群眾需要,契合時代主題的樂曲,是每位作曲家應當關注的重點。如若作曲家一意孤行,沉浸于自己的小世界,不顧現實需要,那么他創作出的作品也不會是一部影響力較強的作品。[3]手風琴自其傳入我國起,一直以“大眾樂器”的身份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中,廣大創作者要“以人為本”,將手風琴樂曲的改編與創作下沉于生活中,避免將手風琴藝術“束之高閣”。
了解民眾喜好,把握時代精神,是手風琴樂曲創作者應當具備的基本素養,無論是拉美探戈,還是法國華爾茲,無論是俄羅斯音樂,還是民族樂,創作者都應當理解并掌握不同風格樂曲的創作技巧,才能夠適時作出改變,滿足人們對手風琴樂曲的現實需求。
(三)俄羅斯文化的影響
手風琴藝術于20世紀在俄羅斯得以長足發展,俄羅斯音樂低沉優美的特點契合了手風琴豐富的表現形式,手風琴藝術也逐漸融入了俄羅斯文化中,同時,具備俄羅斯音樂風格的手風琴樂曲創作技巧也逐漸流入我國,對我國手風琴作品的編創產生了重要影響。
俄羅斯藝術家深耕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并存的音樂創作,以保留文化傳統作為基礎進行手風琴樂曲創作,樂曲中通常充斥和聲,深沉婉轉的旋律極具感染力,能夠引發聽眾的共鳴。因此,在中老年段的音樂愛好者中,帶有俄羅斯文化要素的手風琴樂曲頗受歡迎。
以作品《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為例,經過了半個世紀的考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仍作為經典樂曲于大眾中廣為流傳,樂曲中傳達出的對美好事物的熱愛跨越了地域、語言的阻礙。
(四)傳統文化的融入
近年來,隨著我國綜合實力的增強,中華傳統文化開始走向世界,于國內也掀起了開發中華傳統文化的浪潮。在年輕人中,極具傳統文化色彩的漢服、弦樂也逐漸成了“流行”的代表,傳統文化元素也得以融入手風琴樂曲的創作中。
以民歌、器樂為主要形式的傳統音樂,與手風琴豐富的模擬形式契合度較高,手風琴不僅能夠很好地模擬出傳統器樂的音色,還能對民歌中的情緒準確地表現與傳達。[4]因此,在作曲家的不斷探索下,改編自傳統民歌器樂的手風琴樂曲開始流傳,并逐漸在人們的文娛生活中占據一定的地位。
三、手風琴樂曲編創的技巧
從創作角度出發,相較于鋼琴、提琴等樂器,手風琴的音樂作品較少,這是由于手風琴的誕生時間較晚,文化底蘊不足,且作曲家對手風琴創作技巧的積累不足。要想改變現狀,僅憑少數人的努力是不夠的,因此,筆者建議大家先從手風琴樂曲的改編入手,待深刻了解手風琴的價值功能、表現形式后,再進行作品創作。
從改編角度出發,手風琴與傳統樂器——笙的發聲原理相似,手風琴是利用風箱的起伏變化帶動氣流震動簧片發聲。與鋼琴相比,手風琴較小的體積適合室內外等諸多場合進行演奏;更為豐富的表現形式使其既能夠滿足西洋樂器配合的需要,又能夠參與到民族器樂的演奏中;強大的擬聲能力使其能與各種電音相配合,具備流行色彩。
手風琴多樣的表現手法與靈活的演奏方式,使其能夠不局限于原創或改編的任何一種創作形式,形成獨特的編創技巧。
(一)忠于歷史背景
手風琴樂曲的誕生均與非凡的時代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手風琴樂曲也能夠呈現出當代的民生、社會、文化等特征,這些特征的存在豐富了手風琴的內涵,使手風琴樂曲成為記錄歷史的絕佳媒介。隨著時代的演進,如果恪守傳統的手風琴演奏形式,忽視時代內涵的賦予,那這樣的曲作勢必會被時代所淘汰,不為大眾所接受。以我國20世紀50年代的手風琴作品為例,當時的手風琴樂曲多帶有激昂的旋律、起伏較大的節奏,能夠充分反映時代特色。
除了固定的時代背景外,手風琴樂曲也能夠反映作曲家的個人風格,樂曲是一面鏡子,將每位作曲家的人生境遇記錄下來,聽眾不僅能夠享受音樂帶來的聽覺體驗,也能夠品讀作曲家的百味人生。
以作品《打虎上山》為例,這首曲本為豫劇的伴奏曲,經過了楊智華先生的改編,獨創性地融入了抖風箱的技巧,成為經久不衰的名曲,曲中激昂的旋律也將楊先生的探索精神、創新精神展現無遺。
只有切實地感悟作品的時代背景,了解作曲家的生平經歷,才能夠對作品產生共鳴,使對作品的適時性改編成為可能。[5]相對的,作曲家只有擁有豐富的情感體驗,對時代精神有著深刻理解,才能夠創作出優秀的手風琴樂曲。
(二)獨創演奏技巧
演奏技巧實為樂曲的核心,也是手風琴樂曲編創中的重要部分,是評價樂曲優秀與否的重要標準,也是作品的靈魂所在。演奏者扎實的功底能夠將自己的情緒完本體現,在整體上把握樂曲節奏,在微觀上注意到音符的和諧與否,優化作品的聽覺體驗。
以《顫抖的樹葉》為例,樂曲全篇大量充斥對抖風箱與輪指技巧的使用,呈現出樹葉顫抖的畫面,在演奏的過程中,抖風箱的手臂要用力沉穩,司職彈鍵的手指也要靈活,做到發音清晰有力,不可產生粘連感,破壞樂曲整體的聽感。任何技巧絕非一日之功,大量的演奏練習不可或缺,只有在熟練掌握手風琴的演奏技巧后,演奏者才有資格進行樂曲創作,為樂曲賦予個人演奏風格,使之成為具有“靈魂”的藝術作品。
但倘若作曲家忽視了樂曲對聽覺語言的傳達,僅是一味追求華麗的演奏效果,追求絢麗復雜的指法功夫,可謂本末倒置,一旦以“炫技”作為重點,無論演奏水平如何高,也不可能成為廣為流傳的有內涵的經典作品。
(三)體現人文修養
手風琴作為一項樂器,作曲家審美能力的強弱自然會對其作品產生影響,優秀的作品一定能夠具備極強的聽覺美感,也能夠體現作曲家對更高層次的美的追求,而被大眾打上“庸俗”標簽的作品,也會暴露其作曲家審美趨向需要改變,文化素養需要提升的事實。
人文修養包含了人文知識、精神、情懷等,是一個人的表達能力、共情能力的重要體現,其作品也自然能夠體現出其個人優勢,理論基礎豐富的作曲家,其樂曲結構嚴謹,情緒的藝術化處理標準;而共情能力更強的作曲家的樂曲情感細膩豐滿,演奏聲音具有穿透力與共鳴感,能夠直擊靈魂,也能為聽眾帶來“余音繞梁”的豐富體驗。
相對于通過學習就能獲得的演奏技法與對時代背景的充分了解,人文修養重在作曲家的日積月累,脫離編創作品的單一環節,從全局視角出發,“以人為本”的感性的音樂藝術,又怎能不注重作曲者對美的追求,對完善的自我追求呢?在編創作品之前,作曲家應當考慮:我的作品想傳達給聽眾怎樣的情緒?我想如何展現自我?待心里有了準確的答案之后,再著手進行作品的編創也不遲。藝術源于生活,充實的人生經歷、豐富的人文知識會為作曲家帶來豐富的觀點與創意,創作者要拓寬視野,將目光從音樂藝術領域放大至生活體驗的方方面面,只有源于生活、忠于現實的作品,才能引起大眾的共鳴。
(四)融合傳統器樂
傳統文化之于手風琴藝術中的體現形式相當豐富。以曲作風格為例,傳統文化中關于傳說故事、人物歷史、民俗文化的元素都可以成為手風琴樂曲編創的素材。從現實角度出發,這些元素經過了歷史的考驗,于民眾中流傳已久,融合了這些元素的手風琴曲作也更容易為大眾所接受;從內涵角度出發,傳統文化經歷了五千年的發展,具備濃厚的歷史底蘊,這些元素的使用會為手風琴曲作賦予文化內涵,使其具備流行特征的同時,兼具東方文化的獨特魅力。
以曲作旋律為例,我國傳統器樂多以單旋律為主,手風琴的和聲演奏能夠突出旋律的和聲性,在強調情緒表達之處能夠通過單音配以和弦的形式賦予樂曲生命力與流動感,使傳統樂曲更加豐富立體。
在手風琴樂曲的編創中,我們要充分結合傳統文化的優勢,用深厚的文化底蘊填補手風琴樂曲編創題材的空白,形成獨具風格的手風琴藝術體系。
四、結語
手風琴具有結構簡單、演奏方便、擬聲能力強等優點,靈活多變的演奏技巧為其提供了更多的舞臺,但現階段我國手風琴樂曲的數量與質量略顯不足。相信廣大音樂愛好者能夠通過不斷的探索,為手風琴藝術賦予活力,為傳統文化的傳播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