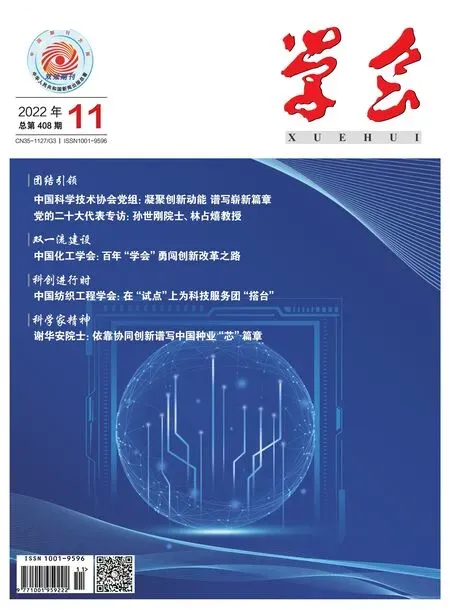謝華安院士:依靠協同創新譜寫中國種業“芯”篇章
本刊特約記者 茉莉
在我國,80%的人吃的雜交水稻都是謝華安的“汕優63”。謝華安身上有很多標簽:中科院院士、植物遺傳育種學家、福建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他現年81歲,雖年事已高,卻依然經常頭戴草帽,腳踩泥巴,活躍在田間地頭,追夢萬里稻香。
謝華安多次跨越育種的“禁區”,傾力讓百姓碗盛滿中國飯。他多年如一日,關注、關心百姓的飯碗,這背后有哪些原因,又有哪些故事?帶著一系列問題,《學會》雜志特約記者面對面對話謝華安院士。
不怕吃苦為了“做有用的科研”
提及水稻育種,謝華安首先強調的是糧食安全問題。“提高糧食安全綜合生產能力,既要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更要藏糧于庫。”他說,糧食安全的基礎在種業,種業是農業的“籌碼”,但糧食產量再高,也要面對兩三年后的陳化問題。陳化導致種質下降,還可能導致生產的糧食不宜食用,這是一個十分現實的難題。
這是一筆大賬,它算出了數額巨大的經濟損失。它甚至關乎國家的糧食安全。
作為水稻育種專家,謝華安深知良種創新對保障糧食安全的重要意義。他說:“糧食安全的基礎在種業,只有保存好這些種質資源,我們才能進一步地去發掘有利的基因。”
正是因為謝華安積極推動種業創新發展,才讓饑荒成為一代人遙遠的記憶。
他回憶說,自己是餓著長大的。在家里,母親已經把水燒開,在外奔走的父親卻還沒有找到糧食,這是常有的事。外婆臨終前的愿望,就是能喝上一碗稀飯。
這些難以磨滅的童年經歷,賦予謝華安質樸的品質和務實的作風,也讓他對科學家吃苦耐勞、不畏艱險的“精神密碼”有了更深的理解。正是因為有這么多的思想積淀,使得他在海南開展水稻種植實踐與研究時,冒酷暑戰高溫,不叫一聲苦。
彼時,環境艱苦,條件落后,10多個人在生產隊的倉庫里擠通鋪睡覺,每晚與農機、稻谷、柴油、農藥、化肥為伴。吃苦,成了謝華安科研工作的日常。
受苦為了什么?為了“讓大家有一碗飯吃”。這是謝華安最樸素的愿望。
“年輕人搞科研,一定要有愛國的精神,要有吃苦耐勞的精神,要有團結協作的精神。”謝華安說,科技人員要做與民生需求匹配、與世界接軌的科研。在此基礎上,要勇于創新,做有用的科研。

謝華安談到了一件事。那是1975年,他率隊到海南尋找第一批雜交水稻親本,看到田間大面積水稻得了稻瘟病。他敏銳地意識到,這一代的水稻不抗病。此后,他意識明確,沿著抗病的方向搞研究。
“不抗稻瘟病的水稻,在生產上是沒有生命力的。”他不辭辛勞,就是要“做有用的科研”。
謝華安還有一個“反其道而行之”的科研巧思。“別人搞科研,用的是最好的品種來做測交的親本。我的創新點在哪里?我用最差的,就是可恢復性差、配合力差的不育系測交。”他想,能跟最差的雜交,還怕跟優質品種配合不好嗎?
這就是“勇于創新”。
為努力守護農業的中國“芯”,謝華安院士對種業科研人員提出希望:不僅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雄心壯志,更要有在科研上永攀高峰的創新思想。
用“麻花理論”推進種業“四性”攻關
在謝華安看來,根據現代種業發展的要求,種業科技攻關的下一步目標,是兼顧豐產性、優質性、抗病性和廣適應性四大特點,培養出綜合性狀優良的超級水稻。
如何理解“超級”二字?謝華安解釋道,豐產性要求提高作物在單位面積的產量;優質性則要求作物檔次更高;提高抗逆性,增強作物抵抗災害的能力,能減少化肥農藥使用;高適應性品種能讓農業生產操作更簡單。
種了大半輩子水稻,謝華安對水稻的“脾性”摸得很透。他特別提到“汕優63”品種。這是他經過無數次雜交試驗,于1981年育成的抗病新品種。經過5年制種技術研究、南方稻區試驗、中晚稻區試驗后,到目前已累計推廣近10億畝,增產糧食700多億公斤。
“這就是集‘豐產性、優質性、抗病性和廣適應性’于一體的水稻品種。”但謝華安并不滿足,他期待有更好的品種取代它。
“農民種田不僅要高產、高效,還要品質好、抗性強,盡量減少因為病蟲害的發生而影響產量,從而提高收入。”謝華安說,現在早已經不單單關注產量,只有把“四性”綜合在一起的“超級品種”,才是生產最需要的品種,也最能贏得農民們的歡心。

謝華安認為,在水稻育種方面,應當具備戰略眼光,像培養領軍人才一樣培育超級品種。“無論是動植物,還是微生物、食用菌,培養單一的優點不難,把‘四性’綜合在一個水平上,培養這樣的‘領軍人才’難度最大,培養出來的才有最高的水平。”
這引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如何運用科技手段,培育此類“超級品種”?
謝華安提出“麻花理論”,即構建學科交叉深度融合的攻關體系。“就像DNA雙螺旋構型,似麻花狀繞一共同軸心,圍繞關鍵育種目標,加強資金、種源、技術、人才等種業要素聚集,培育育種協同創新生態,高質量推進育種聯合攻關。”
“‘明恢63’正是運用‘麻花理論’聯合攻關之下誕生的。”謝華安說。
早在上世紀80年代,謝華安就帶領團隊,選育出抗稻瘟病、強恢復力、高配合力的恢復系“明恢63”。后來的雜交水稻良種“汕優63”,正是以“明恢63”為親本選育出來的。
“明恢63”的父母本,選用的是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的水稻品種IR30和引自圭亞那的圭630。“前者是江西市宜春市農業科學研究所的一名同志給的,后者是莆田市農業科學研究所的一名同志給的。”謝華安談到,“汕優63”選育的成功,不是一個人的功勞,不同學科之間互相滲透、互相促進,為選育優良品種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謝華安說,育種已經進入高技術時代。它的綜合性、系統性、工程性非常強,更需要在跨學科、跨技術的高度上融合創新、合力創新。只有這樣,才能讓育種更有價值,才更能調動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促進創新要素快速流動。
“如此,才能將原來單打獨斗的科研模式向多學科、多單位協同創新轉變,發揮多方的優勢和力量,不斷地提高種業自主創新能力。”謝華安說。
建設種業強國需要健全創新體系
種子是農業的“芯片”。自2013年中國首次提出“建設種業強國”以來,“提升種業自主創新能力”屢屢成為中央一號文件的關鍵詞。黨的二十大對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作出戰略部署,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行動指南。
良田、良種、良法、良機才能有良品。建設種業強國,需要各方努力,需要健全創新體系。

謝華安和福建省龍巖市中小學生一起收割稻子,給孩子們上了一堂特殊生動的勞動課

在三亞水稻國家公園國家南繁水稻科研育種基地,謝華安院士仔細查看水稻長勢情況
“包括南繁硅谷等創新基地在內,越來越多的地方提出打造中國‘種業硅谷’,福建省也肩負著協同創新、產學融合、產業聚集的重大使命,因此,能夠穩定支持農業基礎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至為重要。”謝華安直言,育種,太需要財政扶持和政策支持。
謝華安說,種業發展,不同于其他產業,需要更長的時間、耐心和戰略定力。“一個育種項目出現后,要確保種業研發經費持續穩定,需要長效穩定的財政支持制度。它的周期跨度很大,如果僅以年為周期開展項目申報、評審,這與育種科研規律相矛盾,一旦出現時斷時續的支持力度,必然會影響育種項目的經費來源穩定性和育種科研人員的積極性。”
“一個育種項目,如果周期5年,干3年停2年,這如何是好?這也是我們遇到過的實實在在的情況。”
謝華安拋出這個問題后,是這樣自行回答的——
要健全種業科技創新體系,開展重大技術的聯合攻關,完善體制機制是關鍵。要健全、發揮人才團隊引培、財政資金高效使用以及關鍵技術協同攻關的體制機制和優勢。公益性育種關鍵技術攻關項目需要政府全力提供資金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與種業企業的實驗室之間應建立資源共享和技術互助機制,進一步完善激勵機制,放寬相關利益機制配置。
“提到育種工作,無論是分子標記輔助育種、基因編輯育種,還是其他育種方式,都是多學科協同攻關的過程。但是,要加快突破性新品種培育,加強產業協同創新合作,必須加強創新生態建設。”謝華安說,體制機制理順了,培養、吸引、使用、激勵科技創新人才的各個環節安排合理了,才能組建起種業科技創新聯合體,提升協同創新能力。
“任何大的科研成果,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獲得科研成果難,更難的是獲得成果的同時也獲得團結。”謝華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