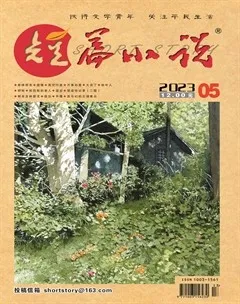創(chuàng)作談:兩個(gè)母親的深度融合
一直想寫(xiě)一篇關(guān)于母親的小說(shuō)。我的母親離開(kāi)我們已經(jīng)9年了,她一輩子受盡了病痛的折磨,在她生命的最后時(shí)刻,我們不但無(wú)法減輕她的痛苦,反而違背她的意志,“殘忍”地將她送進(jìn)ICU.插上了呼吸機(jī)。在ICU里,母親被綁在病床上,不能吃飯,不能說(shuō)話(huà),甚至不能動(dòng)彈一下,就這樣母親掙扎了40來(lái)天,直至最后離去。現(xiàn)在想來(lái),心中還有無(wú)法平息的傷痛,這是我們的孝嗎?是我們的愛(ài)嗎?其實(shí)是我們的自私,是我們的冷酷,更是我們的大逆不道。無(wú)形中,我們剝奪了母親說(shuō)話(huà)的權(quán)利,讓她遭受了我們無(wú)法體會(huì)的痛苦和折磨,真是慘無(wú)人道。母親去世后,我經(jīng)常對(duì)著她的遺像陷入沉思,并常常想起母親病危時(shí),曾對(duì)我做過(guò)的一個(gè)交代。母親說(shuō),選一張好看點(diǎn)兒的照片(做遺像)。這大概就埋下了小說(shuō)的種子,但一直沒(méi)找到更深入的故事。直到若干年前的一天,在本地的晚報(bào)新聞熱線版上,看到一篇尋親文章《九旬老人思念60年前“遺棄”的女兒》,文中說(shuō)市民胡女士通過(guò)晚報(bào)新聞熱線反映,自己的婆婆今年九90歲了,她至今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年輕時(shí)將自己的女兒“遺棄”了,婆婆希望在生前還能見(jiàn)上一面,說(shuō)一聲“對(duì)不起,媽媽當(dāng)年也是迫于無(wú)奈”。這位老婆婆的故事打動(dòng)了我,并觸發(fā)了我的創(chuàng)作靈感,也讓我找到了小說(shuō)的“核”。于是,我將兩位母親的故事融合到一起,擰成一個(gè)人,便有了小說(shuō)中的母親在生命垂危之際,對(duì)遺棄多年的女兒的思念、追悔,并想通過(guò)遺像來(lái)尋找女兒的故事。當(dāng)然文學(xué)不等同于生活,在生活的基礎(chǔ)上,小說(shuō)有了一定的延伸和想象,小說(shuō)得以展現(xiàn)人心的幽微,人性的撕裂、懺悔、救贖,以及兩代人的心海沉浮。母親臨終前的五味雜陳,讓人感受到母性的溫暖。遺像在小說(shuō)中不僅是一個(gè)重要的載體,更成為一種意象。小說(shuō)中的女兒最后不計(jì)前嫌尋母報(bào)恩,而生活中的女兒后來(lái)有沒(méi)有回歸呢?這可能永遠(yuǎn)是個(gè)謎,不過(guò),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老一輩的苦難人生,帶給我們的悲憫情懷。所以,這篇小說(shuō)既是我對(duì)母親的懷念,也是對(duì)天下所有母親的母性大愛(ài)的致敬。
為了深入挖掘文本的意蘊(yùn),這篇小說(shuō)曾數(shù)易其稿,在此致謝《短篇小說(shuō)》雜志,讓這個(gè)小說(shuō)得以呈現(xiàn)。
責(zé)任編輯/文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