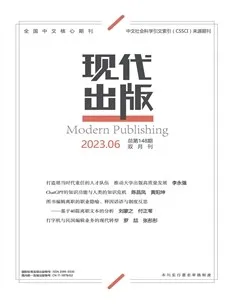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歷時(shí)性案例研究
內(nèi)容摘要:出版深度融合背景下,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已經(jīng)成為出版業(yè)共識(shí)。基于動(dòng)態(tài)能力理論框架,借助建構(gòu)型扎根理論編碼技術(shù)分析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以下簡(jiǎn)稱OUP)2009—2022年年度報(bào)告等文本資料,對(duì)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OUP利用動(dòng)態(tài)能力組合驅(qū)動(dòng)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的演變邏輯進(jìn)行研究后發(fā)現(xiàn),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OUP建設(shè)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漸進(jìn)式演化軌跡主要分為三個(gè)階段:一是探索階段,利用數(shù)字化戰(zhàn)略感知能力,構(gòu)建以產(chǎn)品為主導(dǎo)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將內(nèi)容資源數(shù)字化,嘗試進(jìn)行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二是成長(zhǎng)階段,利用數(shù)字化機(jī)遇捕獲能力,建構(gòu)以服務(wù)為主導(dǎo)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出版活動(dòng)從經(jīng)營(yíng)印刷出版物為主轉(zhuǎn)向構(gòu)建數(shù)字服務(wù);三是加速階段,利用數(shù)字化深化轉(zhuǎn)換能力驅(qū)動(dòng)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整合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
關(guān)鍵詞: 大學(xué)出版社;動(dòng)態(tài)能力;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
課題: 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一般項(xiàng)目“出版企業(yè)知識(shí)服務(wù)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20BXW044)陜西師范大學(xué)研究生領(lǐng)航人才培養(yǎng)項(xiàng)目“價(jià)值共創(chuàng)視角下大學(xué)出版社學(xué)術(shù)出版知識(shí)服務(wù)提升路徑研究”(項(xiàng)目編號(hào):LHRCCX23128)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6.011
大學(xué)出版社作為中國(guó)出版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學(xué)術(shù)知識(shí)傳播、教育服務(wù)等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中國(guó)大學(xué)出版社在四十余年的發(fā)展歷程中,兼具產(chǎn)業(yè)屬性和文化屬性,以產(chǎn)業(yè)效益推動(dòng)科研服務(wù)質(zhì)量提高,以科研資源加強(qiáng)產(chǎn)業(yè)競(jìng)爭(zhēng)力,形成了獨(dú)具特色的大學(xué)出版社發(fā)展之路。但就目前國(guó)內(nèi)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現(xiàn)狀而言,仍然存在動(dòng)態(tài)復(fù)雜的外部刺激和艱難的內(nèi)部挑戰(zhàn),整體發(fā)展呈現(xiàn)出產(chǎn)業(yè)集中度低、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各自為戰(zhàn)、缺乏有效盈利模式等特征。盡管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由來(lái)已久,但究竟是何種能力驅(qū)動(dòng)大學(xué)出版社跨越轉(zhuǎn)型升級(jí)中的階段性障礙,如何在不同階段形成有效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支撐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從而實(shí)現(xiàn)出版高質(zhì)量發(fā)展,學(xué)界對(duì)于這一問(wèn)題至今仍缺乏明確的答案。
一、研究問(wèn)題的提出
為什么有些企業(yè)能夠系統(tǒng)地使其資源和活動(dòng)與環(huán)境保持一致,而另一些企業(yè)卻不能?動(dòng)態(tài)能力解釋了企業(yè)身處復(fù)雜的動(dòng)態(tài)環(huán)境,如何與多方行動(dòng)者合作利用資源、技術(shù)等優(yōu)勢(shì)快速應(yīng)對(duì)外在情境的變化。2018年,大衛(wèi)·蒂斯(David J. Teece)重新評(píng)估了動(dòng)態(tài)能力與規(guī)則、生態(tài)系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系,認(rèn)為將企業(yè)的位置重新定義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而非松散的行業(yè)或者商業(yè)環(huán)境)對(duì)于分析企業(yè)的動(dòng)態(tài)能力更有優(yōu)勢(shì)。與企業(yè)對(duì)特定環(huán)境的反應(yīng)不同,生態(tài)系統(tǒng)是企業(yè)與其他主體合作者之間動(dòng)態(tài)、復(fù)雜、互動(dòng)、共同發(fā)展的關(guān)系。即企業(yè)動(dòng)態(tài)能力的出現(xiàn)過(guò)程并非精準(zhǔn)設(shè)計(jì)的,而是隨其進(jìn)行的活動(dòng)和互動(dòng)出現(xiàn)了很大的變化。
目前出版學(xué)界關(guān)于動(dòng)態(tài)能力的研究成果相對(duì)較少。早期有研究者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將出版企業(yè)動(dòng)態(tài)能力定義為“出版企業(yè)洞察、應(yīng)對(duì)和適應(yīng)媒介環(huán)境變化,對(duì)企業(yè)內(nèi)外部資源和知識(shí)進(jìn)行動(dòng)態(tài)整合和配置,以不斷實(shí)現(xiàn)出版需求和出版價(jià)值創(chuàng)造的組織流程”。徐聲慧、黃倩等人則分析了出版企業(yè)動(dòng)態(tài)能力的內(nèi)涵和構(gòu)成,并提出對(duì)應(yīng)策略。當(dāng)前出版學(xué)界關(guān)于動(dòng)態(tài)能力的研究成果多是從理論層面對(duì)出版企業(yè)動(dòng)態(tài)能力的內(nèi)涵、指標(biāo)評(píng)價(jià)、價(jià)值意義等做出闡釋和分析,大都忽視了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動(dòng)態(tài)能力的演化路徑,尚未明晰動(dòng)態(tài)能力如何作用于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并驅(qū)動(dòng)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出版業(yè)作為時(shí)代的社會(huì)切片,動(dòng)態(tài)能力變化與其發(fā)展脈絡(luò)中的外部環(huán)境息息相關(guān),因而回顧其歷時(shí)性變化顯得十分重要。鑒于此,本文從數(shù)字化戰(zhàn)略感知、數(shù)字化機(jī)遇捕獲、數(shù)字化深化轉(zhuǎn)換三個(gè)方面,探究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不同階段動(dòng)態(tài)能力的演化路徑,如何形成可擴(kuò)展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
二、研究設(shè)計(jì)
(一)案例選取
縱向單案例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充分掌握案例背景,在不同時(shí)間節(jié)點(diǎn)上對(duì)研究對(duì)象進(jìn)行橫向分析和縱向研究,并回答“是如何變化的”“為什么如此變化”“變化后結(jié)果如何”等研究問(wèn)題,確保案例研究深度。本文采用縱向單案例研究方法,選取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作為案例研究對(duì)象,主要出于以下考量:第一,2022年全球出版50強(qiáng)排名中OUP位居第22位,是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大學(xué)出版社,案例主體具有一定的先進(jìn)性。第二,自1989年開(kāi)始,OUP終止圖書印刷業(yè)務(wù),積極向數(shù)字化方向轉(zhuǎn)型,如今OUP正處于數(shù)字化加速轉(zhuǎn)型期,案例主體具備一定的典型性。第三,OUP的目標(biāo)是在世界范圍內(nèi)以出版活動(dòng)促進(jìn)大學(xué)在研究、學(xué)術(shù)和教育等方面的影響力。這與我國(guó)大學(xué)出版社兼具產(chǎn)業(yè)屬性和文化屬性是不謀而合的,案例主體具有可參考性。
(二)研究方法
考慮到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的客觀現(xiàn)象和主觀情境,本文借用建構(gòu)型扎根理論編碼技術(shù)展開(kāi)研究。扎根理論來(lái)源于社會(huì)學(xué),最早由格拉澤(Glaser)和施特勞斯(Strauss)提出,作為一種在系統(tǒng)收集和分析資料的基礎(chǔ)上得出理論的研究路徑。建構(gòu)型扎根理論屬于扎根理論三大流派之一,在編碼環(huán)節(jié),既強(qiáng)調(diào)圍繞文本資料進(jìn)行客觀提問(wèn),如“內(nèi)容關(guān)于什么”“數(shù)據(jù)指向什么范疇”等問(wèn)題,也會(huì)依據(jù)主觀的場(chǎng)景展開(kāi)提問(wèn),如“參與者包含哪些”“觀點(diǎn)是什么”等問(wèn)題。建構(gòu)型扎根理論提倡研究者可以使用不同的數(shù)據(jù)資料,比如田野調(diào)查筆記、報(bào)告、檔案、訪談等,通過(guò)對(duì)原始資料的構(gòu)念、維度提煉及其聯(lián)結(jié)進(jìn)行理論化,其分析層次可以從宏觀滲透到微觀的情感、表達(dá)。具體編碼過(guò)程主要分為兩個(gè)基本階段:
第一階段,收集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2009—2022年年度報(bào)告資料,翻譯完成后約二十萬(wàn)字。年度報(bào)告包含年度總結(jié)、組織變動(dòng)、經(jīng)營(yíng)狀況、未來(lái)變動(dòng)等豐富翔實(shí)的信息,具有重要參考價(jià)值。由于缺乏2009年以前的年報(bào)資料,為保證研究過(guò)程的嚴(yán)謹(jǐn)與連貫,研究者選取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的官網(wǎng)公告、歷史發(fā)展、新聞報(bào)道等文本資料作為對(duì)年度報(bào)告的補(bǔ)充。接著對(duì)OUP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相關(guān)文本資料進(jìn)行篩選和逐步編碼,在忠于文本資料和保持開(kāi)放性原則的基礎(chǔ)上對(duì)數(shù)據(jù)進(jìn)行全面抽象,提取初始編碼。
第二階段,首先,在初始編碼的基礎(chǔ)上圍繞研究問(wèn)題聚焦編碼,使初始編碼更具指向性、概念性。提取重要性高和頻次高的范疇,以理論術(shù)語(yǔ)進(jìn)行編碼,如“數(shù)字基建捕獲”“平臺(tái)集成”等。其次,聚焦編碼后進(jìn)行軸心編碼。 在聚焦編碼階段的重要范疇和高頻次范疇進(jìn)一步上升為主要構(gòu)念和子構(gòu)念,圍繞主要構(gòu)念識(shí)別兩者間的主從關(guān)系,從而得到主要構(gòu)念的維度和屬性,如主要構(gòu)念“外在情境感知”與子構(gòu)念“生態(tài)環(huán)境感知”“政策環(huán)境感知”等。最后,在以上三個(gè)階段編碼基礎(chǔ)上,進(jìn)行理論編碼并提供證據(jù)援引。 理論編碼的目的在于將初始編碼階段打散的數(shù)據(jù),以主要構(gòu)念和子構(gòu)念的方式形成新的具有系統(tǒng)性、關(guān)聯(lián)性和邏輯性的理論表達(dá),使主要構(gòu)念與子構(gòu)念之間的差異關(guān)系以具體形式呈現(xiàn)。
綜上,本文以處于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的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為例,基于動(dòng)態(tài)能力框架,通過(guò)對(duì)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2009—2022年年度報(bào)告等文本資料的內(nèi)容分析,聚焦以下研究問(wèn)題:在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歷程中,動(dòng)態(tài)能力如何作用于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主要研究?jī)?nèi)容包括:(1)揭示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不同階段,識(shí)別支撐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不同階段所需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2)梳理大學(xué)出版社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動(dòng)態(tài)能力組合的演化過(guò)程,為大學(xué)出版社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漸進(jìn)過(guò)程中匹配有效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并逐步構(gòu)建完善的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找到著力點(diǎn)。
三、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實(shí)踐
“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是全球數(shù)字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特定產(chǎn)物。本節(jié)通過(guò)對(duì)OUP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現(xiàn)象和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提煉,系統(tǒng)完整地展示OUP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不同階段,深入揭示復(fù)雜情境下動(dòng)態(tài)能力與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形成的“驅(qū)動(dòng)—支撐”機(jī)制。與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SWOT等戰(zhàn)略分析理論幫助企業(yè)分析如何獲取當(dāng)前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的目標(biāo)不同,大學(xué)出版社建設(shè)動(dòng)態(tài)能力的根本目標(biāo)是持續(xù)實(shí)現(xiàn)更具優(yōu)勢(shì)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動(dòng)態(tài)能力往往不會(huì)直接同時(shí)作用于出版活動(dòng)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和績(jī)效,而是首先作用于價(jià)值創(chuàng)造過(guò)程,進(jìn)而改變出版績(jī)效。
(一)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探索期:產(chǎn)品主導(dǎo)邏輯(1989—2009年)
1. 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探索
這一時(shí)期,OUP的出版活動(dòng)以經(jīng)營(yíng)印刷出版物為主。數(shù)字化形式主要是開(kāi)發(fā)原有版權(quán)資源,數(shù)字化經(jīng)典內(nèi)容,嘗試開(kāi)發(fā)數(shù)字產(chǎn)品,并基于在線內(nèi)容資源的不同特性對(duì)用戶免費(fèi)開(kāi)放。2003年OUP曾嘗試推出牛津?qū)W術(shù)在線(OxfordS c h o l a r s h i p O n l i n e,OSO),但由于市場(chǎng)認(rèn)可度不高而不得以暫時(shí)下線,經(jīng)過(guò)再開(kāi)發(fā)后于2006年再次推出。2009年,被稱為“在線資源的圣杯”的O SO,作為OUP最成功的學(xué)術(shù)在線產(chǎn)品之一,在全球擁有634個(gè)訂閱機(jī)構(gòu),其中坎坷可見(jiàn)一斑。此外,OUP還嘗試推出了牛津國(guó)家傳記詞典在線版本(Oxford Dictionary ofNational Biography,ODNB)等在線資源。總的來(lái)說(shuō),OUP在數(shù)字化探索階段對(duì)于資本投入十分謹(jǐn)慎。
2. 感知能力:數(shù)字化戰(zhàn)略感知
OUP對(duì)于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預(yù)測(cè)以及在探索時(shí)期的種種措施主要基于外在情境感知、資源感知和內(nèi)在制度感知。外在情境感知涉及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政策環(huán)境、市場(chǎng)環(huán)境、用戶行為等方面,OUP對(duì)外在情境的感知著重體現(xiàn)在其對(duì)市場(chǎng)環(huán)境的感知和對(duì)用戶行為的感知兩方面,此時(shí)用戶對(duì)于在線資源的選擇是一種被迫行為,認(rèn)為在線資源是印刷出版物的替代產(chǎn)品或互補(bǔ)產(chǎn)品。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感知、政策環(huán)境感知等為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預(yù)測(cè)提供間接參考,在全球經(jīng)濟(jì)下降和不同地區(qū)印刷出版物市場(chǎng)環(huán)境艱難的境遇下,在線訂購(gòu)和數(shù)字產(chǎn)品為OUP的出版業(yè)務(wù)提供了新的機(jī)遇。資源感知體現(xiàn)在OUP在版權(quán)資源等方面實(shí)力雄厚,對(duì)內(nèi)容和品牌充滿自信,同時(shí)全球化業(yè)務(wù)為整體經(jīng)營(yíng)提供“區(qū)域互補(bǔ)”保障,并通過(guò)學(xué)術(shù)出版業(yè)務(wù)在線銷售的持續(xù)增長(zhǎng)發(fā)現(xiàn)其資源開(kāi)發(fā)的新機(jī)遇。內(nèi)在制度感知為OUP在數(shù)字化探索階段提供主要方向。OUP在全球各地?fù)碛蟹种C(jī)構(gòu),便于掌握國(guó)際市場(chǎng)的不同變化趨勢(shì),洞察轉(zhuǎn)型機(jī)遇;其作為卓越大學(xué)出版社的市場(chǎng)地位和良好形象為前期轉(zhuǎn)型探索提供了穩(wěn)固的營(yíng)收后盾。作為領(lǐng)先的學(xué)術(shù)和教育出版商,OUP分別選擇其廣受全球用戶認(rèn)可的語(yǔ)言類工具書和學(xué)術(shù)專著等內(nèi)容資源率先進(jìn)行在線轉(zhuǎn)換,促成了OED(Oxford English Dicrionary)和OSO的開(kāi)發(fā)。
3. 產(chǎn)品主導(dǎo)邏輯:提供補(bǔ)充性資源
從印刷出版物到在線資源再到數(shù)字服務(wù)的轉(zhuǎn)變是一個(gè)理想過(guò)程。然而正如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所說(shuō),任何情況下行動(dòng)者做出選擇時(shí),理論上可以在諸多路徑中選擇最優(yōu)解,但理論僅是一種對(duì)最優(yōu)情況的探討。在實(shí)踐中,行動(dòng)者很難甚至不可能做出最優(yōu)解,他處于事件發(fā)生的“時(shí)間流”之中,當(dāng)下的時(shí)間緊迫性、事件復(fù)雜性、實(shí)踐模糊性等強(qiáng)迫他必須做出選擇,大學(xué)出版社所面臨的競(jìng)爭(zhēng)環(huán)境的高度不確定性亦是如此。在市場(chǎng)環(huán)境之中,機(jī)遇與危險(xiǎn)并存,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滯后與過(guò)度都可能損害長(zhǎng)久以來(lái)積累的資源或者產(chǎn)生更糟糕的后果。因而必須找到一種緩解“更新”與“維護(hù)”矛盾的方法,即借助補(bǔ)充性資源和能力改變現(xiàn)狀以打破慣習(xí),緩解轉(zhuǎn)換的脆弱,以及加快轉(zhuǎn)換速度。
動(dòng)態(tài)核心能力的形成往往會(huì)面臨“因襲原有路徑”和“戰(zhàn)略更新”之間的矛盾。OUP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必須通過(guò)建立和開(kāi)發(fā)補(bǔ)充性資源來(lái)更新企業(yè)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從而實(shí)現(xiàn)戰(zhàn)略上的轉(zhuǎn)換。因而在線資源和數(shù)字產(chǎn)品的嘗試開(kāi)發(fā)是OUP前期建立補(bǔ)充性資源和能力的關(guān)鍵過(guò)程。在這一過(guò)程中,出版社對(duì)于在線資源的建設(shè)必須從長(zhǎng)遠(yuǎn)的戰(zhàn)略角度而非職能或者經(jīng)營(yíng)收入的角度去考慮如何利用新的市場(chǎng)機(jī)會(huì)或改變產(chǎn)業(yè)、流程等因素。
(二)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成長(zhǎng)期: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2010—2016年)
1. 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成長(zhǎng)階段
成長(zhǎng)階段,OUP敏銳地捕捉到市場(chǎng)環(huán)境的劇烈變化,決定大力投資數(shù)字創(chuàng)新,并強(qiáng)調(diào)對(duì)新技術(shù)、出版活動(dòng)和商業(yè)模式投資的重要性。與初期的數(shù)字化感知不同,數(shù)字化機(jī)遇捕獲意味著出版社要基于自己對(duì)外界環(huán)境的敏感性和反應(yīng)速度做出決定。OUP提出要在數(shù)字服務(wù)方面形成集成解決方案以及跨產(chǎn)品、服務(wù)的無(wú)縫體驗(yàn)。這一階段OUP的出版活動(dòng)發(fā)生了顛覆性的變化,提供了數(shù)量眾多、種類豐富且高質(zhì)量的數(shù)字服務(wù)組合,出版活動(dòng)實(shí)現(xiàn)由經(jīng)營(yíng)印刷出版物為主到構(gòu)建數(shù)字服務(wù)為主的轉(zhuǎn)變。
2. 捕獲能力:數(shù)字化機(jī)遇捕獲
數(shù)字化機(jī)遇捕獲能力具體表現(xiàn)為協(xié)同主體捕獲、內(nèi)在制度捕獲、資源捕獲、數(shù)字技術(shù)捕獲和數(shù)字服務(wù)構(gòu)建。此時(shí)OUP的協(xié)同主體捕獲是對(duì)外多方向動(dòng)態(tài)合作,包含技術(shù)、渠道、內(nèi)容、用戶等多方主體。OUP通過(guò)技術(shù)主體捕獲引入牛津大學(xué)計(jì)算機(jī)科學(xué)系、教育技術(shù)投資企業(yè)實(shí)現(xiàn)數(shù)字產(chǎn)品開(kāi)發(fā)的技術(shù)合作;與索尼、谷歌、亞馬遜等領(lǐng)先技術(shù)公司建立合作伙伴關(guān)系,用戶可分別在其相應(yīng)的用戶渠道訪問(wèn)OUP的數(shù)字產(chǎn)品。同時(shí)邀請(qǐng)其他大學(xué)出版社為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學(xué)術(shù)在線(UniversityP r e s s S c h o l a r s h i p O n l i n e , U P S O ) 提供內(nèi)容。
從內(nèi)在制度捕獲來(lái)看,OUP確立了數(shù)字化成長(zhǎng)階段的主要核心市場(chǎng)。由原先分散的國(guó)際化地區(qū)戰(zhàn)略調(diào)整為依據(jù)全球五大出版業(yè)務(wù)(學(xué)術(shù)出版、國(guó)際學(xué)校、英語(yǔ)教學(xué)、高等教育、詞典開(kāi)發(fā))統(tǒng)一管理。數(shù)字技術(shù)簡(jiǎn)化出版社組織內(nèi)部溝通并深化出版活動(dòng)思維,利用數(shù)字技術(shù)服務(wù)出版社內(nèi)部運(yùn)營(yíng),如在線交流平臺(tái)Oxford Share,促進(jìn)大學(xué)出版社內(nèi)在制度捕獲。
從資源捕獲來(lái)看,這一時(shí)期的數(shù)據(jù)資源積累較為原始。OUP通過(guò)建立語(yǔ)料庫(kù)、全球用戶自定義語(yǔ)言、元語(yǔ)法等一系列措施實(shí)現(xiàn)對(duì)語(yǔ)言數(shù)據(jù)資源的捕獲,并嘗試結(jié)合數(shù)據(jù)資源和出版活動(dòng)提供服務(wù),如利用上萬(wàn)篇兒童小說(shuō)建立寫作語(yǔ)料庫(kù)。此外,為了拓展數(shù)字服務(wù)的市場(chǎng)銷售,OUP圍繞用戶進(jìn)行了大量的營(yíng)銷展示。針對(duì)數(shù)字技術(shù)捕獲,OUP成立了獨(dú)立的全球技術(shù)組織部門,并與高知特(Cognizant,全球領(lǐng)先的IT專業(yè)服務(wù)公司之一)合作獲取技術(shù)支持,同時(shí)積極與技術(shù)社區(qū)接洽,為開(kāi)發(fā)人員提供訪問(wèn)牛津詞典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的權(quán)限,實(shí)現(xiàn)共創(chuàng)。在具體的技術(shù)獲取方面,OUP從語(yǔ)言技術(shù)、教育技術(shù)以及搜索技術(shù)等方面助力其出版活動(dòng)。
立足于內(nèi)部制度,以中觀協(xié)同主體捕獲為基礎(chǔ),通過(guò)數(shù)據(jù)資源和數(shù)字技術(shù)支持,OUP在成長(zhǎng)階段圍繞用戶特定需求和產(chǎn)品特性積極構(gòu)建數(shù)字平臺(tái)集成、語(yǔ)言社區(qū)集成等數(shù)字服務(wù)組合,主要有以下形式:
( 1 ) 在線數(shù)據(jù)庫(kù)。以在線學(xué)術(shù)工具書數(shù)據(jù)庫(kù)最為突出。如牛津書目在線( O x f o r dBibliographies Online,OBO)、牛津?qū)W術(shù)版本在線(Oxford Scholarly Editions Online,OSEO)等。(2)數(shù)字工具。如Ac h i e v er數(shù)字評(píng)估工具、iTools課堂展示互動(dòng)工具、obook和assess互動(dòng)學(xué)習(xí)和評(píng)估工具等,這些工具多是作為單獨(dú)的工具包或者教學(xué)材料的輔助工具推出。(3)語(yǔ)言社區(qū)集成。OUP基于ELT(English LanguageTeaching)資源,深入開(kāi)發(fā)語(yǔ)言元數(shù)據(jù)并構(gòu)建語(yǔ)言解決方案、全球性社區(qū)交流、語(yǔ)料庫(kù)等。如牛津全球語(yǔ)言(Oxford Global Languages,OGL),世界各地的社群能夠憑借母語(yǔ)在OGL進(jìn)行在線互動(dòng),這一社區(qū)包含了如馬來(lái)語(yǔ)等少數(shù)語(yǔ)言,且其語(yǔ)言種類持續(xù)更新,項(xiàng)目覆蓋范圍持續(xù)擴(kuò)大。(4)獨(dú)立的、小規(guī)模的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如為兒童學(xué)習(xí)提供幫助的牛津貓頭鷹Oxford Owl、電子書平臺(tái)Oxford Learner’s Bookshelf等。小規(guī)模的數(shù)字平臺(tái)多是為了實(shí)現(xiàn)單一功能而開(kāi)發(fā)建立。2016年,學(xué)術(shù)期刊遷移到由學(xué)術(shù)出版服務(wù)商Silverchair支持開(kāi)發(fā)的新牛津?qū)W術(shù)平臺(tái),這是OUP學(xué)術(shù)出版的重大轉(zhuǎn)變,朝著跨越期刊、學(xué)術(shù)書籍和在線出版的集成系統(tǒng)邁進(jìn)。
OUP也通過(guò)并購(gòu)和整合推出了一批數(shù)字服務(wù),比如收購(gòu)Numicon觸覺(jué)視覺(jué)教學(xué)系統(tǒng)等,并購(gòu)教育出版商N(yùn)elson Thornes,將其成功整合到OUP的英國(guó)教育出版業(yè)務(wù)中。總的來(lái)說(shuō),這一時(shí)期OUP全面推廣數(shù)字化,尤其是在數(shù)字服務(wù)方面,做出了相當(dāng)多的嘗試與探索。
3. 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構(gòu)建數(shù)字服務(wù)
在產(chǎn)品主導(dǎo)邏輯下,企業(yè)始終圍繞產(chǎn)品進(jìn)行價(jià)值創(chuàng)造和價(jià)值交換。傳統(tǒng)企業(yè)在生產(chǎn)商品時(shí),其價(jià)值創(chuàng)造的最大動(dòng)力在于通過(guò)提高標(biāo)準(zhǔn)化商品生產(chǎn)的效率實(shí)現(xiàn)利潤(rùn)獲取,比如批量生產(chǎn)的詞典成本越低,利潤(rùn)空間也就越大。但是這樣就產(chǎn)生了價(jià)值創(chuàng)造“效率”與“效力”之間的矛盾,OUP提高效率(標(biāo)準(zhǔn)化生產(chǎn))的同時(shí)難以兼顧產(chǎn)品的效力(個(gè)性化定制)。可隨著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的變化,人們的消費(fèi)水平和對(duì)產(chǎn)品的認(rèn)知水平都在提高,產(chǎn)品需求呈現(xiàn)個(gè)性化趨勢(shì),OUP的出版活動(dòng)轉(zhuǎn)而更加強(qiáng)調(diào)效力。基于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所提供的數(shù)字服務(wù)天然帶有用戶導(dǎo)向,比如其學(xué)術(shù)出版業(yè)務(wù)提供的Research Track,根據(jù)學(xué)者需求即時(shí)提供最新研究動(dòng)態(tài)。從使用價(jià)值的角度來(lái)看,產(chǎn)品本身是對(duì)用戶提供的服務(wù)。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替代傳統(tǒng)產(chǎn)品主導(dǎo)邏輯,從新視角理解經(jīng)濟(jì)交換和價(jià)值創(chuàng)造,將顧客體驗(yàn)的價(jià)值共創(chuàng)進(jìn)一步深化和豐富。
OUP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逐漸由傳統(tǒng)的產(chǎn)品主導(dǎo)邏輯轉(zhuǎn)向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這一過(guò)程主要經(jīng)歷三個(gè)階段。首先是以印刷出版物為主、數(shù)字產(chǎn)品為輔的第一階段,數(shù)字產(chǎn)品以補(bǔ)充性資源的形式出現(xiàn)。由于印刷出版物容易受各種外在環(huán)境影響,如國(guó)際運(yùn)輸中的安全因素、消費(fèi)者行為傾向等,所以雖然OUP數(shù)字產(chǎn)品的營(yíng)收未占主導(dǎo)地位,但其傳播范圍和使用頻率均在向好發(fā)展。第二階段是印刷出版物銷售與數(shù)字產(chǎn)品的組合階段。這一時(shí)期,OUP結(jié)合印刷出版物與數(shù)字產(chǎn)品的不同特性,推出“紙電”混合集成產(chǎn)品,比如開(kāi)發(fā)了BigIdea學(xué)習(xí)框架,該計(jì)劃包括新的牛津大學(xué)思想教科書系列,將傳統(tǒng)印刷和數(shù)字格式的學(xué)習(xí)材料混合推出。此外,OUP利用新技術(shù)和客戶需求持續(xù)推出新的數(shù)字產(chǎn)品組合,比如教科書在線資源、數(shù)字工具包、數(shù)字評(píng)估工具等。第三階段是數(shù)字服務(wù)轉(zhuǎn)向階段。OUP意識(shí)到出版活動(dòng)本質(zhì)上是出版社與用戶建立關(guān)系的過(guò)程,而非交換產(chǎn)品本身,用戶購(gòu)買的是產(chǎn)品的服務(wù)能力。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下更加強(qiáng)調(diào)服務(wù)的使用價(jià)值,而使用價(jià)值是由受益者決定的,其是否“增值”取決于受益者,出版社只參與提出價(jià)值主張和創(chuàng)造價(jià)值的過(guò)程。因而在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下,OUP提出“必須是以客戶想要的格式提供我們的內(nèi)容”,從用戶需求的角度進(jìn)行價(jià)值創(chuàng)造。OUP這一時(shí)期推出了大量的數(shù)字服務(wù),形式豐富多樣,既包含新數(shù)字服務(wù)的開(kāi)發(fā),也包括已有數(shù)字產(chǎn)品之間的服務(wù)鏈接和重組。
(三)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加速期: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2017年至今)
1. 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加速階段
根據(jù)2022年年報(bào)來(lái)看,OUP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仍在繼續(xù),處于加速轉(zhuǎn)型階段。 出版活動(dòng)聚焦于學(xué)術(shù)出版、英語(yǔ)學(xué)習(xí)和教育,年報(bào)中關(guān)于慈善活動(dòng)、員工培養(yǎng),以及可持續(xù)出版活動(dòng)、全球性研究等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Governance)內(nèi)容的比例均在提高,這與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生態(tài)觀念十分契合。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成長(zhǎng)階段,OUP提供了數(shù)量眾多的數(shù)字服務(wù),但整體呈現(xiàn)出小規(guī)模、零散分布、功能重復(fù)的特征,且盈利方式有限。此時(shí),對(duì)出版活動(dòng)進(jìn)行“再認(rèn)識(shí)”就顯得格外重要。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加速階段,需要對(duì)未來(lái)的出版活動(dòng)進(jìn)行再思考,什么是合理的出版活動(dòng)?即不僅是圍繞用戶需求提供服務(wù),更重要 的是如何照亮用戶看不到的地方。在滿足用戶不斷變化的需求后,主動(dòng)引導(dǎo)用戶實(shí)現(xiàn)更好的發(fā)展。
2. 深化轉(zhuǎn)換能力:數(shù)字化深化轉(zhuǎn)換
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加速階段,OUP的數(shù)字化深化轉(zhuǎn)換能力具體表現(xiàn)為生態(tài)主體擴(kuò)展、內(nèi)在制度重塑、外在情境改善、數(shù)據(jù)資產(chǎn)轉(zhuǎn)向、數(shù)字技術(shù)落地、服務(wù)生態(tài)構(gòu)建等。
就生態(tài)主體擴(kuò)展來(lái)看,在同用戶、利益相關(guān)者、社會(huì)參與者的合作中,關(guān)注整個(gè)社會(huì)在出版活動(dòng)中的主體互動(dòng)。與大學(xué)、基金會(huì)、出版社等中觀利益相關(guān)者的合作,使得OUP可以利用已有資源和技術(shù)快速形成新的服務(wù)。2020年,OUP開(kāi)發(fā)的牛津洞察(Oxford Insights)平臺(tái),通過(guò)學(xué)習(xí)過(guò)程中產(chǎn)生的數(shù)據(jù)幫助學(xué)生實(shí)現(xiàn)效果評(píng)估。平臺(tái)建立在卡內(nèi)基梅隆大學(xué)開(kāi)放學(xué)習(xí)計(jì)劃(CarnegieMellon’s Open Learning Initiative)12年的研究基礎(chǔ)上,該計(jì)劃證明了學(xué)習(xí)活動(dòng)與學(xué)習(xí)收益之間的強(qiáng)烈相關(guān)性。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在積極參與社會(huì)活動(dòng)之余,吸納社會(huì)力量和用戶共同開(kāi)展出版活動(dòng),這些出版活動(dòng)基本圍繞“循證與反饋”的主題進(jìn)行。
從內(nèi)在制度重塑來(lái)看,制度發(fā)揮著關(guān)鍵作用,平臺(tái)通過(guò)共享、共同的制度去協(xié)調(diào)參與者行為,其價(jià)值共創(chuàng)行為是由參與者產(chǎn)生的制度來(lái)安排的。當(dāng)前OUP的業(yè)務(wù)聚焦于科學(xué)研究、英語(yǔ)學(xué)習(xí)和教育,出版理念側(cè)重評(píng)估產(chǎn)品和服務(wù)對(duì)學(xué)習(xí)者的影響,從順應(yīng)變革到引 導(dǎo)并鼓動(dòng)變革。OUP的制度化安排對(duì)內(nèi)具體體現(xiàn)為以下幾個(gè)方面:組織結(jié)構(gòu)如成立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多元化委員會(huì);組織規(guī)范如信息安全和數(shù)據(jù)隱私(Information Security andData Privacy,ISDP)培訓(xùn);組織對(duì)話如員工和業(yè)務(wù)合作伙伴可以通過(guò)由獨(dú)立的第三方管理的“暢所欲言”頻道報(bào)告道德問(wèn)題;組織學(xué)習(xí)如導(dǎo)師匹配方案,培養(yǎng)女性領(lǐng)導(dǎo)者等。制度從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內(nèi)部為大學(xué)出版社改善外在情境提供了穩(wěn)定的機(jī)制保障和高度延展性。同時(shí),出版社改善外在情境積極拓展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外延,為保持可持續(xù)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提供機(jī)遇。OUP在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中利用資源、技術(shù)、主體地位等多方面優(yōu)勢(shì)主動(dòng)改善外在情境,甚至形成對(duì)外在情境的引導(dǎo)。這種改善突出表現(xiàn)為戰(zhàn)略重點(diǎn)逐步轉(zhuǎn)向循證與反饋,主要通過(guò)數(shù)字服務(wù)、公益引導(dǎo)和組織調(diào)查的方式展開(kāi),打造更具覆蓋力的生態(tài)圈,形成正向反饋互動(dòng)。此外還包括參與開(kāi)放科學(xué)和開(kāi)放教育、推進(jìn)社會(huì)慈善、助力學(xué)術(shù)弱勢(shì)區(qū)域、開(kāi)展社會(huì)醫(yī)療科普、關(guān)注環(huán)境可持續(xù)保護(hù)等。
數(shù)據(jù)資產(chǎn)重構(gòu)為OUP的發(fā)展提供內(nèi)容基礎(chǔ)。OUP在進(jìn)行資源數(shù)字化的過(guò)程中,從內(nèi)容數(shù)據(jù)到用戶數(shù)據(jù)形成了大量的數(shù)據(jù)資源,但就數(shù)據(jù)資源本身而言,要經(jīng)歷從數(shù)據(jù)采集、存儲(chǔ)、管理、使用的全過(guò)程。在OUP的現(xiàn)有數(shù)據(jù)中,數(shù)據(jù)源頭不統(tǒng)一、數(shù)據(jù)格式不一致、底層數(shù)據(jù)不一致等問(wèn)題凸顯,其難題在于如何在平臺(tái)中形成真正有應(yīng)用價(jià)值的數(shù)據(jù)資產(chǎn),構(gòu)建有復(fù)用價(jià)值的數(shù)據(jù)資產(chǎn)庫(kù),實(shí)現(xiàn)可共享數(shù)據(jù)資產(chǎn)的統(tǒng)一管理,并以API接口或數(shù)據(jù)服務(wù)的方式開(kāi)放出去。從業(yè)務(wù)驅(qū)動(dòng)到數(shù)據(jù)驅(qū)動(dòng),實(shí)際上是在出版活動(dòng)的梳理中找到關(guān)鍵的可沉淀的數(shù)據(jù),進(jìn)而轉(zhuǎn)化為數(shù)據(jù)資產(chǎn)反哺出版活動(dòng)形成數(shù)據(jù)服務(wù)。在這一反哺過(guò)程中還會(huì)出現(xiàn)諸如數(shù)據(jù)不一致、數(shù)據(jù)重復(fù)等問(wèn)題,在問(wèn)題逐一解決后才能構(gòu)建數(shù)據(jù)資產(chǎn)庫(kù)。
數(shù)字技術(shù)為OUP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發(fā)展持續(xù)保駕護(hù)航,主要包括數(shù)字技術(shù)常態(tài)投入、語(yǔ)言技術(shù)更新、技術(shù)服務(wù)轉(zhuǎn)化以及硬件技術(shù)研發(fā)等。尤其是數(shù)據(jù)驅(qū)動(dòng)技術(shù),OUP基于豐富的語(yǔ)言數(shù)據(jù)資源,通過(guò)數(shù)據(jù)分析和挖掘能夠?yàn)槌霭嫔缣峁┦袌?chǎng)洞察和預(yù)測(cè),比如2019年牛津兒童年度詞匯是“Brexit”(英國(guó)脫歐),OUP圍繞這一詞匯開(kāi)展了相關(guān)的資料推送和活動(dòng)策劃。
服務(wù)生態(tài)構(gòu)建是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加速階段OUP對(duì)已有數(shù)字服務(wù)的整合、再開(kāi)發(fā)以及生態(tài)整體的價(jià)值延伸,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方面:首先,圍繞服務(wù)的一站式整合。OUP在搭建學(xué)術(shù)平臺(tái)時(shí),將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的所有期刊、書籍和在線產(chǎn)品首次集中在同一個(gè)平臺(tái)。其次,挖掘新的服務(wù)方式,推出線下場(chǎng)景模擬語(yǔ)言教育、AI互動(dòng)教育服務(wù)。最后,立足全球市場(chǎng),其推出的數(shù)字平臺(tái)OED,匯總了世界各地的英語(yǔ)語(yǔ)言更新,方便英語(yǔ)交流。結(jié)合各地市場(chǎng)的不同情況,OUP推廣已經(jīng)在英國(guó)市場(chǎng)成熟的數(shù)字服務(wù),比如澳大利亞牛津語(yǔ)言兒童語(yǔ)料庫(kù)建設(shè)。更為重要的是,OUP正在嘗試價(jià)值延伸,從循證與反饋的角度關(guān)注學(xué)術(shù)研究和用戶學(xué)習(xí)的過(guò)程。這將是未來(lái)一段時(shí)期內(nèi)服務(wù)生態(tài)構(gòu)建的主要方向。
3. 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建設(shè)
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是OUP在數(shù)字化加速轉(zhuǎn)型階段構(gòu)建數(shù)字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主要方式。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作為一種兼具數(shù)字出版企業(yè)角色和數(shù)字出版市場(chǎng)角色的中間性組織,創(chuàng)造了一種虛擬系統(tǒng)空間,一種開(kāi)放式的數(shù)字出版雙(多)邊市場(chǎng)環(huán)境。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加速階段,OUP以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為單位聚合多層次價(jià)值創(chuàng)造主體,通過(guò)內(nèi)在制度規(guī)定出版活動(dòng),規(guī)范整合出版資源并借助新技術(shù)的保障實(shí)現(xiàn)用戶服務(wù),以對(duì)外在情境的積極引導(dǎo)打造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具有開(kāi)放特征。
目前,OUP的主要出版業(yè)務(wù)包含學(xué)術(shù)出版、教育、英語(yǔ)語(yǔ)言學(xué)習(xí)三大板塊,針對(duì)不同業(yè)務(wù),OUP通過(guò)統(tǒng)一的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提供服務(wù)。以“牛津?qū)W術(shù)”(Oxford Academic)為例,2021年,“牛津?qū)W術(shù)”期刊訪問(wèn)量增長(zhǎng)12.1%。“牛津?qū)W術(shù)”和香港大學(xué)出版社、麻省理工學(xué)院出版社等大學(xué)出版社合作,匯集了來(lái)自全球15家著名大學(xué)出版社的24 000種研究出版物。借助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的價(jià)值交換,“牛津?qū)W術(shù)”形成覆蓋了學(xué)者、圖書館和研究機(jī)構(gòu)的全球網(wǎng)絡(luò)。在資源整合上,引入了前期開(kāi)發(fā)的數(shù)字服務(wù),如Grove Music、GroveArt、Oxford Handbook Online、UniversityPress Scholarship Online等。“牛津?qū)W術(shù)”兼具數(shù)字出版企業(yè)角色和數(shù)字出版市場(chǎng)角色的雙重屬性。這種雙重屬性一方面充分利用以往積累的資源優(yōu)勢(shì)、服務(wù)優(yōu)勢(shì)等,借助后發(fā)技術(shù)優(yōu)勢(shì)提供新服務(wù);另一方面以“平臺(tái)”為媒介,鏈接大規(guī)模的多方內(nèi)容資源和多元用戶需求。前者以領(lǐng)導(dǎo)者身份搭建容納生態(tài)系統(tǒng)成員的平臺(tái)架構(gòu),借助標(biāo)準(zhǔn)化處理、技術(shù)等操縱性資源設(shè)立平臺(tái)規(guī)則;后者以開(kāi)放數(shù)字資源實(shí)現(xiàn)成員之間的資源交換和服務(wù)交互,最終激發(fā)平臺(tái)的網(wǎng)絡(luò)外部性,增強(qiáng)用戶黏性。
總的來(lái)說(shuō),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主要呈現(xiàn)以下特點(diǎn):
(1)開(kāi)放性。OUP重新考慮價(jià)值主體在不同價(jià)值層面和價(jià)值環(huán)節(jié)發(fā)揮的作用,由用戶、政府、基金會(huì)、大學(xué)等主體形成“微觀用戶—中觀利益相關(guān)者—宏觀社會(huì)參與者”的多層次生態(tài)圈。生態(tài)主體間存在相互依賴關(guān)系,通過(guò)合作與互助共同應(yīng)對(duì)環(huán)境的變化,其中資源充沛者扮演引領(lǐng)的角色,資源匱乏者扮演倚靠、跟隨的角色,其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話語(yǔ)權(quán)則取決于對(duì)方在自身業(yè)務(wù)推進(jìn)中的不可替代程度。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作為生態(tài)主體中的引領(lǐng)者,通過(guò)服務(wù)用戶、選擇優(yōu)秀合作者、聯(lián)合社會(huì)力量等策略推進(jìn)生態(tài)圈中的多層次互動(dòng)和服務(wù)交換,參與者之間對(duì)外開(kāi)放、合作共生。
(2)不可替代性。自然語(yǔ)言處理(NaturalLanguage Processing,NLP)、生成式AI等技術(shù)持續(xù)迭代,為出版服務(wù)的新形態(tài)提供技術(shù)支持和保障。數(shù)據(jù)資產(chǎn)的引入是新技術(shù)與出版業(yè)務(wù)的嘗試結(jié)合,將出版社在長(zhǎng)期出版活動(dòng)中的用戶數(shù)據(jù)、業(yè)務(wù)數(shù)據(jù)和文本數(shù)據(jù)等在經(jīng)過(guò)規(guī)范化的數(shù)據(jù)處理后沉淀為可復(fù)用、可調(diào)動(dòng)的數(shù)據(jù)資產(chǎn)庫(kù),幫助出版社構(gòu)建起強(qiáng)有力的堡壘。事實(shí)上,這種堡壘的構(gòu)建僅僅是出版社單方面的積累,更為重要的是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為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發(fā)展提供了強(qiáng)大的內(nèi)生動(dòng)力。一方面,捕獲多元主體提高了用戶離開(kāi)平臺(tái)的轉(zhuǎn)移成本,解決了用戶使用數(shù)字服務(wù)的多重歸屬現(xiàn)象;另一方面,依靠生態(tài)主體擴(kuò)展所產(chǎn)生的顯性價(jià)值和隱性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平臺(tái)商業(yè)運(yùn)轉(zhuǎn)的正循環(huán),激發(fā)正向網(wǎng)絡(luò)效應(yīng)獲取價(jià)值,亦即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另一特征:正向反饋機(jī)制。
(3)正向反饋機(jī)制。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往往會(huì)因外在情境的波動(dòng)而調(diào)整內(nèi)在制度,繼而促使內(nèi)部動(dòng)態(tài)發(fā)展,這種發(fā)展具有被動(dòng)且緊迫的特點(diǎn)。動(dòng)態(tài)能力可以為出版社增強(qiáng)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但是動(dòng)態(tài)能力在不同發(fā)展階段中的作用還取決于大學(xué)出版社自身對(duì)外界情境的敏感性和反應(yīng)速度。如果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對(duì)于來(lái)自外在情境的沖擊一直是即時(shí)反饋,則系統(tǒng)運(yùn)轉(zhuǎn)很難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不穩(wěn)定的外在情境要求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基于動(dòng)態(tài)能力做出中長(zhǎng)期的戰(zhàn)略規(guī)劃和判斷實(shí)現(xiàn)超前引導(dǎo)。隨著生態(tài)主體擴(kuò)展、數(shù)據(jù)資源增多、服務(wù)經(jīng)驗(yàn)涌入,大學(xué)出版社可服務(wù)領(lǐng)域拓寬、可賦能環(huán)節(jié)精進(jìn),生態(tài)反哺效果逐漸明顯,形成正向反饋機(jī)制。大學(xué)出版社作為主導(dǎo)者和發(fā)起方,這一完備的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已然成為價(jià)值創(chuàng)造的源泉,成長(zhǎng)性收益有助于大學(xué)出版社將對(duì)外在情境的超前引導(dǎo)納入未來(lái)的出版活動(dòng)規(guī)劃,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
在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視角下,出版社需要回歸到出版活動(dòng)進(jìn)行再思考,回答“出版是什么,出版功能是什么”的問(wèn)題。只有這樣,大學(xué)出版社才能主動(dòng)融入社會(huì),發(fā)揮出版的引導(dǎo)作用,通過(guò)對(duì)外在情境的外在效用形成開(kāi)放、動(dòng)態(tài)、可持續(xù)的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出版的功能是出版自身的所固有的作用于讀者或社會(huì)的效用及價(jià)值,由出版自身的內(nèi)部要素結(jié)構(gòu)所決定,但要通過(guò)作用于讀者或社會(huì)體現(xiàn)其影響和價(jià)值。大學(xué)出版社在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中對(duì)外在情境的主動(dòng)融入和引導(dǎo)作用恰恰是“出版自身所固有的作用于讀者的社會(huì)效用及價(jià)值”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
四、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大學(xué)出版社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演化路徑
本文從動(dòng)態(tài)能力的感知、捕獲、深化轉(zhuǎn)換三個(gè)維度,結(jié)合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分析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背景下動(dòng)態(tài)能力驅(qū)動(dòng)大學(xué)出版社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的演化路徑。以O(shè)UP為核心的價(jià)值網(wǎng)絡(luò)集聚多方資源,圍繞內(nèi)在制度,借助新技術(shù)實(shí)現(xiàn)資源整合和服務(wù)交換,并通過(guò)改善外在情境實(shí)現(xiàn)價(jià)值創(chuàng)造的再循環(huán)和擴(kuò)展,推動(dòng)價(jià)值在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內(nèi)外持續(xù)共創(chuàng)共享。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不同階段利用其動(dòng)態(tài)能力組合與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形成“驅(qū)動(dòng)—支撐”助力機(jī)制,是OUP最終構(gòu)建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重要路徑。
(一)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根本在于戰(zhàn)略指引
這種指引首先是意識(shí)變革,決定著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方向,技術(shù)、資源、服務(wù)等都是根據(jù)戰(zhàn)略做出的調(diào)整和相應(yīng)支撐。數(shù)字化謹(jǐn)慎投資、全面推廣數(shù)字化、數(shù)字化變革再思考是大學(xué)出版社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意識(shí)變革必然要經(jīng)歷的三個(gè)階段。在探索階段,出版社需要結(jié)合內(nèi)部制度、已有資源、外在變化等多方面感知對(duì)數(shù)字化環(huán)境做出判斷和嘗試,因而這一階段出版社的戰(zhàn)略指引是謹(jǐn)慎小心的,數(shù)字化投資多是集中在資源數(shù)字化和試點(diǎn)數(shù)字產(chǎn)品。在成長(zhǎng)階段,大學(xué)出版社已經(jīng)明確判定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是必然趨勢(shì),如何勾勒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藍(lán)圖成為該時(shí)期的重點(diǎn)。OUP在前期資源數(shù)字化和數(shù)字產(chǎn)品試點(diǎn)的基礎(chǔ)上,全面推廣數(shù)字化經(jīng)驗(yàn),推出了大量的數(shù)字服務(wù),數(shù)字服務(wù)的數(shù)量、種類都大大豐富。但也會(huì)迎來(lái)自己的數(shù)字化困境,即數(shù)字化服務(wù)孤島式分布、數(shù)據(jù)難以統(tǒng)一等。在加速階段,出版社迎來(lái)了意識(shí)變革的再思考,具體表現(xiàn)為在營(yíng)銷、出版流程、服務(wù)等方面的數(shù)字化整合,尤其是積極主動(dòng)改善外在情境的可持續(xù)服務(wù)生態(tài)構(gòu)建,使得出版活動(dòng)外部成為全社會(huì)層面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活動(dòng)。
(二)動(dòng)態(tài)能力由不同子能力組合而成
數(shù)字化戰(zhàn)略感知能力是指大學(xué)出版社為了識(shí)別當(dāng)前和未來(lái)的機(jī)會(huì)與威脅對(duì)環(huán)境進(jìn)行了解和分析的能力;數(shù)字化機(jī)遇捕獲能力是指大學(xué)出版社在借助技術(shù)支持、服務(wù)構(gòu)建等方式整合資源或各種能力等來(lái)抓住機(jī)遇的能力;數(shù)字化深化轉(zhuǎn)換能力是指大學(xué)出版社重新部署和配置特定的有形和無(wú)形資產(chǎn)的能力,構(gòu)建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可持續(xù)循環(huán)發(fā)展。研究揭示了不同階段大學(xué)出版社動(dòng)態(tài)能力的演化過(guò)程,即“數(shù)字化戰(zhàn)略感知—數(shù)字化機(jī)遇捕獲—數(shù)字化深化轉(zhuǎn)換”。在探索階段,數(shù)字化戰(zhàn)略感知是出版社進(jìn)行數(shù)字化嘗試的參考依據(jù),是后續(xù)階段出版社繼續(xù)進(jìn)行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基礎(chǔ)。在成長(zhǎng)階段,出版社明確指出要大力投資數(shù)字創(chuàng)新。此時(shí),出版社數(shù)字化機(jī)遇捕獲重組內(nèi)在制度,通過(guò)協(xié)同主體捕獲、資源捕獲、數(shù)字技術(shù)捕獲實(shí)現(xiàn)數(shù)字服務(wù)構(gòu)建,為加速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做好準(zhǔn)備。在加速階段,出版社整合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充分利用大學(xué)出版社、政府、社會(huì)組織、基金會(huì)等擴(kuò)展生態(tài)主體,以重塑內(nèi)在制度為核心,進(jìn)行數(shù)據(jù)資產(chǎn)轉(zhuǎn)向和數(shù)字技術(shù)持續(xù)更新,并在其出版活動(dòng)中構(gòu)建服務(wù)生態(tài),以改善外在情境為外延,形成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
(三)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支撐
從產(chǎn)品主導(dǎo)邏輯到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再到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是不同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階段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的具體體現(xiàn),也是非數(shù)字原生大學(xué)出版社可行的轉(zhuǎn)換過(guò)程。
首先,在探索階段,由于出版社并非數(shù)字原生企業(yè),其必然面臨著需要將已有的大量資源向數(shù)字資源轉(zhuǎn)化的過(guò)程,OUP選擇將已有資源數(shù)字化,把在線資源作為補(bǔ)充性資源推出。這一階段出版社的數(shù)字資源營(yíng)收有限、見(jiàn)效慢。但是出版社仍然需要穩(wěn)定的經(jīng)營(yíng)收入來(lái)源,所以在這一時(shí)期其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沿守經(jīng)營(yíng)傳統(tǒng)印刷出版物的產(chǎn)品主導(dǎo)邏輯。
其次,在成長(zhǎng)階段,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由產(chǎn)品主導(dǎo)邏輯向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轉(zhuǎn)變,經(jīng)歷由以印刷出版物為主、數(shù)字出版物為輔到產(chǎn)品組合再到以數(shù)字服務(wù)為主。2016年,OUP的數(shù)字服務(wù)占據(jù)其學(xué)術(shù)出版營(yíng)業(yè)額一半以上。通過(guò)前期的資源數(shù)字化積累,OUP在資源方面已經(jīng)初步構(gòu)建起自己的堡壘,從提供產(chǎn)品轉(zhuǎn)向提供服務(wù),這并不意味著原有產(chǎn)品的消失,而是作為數(shù)字服務(wù)的一部分出現(xiàn)。此時(shí),出版社所提供的不但是一個(gè)具備使用價(jià)值的產(chǎn)品,更重要的是價(jià)值主張進(jìn)階,服務(wù)成為出版社、用戶、協(xié)同主體之間傳遞價(jià)值的載體。用戶嵌入價(jià)值創(chuàng)造過(guò)程,與出版社對(duì)話進(jìn)而提出個(gè)性化需求,參與服務(wù)構(gòu)建。
最后,在加速階段,出版社主要運(yùn)用數(shù)字化深化轉(zhuǎn)換能力加快整合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兼具社會(huì)效益和經(jīng)濟(jì)效益,形成良好的生態(tài)循環(huán)。OUP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構(gòu)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漸進(jìn)的過(guò)程,具體經(jīng)歷了“產(chǎn)品主導(dǎo)邏輯—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的轉(zhuǎn)變,這與其動(dòng)態(tài)能力組合密不可分。正是前期數(shù)字服務(wù)的持續(xù)積累,才能實(shí)現(xiàn)服務(wù)整合和深化。也是得益于數(shù)字技術(shù)的發(fā)展,可以開(kāi)展基于循證和反饋的新時(shí)期出版活動(dòng),其生態(tài)主體得以擴(kuò)展至整個(gè)社會(huì)。根源上OUP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離不開(kāi)其內(nèi)在制度的調(diào)整,出版社使命、業(yè)務(wù)聚焦、出版理念等使其不僅是內(nèi)在循環(huán)、松散耦合的,更是對(duì)外包容、動(dòng)態(tài)鏈接的。
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通過(guò)價(jià)值創(chuàng)造主體為“生態(tài)圈”各方所提供的服務(wù)實(shí)現(xiàn)最終目標(biāo)。首先,面對(duì)微觀層用戶,內(nèi)在制度的動(dòng)態(tài)調(diào)整決定了出版社對(duì)于“出版活動(dòng)”的認(rèn)知,決定了如何借助新技術(shù)為用戶服務(wù)。其次,面對(duì)中觀層利益相關(guān)者,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還涉及產(chǎn)業(yè)鏈的完整問(wèn)題。大學(xué)出版社的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需要在制度的基礎(chǔ)上,利用技術(shù)、內(nèi)容等操縱性資源達(dá)成主體間價(jià)值共創(chuàng),并分享發(fā)展中產(chǎn)生的各種隱性價(jià)值如數(shù)據(jù)等,實(shí)現(xiàn)合作共贏。最后,在宏觀層面回歸到出版的社會(huì)服務(wù)功能,主要是服務(wù)于社會(huì)政治建設(shè)的效用、服務(wù)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價(jià)值以及促進(jìn)文化發(fā)展或進(jìn)步的積極作用,如社會(huì)共同參與的“循證與反饋”調(diào)研活動(dòng),出版社和宏觀、中觀層面的政府、科研機(jī)構(gòu)、高校等主體聯(lián)合發(fā)布的報(bào)告Education: the Journey Towards aDigital Revolution 和Addressing the DeepeningDigital Divide 。這種多層次的服務(wù)相互關(guān)聯(lián),在為服務(wù)教育工作者、父母、學(xué)習(xí)者等各類用戶的同時(shí),從根本上促進(jìn)整個(gè)行業(yè)生態(tài)和社會(huì)教育的良好發(fā)展。
五、研究貢獻(xiàn)及展望
(一)研究貢獻(xiàn)
通過(guò)對(duì)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過(guò)程中動(dòng)態(tài)能力驅(qū)動(dòng)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的演化過(guò)程分析,對(duì)比現(xiàn)有研究,本文的理論貢獻(xiàn)有以下幾點(diǎn):
第一,本文有效地回答了“動(dòng)態(tài)能力如何驅(qū)動(dòng)大學(xué)出版社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這一基本問(wèn)題,總結(jié)數(shù)字化戰(zhàn)略感知、數(shù)字化機(jī)遇捕獲、數(shù)字化深化轉(zhuǎn)換三個(gè)不同動(dòng)態(tài)能力組合及作用機(jī)制,并通過(guò)對(duì)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從產(chǎn)品主導(dǎo)到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這一完整過(guò)程的系統(tǒng)性考察,提煉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加速階段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的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強(qiáng)調(diào)建設(shè)主動(dòng)引導(dǎo)外在情境的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這既有助于彌補(bǔ)已有文獻(xiàn)對(duì)于動(dòng)態(tài)能力作用機(jī)制闡明的不足,也回應(yīng)了趙中平等人的觀點(diǎn),即大學(xué)出版社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工作之所以尚未形成常規(guī)性工作機(jī)制,與滿足于傳統(tǒng)出版而造成轉(zhuǎn)型主動(dòng)性不足等因素密切相關(guān)。以往文獻(xiàn)主要研究了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現(xiàn)實(shí)困境和未來(lái)路徑,缺乏內(nèi)在驅(qū)動(dòng)機(jī)制探討和系統(tǒng)性分析。本文基于動(dòng)態(tài)能力框架,考察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階段的不同背景和行為,最終提煉出以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為直接表現(xiàn)形式的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本文推進(jìn)了出版深度融合背景下對(duì)大學(xué)出版社如何轉(zhuǎn)型、轉(zhuǎn)型方向的理論認(rèn)知,避免陷入“模仿—落后—循環(huán)模仿”的困境,為后續(xù)的相關(guān)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第二,本文整合提出了動(dòng)態(tài)能力與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共同形成的“驅(qū)動(dòng)—支撐”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助力機(jī)制,進(jìn)而揭示出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多維度進(jìn)階過(guò)程,能夠有效拓展動(dòng)態(tài)能力和價(jià)值創(chuàng)造的理論內(nèi)涵與適用情境。傳統(tǒng)出版社轉(zhuǎn)型面臨舊模式與新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迷思,但已有研究多忽略了如何分階段、跨層次地考慮轉(zhuǎn)型障礙,對(duì)探討動(dòng)態(tài)能力和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如何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過(guò)程中助力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建設(shè)缺乏充分的理論探討,且與大學(xué)出版社的情境結(jié)合不夠緊密。本文在國(guó)內(nèi)大學(xué)出版社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的迫切需求與能力不足的矛盾情境下,追蹤牛津大學(xué)出版社不同階段轉(zhuǎn)型過(guò)程,提出了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階段形成的“驅(qū)動(dòng)—支撐”助力機(jī)制,強(qiáng)調(diào)動(dòng)態(tài)能力形成與價(jià)值創(chuàng)造模式更新并非孤立運(yùn)行,而是在共進(jìn)中助力大學(xué)出版社突破當(dāng)前階段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障礙,既作用于大學(xué)出版社個(gè)體的問(wèn)題改善與自我升級(jí),將原有大學(xué)出版社的“被迫式轉(zhuǎn)型”躍升為“主動(dòng)式引導(dǎo)”;又促使大學(xué)出版社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向以數(shù)字出版平臺(tái)為直接表現(xiàn)形式的服務(wù)生態(tài)系統(tǒng)邁進(jìn),實(shí)現(xiàn)可持續(xù)共享發(fā)展。這一結(jié)論有助于拓展動(dòng)態(tài)能力適用情境,并延伸傳統(tǒng)的服務(wù)主導(dǎo)邏輯理論,為后續(xù)研究提供新的啟發(fā)。
(二)研究展望本研究嚴(yán)格遵循縱向單案例研究的范式和方法,但仍有以下不足之處,需要未來(lái)研究進(jìn)行拓展。首先,本研究采用單案例研究,雖然盡可能考慮了時(shí)間和情境因素,但是不同出版社在同等情境下是如何利用動(dòng)態(tài)能力應(yīng)對(duì)轉(zhuǎn)型障礙,如何尋找轉(zhuǎn)型方向的,具體表現(xiàn)可能又會(huì)有差別。因此,未來(lái)研究可以不局限于此而選擇運(yùn)用多案例研究進(jìn)行更為細(xì)致的觀察與探究。其次,中國(guó)大學(xué)出版社的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也已經(jīng)取得了一定的進(jìn)展和突破,對(duì)于數(shù)字轉(zhuǎn)型路徑、建議等不乏研究成果。但出版社轉(zhuǎn)型之路一直處于“時(shí)間流”之中,對(duì)于轉(zhuǎn)型實(shí)踐中重要的過(guò)程性問(wèn)題,探索過(guò)程背后的深層驅(qū)動(dòng)和支撐機(jī)制,在研究方法、理論發(fā)展上仍有廣闊空間。
(作者肖超系陜西師范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副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楊龍系陜西師范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2022 級(j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