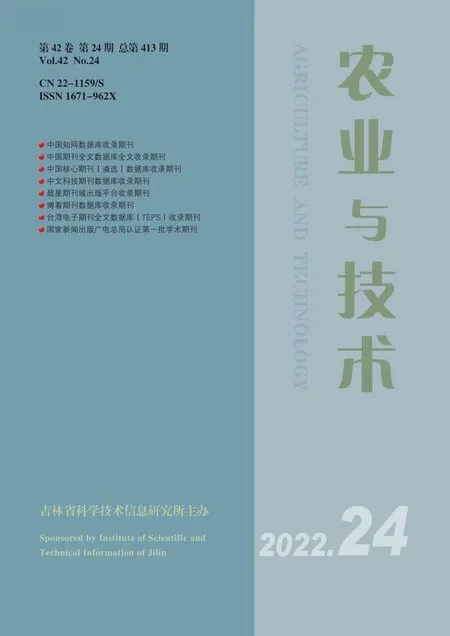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時空變化特征分析
廖洋一 蘇維詞,2 李雪蓮
(1.重慶師范大學地理與旅游學院,重慶 401331;2.貴州省山地資源研究所,貴州 貴陽 550001)
推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是當前我國高質量發展的重大舉措,城鄉融合發展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途徑與抓手。鄉村振興大背景下城鄉融合發展策略問題是黨和政府重點關注的問題,深入研究新時代城鎮化與城鄉融合的重大問題、發展態勢和實現途徑,探討城鄉融合發展的關鍵制度和改革思路,成為當前各學術界亟待解決的問題和學術研究的重點[1]。國外學者對城鄉關系問題的研究較早,如法國學者圣西門、傅立葉和英國學者歐文最早在16世紀對城鄉關系提出相關觀點,并形成了初步的城鄉關系理論,主張消滅城鄉對立[2-4];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城鄉融合是將城市與農村各自的優勢結合起來,彌補各自的短板,尋求城鄉共同進步協調發展[5];麥基以亞洲國家的城鄉發展關系為基礎,對區域內良性城鄉關系定義出城鄉融合區概念[6],總的來說國外多表現為對城鄉關系創新的探討,但是基于具體區域城鄉融合水平的測度研究較少[7]。國內學者近年從城鄉融合概念內涵、評價、發展模式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如張日波指出城鄉融合是區域多維度融合,通過區域內城鄉各層次要素融合發展能夠從各維度縮小城鄉差距,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最終實現城鄉發展成果共享[8];周新秀和劉巖從經濟、人口、社會、空間以及生態環境多個層面構建城鄉融合評價指標體系,利用AHP法對山東省17個地市城鄉融合情況進行探索分析[9];李興科從經濟、社會和政治內涵下構建城鄉評價指標體系,將層次分析與頭腦風暴法2種相結合分析我國城鄉一體化水平發展階段[10];陳艷清將城市與鄉村視為一個綜合體,基于先進典型示范村的發展特色歸納了城鄉融合的5種模式[11]。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國內外學者對于城鄉融合的研究已經相對成熟,提出了許多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和結論,這也是本文深入探究的基礎。但不可忽視的是,微觀層面自下而上探討局域城鄉發展關系的研究較少,基于地理學視角的城鄉融合發展研究體系與框架有待完善[12],城鄉融合綜合測度水平時空異質性的探究尚缺。同時重慶三峽庫區作為全國首個——成渝城鄉統籌示范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庫區城鄉二元結構典型突出,產業“空心化”較為明顯,其城鄉發展在我國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因此,科學測度重慶三峽庫區的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探明其時空演變特征,對于庫區城鄉的協調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研究區概況
重慶三峽庫區地處中國西南內陸地區(E105°49′~110°12′,N28°31′~31°44′),位于中國地勢第2階梯向第3階梯的過渡地帶,地形多以山地、丘陵相間分布,地表起伏較大,區域內總面積達4.3968萬km2,占三峽庫區總面積的77.54%,占重慶市總面積的53.36%[13],共涉及江津、巴南、渝北、長壽、涪陵、武隆、豐都、石柱土家族自治、忠、萬州、開州、云陽、巫溪、巫山、奉節等15個區縣(市)(6個主城核心區城鎮化在90%以上,故不作討論對象)。2019年區域內總常住人口達1353.34萬人,其中822.92萬人為城鎮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2.81%,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60.6%[14];庫區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為2.40,城鄉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比為1.93,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之比為0.91[15]。這表明庫區內部城鄉發展問題客觀存在,在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背景下,有必要對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進行研究。

圖1 研究區位置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文以重慶三峽庫區15個區縣為研究單元,研究年限為2013—2019年,主要數據來源于同時段的《重慶市統計年鑒》《重慶調查年鑒》《重慶數據》、各區縣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國環境監測總站《長江三峽工程生態與環境監測公報》《重慶市新型城鎮化規劃(2021—2035年)》、行政區界線以重慶市2019年劃定成果為準,三峽庫區重慶段地圖、DEM數字高程圖由國家地球系統科學數據中心和地理空間數據云網站獲得[16]。
2.2 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以城鄉融合發展的內涵為基礎,考慮指標選取的全面性、科學性及可收集性原則,借鑒相關研究成果[17-19],從經濟、社會、生活、生態等4個維度上構建包含23個二級指標在內的庫區城鄉融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

表1 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3 研究方法
2.3.1 城鄉融合水平綜合評價模型
本文涉及多個指標,需采用綜合評價模型測度城鄉融合水平。采用極值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用熵值法確定各評價指標權重,最后用加權綜合評價模型測算出2013—2019年重慶三峽庫區綜合城鄉融合水平以及子系統城鄉融合水平。具體計算步驟詳見周文霞等的研究[20]。
2.3.2 探索性空間數據分析
為了更加準確、具體、直觀地分析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評價結果,本文借助ArcGIS 10.5和GeoDa 2個數據平臺,采用全局Moran′s I指數和局部Moran′s I指數分別對庫區城鄉融合水平綜合得分進行全局自相關、局部自相關的度量。具體計算步驟詳見張利國等的研究[21]。
3 結果與分析
3.1 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時序演變特征
運用熵值法對2013—2019年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進行計算,得表2并參考相關研究[22],以0.2、0.4、0.6、0.8為閥值將城鄉融合水平進行分級,分別定義為城鄉融合低水平區、中低水平區、中等水平區、中高水平區、高水平區,再進行空間可視化制圖得圖2。
由表2可知,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綜合水平總體呈不斷上升趨勢,城鄉融合綜合得分由2013年的0.301升至2019年的0.584,年均增長率為11.68%。城鄉融合獲得較快發展的同時,不同維度城鄉融合增長速度存在差異,城鄉經濟融合、社會融合、生活融合、生態融合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3.59%、2.88%、4.83%、4.53%,生活融合和生態融合發展較快,經濟融合穩步提升,社會融合發展較慢。其原因在于,研究期間庫區在互聯網普及率、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人均交通通信消費支出、人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等指標上城鄉間的差異相對較小,對城鄉生活融合水平的提高產生了較大的正向作用;城鄉生態融合水平最低,但提升速度較快,這與庫區整體生態環境建設良性發展和環境污染有效治理有關,建成區的綠化覆蓋率和城市公園建設、空氣污染的治理等方面的指標均表現較好;7a間城鄉經濟融合水平在4個層面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地區經濟發展總值增加、產業結構優化水平不斷提高是城鄉經濟融合水平穩步提高的重要影響因素;從社會保障指標來看,財政收入增速的減緩與民生剛需增加矛盾表現突出,城鄉二元結構差異明顯等社會發展效率問題的存在,導致這一階段庫區社會融合水平增長較慢。

表2 2013—2019年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綜合得分及各維度得分
由圖2可知,2013年庫區城鄉融合發展低水平和中低水平區縣分別是3個和8個,共計11個,占庫區區縣總數的73%,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0個和2個,僅13%,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區縣逐漸增加,2019年中等水平(7個)和中高水平(3個)合計達到10個,占庫區總區縣個數的67%。庫區城鄉融合發展整體水平由研究初期的低水平、中低水平提高到中等水平和中高水平。從研究區內部的總體空間格局分異情況看,城鄉融合水平西南高,東北低,內部空間分異較明顯。西南部的渝北區、巴南區明顯為庫區的經濟重心,其城鄉融合在經濟發展地域條件、產業協調能力、社會公共基礎設施水平和交通通達度都較好,而相比之下,庫區東北部的區縣由于偏離主城區,丟失了重慶經濟發展中心的溢出效應,加之庫區東北腹地的各區縣大多處在山地地形區,交通不暢,對外開發水平較低,產業承接和傳導能力較弱,使得其城鄉融合一直處于較低水平。其中萬州區在渝東北三峽庫區城鄉融合發展較為明顯,萬州區作為渝東北區域的驅動中心,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節點城市,是渝東北三峽庫區重要的生態建設腹地,對周邊開州區、忠縣、云陽縣等地區的虹吸效應明顯,在其本身城鄉融合水平良好的基礎下,水平較高且總體較為穩定。

圖2 2013年和2019年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
3.2 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空間分異特征
采用ArcGIS軟件中的空間統計工具計算2013—2019年的全局Moran′s I指數,見表3。結果表明,2013—2019年的Moran′s I值、Z-score均為正值,且P值均小于0.01,說明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值的空間分布并非隨機的,而是表現出一定的相似值之間具有地理集聚現象。全局Moran′s I指數從2013年的0.8002下降至2016年的0.7976再上升至2019年的0.8079,表明研究時段內庫區城鄉發展的空間相關性先減弱后增強,集聚現象趨于顯著。通過全局Moran′s I指數的波動變化,說明重慶三峽庫區各區縣城鄉融合水平的各維度發展具有快慢之分,由于地區發展基礎條件、發展機遇及城鄉總體治理水平的不同,各區縣城鄉融合水平的速度未達到相對協調。

表3 2013—2019年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的全局空間自相關指數
為進一步探索重慶三峽庫區內部城鄉融合水平的集聚狀況,利用Geoda軟件繪制的2013年和2019年局部Moran散點圖如圖3所示,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空間格局的聚集形態總體較為穩定,高高值和低低值的空間集聚明顯,而高低值和低高值的空間集聚效果不顯著。將庫區城鄉融合水平空間關聯特征進一步劃分為4種不同的類型:高高集聚(H-H),格網自身與周邊格網的城鄉融合綜合得分都較高,主要分布在庫區西南部的渝北區、巴南區、長壽區、江津區、涪陵區,結合城鄉融合水平各評價指標綜合表現來看,這些地區在經濟融合、社會融合、生活融合、生態融合等層面都表現得更為良好;低低集聚(LL),格網自身與周邊格網的城鄉融合綜合得分均較低,主要集中分布于庫區東北部的巫山、巫溪、奉節和云陽等縣,分布較為集中,從城鄉融合的綜合得分情況來看,這些區在農業現代化水平、經濟發展效率、產業協調水平和交通公共基礎等幾類的指標綜合得分較低,城鄉融合水平欠佳;高低集聚與低高集聚(H-L、L-H),格網自身的城鄉融合綜合得分較高(低),但周邊格網較低(高)。重慶三峽庫區的高低集聚區、低高集聚區分布較少且分散,主要表現為武隆區和萬州區。

圖3 2013年和2019年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Moran's I散點分布
4 結論與討論
通過對2013—2019年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時空演變特征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研究期間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城鄉融合綜合得分由2013年的0.301增加至2019年的0.584,城鄉融合水平等級由低水平、中低水平提升至中等水平和中高水平,同時不同維度城鄉融合發展速度有所差異,生活融合和生態融合發展較快,經濟融合穩步提升,社會融合發展較慢;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空間格局呈現出西南高-東北低、內部分異顯著的特征,城鄉融合水平綜合得分均值由高到低依次為庫區尾部(主城及渝西走廊)、庫區中部、庫區腹地,城鄉融合水平具有顯著的空間正相關性,庫區內部大部分區縣高高值和低低值聚類明顯。
本文嘗試性地構建了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評價指標體系,但局限于數據的可收集和處理能力,指標體系的構建多從社會經濟指標等出發,城鄉融合要素收集的動態數據較少,未來可以提高動態流數據挖掘能力,對城鄉融合測度更為精準。在研究尺度上,未來將不斷縮小研究尺度,以鄉鎮尺度具體情況為研究單元,進行城鄉融合水平的分析和具體發展路徑探究,以期揭示城鄉融合現狀格局及問題更加精準。另外,本文僅對重慶三峽庫區城鄉融合水平時空演變進行了研究,今后將根據城鄉融合發展趨勢,結合國內城鄉發展環境和重慶市總體城鄉規劃,預判庫區未來城鄉融合發展走向,為統籌庫區城鄉規劃和精準施策提供科學的參考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