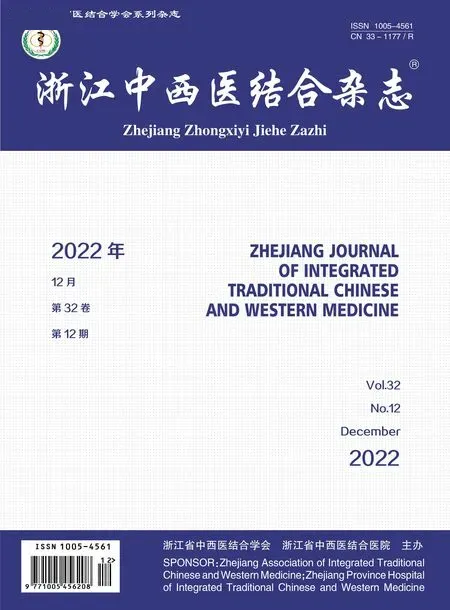疏肝和中湯治療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臨床觀察
許 安 王 峻
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是多種因素參與導致的一種功能性胃腸疾病,其發病原因與精神因素、遺傳因素、飲食因素等密切相關[1-3],其中精神因素在該病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醫學界的重視。目前,對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發病機制認識為內臟高敏感和結腸運動障礙[4-5]。該病并無臟器實質損傷,但長期的不適癥狀會導致患者生活質量下降。臨床治療以胃腸道解痙、抑制腸道蠕動配合腸道菌群調節及抗焦慮抑郁藥為主[2],但多種西藥長期服用,總體效果并不理想。本研究采用自擬疏肝和中湯聯合西藥治療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取得了較好的臨床療效,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18 年1 月至2021 年6 月杭州市紅十字會醫院消化內科及中醫科門診和住院的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70 例,采用SPSS 13.0 版統計軟件生成的隨機數字表,將患者隨機分成治療組和對照組,各35 例。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符合赫爾辛基宣言醫學倫理原則。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 參照《內科學》[6]羅馬Ⅲ標準制定。(1)病程6 個月以上且近3 個月來持續存在腹部不適或腹痛,并伴有下列特點中至少2 項:①癥狀在排便后緩解;②癥狀發生伴隨排便次數改變;③癥狀發生伴隨糞便性狀改變。(2)支持腸易激綜合征診斷:①排便頻率異常(每日排便>3 次);②糞便性狀異常(稀水樣變);③糞便排出過程異常(費力、急迫感、排便不盡感);④黏液便;⑤胃腸脹氣或腹部膨脹感。(3)缺乏可解釋癥狀的形態學改變和生化異常。
1.2.2 中醫診斷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布的《中醫病癥診斷與療效判定標準》[7]制訂:(1)大便次數增多,每天3 次及以上,便質稀溏或呈水樣便,大便量增加;(2)癥狀持續3 個月以上。
1.2.3 中醫證候標準 參照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發布的《中醫病癥診斷與療效判定標準》及國家技術監督局發布《中醫臨床診療術語證候部分》[8]制訂脾虛肝強證候標準:主癥:泄瀉腸鳴腹痛,每因情志不暢而發或加重,瀉后痛緩,乏力,食欲不振,脈弦;次癥:胸脅脹悶,脘腹脹滿,噯氣,食欲不振,口淡口苦,舌質淡紅,苔薄白;上述癥狀分級量化表見表1。

表1 癥狀分級量化表
1.3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符合西醫診斷標準;(2)符合中醫診斷及中醫證候標準;(3)年齡18~60 歲,病程≥3 個月,腸鏡檢查未見明顯異常,肝腎功能正常;(4)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1)經檢查證實為痢疾、霍亂、慢性腸炎以及全身性疾病、寄生蟲感染、惡性腫瘤等導致的腹瀉;(2)合并心腦血管、肝腎、內分泌和造血系統疾病等嚴重原發基礎疾病,或有精神疾病患者;(3)妊娠及準備妊娠、哺乳期婦女;(4)過敏體質及對本藥物過敏者;(5)既往2年內有酒精、藥物濫用或依賴史。
2 方 法
2.1 治療方法 對照組:使用思密達(天津制藥有限公司,批號T2021136847,規格3.0 g)3.0 g,每日3 次口服;地衣芽孢桿菌活菌膠囊(浙江京新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批號H20204568,規格0.25 g)0.5 g,每日3次口服。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自擬疏肝和中湯治療(組成:柴胡10 g,黨參15 g,炒白術12 g,生雞內金9 g,山藥20 g,炒薏苡仁10 g,芍藥、烏梅各6 g,棗肉10 g,干姜6 g,甘草3 g),每日2 劑,水煎,分早晚2 次溫服,上述中藥復方由醫院中藥房提供,藥物購自浙江中醫藥大學中藥購銷中心。兩組均以15 d 為1 個療程,共治療4 個療程。
2.2 觀察指標 記錄兩組患者治療前后癥狀積分、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評分[9]、腸易激綜合征病情嚴重程度量表(IBS-SSS)評分[10]。
2.3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 13.0 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均符合正態分布,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t 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 結果
3.1 兩組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一般資料比較研究計劃入組70 例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其中2 例因其他疾病影響,自動退出,失訪2 例,最終66例患者完成治療觀察,脫失率5.71%。治療組34 例,男15 例,女19 例,年齡(56.38±16.31)歲,病程(5.29±1.23)年;對照組32 例,男13 例,女19 例,年齡(58.21±19.42)歲,病程(5.33±1.68)年。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2 兩組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治療前后IBSSSS 評分、癥狀積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IBS-SSS評分及癥狀積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患者IBS-SSS 評分及腹瀉、腹脹腹痛、腸鳴、口淡口苦癥狀積分均優于治療前(P<0.05),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組患者脘腹痞滿、食欲不振、乏力、噯氣癥狀積分改善優于對照組(P<0.05)。見表2-3。
表2 兩組腹瀉型腸易激合征患者治療前后IBS-SSS 評分比較(分,)

表2 兩組腹瀉型腸易激合征患者治療前后IBS-SSS 評分比較(分,)
注:對照組以思密達和地衣芽孢桿菌活菌膠囊治療;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加自擬疏肝和中湯治療;IBS-SSS 為腸易激綜合征病情嚴重程度量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aP<0.05
3.3 兩組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治療前后HAMA、HAMD 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HAMA、HAMD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治療組HAMA 評分及HAMD 評分均較對照組降低(P<0.05)。見表4。
表4 兩組腹瀉型腸易激合征患者治療前后HAMA、HAMD評分比較(分,)

表4 兩組腹瀉型腸易激合征患者治療前后HAMA、HAMD評分比較(分,)
注:對照組以思密達和地衣芽孢桿菌活菌膠囊治療;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加自擬疏肝和中湯治療;HAMA 為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D為漢密爾頓抑郁量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aP<0.05;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bP<0.05
4 討論
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是最常見的胃腸道功能性疾病,全球發病率約10%~15%[11],嚴重危害患者身心健康。現代醫學研究并未完全闡明腸易激綜合征的發病機制,近年來,“腦-腸”軸功能紊亂被用于解釋該病的病理生理學改變。研究發現,心理社會壓力往往在腸易激綜合征癥狀出現之前就對腸道功能產生影響,針對中樞神經系統的治療也被證實可以改善腸易激綜合征患者的癥狀[12]。目前對于腸易激綜合征的治療主要包括改變生活習慣,使用解痙鎮痛藥物、5-羥色胺3受體阻滯劑、抗抑郁藥物等,但效果并不令人滿意[13-19]。本研究顯示,對照組患者IBS-SSS評分較治療前改善(P<0.05),但乏力、口苦、腹脹等癥狀積分較治療前并未改善,同時焦慮、抑郁量表評分較治療前無明顯改善(P>0.05),認為這些癥狀可能加重了患者的精神心理壓力,從而影響治療效果。
表3 兩組腹瀉型腸易激合征患者治療前后癥狀積分比較(分,)

表3 兩組腹瀉型腸易激合征患者治療前后癥狀積分比較(分,)
注:對照組以思密達和地衣芽孢桿菌活菌膠囊治療;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加自擬疏肝和中湯治療;與本組治療前比較,aP<0.05;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bP<0.05
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屬于中醫“泄瀉”范疇,致病因素有外感六淫,七情內傷,飲食不節。《醫方考》云:“瀉責之脾,痛責之肝,肝責之實,脾責之虛,脾虛肝實,故令痛瀉。”肝郁常源于情志不舒,脾虛則常源于飲食所傷,《景岳全書》曰:“凡遇怒氣便作泄瀉者,必先以怒時挾食,致傷脾胃,故但有所犯,即隨觸而發,此肝脾兩臟病也。蓋以肝木克土,脾氣受傷而然。”因此,泄瀉一病與肝氣疏泄功能關系密切。治療方面,《傷寒雜病論》對于肝失疏泄泄瀉者提出調和肝脾治法。治療本病首先應著眼于調暢氣機,恢復臟腑的升降功能。本院名中醫王峻教授認為,腸易激綜合征為典型的“肝強脾(胃)弱”,其病本為脾胃虛弱,肝強癥狀為脾胃虛弱誘導,且多為脾胃陽虛,患者臨床除易見肝脾不和證候外,多有脾胃陽虛表現,表現為泄出物清稀,味清,泄出后乏力更甚。因此治療該病多從脾胃虛弱之病本出發,尤其注重溫胃健脾,喜用黨參、干姜、官桂、薏苡仁等益氣溫陽健脾,在溫胃的同時又注重“六腑以通為用”“胃腑喜潤惡燥”的特性,加用陰柔之芍藥柔肝健脾,避免溫藥過于燥胃;在此認識基礎上,王教授喜用酸棗仁、烏梅等酸味藥物,達到柔肝、收斂、安神的作用。本研究正是采用了王教授治療腸易激綜合征的常用組方,以柴胡、黨參為君藥,疏肝健脾(胃),白術、生雞內金、山藥健脾助運,芍藥、烏梅柔肝疏肝收澀,棗肉健脾養胃,炒薏苡仁、干姜健脾溫陽,甘草調和諸藥,全方配合嚴謹,共奏疏肝健脾收斂功效。本研究顯示,該復方治療腸易激綜合征可以改善腸易激綜合征患者腹瀉、腹脹腹痛、腸鳴、口淡口苦癥狀(P<0.05),同時改善患者抑郁焦慮狀況(P<0.05),達到肝脾同治的治療效果。
本研究顯示,疏肝和中湯可以改善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患者的部分臨床癥狀,同時可改善患者焦慮、抑郁評分,作用優于單純常規西藥治療(P<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