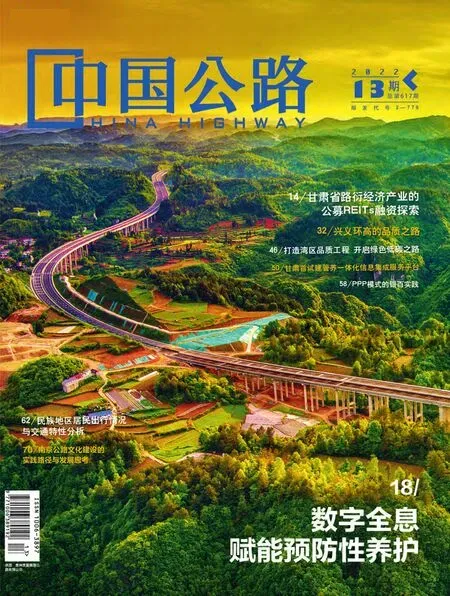執法改革落地中的煩惱和執行中的困惑
文 浮塵
成天一針見血,
自認快意恩仇。
苦心尋章摘句,
風雨中猶清醒。
所謂生民立命,
過眼便成浮塵。
文章若能濟世,
應問懸壺之人。
經過此前的介紹,我們對照改革要求,對行業、改革主持者、參與方和外部環境進行了逐一梳理。形成了“行業不愿執法分離”“改革主持者只管做完前半篇文章”“分離雙方在非對稱博弈中處境尷尬”“外部環境對改革支撐乏力,甚至可能導致工作局面進一步復雜化”等相關結論。下面,接著談談執法改革在落地中的煩惱和操作中的困惑。
落地中的煩惱
“三個不變”削弱了執法行業
“人員身份不變”將部分在崗執法人員擋在了綜合執法的大門之外,客觀上削弱了執法隊伍實力。例如:某省改革前執法持證人員9492人,改革后僅余6582人。
“機構級別不變”阻塞了人員上升通道,自由選擇的天平偏向了級別相對較高的行業部門,為人才進入渠道阻塞埋下了不均衡博弈的隱患,在影響執法延續性的同時,對行業可持續發展構成危害。
“編制總量不變”因人員身份、機構規格等問題疊加,落到執法隊伍的編制實際上已不足改革前的四分之三,且實際到位人員的專業結構、知識儲備、執法實踐均較改革前有明顯下滑趨勢。
簡而言之,“三個不變”實際上造成了執法機構級別相對較低,到位人員數量相對較少,執法能力相對下降。
“自主決策”影響了工作延續
為求穩定,改革在隱秘狀態下推進;為求穩定,改革主持者局部出讓決策權。即:在不違背“三個不變”的前提下,改革模式自主選擇,選擇自由的人員,去向由這部分人自己做主。看似公平的背后,實際上是“局部最優”思維的集中體現。“自主決策”不單是權益出讓,也是力求穩定的權宜之計。在行業接下這根“橄欖枝”的同時,也就意味著要對后續責任做出承諾。
“局部最優”框架下進行的“自主決策”,違背了改革突破常規的最基本要求。因為,“自主決策”并未從根本上厘清行業與執法之間的關系,反而因缺乏有效指導而造成了職能分配多元化的格局。例如:部分執法機構承擔了行業管理職責,部分行業部門承擔了執法任務。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涉改機構部分參與了“自主決策”,一些棘手職能在三定方案中被選擇性遺忘。
以上問題集中表現為后期管理中的“一對多”“多對一”或“找不到對應關系”,直接影響改革后工作對應難度,繼而延長改革“陣痛期”。
思維慣性影響了履職歸位
改革后,行政權力向行業主管部門集中,執法職能向綜合執法機構集中,行業部門承擔行政輔助、技術支撐等事務性和社會公眾服務性工作。職能重新分配后,行業主管部門統攬全局、深度下水的要求呼之欲出;執法機構維護行業秩序、做強法治保障的任務更加清晰;行業部門做好基礎保障、夯實行業基礎的工作更加繁重。新定位、新職能、新角色,需要新形象、新擔當、新作為。
然而,實際與要求之間卻呈現三大反差:
一是角色轉變反差。由于缺乏剛性的考核標準,在思維慣性的作用下,一些主管部門還沒有適應新的工作要求,因循傳統思路思考問題,習慣以行政命令代替自身履職、以“任務分解”搞定本職工作。
二是媒體帶動反差。在最大限度發揮地方積極性,減少執法層級、推動執法下沉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事權范圍內的事,在一些媒體報道的“加持”下,卻出現上級親自過問、親自調度的情況,這與管理事權下放、調用資源下沉的現實相悖,易造成工作錯位、行業內卷。
三是保障與要求反差。一方面,保障類型、保障標準和保障程度等細化指標尚未出臺,資源匹配不到位;另一方面,各種規定不斷翻新,匹配內容越來越多。在地方基礎保障不到位時,上級財政往往以“財權與事權統一”為由,拒絕給予補助資金支持。
“穿新鞋走老路”、媒體“帶亂節奏”、沒有補助凈提要求等亂象,降低了行政效率,也是基層反映集中,影響工作聚焦、歸位履職的焦點問題之一。
操作中的困惑
“增減對比”強烈
前面談到了單位物理分離后,可利用資源減少的情況,旨在講清“減量”造成的工作煩惱應該引起重視。同時引出了媒體帶動“事增”,以及上級要求不斷提高引起的反差。從執法角度分析,這種“減少”背景下的“增多”非常惹眼,在“增減對比”的背后,凸顯出涉改對象的無奈。
隊伍人員減少近四分之一時,執法任務卻從路上覆蓋到了水上,從路政運政延伸到工程質監、水運執法,從“兼職執法”變成了對標軍事化、職業化。簡單來講,就是在隊伍力量被削弱、保障尚未完全到位時,對綜合執法的要求卻越來越高,執法部門的壓力顯著增加。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改革前,執法職能分散在各部門時,執法隊伍承擔的職能相對單一,技術人員可以共用、工作資源可以共享,執法的針對性相對更強。改革后,因分家未能得到的資源,又因單位獨立、領導分設等原因,連共用、共享的渠道都被隔斷了,與改革前相比,執法隊伍可利用的資源不是“做大了”,而是實實在在地減少了。
“強者”主動出招
任務增加不僅體現在有形的改變上,也體現在無形的博弈中。例如,在改革后不久,此前僅以威懾手段存在,連續數年沒有執法案例的領域,便因被認為“沒有主動作為”,影響協調發展。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在海事職能劃分中,一種觀點便以“動”“靜”作為工作界線,認為水上應該與路上比較——靜態的路產路權維護歸交通,動態的交通秩序管理歸交警。
這是一個有趣的觀點,因為選題的原因,本系列文章不宜做深入探討,在此先行按下,待時機成熟后再談。應該說,類似觀點如果在改革之初提出,會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因為這涉及三定方案中的職責劃分、資源調配和基礎保障。但當一切都已經成型,再在執行過程中去談“三定”已定的事項,不合時宜。特別是在“以最大限度保持行業完整性”的改革中,連海事調查官、船舶安全檢查員都沒有劃轉的前提下,非對稱博弈的強勢方這么講,似乎并不妥帖。
談判“三條原則”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后期博弈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觀點,其主要問題在于割裂了改革背景、掐斷了改革思維,站在“局部最優”角度思考工作。相信在后期的博弈中,類似觀點還會很有市場。為避免陷入無休止的爭議,筆者在此提出合作博弈的三條原則:一是“三定方案”是談判的基礎,作為既定規則,不可輕易突破;二是承攬工作必須與人員機構、設備保障等基礎支撐相匹配;三是“裁判員”必須秉持客觀公正,將改革思路延續至爭議解決的全過程。
本期討論中,我們就“三定方案”“自主決策”落地中的問題進行了剖析,基于慣性思維帶來履職偏差,分家帶來的強弱對比得出結論:在最大限度保持行業完整性的改革方案中,執法隊伍力量不是增強而是被顯著削弱,執法隊伍到位人員很難實現工作無縫對接,在面對更高要求時,其在過渡期將面臨很大的執業風險。為盡可能幫執法行業在非對稱博弈中爭取談判籌碼和話語權,筆者試著給出了后期博弈的“三條原則”。那么,萬眾期待的執法協作會是一條通往解決問題的道路嗎?咱們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