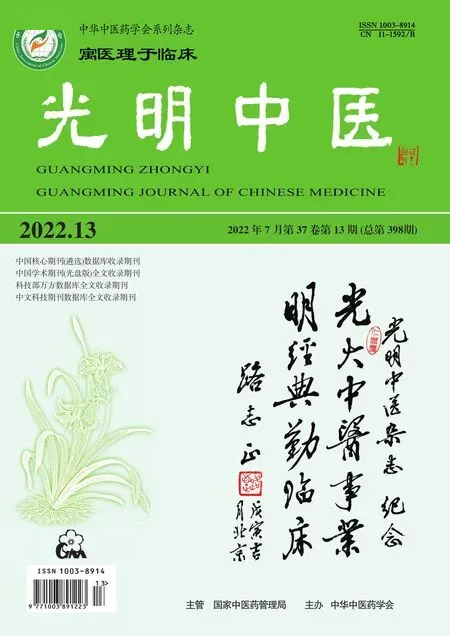魏勇軍教授疏肝祛瘀法治療肝硬化
徐海龍 張軍海 劉雅雪
肝硬化是臨床常見的慢性進行性肝病,由一種或多種病因長期或反復作用形成的彌漫性肝損害。在中國大多數患者為肝炎后肝硬化,少部分為酒精性肝硬化和血吸蟲性肝硬化。病理組織學上有廣泛的肝細胞壞死、殘存肝細胞結節性再生、結締組織增生與纖維隔形成,導致肝小葉結構破壞和假小葉形成,肝臟逐漸變形、變硬而發展為肝硬化。早期由于肝臟代償功能較強可無明顯癥狀,后期則以肝功能損害和門脈高為主要表現,并有多系統受累,晚期常出現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腦病、繼發感染而死亡[1]。目前西醫對肝硬化的治療以保肝、抗病毒降酶及防治并發癥等綜合治療為主[2],雖然近年來核苷(酸)類似物抗病毒藥物的使用使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患者的病情得到一定控制,但由于其耐藥性、價格昂貴,患者依從性差,遠期療效欠佳,復發率高[3]。且其5年生存率僅為55%~84%[4]。
魏勇軍主任中醫師,河北省名中醫,河北中醫學院教授兼碩士研究生導師,河北省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第五批河北省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從事中醫臨床工作30余年,精通中醫經典理論,匯通古今各家學說,善用經方治療疑難雜癥,臨證突出抓主證、審病因、識病機、選方藥四要素,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中醫學中雖無肝硬化這一病名,但根據其臨床表現,可歸屬“脅痛”“黃疸”“積聚”“臌脹”等病證范疇。肝硬化的病因病機復雜,眾多醫家側重點也各有不同。但肝硬化的發展是由氣分入血分的過程,而病情也逐漸加重[5]。在肝硬化的治療上魏勇軍教授認為肝脈不暢,肝血瘀阻為肝硬化核心病機,運用疏肝解郁、活血通絡為主要治療法則而取得顯著療效。
1 肝脈不暢 肝血瘀阻為肝硬化之核心病機。
治病必求于本,疾病的本就是疾病之本質的基本病變。肝主疏泄,性喜條達,主升主動,具有調暢全身氣機,推動血液運行的生理功能。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則氣血調暢,經絡通利,臟腑、器官活動也正常。肝以血為體,以氣為用,主貯藏血液和調節血量,并司全身氣機的調暢,若肝之疏泄功能失常,可直接影響到氣機的暢達。中醫認為“血不自行,隨氣而行,氣滯者,血也滯也”。氣滯于中,血因停積,凝而不散,愈積愈滯,成為積證。魏勇軍教授故指出肝脈不暢,肝血瘀阻為肝硬化之核心病機。
1.1 肝氣不舒 肝脈不暢為先導肝主疏泄,調暢全身氣機,并促進精血津液的輸布,參與脾胃之氣的升降,參與排泄膽汁及調暢情志。當疫癘之邪氣侵襲肝臟,肝主疏泄功能失常,則肝氣郁滯,脾胃功能失常,則出現乏力、厭油膩、黃疸、納差、疼痛等臨床表現。
《素問·五臟別論》中有“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認為五臟產生七情六欲,而七情六欲過及又影響五臟正常的生理功能。而情緒劇烈變化首先影響肝的疏泄和條達。當今社會,生活節奏快,而人們精神也處于高度緊張當中,加之社會和患者本人對肝病的認識不足,“談肝色變”現象普遍存在,而社會各行業的大門也有很多變相地對肝病患者緊緊關閉。且慢性肝病患者,由于病程較長,患者思想負擔較重,更容易出現肝氣郁結的癥狀。趙相英[6]通過調查表明,64.3%慢性肝炎患者存有輕至中度抑郁情緒,60%存在肯定的焦慮情緒。而肝為剛臟,性屬木,喜條達而惡抑郁,感染疫癘之邪后,加之情緒不暢,心情抑郁,內外合邪更加導致肝之疏泄功能失常。
1.2 肝血瘀阻 積聚生焉為病變中醫認為血瘀包括“血”和“脈”兩個方面的病變,在血的方面認為內結為血瘀、污穢之血為血瘀,即所謂“惡血、留血、衄血”等。在脈的方面認為“久病入絡為血瘀,離經之血為血瘀”。明代張景岳《景岳全書·積聚論治》曰:“積者,積壘之謂,由漸積而成者也……是堅硬不移者,本有形也,故有形者曰積”;清朝林佩琴《類證治裁》謂:“諸有形而堅著不移者為積,諸無形而留止不定者為聚,積在五臟,主陰,病屬血分……”,可見積聚之病主臟、主陰而病在血分,與肝硬化時肝臟腫大,觸之堅硬,固定不移的特征完全一致。
肝硬化的血瘀狀況則同樣具有血和脈兩方面的改變。現代研究證實,肝硬化具有肝內微循環障礙,由于肝細胞腫脹或壞死,炎性細胞浸潤,結締組織增生,再生結節的形成壓迫血竇,使之變窄,血流不暢,內結為瘀,肝竇內血行不暢,再加上慢性炎性反應,使肝竇內血液黏滯度升高,成為高凝狀態或小血栓形成,使肝竇內血流瘀滯,同時由于肝內纖維化、假小葉形成,促使肝內血管側支分流形成,又可使肝內有效循環血流減少,肝竇毛細血管化,肝竇內皮細胞孔隙減少而致肝竇血液與肝細胞間物質交換障礙。此外,肝實質細胞凋亡后留下的細胞間隙也將迅速被細胞外基質和膠原所填充,加速肝纖維化的進程[7]。而肝血竇內(如內皮細胞、Kupffer細胞等)NO產生不足以及循環中ET-1、血管緊張素Ⅱ、兒茶酚胺、白三烯等的作用,會使肝血竇阻力增加[8]。由于肝內結締組織增生,使肝臟變硬,肝實質細胞總量減少,影響肝臟的代謝及循環等,進一步引起脾功能亢進、門靜脈高壓、脾臟瘀血等而引起出血,從而又形成了離經之瘀血。而王曉慧等[9]觀察到乙肝肝硬化患者的中醫體質類型呈一定的規律分布,觀察數據指出乙肝肝硬化患者主要以血瘀、陽虛、氣郁體質多見,肝硬度值最高的為血瘀體質患者。
2 疏肝袪瘀為治療大法
中醫學認為“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氣行則血行,氣止則血止”“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血能載氣,血能生氣”等等,在《醫學真傳》中有“人之一身,皆氣血之所循行,氣非血不和,血非氣不運”可見氣血相連,關系密切,即一身氣血不能相離,氣中有血,血中氣,氣血相依,循環不已。肝硬化患者本質乃肝脈不暢,肝血瘀阻,肝郁不舒則脾難健運,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積滯不消而正氣難復。而疏其肝,活其血,祛其瘀,氣血調和,肝臟功能正常,則“結節散,硬變軟”。
2.1 擬方柴胡12 g,當歸15 g,丹參15 g,赤芍15 g,生牡蠣(先煎)30 g,紅花9 g,桃仁9 g,川楝子12 g,郁金15 g,鱉甲30 g,生大黃6 g,水蛭10 g,土鱉蟲10 g。
2.2 加減黃疸明顯者,加茵陳、梔子、金錢草、大青葉;濕熱明顯者,加薏苡仁、土茯苓、龍膽草;轉氨酶高者加垂盆草;腹脹明顯者加紫菀、桔梗;大便溏者加茯苓、太子參;鼻出血者加白茅根;腹水者加己椒藶黃丸。
2.3 方藥分析在疏肝方面,魏勇軍教授首選逍遙散。逍遙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治婦人諸疾》,認為其既能疏肝,又有健脾的作用。魏勇軍教授認為五臟惟肝為最剛,而又于令為春,于行為木,具發生長養之機,一有怫郁則其性怒張。而逍遙散能調營扶土使肝木條達,膽氣宣通,在治療肝硬化上能起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的作用。且服用后使肝氣條達暢通,能讓人感到快樂,把煩惱拋諸腦后。而在活血祛瘀方面,首選抵當湯。抵當湯出自《傷寒雜病論》,其主要用于瘀血發狂、瘀血發黃、瘀血發熱、瘀血經閉、瘀血虛勞等等。清代柯琴在其《傷寒附翼》中謂:“水蛭,蟲之巧于飲血者也,虻,飛蟲之猛于吮血者也。茲取水陸之善取血者攻之,同氣相求耳”;更佐桃仁之推陳致新,大黃之苦寒,以蕩滌邪熱,名之曰抵當者,謂直抵其當攻之所也”。而在實際運用上也遵從裴永清教授[10]之法,以土元易虻蟲,外加鱉甲、牡蠣等藥。清代名醫葉天士曰:“其通絡之法,每取蟲蟻迅速飛走諸錄,俾飛者升,走者降,血無凝著,氣可宣通”,《神農本草經》中說:“水蛭,味咸平,主逐血、下瘀血、月閉、破癥瘕積聚、無子、利水道”,裴永清[10]認為其是“作用最強、最有效、最安全的凝血酶抑制劑”。現代藥理研究也證實從水蛭中分離出的水蛭素為目前最強的凝血酶抑制劑,可阻止纖維蛋白凝固,能活化纖溶系統,促進血栓溶解,對各種血栓病都有效。水蛭素還能明顯降低血小板表面活性,并降低血 小板黏附性,抑制血小板聚集[11,12]。而管麗佳[13]研究發現桃仁單藥能夠有效增加肝血的流量,在提高膠原酶活性和膠原分解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抑郁貯脂細胞的活性化和增殖。《本草綱目》認為:“鱉甲善能攻堅,又不損氣,陰陽上下有痞滯不除者,皆宜用之”。現代藥理研究也發現,鱉甲可以增強肝細胞外的基質合成,改善肝臟內微循環[14]。并且鱉甲能抑制結締組織生成、提高血漿白蛋白[15],可縮小脾臟[16]。大黃有廣譜抗病毒作用,有恢復肝細胞正常功能,促進肝功能再生及肝功能RNA合成,刺激人體產生干擾素[17]。
3 典型醫案
張某,男,56歲。2016年8月10日初診。主訴:全身乏力20余日加重伴腹脹納差1年。患者于20余年前因全身乏力于當地醫院就診,診斷為乙型肝炎,給予保肝治療(具體不詳),患者癥狀好轉后停藥,未定期復查,未治療。一年前,出現肝區不適,腹脹,飲食欠佳,經查:肝功:總膽紅素23.2 μmol/L,直接膽紅素10.8 μmol/L,間接膽紅素12.4 μmol/L,谷丙轉氨酶89 IU/L、谷草轉氨酶62 IU/L,γ-GGT 151U/L,乙肝DNA定量1.23E+05(IU/ml)。肝膽彩超:肝硬化,脾臟大,少量腹水。患者素有大量飲酒史。刻下癥見面色暗,口干苦,不思飲食,時干嘔,腹脹,乏力,肝區不適,大便黏滯不爽,舌下脈絡紫暗,苔黃膩,脈滑。診為肝脾不和,濕阻血瘀之鼓脹。治宜疏肝健脾,活血袪瘀利濕,方用逍遙散方合抵擋湯加減:柴胡12 g,當歸 15 g,赤芍15 g,丹參15 g,桃仁10 g,土鱉蟲10 g,生牡蠣30 g,醋鱉甲15 g,郁金15 g,川楝子10 g,紫菀12 g,桔梗10 g,水紅花子12 g,大腹皮15 g,垂盆草 30 g,金錢草30 g,水蛭8 g,雞內金15 g,陳皮15 g,炒谷芽、炒麥芽各15 g。7劑,水煎溫服,日1劑。2016年8月17日二診。藥后腹脹稍減,口干、口苦改善,食欲增加,繼服上方10劑。8月27日三診。腹脹明顯減輕,無惡心、嘔吐,體力增加,大便日1次,無黏滯不適,復查:總膽紅素13.5 μmol/L,直接膽紅素6.5 μmol/L,間接膽紅素7 μmol/L,谷丙轉氨酶46 IU/L、谷草轉氨酶 45 IU/L。上方去金錢草、垂盆草,10劑,水煎服。9月6日四診。下肢稍浮腫,稍有乏力,余無不適感,上方加防己、茯苓、益母草,10劑,水煎服。后經上方加減治療12個月,經查彩超,肝硬化明顯改善,脾臟縮小,腹水消失,全身無不適感。
按:該患者感染乙型肝炎病毒之后,未加治療和調攝,并長期大量飲酒,導致濕熱之邪蘊結肝膽,久之,濕熱瘀毒阻滯氣機,氣滯血瘀而致肝脾腫大,腹脹納差乏力浮腫等癥,治宜疏肝解郁,健脾化濕,活血消癥,方用逍遙散方合抵擋湯加減,疏肝解郁、活血通絡貫穿治療的始終,期間配合清熱利濕解毒健脾軟堅之藥,守法守方結合辨證施治而效顯。
4 小結
中醫認為肝臟是調暢氣血、促進血液循環的重要器官,肝失疏泄,氣滯血瘀是導致肝功能障礙、肝纖維化[18,19]、肝硬化的主要因素。檢索有關“肝纖維化”的1978—2016 年中國生物醫學數據庫發現,活血化瘀治法文獻頻次最高[20]。而徐列明等[21]認為活血化瘀的關鍵在于有抑制肝纖維化的形成或促使其逆轉的功能。而陳艷等[22]也認為活血化瘀法治療肝纖維化的作用是多靶點、全方位的。在肝硬化的治療上魏勇軍教授始終以肝脈不暢,肝血瘀阻為肝硬化核心病機,疏肝解郁、活血通絡為主要治療法則貫穿于肝硬化的治療始終。在治療的過程中同樣注重祛邪與扶正并重。祛邪尤注重濕,認為乙型肝炎纏綿難愈正是濕邪在作祟,而肝病之發黃正是濕與瘀的結合,故清利大小便配合活血化瘀,使濕邪從二便而出也常見于魏勇軍教授治療肝硬化的過程中。扶正就是補益正氣,人身之正氣不足才感染上乙型肝炎病毒,而正不勝邪不能祛邪外出,正邪糾纏才導致病情纏綿不愈,即使是濕邪較重時也會用上少量補益正氣之黃芪,一是補益正氣,二是健脾化濕。上方為自擬方,為魏勇軍教授治療肝硬化的基礎方,諸藥合用,起到疏通肝之血脈,清除肝之瘀積的作用。肝氣得舒,肝血得活,肝結得散,則硬化易除。魏勇軍教授常說對肝硬化的治療,不可速求,要守法守方,堅持治療,才能獲得滿意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