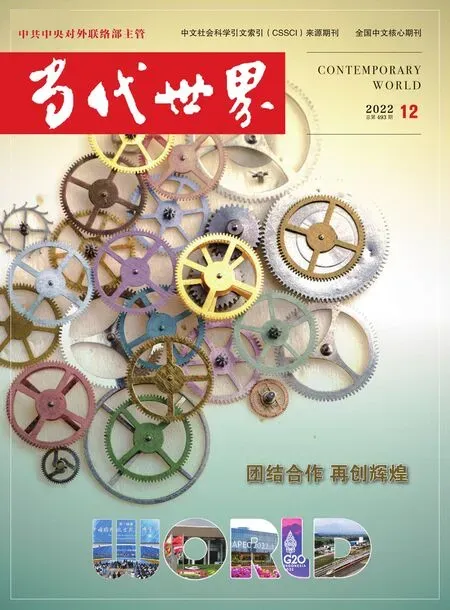地緣政治博弈與中亞地區秩序
曾向紅
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中亞五國獨立30余年來,雖然域內國家間及其與域外大國之間的互動不乏矛盾與沖突,但地區秩序仍整體保持穩定。這是中亞地區與同屬歐亞空間的高加索地區、東歐地區的一個顯著差別。然而,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延、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尤其是2022年1月爆發的哈薩克斯坦騷亂與2月爆發的俄烏沖突,對中亞地區秩序穩定造成了一定沖擊。本文旨在探尋影響中亞地區秩序演變的主要因素及其未來發展方向,這對于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把握好地區熱點問題走向和構建穩定的周邊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中亞地區秩序保持穩定的主要影響因素
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盡管中亞地區局勢起伏波動,國家間關系時好時壞,問題與挑戰不少,但中亞地區并未爆發國家間戰爭,地區穩定局勢并未遭受顛覆性的破壞,中亞地區秩序展現出整體穩定的明顯特征。大體而言,中亞地區秩序的穩定主要受四大因素影響。

2022年9月14日,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參觀者在“上合之窗”活動現場留影。
其一,中亞“準單極”的地區權力結構長期未變。考慮到俄羅斯在中亞的傳統影響及其在中亞事務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俄羅斯可被視為中亞地區權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鑒于俄羅斯的國家實力相較于中亞五國具有明顯優勢,中亞地區格局大致可被視為一種“準單極”的權力結構,且這種權力結構自中亞國家獨立以來未發生明顯變化。這客觀上有助于各國對彼此的行為持有較為穩定的預期,進而保障地區秩序的穩定。
其二,中亞各國長期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為了鞏固自身主權,并盡可能實現利益最大化,中亞國家大多長期奉行以俄羅斯為重點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其中,土庫曼斯坦雖然奉行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但仍要在各域外大國之間尋求平衡,以維護自身利益。通過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中亞各國一方面得到域外大國的諸多支持,并由此在國際交往中獲得諸多收益;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域外大國對中亞事務的肆意干涉,客觀上有助于中亞地區秩序的穩定。
其三,中亞國家摸索出“穩定優先”的沖突管理模式。過去30多年來,中亞五國為處理領土、資源、民族等問題逐漸摸索出一套“穩定優先”的沖突管理模式:各國之間雖然不乏爭端與齟齬,個別中亞國家有時對鄰國表現得比較強勢,但各國主要依靠話語建構、空間管控和經濟手段來應對分歧,而無意通過主動挑起與其他中亞國家之間的矛盾來獲益,從而有效避免了沖突的升級。中亞國家間形成“穩定優先”沖突管理模式,與各國的優先目標在于推進國家建設、維護穩定息息相關。
其四,域外主要大國在中亞采取“可控競爭”的互動模式。與上述第二個因素密切相關,諸多域外行為體逐步形成了一種“可控競爭”的行為模式,這尤其體現在美歐與中俄伊(朗)之間。該行為模式主要基于相關國家對一些“潛規則”的遵守,如不公然挑戰俄羅斯在中亞的特殊地位、尊重中亞國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力促中亞穩定等。這種“可控競爭”互動模式的形成,為促進中亞地區秩序穩定帶來更多確定性。
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對中亞地區秩序的沖擊
近年來,新冠肺炎疫情反復延宕、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俄烏沖突、中亞國家外交政策調整等多重因素導致中亞地區秩序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不過,相較而言,俄烏沖突的久拖不決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事態或許是這些因素中影響最為深遠和持久的。
其一,中亞“準單極”的權力結構出現松動。俄羅斯在哈薩克斯坦2022年1月發生騷亂期間,通過迅速出動集安組織力量幫助哈平叛,極大地提高了其在歐亞空間的威望和影響力。俄烏沖突以來,俄羅斯對歐亞空間的掌控能力是否會下降目前尚難斷言,但西方及其他行為體加強在中亞的滲透之勢已非常明顯。如2022年以來,印度、美國、歐盟、土耳其、日本等均加大了對中亞各國的外交攻勢,明顯是希望在俄羅斯著眼于俄烏沖突而無暇他顧之際擴大各自在中亞的影響。
其二,中亞國家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面臨變數。在此方面的最大變數可能是哈薩克斯坦。一段時間以來,美哈高層互動頻繁。美國高層多次表示支持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于2022年3月16日提出的“全面改革”政治議程,并表示對俄制裁不會給哈薩克斯坦帶來負面影響。托卡耶夫的“全面改革”被認為帶有“西化”的特征。不論效果如何,由于其在中亞國家中的體量和分量,改革成敗均會產生重要外溢效應,或許會影響到其他中亞國家對發展道路的選擇。對于中亞地區秩序而言,在俄羅斯威望和實力均遭到俄烏沖突久拖不決的挑戰這一背景下,哈薩克斯坦是會繼續維持與俄羅斯的親密關系,還是會逐漸疏遠俄羅斯甚至采取親西方路線,其政策選擇將是影響中亞地區秩序的一個重要因素。

2022年1月4日,民眾在哈薩克斯坦曼吉斯套州首府阿克套市中心廣場集會,抗議液化天然氣漲價。
其三,中亞各國內政及彼此間關系的變化對地區秩序演變的影響將更為重要。長期以來,中亞各國的內政或國家間關系雖然存在問題,但并未產生使整個中亞地區失穩的后果。俄烏沖突久拖不決,很有可能使中亞國家的政局變動和國家間關系改變成為影響中亞地區秩序變化的新動因。因持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亞國家近年來面臨非常沉重的經濟發展壓力,西方在俄烏沖突后對俄羅斯施加的強力制裁,更是令與俄羅斯存在千絲萬縷聯系的中亞各國經濟發展雪上加霜。尤其是嚴重依賴俄羅斯僑匯收入的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兩國,其國內政局遭遇的挑戰尤為嚴重。為轉嫁經濟發展面臨的壓力,不排除中亞國家利用民族主義情緒挑起國家間危機,如吉塔邊界摩擦反復出現就與此有關。2022年9月14日,吉爾吉斯斯坦與塔吉克斯坦在雙方邊境爭議地區再次爆發沖突。一旦特定中亞國家出現失穩或中亞國家間爆發大規模沖突,中亞地區秩序將受到沖擊,甚至不排除動蕩蔓延到臨近地區。
其四,大國之間原本存在的“可控競爭”局面或將發生變化。當前西方奉行“雙遏制”的全球戰略思維,即同時遏制俄羅斯與中國。中亞的地理位置使之成為西方實施“雙遏制”戰略的最佳場所。事實上,近年來,美國多次向中亞國家表達了想在中亞重新設立軍事基地的意愿,但中亞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對此屢屢婉拒。根據歷史經驗,其他域外大國尊重俄羅斯在中亞的特殊利益和地位是“可控競爭”互動模式能夠維持的重要前提。一旦相關國家不再顧及俄羅斯在中亞的特殊訴求,那么大國在中亞的競爭將升級,不排除會直接激化各大國以及中亞國家間的矛盾,進而導致整個中亞地區陷入動蕩。
根據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受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影響,維系中亞地區長期穩定的相關因素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與此同時,中亞五國在影響中亞地區秩序方面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們對發展方向的選擇與對彼此間關系的管理將在塑造中亞地區秩序方面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
中亞地區秩序演變的基本趨勢
通過提煉過去30年來有效保障中亞地區秩序維持基本穩定的幾種因素,結合當前地區沖突所展現出來的變化,大致可對中亞地區秩序演變作出以下基本判斷。
其一,中亞地區秩序的演變方向更多受到權力競爭的影響。長期以來,中亞地區是大國博弈的重要場域。正因如此,人們習慣使用“新大博弈”之類的術語或隱喻來概括大國在該地區的互動。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域外大國的權力博弈是影響中亞地區秩序演變的重要因素。此外,中亞地區缺少涵蓋主要域外大國和中亞五國的多邊合作機制,這說明各行為體對于如何參與中亞事務難以達成基本共識,且不愿意放棄主要通過雙邊方式參與中亞事務的路徑。在這種情況下,主要行為體可避免自身行動受到其他大國或多邊機制的束縛,同時可通過行使權力以影響地區秩序的走向。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俄烏沖突令大國競爭或對抗進一步加劇,這種趨勢無疑會波及它們在中亞地區的互動,使各大國將更多地從權力競爭的角度開展互動。如此一來,中亞地區秩序的整體穩定狀態也會因此受到難以預料的沖擊。
其二,各行為體主要受到工具理性而非價值理性行為邏輯的驅動。受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的影響,無論是出于牟利還是止損,某些域內外行為體正加大對中亞地區的關注和投入。盡管互動并不意味著相關國家會徹底拋棄國際社會廣為接受的規范與規則(如主權平等原則、不干涉他國內政原則等),但顯而易見,規范和規則對部分行為體的約束作用有可能會進一步下降。事實表明,在21世紀初歐亞地區爆發所謂“顏色革命”浪潮時,美國罔顧恪守尊重各國主權、不干預他國內政原則,極力推行西式民主和人權議程,給地區秩序帶來較大沖擊。隨著俄烏沖突后美俄關系進入戰略對抗階段,美俄等行為體為增強在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大概率將更多依靠工具理性邏輯來制定各自中亞政策,即在參與中亞事務時更多地計算相關政策的成本與收益,而較少受相關國際規范和規則的約束。這一趨勢不利于維系中亞地區的穩定局面。
其三,中亞五國在影響地區秩序方面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自獨立以來,中亞五國通過積極與域內外各大國互動,積累了豐富的外交經驗。它們在獨立之后能長期保持多元平衡外交政策而未動搖,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地區權力結構為它們靈活調整與各大國之間的遠近關系留下了廣闊的空間。盡管中亞五國在奉行多元平衡外交政策的嫻熟程度方面有所差異,而且特定國家因實施這一政策而遭遇過挫折,但整體而言,各國在30多年的時間里外交手腕越來越靈活、行事越來越老練。面對當前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導致大國競爭升級等問題,中亞五國整體均恪守了中立原則。不僅如此,各國還利用域外大國加大對中亞關注和投入的機遇,積極與之互動,進而與多數大國的關系均有所深化,這說明它們主動塑造地區秩序的能動性在增強,這對于中亞地區秩序的穩定或許是一種利好。

2022年7月21日,第四次中亞國家元首協商會議在吉爾吉斯斯坦舉行。
其四,中亞地區一體化的重啟有望為中亞地區秩序的穩定貢獻積極力量。面對中亞地區權力格局的松動和大國競爭趨于激烈的態勢,中亞各國一方面加強與各大國的互動,希望增強自身對外運籌的主動性;另一方面也意識到聯合自強的重要性,希望借此增強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中亞五國重新聯合自強的動向,大體始于2018年召開的第一屆中亞五國元首峰會。經過四年多時間,中亞五國間的合作取得了積極進展。如2022年7月21—22日,第四屆中亞國家元首協商會議在吉爾吉斯斯坦舉行,這是繼2018年3月、2019年11月、2021年8月之后舉行的最新一次中亞國家元首峰會。此次峰會旨在加強中亞國家間互動并擴大合作,以共同應對區域安全挑戰和威脅。此次峰會成果豐富,如各國發表了聯合聲明;吉、哈、烏三國元首簽署了《21世紀中亞發展友好睦鄰合作條約》(塔、土兩國將在各自國家完成國內流程后簽署該文件);通過了《拯救咸海國際基金創始國元首關于延長拉赫蒙擔任拯救咸海國際基金主席任期的決定》《中亞國家在多邊形式下互動的構想》《中亞“綠色議程”區域方案》《2022—2024年區域合作發展路線圖》等重要文件。盡管中亞五國元首峰會并未改組或升級為正式的國際制度,且未明確峰會的目標在于推動中亞地區的一體化,但在國際和地區形勢更趨復雜乃至動蕩的背景下,中亞五國第四次元首峰會簽署重要文件、達成廣泛合作共識,對于保障中亞地區秩序的穩定無疑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總而言之,展望新形勢下中亞地區秩序的演變趨勢,其中既有令人憂慮的態勢,如大國競爭可能更趨激烈、域內外行為體更多地計算成本與收益而弱化對規則、規范的重視,但也有積極態勢,如中亞國家的能動性在增強、各國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彼此間的團結等。鑒此,中亞地區秩序的長期穩定能否得到保持仍有待觀察。
結語
在當前背景下,中亞地區保持長期穩定的影響因素均受到沖擊。一旦特定行為體的中亞政策變得激進,大國在中亞的“可控競爭”互動模式將被打破,繼而沖擊整個地區的現有秩序和格局。面對地區發展的困難與挑戰,中亞各國一方面積極探索對內政外交政策進行必要調整,另一方面明顯加強了彼此間的合作,希望借此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

2022年8月31日,滿載土庫曼斯坦甘草中藥材原料的中歐班列回程列車抵達西安國際港站。
與此同時,在中亞地區秩序演變的過程中,上合組織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不容低估。在新的國際和地區形勢下,上合組織應切實加強組織建設,開拓新的合作議程,進一步推動構建上合組織命運共同體,同時為促進中亞地區秩序的穩定貢獻力量。目前,上合組織正式成員國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已被接納,而白俄羅斯正申請成為上合組織成員國,埃及、沙特等國也表達了加入上合組織的意愿。如果上合組織能有效應對俄烏沖突、阿富汗局勢變化帶來的各種挑戰,其內部凝聚力和國際地位將會持續提升。總之,中亞國家在對外交往中能動性的提高和當前聯合自強的新態勢,以及負責任的域外大國建設性地參與地區新秩序的構建,有望成為大變局下維系或重構中亞地區秩序的“穩定之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