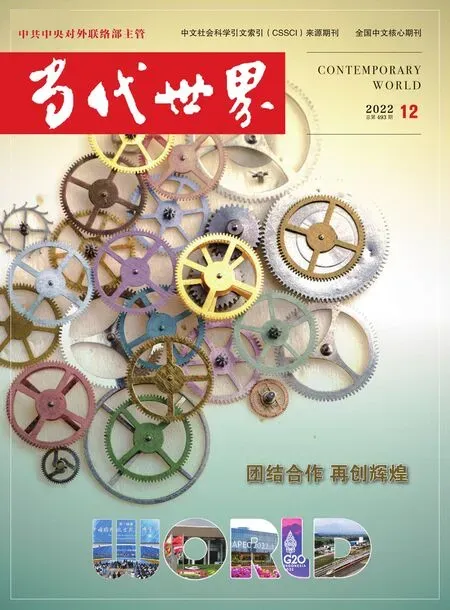拜登政府的經濟外交戰略及其前景
李 巍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發出了消除“特朗普主義”影響、重新激活美國全球領導力的明確信號。拜登政府不再強調所謂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大力推行政府主導的經濟外交,在產業鏈、高端技術、基建和數字貿易等方面構建排他性經濟聯盟。拜登政府一系列重大的經濟外交舉措實質是為了遏制中國,在經濟上構建針對中國的“統一戰線”,通過政府力量強行改變現有全球市場格局。美試圖通過這些舉措將重振國內經濟與強化對華經濟競爭合二為一,由此深刻影響中國發展和安全的外在地緣政治經濟環境。
拜登政府推行以遏制中國為導向的經濟外交戰略
拜登是在美國內外均面臨諸多嚴峻挑戰的背景下上臺的,其走馬上任之后旋即推進包含經濟戰略在內的各種政策議程。拜登政府的經濟戰略分為對內的產業支持政策和對外的經濟聯盟外交兩個方面。在產業政策方面,拜登政府利用民主黨在國會的優勢席位,先后通過了《基礎設施投資與就業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通脹削減法案》,這三個法案是拜登政府在經濟立法上的重大勝利,也構成了“拜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其目的是推動所謂在岸生產、復興本土制造業,以加強其國際經濟競爭力。
美國經濟戰略的實施離不開盟友和伙伴的配合。因此,除了內政措施,拜登政府還在國際上大力推進經濟外交,試圖以所謂經濟安全為旗號構建新的國際經濟聯盟,將經濟聯盟與所謂“民主聯盟”相互協同,打造對外戰略的雙輪驅動。具體而言,拜登政府的經濟外交戰略主要在全球和區域兩個層次展開。
在全球層面,美國主要在供應鏈韌性與基礎設施建設兩個方面發力。在供應鏈外交方面,美國先后主持召開了兩次與供應鏈相關的全球會議,即2021年11月拜登親自召集的全球供應鏈韌性峰會,以及2022年7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商務部長雷蒙多共同主持的供應鏈部長級論壇。兩次會議都是美國為構建供應鏈聯盟所進行的外交努力,體現出美國領導全球供應鏈重塑的雄心。全球供應鏈韌性峰會由包括美國在內的16個經濟體參加,成員均是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國家;部長級論壇有18個經濟體參加,在峰會成員基礎上新增了巴西與法國。相比之下,部長級論壇進一步推進了供應鏈的實質性合作,各方在會后發表聯合聲明,承諾將通過落實透明、多樣、安全和可持續的四項原則,維護供應鏈的長期彈性與穩定。
在基建外交方面,美國推動七 國 集 團(G7)于2022年6月舉行領導人峰會,正式宣布啟動所謂“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PGII)計劃。PGII的前身是拜登政府在2021年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表面標榜助力G7投資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實則是為制衡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拜登宣布美國未來五年內將為PGII籌集2000億美元,并爭取與G7國家共同籌集6000億美元用于全球基建投資。白宮還為此發布備忘錄,將清潔能源、信息和通信技術網絡、衛生系統確定為優先投資的支柱產業。
在區域層面,拜登政府的經濟外交戰略在印太地區、大西洋地區、美洲地區和南太平洋島國多管齊下、全面鋪展。印太經濟框架(IPEF)是拜登政府在亞太地區最主要的對華經濟競爭機制。2022年5月,美國、澳大利亞、文萊、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西蘭、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在東京宣布啟動該框架,太平洋島國斐濟隨后加入,至此,IPEF已有14個成員國。IPEF旨在保障供應鏈韌性,加強清潔能源、數字和技術部門的合作,其四個關鍵支柱為貿易、供應鏈、清潔能源以及稅收和反腐敗,分別對應互聯經濟、彈性經濟、清潔經濟和公平經濟。6月,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召集IPEF伙伴國在巴黎舉行非正式會談,闡述了美國對打造IPEF貿易支柱的愿景,并期望在貿易支柱下啟動談判。7月,IPEF成員國在新加坡舉行首次高官和專家會議,討論框架內的合作內容;同月,戴琪和雷蒙多共同主持了IPEF首次部長級線上會議,各方稱將在上述四個方面加強合作,以建設具有高標準和包容性的經濟框架。9月,IPEF成員國在洛杉磯舉行了首次線下部長級會議,就啟動正式談判達成協議。IPEF填補了美國在印太戰略中經濟合作機制缺失這一空白,表明美國希望重塑區域經濟秩序和復興區域經濟領導力的意向,將對該地區以RCEP和CPTPP為兩駕馬車的既有經濟合作格局形成巨大沖擊。

2022年11月4日,美國總統拜登在加州就《芯片和科學法案》發表講話。
“芯片四方聯盟”(Chip 4)是美國企圖在印太方向構建的另一經濟同盟。這一針對半導體產業的特殊聯盟覆蓋設計、制造等半導體產業鏈各環節,旨在拉攏韓國、日本和中國臺灣等具有半導體先進制造能力的經濟體,并通過構建“小院高墻”將中國排除于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之外。目前,日本和中國臺灣對加入Chip 4的態度較為積極,而韓國由于對中國半導體市場和制造能力依存度較高,對加入Chip 4存在較大顧慮,希望在中美間尋求平衡。
拜登政府的經濟外交也在歐洲方向持續發力。2021年6月,拜登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布魯塞爾美歐峰會上正式宣布成立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TTC)。在某種程度上,TTC以一種新的形式“復活”了此前因美歐分歧而不了了之的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伙伴協議(TTIP),并在貿易之外增加了技術合作內容。2021年9月,布林肯、雷蒙多及戴琪三位牽頭人與歐盟相關負責人在匹茲堡共同主持了首屆TTC部長級會議,標志著TTC作為美歐跨大西洋經濟合作新機制全面啟動。首次部長級會議就推進投資審查、多邊出口管制、人工智能技術的研發和應用規則、半導體供應鏈韌性、應對“非市場經濟體”帶來的挑戰等五個方面達成合作共識。2022年5月,美歐在巴黎召開TTC第二次部長級會議,宣布成立供應鏈、貿易對話等兩個早期預警系統。對于未來的工作安排,會議將氣候變化、綠色公共采購和電動汽車等氣候和清潔能源技術作為對話重點。TTC第三次部長級會談于12月5日在美國馬里蘭州科利奇帕克舉行,會后美歐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在消除歐盟對美國氣候法的擔憂方面取得了進展,但未能徹底解決問題。
美國還在其“后院”發起“美洲經濟繁榮伙伴關系”(APEP)倡議。2022年6月,在洛杉磯舉辦的第九屆美洲峰會上,拜登宣布啟動涵蓋投資、清潔能源、供應鏈和貿易等領域的合作倡議,制定了美國與美洲國家經濟合作框架,稱未來將與合作伙伴討論這項框架并開啟正式談判。雖然這一伙伴關系的細節尚未確定,但毫無疑問,這昭示著美國在美洲的經濟參與程度將大幅提高。

2022年9月13日,由于美國8月份通脹高于預期,紐約股市三大股指大幅下跌。
不僅如此,美國還與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等國聯手在南太平洋地區啟動“藍色太平洋伙伴”倡議(the Partners in the Blue Pacific, PBP),旨在幫助太平洋島國解決氣候變化、非法捕撈等問題,加強五國在太平洋島國的外交存在。此舉是以美國為首的海洋國家在中國和所羅門群島達成新的安全合作框架協議后,針對中國在太平洋地區不斷上升的影響力所發起的遏制措施。總之,拜登政府正在多個層次大力實行經濟外交戰略,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經濟秩序,試圖削弱中國在全球經濟網絡中的地位。
拜登政府經濟外交戰略所帶來的影響
拜登政府的經濟外交戰略主要針對中國,其在全球和區域層面構建的多個經濟伙伴關系都將中國排除在外。這些行為將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三個方面的重大影響。
第一,在全球和區域層面進一步激化中美經濟競爭氛圍。從2010年開始,在美國逐步加大對華遏制背景下,中美經濟競爭色彩開始日益顯著,這一現象在2018年美國對華發起全面“貿易戰”之后更加突出。拜登政府的經濟外交戰略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對華經濟競爭的烈度,尤其是其突出強調與國際經濟合作相關的“國家安全戰略考量”,使經濟要素日益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武器。這使得中美在全球和區域經濟治理中的合作越來越困難。不僅如此,美國針對中國的經濟外交戰略涉及領域越來越廣,包含產業、技術、數字貿易、清潔能源、基建和供應鏈等,使美國對中國的打壓遏制鋪展并滲透到各個經濟領域,也惡化了中美在雙邊經濟關系中開展合作的氛圍。
第二,加劇全球經濟分裂甚至形成兩個平行的市場體系,進而危及全球經濟治理。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美兩國的經濟融合。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逐步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旗手”。可以說,美國的對華接觸戰略是維系經濟全球化進程順利運行的重要基礎。如今,美國放棄接觸戰略轉而采取對華遏制戰略,拜登政府發起的諸多國際經濟倡議大多都以排華為目的,企圖構建不包括中國的新體系。但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一大制造業大國、世界13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世界離不開中國。美國的經濟外交逼迫多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嚴重干擾了全球市場的正常運行,與美國一貫標榜的所謂自由國際秩序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必將加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混亂,引發國際規則競爭與沖突,從而與真正的經濟全球化漸行漸遠。
第三,壓縮中國經濟發展空間并危及中國經濟安全。拜登政府經濟外交戰略涉及印太、歐洲、美洲、南太平洋等多個區域,幾乎遍布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聯合其盟伴擠壓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空間,如中歐全面投資協定(BIT)、中國與中東歐合作機制等中國力推的國際經濟合作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因美國的施壓而遭遇障礙。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優質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正常業務拓展也因為美國的經濟聯盟外交而大受阻滯。而PGII的目標更是直指“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合作造成了一定沖擊。不僅如此,美國通過這些林林總總的經濟合作框架,試圖重塑全球產業結構,主要體現在推動高端產業回流美國本土以及推動中低端產業轉移至印度、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這將危及全球的產業安全和經濟秩序穩定。
總之,拜登政府上臺以來,推出了一系列眼花繚亂的經濟外交舉措,試圖建立一堵包圍中國的“圍墻”,其根本目的是借助地緣政治力量削弱中國的供應鏈優勢,進而打擊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拜登政府經濟外交戰略面臨的挑戰
盡管拜登政府的經濟外交戰略看似緊鑼密鼓、聲勢浩大,但有多少政策舉措能夠最終實質性落地,還存在諸多變數。回顧歷史,美國的不少內政外交政策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后草草收場不了了之。拜登政府經濟外交戰略的限度,主要緣于美國國內與國際社會的雙重壓力,并且還要面對具體領域政策實施中的諸多障礙。
在國內層面,美國的經濟外交戰略面臨民眾是否支持與政治如何搖擺的雙重難題。一方面,拜登政府權力穩固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于得到國內中產階級的支持。而作為美國支柱的中產階級主要關注國內經濟發展,而非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國際戰略,他們對于拜登政府將大量資源投入到經濟外交上的支持力度有限。雖然拜登政府稱美國外交政策是為“更好地服務于中產階級”,以捆綁內政與外交的方式博取民眾好感,但關注經濟增長與就業崗位的中產階級更加看重直接且短期的結果,而非動員式的口號。

2022年5月17日,學生在紐約大通銀行總部外集會,抗議石油投資并呼吁關注氣候變化。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的經濟外交戰略能否發揮效果還需考慮美國政黨輪替的因素。拜登政府的這些經濟外交舉措,需要長期一以貫之的努力,而難以在短期內見效。但是美國業已形成的極化政治和否決政治將妨礙美國經濟外交戰略的連貫性。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奧巴馬政府八年經濟外交努力在旦夕之間就付之一炬,導致外交資源大量浪費,美國兩黨政治的荒謬性可見一斑。在2022年美國中期選舉中,共和黨以微弱優勢擊敗民主黨拿下眾議院多數席位,府會一致的局面被打破,拜登政府的經濟外交戰略必然會受到共和黨領導的眾議院的諸多掣肘。兩年后的總統選舉也是政策延續的難關。拜登政府能否在兩年之后連任已成重大懸念,在這種背景下,拜登政府主推的多個國際經濟合作機制和倡議能否熬過政黨輪替這一關,充滿巨大變數。
在國際層面,美國同樣面臨著重大的盟伴分歧,其盟伴們不完全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的經濟外交戰略旨在聯合盟伴共同遏制中國,但對于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而言,遏制中國不僅不是他們的利益所在,而且會使他們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不少國家難以心甘情愿搭上美國的“戰車”,只是在美國的脅迫和利誘之下“逢場作戲”。俄烏沖突更是對美國和西方領導下的世界秩序造成了巨大沖擊。在俄烏沖突中,印度、沙特等國采取了與美國不同的行動與立場,更是放大了區域多元性和差異性。在美國國際領導地位相對下降的新階段,挑戰來源的多元性、美國與盟伴之間的利益分歧等因素,對美國的國際協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將增加美國彌合伙伴間分歧以形成合力的成本。
不僅如此,美國目前推動的印太經濟框架、美洲經濟繁榮伙伴關系等都是比較松散的合作倡議,缺乏執行上的約束力,雖然大多已經確定原則和方向,但尚未出臺具體的路線圖。如果美國不能提供實質性的好處,僅讓盟伴充當排華反華的排頭兵,恐怕難以得償所愿。實際上,未來美國經濟外交的諸多倡議成效如何,都要取決于其執行力。如果這些框架沒有具體落實的動作,而只停留在口號與倡議上,美國的盟友和伙伴也將虛與委蛇。比如,作為印太經濟框架重要成員的印度,在參加完2022年9月舉行的印太經濟框架首次線下部長級會議之后便明確表示,因“看不到好處”而退出該框架四大支柱之一的貿易領域的談判。
相比之下,中國的諸多優勢會對拜登政府的經濟外交戰略形成強大的對沖之勢。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在基礎設施、市場規模、人才儲備和產業集群等方面積累了巨大的優勢。這些優勢對于全球商業力量而言,已然形成一種強大的“磁場效應”。拜登政府企圖通過經濟外交戰略改變市場格局猶如逆水行舟,畢竟市場的主體是企業而不是政府,企業以追求利潤為宗旨,未必會完全遵照政府指揮而違背市場規律。
結語
相較于特朗普政府,作為美國建制派力量的代表,拜登政府的國際戰略從制定到實施都在恢復其正常狀態。與歷屆美國政府相比,經濟外交是拜登政府國際戰略的重要新內容,其在全球和區域兩個層面都推出了諸多新的經濟合作倡議。這些倡議主要針對中國,無疑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安全造成一定沖擊,但最終有多少能夠落地仍需觀察。
面對拜登政府經濟外交戰略的全面打壓與圍堵,中國需要充分發揮在基礎設施、市場規模、人才儲備和產業集群等方面業已形成的巨大優勢,通過積極構建最廣泛的經濟伙伴關系網絡,來化解美國施加的遏制戰略壓力。相較而言,中國需要推動中日韓和中國—海合會這兩大自貿區談判盡快取得進展,進一步深化與東南亞國家的多領域合作,全面加強和東盟這一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在經濟上的精準對接。同時,實施差別化的經濟外交政策,重視對歐洲的經濟外交,積極應對美國的“小院高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