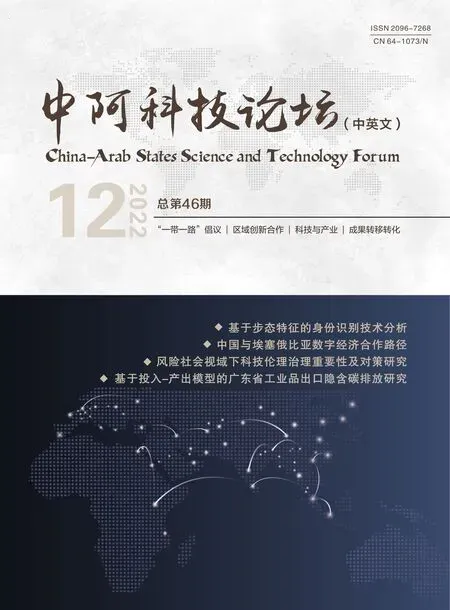技術(shù)賦能下《流浪地球》中的主旨表達與敘事方法
田李艷
(北方民族大學,寧夏 銀川 750000)
開始沒有人在意這場災難,山洪、旱災、物種滅絕,直到城市消失,災難與人息息相關。確實,在鏡頭跳躍中飛鳥漫天,猴子孤零零地觀望,人類的生存空間給人以不適的恐怖之感,面對令人擔憂的地球生態(tài),面對無法延續(xù)生命的世界,人類致力于開拓新空間,科幻作家們大膽想象,依據(jù)科學規(guī)律,揣摩建構(gòu)未來社會,《流浪地球》這部電影便做出了探索新世界的大膽嘗試。
1 技術(shù)賦能:多媒介表達中的視覺呈現(xiàn)
1.1 技術(shù)賦能創(chuàng)建影視空間
根據(jù)媒介延伸理論,未來媒介的發(fā)展包括三方面:延伸人類的生命、延伸人類創(chuàng)造的媒介以及延伸人類生存于其中的真實世界[1]。事實上,科技的發(fā)展已經(jīng)證實了這一理論。電影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類的生活方式。中國電影在中國文化上加持科技元素,使得中國科幻電影給人煥然一新的感受。
“空間性和人類的存在與生俱來,人類生活的空間維度深深地關系著實踐與政治。”[2]人類的生存空間因科技的進步與革新在實踐中變化與開拓。《流浪地球》以科技為媒介延伸著人類、生命和虛擬仿真的生存空間。影片立足人類大膽想象的“流浪計劃”,通過科技在視覺上、地理空間呈現(xiàn)上構(gòu)成了領航員國際空間站、地下城和地面生活區(qū)三大景觀。由于影視視頻的變化性、流動性、跳躍性及碎片化零散片段的景觀呈現(xiàn),在時空流動中展現(xiàn)人類的設想必須有強大的科技支持。影片中,國際空間站、地下城和地面生活區(qū)的呈現(xiàn)得益于強大的技術(shù)支持,其中以國際空間站、地下城最為明顯。技術(shù)賦權(quán)讓人類創(chuàng)造出類似烏托邦的虛擬世界,利用技術(shù)從時空、色彩、敘事等方面將事物的本體“搬”到電影中,通過數(shù)字繪景、光效、三維特效造型、虛擬現(xiàn)實(virtual reality,VR)技術(shù)造型、音響合成音效等高科技手段打造科幻場景。同時,人類去火星重建人類文明,建立人類文明數(shù)字資料庫,都離不開科技的支撐。
1.2 數(shù)字化技術(shù)創(chuàng)新視聽表達
科學技術(shù)不斷發(fā)展,走進人類生活,滲入各行各業(yè)。數(shù)字媒體技術(shù)進入影視藝術(shù)領域,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媒介技術(shù)的革新發(fā)展開始推動人類生活從空想走向真實,仿真化、虛擬時空變?yōu)楝F(xiàn)實。媒介技術(shù)深刻地影響了影視藝術(shù)。《流浪地球》在技術(shù)的支持下展開了不同的視覺景觀。運用雙鏡頭3D攝像技術(shù)、3D技術(shù)特效鏡頭、電腦特效合成技術(shù),打造出各種工業(yè)質(zhì)感的發(fā)動機、補給站、空間站等。鏡頭特寫酒瓶加火花燃燒的畫面,展現(xiàn)地下城全景圖。空間定位技術(shù)、車載通信、實時遙感測繪技術(shù)實現(xiàn)在太空對地下災難的實時關注。發(fā)動機燃燒噴射的火焰與空間站爆炸的火焰畫面,以及木星與地球的光暈呈現(xiàn)都是基于畫面光效的應用。
利用數(shù)字媒體合成技術(shù)可對視頻、音頻、圖像等要素進行處理合成,增強影視作品的視聽效果。影片中創(chuàng)造性地制作了肉眼可見的大片雪花在空中飄灑,展現(xiàn)出極寒天氣下的惡劣環(huán)境。快鏡頭展現(xiàn)滾石災難和持續(xù)從天而降的煙霧,慢鏡頭展現(xiàn)殘骸“漫天飛舞”。虛擬現(xiàn)實地震,虛擬技術(shù)還原了地動山搖的災難場景。3D立體環(huán)繞視聽技術(shù)的應用,打造出韓朵朵被劉啟帶走制造教室混亂時的音響畫面,虛擬地下城風暴場景讓人們身臨其境。這種虛擬技術(shù),實現(xiàn)對災難景象的虛擬再現(xiàn),讓觀眾獲得身臨其境的體驗。
可以說,在電影《流浪地球》中,演員操控現(xiàn)代化設備機器,人機努力合二為一,這類通過科技實操推動影視情節(jié)發(fā)展的方式比比皆是。各種媒介手段的使用使得電影呈現(xiàn)出宏偉又具有強烈代入感的視覺效果,特別是通過電腦動畫技術(shù)實現(xiàn)航天員在太空迅速拉隊友的一組連續(xù)、完整的鏡頭,令人驚艷。
2 主旨表達:景觀書寫下的中國精神
2.1 透過景觀書寫,反思技術(shù)利弊
技術(shù)作為現(xiàn)實的鏡子,技術(shù)手段加持在影片中,把自然景觀人文化處置,寄托著作者的思考。影視來源于生活并超越生活,影像展現(xiàn)著時代景觀的同時又對人類進行自我反思、自我關照,也寄托著人們的審美想象與期盼。《流浪地球》反思著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寄托著人類對新空間的探索與希望。
生存環(huán)境“景觀”進入文學作品中,是指帶有地域性、處所性和場景性的地方和地點所呈現(xiàn)出來的自然屬性特征所具有的感性面貌,也可以說是以一個地方的自然地理感性形式呈現(xiàn)給人的視覺效果[3]。而社會人文景觀是包括人類及人類各種實踐生產(chǎn)生存的活動。影片中的景觀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產(chǎn)物,印上了人類活動的痕跡,是觀眾觀賞時感性直觀與審美思考的基本媒介。影片中,領航員國際空間站救援隊掃描地貌準備救援,紅色的警報燈閃爍不止,隱喻了在整體的冷色調(diào)和暗色調(diào)下,危險與希望共存。影片特寫鏡頭劉父告別親人去執(zhí)行任務,充滿了溫情;韓朵朵上課談論“希望”的話題,暗含人們渴望美好;人間煙火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特寫,體現(xiàn)了地面生活的生機。在鏡頭的變化中,觀眾看到了空間站的探索景觀、地下城的災難景觀和地面城市相對和諧溫馨的景觀,在自然景觀、人文景觀的切換中,感受到作者的生態(tài)憂患意識,同時也看到了中國希望。
“哈貝馬斯認為,隨著現(xiàn)代技術(shù)的誕生,出現(xiàn)了技術(shù)力量的倒置:技術(shù)由本來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中解放人類的力量,變成一種政治統(tǒng)治的手段。”[4]技術(shù)帶來便利和希望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的隱患。影片中,沒有地下城、空間站的開拓,就沒有地下城的死亡、空間站執(zhí)行任務的犧牲。自然景觀反映了環(huán)境惡化的生態(tài)問題,以人文景觀襯托出的自然危機,實際上是社會生存困境與人性弱點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在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交織中,人們思索著科技的進與退。人類和科技是逾越不了宇宙的,在宇宙之外可能有更大的世界。人類借助科技建設新秩序、新空間的艱難與教訓,科技世界以冰冷的姿態(tài)提醒人類應該遵循自然規(guī)律、愛護地球。對世界的探索萬萬不能破壞自然,在宇宙面前人類是渺小的,人類過度建設必將走向毀滅。宇宙規(guī)律的冷酷以絕對優(yōu)勢壓倒了人對自我的肯定,而人類所付出的代價是慘重的。
2.2 透過家園的破與立,審視中國精神
2.2.1 家園情懷推動流浪之旅
“家園意識”在文學命題的傳承中是一種文化因子,“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漢書·元帝紀》)。這種“故土難離”的生存觀,是中國傳統(tǒng)觀念的體現(xiàn),也是中華五千年農(nóng)耕文明的沉淀,濃縮了中國人民最樸素的家園觀[5]。影片開始講述了劉培強告別地球去執(zhí)行任務的不舍與堅持,以犧牲“小我”陪伴孩子的時間,換取小家大家的延續(xù)。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家園意識就是“家國天下”,有家有國有天下情懷。“家國”不僅是廣義上的土地和人口,更多的是一種文化精神。在這種文化氛圍中,中國人注重自己的身份認同,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沖突下,人們選擇放棄自己的私利轉(zhuǎn)而保全家庭和國家。家園意識內(nèi)化在每個人的血液里。俄羅斯領航員在空間站帶著的伏特加代表著他的家園情結(jié),爺爺懷念奶奶的飯是他的家鄉(xiāng)情結(jié)。北京三號地下城賣東西的市井煙火氣息,人們打麻將、過年舞獅子的氛圍感,充滿著濃郁的家的味道。影片中的親情讓人感動,多次插敘劉培強參與和關注兒子地下救援的畫面彰顯了父子情,姥爺去世前叮囑劉啟帶韓朵朵回家彰顯了子孫情。劉啟與朵朵共同成長的兄妹情,救援隊隊員團結(jié)作戰(zhàn)的戰(zhàn)友情與兄弟情,人類對地球的依戀之情,這些情感使得人心相通,以人間的溫情戰(zhàn)勝末日的冷酷無情。
海德格爾在《返鄉(xiāng)——致親人》中曾言:“‘家園’意指這樣一個空間,它賦予人一個處所,人唯有在其中才能有‘在家’之感,因而才能在其命運的本已要素中存在。這一空間乃由完好無損的大地所贈予。”[6]影片多次慢鏡頭插敘劉培強看家人合照,即使身在太空站,他最牽掛的仍然是地球的親人們,他的歸屬依然是小的家庭和大的國家。中國人擁有濃厚的鄉(xiāng)土情懷和家園意識,面對家園即將毀滅的危機,人類萬眾一心帶著家園一起流浪。只有在地球家園中,人類才有安全感。
“返鄉(xiāng)”是文學作品中經(jīng)典的主題,體現(xiàn)了中國人的家園情懷。習近平多次強調(diào)要大力弘揚“家國情懷”,對文化文藝工作者提出要求:“要有信仰、有情懷、有擔當,樹立高遠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國情懷,努力做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有貢獻的藝術(shù)家和學問家。”[7]《流浪地球》以“流浪”的形式推進,人類最終要去向新的家園,家園是人類的根基。電影中“回家”的呼聲最高,家?guī)缀跏敲總€人的追求。“家”不僅指角落里的房子,還指親人及精神寄托。朵朵認為爺爺?shù)碾x開就是家園的丟失。影片中人們都有著“回家”的心愿。當姥爺韓子昂奄奄一息時,他叮囑劉啟“戶口,當哥哥的,要照顧好妹妹,帶朵朵回家”,朵朵說“我想回家”,劉啟等執(zhí)行完任務后要和爸爸在家團聚,人類渴望回歸家園。不僅是人類,生物也渴望回到地球家園,鯨魚游這么遠,應該也是為了回家吧。地球的生命都在流浪,都在渴望回家。
2.2.2 命運與共展現(xiàn)大國敘事
2020年11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利雅得峰會“守護地球”主題邊會上致辭強調(diào):“地球是我們的共同家園。我們要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攜手應對氣候環(huán)境領域挑戰(zhàn),守護好這顆藍色星球。”[8]《流浪地球》以大國外交的視野展開了中國的大國敘事立場,很好地詮釋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影片書寫中國式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人類團結(jié)協(xié)作,舍小家為大家,勇于拼搏,勇于奮斗,克服一切苦難,保護人類共有家園——地球,體現(xiàn)中國的責任與擔當。相比好萊塢科幻電影對地球災難的解讀,中國文化之下,拯救地球的不是美式的個人英雄主義文化,不是一兩個“超級英雄”。祖國是人民最堅實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在我國集體主義的文化下,拯救地球的是每一個普通人,每一個普通的英雄。影片中,劉培強多次欲救援兒子而違規(guī)操作,受到聯(lián)合政府的批評。他盡管擔心小家,卻依舊選擇將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救援工作中,擔當起執(zhí)行任務的重擔,助力地球逃離太陽系前往新家園。韓子昂作為運輸車駕駛員,勇?lián)\送“火石”、重啟行星發(fā)動機重任,在生死關頭,把生的希望留給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劉啟在“流浪地球”計劃中失去至親爸爸和爺爺,毅然堅持著尋找新家園的計劃。這些平凡的小英雄,在災難面前,挺身而出,不畏犧牲,拼力救援,平息災難。這正是平凡中國人的不凡擔當。
領航員國際空間站莫斯、技術(shù)員李一一等所有參與“流浪地球”計劃的人,都在為逃離太陽系,尋找新家園而努力,團結(jié)就是力量。“流浪地球”計劃的成功是全人類共同努力的結(jié)果,木星點火任務是由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救援隊員集體共同協(xié)作完成。人類的命運是一體的,在經(jīng)濟全球化、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勢下,人類同呼吸,共命運,共擔當,尋找家園。影片也證實了只有各國人互相幫助、鼓勵、支持才能贏取最后的勝利。
中國科幻電影呈現(xiàn)中國電影的全球敘事,影片將我國東漢時期張衡發(fā)明的地動儀廓形作為發(fā)動機核心造型,并以現(xiàn)代火箭推進器內(nèi)部結(jié)構(gòu)為參考構(gòu)建其巨大的內(nèi)腔結(jié)構(gòu),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工藝造型與現(xiàn)代科技相互結(jié)合的整體風格,增強了視覺、聽覺等多方位的刺激感,提升了觀眾的感官體驗[9]。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發(fā)展中華文明、實現(xiàn)民族復興的強大根基和不竭動力。不忘歷史,繼往開來,要在傳承古代技術(shù)文明中不斷前行。中國科幻電影要想融入當今科幻潮流,進一步走入國際科幻市場,必須講好中國故事,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
3 敘事策略:傳遞中國智慧
3.1 敘事線索的鋪展
技術(shù)重構(gòu)了電影時空,觀眾可以通過電影對任何時間的任意空間有所了解[10],在時空變換中,故事的敘事視角靈活多變。我國的科幻電影仍處于探索發(fā)展階段,國產(chǎn)科幻電影在不同的主題和情節(jié)下采用的是相同的敘事結(jié)構(gòu),即因果式線性結(jié)構(gòu)。根據(jù)事件發(fā)生的起因、經(jīng)過、結(jié)果展開敘事。影片的開始就告知觀眾:起初,沒有人在意這場災難;后來,災難和每個人息息相關。300年后太陽系不存在,聯(lián)合政府計劃移民,將地球推出太陽系。這也就是流浪地球故事的前因后果。流浪地球的起因是地球災難頻發(fā),300年后太陽系不存在了,人類為了延續(xù)文明而開啟計劃。經(jīng)過是在聯(lián)合政府的指導下,全世界各國人民將帶領地球一起逃亡至火星。結(jié)果是人類以慘重的代價逃離成功。這種按照正常時間順序的常規(guī)線性敘事模式,看起來清晰簡單。
“中國式盒子”是這類復調(diào)式敘事結(jié)構(gòu)的形象比喻,指一個敘事層面的表述被包含在另一層面里。影片中人物既承擔第一層面的敘事角色,又擔當嵌套在第一層面中的第二層面的被敘述者,完成復調(diào)式敘事職責[11]。影片《流浪地球》有兩條線索,一是以劉培強為主要人物展開敘事,以劉培強告別親人,去空間站執(zhí)行任務為主線,貫穿影片始終,以劉啟、韓朵朵去地下城及獲救為高潮,結(jié)果是在劉培強的幫助下救援成功。二是以劉啟、韓朵朵為主人公視角敘事,劉啟帶著妹妹偷偷去地下城,爺爺前來救援,被迫加入逃離計劃,經(jīng)歷各種危險最終爺爺死亡,而劉啟他們在父親的幫助下獲救。整個故事中,空間站有引領地球行進、監(jiān)控地球前進軌跡并負責協(xié)調(diào)地球表面各發(fā)動機間關系的作用。復調(diào)式敘事結(jié)構(gòu)的電影各條線索“缺一不可,相互闡明,相互解釋,審視的是同一個主題,同一種探詢”[12]。這一開放式的“主觀化”,從多個敘事層面、多個角度展現(xiàn)一個故事,劃分明晰,旨在對事件進行客觀表現(xiàn)或多層探討,豐富文本闡釋。這樣不僅打破了單一敘述視角的平鋪直敘和枯燥乏味,更容易在劇情中設置懸念,以此引發(fā)觀眾主動地進行多重維度的思考。
3.2 敘事手法的應用
中國影片結(jié)合視覺、聽覺元素,運用插敘、倒敘和順敘的手法,利用影視蒙太奇手段進行層級嵌套結(jié)構(gòu)的敘事。關于這一人文精神重構(gòu)的方法,詹秦川等認為影片通過空間場景建構(gòu)、人物情感表達以及多條敘事線的沖突三個層面來完成[13]。不僅通過這三個層面構(gòu)建人文精神,還運用了視聽元素、插敘的手法和蒙太奇手段。《流浪地球》把故事放在執(zhí)行宏大太空任務的背景之下,將空間鏡頭、人物視點鏡頭、回憶鏡頭等來回切換進行聯(lián)結(jié),在空間站、地下城景觀、人物間不斷切換鏡頭,在劉培強救援時還插入劉啟對父親的不滿,這與影片開始劉啟對劉培強的離開疑惑與不滿構(gòu)成呼應。這種呼應與對比更加凸顯人物性格和精神。靈活而自由的敘事手法,使觀眾不自覺地進入驚心動魄的救援故事之中。
3.3 敘事模式的打造
美國劇作家悉德·菲爾德所開創(chuàng)的三幕式理論是情節(jié)結(jié)構(gòu)安排的一種經(jīng)典范式[14]。《流浪地球》在情節(jié)安排上基本遵循著三幕式理論,以三個空間的切換來推動故事的進展。第一幕介紹流浪地球的主要人物、流浪原因以及流浪條件和準備,第二幕是主人公經(jīng)歷逃離過程中的挫折與困難,第三幕是交代流浪結(jié)果,以慘痛的代價獲得成功。三幕式理論使情節(jié)緊湊、關聯(lián)性強,故事內(nèi)容清晰明了。影片是在“當下”和未來的“虛擬現(xiàn)實”時空之間穿梭展開。建構(gòu)了故事發(fā)生的時間是距今半個世紀以后的2075年,影片大半部分是在講述虛擬未來的故事,而地下城生活就最能體現(xiàn)虛擬世界。
熱奈特的上帝視角(全知視角)敘事,即敘述者>人物。電影的敘述者以全知視角進行敘述,領航員國際空間站總控室引導了此次救援,總控室預測到木星會和地球相撞,啟動災難預警程序向聯(lián)合政府通報,為國際空間站備用補給導航儀啟動人工矯正程序。劉培強作為領航員國際空間站的工作人員,他既知道空間站的情況,又知道地下救援情況,對整個故事的發(fā)展了如指掌。
《流浪地球》一上映就獲得追捧,該影片的創(chuàng)新對于國產(chǎn)科幻電影而言意義重大。它開始探尋新的敘事模式,進行創(chuàng)新的藝術(shù)實踐,將一貫單純的線性時間線變成了在時空里可以首尾相連、首尾呼應、周而復始的圓圈。首尾呼應的敘事,加深了觀眾對影片及其主題的印象。首尾呼應的同時,影片也遵循總分總的敘事結(jié)構(gòu)。在影片開始介紹了流浪地球的背景、原因,人類的計劃、準備;影片結(jié)束時總結(jié)了人類3年后5個階段的流浪計劃。電影用重復手法,使片頭與片尾相呼應,進一步指出流浪地球的重要性,彰顯影片結(jié)構(gòu)的嚴謹。影片開始營造了舞獅子的歡天喜地的佳節(jié)氛圍,以劉啟和朵朵去外邊過年為流浪地球的故事背景,這與流浪結(jié)束后分配任務,加載春節(jié)十二響破解程序形成首尾呼應。以人們戰(zhàn)勝“年”這一怪物的喜悅隱喻流浪地球計劃的成功。《流浪地球》反復強調(diào)希望,強調(diào)希望的寶貴,強調(diào)希望是帶人類回家的路。韓朵朵一心想去外邊尋找希望,在多次救援失敗后看不到希望時,她接通了救援信號,重燃希望之火,她作為一名被撿來的孩子,就寓意著新生與希望。
《流浪地球》作為一部硬核科幻電影,技術(shù)加持下呈現(xiàn)中國式視效景觀,傳遞著中國智慧。
4 結(jié)語
《流浪地球》作為一部中國的硬核科幻電影,改變了觀眾對國產(chǎn)科幻電影的刻板印象,受到了觀眾的好評。數(shù)字化技術(shù)建構(gòu)家園的毀滅和建設開發(fā),給觀眾帶來逼真、震撼的視聽體驗,滿足了觀眾的好奇心。通過技術(shù)加持呈現(xiàn)中國式視效景觀,在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交織中,體現(xiàn)了作者的技術(shù)憂患和生態(tài)危機意識。在中國式的敘事中傳遞著中國精神和智慧,立足于家國意識,展示中國英雄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和擔當。從家園、根的開拓中引發(fā)觀眾的情感共鳴。多層次敘事的解讀,傳遞全面深刻的中國智慧。《流浪地球》是中國科技和智慧的結(jié)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