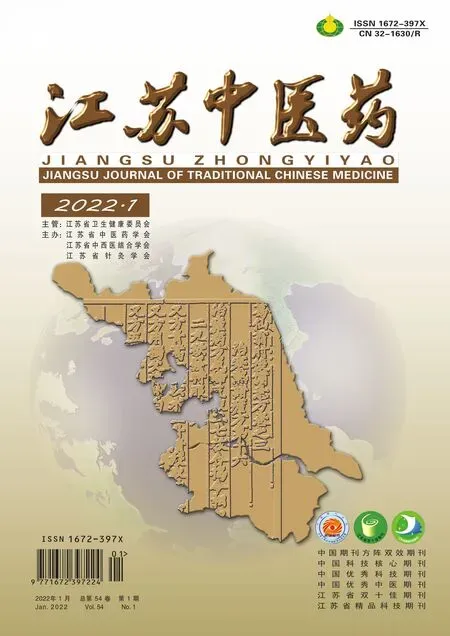基于《章次公醫案》論失眠辨治
蘇苑苑 蘇 瑩 王海南 王 忠 李 平 韓 飛
(1.濱州市中醫醫院,山東濱州 256600;2.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北京 100053;3.中國中醫科學院中醫臨床基礎醫學研究所,北京 100700;4.北京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北京 100029)
失眠多由飲食不節、情志所傷、體虛勞倦等引起臟腑功能失調,導致火、濕、痰等病邪滋生以及氣血、陰陽虧虛,最終邪氣上擾心神或心神失其濡養,致使神不安宅。臨床上多種急慢性病癥,如神經官能癥、更年期綜合征、腦震蕩后遺癥、高血壓、肝病、甲狀腺功能亢進、貧血等均可出現失眠的臨床表現[1]。章次公作為孟河醫派四大家之一丁甘仁的學生,是我國杰出的中醫教育家、臨床家,國醫大師顏德馨稱其為“高瞻遠矚,百年來第一人”[2]。本文將介紹《章次公醫案》[3]229中辨治失眠醫案5則,探討其辨治失眠之思路,以更好地指導臨床。
1 醫案拾粹
1.1 肝虛不寐案 梁男。夜難成寐,多夢,心悸,古人以為肝虛,以肝藏魂故也。凡補肝之藥,大多有強壯神經之功能。明天麻9 g,杭白芍9 g,穞豆衣12 g,大熟地12 g,當歸身9 g,炙遠志5 g,炒棗仁9 g,抱茯神9 g,潼沙苑9 g,柏子仁9 g,黑芝麻12 g。二診:寐為之酣,悸為之減,但多夢則如故。大熟地18 g,當歸身9 g,杭白芍9 g,山萸肉9 g,五味子5 g,菟絲子9 g,炙遠志5 g,抱茯神9 g,潼沙苑9 g,夜交藤12 g,左牡蠣30 g。另:首烏延壽丹90 g,分十日服完。
通過醫案中對“肝虛”的描述及以方測證,分析該患者病情以肝陰肝血虧虛、肝陽上擾心神為基本病機。肝陰不足,肝陽上擾,則神不安;肝血不足,則魂不藏,導致失眠、多夢、心悸等一系列癥狀。初診選用熟地黃、白芍、當歸、沙苑子、穞豆衣、黑芝麻以滋肝陰、養肝血;考慮患者易眩暈,故以天麻平肝鎮靜;酸棗仁、柏子仁、茯神、遠志養心寧神。藥后失眠、心悸癥情改善,二診針對多夢如故,在原方的基礎上增加熟地黃用量,去穞豆衣、黑芝麻,加山萸肉、五味子、菟絲子,去天麻,加牡蠣、夜交藤,同時配合中成藥首烏延壽丹,此方源自《世補齋醫書》,補虛為主,兼去實邪。二診在上方基礎上加補腎藥,推斷其有腰膝酸軟癥狀,故進一步加強補虛強壯、鎮靜安神作用。
1.2 胃不和不寐案 周女。病失眠已久,最近時時作噦,苔白膩滿布。因其以往疊用滋陰安神劑無效,《內經》有云:“胃不和則臥不安”,當先從治胃入手。炮附塊9 g,大川芎9 g,姜半夏24 g,北秫米12 g,香甘松9 g,炙甘草3 g,肉桂末1.8 g(分三次吞)。注:服此方兩劑,即得安寐。
章次公在運用滋陰安神方藥無效基礎上,從看似與患者失眠主訴無關的“時時作噦”一癥著手,結合舌苔白膩,推斷其還存在胃脘脹滿癥狀,另辟蹊徑,考慮為“胃不和則臥不安”。脾陽虛不能運化水濕,痰濕壅滯于胃,胃不和則臥不安;或胃有宿食,變生痰濁,影響心神。濕為陰邪,方中以附子、肉桂振奮脾腎陽氣,推測患者喜溫喜按,陽氣充足則痰濕可化;半夏、秫米和胃化痰,此二藥出自《黃帝內經》半夏秫米湯,半夏燥濕健脾,秫米益胃和中,并能遏制半夏毒性,兩藥相和,調暢脾胃,疏通道路,引陽入陰[4];川芎為“血中氣藥”,甘松醒脾暢胃、解痙定痛,為開郁鎮靜、安腦助眠之良藥[5],兩者相伍以調和脾胃氣血;炙甘草和中緩急。諸藥配伍,陽氣得復,痰濕得化,脾胃運化功能恢復,心神即安,失眠亦隨之好轉。
1.3 陰陽失交不寐案 姚男。頭昏,夜難安寐,口干唇碎,服西藥七、八月無效。每夜必飲水數次,否則口干不可名狀,影響睡眠。察其舌色淡白無華,按其脈沉細無力,不能以為熱證而投涼。附塊6 g,生白術12 g,熟地30 g,五味子5 g,黨參12 g,懷牛膝12 g,麥冬12 g。二診:很有效,口干沒有從前嚴重,夜寐也較安。原方去牛膝,加當歸、棗仁。
根據“脈沉細無力”推測可能存在乏力癥狀,“舌色淡白無華”推斷其多面色萎黃,“口干、唇碎、每晚渴飲”等躁證易誤診為熱證而猛投涼藥,章次公認為此火非實火而為虛火,即腎元虧虛、陰陽失調、心腎不交、心火內熾之象引發失眠,施以全真一氣湯治之。此方源于《馮氏錦囊秘錄》,由別直參、麥冬、五味子、熟地黃、江西術、淡附片、酒蒸懷牛膝組成,何廉臣謂此方“功在于一派滋養陰液之中,得參附氣化,俾上能散津于肺,下能輸精于腎。且附子得牛膝引火下行,不為食氣之壯火,而為生氣之少火,大有云騰致雨之妙,故救陰最妙”[6]。二診見效,口干已輕,夜寐較安,考慮腰膝酸痛已除,原方去牛膝,加當歸、酸棗仁補血益陰、養心安神,以鞏固其療效。
1.4 虛火不寐案 雷女。夜晚難以入睡,服安眠藥亦無濟于事;偶爾入睡,則亂夢紛紜;因而白晝疲憊不堪,每晚飯后則其精神特別興奮。此屬虛火。川連3 g,黃芩6 g,生白芍18 g,阿膠30 g(分沖),棗仁18 g,茯神18 g,雞子黃二枚(分沖)。二診:連服五劑,失眠情況已有顯著改善,晚上精神不如前之興奮;頭脹,有時昏沉。棗仁30 g,川芎9 g,知母12 g,茯神18 g,遠志9 g,清炙草3 g。另:歸脾丸120 g,每睡前服9 g。
此案圍繞“每晚飯后則其精神特別興奮”一癥將失眠辨為虛火,首診以黃連阿膠湯滋陰降火,佐以酸棗仁、茯神養心安神。黃連阿膠湯出自《傷寒論》:“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方中黃連、黃芩苦寒瀉火,使心氣下交于腎,白芍、阿膠、雞子黃滋養腎陰,使腎水上濟于心,以奏陰陽相通、神有所歸之效[7]。藥后虛火一癥顯著改善,改用酸棗仁湯加味(原方以茯神易茯苓,加遠志)配伍歸脾丸以緩圖治之。酸棗仁湯源自《金匱要略》,主治“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仁養肝血、寧心神,知母滋陰清熱、除煩安神,茯神、遠志以寧心安神、定悸止驚,川芎調和氣血,甘草和中緩急。諸藥相伍,標本兼治、養中兼清、補中有行,共奏養血安神、清熱除煩之效。歸脾丸出自《醫學六要》,丸者緩也,章次公取湯藥速效的同時,考慮患者平素多心悸怔忡、健忘、食少體倦,配丸藥益氣健脾、養心安神以緩圖。
1.5 產后不寐案 吳女。產后思慮勞煩,腦力受其打擊者良巨,以致輾轉難以入眠。酸棗仁9 g,知母9 g,煅牡蠣30 g(打),北秫米9 g,粉草2.4 g,大川芎5 g,抱木神9 g,仙鶴草15 g,懷山藥9 g,川雅連0.6 g,上安桂0.6 g(研吞)。
依據“產后思慮勞煩”,章次公辨此為產后氣血不足,伴情志不暢,肝郁日久化火,上擾心神之失眠,屬虛實夾雜之象。治療上除酸棗仁湯以外,考慮其平素易乏力、出虛汗,配以仙鶴草、山藥、秫米、牡蠣以益氣和胃、化痰安神,同時聯合交泰丸。交泰丸源自《韓氏醫通》,用于治療心腎不交、怔忡失眠之證,方中取黃連苦寒,入少陰心經,降心火,不使其炎上;取肉桂辛熱,入少陰腎經,暖水臟,不使其潤下;寒熱并用,水火既濟,交通心腎。全方既以患者產后氣血多虛的體質狀態為本,施以補益氣血、養心安神之藥,又不忽視情志郁火所造成的影響,補虛瀉實,上中下三焦兼顧,引火歸元,使神寧、魂藏、魄靜。
2 辨治探源
2.1 臟腑辨治——滋陰潛陽,兼重溫陽《黃帝內經》中記載:“衛氣晝日行于陽,夜半則行于陰……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依據“乙癸同源、陰平陽秘”等中醫傳統理論,上述醫案中章次公立足臟腑辨治,認為病位多以心、肝、腎為主,亦不離肺、胃,治療上或偏于陰,或重于陽,或陰陽兼顧;病性以陰虛為主,兼有陽亢,多從滋陰潛陽著手,多使用雞子黃、阿膠、白芍以滋養肝腎之陰,以明天麻、穞豆衣平肝潛陽,少佐黃芩、黃連以清瀉肺胃火邪。當陽氣不足時重視培補陽氣,在對于滋陰安神劑疊用無效時,不失為補充,與章次公所主張的“根據實踐經驗,有些失眠患者,單純用養陰、安神、鎮靜藥效果不佳時,適當地加入桂附一類溫陽興奮藥,每可奏效”[3]231相一致。“服此方兩劑,即得安寐”即是該法療效突出的說明。
2.2 氣血辨治——養血安神,調和氣血心藏神,心血充盈,則神得以寧;肝藏魂,肝血充足,則魂得以安;脾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氣血充足且舒達調暢,則神魂得安,若氣血乏源或氣血瘀滯,則神魂得不到濡養,從而影響睡眠。章次公常選用酸棗仁湯養血安神,清熱除煩;健脾不離補氣,養心不離補血,取歸脾丸益氣補血,健脾養心,使心血旺、脾氣壯,則神自寧。兩方補益氣血之外,常配伍川芎、木香等以活血理氣、通補結合、補而不滯。雷案二診更是將酸棗仁湯與歸脾丸聯合治療以加強藥效,可見章次公尤其重視臟腑氣血和合對于人體睡眠的重要性。
2.3 中西結合,全面兼顧從醫案中關于對“凡補肝之藥,大多有強壯神經之功能”的簡單描述,可以看出章次公將現代藥理學應用于失眠治療,反映出其對中西醫理論的融會貫通。在雷案診治中章次公主張睡前服用歸脾丸,體現出其將時間藥理學應用于失眠診治過程中,是其治療的一大特色。章次公在繼承前人經驗的同時亦注重劑量的變化、藥味的加減、合方的聯用,可見其師古而不泥古。章次公還重視“對藥”的應用,“對藥”有增效解毒之功如黃連配肉桂以交通心腎,半夏配秫米以化痰和胃,川芎配甘松以調和氣血等。
3 結語
《章次公醫案》未標明各味藥物的劑量,國醫大師朱良春在《章次公醫術經驗集》[8]中標注的單位為“克”,筆者在多番對比和臨床實踐后,亦認為以“克”為單位符合章次公本意。針對失眠一疾,安眠藥臨床療效確切,但不良反應較多,且有一定的藥物依賴性。中醫學以辨證論治和整體觀念為基本特點,自《內經》開始便有關于“目不瞑”“不得臥”的論述,并且在后世歷代醫家臨床實踐的過程中,失眠診治的理法方藥不斷完善。章次公醫案用詞簡練易懂,且善于抓主癥、明主因,用藥靈活,擅以調臟腑陰陽、氣血治療失眠而取效,對臨床診治失眠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