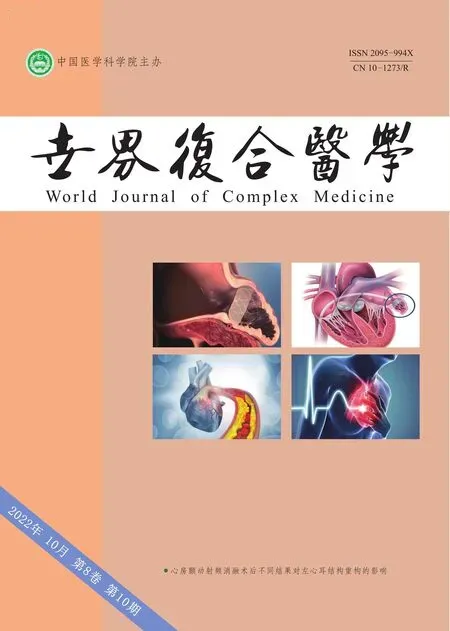心房顫動射頻消融術后不同結果對左心耳結構重構的影響
杜薇,羅彩東,戴閩,黎東,賴柱宏,王虎,牟英
綿陽市中心醫院心血管內科,四川綿陽 621000
心房顫動(atrial fibrillation,AF)是一種以快速、無序的心房電活動為特征的室上性快速性心律失常,是臨床上最常見的心律失常之一。房顫是缺血性腦卒中的獨立危險因素,與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發生發展密切相關,可顯著增加患者殘疾及死亡風險[1]。根據現有指南,癥狀反復的房顫患者如對抗心律失常藥物治療不耐受或效果不佳,應優先考慮射頻消融治療(IIa,B)[2]。左心耳(left atrial appendage,LAA)是原始左心房的殘余結構,沿左心房(left atrium,LA)前側壁向前下延伸形成盲端。左心耳的形態結構與房顫患者心房內血栓形成、房性心律失常的產生及維持有關[3-4]。研究表示,心臟的結構重構與房顫發生、發展、長期維持有關,射頻消融手術成功治療房顫后可逆轉左心房、肺靜脈、左心耳在房顫進程中發生的結構重構[5-6]。然而上述關于左心耳的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小,且缺乏對包括持續性房顫在內的房顫患者的研究,因此有關房顫射頻消融術對左心耳結構重構的影響目前仍需進一步驗證。
因此,本研究選取2018年1月—2019年6月期間于綿陽市中心醫院心內科首次成功接受房顫射頻消融治療的非瓣膜性房顫患者42例,旨在通過冠狀動脈增強CT(以下簡稱冠脈CTA)對房顫患者射頻消融手術前后左心耳容積、左心耳開口面積、左心耳開口長短徑等指標進行測量,以探究房顫射頻消融術對左心耳結構重構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研究納入于本院首次成功接受房顫射頻消融治療的非瓣膜性房顫患者42例,年齡41~75歲,平均(61.9±7.1)歲;男22例(52.4%),女20例(47.6%);其中陣發性房顫25例(59.5%),持續性房顫17例(40.5%)。隨訪24個月期間共16例(38.1%)患者房顫復發,且至隨訪終點仍未轉復為竇律,另外26例(61.9%)在隨訪期間未監測到房顫復發。本次研究患者及家屬均知情同意,研究取得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于本院心內科首次成功接受心內電生理檢查及頻消融治療的非瓣膜性房顫患者。
排除標準:患有嚴重心臟瓣膜病、先天性心臟病、心肌病或惡性腫瘤者;處于急性冠脈綜合征、腦血管病、感染、甲狀腺疾病的急性發作期者;既往曾接受房顫射頻消融手術治療者;無法配合研究或隨訪者。
1.3 資料收集
患者術前常規完善血生化檢查、經胸心臟彩超(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ghy,TTE)、經食道心臟彩超(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ghy,TEE)、冠脈CTA等。利用電子病歷系統,查詢并記錄患者相關病史、術前基本情況及輔助檢查結果。
1.4 左心耳結構指標測量
交互式醫學影像控制系統(materialise's interactive medical image control system,MIMICS)可利用CT二維數據集重建局部解剖三維結構[7]。在MIMICS 17.0軟件中導入患者冠脈CTA影像,選擇心房處于最大容積時即心室收縮期圖像,重建出患者左心房、左心耳三維結構(圖1),并對上述結構相關數據進行測量(圖2)。

圖1 利用MIMICS 17.0軟件重建左心房及左心耳三維模型Figure 1 3D model of the left atrium and left heart ear reconstructed using MIMICS 17.0 software

圖2 左心耳相關數據測量Figure 2 Measurement of data related to the left heart ear
1.5 射頻消融與術后隨訪
利用三維電解剖標測系統,對患者左房基質進行改良,并進行環肺靜脈隔離,部分患者需進行額外線性消融、碎裂電位消融等。所有患者射頻消融手術順利,術中無并發癥。
射頻消融術后分別于第3、6、12、24個月對患者進行電話或門診隨訪。隨訪內容包括患者日常癥狀、用藥情況、24 h動態心電圖以及有無房顫復發、腦卒中、心血管死亡等事件發生。患者在房顫射頻消融術后24個月內復查冠脈CTA,以對術后左心房、左心耳的結構變化做進一步評估。房顫復發定義為在患者接受射頻消融手術3個月后,由心電監護、心電圖或動態心電圖記錄到持續超過30 s的快速性房性心律失常。
1.6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26.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處理,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表示,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n(%)]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 有統計 學意義。
2 結果
2.1 射頻消融術后房顫未復發患者與復發患者臨床資料對比
隨訪24個月期間16例(38.1%)有房顫復發,26例(61.9%)未監測到房顫復發。房顫復發與未復發患者臨床資料對比見表1。

表1 射頻消融術后房顫未復發患者與復發患者臨床資料對比Table 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data between patients with no recurrence of atrial fibrillation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and patients with recurrence
2.2 射頻消融術前、術后左心耳及左心房各項指標變化情況對比
42例房顫患者于射頻消融術后24個月對冠脈CTA進行復查。手術后,房顫復發患者左房容積、左心耳容積、左心耳開口長短徑以及左心耳開口面積均較術前顯著增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房顫未復發患者手術前后左房容積、左心耳容積、左心耳開口長短徑以及左心耳開口面積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射頻消融術前、術后左心耳及左心房各項指標變化情況對比(xˉ±s)Table 2 Comparison of changes of indexes of left atrial appendage and left atrium before and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xˉ±s)
2.3 房顫復發和未復發患者射頻消融術后左心耳結構重構情況對比
此外,定義△x為相應指標射頻消融術后測量值與術前測量值的差值,比較房顫復發組與未復發組患者相應指標手術前后的變化情況。在射頻消融術后24個月,房顫復發患者的左心耳容積的增大程度明顯大于未復發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同時,房顫復發患者術后左房容積則較術前增大,而未復發患者術后左房容積較術前縮小,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房顫復發和未復發患者射頻消融術后左心耳結構重構情況對比Table 3 Comparison of left atrial appendage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recurrence of atrial fibrillation

表3 房顫復發和未復發患者射頻消融術后左心耳結構重構情況對比Table 3 Comparison of left atrial appendage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after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recurrence of atrial fibrillation
指標△左心耳容積(mL)△左心耳開口長徑(mm)△左心耳開口短徑(mm)△左心耳開口面積(mm2)△左房容積(mL)未復發(n=26)0.5±1.7 0.6±2.0 0.3±1.4 12.2±50.4-2.6±14.4復發(n=16)2.4±1.9 1.4±2.2 1.2±2.0 48.1±67.4 16.6±10.4 t值-3.423-1.362-1.766-1.972-4.653 P值0.001 0.181 0.085 0.056<0.001
3 討論
3.1 房顫進程中左心耳的結構重構
既往研究表明,左房的結構重構和電重構與房顫發生、發展以及長期維持密切相關[8]。持續性房顫患者左房容積明顯大于陣發性房顫患者;射頻消融術后12個月房顫復發患者的左心耳容積較無房顫復發患者增大37.9%;左房容積隨房顫負荷增加而進一步增大[9]。目前認為左房結構重構可致使房顫發生,而房顫的發生與發展則進一步促進左房的結構重構[10]。本研究中,射頻消融術后24個月,有房顫復發的患者的左心耳容積較無房顫復發的患者增大39.1%,且其左心耳容積、左心耳開口長短徑、左心耳開口面積以及左房容積較術前均有明顯增大,增大程度顯著大于無房顫復發的患者(P<0.05)。提示在房顫進程中,左心耳同左心房一樣發生了結構重構,左心耳結構重構程度與房顫負荷有關。
左心耳作為胚胎時期原始左心房的殘余,可通過主動舒縮來調節左房內壓力負荷及容量負荷。房顫狀態下,左房失去有效的規律收縮,左房內壓力增高,左心耳可代償性增大[3]。有研究發現在左心耳的4種形態中,具有“雞翅”形左心耳的患者卒中風險最低[4],而在竇性心律患者、陣發性房顫患者以及持續性房顫患者中,“雞翅”形左心耳患者所占比例依次降低[11],提示在房顫進程中,左心耳形態發生了重構,而該重構趨勢增加了患者發生卒中的風險。Yu HT等[12]發現,房顫過程中左心耳重構具有性別差異,同等條件下女性患者的左心耳結構重構更明顯、功能受損更嚴重。因此,在后續研究中,可以針對不同性別、不同左心耳形態的房顫患者做進一步探究。
3.2 射頻消融術后左心耳的逆重構
射頻消融術成功治療房顫后左心房、左心耳及其相關結構發生逆重構已有相關報道。在Tsao HM等[13]的研究中,術后房顫未復發的患者左房容積較術前縮小了7.9%,肺靜脈開口面積較術前縮小了9.1%;在Beukema WP等[14]的研究中,無房顫復發的患者左房內徑較術前縮小了9.1%;Tian X等[6]的研究則指出,在陣發性房顫患者中,無房顫復發的患者其左心耳開口面積、左心耳頸面積以及左心耳深度較術前均有明顯縮小。提示房顫患者左心房及左心耳的結構重構具有可逆性,在去除病因后,已發生改變的心臟結構可有不同程度的恢復,其機制可能與心房肌組織炎癥減輕、氧化應激損傷恢復、自主神經系統功能調控有關[15]。
本研究中,無房顫復發的患者術后平均左房容積較術前縮小了2.5%,而其術后左心耳容積、左心耳開口長短徑以及左心耳開口面積較術前仍稍有增大,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出現上述結果的原因可能與年齡因素有關。已知隨著年齡的增長,左心房及左心耳容積有增大的趨勢[16],因此對于無房顫復發的患者,可能在其左房及左心耳發生逆重構回縮的同時受到年齡因素的影響,多種因素的作用彼此影響互相抵消,從而導致射頻消融手術前后左房及左心耳容積無明顯變化。
3.3 對房顫治療的啟示和展望
在房顫藥物治療方面,已有研究表明Ac-SDKP、GM-CT等特異性阻斷劑在減緩心臟重構、降低房顫負荷中可發揮積極作用[17-18]。在房顫的電生理治療方面,左心耳電隔離在房顫診治方面亦逐漸引起了重視。Reissmann B等[19]發現左心耳電隔離對持續性房顫患者術后維持竇性心律起到積極作用。Di Biase L等[20]的BELIEF研究則證實對于長程持續性房顫患者,給予額外的左心耳電隔離可減少房顫復發且不增加并發癥發生率,在傳統標準消融治療的基礎上給予左心耳電隔離可提高射頻消融的遠期成功率。因此,左心耳重構的特異性阻斷劑、在左心耳逆重構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的生物因子以及在房顫標準消融治療的基礎上加以對左心耳的電隔離或可為房顫靶向治療以及卒中防治帶來新的曙光。
4 結論
綜上所述,射頻消融術成功治療房顫后(術后24個月無房顫復發)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并逆轉房顫進程中左心耳及左心房發生的結構重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