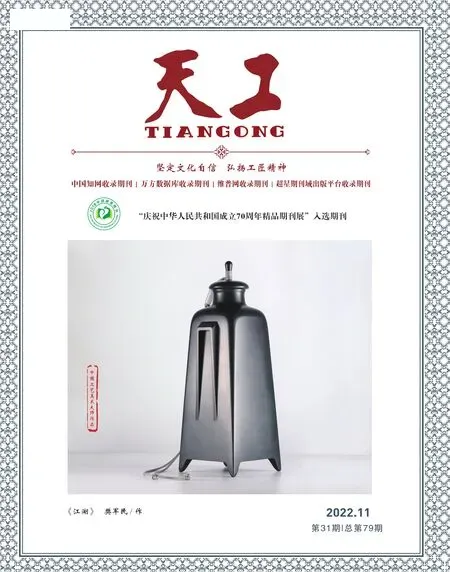淺析傳統工藝的場域解讀
——以江蘇邳州玉雕工藝為例
李沛竹 孫仲鳴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一、中國傳統工藝場域建模
(一)傳統工藝場域生成
傳統工藝生產作為一種生產方式,在理論與實踐中都需要借助一定的載體或機制才能展開。社會生活這一載體是傳統工藝存在的基礎。社會生活及生產在數千年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在傳統社會中生產資料變化速度緩慢,但在當下科技的不斷發展和進步帶來了社會軟環境的巨變。隨著社會關系在內的生產要素的變化,社會生產的形式結構與內外部關系都被重新塑造。而時代性是傳統工藝在漫長歷史中得以保存流傳且發揚精進的重要原因。傳統工藝的時代性寄寓在社會的時代性之中。
隨著時代的發展,眾多中國傳統工藝的從業者經歷了身份的重構,而傳統工藝只有積極滿足社會日新月異的文化消費需求,在文化、藝術及消費的各種產業關聯與社會關系中不斷發現場域,探索它的當代質點和結構,才能免于隨著社會的更迭而中斷消失。
場域的形成需要一系列元素及結構的完善,逐步發展成為與其他場域基本同構的穩定形態。新的傳統工藝場域在建立前期沒有所謂的結構體系。改革開放后,我國涌現出許多特色鮮明的傳統工藝產業集群。傳統工藝區別于原有文化場域的符號和這一行業的前后輩關系、身份關系等基本確定了場域內的結構。
布迪厄將所有場域置于社會空間之中,將權力場域視為“元場域”。權力場域即是統治階層所掌控的場域,其中重要的對立是經濟場域和文化場域,筆者更傾向于在這里把傳統工藝納入文化,這就意味著對它的考察不局限于其本身,而是置入互動共生的社會關系和文化氛圍中進行同一性把握。傳統工藝作為一個多側面、多層次、間性化的復合體和中介體,包含審美價值、經濟價值、文化資本象征價值等眾多價值要素,而我們在對傳統工藝進行探索時,要關注其構成方式、發展演化、關系形態的整體性和綜合性,特別是其在生存和發展的實踐中展現的精神文化內核,尋找傳統工藝在當代發展的關鍵內核和內驅動力。因此,傳統工藝從屬于文化場域,同樣存在與其他場域的沖突和自身的內部反抗。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很好地解釋了文化場域所處的位置和功能,從他原有的理論入手,可以明確中國傳統工藝場域的位置狀態。
邳州玉雕產業自20世紀70年代興起。1973年9月,來自中央美院的陳天教授帶領邳縣文化館的幾個人創辦了邳縣工藝美術廠玉雕車間。他們作為文化的生產者,同樣具有文化資本,拋去了在原有藝術場域內的身份,持有剩余的文化資本,這一部分文化資本必須與經濟資本相協調,才能在社會空間中取得相對平衡的可以繼續的位置。玉雕車間主要雕刻爐瓶、貔貅等大件玉器,被江蘇省輕工廳及外貿局定為全省第七家工藝品出口定點廠。而相比于江蘇其他地區,這一場域剛剛起步,發展較為緩慢,結構不甚穩固,玉雕車間的初代師父們在徐州玉雕廠學習玉雕技術后,相繼開始收徒傳藝,傳承玉雕技藝,擴大邳州產業規模。這一階段技藝的傳承以血緣、親緣為主,產品以供給外貿出口為主。而市場經濟的引入,將藝術場域與經濟場域的資本置換渠道打開并擴大了,經濟場域的資本置換成為爭奪的目標。
2000 年邳縣玉雕廠解散,促使邳州玉雕產業由國有化向個體化轉變,并加快了玉雕個體加工業逐漸產業化。這時候傳統玉雕工藝在邳州具備成為“圈”的可能,以邳州主城區為主聯動周圍鄉鎮發展的玉雕產業分布格局逐漸形成。
(二)傳統工藝場域的結構特征
布迪厄的場域的結構特征應當從四個方面去概括:一是場域是為了控制有價值的資源進行斗爭的領域;二是場域是由在資本的類型與數量的基礎上形成的統治地位與被統治地位所組成的結構性空間;三是場域把特定的斗爭形式加諸行動者;四是場域在很大程度上通過自己的內在發展機制加以建構,具有一定自主性[1]。
對于中國傳統工藝場域來說,有價值的資源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文化資源,具備轉換為其他資源的能力;二是藝術經濟資源,即可以用于藝術的經濟資源,這一資源的持有者在傳統工藝場域里具有控制權力,因此,不能僅僅將這一資源看作是經濟場域的權力置換[2]。
1.中國傳統工藝場域的關系網絡
中國傳統工藝場域中占統治地位的群體之一是傳統工藝的藏家,他們通過收藏行為控制藝術家作品的價格,并通過持續持有藝術家的作品來保持對傳統工藝的控制力。這些大藏家又依靠民營藝術館、民俗館來掌控傳統工藝的話語權,在傳統工藝場域具備文化和經濟雙重優勢。傳統工藝大師也是他們所掌握的文化資源,因此傳統工藝大師緊緊圍繞著藏家群體。處于被統治地位的是從事傳統工藝的中低層工藝師,他們掌握文化生產的權力,但是不具備評價和定價的權力,在傳統工藝場域里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傳統工藝場域中有展館、藝術媒體和批評家等。展館和其他非藏家經營的藝術機構依靠從藝術家手上購買作品再銷售給藏家賺取傭金,它們既沒有一手的文化資源也沒有話語權力,更沒有最終的經濟決定權,只是傳統工藝市場運行規則下的一個渠道。處于這些統治權力之下的是中小型的藝術中介,包括一些小畫廊,以及中小藏家和中低層的藝術家等,他們擁有的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是分散開的,與場域的聯系程度比較松散,處在最下層的位置(如圖1)。

圖1 中國當代藝術場域權力的結構示意圖
正因為形成了有如上特征的中國傳統工藝場域,進入場域的角色只有遵守規則才能存活在場域中。
2.中國傳統工藝場域的權力模型
任何一個場域的權力關系都有統治和被統治的粗略分層,但場域的權力關系必定是按照一定的規則運轉的。中國傳統工藝從業群體是在綜合條件下形成一種星云式的權力關系。如果說完善的、具有固定等級權力關系及運營模式的社會場域類似于一個恒星系統,那么中國傳統工藝場域在形成過程當中更接近于——看似混沌卻已經有了成形的趨勢但尚缺內核的星云結構。
中國傳統工藝場域是由交往建立的,關系結構相對分散,不存在絕對的權力核心和嚴格的層級關系,所有的傳統工藝大師、藏家及展館等都各自擁有一定的藝術權力。傳統工藝大師和著名評論家是藝術品的實質生產者,他們的藝術權力是區別傳統工藝與工業批量制成品的因素。新科技和機械化沖擊了傳統的“手作”時代,量化生產使每件產品不再保留手工制作的唯一性,而工藝大師的手工藝術品創作極大地幫助了傳統工藝的存續,帶來的個性化職業發展與多樣性的生活樣貌都促進了社會良性且多元的發展。且在工藝大師的保護下,才可能有更多的人投入中國傳統工藝場域,為新生力量爭取發展成長的時間。
示意圖中的軌道是預計可能會出現的位置關系,這種星云狀結構與等級制度下的權力結構的不同之處有三:第一,權力關系是相對的;第二,無論權力大小均不可替代;第三,存在跨越權力的交往和協作。
以邳州為例來觀測這種星云結構的模式,工藝大師的聚集,逐漸吸引更多從業者入住邳州;建立多種生產模式;繼而逐步發展相關玉雕鏈及文旅產業。而工藝大師作為傳統工藝的先鋒,努力為傳統工藝尋求新的現代社會載體,適應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社會生活形態的巨變,尋求與現代生活空間的互動,重新構建傳統工藝的價值體系,融合現代的設計意識、美學態度和價值主張,找到傳統工藝當下的新應用場景和生存模式,找到切實可行的工藝創新和美學加值的道路。在智能制造社會下仍然保有傳統工藝的溫暖無疑是重要的。隨著經濟的發展,一部分消費者逐漸不滿足于機器批量生產的工業品,轉而傾向于擁有手工痕跡和溫度的作品,這是時代發展下美好生活發展的新樣式,而不同的市場區分也證明了傳統工藝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他方式的合理性。而隨著產業集聚產生積聚效應,眾多個人工作室產生,也有相關藝術從業者及高校畢業生來此尋找機會。邳州可落實產業發展政策,準確引導產業合理分布,擴大玉雕產業規模,打造品牌龍頭企業,加大品牌宣傳力度,促進產業轉型創新,形成玉雕產業集群發展,最終建成完善的場域。
二、場域危機下對傳統工藝的思考
從藝術社會學的角度對傳統工藝進行審視,其在當下衰微的實質是傳統工藝場域的存續危機。這一危機首先表現在傳統工藝場域在社會場域體系中的邊緣化;其次,傳統工藝場域的內部生態不斷萎縮,導致傳統工藝場域本體的消減;最后,傳統工藝場域的“折射功能”喪失,逐漸失去積極有效應對外部變化的自主能力。想要解決傳統工藝的場域危機問題,就要通過與當下審美的勾連,打通傳統工藝場域和其他社會場域的融通渠道,并重構傳統工藝內部場域,從而為其注入活力。
傳統工藝的堅守和發展是依存于傳統社會生活的,具有現實指涉性,一旦被剝離,其生存語境就會發生巨大變化。傳統工藝可以在傳統社會中傳承發揚的原因,除了自身具有成熟而獨立的運作機制之外,還因為其通過現實性而與其他場域相勾連,使自己成為多個場域的參與者。而在與不同場域的勾連中,傳統工藝不僅維持了自身場域存在的合理性,也在社會場域中爭取了足夠的權力資源,使自身得到充分的發展。
而在傳統場域的內部生態方面,藝術家、消費者、贊助者三方勢力的整體衰弱,造成了傳統工藝場域的失衡。其中最為嚴峻的是經過社會場域的震蕩剝離,傳統工藝的消費群體被迅速分流,大量減少,而這帶來了傳統工藝社會根基的松動,缺乏與市場的關聯,場域存在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
“折射功能”是布爾迪厄提出的場域應對外來干擾最主要的手段,場域的自主度以它的折射能力為主要指標[3]。而傳統工藝場域在面臨經濟場膨脹導致的文化場重置而引起的整體效應時,難以做出折射,導致自身場域與他場域運行規則的動態平衡被打破,影響到自身場域運行和傳承的穩定性,而只能在經濟場的擠壓下急劇收縮。
以邳州玉雕工藝為例,它在傳統社會中不是一個封閉的藝術存在,而是開放的、商業化的,在人們的文化消費中占有重要地位。邳州玉雕屬于“北玉”中的“淮派玉雕”一支,風格兼具北方的大氣敦厚與南方的秀氣靈動。但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邳州玉雕工藝也面臨著場域收縮的問題,市場秩序混亂、產品同質化問題嚴重、手工藝匠人數量減少,而玉雕工藝習得周期較長、收入不穩定、社會地位不高等問題也導致很難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投身其中。玉雕工藝在當下吸納的消費群體多非青年人,當下年輕人的審美多與傳統玉雕不符,所以如何維系消費群體是玉雕工藝這一場域面臨的重要問題。
解決傳統工藝的場域危機問題,就要打通傳統工藝場域和其他社會場域的融通渠道。這要求我們推動傳統工藝成為當代社會生活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以此擴大消費群體,鞏固傳統工藝場域的立足之本。當代社會與傳統社會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它的現代消費主義的精神維度,換言之,我們當前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以消費主義進行定義的時代。在美學形態上,消費社會呈現為沃爾夫岡·韋爾施所說的“日常生活的美學化”。它包括了日常生活表層的審美化,技術、傳媒對物質、社會現實的審美化,人類生活實踐態度和道德方向的審美化,認識論的審美化四個層面[4]。可以說,現代消費社會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美學基礎上的,我們在探索傳統工藝的發展道路時要充分探索當代消費群體的文化和審美體驗。
現代消費社會要求我們不僅要完成物的生產,還需要審美的生產。傳統工藝場域想要復興就要在其當代價值體系構建中完善傳統工藝的生活觀和藝術觀,構建符合現代社會生活審美的器物文明體系,通過工藝美學對日常生活的滲透,重新尋找傳統工藝在眾多場域交織的社會體系中的位置,以此形成重塑現代社會生活的力量。而在消費社會中,物不再顯現為某種用途,而是轉化為一種符號去看它的全部價值,以此還原到社會對傳統工藝的消費生產,則可以嘗試探索傳統工藝作為“價值符號”在現代社會“價值主體”中的位置[5]。
此外,數字信息技術為社會體系帶來的影響與變革,在很大程度上使人與物的對象性關系演變為心物交融、生存互化的多維化關系。在文化共生與社會互動上也不斷激發人們對視覺文化、審美文化、大眾文化的文化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