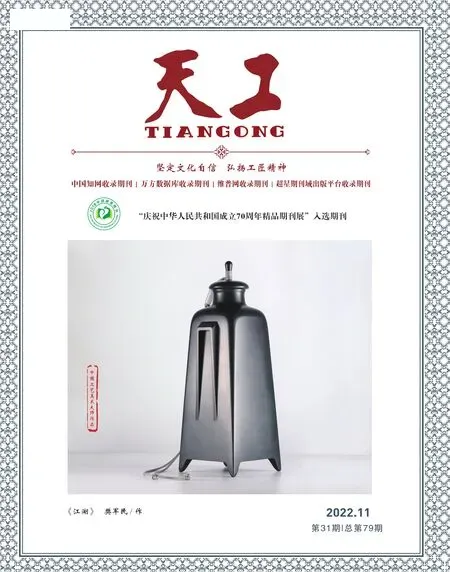淺談湘繡手工藝“畫意”之美
胡 月 湖南師范大學
湘繡與國畫皆屬于中國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湘繡作為明清時期興起的實用性技藝,在當下湘繡藝術化演變的時代發展中,借鑒國畫藝術中的精髓,從線技、色雅、意境、藝格等方面進行分析,以促進未來湘繡藝術的發展。基于文化同源的藝術交流,助力湘繡這門技藝回歸雅致與藝術性的變革之路。
一、湘繡與國畫之緣——致精之藝
古人稱:繡近于文,可以文品之高下衡之。繡通于畫,可以畫理之深淺評之。在書法藝術中有“書畫同源”一說,書法和繪畫在用筆、留白等技術和審美上有著異曲同工之處。而刺繡藝術作為一門手工藝,其藝術性來源于畫稿。與其說繡通于畫,不如說繡出于畫。繡工們手拿繡針一針一線賦予畫稿生動的靈魂,繡出擁有自己主觀意識和客觀存在的藝術結晶。宋代是藝術發展的高峰期,宋代帝王諸如宋仁宗、宋徽宗等,都對國畫有著不同程度的興趣。出于對美的極致追求和裝飾宮廷的需要,經典的繪畫作品層出不窮。在宋代,憑“畫學”為基礎,催生了宮廷藝術類刺繡創作的黃金時期。后世眾多繡家都喜用繡來表現宋元畫作。明代,顧繡在文人對藝術的極度推崇與追求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后來又有以“顧繡”之名統稱“刺繡”之勢,成為中國刺繡藝術的代表和時代審美標志。從傳統藝術角度來說,無論是民間的繡片、荷包、枕頂等日用品繡,還是純粹的文人雅玩(顧繡),乃至宮廷藝術性創造(宋繡),其繡稿都脫胎于國畫。①邵曉錚:《中國刺繡鑒賞寶典》,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國畫中是用筆觸展現線條,而湘繡中的線條則體現在對針法繡線的運用上。據記載,湘繡中有近百余種針法,在展現畫稿的真實上,湘繡的針法進行了多次變革創新。鬅毛針針法就是其變革下的一種,也是最具特色的一種。采用不同的針法可以展現不同的藝術效果。國畫與湘繡在線條的表達上,皆是對藝術美感的追求與表現的殊途同歸。色暈墨潤,渾筆墨于無痕,不審視,不知其為繡畫也。湘繡在針法技巧的運用上展現出類似于國畫一般的視覺感受,遠觀具畫之美意,近視兼藝之工巧。
湘繡之于國畫,以繃布為紙、繡針為筆、繡線為色、針法為技,繡繪出屬于湘繡的藝術美學。湘繡在歷代大師的傳承與創造下,針法技藝不斷成熟,摻針交織出色彩變化的豐滿層次;鬅毛針塑造出獅與虎毛發的輕盈擺姿;旋游針勾勒出瑞獸眼神中的炯神生氣;簾針描繪出山川的若虛隱境……湘繡高超的雙面全異繡更是營造出一塊布兩面形的獨特藝術審美形式。藝術的形式美感講究對稱與均衡、韻律與節奏、變化與統一的相互作用,繡品同時又要兼顧“齊、光、直、勻、薄、順、密”②(清)丁佩:《繡譜》,中華書局,2012,第115-130頁。的審美取向,一幅優秀的作品定是形式美感與審美取向集大成為一體的凝結呈現。
有美言贊湘繡:“繡花花生香,繡鳥能聽聲,繡虎能奔跑,繡人能傳神”。這是對湘繡已經取得的藝術成就的認可,同時我們不得不清楚地明白湘繡類比國畫,在藝術發展上任重而道遠。我們可以借鑒國畫的畫形、畫題、畫法,卻無法真正展示國畫的畫品、畫意、畫格。那么如何擺脫湘繡作為國畫的二次附屬藝術形式的存在,獨立為純藝術的欣賞門類,脫胎于生產生活,學藝于國畫,再創造于藝術價值,這是值得深思的。縱觀國畫的發展史,題材便有人物畫、花鳥畫、山水畫之別,流派分別有院體畫、文人畫、民間畫三類,湘繡的藝術表現形式就稍顯不足。歸因國畫的發展繁景,線的表現技法功不可沒,筆法的行、收、提、按、停、點表現,皆是對線的美感塑造。中國畫線條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特色,魏晉的清古拙樸、唐代的豐腴富態、宋代的嚴密有韻、元明的格調清逸、清代的雅秀蘊藉。①張曉春:《中國畫線描中的形式美》,《美與時代》2021年第5期,第48-49頁。基于湘繡藝術化的演變,湘繡針法是否也可以像國畫的筆法一樣思考、運用、去展示呢?國畫側重情感表達,顧愷之謂“傳神寫照”,湘繡藝術也更應該注重“神”而非形,藝術講究的便是“神似非形似”,湘繡針法脫離形的描繪而流露出“神韻”之時,便是湘繡藝術高峰的來臨。任何一種藝術形式必定是依托其獨特的審美價值而存在,湘繡的價值如果僅僅是如畫般作為藝術欣賞品,終究是跨越不了國畫這座高山,應該發展其獨特的實用性質或表現形式,那么針法就完全可以向國畫學習,這種學習是意識流的借鑒而不是形式流的模仿,知國畫線藝技法之所以然,才能創造湘繡針法技巧的致精之藝。
二、賦彩之雅:色的樸素回歸
國畫中山水畫大致分屬有水墨山水、青綠山水、金碧山水三類。可以這樣理解三類山水畫——水墨山水施色作畫限制于原材料的墨黑與紙白;青綠山水施色依托于山水事物的固有色彩屬性;金碧山水施色是一種主觀的色彩情緒營造。這樣理解下的山水畫體現的是除卻藝術感受外的樸素價值取向,這種取向性有利于對湘繡藝術發展提供參考。湘繡的色彩觀也應該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色彩點綴:限于材料色的表達,注重裝飾的實用性,色彩作為服飾點綴成分;第二階段,美的記錄:表現事物美化的本色值,注重生活中事物原始色彩美的記錄;第三階段,色的求真:用更豐富的色彩刻畫物的真實;第四階段,色之歸素與彩之求華:色之歸素專注于物的固有色,彩之求華追求用色彩表現物的氣韻之華貴、姿態之華實,回歸色彩的自然本色,不過多分色刻畫其真實感,轉而以色繪“韻”,讓色彩服務于物的“神”。第一、二階段是湘繡色彩觀的初級階段,已經為湘繡打下工藝技法的基石,現在湘繡處于第三階段色彩觀中期,現階段湘繡作品趨向于對寫實與精致的追求,湘繡藝術化演變即將進入的是色彩觀第四階段,這一階段如何進行色彩的應用?使湘繡藝術化再度進入高潮期?國畫藝術色彩觀提供了參考價值。
湘繡作品的施色取決于繡線的顏色,審視歷代湘繡作品,隨著時代的發展,繡線色彩種類越發充實,作品展現的色彩層次也愈發豐富。色線分類越多越能展示出色彩的多層次,這種施色似在追求物的逼真,即苛求色的漸變,體現出物的外形鮮活,而非通過色的施加完備物的神韻,過于注重描繪物的形貌而忽視了物的精神骨骼。藝術講究對比,當著重刻畫于“物形”的時候,那么對比出的就是對“物神”的忽略,所謂“畫龍畫虎難畫骨”便是其理,可以通過技藝對形進行精致的描繪,卻難以用技藝同樣塑造隱藏在形背后的內在“生氣”。謝赫就國畫中色彩提出了“隨類賦彩”的觀念,依據自然物的色彩進行情緒傳達,不同類別的物通過施加不同的色彩來表現。在進行色彩使用時應該講究物的固有色彩,卻又不拘泥于物的色相,為營造作品的情緒,可適當進行色相協調。施色濃烈,產生感官上的對比刺激進而強化情感;施色和潤,注重色與色的協調,使畫面統一為一個整體,使人感到溫潤雅致。
“色和淡而不可灰,灰則無生氣;可厚而不可膩,膩則無神韻”②朱屺瞻:《國畫施色之道》,《老年教育》2020年第3期,第12-13頁。,國畫中施色考驗的是運筆,而湘繡中施色則考驗針法的使用和繡線的色搭,一絲一線的粗細與長短都影響著畫面效果的呈現。色的華麗與充實僅僅是一種藝術表現手段,更多的是回歸色的樸素,回歸到自然本色,不過分追求色的豐富,也許摒棄對色彩豐富的追求,更能關注到物所承載的內在美,而后再進行對物的彩之求華,才是錦上添花的藝術。國畫染色、點染、罩色、潑彩等施色技法,無不是對藝術美感的追求,湘繡又何嘗不可運技于身,在借鑒施色技法的同時思考國畫對藝的內在探究理念,方可建立具備湘繡特色的施色技法,讓湘繡的美不僅僅體現在繡藝之精,更開創湘繡獨屬的特征標識。
三、留白之境:意的情緒營造
國畫的留白手法可謂是對虛實之境的絕妙營造,《畫荃》謂曰:“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國畫中有意為之的留白,是作品主題、情感意境、審美趣味的傳達,這種“少即是多”的手法,飽含中國文化的哲學觀。“以虛為虛,就是完全的虛無;以實為實,景物就是死的,不能動人;唯有以實為虛,化實為虛,就是無窮的意味,幽遠的境界”③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40頁。虛實之境的奧妙就在于此。留白塑造的意境,直觀上是構建藝術的虛實關系,其內在本質是營造情緒的內涵屬性。所有藝術不外乎是情緒的傳達,喜、怒、哀、樂情緒,通過藝術作品作為間接載體的形式直觀地呈現出來,“有意味的形式”①李澤厚:《美的歷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第17頁。即是將含義賦予形式之上。湘繡藝術化的轉型,不僅要體現繡的雅美精致,更要用繡藝去承載一種精神層面的情緒表達。
湘繡的特殊屬性限定了其一針一線精工巧技的制作,這堪稱純粹實的技藝手法,如何構建虛的意境呢?留白不失為一種意境構筑的絕佳之選,湘繡的留空之白,便體現為無針線落于繃布之上,為虛實之意的塑造。現階段湘繡作品之于留白的藝術運用,源自國畫藝術的成熟形式,卻缺少了深層次對留白的思考。國畫中“馬一角夏半邊”的藝術表現手法,之于湘繡藝術同樣適用,但是這種適用又必須基于情感上的共鳴而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模仿。國畫墨色與留白的相互依托才能到表達意境,湘繡的留白應該將作品情緒、繡針屬性、繡線特質三位一體相互融合,才可稱為有用之白。同時,留白的手法不應該限于經營位置的使用,萬物皆可留余之白,所謂“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留白之境,留的是華夏藝術審美的意境;留的是湘繡藝術發展的困境;留的是湖湘精神傳達的缺境。湘繡作為湖湘精神最好的表現體,用繡藝傳達湖湘精神的內在情緒再合適不過。湖湘精神需要實物載體來呈現,湘繡藝術需要精神內核來支撐,二者結合為二者的共贏,可以解決困境與缺境的問題。湘繡技藝要想成為真正的藝術,必須經歷從仿真到繪意的傳達、仿形到繪境的塑造、仿藝到繪藝的升華。恰如國畫留白之境的意境表達,湘繡的意境塑造不僅需要借鑒留白之法,更需要對留白藝術形式背后的藝術審美觀進行深層次思考,結合湖湘精神開啟湘繡藝術的再創造。
四、繪像之格:美的精神不屈
國畫作為表現精神的具象載體藝術,每一位國畫藝術家都有著自己想要傳達的情感。八大山人朱耷就塑造了翻白眼神情的魚、鳥,用以抒發心中的悲憤、郁郁之氣;梁楷用豪放的潑墨技法塑造出相俗骨傲的仙人形象,實為對“心誠是佛”的態度的表露;文人用梅、蘭、竹、菊四君子題材展示君子清高的志氣;董源與巨然山水抒寫南方迷蒙漫漫,風雨之變的江南景色;荊浩與關仝刻畫北方山水雄偉荒寒之魄……從作品中感受到的任何一種情緒,飽含著作者繪像之法中的不屈精神。湘繡同樣如此,繡藝技法源自歷代無數先輩的探索總結,皆是對美的經驗總結。中華民族是浪漫的民族,中華兒女身體里流淌著探求美的屬性基因,在無數次與生存的搏斗中,尋找到美的本屬因子,并反復錘煉融入生活,讓生活變得豐滿而精彩,通過技藝展示脫胎于思想的情感美。湘繡作為脫胎于側重實用性的裝飾美學產物,其傳統的內在藝格在于功用,當下湘繡藝術化發展,功用性價值日趨減弱,但藝術性品格還未明確,這是湘繡藝術發展必然要探討的。
繪像藝術的品格在于對美的不屈精神的傳遞。任何一門藝術如果能夠占據一方天地,定是其中所蘊含的精神品格受到人們的欣賞與推崇。湘繡要區別于其他刺繡藝術,就要借鑒國畫豐富的藝格精神,將這種藝格精神與湖湘精神融會貫通。湘繡的雙面全異繡,不單是湘繡技藝上的高峰,更是精神上的升華。似如中華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繡面的正與反恰如陰與陽的對立統一,繡線與繡線之間交織遮蓋的協調,是二者調和折中的統一,湘繡將兩個不同的形象聯結于同一張繡布,做到技法與藝術的高超結合,散發出的藝術魅力令人交口稱贊。雙面全異繡作為特色繡技典范之一,的確讓人耳目一新,但同時也應該存有危機感。技法再高超,經過重復實踐訓練便可以達到技藝的復刻,當技藝得以大規模采用的時候便會失去它的優勢,所以融入不可被復刻的獨屬于某個地域的精神藝格,才能真正立于藝術不敗之地,這也是湘繡藝術發展的正確道路。
五、結語
湘繡藝術化征途漫漫,國畫之于湘繡的借鑒意義,屬于基本的藝術層探討。湘繡藝術化發展道路寬廣,華夏藝術門類眾多,其他門類的藝術之于湘繡,有許多值得借鑒的點,卻不會脫離線技、色雅、意境、藝格幾個方面,所以湘繡扎穩根基的藝術之始變,向國畫借鑒學習開啟藝術化征途,必是平坦且具有光明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