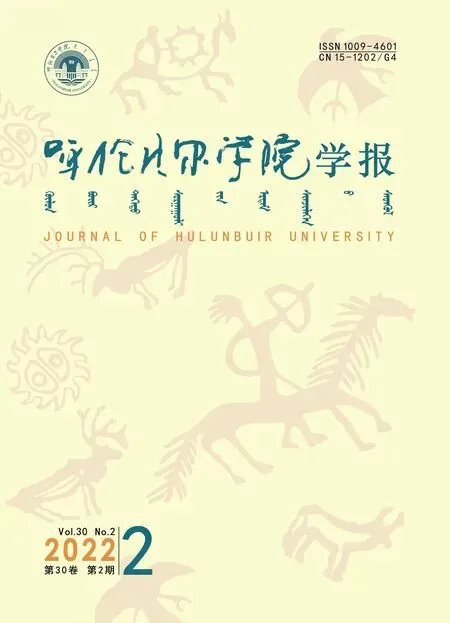理想與現實的錯位
——愛情悲劇《傷逝》中的啟蒙敘事價值
寧一然 朱海坤
(深圳大學 廣東 深圳 518060)
愛情自古以來即是文學作品恒久探討的命題。文學作品常常借助對戀愛伴侶的歌詠描繪,表達個人理想的向往或現實狀況的隱憂,是文本語境和作家思想表達的高度凝縮。《傷逝》為魯迅筆下富有代表性的戀愛敘事作品,涓生與子君勇敢沖破封建社會道德的自由戀愛看似勇敢且珍貴,但從熱戀到分手的轉瞬即逝,個中緣由耐人尋味。作為戀愛敘事的《傷逝》,伴侶形象和戀愛生活的表層時刻充滿理想與現實的錯位,導致了愛情悲劇的上演。站在啟蒙敘事的角度,《傷逝》中的愛情悲劇,恰恰展現出當時作為啟蒙者的知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無所適從。愛情生活表象存在的處處錯位實際對應著啟蒙話語理想與現實實際的錯位,這些錯位構成小說的矛盾沖突,讓這部愛情敘事成為具有符號化色彩的復雜文本,深藏著對啟蒙知識分子的諷刺和反思。
一、作為戀愛敘事的《傷逝》:錯位的表層滲透
站在戀愛敘事的角度,《傷逝》作為一部愛情悲劇,從始至終充滿了戀愛雙方理想與現實的錯位。未進入熱戀同居的雙方對彼此和未來生活抱有美好期待,成為理想的幻影,構成與現實真實的對立。
(一)對伴侶的主觀想象與現實的錯位
英國文學評論家I·A·理查茲注意到了人在接觸事物時的奇妙心理過程:“人與事物的接觸總帶有符號化的色彩,即基于機體的需求賦予其意義,因此,與其說人在談論(指稱)事物本身,還不如說人在談論(指稱)他說指向的對象。”[1]《傷逝》全篇以涓生的視角回顧著愛情的始末,描繪著伴侶子君形象的初見和轉變。因而子君的形象被附加上強烈的他者視野,他者的期待與子君真實形象構成了錯位。
作為啟蒙知識分子的涓生個人對于伴侶有先行的主觀期待預設。一年前處在熱戀階段的子君符合涓生對理想伴侶的想象:蒼白清瘦的子君,臉上帶著笑渦的子君,形象上之純凈靈動,如同子君經常帶給涓生的老槐樹的新葉和紫白的藤花,與老槐樹、老樹干等一切具有陳舊色彩的周圍之物形成對比。在思想層面,子君對家庭專制、打破舊習慣、男女平等、易卜生、雪萊等帶有進步觀念的話題充滿好奇,并將進步意識化為行動,在二人交往半年后勇敢沖破胞叔和父親的阻撓,發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2]這般響亮的獨立宣言,做出大膽追求自由愛情的驚人舉動。子君身上展露出主動爭取婚姻自由和獨立自主的可貴進步意識,與當時社會一切舊思想、舊道德形成強烈對比,震動著涓生的靈魂,讓涓生感到“說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國女性,并不如厭世家所說那樣的無法可施,在不遠的將來,便要看見輝煌的曙色的”[3],仿佛看到了未來婚姻生活的希望。青春活潑的外表同進步的思想一起深深吸引著涓生,成為涓生理想型的實體,滿足了涓生對于未來理想伴侶的期待。
但現實中,回歸日常生活的子君逐漸展露出真實的居家樣貌,與先前帶給涓生理想的進步形象大相徑庭。在涓生眼中子君完全變了模樣:同居后的子君 “竟胖了起來,臉色也紅活了”[4];每天圍繞做飯、喂養動物等家務忙碌,“終日汗流滿面,短發都粘在腦額上;兩只手又只是這樣地粗糙起來。”[5]形象上由青春到粗糙的變化逐漸顛覆過往印象;性格上也不如以前一般聰穎、幽靜、體貼,在涓生眼中子君成為只顧著做飯和與房主爭執的庸常家庭婦女,失去了靈動的閃光;在涓生最為在意的精神層面,子君成為家庭主婦后早已什么書都不看,完全陷入為日常瑣事煩惱的庸常,先前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思想蕩然無存。子君在戀愛后自動退回到廚房成為家庭婦女的一員,從形象到性格思想均脫離了涓生的期待,讓涓生對這段戀愛關系的態度發生由興奮到倦怠的轉變。他愛的是幻想中真正進步的革命伉儷,無論婚前、婚后都能維持覺醒進步的意識,并在生活中付諸實踐。相比于攜手進步的伴侶,同居后現實中的子君在涓生眼里更像負擔和累贅,理想與現實的錯位動搖著維系愛情的根基。
(二)有邊界的自由戀愛生活
子君與涓生的自由戀愛突破家庭的阻攔和社會意識的束縛,當心意相投的純情男女勇敢地將所有男女青年內心向往的自由戀愛化為現實,心中必定對未來的同居生活產生無限的憧憬。然而自由戀愛的“自由”若要成真實則不易,未經現實考驗的自由戀愛實則是有邊界的自由,憧憬與現實成為戀愛敘事中的第二重錯位。
同對伴侶的想象一致,涓生對于同居后的生活也具有先行的預設期待。本以為憑著真正的愛情自由結合成為家庭的青年男女會過上想象中的自由安寧的幸福生活:如熱戀時期一樣交心夜談、讀書散步;和同樣有進步意識的伴侶談論進步思想,共擔生活的風雨,共同進步,讓愛情“時時更新,生長,創造”[6]。然而現實中同居后的生活完全被日常的瑣碎侵占,子君的日常活動完全圍繞家務打轉,沒有空閑時間再像熱戀時期一樣靜下來讀書,和涓生討論進步思想,日常似乎只剩下 “每日‘川流不息’的吃飯;子君的功業,仿佛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喂阿隨,飼油雞……”[7]好景不長,涓生被原單位開除,為了維持一家生計他忙于書稿的翻譯自顧不暇,但日漸困窘的家境和子君的粗糙越來越讓涓生不能感到安寧:因為子君吃飯,涓生的工作經常被催促打斷;因為子君經常將剩飯菜喂給小狗和油雞們,致使供給家中人的飯菜甚至不夠,讓涓生內心產生“覺了我在這里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8]的荒謬感,難以與子君溝通交流。
諸事不順的生活和“變化”了的子君處處讓涓生感到不適,有子君在的家庭生活讓他甚至感覺壓抑,以至于只有獨處才能感覺到久違的放松和自由。脫離穩定物質基礎的支撐,沒有理想伴侶的配合,加之同居前對自由愛情的想象過于美好,理想與現實的錯位讓自由戀愛實則成為一種有限的自由,加劇涓生迫切想要擺脫子君的想法。同居前,涓生經常對子君講述的各種西方進步思想,以及反復強調和描繪的愛情理想,均成為與眾不同的先進啟蒙話語深深吸引子君:“我的言辭,竟至于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我的舉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下,敘述得如生,很細微……”[9]然而回過頭看,涓生的言辭實質上是符號化的建構過程:涓生口中的愛情和伴侶實質都是具有指向性的說辭,帶有“應該是怎樣”的預設要求,為愛情中錯位的產生埋下伏筆。私人生活中理想與現實的處處錯位擴大了戀愛的裂隙,是愛情走向悲劇的直接誘因。
二、錯位的產生原因
在戀愛敘事中,理想變成幻覺泡影的沒落離不開現實物質層面為個體生存施加的困境和戀愛雙方主體的意識差異。
(一) 物質生活的困境打破美好愛情的幻想
涓生和子君的同居生活在開始之初便面臨著物質生存的考驗:為尋找住處二人花費了大半的籌款,卻也只找到了在涓生看來十分敷衍的住處;子君為此賣掉了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環,與家人鬧開,難以回頭;接著,同居過程中涓生被原單位辭退,直接讓全家失去經濟來源。熱戀中的青年男女在對未來的憧憬中以為憑借愛可以戰勝一切,但現實生活的困境逐漸暴露伴侶雙方與期待不同的真實面貌,追求精神契合的伴侶不得不直視現實的生存問題,觀念的不合加之形象的改變慢慢落空彼此的期待,成為雙方內心的芥蒂,讓原本因精神契合從而走在一起的戀愛雙方失去感情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撐。日常生活帶著種種生存考驗入侵愛情理想,未能承受住現實打擊的愛情與原先的期待構成錯位。
(二) 子君的個人選擇和有限的自我覺醒促成個體的全面倒退
子君依靠他人解放的自我覺醒只是一時,程度不深。子君大膽與家庭決裂奔向自由戀愛的行為是子君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身為人的獨立自由屬性,擁有追求自由愛情的權利。只可惜子君的自我覺醒只是被動覺醒,文中從頭到尾只有涓生主動為子君講解新思想,子君被動聽從然后點頭,并無其他主動進一步學習了解新思想的舉動;思想啟蒙的唯一來源是涓生,后續涓生因物質和心理層面的雙重困擾產生對子君的厭惡,讓子君無法得到進一步被啟蒙的契機,由此覺醒意識不進則退,“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還是一個虛空”。[10]子君本身應該不缺少掙錢的能力,個體身上也展現出難能可貴的覺醒意識。但出于個人選擇,子君在根本上并沒有延續覺醒的動力,完全把自己限制在家庭的框架內:在行動上沒有邁出家門、走入公共空間尋求經濟獨立,而是選擇安心料理家務,照顧夫婿,飼養自己喜歡的油雞和小狗阿隨,并心安理得。涓生的收入是維持生活的唯一來源,自然在家庭結構中掌握著經濟權利帶來的話語權,而經濟不能獨立的子君附庸性質的存在。涓生失業后家庭生活更為拮據,但是子君仍沒有選擇參與維持家庭經營的活動之中,只能仰賴涓生一人繼續尋找家庭困難解決的出路。深陷生活的瑣碎之中且不主動繼續尋求進步意識的熏陶,因而子君的性格和思維變得更為保守、庸俗、頹唐,引發掌握作為話語權主導的丈夫內心的不滿和反感,戀愛雙方的關系逐漸走向不平等加劇夫妻感情的隔膜。沒有物質支撐的愛情理想難以維持美好,所以當涓生明確表示出不愛子君的態度,二人感情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基礎消逝不再,作為丈夫附庸的子君也無法繼續再呆在原地,只能被動地離開,回到原生家庭之中。
同居后的子君依賴涓生和涓生的愛而活,自己對自由愛情和未來生活的想象可能僅限于能夠自由地和心上人一起私奔出逃,盡好自己照顧家庭生活的本分。如,飼養喜歡的動物,而無其他進一步的生活規劃,也忘記了進一步學習追求新思想的覺醒意識。子君在精神上和物質上都依賴于涓生。既難以獨立維系物質生活,又失去涓生的愛,走投無路的子君只能又回到來處。
(三) 當知識分子的偏見遇上現實
涓生將自己視作進步的新知識分子,在精神至上的年代,涓生的意識里存在對日常生活的固有偏見。生活中做飯吃飯、飼養動物、與鄰居溝通等日常事務,在他眼里是一種形而下的瑣碎存在。作為進步人士,料理日常生活瑣事不在他的職責和關心的范圍內,他的伴侶應該同樣是思想進步的女性,不該囿于廚房家庭等日常瑣事之中,而是應該追求思想上的進步。不尋求經濟獨立、不繼續討論進步思想、終日圍繞家務打轉的子君在涓生看來是未脫盡舊思想束縛的表現。因此涓生不理解子君對動物的喜愛,不理解子君照料家務的辛苦,對子君的冷漠和偏見進一步加劇。掌握經濟權的男性一方在精神上也占據主導,認定其不是自己所愛之人后便可將對方拋棄,而子君毫無還手之力,成為啟蒙理性殺人的犧牲品。
三、帶有啟蒙敘事色彩的愛情悲劇
戀愛生活中理想與現實的錯位離不開啟蒙知識分子的個人偏見,而知識分子對日常生活的偏見深植于20世紀20年代的社會時代語境,由此,《傷逝》中子君與涓生的愛情悲劇成為文本表層的外衣,在啟蒙敘事的觀照中深化成為帶有豐富意蘊的符號:其能指意義是令人唏噓的自由戀愛幻想破滅;所指意義則揭示著當時的啟蒙知識分子理想撞見現實的無能為力,伴侶和戀愛生活中的錯位實則象征著啟蒙話語與現實的錯位,直指對啟蒙者的反思在啟蒙敘事中,按照啟蒙主體和啟蒙對象進行劃分,知識分子與一眾封建思想的堅守者和執行者自然形成兩大陣營的對立。蒙昧未開、安于現狀的下層普通群眾構成阻礙社會向前變革的慣性勢力。魯迅在作品中構建知識分子形象進行自我言說的同時,表達了對于同類知識分子群體的關注、期盼和反思,進而探討啟蒙的方式、價值與意義。知識分子與國運的直接關聯賦予思想和知識更為崇高的意義。為將沉睡的國民從被封建舊思想道德鑄成的“鐵屋子”中喚醒,啟蒙知識分子將思想啟蒙視為己任,精神至上成為時代語境的主流社會意識。陳獨秀宣告“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 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1]在救亡圖存的感召下,進步青年紛紛離開家庭,拋棄庸常的物質生活走向獨立、理想、革命等精神高地,在宣傳思想解放的前沿廣場為推動社會變革振臂高呼,傳遞著自由、平等、獨立等進步觀念,希冀實現自身價值,成為與庸眾對立的閃光。
然而啟蒙知識分子回到日常生活,對外高舉的自由、平等、獨立等啟蒙話語旗幟在日常生活難以為繼。如,知識與理想兼備的進步分子涓生根本無法維系自己心向往的自由戀愛理想,更無法發揮自己所長在思想上進一步深入啟蒙、徹底解放初步覺醒的伴侶;再如,《孤獨者》中的魏連殳為了生存被迫犧牲理想委身于世俗……精神的清高無法抵擋日常生活泥沙俱下的洪流,一眾在廣場上為理想振臂高呼的啟蒙者成為日常生活中的落魄者,造成理想與現實形成不可調和的錯位;在《傷逝》中以愛情悲劇的方式展現出來,伴侶和愛情生活的錯位實質是啟蒙與現實的錯位;伴侶和愛情雙雙消散的涓生帶著深深的悔恨為子君送葬,子君的死和愛情失敗宣告著啟蒙知識分子面對生活實際的無所適從,即思想的崇高無法解決個人實際生存的危機。對精神至上的狂熱追求脫離了實際生活的需求,口號在被視為形而下的真實生活問題面前無用武之地,幾乎成為與現實脫節的虛空。肩負神圣啟蒙使命和職責的知識分子在愛情日常中的無所適從構成想象與實際情況的錯位、理想中熱烈滔滔的啟蒙進程與現實中無法深入的民眾淺層覺醒形成尷尬錯位,啟蒙知識分子的口號與行動、啟蒙事業與個人生活在尷尬錯位中形成對啟蒙主體價值和意義的深刻揭示和反思,使得愛情悲劇的敘事在對啟蒙話語的反思中超出愛情的一般主題,浸染了更為深沉的啟蒙色彩。
結語
理想與現實的錯位若無法根除,“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啟蒙主義言說和文學革命的倡導終究只是圈內文化人的自說自話,并沒能馬上發揮出實際的社會功效,魯迅張揚啟蒙卻又深感啟蒙無效即是明證。”[12]啟蒙的步伐不能就此在生活失敗的消極中觀望停留,不能因為暫時的失敗被判為毫無意義的死刑。因而在《傷逝》的最后,涓生出于個人生存和知識分子的使命決心“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13],如同絕望的反抗。但是這種前行帶著對子君無盡的悔恨和悲哀,愛情的失敗成為身為知識分子的涓生在啟蒙的漫漫長路中,對何為有效的啟蒙、理論如何與實踐結合等啟蒙使命和前景的警醒和反思。《傷逝》借助對愛情悲劇的書寫,表達對啟蒙知識分子的自身局限性的反觀,愛情敘事下的愛情悲劇展現出知識分子在私人生活中無所適從的困窘,凝縮了不同時代、社會背景下人的精神困境。因而,愛情中的錯位書寫實則反映著啟蒙話語與現實錯位,讓愛情敘事增添了啟蒙敘事的深刻意義,成為對啟蒙者的觀照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