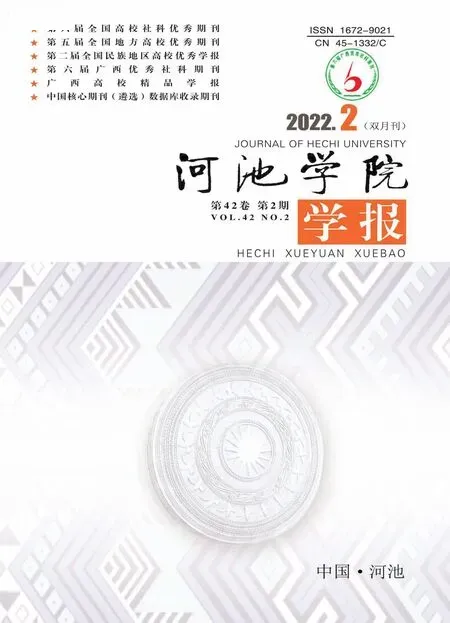基于傳奇視角的老舍作品敘事藝術及其意蘊探析
王 興
(河南財經大學 素質教育中心,河南 鄭州 450046)
傳奇傳統與現代文學形成之間有很強很密的文本上的“互文性”。現代文學經典作家老舍深受“傳奇”等文化傳統的熏陶與影響,其作品帶有鮮明的“傳奇氣味”。而富有“中國經驗”意味的傳奇傳統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載體,在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性的當代,文化與文學領域內“我(們)是誰”的認同問題被推到理論前沿,以傳奇為代表的民族文化傳統重現和表征著“我(們)”的形象,因此,在中國現代文學實踐中對傳奇等民族文化傳統的精神探源與現代承傳探討,在民族文化認同的當下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一、知人論世:老舍與作為文化傳統的傳奇
作為中國傳統文學重要的文體類型與敘事模式,“傳奇”內涵豐富且具有重要意義。“傳奇”在《辭海》中被解釋為“小說體裁(一般指唐宋文言短篇小說如《李娃傳》)、傳奇小說集、戲曲形式、中世紀歐洲長篇敘事詩等幾種典型。”[1]1619而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學發展歷程中,“傳奇”是一個多元概念,其與時代發展亦步亦趨:“傳奇之名,實始于唐。唐裴铏所作《傳奇》六卷,本小說家言,為傳奇之第一義也。至宋則以諸宮調為傳奇……則宋之傳奇,即諸宮調……元人則以元雜劇為傳奇,《錄鬼簿》所著錄者……至明則以戲曲之長者為傳奇,乾隆間……遂分戲曲為雜劇傳奇二種,余曩作《曲錄》從之。蓋傳奇之名,至明凡四變矣。”[2]64起源于神話、志怪的“傳奇”是中國敘事文學的核心元素,在文學發展歷程中被不同的時代注入新的不同的元素,并逐漸成為中國傳統文學的一種基本敘事模式與傳統。“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異,然敘述婉轉……變異之談,盛于六朝……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3]70“傳奇”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唯奇能傳、無奇不傳的審美旨趣追求貫穿古代文學多種體類、多個歷史發展階段。作為一種特殊的敘事話語與敘事模式,內涵豐富且有“中國經驗”意味的“傳奇”并不僅限于古代文學,它也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載體,對歷代文學創作實踐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產生了深刻影響。
中國現代文學在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雖以反叛傳統為旗幟,但對傳統而言并非斷裂性存在。因此,現代文學轉型與中國文化傳統承襲常常成為熱點話題。老舍作為現代文學經典作家,其小說及其文學風格因帶有傳奇色彩而廣受現代讀者喜愛。“鄭西諦說我的短篇小說每每有傳奇的氣味!無論題材如何,總設法把它寫成個故事——無論他是警告我,還是夸獎我——我以為是正確的。”[4]312老舍小說中的傳奇色彩除了其取材具有傳奇性外,還在于老舍自幼受到的傳奇等文化傳統的深刻影響。《三俠五義》是老舍童年時期最喜歡的啟蒙讀物,他少年讀書期間“最先接觸到的就是《施公案》一類的小說”[5]。他的課余娛樂生活則是最愛去小茶館聽評書。“我十二三歲時讀《三俠劍》與《綠牡丹》也是那樣的起勁入神。”[6]29民間傳奇故事蘊含的俠義內容與理想精神等都深深地吸引著成長中的老舍,他甚至達到癡迷的境地——“有一陣很想當黃天霸。每逢四顧無人,便掏出瓦塊或碎磚,回頭輕喊:看鏢!有一天,把醋瓶也這樣出了手,幾乎挨了頓打。這是聽《五女七貞》的結果。”[7]246以傳奇傳統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為老舍的成長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老舍不僅從小熱愛評書、相聲等民間通俗文藝,還樂于結交社會上的各色江湖朋友,熱衷于極富俠義精神的傳統武術。他在濟南生活時期還曾專門走訪號稱“山東第一桿槍”的拳師馬永奎,與之相談甚歡并拜師學藝,從他那里獲得不少武林界的傳奇素材。1931年,老舍受邀在美國加州學院為廣大師生作《唐代的愛情小說》的專題講座。1934年,他還專門寫了《洋涇浜奇俠傳》(《小說半月刊》約稿)。由此可見老舍對傳奇傳統的深厚造詣與古典文學素養。因此,老舍作品中的傳奇敘事特征與現實主義風格中的浪漫主義色彩便也是自在情理之中。
《老舍選集》自序中有其夫子自道——選集內作品皆“講到所謂江湖之事的:《駱駝祥子》是講洋車夫的,《月牙兒》是講暗娼的,《上任》是講強盜的,《斷魂槍》是講拳師的”[8]194。其中,《黑白李》是“只用傳奇的筆法,去描寫黑李的死”[8]194,而極富江湖傳奇色彩的《斷魂槍》則是老舍先生謀劃許久的武俠傳奇長篇《二拳師》篇幅中的“一小塊”[8]194。在其文學世界所展示的現實人生中,他為讀者講述著一個個傳奇的故事。曲折離奇的故事情節、評書式的傳奇講述方式、坎坷離奇的人物命運,都是作家對當時現實人生的思考與文化反思,與傳奇傳統中“游戲成文聊寓言”模式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極富“中國經驗”意味的傳奇傳統深刻地影響著老舍的個人成長、文學創作與審美追求,其對傳奇傳統的承襲、轉換與創新造就了老舍小說的傳奇色彩與獨特藝術魅力。
二、人文關懷價值旨歸:主題內容的傳奇特質
老舍作為現代文學中的經典作家,因其對包括傳奇等民族文學傳統的承襲創新,造就了其文學作品的可讀性與接受度,比如老舍先生于20世紀風云變幻的30年代所創作的《趕集》《蛤藻集》《集外集》等即如此。“五四以來的小說創作一直處于推崇現代、反叛傳統的思路中,包括老舍也時刻警醒自己是現代作家,要創作現代小說。然而‘中國小說的形式’作為一種強大的民族無意識力量,老‘象找替身的女鬼似的向我招手’。”[9]226以啟蒙救亡為使命的現代作家雖時刻不忘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但其創作總是有意無意地承傳著由來已久的民族文學傳統。鄭振鐸認為老舍小說的傳奇性在于其強烈的故事性特點,其實,同為現代文學經典作家,如果說魯迅習慣在平實故事講述中深挖思想寓意,那么老舍則側重于用曲折離奇的故事來引導現代讀者自己探尋小說文字后面的寓意。因此,文學敘事的傳奇性特征并不是老舍的最終目標。老舍的傳奇文學世界中,“從內容上說,傳奇不只是談神論鬼與英雄俠客的專利,更是對歷史滄桑與世態人情的真實演繹”[10]。老舍作品將現實融入傳奇故事,其文學講述兼顧故事吸引力與深刻寓意,所展示的現實悲歡離合與世態炎涼,正是舊中國時代語境下社會各階層群體真實生活狀態與各樣精神風貌的深刻呈現。這不僅極大豐富了現代小說的時代容量與社會內涵,也自然契合傳奇以小見大的文學傳統。
在小說主題內容上,老舍總是把文學視點聚焦于俗世底層中小人物不平凡的經歷和遭遇,通過為現代讀者講述曲折離奇的市井江湖故事,揭露啟蒙救亡時代語境下舊中國的社會現實,深情關注底層民眾命運,兼顧小說的哲理性與通俗性。比如,在大家熟知的《柳家大院》《我這一輩子》《抱孫》《鄰居們》《不成問題的問題》等小說文本中,老舍總是能夠從小人物的現實生活著眼,讓事件發展常悖于正常境遇,故事情節多有巧合且結局又極其荒誕。作品讀來給人以現實中極富傳奇荒誕色彩之感,作家在文學實踐上真正做到了源于現實又超越現實。顯然,這極容易讓人想到以唐傳奇、宋元話本為典型的市井傳奇小說,老舍也像其作者一樣為吸引讀者而突出強烈的故事性,他常在文本開始或情節推進中間多次精心設置各類懸念、制造意想不到的包袱,用說書式話語講述引導現代讀者展開豐富想象,而最終故事結局與人物命運常超乎想象。顯然,老舍在文學實踐中繼承了傳奇等傳統小說側重情節轉折、強調故事性與傳奇性的常用模式。
以《我這一輩子》為例,小說以第一人稱限制敘事視角,講述“我”作為一名社會最底層巡警的并不轟轟烈烈的一生。這里有讀者所熟知與習慣的文學敘事審美接受經驗:故事講述有頭有尾、側重完整,情節發展多變不一,命運結局出人意料,底層市井小巡警奮力掙扎生存的曲折人生悲劇講述中,依然充滿了傳奇色彩與荒誕意味。本來做著體面裱糊匠職業的“我”與俊俏的妻子育有一兒一女,生活簡單平凡,然而不知怎么的,妻子就和傻大黑粗的師哥私奔了。這也成為“我”永遠揮之不去的心結與人生命運的轉折點。“直到如今,我還是不能明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所不能明白的事也就是當時教我差點兒瘋了的事,我的妻跟人家跑了。”[11]62出人意料的生活變故與事業打擊突然改變了“我”看似一帆風順的一生,也成為“我”無可把控的命運的轉折點。意外與打擊一次次不期而遇,貧苦的巡警生活還因上司局長毫無征兆的一句“有胡子的全脫了制服,馬上走!”這一極其荒唐的緣由而被終止,使“我”丟了唯一可以果腹的飯碗。小說中荒誕不經的情節與人物戲劇性突轉的命運,也似乎讓“我”與讀者們認識到,無論你多么堅強,再怎么努力掙扎,都宿命般地無法改變這多災多難的生活與不可捉摸的荒誕人生。小說借市井小民現實生活的傳奇生命,也表達著作家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無常與荒謬的揭露。
老舍有著將市井小民世俗生活荒誕化、戲劇化展現的超凡能力。《抱孫》中的王老太太為了能夠實現抱孫子的愿望而經歷了數次大起大落的人生,其心理從期盼、興奮、擔憂、痛苦再到希望、暗喜與心死。小說情節也從王少奶奶懷孕、難產、生子再到人財兩空,小說最終揭示——老太太因為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識而害了兒媳與孫子。一個底層市井家庭生孩子的故事被跌宕起伏的情節與離奇不定的人物命運走向所加持,大起大落的故事推進總是能夠讓讀者為王少奶奶與孩子捏一把汗。而《柳家大院》為讀者講述了小王媳婦被虐慘死的故事,講述方式也是借不尋常的筆法展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出人意料的故事。尤其是小說中的小姑子也是迫害其嫂子的幫兇,最后意外地被其父親戲劇性地賣掉,這深刻展示了近現代中國男尊女卑觀念對女性的戕害。《聽來的故事》則用荒誕幽默的筆觸,借助第三人稱限制視角為讀者講述孟智辰不可思議的步步升官史,其能步步升官竟是因為他出人意料的“默默中抓住種種人的最高的生命理想”,深諳熟悉了這“沒辦法就是辦法的時代”的處世精髓。《鄰居們》中毗鄰而居的明家與楊家因雞毛蒜皮的“葡萄事件”“寄錯信事件”等生活誤會與各種不湊巧,鬧出了一系列明爭暗斗、啼笑皆非的故事,而多次的誤會與爭斗事件后面則是作家對人性暗河的揭示。《鄰居們》小說文本中所產生的戲劇性都是由作者精心安排的一次次誤會與不湊巧所帶來的。小說的故事敘述雖娓娓道來,情節發展也層層遞進,但故事卻是按照非常規邏輯結束而達到出乎意料的效果,作者似乎也在告訴讀者無常的人生才是常態。
老舍也擅長通過故事結局突變給讀者制造“驚喜”,從而賦予故事傳奇特征。比如《黑白李》中,人們都會按照故事既定的講述推理出一定是白李在暴動中犧牲了,而實際上,犧牲的卻是黑李。情節戲劇性的突轉與突兀的結局安排,使讀者詫異后又瞬間能夠恍然大悟。《不成問題的問題》中,最后也是農場人事管理上“劣幣驅逐良幣”,實干勤勉的尤大興終被只會帶來虧損的丁務源替代,故事發展荒誕可笑卻又契合人情至上的中國傳統社會邏輯。而在老舍的《一筒炮臺煙》《戀》《愛的小鬼》等作品中,同樣也是故事情節發展突變,結局出人意料而蘊含引人深思的主旨。如果說傳奇傳統敘事注重情節的出乎意料是為了引起讀者關注,那么老舍將傳奇因素加入市井生活而使情節出人意料則能夠為其小說文本帶來荒誕與戲劇性,進而旨在展示生命無常與人性的不可捉摸,其文字背后是肩負啟蒙使命的現代知識分子老舍對時代語境下舊中國社會的理性思考與人性探索。
老舍作品中也有對舊中國社會中另類特殊職業,諸如鏢師、拳師、暗娼、劫匪、騙子等江湖傳奇的講述。比如《小鈴兒》借鑒唐傳奇《謝小娥傳》替父復仇的傳奇程式,為讀者展示了小鈴兒充滿武俠情懷的復仇故事。《殺狗》則為現代讀者講述了一位不畏強暴、鐵骨錚錚的老拳師奮勇抗爭、抗日愛國的傳奇故事,語言風格極富傳統民間武俠傳奇風味,如“一道白閃猛孤仃的把黑暗切成兩塊……白光不動,黑影在白光邊上顫動……白光昂起,黑影低落”[12]38。小說借助武俠傳奇的講述方式為現代讀者展示著民族個體抗日愛國的故事。《浴奴》是烈婦復仇傳奇,《月牙兒》是神秘奇異的暗娼傳奇,《兔》則是一個刺激而復雜的江湖社會生存傳奇故事。《上任》為現代讀者講述由匪而官的尤老二企圖“用黑面上的人拿黑面上的人”未果的官匪傳奇故事,《斷魂槍》中則始終籠罩著隱秘的江湖傳奇氛圍。老舍于此借江湖傳奇故事反映社會現實——“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這是走鏢已沒有飯吃,而國術還沒被革命黨與教育家提倡起來的時候。”[13]270在老舍的現代小說文本實踐中,“這些非常態生活本身就具有了傳奇文學所需要的‘奇’的美學屬性。……選擇生僻怪異的題材以增敘事的傳奇或神秘的審美趣味,就成為了從魏晉志怪及唐宋傳奇延續下來的‘傳奇系’文學的一個創作傳統”[14]。
三、現代文學實踐策略:文本修辭形態的傳奇特征
老舍在其傳奇文學世界建構中,除了小說主題內容方面的傳奇旨趣追求外,常側重通過文學的修辭形態來增加文本的傳奇性特征。“‘修辭’,廣義地說,指的是作者如何運用一整套技巧,來調整和限定他與讀者、與小說內容之間的三角關系。狹義地說,則是特指藝術語言的節制性的運用。”[15]124概言之,廣義的“修辭”就是小說家用什么樣的講述語言將故事敘述出來,而我們熟知的中國古典小說典型話語修辭形態就是所謂的“虛擬的說書情境”。在老舍的文學世界建構中,他則通過設定說書情境、語言的民間化、反諷等講述現代市井傳奇故事,賦予作品內在傳奇氣蘊。
老舍的小說創作深受傳奇等中國文學傳統講述方式的深刻影響。正如其自述:“鄭西諦說我的短篇小說每每有傳奇的氣味!無論題材如何,總設法把它寫成個故事。”[4]312中國傳統小說敘事一般是一種為現代讀者所熟知的典型說書情境,如所謂的“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話分兩頭,事歸一面”等。這也正是唐傳奇所確立的“敘述婉轉”“作意好奇”開創性地賦予中國古代小說的典型修辭話語形態。可以說,以傳奇為代表的古典小說之所以能讓讀者欲罷不能,正是在于其講故事的方式。而由唐宋時期便興起流行的說書藝術,常常是說書人以全知視角為聽眾“講”一個故事。“小說之所以是小說不僅在于它是故事,關鍵在于它是講故事。當人們把聽故事與講故事分開,并關注于講故事這件事的時候,小說作為一種藝術就誕生了。”[16]從敘事藝術看,傳奇的本質其實正在于其是“講故事”的藝術。老舍曾自述自己十分善于說故事,認為“是小說就得有個故事,但故事本身并不就是小說”[9]234。現代作家雖以啟蒙救亡為使命,但老舍深受傳統說書藝術熏陶與古典小說影響,其文學世界的展示總是通過類似說書人的方式來完成,我們也總能在小說家提供的故事情節中感知到一個旁觀者的敘事視角存在。
老舍自然深知“說書”講故事這種傳統敘事的魅力,因此常以第一人稱視角方式融入創作,使其小說自帶說書人風格,始終能夠緊緊抓住讀者。小說中的說書氛圍與傳奇故事意蘊,使得老舍的文學世界呈現更顯成熟流暢。《我這一輩子》中所展示的生命打擊與命途多舛讓讀者感同身受,《黑白李》中死掉的到底是黑李還是白李始終讓讀者放心不下,《柳家大院》中來自大雜院的老王在一次次殘忍虐待兒媳導致其最終死去后,竟想起來要變賣始終與自己一條戰線的女兒,小說的故事走向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內。這些小說所描述的故事之所以能勾人心弦正是在于老舍講故事的方式。限制視角實現了“作者的隱退”,從而賦予中國小說現代品格,如果說五四小說采用第一人稱限制視角是為了抒情,那么老舍作品中采用限制視角多數則是為了講好故事。老舍小說中的說書情境常在文本開頭便開門見山,突顯主人公鮮明性格,比如《鐵牛與病鴨》中“王明遠的乳名叫‘鐵柱子’。在學校里他是‘鐵牛’。好像他總離不開鐵”[17]104;《毛毛蟲》的開頭:“我們這條街上都管他叫毛毛蟲。他穿的也怪漂亮,洋服,大氅,皮鞋,啷當兒的。可是他不順眼,圓葫蘆頭上一對大羊眼,老用白眼珠瞧人。”[18]196這些開場極容易讓讀者想到傳統文學唐傳奇中諸如《南柯太守傳》的開頭:“東平淳于棼,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氣,不守細行。”[19]107抑或是《東城老父傳》開頭的“老父,姓賈名昌,長安宣陽里人”[19]168等,開篇便把人物形象與性格凸顯。交代故事背景、既定主題呈現等也是老舍小說中用來吸引讀者的說書情景常用方式,比如《柳家大院》中“這兩天我們的大院里又透著熱鬧,出了人命。事情可不能由這兒說起,得打頭兒來”[20]68。《斷魂槍》中“沙子龍的鏢局已改成客棧。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13]270類似說書場景的呈現。又如《上任》中“尤老二去上任。看見辦公的地方,他放慢了腳步”[21]127,《抱孫》中“難怪老太太盼孫子呀;不為抱孫子,娶兒媳婦干嗎?”[22]77老舍作品中鮮明的說書情景,顯然能夠給讀者帶來強烈的故事性。我們也能夠發現,老舍小說中設置的說書情景里,常會有一個自問自答的畫外音來推動情節發展,如小說《大悲寺外》文本中反復出現的“他為什么作學監呢……他作什么不比當學監強呢?”[23]27老舍小說中類似說書講故事的方式與情境,總能給現代讀者帶來一種強烈的感情觸動,進而增強故事本身的傳奇色彩。
作為“人民藝術家”的老舍,自幼深受《施公案》等古典文學與中國民間通俗藝術熏陶與影響,十分熟悉民間語言傳統與習慣。其小說語言俗白質樸、簡明通俗、幽默風趣,能夠做到雅俗共賞又貼近市井生活,因此深受現代讀者大眾喜愛,其小說文本的傳奇特質也藏于通俗化的民間語言形式中。正如老舍自述“那里的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兒茶的吆喝的聲音,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張彩色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的描畫它。它象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24]430。因此,老舍在文學創作中十分擅長借鑒使用民間語言形式,比如《柳家大院》中“她和她爸爸一樣討人嫌,能鉆天覓縫地給她嫂子小鞋穿。真要來個吊死鬼,可得更吃不了兜著走。別裝孫子啦”[20]72。小說文本中經常出現的民間口頭語與表達方式,生動真實地再現了中國傳統市井生活的典型場景。老舍也會通過方言使用來增強其小說講故事的表現力,比如在《柳家大院》小說文本中出現的“死巴”“高招兒”“節骨眼”“狗著”等都是典型的北京民間方言土語,能夠讓北京普通讀者對小說與所講述的故事感到熟悉而親切。老舍從小就熟知以傳奇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民間通俗文藝,其鮮明特質就是語言形式的口傳、鮮活與質樸、白俗。而老舍的小說語言也常用民間方言、俗語與白話,來實現傳奇文本的敘事功能與營造強烈的故事情境,進而形成雅俗共賞的文學風格與傳奇性特征。
另外,老舍也常通過反諷增強其文本的故事可讀性,引導讀者挖掘小說深層意義。“什么才是‘反諷’性的修辭?孫述宇把它譯成‘表里不一’,正確地表述了這一轉義外來語的實質意義……反諷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前后印象之間的差異,然后再通過這類差異,大做文章。”[15]146我們在以傳奇為代表的傳統古典文學中經常看到反諷作為一種語言修辭藝術的使用,比如《西游記》中其對各類妖魔鬼怪的寓意影射,《紅樓夢》中其對各色人物口是心非的明褒實貶意指,《金瓶梅》中其對市井生活中俗人俗事的挖苦諷刺,《水滸傳》中其在對歷史英雄人物的肯定中又質疑人性之黑暗等等。老舍熟知中國傳統傳奇小說中借反諷表達真實主旨與言外之意的套路并將其運用于創作的作品中,比如他的《不說謊的人》《犧牲》《開市大吉》《善人》等,都自帶反諷特質。《犧牲》中言必稱“美國家家有澡盆”的毛博士,處處看不上臟亂差的中國卻還必須生活在這里,他的十二次“犧牲”中的每一次都是作家的調侃與諷刺。標榜高級知識分子與接受過當時西方先進文化的人,實則是徹頭徹尾的極具封建頑固思想的利己主義者。而《善人》中敘寫的“穆女士一天到晚不用提多么忙了,又搭著長得富泰,簡直忙得喘不過氣來……她永遠心疼著自己,可是更愛別人,她是為救世而來的”[25]200。小說用極致的反諷展示著穆女士言不符實的偽善言行與嘴臉。《不說謊的人》中,作家則借“不說謊”來諷刺周文祥的自我妄信與唯我獨尊。反諷能夠讓小說故事性更強,使得文學空間停留在現實與荒誕之間,賦予文本傳奇性特質。“奇書文體的首要修辭原則,在于從反諷的寫法中襯托出書中本意和言外的宏旨。”[15]156老舍小說中的反諷并不止于故事本身,而在于通過表里虛實實現小說主旨的特別寄寓。老舍小說語言中說書情境的設置、民間化語言的借鑒與反諷修辭形態等共同建構了其文學世界的傳奇品質。
四、結語
富有“中國經驗”意味的“傳奇”作為古典文學的一種固有傳統,對后世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深受傳奇等文學傳統的熏陶與影響的中國現代作家老舍,用承襲創新的態度來描摹自己筆下的市井江湖的傳奇世界。他的小說實踐不僅繼承了傳奇傳統,實現了文學傳統在同源關系上的文學歷時性接受,而且在借鑒與個人化創新后形成一種獨特的傳奇風貌。經濟全球化與消費主義浪潮正深刻改變著中國文學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文化多元性與混雜性越來越顯著。以“傳奇”為代表的民族文化傳統因其重現和表征著“我(們)”的形象,因而成為文化身份認同的重要手段和場域。“傳奇”傳統所表征的豐富內涵在當代恰恰可以擔當起民族文化身份認同的重要責任,而這也正是重新探討現代經典作家老舍與傳奇傳統關系的當代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