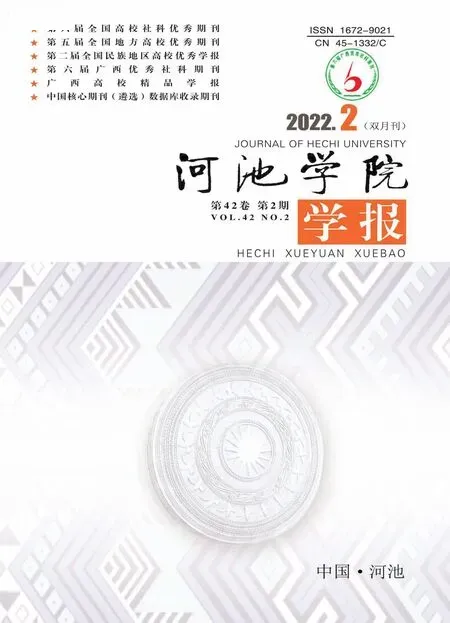殷周金文賞賜類動(dòng)詞考索
寇占民
(河池學(xué)院 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廣西 河池 546300)
殷周金文所記錄的內(nèi)容十分豐富,主要記述殷周社會(huì)君臣的重要活動(dòng),再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統(tǒng)治集團(tuán)的言語(yǔ)行為。其中記錄賞賜內(nèi)容的銘文占金文的絕大多數(shù),這是因?yàn)橘p賜制度是殷周特別是西周社會(huì)政治制度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它業(yè)已成為西周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幾乎滲透到了社會(huì)生活的各個(gè)領(lǐng)域。可以說(shuō),西周的賞賜活動(dòng)就像殷商的祭祀活動(dòng)一樣,成為了社會(huì)活動(dòng)領(lǐng)域中的常態(tài)化行為。賞賜制度深刻地影響著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政治、經(jīng)濟(jì)、軍事、文化、宗教以及人們的思想意識(shí)和價(jià)值觀念。殷周賞賜類銘文在金文中占有的比例較大,就是因?yàn)榇蠖鄶?shù)青銅器的制作都源于獲得了某種賞賜,無(wú)論是軍事、冊(cè)命、朝覲和祭祀類銘文,凡是參與王朝活動(dòng)而有功者都會(huì)得到統(tǒng)治者的賞賜。從主題分類上看,真正稱為賞賜銘文的并不多,但是由于殷周銅器銘文的內(nèi)容大多為旌功之辭,所以大多金文中都出現(xiàn)了賞賜環(huán)節(jié)。從廣義上來(lái)說(shuō),凡是出現(xiàn)賞賜環(huán)節(jié)的都可以列入賞賜類銘文。
一、賞賜類銘文的概述
每一類不同主題的銘文在行文上都有著自己的特點(diǎn)。冊(cè)命類銘文的賞賜活動(dòng)是在冊(cè)命官職程序之后進(jìn)行,軍事類銘文的賞賜活動(dòng)是在戰(zhàn)后的祭祀或獻(xiàn)俘活動(dòng)之后進(jìn)行,朝覲類銘文的賞賜活動(dòng)是在朝覲活動(dòng)之中進(jìn)行,祭祀類銘文的賞賜活動(dòng)是在祭祀之后進(jìn)行。殷周金文中的賞賜者主要是當(dāng)朝天子和諸侯等貴族集團(tuán),受賞者大都為有功績(jī)于國(guó)和家的文臣武將。由于獲得天子和諸侯等貴族集團(tuán)的賞賜是人生中最為榮耀之事,對(duì)于這一儀式的記述最為詳盡,所以這一環(huán)節(jié)在各類銘文中都占有突出的位置。從數(shù)量上來(lái)看,賞賜類動(dòng)詞的數(shù)量較多;從詞頻上來(lái)看,賞賜類動(dòng)詞出現(xiàn)的頻率較高,為此我們列專文加以討論。一方面,我們從動(dòng)詞的語(yǔ)義和語(yǔ)法角度加以歸納整理,目的就是為了了解這類動(dòng)詞的意義與功能特征;另一方面,我們從語(yǔ)用角度進(jìn)行分析總結(jié),目的就是為了對(duì)金文文體要素的梳理與歸納。
從商代晚期就出現(xiàn)了賞賜類銘文,一直到西周晚期沒有中斷,賞賜銘文貫穿了商周社會(huì)。例如,商代晚期的作冊(cè)盤甗銘、小臣邑?cái)秀憽⑿∽邮劂懞托〕加嶙疸懙龋髦艹跄甑睦憽⑹鍓鞣蕉︺懞筒粔垠懙龋髦芡砥诘捻瀴劂懞筒黄潴w銘等。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賞賜類銘文的文辭較為簡(jiǎn)短,記錄的內(nèi)容簡(jiǎn)單,一般只有賞賜的時(shí)間、對(duì)象和物品。從西周早期后段開始,賞賜類金文行文記事比較復(fù)雜,內(nèi)容逐漸豐富起來(lái)。不僅出現(xiàn)了賞賜的時(shí)間、對(duì)象和物品,還出現(xiàn)了賞賜的儀式程序和賞賜原因的記述,更為重要的是在行文上增加了賞賜者與受賞者的言語(yǔ)的直接記錄,賞賜類銘文由單純記事發(fā)展到了記言。這是殷周賞賜類金文文體要素上的一個(gè)重大變化,這一“記言”要素的出現(xiàn)對(duì)后世記事類文體特征與功能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總之,賞賜類銘文最重要的標(biāo)志就是在記述文辭中出現(xiàn)了賞賜類動(dòng)詞,可以說(shuō),對(duì)這類動(dòng)詞的梳理是掌握賞賜類銘文要素的鎖鑰。本文以殷周賞賜類銘文為語(yǔ)料,對(duì)所有的賞賜類動(dòng)詞進(jìn)行窮盡式的數(shù)量統(tǒng)計(jì),以期準(zhǔn)確地反映出該類動(dòng)詞面貌①本文以殷周金文近500篇賞賜類銘文為語(yǔ)料,進(jìn)行數(shù)量統(tǒng)計(jì)與分析。選用的著錄書有: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bǔ)本,中華書局2007年出版),本文簡(jiǎn)稱《集成》;劉雨、盧巖編著《近出殷周金文集錄》(中華書局2002年出版),本文簡(jiǎn)稱《近出》;鐘柏生、陳昭容、黃銘崇、袁國(guó)華編著《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曁器影匯編》(臺(tái)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出版),本文簡(jiǎn)稱《新收》;吳鎮(zhèn)烽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本文簡(jiǎn)稱《銘圖》。以后文中出現(xiàn)均按此例,不再另注。。
二、賞賜類動(dòng)詞的梳理
由于賞賜類金文在各類主題銘文中的分布較為廣泛,這給我們統(tǒng)計(jì)賞賜類銘文帶來(lái)了一定的難度。但是,我們依據(jù)動(dòng)詞的意義與功能,結(jié)合每篇銘文的敘事主題,同時(shí)參考動(dòng)詞出現(xiàn)的頻率,采用等級(jí)分類方法,將主題標(biāo)志性(或代表性)動(dòng)詞(共計(jì)30個(gè))分為3類。一類賞賜動(dòng)詞2個(gè):賜、賞。這類動(dòng)詞出現(xiàn)的頻率較高,它們都在百次以上,成為賞賜類金文的典型標(biāo)志。二類賞賜動(dòng)詞8個(gè):休、釐、令、命、舍、兄、、賓。這類動(dòng)詞作為賞賜義都在10次左右,成為賞賜類金文的次要標(biāo)志。三類賞賜動(dòng)詞20個(gè):益、畀、、儕、付、歸、畮、受、、友、叀、褱、贛、分、、稟、曾、以、、加。這類動(dòng)詞作賞賜義不超過(guò)5次,多數(shù)不是該詞的核心義,而是其引申義和假借義。
依據(jù)賞賜動(dòng)詞的類別與詞頻詳述如下。所錄銘文字形一律采用寬式隸定,行文盡量使用通行字體。
(一)一類賞賜類動(dòng)詞的整理
1.賜
關(guān)于金文中表賞賜義的“賜”,最常見寫作“易”,偶爾也寫作“錫”“睗”“”等。經(jīng)過(guò)學(xué)者們的考證,“易”應(yīng)為“益”之省文,本義就是傾注,引申為“賜予”義[1]216-228[2]358-361;或認(rèn)為“易”與“益”為一字分化[3]7-21;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易”與“益”是假借關(guān)系[4]52。例如:
(1)癸巳,王易(賜)小臣邑貝十朋,用乍(作)母癸尊彝,隹(唯)王六祀,彡(肜)日,才(在)四月。(小子邑?cái)?商晚《集成》15.9249)
(2)隹(唯)九月初吉戊戌,王在大宮,王姜易(賜)不壽裘,對(duì)揚(yáng)王休,用作寶。(不壽簋 西早《集成》7.4060)
(3)□伯令生史事(使)于楚,伯錫(賜)賞,用作寶簋。(生史簋 西中《集成》7.4101)
(4)王睗(賜)乘馬,是用左(佐)王;睗(賜)用弓,彤矢其央。睗(賜)用戉(鉞),用政蠻方。(虢季子白盤 西晚《集成》16.10173)
(5)用(賜)眉?jí)郏f(wàn)年無(wú)疆。(鄀公平侯鼎 春早《集成》5.2771)
例(1)為商代晚期金文,用“易”表賜。銘文大意是在帝辛六年四月癸巳這一天舉行肜祭,商紂王賞賜給了小臣邑十朋貝,邑用來(lái)給母癸制作了這件尊彝。例(2)銘文也用“易”表賜。不壽簋銘是一篇西周早期標(biāo)準(zhǔn)的賞賜銘文,文中除了記述賞賜的時(shí)間、地點(diǎn)、賞賜者和受賞者之外,還出現(xiàn)了答謝之辭“對(duì)揚(yáng)王休”。例(3)用“錫”表賜,為假借。看來(lái)借“錫”為“賜”是在西周中期開始的,古文獻(xiàn)中常見。例(4)用“睗”表賜,屬于假借。例(5)用“月易”表賜,也屬于假借。金文表示賞賜義的“易、益”為本字,“錫、睗、月易”為假借字。
從主題分類角度來(lái)看,上揭銘文可以劃分為賞賜類銘文的是例(1)(2)。銘文中只出現(xiàn)賞賜者、受賞者、賞賜物和賞賜時(shí)間,這些文體要素代表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賞賜類銘文的一般體例。例(3)敘述生史出使楚地,回來(lái)后得到賞賜,屬于朝覲類銘文。例(4)虢季子白盤銘文敘述的是西周末年征伐獫狁之史實(shí),應(yīng)當(dāng)歸入軍事類銘文。殷周金文大凡進(jìn)行賞賜都是有原因的,銘文在作器之因中往往敘述被賞賜的原因,因此只有那些沒有敘及原因的銘文我們才歸為賞賜類,記述原因的銘文按其內(nèi)容歸入相應(yīng)類別。例如,西周早期青銅器麥方尊(《集成》11.6015)銘也敘及了賞賜之事,“作冊(cè)麥易(賜)金于辟侯,麥揚(yáng),用作寶尊彝”。這是井(邢)侯覲見周王,并參加了一系列活動(dòng),回到井(邢)國(guó)之后,井(邢)侯賞賜了一直跟隨著他的史官作冊(cè)麥,此銘文應(yīng)當(dāng)歸入朝覲類。
2.賞
殷周金文中表示賞賜義的“賞”主要有兩種寫法:賞與商。“商”為“賞”的假借字。從商代晚期的金文就有假“商”為賞,一直到春秋時(shí)期的金文中還有這種用法。表示賞賜義的“商”,在金文中有時(shí)也寫作“”,這種寫法大多出現(xiàn)在商末周初的銘文里。例如:
(8)己亥,揚(yáng)視事于彭,車叔商(賞)揚(yáng)馬,用作父庚尊彝。(揚(yáng)方鼎 西早《集成》5.2612)
(9)唯六月既死霸壬申,伯屖父蔑御史競(jìng)歷,賞金,競(jìng)揚(yáng)伯屖父休,用作父乙寶尊彝簋。(御史競(jìng)簋西早《集成》8.4134)
(11)我先祖受天令(命),商(賞)宅受或(國(guó))。(秦公鐘 春早《集成》1.126)
(二)二類賞賜動(dòng)詞的整理
1.休
楊樹達(dá)認(rèn)為:“休字蓋賜予之義,然經(jīng)傳未見此訓(xùn),蓋假為好字也。”[4]83楊氏認(rèn)為“休”作賜予之義是假借“好”字為之。陳初生先生從楊氏說(shuō)[5]624。甲骨文中“休”從亻、從木,金文與甲骨文字形相同,只是有些字木形突出樹冠,因此學(xué)者們認(rèn)為休字從亻從禾[6]985-989。《說(shuō)文·木部》的“休”或體作“庥”,累增意符“廣”變?yōu)樾温曌帧M怀鋈嗽谘隗w之下,獲得庇護(hù)。休字古文字形表示人在樹蔭之下,納涼、避雨等行為,引申為獲得益處、好處。金文中,休有名詞性,作賞賜之物;用作形容詞,表示美好的;用作動(dòng)詞,就是賞賜義。這樣看來(lái),“休”本來(lái)就有“賜予”義,不必假借“好”字為之。例如:
(14)王侃太保,賜休余土。(太保簋 西早《集成》8.4140)
(17)辛宮易(賜)舍父帛、金,揚(yáng)辛宮休,用乍(作)寶鼎,子子孫孫其永寶。(舍父鼎 西早《集成》2629)
(18)拜稽首,對(duì)揚(yáng)天君休。(公姞鬲 西中《集成》3.753)
(19)柞拜手,對(duì)揚(yáng)中(仲)大師休。(柞鐘 西晚《集成》1.138)
(20)弗敢不對(duì)揚(yáng)朕辟皇君之易(賜)休命。(叔尸镈 春晚《集成》285.3)
例(12)(13)中的“休”用作動(dòng)詞,為賞賜義。“休”后用于引介賓語(yǔ)。例(14)(15)“休”與“賜”同義,連用組成“休賜”“賜休”,表示賞賜義。例(16)“休”與也是同義連用,表示賞賜義。殷周金文中的“休”還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賞賜環(huán)節(jié)之后,受賜者對(duì)賞賜者的答謝頌揚(yáng)之辭中,經(jīng)常與“揚(yáng)/對(duì)揚(yáng)”組成“揚(yáng)/對(duì)揚(yáng)……休”的句式。“休”為名詞,賞賜、恩惠義。這種形式最早見于西周早期,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時(shí)期。如上揭例(17)-(20)。
2.釐
3.令
《說(shuō)文·卩部》:“令,發(fā)號(hào)也。從亼、卩。”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皆與之同構(gòu)。《說(shuō)文·口部》:“命,使也。從口,從令。”“命”乃“令”之分化字。林義光曰:“諸彝器令、命通用,蓋本同字。”殷商甲骨文及西周初期金文中有“令”無(wú)“命”,西周中期始見從“令”加“口”之“命”字。除了人名用字外,二者的用法完全相同,分化為異詞異字,乃后來(lái)之事。洪家義先生認(rèn)為:初有令,后有命,而兩個(gè)字音義皆同;分化的原因是源于上古復(fù)輔音ml,分化為m與l[7]122-126。例如:
(26)楷伯于遘王,休無(wú)尤。楷伯令厥臣獻(xiàn)金、車。(獻(xiàn)簋 西早《集成》8.4205)
(27)隹(唯)八月初吉庚午,王令燮在(緇)市、旅(旂),對(duì)揚(yáng)王休用作宮仲念器。(燮簋 西中《集成》7.4046)
例(26)為西周早期金文,文中用“令”表示賞賜義,獻(xiàn)為人名,此句為雙賓句式。郭沫若認(rèn)為“金當(dāng)是天子所錫,車當(dāng)是楷伯所錫”[8]45。例(27)為西周中期金文,文中也用“令”表示賞賜義。從主題分類上看,例(27)是典型的賞賜類銘文。例(28)為西周晚期金文,文中用“令”和“”同義連用共同表示賞賜義。“令”作賞賜義的使用頻率雖然不高,但這種用法貫穿整個(gè)西周金文。
4.命
(29)王呼命汝赤巿、朱黃、玄衣黹屯、鑾旂。(即簋 西中《集成》8.4250)
(31)內(nèi)史尹氏冊(cè)命楚:雍巿、鑾旂。(楚簋 西晚《集成》8.4246)
“命”作賞賜義是從西周中期開始出現(xiàn)的。例(29)用“命”表示賞賜義。即簋銘是一篇典型的賞賜類銘文,涉及到了賞賜的儀式和儀節(jié)等內(nèi)容。例(30)作為賞賜義的“命”在康鼎原拓片中有些模糊,看似好像“令”,其實(shí)對(duì)照上句中的“命”字可以看出,應(yīng)為“命”字。例(31)為西周晚期冊(cè)命金文,與典型的冊(cè)命金文不同,一般冊(cè)命金文中“冊(cè)命”一詞之后應(yīng)出現(xiàn)“受命者+官名”。可是楚簋銘文較為特殊,后面接著是賞賜的服飾。西周晚期師察簋(《集成》8.4253)銘與例(31)銘文類似:“王乎尹氏冊(cè)命師察:賜女(汝)赤舄、攸(鋚)勒”。但師察簋銘文“冊(cè)命師察”后出現(xiàn)了動(dòng)詞“賜”,文意顯豁。所以,例(31)中的“命”可能有兩種解釋,一是表冊(cè)命義,二是表賞賜義。我們暫時(shí)作賞賜義解。
5.舍
“舍”常出現(xiàn)在交易活動(dòng)的金文中,表“施舍”“給予”義,作謂語(yǔ)。例如,五祀衛(wèi)鼎、九年衛(wèi)鼎、曶鼎、散氏盤銘中的“舍”,為一般性“給予”“付予”義。但在非交易的金文辭中,特別是出現(xiàn)在上對(duì)下的“給予”中,就是賞賜義。“舍”作施舍、賞賜義,后來(lái)寫作“捨”,現(xiàn)又簡(jiǎn)化為“舍”。例如:
(32)王曰:令眔奮,乃克至,余其舍汝臣十家。(令鼎 西早《集成》5.2803)
(34)內(nèi)(芮)公舍霸馬兩,玉、金,用鑄簋。(霸簋 西中《銘圖》9,355,04609)
(35)賓出,白(伯)遺賓于郊,或(又)舍賓馬。(霸伯盂 西中《銘圖》13,457,06229)
例(32)令鼎銘文敘述了一場(chǎng)駕馭比賽,周王對(duì)令和奮許諾,如果你們能夠按要求到達(dá)目的地,就賞賜給奴隸十家。令按要求完成了任務(wù),最終得到了周王的賞賜。“舍”為賞賜義。例(33)-(35)中的“舍”也都是賞賜義。這個(gè)詞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的銘文里。
6.兄
殷周金文中作賜予義的“兄”,后世文獻(xiàn)寫作“貺”。《爾雅·釋詁》:“貺,賜也。”《說(shuō)文·新附》:“貺,賜也。”《詩(shī)經(jīng)·小雅·彤弓》:“我有嘉賓,中心貺之。”例如:
(37)令作冊(cè)折兄(貺)圣土于相侯,賜金,賜臣。(作冊(cè)折觥 西早《集成》15.9303)
例(36)為殷商晚期銘文,例(37)為西周早期銘文,銘辭中都出現(xiàn)了動(dòng)詞“兄(貺)”,用為賞賜義。例(38)“兄(貺)”“畀”同義連用,均為賞賜義。“兄”通“貺”,在殷周金文中作賞賜義出現(xiàn)了15次,西周晚期銘文中沒有見到這種用法。
8.賓
金文中“賓”作為覲禮中的賓賜行為,有饋贈(zèng)義。孫詒讓曰:“(金文)賓即禮經(jīng)之儐也。《覲禮》郊勞、賜捨,侯氏皆用束帛、乘馬儐使者。”[12]32例如:
(46)王在宗周,令史頌省穌□里……穌賓璋、馬四匹、吉金。(史頌簋 西晚《集成》8.4231)
上揭例句中的“賓”均為饋贈(zèng)義,都是受聘者對(duì)使者回饋之禮。例(43)銘辭大意是王姜派作冊(cè)安撫夷伯,夷伯賓賜了作冊(cè)貝和布。夷的族姓,據(jù)唐蘭研究為姜姓[13]308。周王的姜姓王后派人慰問自己的母國(guó)。例(44)銘辭大意是公派繁表?yè)P(yáng)了伯,伯也勉勵(lì)了繁,并賓賜給繁柀和貝。銘辭中“伐”為夸美之義[14]69-71。例(45)銘辭大意是師黃饋贈(zèng)了玉璋一個(gè)、馬兩匹。例(46)銘辭大意是周王在宗周,命令史頌聘問穌……穌饋贈(zèng)史頌玉璋、馬四匹和青銅。
(三)三類賞賜動(dòng)詞的整理
1.益
益既引申為增益,故再引申為錫予,錫予即是使無(wú)者有之,有者多之,但由益()而易()的變化,如無(wú)德器出現(xiàn),三千多年來(lái)已失傳,無(wú)人知道它們本是一個(gè)字,這是漢字由繁而簡(jiǎn)的一種過(guò)程。
嚴(yán)一萍、張光裕二先生均認(rèn)為德器的“益”與“易”不是繁簡(jiǎn)關(guān)系,而只是一種同音假借[17]5873-5877[18]53-56。可備一說(shuō)。例如:
(47)王益德貝廿朋,用作寶尊彝。(德鼎 西早《集成》4.2405)
(49)唯王正月初吉,辰在壬寅,夷伯夷于西宮,嗌貝十朋。敢對(duì)揚(yáng)王休,用作尹姞寶簋,子子孫孫永寶用。(夷伯簋 西中《近出》2.481)
上揭例(47)(48)用“益”表賜。金文常用來(lái)表示賞賜義的“易”為“益”的簡(jiǎn)化形體字,“益”是形體完整字。“易”字甲骨文作、、等形,與金文字形相近,應(yīng)是的截省。金文中表示賞賜義的還寫作“嗌”。例(49)用的是“嗌”表“賜”,為假借用法。戰(zhàn)國(guó)楚簡(jiǎn)文字中“益”常寫作“嗌”,也為假借。例如,上博簡(jiǎn)《容成氏》:“禹於是乎讓嗌(益),啟於是乎攻嗌(益)自取。”[19]276《詩(shī)經(jīng)·維天之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以往訓(xùn)釋此句中“溢”字為“慎”“恤”等義[20]936[21]476,很是牽強(qiáng)。這里“溢”應(yīng)為借字,假作“益”,為賞賜義[22]293。
2.畀
(50)王則畀柞伯赤金十鈑。(柞伯簋 西早《近出》2.486)
(51)賜畀師永厥田陰陽(yáng)洛疆眔師俗父田。(永盂 西中《集成》16.10322)
金文也用“畀”表示賞賜義。例(50)單用“畀”表示賞賜義。例(51)“賜畀”同義連用,表示賞賜義。
4.儕
殷周金文中作“給予”講的“儕”,后世文獻(xiàn)皆作“齎”。儕,上古崇紐脂部,齎,上古精紐脂部。精、崇同為齒音,脂部疊韻。音理可通。《說(shuō)文·貝部》:“齎,持遺也。”徐鍇《說(shuō)文解字系傳》:“持以遺人也。”這里的“遺”為贈(zèng)送義。《廣雅·釋詁》:“齎,送也。”這個(gè)詞主要出現(xiàn)在西周晚期。上對(duì)下的“給予”就應(yīng)為“賞賜”。例如:
(53)侯賜者臣二百家,劑用王乘車馬、金勒、冖衣、市、舄。(麥方尊 西早《集成》11.6015)
(54)唯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王曰:令女(汝)羞追于齊。儕(齎)女(汝)母五易(錫)登盾生皇(凰)。(五年師簋 西晚《集成》8.4218)
(55)王親儕(齎)晉侯穌矩鬯一卣,弓、矢百,馬四匹。(晉侯穌鐘 西晚《近出》1.45)
例(53)中假借“劑”為“齎”,為贈(zèng)送義。例(54)(55)主詞都是周王,接受賞賜者為其臣屬師與晉侯穌,因此銘辭中的“儕(齎)”均為賞賜義。
5.付
殷周金文中“付”,經(jīng)常表示“給予”義,但是上對(duì)下的“給予”就應(yīng)為“恩賜”義。例如:
(56)妊氏令螨事保厥家,因付厥且(祖)仆二家。(螨鼎 西中《集成》5.2765)
(57)肆天子弗望(忘)厥孫子,付厥尚官。(虎簋蓋 西中《集錄》2.491)
例(56)依據(jù)殷周金文的文例,此處的“付”應(yīng)當(dāng)解作賞賜義。螨鼎銘接著敘述就是受賜者的答謝之辭“螨拜稽首”,這正符合賞賜銘文的文例。例(57)為1996年陜西丹鳳縣發(fā)現(xiàn)的虎簋蓋銘文中的文辭,“付厥尚官”中的“付”應(yīng)為賞賜義,這里的“尚”一般認(rèn)為通作“常”[23]81-83,“付厥尚官”就是賜予常官。另外,金文中“付”,經(jīng)常作“付與”“給予”義。例如:
(58)邦君厲眔付裘衛(wèi)田。(五祀衛(wèi)鼎 西中《集成》5.2832)
(59)我既付散氏田器。(散氏盤 西晚《集成》16.10176)
6.歸
殷周金文中作“贈(zèng)送”義講的“歸”字,一般認(rèn)為通“饋”,其實(shí)應(yīng)為“歸”的引申義。《廣雅·釋言》:“歸,返也。”引申為一般的“贈(zèng)送”,如果是上對(duì)下的贈(zèng)送,就是賞賜義。例如:
(60)王令士道歸貉子鹿三。(貉子卣 西早《集成》10.5409)
(61)中乎歸生鳳于王。(中方鼎 西中《集成》5.2751)
殷周金文中“歸”作饋贈(zèng)、賞賜義出現(xiàn)約7次,都出現(xiàn)在西周早期和中期銘文里,西周晚期銘文中沒有見到這種用法。如上揭例(60)-(62)。
7.畮
(63)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吊(叔)初見于衛(wèi),賢從,公命事,畮(賄)賢百畮糧。(賢簋 西中《集成》7.4104)
(64)淮尸(夷)舊我帛畮(賄)人,母(毋)敢不出其帛,其積,其進(jìn)人。(兮甲盤 西晚《集成》16.10174)
郭沫若在論及賢簋銘中“畮”字時(shí),曰:“上畮字是動(dòng)詞,蓋叚為賄,猶賜也,予也。賄古文作(《一切經(jīng)音義》四),正從每聲。”[8]225例(63)“畮”作謂語(yǔ),“賜予”義。另外,“畮”在金文中常作定語(yǔ),表示“貢納錢財(cái)?shù)摹保@種用法的“畮”往往是臣對(duì)君、下對(duì)上的一種貢納制度。如上揭例(64)。“畮”通“賄”,作賄贈(zèng)、賜予義,在殷周金文中出現(xiàn)約3次,都出現(xiàn)在西周中晚期的銘文里,西周早期銘文中沒有見到這種用法。
8.受
(67)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商(賞)宅受(授)或(國(guó))。(秦公鐘 春秋《集成》1.262)
金文“受”作授予、賜予義,后世文獻(xiàn)上寫作“授”。例(65)中的“受”出現(xiàn)在賞賜物品前,直接賓語(yǔ)都是“貝”等物品,“受”的賞賜意義非常明顯。例(66)中“受”與“”同義連用,“受”表示賞賜義。例(67)中“商(賞)宅受(授)或(國(guó))”主語(yǔ)顯然是天,“商(賞)”與“受(授)”意義相近,都為賞賜義。
10.友
(69)應(yīng)侯視工友賜玉五瑴、馬四匹、矢三千。(應(yīng)侯視工簋 西中《新收》78)
例(69)“友”通“賄”,作賄贈(zèng)、賜予義。銘文中“友”與“賜”同義連用。“友”金文中也有用作一般“付給”義。郭沫若認(rèn)為例(70)中“友”讀為“賄”,為“還付”義[8]125。可備一說(shuō)。
11.叀
12.褱
關(guān)于例(73)中的“褱”,裘錫圭先生認(rèn)為:“‘褱’,讀為‘懷’。《詩(shī)·檜風(fēng)·匪風(fēng)》:‘懷之好音’,毛傳:‘懷,歸也’,就是給予的意思。”[9]17此句中的“受”與“褱”同義連用,也應(yīng)為“授予”義。例(74)同為微氏家族青銅器銘,“褱”的用法與例(73)相同。
13.贛
(75)王贛祼玉三品、貝廿朋。(鮮簋 西中《集成》16.10166)
例(75)中的“贛”,依據(jù)辭例應(yīng)為“賞賜”義[25]8-19。李學(xué)勤先生認(rèn)為此字從“章”,“章”“商”音通,作“賞”解[26]285。
14.分
(76)己侯貉子分己姜寶。(己侯貉子簋 西中《集成》7.3977)
馬承源注曰:“分,與或予。”[27]245例(76)中的“分”在此應(yīng)為分賜義。
16.稟
(78)使厥友妻農(nóng),廼稟厥帑,厥小子。(農(nóng)卣西中《集成》10.5424)
例(78)中的“稟”也寫作“廩”,楊樹達(dá)釋為“廩給”義[4]126,張 世超 等 學(xué) 者 認(rèn) 為是 授 給、供 給義[29]1394。銘辭中的“稟”在這里應(yīng)為贈(zèng)送義。
17.曾
金文中的“曾”多用作增加義,后寫作“增”;也用作賜予義,后寫作“贈(zèng)”。我們認(rèn)為“增”“贈(zèng)”應(yīng)為“曾”的后起分化字。
(79)青公使司史盾曾匍于柬(館):麀賁、韋兩、赤金一勻(鈞)(匍盉 西早《集錄》943)
(80)戊辰,曾。王蔑段歷。(段簋 西中《集成》8.4208)
例(79)(80)中的“曾”為賞賜義,后世文獻(xiàn)寫作“贈(zèng)”。關(guān)于例(80)中的“曾”,郭沫若認(rèn)為:“曾,殆贈(zèng)之省文。”[8]50這大概是有問題的。
18.以
裘錫圭先生認(rèn)為甲骨文中的“以”常用作“攜帶”“帶領(lǐng)”義,有時(shí)也作“致送”義[2]179-184。西周金文也沿襲了“率領(lǐng)”“致送”這一意義,“以”又由“致送”義引申為“賜予”義。
(81)王乎殷厥士,爵叔夨,以尚(裳)、車、馬、貝卅朋。(叔夨方鼎 西早《銘圖》5,234,02419)
例(81)“以”字所處位置正是賞賜類動(dòng)詞“賞”“賜”常出現(xiàn)的地方,作賞賜義無(wú)疑。例句中“殷”左安民先生釋為“正定”義,“爵”吳振武先生釋為“封爵”義[29]46。銘辭大意是周王招呼正定貴族名分,封爵叔夨,并賞賜輿服、車馬和三十朋貝。
(82)辛乍(作)寶,其亡(無(wú))彊(疆),氒(厥)家雝德,用氒(厥)□多友,多友釐辛,萬(wàn)年隹(唯)人(仁)。(辛鼎 西早《集成》5.2660)
20.加
《說(shuō)文·力部》:“加,語(yǔ)相增加也。”“加”由語(yǔ)相加,引申為物相加,自然引申出授予、施恩義。
例(84)中“加”為動(dòng)詞賞賜義。“加”作動(dòng)詞還出現(xiàn)在西周晚期青銅器虢季子白盤(《集成》16.10173)銘中,“王孔加子白義(儀)”,一般都認(rèn)為此銘中“加”通“嘉”。實(shí)際上,“加”本為語(yǔ)相加,自然引出贊美、表彰義。
三、結(jié)語(yǔ)
殷周賞賜類銘文數(shù)量眾多,內(nèi)容豐富,是研究殷周特別是西周賞賜制度的最詳實(shí)的材料。對(duì)這類材料的整理應(yīng)從其核心詞語(yǔ)的意義和功能開始,動(dòng)詞正是研究金文各類主題的重點(diǎn)與焦點(diǎn),所以對(duì)動(dòng)詞的梳理是研究金文主題的基礎(chǔ)與標(biāo)尺。在這里,我們只是對(duì)殷周金文賞賜類動(dòng)詞進(jìn)行了分類梳理,目的就是初步建立起金文主題分類的依據(jù)。從整體上來(lái)說(shuō),金文中出現(xiàn)了這類詞語(yǔ),我們就可以判定其為賞賜類銘文。但是由于金文流行時(shí)間較長(zhǎng),從商代晚期一直到戰(zhàn)國(guó)晚期。流行地域較廣,從燕趙大地一直到江漢流域。加之殷周時(shí)期正是金文從發(fā)展到成熟的階段,早中晚期的銘文內(nèi)容與形式都存在著很大的變化,所以即使是主題相同的銘文也會(huì)出現(xiàn)不同的文體要素。同為賞賜類動(dòng)詞,詞義之間也會(huì)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即使同一個(gè)動(dòng)詞,前后期也存在意義與功能上的變化。例如,就使用率最高的一類賞賜動(dòng)詞“賞”與“賜”來(lái)說(shuō),其使用頻率上、位置分布上、語(yǔ)法功能上也不盡相同[31]48-51。作賞賜義的“賜”,從殷商晚期到春秋晚期每一個(gè)階段都在使用,出現(xiàn)的頻率也最高,大致出現(xiàn)600多次。“賜”在金文中作謂語(yǔ),一般帶有雙賓語(yǔ)。直接賓語(yǔ)為物品,間接賓語(yǔ)為受賞者。作賞賜義的“賞(商)”,從商代晚期一直到春秋晚期也都出現(xiàn)過(guò),但主要流行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大致出現(xiàn)了90多次。“賞(商)”在金文中作謂語(yǔ),可以帶雙賓語(yǔ),也經(jīng)常帶單賓語(yǔ),也可以用介詞“于”引介賓語(yǔ)。賞賜類動(dòng)詞所帶賓語(yǔ)多為人和物,也有較為抽象的事物。例如,作賞賜義的“褱”,常出現(xiàn)在祝嘏辭中,所帶賓語(yǔ)也多為壽福之類的內(nèi)容。
殷周時(shí)期特別是西周時(shí)期賞賜類銘文如此之多,反映了賞賜制度的盛行,它業(yè)已成為維系西周社會(huì)運(yùn)行的機(jī)制,再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政治制度與禮儀制度。通過(guò)對(duì)殷周金文賞賜類動(dòng)詞的整理與研究,為我們進(jìn)一步了解金文所反映的主題思想和社會(huì)制度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與參考。
收稿日期 2021-12-14
[責(zé)任編輯 韋楊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