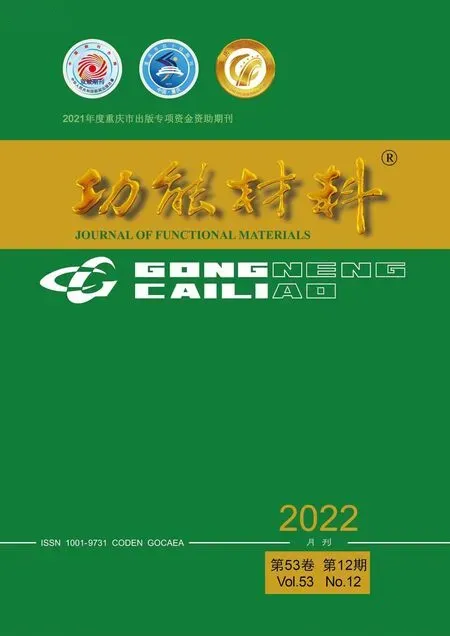Fe-Si合金磁性能和力學性能的第一性原理計算*
王 婷,楊吉春,劉香軍,楊昌橋
(內蒙古科技大學 材料與冶金學院,內蒙古 包頭 014010)
0 引 言
Fe-Si合金(硅鋼)具有高磁導率,低矯頑力,高電阻率,低鐵損等一系列優秀的軟磁材料性能,是制造高頻電氣設備、節能變壓器和電動汽車的理想軟磁材料[1]。Si的摻雜可以使bcc-Fe結構更穩定,有利于提高其他合金元素在bcc-Fe中的均勻性[2];Fe-Si合金的Si含量提高合金的軟磁性能(包括高電阻率、高磁導率、低磁晶各向異性和接近零的磁致伸縮系數)[3]的同時使合金塑性變形性能顯著下降,在室溫下的延展性隨著Si含量的增加而降低[4-5];這種現象阻礙了Fe-Si合金工業應用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研究硅鋼磁性能與力學性能的行為、機理及根源有助于開發、使用硅鋼。
Fe-Si合金具有優異的軟磁性能與它的微觀結構密不可分。胡玉平等[6]計算了Fe-Si體系的磁性,得出Si置換α-Fe超晶格頂角處Fe原子得到的體系比取代體心位置Fe原子的體系磁性要好。Choi等[7]與Saengdeejing等[8]計算了隨著Si含量的升高,出現B2與DO3有序相增多,是硅鋼力學性能降低的主要原因。戶秀萍[9]計算了Si對α-Fe的結構穩定性和力學性能,并給出了相應的解釋。但是這些計算只是單一的給出了Fe-Si合金的磁性能或力學性能,并沒有綜合闡述磁性能與力學性能的微觀作用機理。
Si作為提高合金磁性的重要合金元素,其磁性作用的原子層次尚缺乏系統的研究,因此從微觀水平探索Si固溶于α-Fe中磁性能與力學性能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采用第一性原理的方法計算了Si置換α-Fe頂角位置的Fe原子時體系的磁性能及力學性能,從微觀層次解釋了Si的摻雜對α-Fe磁性能與力學性能的影響機理。
1 計算方法與模型
本文采用基于密度泛函理論(Density Function Theory, DFT)的VASP(Vienna ab initio simulation package)軟件包計算Fe-Si體系的磁性能、力學性能與電子結構。電子間的交換關聯相互作用采用廣義梯度近似GGA(Generalized gradient approximation)[10-11]中的PBE (Perdew-Burke- Ernzerh)泛函方法,通過對平面波截止能和MP-k(Monhkorst-Pack)[12-13]網格大小的優化,平面波截止能為450 eV,布里淵區的積分計算使用4×4×4的MP-k(Monkhorst-Pack)型的k網格。自洽循環能量收斂設為1.0×10-6eV/atom,力收斂為0.2 eV/nm。計算中Fe、Si原子的價電子分別采用Fe(4s23d6)、Si(3s23p2)。
α-Fe為體心立方結構,屬于立方晶系,空間點群為Im-3m,晶格常數為a=b=c=0.2866 nm[14]。本文以α-Fe為初始模型建立了2×2×2的晶胞模型,Si原子取代晶胞中的頂角位置,如圖1(a)所示。本文根據Fe原子與Si原子的距離考慮了2種Fe原子的位置,如圖1(b)所示,Fe1與Si原子距離最近,位于體心位置;Fe2與Si原子次臨近,位于棱線位置;對α-Fe晶胞進行優化計算得到晶格常數a=0.2831 nm,體積模量B=159.04 GPa,Fe原子的磁矩為2.24μB,表1為前人計算和實驗的計算結果,本次的計算結果與前人的計算結果基本一致,說明本次的計算方法合理可靠。

圖1 (a)Fe-Si晶胞模型,(b)Fe-Si(010)截面示意圖Fig.1 (a) Cell model and (b) the (100) plane cross-sectional schematic of Fe-Si

表1 α-Fe平衡晶格常數a、體積模量B、磁矩M.
2 結果與討論
2.1 Fe-Si體系的穩定性
為研究Fe-Si體系的穩定性,本文計算了體系的溶解能Esol和結合能E0,Fe-Si體系的溶解能和結合能用以下公式計算[18]:
(1)
(2)
式中:Etot代表晶體的總能量,eV;E(Fe)、E(Si)組成晶體的原子處于自由狀態時的總能量,eV;n為Fe超胞中Fe原子數。

表2 純Fe及Fe-Si體系的溶解能(Esol)和結合能(E0)
溶解能用來表示摻雜元素在鋼中固溶的難易程度,當溶解能為負值,表示摻雜體系可以穩定存在;Fe-Si體系的溶解能和結合能的計算結果如表2所示,Fe-Si體系的溶解能為負值,說明Fe-Si體系可以穩定存在。體系的結合能越小,原子間的結合能越強,體系越穩定。Si的摻雜降低晶胞的結合能,使得晶胞更穩定,說明Fe-Si體系的穩定性要大于純Fe體系。
2.2 磁性能
由表3可知,處于不同位置的Fe原子的磁矩不同,Si原子的磁矩與Fe原子反平行排列,Si原子的磁矩-0.09μB,并且Fe2原子的磁矩大于Fe1原子的磁矩,這是由于Fe1-Si的鍵長小于Fe2-Si的原因[19-20]。

表3 摻雜體系中的Fe-Si鍵長,各原子Fe原子磁矩及體系的總磁矩.
材料中原子的內交換作用會使原子的磁矩增大,而原子間的共價雜化作用會使原子的磁矩減小[21]。與純Fe體系中的Fe原子相比,Fe1原子的磁矩小于純Fe體系中Fe原子的磁矩,Fe2原子的磁矩大于純Fe體系中Fe原子的磁矩,這可能是由于Fe1位置Fe原子的內交換作用小于Fe-Si鍵的共價雜化作用,Fe2位置的Fe原子的內交換作用大于Fe-Si鍵的共價雜化作用導致的。
由表3可知,Fe-Si體系的總磁矩小于純Fe體系,故Fe-Si體系有較低的磁致伸縮系數[22];低的磁致伸縮系數可以提高磁導率和降低矯頑力,這些都是軟磁材料的基本特征。
2.3 力學性能
摻雜體系的力學性能可以根據所得的彈性常數進行計算。α-Fe屬于立方晶系,由于存在對稱關系,具有3個獨立的彈性常數C11,C12,C44。晶格的力學穩定性可由Born-Huang判斷[23-24]進行判斷,需滿足式(3)晶體才能穩定存在。
C11>0, C44>0, C11>C12, C11+2C12>0
(3)
純Fe及Fe-Si體系的彈性常數計算結果見表4,將彈性常數帶入式(3)進行驗證,結果表明所有摻雜體系都滿足Born-Huang力學穩定性判據,因此摻雜體系均滿足彈性穩定機制,晶體結構穩定,這與溶解能的分析結果一致。

表4 純Fe及Fe-Si體系的彈性常數(GPa)
根據計算出的獨立彈性常數,通過Voigt-Reuss-Hill[25]近似,可以計算出摻雜體系的體積模量B、剪切模量G和彈性模量E、泊松比σ,預測材料的維氏硬度Hv[26]和可加工指數μM[27],計算公式如式(4)~(12):
(4)
(5)
(6)
(7)
(8)
(9)
(10)
HV=2(k2G)0.585-3,(k=G/B)
(11)
(12)
式中:B和G的下標H、V和R分別代表Hill、Voigt和Reuss近似。
圖2(a)為純Fe及Fe-Si體系的彈性模量與維氏硬度,Si摻雜后,降低了純Fe體系的B值(從159.04減小到153.13 GPa),Si提高了體系的G值(從77.31提高到80.09 GPa)與E值(從199.58 GPa提高到204.29 GPa),即Si降低了摻雜體系的不可壓縮性,提高了摻雜體系抗剪切形變的能力和剛度;Si摻雜后,體系的維氏硬度值增加(從7.94 GPa增加到9.17 GPa),即Si提高了純Fe體系的硬度。泊松比與Plug比(B/G)可用來反應材料的韌性和脆性,泊松比和Plug比(B/G)越大,材料的韌性越好,可加工指數(μM)評估金屬材料的可加工性,可加工指數越大,金屬材料越容易加工。由圖2(b)所示,Si摻雜后,體系的泊松比σ和B/G值均下降,即Si的摻雜降低了體系的韌性,體系的可加工指數μM降低,即Si的摻雜降低了體系的可加工性能。

圖2 (a)純Fe及Fe-Si體系的彈性模量與維氏硬度, (b) 純Fe及Fe-Si體系的Plug比、泊松比、可加工指數Fig.2 (a) Elastic modulus and Vickers hardness of pure Fe-Si and Fe-Fe systems, and (b) Plug ratio, Poisson’s ratio, and machinability index of pure Fe and Fe-Si systems
2.4 幾何結構
由圖3可知,Si摻雜后,晶胞結構不變仍然是bcc結構,Fe-Si體系的晶格常數a=b=c=2.830 nm,晶胞體積為22.66×10-3nm3,小于純Fe體系晶格常數2.833 nm與晶胞體積(22.69×10-3nm3),這是由于Si原子的原子半徑小于Fe原子引起點陣收縮所致。晶格常數的變化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體系磁性的變化,晶格常數減小,晶格畸變量增加,體系的宏觀磁性得到改善[6],所以Fe-Si體系的宏觀磁性要大于純Fe體系。

圖3 結構優化后(100)晶面上的結構示意圖:(a) Fe; (b) Fe-SiFig.3 The (100) plane cross-sectional schematic after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 Fe; (b) Fe-Si
由圖3可知,Si摻雜后,晶胞結構不變仍然是bcc結構,Fe-Si體系的晶格常數a=b=c=0.2830nm,晶胞體積為0.02266 nm3,小于純Fe體系晶格常數(0.2833nm)與晶胞體積(0.02269nm3),這是由于Si原子的原子半徑小于Fe原子引起點陣收縮所致。晶格常數的變化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體系磁性的變化,晶格常數減小,晶格畸變量增加,體系的宏觀磁性得到改善[6],所以Fe-Si體系的宏觀磁性要大于純Fe體系。由圖3可知,Fe-Si體系中的Fe-Fe鍵長小于純Fe體系中的Fe-Fe鍵長,使得Fe-Si體系中Fe原子磁矩的局域性更強,這也是Fe-Si體系的居里溫度小于純Fe體系的根本原因。
Fe-Si體系中既有Fe-Fe鍵,又有Fe-Si鍵,其平均鍵長為0.25453 nm,純Fe體系中只有Fe-Fe鍵,平均鍵長為0.26416 nm,即Si的摻雜使得體系的平均鍵長減小,由鍵長越短鍵能越強理論可知,Fe-Si體系中的金屬鍵強度大于純Fe體系,這也是Fe-Si體系的維氏硬度Hv大于純Fe體系的根本原因。
Fe-Si體系中,Fe-Si鍵的鍵長為0.24511 nm遠小于Fe原子與Si原子的原子半徑之和(0.172 nm+0.146 nm=0.318 nm),說明Si可以促進α-Fe穩定,這與結合能的計算結果一致。
2.5 電子結構
2.5.1 態密度
圖4顯示了純Fe和Fe-Si體系的總態密度(TDOS)和分波態密度(PDOS),圖中虛線表示費米能級。從圖中可以看出,在費米能級附近的PDOS均不為0,說明體系中存在金屬鍵。從圖4(a)中可以看出,純Fe體系的能量區間為-10~10 eV,在費米能級附近的態密度主要由Fe d 軌道電子提供;在整個純Fe體系中,Fe s和Fe p軌道都貢獻的很小,可以清楚地觀察到純Fe體系的磁性主要來自于Fe d軌道。

圖4 純Fe及Fe-Si體系的TDOS和PDOS圖Fig.4 The TDOS and PDOS of pure Fe and Fe-Si
從圖4(b)中可以看出,Fe-Si體系的能量區間為-10~9 eV,在費米能級附近的態密度主要由Fe d 軌道電子提供;在-10.0~-9.1 eV區間內的磁性主要由Si s軌道貢獻,在-7.2~-1.5 eV區間內的磁性主要由Fe d和Si p軌道雜化貢獻,在此區間內Fe與Si之間有較強的相互作用;可以清楚地觀察到Fe-Si體系的磁性主要來自于Fe d軌道和Si p軌道雜化貢獻,這使得Fe-Si之間成鍵有較強的方向性,從而使得Fe-Si體系的韌性減小。

圖5 純Fe及Fe-Si體系的DOS對比圖Fig.5 Comparison of DOS for pure Fe and Fe-Si systems
圖5為純Fe和Fe-Si體系的總態密度對比圖。從圖中可以看出,Fe及Fe-Si體系的上下兩部分的DOS都不對稱,說明Fe、Fe-Si體系都具有磁性;并且Fe-Si體系的不對稱性要強于純Fe體系,說明Fe-Si體系的宏觀磁性要大于純Fe體系,這與幾何結構的分析結果一致。Si的摻雜使得態密度的峰值整體左移,費米能級附近的態密度減小,說明Fe-Si體系的導電性要小于純Fe體系,故Fe-Si體系的電阻率要大于純Fe體系的電阻率[28-29]。
2.5.2 電荷密度
電荷密度圖可以更直觀的觀察原子間的相互作用。體系中標尺的電荷密度范圍為0~1.0×103e/nm3,由圖6(a)可知,純Fe體系中Fe原子間的相互作用是金屬鍵,圖6(b)可知,Si的摻雜引起了體系中電子的重新分布,Fe-Si之間是以共價鍵的方式連接,并且Si原子是被迫在與Fe原子相反的方向發生極化[30]。Si原子的電荷密度減小,Fe原子的電荷密度增大,且Fe-Si體系的電荷總密度大于純Fe體系,這是Fe-Si體系韌性減小的主要原因[31]

圖6 純Fe及Fe-Si體系的電荷密度圖Fig.6 Charge density of pure Fe (a) and Fe-Si system (b)
3 結 論
(1) 磁性能的計算結果表明,Fe-Si體系的總磁矩小于純Fe體系,使得Fe-Si體系有較低的磁致伸縮系數。Fe-Si體系晶格畸變量增加,Fe-Si體系的宏觀磁性得到改善;
(2) 力學性能的計算結果表明,Si的摻雜降低了體系的不可壓縮性,增大了體系的抗剪切應變的能力和剛度;與純Fe體系相比,Fe-Si體系的硬度增大,韌性減小,可加工應能降低。Fe-Si體系的平均鍵長小于純Fe體系的平均鍵長,鍵能增強,這是Fe-Si體系的硬度大于純Fe體系的根本原因;
(3) 電子結構的計算結果表明,純Fe體系的自旋磁矩主要由Fe 3d軌道電子貢獻,Fe-Si體系的自旋磁矩主要由Fe 3d 與Si 3p電子雜化貢獻,Fe-Si體系的費米能級左移,使得Fe-Si體系的電阻率增大,增強體系的軟磁性能,同時Fe-Si體系的電荷總密度大于純Fe體系,這是Fe-Si體系韌性減小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