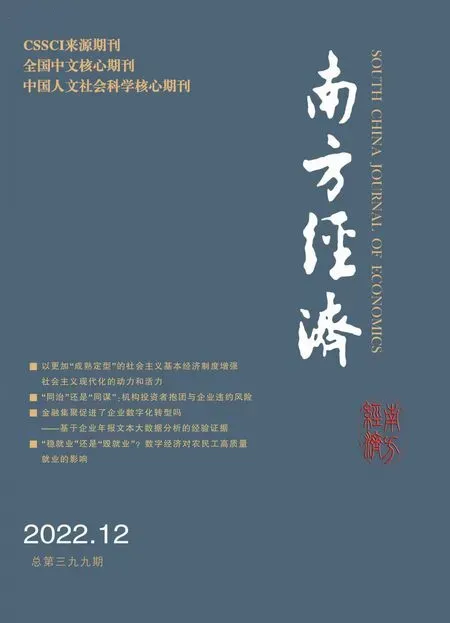金融集聚促進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嗎
——基于企業年報文本大數據分析的經驗證據
李華民 崔 皓 吳 非
一、引言
目前,人類社會正經歷自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后的新一輪以數字技術為引領的信息革命,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的數字經濟發展正步入快車道。根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顯示,在新冠肺炎疫情與國際經濟貿易不確定性的雙重疊加沖擊下,中國的數字經濟依然保持高位發展,2021年增速達9.7%,總規模達39.2萬億,占GDP比重達38.6%,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要“發展數字經濟,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這深刻反映出國家對數字經濟的高度重視。作為驅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愈發重要(陳文、吳贏,2021)。企業作為宏觀經濟中的經濟細胞,既是數字經濟發展所依托的核心載體,也是數字經濟浪潮中重要的推動者,國家層面也出臺了系列政策措施積極推動數字化轉型(圖1)。企業通過將數字技術與現有生產管理制度相互交融,不僅有效的提升了企業生產效率與核心競爭力,同時在宏觀層面也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實現在經濟新常態下的“彎道超車”。據此,針對中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實踐研究富有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圖1 國家政策對數字化轉型的支持脈絡梳理
如何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縱覽近代經濟史,凡是通過技術進步在國際競爭中獲得領先的國家(如美、英、德等國),它們的迅猛發展大多離不開金融的強大助力(Sylla,2002),Hicks(1969)更是斷言,“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在驅動經濟創新轉型上具有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2)《習近平:深化金融改革 促進經濟和金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jhsjk.people.cn/article/29407694.。確實,金融對變革性理念、技術等應用于企業發揮著關鍵作用(厲以寧等,2019)。現有研究將金融按服務實體經濟的方式進行界分,區別了以銀行部門為代表的間接金融和以資本市場為代表的直接金融。一方面,盡管銀行業機構在評估信息和處理高風險項目上存在劣勢(鐘騰、汪昌云,2017),但在當前階段中,通過前沿數字技術與銀行機構的深度融合,賦能銀行主動深度嵌入企業創新轉型鏈條(劉長庚等,2022;侯世英、宋良榮,2020),促進了企業全產業鏈創新升級。同時在利率政策、抵押物門檻等方面對企業創新活動給予特殊支持(Mann,2018),有力提升了企業創新活力。另一方面,資本市場的制度設計具有更強的價格發現功能(薛海燕等,2020),能夠更有效處理“風險—收益”平衡關系(辜勝阻、莊芹芹,2016),引導資金流向高風險高收益的創新項目中(何筠、李碧寒,2020)。不難發現,針對不同金融渠道促進企業創新轉型的研究已經較為豐富,但是金融市場是一個有機整體,孤立地考慮金融部門的部分子集對微觀結構主體的影響可能會出現一定遺漏偏差,特別是在當前金融發展關聯度集聚度越來越高,各類金融活動和資源在特定轄域內的邊界逐漸模糊的情形下,考察整體性金融集聚對微觀結構主體創新轉型的影響,具有高度的學理價值和實踐指導意義。
然而,目前以金融集聚為切入點對企業創新轉型進行深入研究的文獻相對較少,本文只能通過現有文獻的核心結論進行推定。一方面,有大量文獻認為金融集聚能夠激發轄域內的金融活躍度,為企業的創新轉型提供金融便利(Zhou,2022),有效緩解企業對創新轉型因資金不足而面臨的“想而不能”窘境(曲昳,2022)。由此,金融集聚對區域內企業的創新升級有著顯著的正向推動力(錢晶晶等,2021)。另一方面,有文獻認為金融集聚超過合理邊界后所形成的過度富余狀態,具有較為典型的壟斷特征(周天蕓等,2012),這會使得金融行業利潤率高于大多數實體企業,從而對企業產生融資擠出效應(陳雨露、馬勇,2012)。此外,金融集聚下所形成的過度聚合,會使得金融市場的波幅加劇,風險積蓄水平顯著提升,也不利于企業高質量發展(黎杰生、胡穎,2017;周天蕓等,2012)。不難發現,關于金融集聚對企業創新轉型升級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性結論。基于上述情況,本文希望通過創新的研究成果建立起“金融集聚—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的分析框架,為金融業更好地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探索出更多可能。
本文可能的創新之處在于:第一,在研究立意上,將提升中國區域金融發展質量與微觀結構主體之間建立起有機聯系,試圖分析出“金融集聚—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的關聯,從而將原有研究文獻聚焦于特定金融業態(銀行業、資本市場)對企業的研究,上升至整個金融業態集聚的影響上來,以期能夠豐富關于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相關文獻。第二,在研究思路上,基于金融功能視角,從信息、財務、創新三大路徑機制,解讀金融集聚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傳導路徑,為理解金融集聚的作用渠道提供了新的經驗和分析范式。第三,在研究內容上,重點突出了當前更加關注金融監管、強化金融規范發展的實踐需求和時代特色,在“金融集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范式中,創新性地引入了金融監管元素,考察在不同金融監管程度下,金融集聚所能發揮的效用是否存在差異,為當前金融監管層提供更為深入有效的政策建議導向指引。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研究表明,金融資源在一定空間內的集聚能形成高效供給的金融體系(于斌斌,2017;龔勤林、宋明蔚,2021)。具體來看,金融集聚強化了轄域內金融機構的競爭度,提高了區域內信息傳播的效率,為獲取更加優質的金融資源提供基礎,企業的預期也會隨著發展境遇的改善而得以優化,從而具備了更加積極主動的發展創新能動性。從這個角度來看,金融資源的有效集聚使得企業在金融市場融資時面臨著更小的外部阻力,能夠實現融資約束緩解與融資成本降低的雙重擬合,企業在推進創新轉型項目時往往有著更多的資源支撐。有鑒于此,本文從財務困境緩解、正向預期優化和創新活力激發三條路徑,論證“金融集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渠道機制路徑。
(一)財務困境緩解渠道
金融集聚能夠有效緩解企業融資約束,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奠定財務基礎。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中國企業在發展創新過程中所面臨的融資困境的具體表現,金融資源的富集能夠使得金融機構形成規模效應,提升區域內金融市場的資金運轉效率(劉降斌、劉秋明,2021),能夠通過網絡效應使得金融機構間信息互聯互通,有利于更加及時準確掌握企業融資需求,金融機構從資金供給側發力精準識別企業需求,有效拓展企業外部資金來源,分散企業轉型風險,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具體來看,第一,金融機構的高度集聚將有效改善區域內金融市場業態,使得區域金融市場更加完善與規范,同時能夠促進區域間合作加強(張玉華等, 2021),有利于資源合理配置,為企業營造良好的外部融資環境。同時金融資源的高度富集使得金融機構間的競爭加劇,使得金融機構主動創新金融工具,能夠針對企業自身現狀量身打造金融服務方案,有效提升金融服務效率(毛其淋、陳樂遠,2022;余振等,2012),使得企業能夠獲得與自身發展相適配的個性化融資支持。第二,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機構在區域中集聚能夠為企業帶來多渠道融資方式,同時提供豐富的金融產品與有競爭力的資金報價,有效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與融資門檻(胡璇,2022)。通過不同金融業態間的創新融合,可實現優勢互補,組合出符合企業數字化轉型特點的金融產品。企業數字化轉型難度大、轉型周期長,需要低成本資金的長效支持,豐富的個性化融資解決方案能夠為企業在數字化轉型時提供穩定的長期資金來源,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順利開展。
(二)正向預期優化渠道
金融集聚能夠有效改善企業預期,進而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營造良好的氛圍。金融機構在特定區域內的集聚,能夠有效提升金融機構間、企業間、金融機構與企業間的信息交流共享程度,降低信息獲取成本(Lall et al.,2004),信息不對稱性問題的減弱將引導資金流向透明度更高的企業(周鴻衛、劉子龍,2020)。特別是金融集聚在有效改善企業資源邊界約束的限制后,企業在豐富資源支撐下,對未來的發展將會有更積極的主觀能動性(周南南、林修宇,2020)。易言之,金融集聚形成的金融要素改善效果,提升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轄域內的企業在較好的金融資源支撐下會展現出更加正向積極的預期。應當說,這種預期改善會對企業的創新轉型決策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如果企業對自身未來的預期呈現出較為樂觀的態勢時,為了符合市場發展的預期,企業經營管理者往往會采取更具變革性的戰略措施(王永貴、汪淋淋,2021)推動企業更加關注創新轉型(Sung et al.,2019)。另一方面,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嵌入了前沿的數字技術,本身就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想要推動數字化轉型項目的開展,企業必須對創新轉型具有更高的“容忍度”和更大的接納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企業自身具有較強的積極預期時,將推動企業尋找全新的經濟增長點,優化企業的決策導向,為高風險的數字化轉型活動騰挪出更多“試錯空間”。
(三)創新活力激發渠道
金融集聚能有效促進企業科技創新,為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提供科技支撐。金融資源的集中帶來了資金、人才、技術、信息等企業創新所需的各種要素在特定范圍內的高度聚集,并加速要素間的相互融合,為企業營造出良好的科技創新氛圍,有助于迸發技術進步的活力,加速企業創新能力的躍升,進而賦能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具體而言,一方面,在金融集聚區中集中的大量技術型人才與先進技術通過知識溢出效應在區域內迅速擴散,使得金融集聚區作為科技與人才中心的優勢得以更為順暢地發揮出效果,為企業個體創新升級提供良好的環境,輻射帶動區域整體的知識水平躍升(耿德林,2020;王丹、葉蜀君,2015),提升企業研發推出新產品速度,進而直接促使企業創新能力躍升,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打下良好的科技基礎。另一方面,金融集聚使得區域內企業頭部效應更加凸顯,優勢資金將優先流向迅速采用先進生產技術的企業(金融資源的配置導向將以生產率或潛力最優為原則),進而倒逼企業轉型升級(余泳澤等,2013),激勵處于相對落后地區的企業加快創新轉型。
假設:金融集聚能夠有效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匯總了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2007—2019),并基于此為研究樣本展開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研究。本文對所得初始數據進行了如下處理,第一,剔除金融類企業;第二,剔除ST、*ST、PT及期間退市企業;第三,剔除企業在IPO當年的樣本;第四,為了保證所得樣本質量,只留存至少有連續五年完整核心數據的樣本;第五,為減少極端值對本文的影響,對本文中所有微觀層面的連續型(非比值)變量進行1%和99%的縮尾處理。本文的基本財務數據均選取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上市企業年報文本數據則源自巨潮資訊網。
(二)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
企業數字化轉型(LnDG)。本文認為,數字化轉型會對企業整體經營產生重大影響,是事關企業發展大局的重要抉擇,這種行為導向的轉變有著極大的可能會在企業的公開文本中(如企業年報)進行披露。因此,通過提取企業年報中的有關詞頻進行統計測度并以此來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強度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本文借鑒吳非等(2021)的做法,將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指標按照功能架構分為:“底層技術運用”和“技術實踐運用”兩個大類,其中,底層技術主要具體細分為“ABCD”技術,即人工智能(AI)、區塊鏈(BC)、云計算(CC)、大數據(DT)四類,有關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知識圖譜可參見圖2。利用Python與Java PDFbox 庫對滬深兩中A股全部上市公司年報的所有文本信息進行提取后進行歸納匯總,將匯總資料結果與企業數字化轉型關鍵詞進行對比匹配與頻數測度,基于此,建立用于衡量企業數字化轉型水平的原始指標。因所得數據右偏表現突出,本文對所測得數據進行了對數化處理。

圖2 企業數字化的“ABCD”底層技術與實踐運用圖譜
2.核心解釋變量
金融集聚(LPFA)。參考王文靜、劉詩琳(2020)、莊毓敏、儲青青(2021)的做法,從金融全業態集聚角度出發,借鑒傳統熵值法,以中國30個省級行政單位為統計對象,對其金融業發展數據進行爬取梳理,與區域金融中的三種主要業態相結合,從銀行、證券和保險三大行業中分別選取5類核心指標建構出全景式金融發展評價指標,最后運用區位熵形成最終的金融集聚變量。最終詳見圖3所示。考慮到當前金融部門發展具有很強的“省級分權”式管理模式,如銀行業市場,每個省份內的銀行機構都有省級分行指導和布局,具有明顯的“一盤棋”式集中統籌管理,在該省份下,銀行業的發展模式和導向都是相近的,低一級銀行部門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權”其實相對較小,在這種情形下,省級內部的銀行機構的集聚發展導向更為突出(證券、保險業市場也是如此)。基于此,本文選取了省級口徑的金融集聚指標來進行刻畫。
(1)
其中,LPFAi為地區i的金融集聚水平,Fin為地區金融業融合發展程度,Pop為地區人口規模。

圖3 金融集聚的三種分類組合構成
3.控制變量
為提升研究的準確度,本文在實證模型中加入了對被解釋變量具有重要影響的控制變量。具體包括企業總資產(LnAsset)、企業總收入(LnIncome)、杠桿率(Lev)、兩職合一(Mega,董事長與總經理兼任時取1,否則為0)、第一大股東股權集中度(Share)、日均換手率總股數(ADTR)、審計意見(Aduit,審計單位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取0,否則為1)、機構投資者持股占比(Institution)。
(三)模型設定
為研究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本文設定了如下模型加以檢驗。
LnDGi,t=φ0+φ1LPFAi,t-1+∑CVs+∑Ind+∑Year+εi,t
(2)
其中,企業數字化轉型(LnDG)是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省域層面的金融集聚度(LPFA)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CVs為包括了前述控制變量集。ε為隨機誤差項。本文中企業數字化創新可能受時間與行業特征等難以觀測因素影響,或對“金融集聚—企業數字化轉型”所原有的關系產生干擾,故在本文中引入行業和時間虛擬變量,以減少上述因素對研究結果所產生的或有沖擊。由于金融集聚影響傳遞至企業數字化轉型可能存在一定時滯,本文對金融集聚變量采用滯后1期處理,這既考慮到了變量傳遞變化之間的時間需要,又能減少可能存在的互為因果問題。
四、實證結果與經濟解釋
(一)基準回歸
表1針對“金融集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核心基準關系展開實證研究。在控制“時間—行業”雙向固定效應的回歸(1)中,金融集聚(L.LPFA)的回歸系數為0.382且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在回歸(2)中納入了控制變量集,所得的回歸系數為0.325同樣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雖然在納入控制變量后回歸系數有所下降,但這可能是新加入的控制變量集吸收了部分相關影響所致。上述結果表明金融集聚的發展效果越好,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這為本文的核心假說提供經驗證據支撐。考慮到當前金融業態具有較強的輻射和覆蓋能力,考察特定區域金融集聚的影響是否會外溢至轄區外部對實體經濟產生作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有鑒于此,本文刻度了除本省之外其余省份的金融集聚均值指標(LPFA_Peer)進行檢驗。研究發現,本省之外的金融集聚發展能夠對本省轄域內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產生正向積極影響(回歸系數為0.312且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特別地,本省之外的金融集聚與本省的金融集聚之間,能夠形成良好的“合力”,從而共同推進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回歸系數為0.745且通過了5%的統計顯著性檢驗)。本文認為,當前中國金融業的發展,正在逐步深度嵌入前沿的數字技術,形成了“廣覆蓋、高滲透、低成本”的金融服務體系,這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地理要素帶來的金融供給阻隔,由此形成了顯著的“溢出”和“協同”效果。
(二)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處理
為提升核心結論的確當性,本文對模型的穩健性和內生性做了如下處理。第一,延長模型中的時間窗口,以檢驗在更長的周期內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軌跡;第二,采用不同的核心變量口徑進行檢驗,力求獲得更為細化經驗證據以支撐核心結論;第三,剔除部分特殊樣本,考慮到樣本中某些不可觀測因素會干擾核心關系,本文針對這些樣本進行剔除處理。
1.延長觀測窗口
如表2所示,本項實證回歸主要研究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持助力是否具有長效激勵作用。具體可劃分為兩個處理手段,第一,對核心解釋變量(LPFA)進行多時期的滯后項處理;第二,對被解釋變量(LnDG)進行前置處理。研究發現,在回歸(1)~回歸(3)中三個金融集聚(LPFA)滯后項回歸系數均有著高度顯著并通過了5%的統計顯著性回歸,即在這三個滯后期內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均存在明顯的促進作用;在回歸(4)~回歸(6)中本項研究對被解釋變量(LnDG)進行了前置處理,在三個不同前置時期內的組別中,結果顯示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支持作用依然明顯。研究結果表明,金融集聚在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作用長期內具有顯著的動態可疊加效果,這為驗證本文所提出的核心假設提供了支撐。

表1 金融集聚與企業數字化轉型
2.核心變量口徑分解
在表3的檢驗中,本文通過對核心解釋變量的計算方式與口徑進行變更處理,以在多個更為細化的角度來檢驗本文的核心結論。具體而言,本文將金融集聚按金融業態細為銀行業集聚(PBAL)、證券業集聚(PSAL)、保險業集聚(PIAL)三種不同口徑,并分別針對上述不同金融業態開展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在對核心解釋變量的計算口徑進行細分變更后,回歸(1)~回歸(3)均為正相關且均通過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說明變更上述計算口徑條件下主要金融業態均能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產生助力效果,顯示出金融集聚仍對企業數字化轉型起顯著的促進作用,本文的核心結論依舊沒有發生變化。

表2 穩健性檢驗I:延長觀測窗口

表3 穩健性檢驗II:變更核心變量口徑
3.剔除部分影響因素
表4的檢驗主要將樣本中存在的特殊樣本點刪除,以便更為干凈地識別金融集聚與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的影響關系。本文從“時間—空間—企業”三個層面對其中的特殊性樣本進行剔除。具體來看,在時間維度上,本文的樣本期中包含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15年中國股災這兩個重要的時間點,這類危機所產生的誤差難以通過技術手段進行校正。針對上述情況,本文剔除了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股災時點的樣本(考慮到金融危機沖擊存在的時滯,對其后續年份一并刪節)。在空間維度上,由于直轄市具有較為特殊的經濟政治屬性,以及中國東部地區擁有各項明顯稟賦優勢等因素,可能會對本文的核心結論產生一定干擾,遂本文亦將歸屬為這類地區的樣本進行剔除。在企業維度上,考慮到本文的數字化轉型變量是由企業年報文本識別而來,年報文本的信息披露可能會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那些信息披露質量較高的年報(如年報經由四大會計事務所審核以及年報信息披露考核在A、B級別的樣本)。由表4的實證檢驗可知,在對原有樣本進行“時間—空間—企業”層面的特殊要素剔除處理后,本文的核心結論“金融集聚能夠有效助力企業數字化轉型”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表4 穩健性檢驗III:剔除部分因素
4.邊際效應分析
前述實證分析基本確證了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正向影響,但尚未分析金融集聚影響效力可能具有的邊際效果。基于此,本文基于金融集聚(LPFA)進行了邊際分析(詳細的分析結果可參見圖4)。從圖例中可以發現,在每一個邊際變動點上,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都維持著穩定的正斜率。這意味著,隨著金融集聚的強度越來越大,其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邊際彈性逐漸上升。應當說,本部分的研究結論同前文均保持著高度一致。

圖4 穩健性檢驗IV:邊際效應分析 圖5 穩健性檢驗V:分位數檢驗
5.分位數檢驗
隨著企業數字化轉型強度的提升,不同數字化轉型水平下的企業稟賦和表現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對此,本文針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強度進行分位數層面的檢驗。從數據分析結果(圖5)來看,金融集聚在條件分布的差異化節點上,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展現出了不同的驅動力。研究發現,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相對較低區間中(20分位數點至70分位數點),金融集聚影響的擬合線斜率大體為正,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相對不夠充分的情形中,金融集聚具有較為良好的驅動力;而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較強區間中(大于70分位數點),金融集聚所能展現出的驅動力出現了一定的下降趨勢,這意味著,在較高的數字化轉型階段中,可能僅僅依靠于金融資源的驅動會存在一定的不足,這需要一定的配套輔助措施才能將企業數字化轉型更有效地推動至高級階段中。但從整體來看,作用效果的擬合線及其置信區間始終處于橫軸上方,這意味著金融集聚的數字化轉型驅動效果一直保持為正,這也同本文的核心結論保持高度一致。
6.固定效應變更
為了進一步吸收那些不可觀測因素的影響,減弱實證分析中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了“高階固定效應”的方式來進行檢驗。具體來看,在原有實證分析控制了“時間—行業”固定效應的基礎上,本文還進一步納入了“時間×行業”的交乘聯合固定效應(回歸(1)),以吸收那些隨著時間變化卻又不可觀測的行業因素。進一步地,本文為了提升對地區要素稟賦的控制程度,還分別納入了城市固定效應(回歸(2))以及“時間×城市”的交乘聯合固定效應(回歸(3)),以吸收那些隨著時間變化卻又不可觀測的地區效應。在回歸(4)中,本文還控制了企業層面的固定效應。經由上述多種類多方法的固定效應變更,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促進作用依舊顯著(均至少通過了5%的統計顯著性檢驗),本文的核心結論并未發生任何改變。

表5 穩健性檢驗VI:采用高階固定效應
7.排除其他競爭性解釋
在本部分實證檢驗中,本文依照彭俞超等(2018)的研究思路,進一步在回歸方程中納入其他重要控制變量,通過這類因素的納入來排除可能存在的競爭性解釋,也能夠緩解遺漏變量帶來的內生性偏誤問題。
具體來看,本文在回歸(1)中先納入了科技金融試點(TF)以及金融科技發展(Fintech)水平(王小燕等,2019),將其作為對轄區內實體企業創新轉型具有重要影響的其他金融因素;在回歸(2)中,則納入了是否開通高鐵(Railway)以及是否為寬帶試點城市(broadband),將其作為轄區內對實體企業創新轉型具有重要影響的技術基礎因素;在回歸(3)中,則考慮了產業結構優化—第二第三產業比值(Structure23)、國內生產總值增速(GDP_Speed)以及高等院校數量(Universities)因素,將其作為轄域內實體企業創新轉型的重要外部基礎條件。在最后一列檢驗中,則將前述的所有重要因素均放入同一方程中進行檢驗。
不難發現,本文的核心結論在各個方程中均顯著成立。該部分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本文所發現的金融集聚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核心結論是確當的,其效果并不能用現有研究中這類重要的“金融—技術—經濟”等指標所解釋,這些發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遺漏變量所帶來的內生性偏誤問題。
8.工具變量法
必須承認的是,盡管前述實證進行了大量的穩健性檢驗,但回歸模型中依舊難以規避遺漏變量等內生性問題的擾動。本部分進一步采用了工具變量法來減弱內生性的干擾。具體來看,本文選取了企業所在地的“經度、緯度”作為工具變量開展檢驗。其理由是,一方面,金融的集聚發展在地域上具有明顯的集聚特征,在特定區域上的金融集聚更強,效果更明顯,從這個角度來看,金融部門集聚的經度和緯度之間存在相關性;另一方面,作為獨立的企業主體,其行為決策(包括但不限于企業數字化轉型)與當地的經度、緯度并不存在明確的因果關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工具變量的排他性需求。事實上,地理因素已經作為一個有效的工具變量在經濟學研究中被廣泛使用,本文也采用這種方法進行內生性處理。

表6 穩健性檢驗VII:排除其他競爭性解釋
實證結果發現(實證結果可參見表7),Kleibergen-Paap rk LM統計檢驗結果表明,不存在識別不足的問題(均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Hansen J統計量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即表明工具變量是有效的。在經由工具變量的調整后,原有的核心結論依舊保持不變,這說明,本文的核心結論是穩健確當的。

表7 內生性處理:工具變量法
(三)異質性檢驗
在前述檢驗中,本文確證了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具有正向作用的核心結論。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屬性的企業稟賦要素不同,生產創新決策的側重點也有所差異,不同企業在面對相同的金融集聚影響時,可能會具有差異化的反應特征。為了精準識別金融集聚對異質性企業所產生的不同影響以便提出更為恰當的政策建議,本文在前文研究上按照所有制屬性、戰略創新地位以及生命周期發展階段進行劃分,基于上述企業特征進行分組檢驗,以期獲得更加精細化的實證發現。
在表8的回歸(1)~回歸(2)中,本文以企業的產權性質作為劃分依據開展異質性檢驗。結果發現,金融集聚對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并不顯著;而對非國有企業組別的回歸系數為0.569且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這表明,金融集聚對非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有著更為突出的轉型驅動效果。本文認為,一方面,國有企業由于嵌入了國家信譽,在金融市場中更容易獲得豐厚的金融資源,因此國有企業在面對金融集聚所帶來的“福利”時反應并不明顯。另一方面,國有企業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性責任(諸如社會就業、環境治理、社會穩定等),同時國有企業往往面臨更嚴厲的監管與考核(王萍、卜華,2022),這會使得國有企業發展更加追求穩健(王玨等,2015),在進行轉型創新活動時也往往更為謹慎(徐曉萍等,2017)。即便存在有效的金融集聚業態,也難以有效驅動國有企業開展系統性的數字化轉型活動。與之不同的是,非國有企業在融資環境方面處于明顯劣勢,同時非國有企業在市場主體中占多數,資金市場供需矛盾尤為突出。金融集聚所形成的資金充裕效果,能夠給這類企業帶來更為顯著的資源約束緩解作用。更為重要的是,相比國有企業在經濟社會中所擁有的市場優勢地位,非國有企業往往面臨著更加激烈的競爭狀況,這類企業更愿意從數字創新活動中彌補自身劣勢,改善企業未來發展前景。因此,在金融集聚的強有力支持下,非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會明顯加快。

表8 異質性檢驗I:企業屬性
在表8的回歸(3)~回歸(4)中,本文以科技創新屬性為劃分依據開展異質性檢驗。結果顯示,戰略性新興企業能受到金融集聚的明顯驅動(回歸系數為0.385且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但金融集聚卻并沒有對非戰略性新興企業的數字化轉型起到明顯助推(t值僅為1.58)。本文認為,戰略性新興企業多具有開展數字化轉型所需的科技底蘊與高素質人才隊伍配備,也更加關注前沿數字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更重要的是,這類企業通常面臨著競爭激烈市場環境,企業的技術更新迭代迅速,對金融資源的需求更加強烈。與此同時,金融集聚形成了高質量的金融資源聚合,轄域內金融機構能夠實現高質量金融供給和風險容忍度提升的雙重擬合,能夠引導金融資源更多地注入到具有良好未來發展前景的企業(如具有較高意愿推動數字化轉型的企業)中,因此金融集聚對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升級具有較強的助推作用。而非戰略性新興企業所面臨的市場競爭并不足夠激烈,企業的轉型意愿偏弱,即便金融集聚能夠顯著改善企業的財務狀況,但這類資源的注入也會被企業“分散”至其他一般性的生產項目中,無法實現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有效助推。

表9 異質性檢驗II:企業生命周期階段
在表9的實證研究中,本文以企業生命周期為劃分依據(劉詩源等,2020)開展異質性檢驗。研究發現,金融集聚能夠顯著驅動處于成長期與成熟期的企業進行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回歸系數分別為0.377與0.352,均通過了1%置信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而金融集聚對于衰退期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作用并不明顯(回歸系數為0.110,t值僅為0.89)。根據企業生命周期理論,在企業發展的每個階段上,自身生產經營特點、融資手段、融資方式等均會出現較大變化。處于成長期的企業發展迅速、開拓市場速度較快,在創新方面資金投入量大,于是對資金的需求尤其旺盛,金融資源短缺現象特別突出,金融集聚為企業成長階段的資金融通提供便利支持,有力促進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進入成熟期的企業在生產銷售等各方面達到相對完善的程度,擁有相對充沛現金流與資產積累,具有良好的企業創新內部環境。這類企業能夠有效地將由金融集聚所帶來的“資源紅利”轉換成為良好的數字化轉型創新資源條件,從而展現出有效的轉型驅動效果。與之成鮮明對比的是,衰退期企業在市場中的地位開始下降,企業發展減緩甚至衰退,相關的財務和生產指標趨于惡化。此時企業首要目的是獲取維持正常生產、經營和財務穩定的所必需的資金支持,而非將其投入到創新轉型活動中。此時金融集聚為這類企業形成的金融條件改善效果,大多被企業集中轉入了基本的生產、財務項目中,對于數字化轉型這樣的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活動而言,無法形成強有力的支撐作用。
五、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機制檢驗
在前述研究中,本文確證了金融集聚能夠有效驅動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核心關系,并挖掘了豐富的差異化特征事實。但考慮到前述研究僅僅涉及“金融集聚—企業數字化轉型”之間的現象刻畫,并未深入分析金融集聚通過怎樣的渠道機制作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有鑒于此,本文在前文的邏輯分析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實證研究的方式,針對金融集聚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機制渠道展開檢驗。
為了詳細探討其中的影響機制路徑,本文借鑒了溫忠麟等(2004)的機制分析步驟,構建了如下遞歸模型展開識別檢驗:
LnDGi,t+1=φ0+φ1LPFAi,t-1+∑CVs+∑Ind+∑Year+εi,t
(3)
Mediatori,t=θ0+θ1LPFAi,t-1+∑CVs+∑Ind+∑Year+εi,t
(4)
LnDGi,t+1=γ0+γ1Mediatori,t+γ2LPFAi,t-1+∑CVs+∑Ind+∑Year+εi,t
(5)
其中,機制變量選取了既同金融集聚相關,同時也會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產生影響的因素。特別地,本文還借鑒了唐松等(2020)的研究,針對被解釋變量(LnDG)采取前置1期處理,機制變量(Mediator)保持當期的數據結構,而核心解釋變量(LPFA)的進行滯后1期處理。這樣處理的好處在于,既能減弱變量之間互為因果干擾,又能考慮到變量之間影響所需要的時間。依循前述的理論分析,本文選取了三個機制變量進行識別檢驗。在財務緩解機制識別上,本文參考Hadlock and Pierce(2010)的研究,設計出企業的融資約束(SA)指標來衡量企業面臨的資源約束狀況;在預期優化機制識別上,本文基于企業年報詞匯的大數據識別,以LM詞典為評判依據識別出年報文本的語態,刻畫出企業對自身的積極預期強度,即年報語調Tone=(積極詞匯數-消極詞匯數)/(積極詞匯數+消極詞匯數);在創新提升機制識別上,本文參考龍小寧、林志帆(2018)的研究,使用企業研發支出強度(R&D,研發支出/營業收入)來刻畫企業的創新活躍度。詳盡的回歸結果可參見表10—12。
(一)財務困境緩解機制路徑
在表10的實證檢驗中,本文基于“財務機制”視角分析金融集聚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機制。實證結果顯示,金融集聚能有效緩解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困境(L.LPFA的回歸系數為-0.158且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確實,金融集聚能夠促進證券、銀行、保險等多種金融業態在區域內的高質量聚合,使得區域中金融機構間的競爭加劇,推動金融機構采用更為多元的技術信息手段,挖掘發現更多的潛在優質客戶,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這種改善主要體現在金融集聚能夠有效拓寬企業的融資渠道,提升了企業內部的金融資源充裕度。進一步研究發現,企業融資約束對數字化轉型進程的推進有顯著不利影響(SA的回歸系數為-0.083且通過了5%的統計顯著性檢驗)。本文認為,在一個資金緊缺的情景中,企業為了維系基本的財務、生產的“底線”運營,不會將有限的資金注入到高風險、高投入、長周期的數字化轉型項目中。由此,金融集聚在改善了企業融資約束后,會對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帶來顯著的驅動效果(Sobel-Goodman Mediation Tests的Z值為2.114,通過了5%的統計顯著性檢驗,傳導機制是正向有效的)。

表10 機制識別檢驗I:財務困境緩解
(二)預期優化機制路徑
在表11的實證研究中,本文基于“預期機制”分析金融集聚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機制。檢驗結果顯示,金融集聚程度越高,企業年報所展示的預期和語調則越積極(L.LPFA的回歸系數為0.024且通過了1%置信水平下的統計顯著性檢驗)。本文認為,地方的金融集聚發展程度越高,往往意味著當地的金融資源要素配置效率越高,在得到較好金融要素支撐的條件下,企業通常會有較好的預期,特別是在金融集聚有效改善企業內部的資源邊界約束后,企業對未來的發展將會持有更為積極的態度。進一步來看,企業積極的預期能夠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形成積極促進效果(Tone的回歸系數為2.318且呈現出高度顯著狀態)。需要認識到的是,企業數字化轉型是一項系統工程,本身就具有較強的不確定性特征,企業對自身發展態勢的判斷會對這類創新轉型決策具有重要影響。如若企業對未來的預期較為樂觀,則更容易給這類高風險的創新轉型活動騰挪出更多的“容錯空間”,激發企業對高潛力項目的注意力和支持力度,從而有利于企業數字化轉型項目的開展。由此,金融集聚在優化了企業預期后,會對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帶來顯著的驅動效果(Sobel-Goodman Mediation Tests的Z值為6.439,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傳導機制是正向有效的)。

表11 機制識別檢驗II:預期優化機制
(三)創新能力提升機制路徑
在表12的實證檢驗中,本文基于“創新機制”視角分析金融集聚影響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作用機制。實證結果顯示,金融集聚對驅動企業創新能力提升效果明顯(L.LPFA的回歸系數為0.006且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本文認為,金融集聚在改善了企業的資源邊界約束后,企業無需再將過多的精力和資源集中在一般性的生產、財務項目上,能夠有富余的資金開展專項的研發創新活動。特別地,金融集聚效果越大,這類金融往往會面臨著越為激烈的市場競爭,則有能力篩選轄域內有較大發展潛力的企業進行專項的金融支持,由此也會倒逼企業增加研發投入強度。進一步研究發現,企業研發投入強度的增加會顯著提升企業數字化轉型強度(R&D的回歸系數為2.903且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應當說,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底層技術即在于技術創新的支撐,而研發投入強度的增加,恰恰能夠為這種創新活動提供堅實的基礎。由此,金融集聚在提升了企業的研發強度后,會對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帶來顯著的驅動效果(Sobel-Goodman Mediation Tests的Z值為3.666,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傳導機制是正向有效的)。

表12 機制識別檢驗III:創新能力提升
六、拓展性研究:基于金融監管視角下的金融集聚影響效果檢驗
在過往的經濟、金融實踐中,中國的金融業態一直在一個較為寬松包容的環境中發展(黃浩,2018),這為金融的高質量發展打開了足夠廣闊的創新空間。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金融業態在缺乏監管的情形下,會引發更為復雜的風險關聯,極容易蘊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金融業態本身就具有顯著的“市場逐利”型特征,金融在服務實體經濟過程中依舊會有明顯的結構性錯配問題。有鑒于此,如何構建一個有助于區域金融業態發展的良好環境,對其進行有效的規制和引導,是新時代新階段下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命題。本文認為,金融監管作為金融體系制度建設的重要一環,是金融實踐中的基礎性要素,對充分釋放金融功能具有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形成金融發展和監管強大合力,補齊監督短板,避免監管空白”(3)《讓金融監管為金融發展保駕護航——落實習近平總書金融安全重要講話精神系列述評之五》,中國政府網,2017-05-07,htt://www.gov.cn/ximwen/2017-051071content-5191592.htm.。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何在一個更好的金融監管環境中推動金融集聚業態與微觀結構主體創新轉型的深度融合,具有高度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然而在現有文獻中,有關金融監管如何有效規范金融發展以服務實體經濟的文獻并未展現出具有一致性的結論。一方面,強化金融監管有助于克服金融市場與生俱來的脆弱性,有效扼斷金融風險的放大路徑,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運行(Kregel,1997;Meltzer,1967),促使金融機構規范有序地開展經營業務,為促進服務實體經濟效率提升提供了良好的秩序保障(馬亞明、楊蘭,2022)。但另一方面,政府規則下的金融監管也往往滯后于金融市場的發展,極易出現監管錯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實踐中的監管強度難以把握,過度監管會對金融系統造成沖擊(蔣海,2001;張曉燕等,2022)。于此,本文進一步提出的問題是,在金融監管愈發重要的大背景下,金融集聚能否展現出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有效驅動力?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在已有“金融集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范式中,進一步嵌入了金融監管這一重要元素。借鑒唐松等(2020)的研究文獻,以地區金融監管支出/金融業增加值作為地區金融監管強度的代理變量(IFS)。首先,以中位數為界,劃分出地區金融監管的強弱組別,并重新進行本文的基準檢驗;其次,本文還采用金融集聚與金融監管的交互項進行二次驗證,以增強研究的有效性和說服力(表13)。

表13 金融集聚、金融監管與企業數字化轉型
表13的實證研究發現,在金融監管強度大的環境下,金融集聚能夠有效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回歸系數為0.490且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然而在金融監管強度較小的環境中,金融集聚并未對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升級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不具有統計顯著性)。為了提升結論的說服力,本文還進一步開展了交互項檢驗(L.LPFA×L.IFS)。其中,交互項系數為0.147且通過了1%的統計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在金融監管強度越大的地區,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力越強,金融監管在“金融集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系中起著正向調節作用。本文認為,金融監管能夠有效規范和約束金融資源的流向,強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大創新需求的靶向性,拓展金融集聚對實體經濟支持的深度和廣度。進一步地,金融監管能夠為金融部門的“套利空轉”行為設置更高的門檻與合規成本,降低金融集聚業態下所可能產生的脫實向虛行為,實現金融業態集聚的規范化、健康化發展,從而為轄域內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提供了穩定高效的金融生態場景。
七、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企業數字化轉型作為引領新經濟高速發展的關鍵抓手,對培育提升企業核心價值,帶動新經濟增長點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針對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展開探索,基于中國滬深A股上市企業2007—2019的數據信息,研究構建出數字化轉型有關指標,檢驗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并對機制路徑進行了識別,并在此基礎上將金融監管嵌入核心關系框架中。
本文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第一,本文的核心假設“金融集聚能夠有效驅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在經歷多重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后依然顯著;第二,金融集聚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會因企業屬性的不同而存在異質性。具體來看,對于非國有企業、處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初創期與成熟期的企業而言金融集聚能夠顯著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相反對于國有企業、處于非戰略性新興產業與衰退期的企業而言金融集聚對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升級活動的影響較弱;第三,金融集聚作用于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的路徑渠道主要有,疏解企業融資約束困境、優化企業預期與提升企業創新能力,通過三大路徑對企業各方面競爭能力的改善,提升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第四,有效的金融監管是金融集聚發揮效力的重要外部基礎條件,在較強的金融監管組別中,金融集聚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驅動效果更為明顯。
本文的政策研究建議是:第一,政府要為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活動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要持之以恒地鼓勵與支持企業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力度,引導企業立足本業守正創新,將自身優勢做優做大做強。同時政府要充分把握好金融集聚這一有效促進企業創新發展的關鍵要素,加速促進金融集聚發展,努力使之成為經濟騰飛的制勝法寶。要充分發揮金融集聚帶來的信息、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溢出效應,主動搭建涵蓋各市場的溝通服務平臺,為企業融資、信息咨詢等牽線搭橋,其中應將政策重心向非國有企業、創新發展勢頭良好的企業傾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提供全方位的非大水漫灌式的精準支持。 第二,金融機構要充分利用金融集聚的契機,加強不同金融機構間的交流合作,充分發揮規模經濟的優勢,特別強化與不同業態金融機構間的互聯互通,對區域內企業形成資金合力。在綜合利用各方信息交流機制的基礎上,精準識別企業發展前景與融資需求,為企業量身定做資金支持計劃,為企業開展數字化創新提供高效優質的金融服務。第三,作為數字化轉型主要載體的企業,應把握時代發展大勢,以更為積極主動姿態融入數字化發展浪潮中,對照自身與區域內所集聚的先進企業樣本,積極適時開展數字化創新活動,培育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第四,在金融集聚區中金融監管應堅持有所為且有所不為的原則。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市場活躍的融資氛圍同時,當好金融市場的“守夜人”,加強對金融市場的凈化。在引導金融機構將資金更多地流向實體經濟,鼓勵更多企業開展創新升級,加速企業數字化轉型進程的同時,堅決防止企業脫實向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