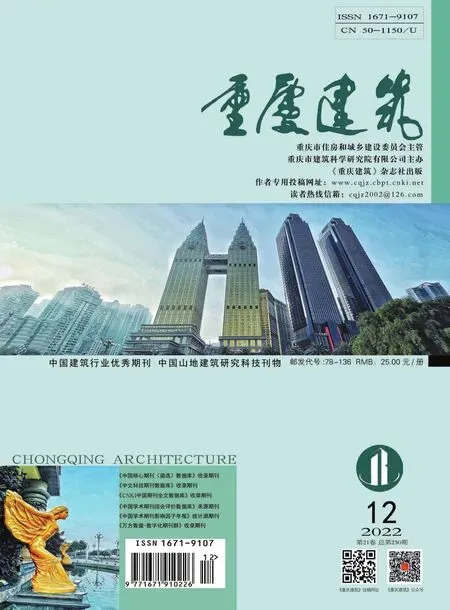踐行以人為核心的韌性城市理念
政府文件中,“十四五”規劃首次提出“韌性城市”概念,其語境是“增強城市防洪排澇能力,建設海綿城市、韌性城市”。這里的“韌性”與建設海綿城市的要求相并列,成為增強城市防洪排澇能力后要達到的城市硬實力建設目標。“韌性”一詞,成為對建設海綿城市效果的一個補充說明。
二十大報告再次提出有關“韌性城市”的概念時,“韌性”在文本中的地位及其內涵則發生了巨大變化。“堅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提高城市規劃、建設、治理水平,加快轉變超大特大城市發展方式,實施城市更新行動,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打造宜居、韌性、智慧城市。”這里的“韌性”,不再是建設海綿城市一類的技術性語言了,它成為與“宜居”“智慧” 這樣具有同等戰略重要性的對城市治理進行宏觀指導的思想。而無論是“宜居”“智慧”或“韌性”,最終指向的,都是讓城市更好地服務于人。
關于城市工作的人本主義,早在2015 年12 月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就提出“建設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后來,在多次領導人講話中,以及“十四五”規劃和二十大報告中,“以人為核心”均一再提及,說明決策層關于這一城市工作政策的連貫性和一致性。7 年來,“以人為核心”的人本主義是始終不變的政策目標,處于發展中的則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思想和理念,“韌性”就是其中一個樣本。從7 年前的城市工作會議并未提及,到“十四五”規劃將之與“海綿”并列,到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拓寬其意義,將其提到與“宜居”“智慧”這樣的戰略性話語的高度,足見追求“韌性”對于城市建設和管理的越來越緊迫的重要意義。
“韌性”一詞最早起源于工程材料學,表示物理系統受擾動脅迫后保持穩定力的能力,上世紀70 年代被引入生態學領域,用以描述大自然遭到擾動后的恢復力。2002 年,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首次提出“韌性城市”的概念,將其引入城市與防災研究中,進而掀起研究城市韌性的熱潮。就像我們“十四五”規劃提到“韌性”時所指一樣,最初有關“韌性城市”的研究,也多是將它當作一種工具理性,旨在推動城市硬件升級,夯實城市硬實力,以抵抗諸如熱帶風暴、地震、洪水、海平面上升、重大傳染病等威脅。但這一概念的內涵逐步得到演進,城市管理者和研究者發現,城市不僅需要具備韌性較強的硬件,還需要具備強韌性的軟件,尤其是隨著城市規模越來越大,運行越來越復雜,城市參與者和文化越來越多元,互聯網技術對城市各領域的持續重塑,等等,城市日益面臨越來越多的非傳統安全風險,“韌性城市”的內涵逐步由“應對災害的防御能力外延為應對城市處理各種壓力和風險的綜合能力”。

目前,關于“韌性城市”相對權威的界定是,“城市系統及其所包含的跨時空尺度的社會生態和社會技術網絡,在面對干擾時能保持或迅速恢復所需功能并適應變化的能力,同時對限制當前或未來適應的能力進行改造轉型”。由此可以看出,對于城市這個“復雜巨系統”,具備韌性是它遭遇各種危機仍能正常運轉的關鍵。因而,城市韌性建設不再是針對某項具體危機進行缺陷修補和功能加強等,而是成為一種城市建設和管理的思維方式,即在城市建設和管理的每個環節,都要融入構建韌性城市的思維,使城市具備“在災害和變化中不斷調整適應,整合各類資源實現學習、適應、自組織的演化能力”。
“韌性城市”落實到行動上,首先需要有一個對該理念的系統性詮釋。洛克菲勒基金會提出的韌性城市框架,正是這樣一個將戰略目標進行拆解的行動指南,有助于了解影響城市韌性的眾多因素,并對癥下藥。框架包括4 大維度,即個人的健康和福祉、城市基礎設施和服務、經濟和社會、領導和戰略。其中放在首位的,仍然是城市中生活的人,具體而言,就是滿足人類基本需求、支持生計與就業、保障生命健康等。
當前,構建并實施以人為核心的韌性城市理念,非常緊迫。隨著疫情防控措施進一步優化,城市韌性面臨進一步考驗。以人為核心的韌性城市理念,要求防控措施調整轉段平穩有序,要求城市避免陷于突增的資源壓力、穩定壓力、輿論壓力等,要求城市不讓它的居民因防疫政策轉向而突遭生存壓力。本質上,這考驗的是一種系統性的城市韌性,包括制度韌性、社會韌性和個體韌性等,制度韌性實現兜底,社會韌性實現互助,個體韌性實現發展。根據已有研究,處于中觀層面的社區,仍然應該作為韌性建設的抓手,它將政策和資源釋放給基層,也是基層聲音和信號的收集和傳遞者,它本身就是讓城市保持良性運轉的“韌帶”,是以人為核心的韌性城市理念的直接踐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