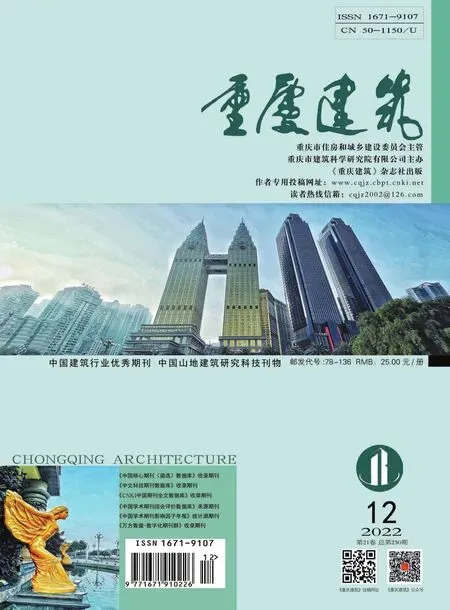重慶銀杏堂大雄寶殿復原研究
陳勇,何玢華
(1 重慶大學建筑規(guī)劃設計研究總院有限公司,重慶 400044;2 石柱土家族自治縣文物管理所,重慶 409100)
1 項目概況
銀杏堂建筑群位于重慶市石柱縣北部河嘴鄉(xiāng)銀杏村,與梁平雙桂堂齊名,并稱“川東姊妹堂”。根據(jù)2012 年對銀杏堂的現(xiàn)狀測繪及2015 年修繕過程中發(fā)現(xiàn)大雄寶殿木構件改動較大,再結合2010 年對秦重陽老人(時年93 歲,解放前在寺內(nèi)學藝)和附近村民的口述歷史采訪,得知原大雄寶殿和法堂均為三重檐,殿高16m 左右。在解放后土改時期,大雄寶殿和法堂作為糧倉和會議室使用,村民認為殿堂太高,冬季太冷,以及搬運東西不便,遂將第三層檐拆除。本次研究擬將銀杏堂大雄寶殿恢復至光緒十九年(1893 年)時期的制式。
2 歷史沿革
銀杏堂原名蟠龍寺(盤龍寺),據(jù)傳該寺初建于唐朝,歷經(jīng)宋元時期歷次兵燹戰(zhàn)禍。關于銀杏堂記載的歷史文獻寥寥無幾。其一是石柱地方志,據(jù)清乾隆《石柱直隸廳志》載:“城北銀杏寺,創(chuàng)自前明初,廳境大剎也。殿宇深邃,僧徒眾多……初名山王廟、銀杏寺。乾隆間,有僧透月,著名遠近,本寺住持,具啟梁邑雙桂堂敦清,更名銀杏堂,安祥傳戒,佛法大振……”清道光二十三年《補輯石柱廳新志》載:“銀杏寺,在城東北二百里,創(chuàng)自前明萬歷中,廳境大剎也。殿宇深邃,僧徒繁多,每歲開壇授具足戒。”[1]其二是寺院內(nèi)碑刻,據(jù)寺院清乾隆十六年(1751 年)《大乘妙法蓮花經(jīng)重修福德碑》載:“……究考古殿梁記,乃復辟于明之正德庚辰。有果聰和尚,為重開住持建大殿。嘉靖戊午有大舟和尚修前殿。……萬歷間,住持廣淵和尚,有虞公陳大夫,慨捐帑貲,裝修殿宇察舍,砌筑山門、垣堵。……于正殿,塑裝三身大佛、二柱金龍及合堂。……山朽于乾隆庚申春,應諸檀命,免為焚獻。是夏,幸諸檀同心葉志,重修后棟藏樓及廚房浴室。……于丙寅秋,重建大殿、前殿。”(圖1)銀杏堂大殿由果聰大和尚于明正德十六年(1520 年)復建,明嘉靖三十五年(1558 年)由大舟大和尚修前殿,明萬歷年間由廣淵大和尚砌筑山門、垣堵,于正殿塑裝三身大佛,二柱金龍及合堂。崇禎十七年、順治元年(1644 年)明代高僧破山海明禪師受明吏、兵部之請,入寺兼任第三十五世方丈。永歷四年、順治六年(1649 年)銀杏堂毀于朱容蕃兵變。
雍正初年(1723 年)由定慈大和尚復建盤龍寺。乾隆五年(1740 年)春,梁平雙桂堂透月和尚來寺主持,由于清朝大興文字獄,遂將寺名更名銀杏堂。乾隆十一年(1746 年)秋,由石柱宜慰使馬宗大、孔昭給印捐資,先后重修大殿,前殿。乾隆十三年(1748 年)春,重修東廊、禪堂山門(圖1)。據(jù)寺院清嘉靖四年《護寺四王碑》載:“乾隆癸卯歲(1783 年),大殿火延至前殿,四天王像皆灰燼……越明年,天嚴成,是歲兼拴子文館于陳秦處士家,寺僧請保……成不果鐫碑,歲以原文遺失,今復屎予繼序。”(圖2)清嘉慶二年(1797 年)春,由大魁大和尚重修被火毀寺院,并于嘉慶四年完工。據(jù)大殿廊道石柱所刻《重修大殿方丈碑記》(光緒十九年)載:“凈緣和尚者,俗姓汪氏……光緒十四年進方丈,十五年上謁劉公,毅然以重輝寶剎為己任。……是年冬,鳩工尼材,越明年,方丈告竣畢,非有志者事竟成哉!且夫一人有感,眾人斯應,一善既成,眾善畢舉。”(圖3)清光緒十六年(1890 年),由凈緣大和尚重修大雄寶殿,并重獲四川總督府葑地批諭。

圖1 大乘妙法蓮花經(jīng)重修福德碑(乾隆十六年)

圖2 護寺四王碑(嘉靖四年)

圖3 重修大殿方丈碑記(光緒十九年)
1952 年,寺院及所有山地田產(chǎn)收為國家財產(chǎn),歸屬石柱縣人民政府管轄,并將此地設置為河嘴鄉(xiāng)政府臨時駐地,同時入駐的有供銷、糧食、醫(yī)務、學校,以及現(xiàn)銀杏堂村村民住地和集貿(mào)市場。廟內(nèi)居住的村民認為大雄寶殿和法堂室內(nèi)凈空太高,冬季太冷,遂降低室內(nèi)空高,將原三重檐改為兩重檐,同時被毀的還有明間內(nèi)金柱上兩根雕刻精美的木龍。2003 年,銀杏堂交由某旅游開發(fā)公司管理,該公司對大雄寶殿進行翻修,并將二層檐口高度提高2m。2015 年3 月,政府再次對大雄寶殿進行專業(yè)維修,由于缺乏相關資料,亦按現(xiàn)狀的重檐歇山屋面進行修繕。
3 現(xiàn)狀分析
3.1 銀杏堂整體環(huán)境
銀杏堂建筑群位于盤龍山之麓,官渡河西側,面向前方山形呈筆架山狀。建筑群坐西北朝東南,東北方和西南方山勢平緩,視野空遠。盤龍山因其山形酷似盤龍的形態(tài)而得名,整個山脈共分九峰,蜿蜒數(shù)公里,官渡河順其山腳而過,河水流到盤龍山第一峰靈鷲峰下。靈鷲峰又稱龍頭,總面積約三百畝,半山腰上對稱有約300m2天生水塘,猶如龍的兩只眼睛,而寺廟就建在水塘以上部位,即龍頭頂上(圖4)。

圖4 銀杏堂衛(wèi)星圖
3.2 銀杏堂建筑群平面布局
銀杏堂是石柱縣境內(nèi)規(guī)模最大的佛寺,總體布局采取院落與天井相結合的形式,占地面積46000m2,建筑面積3197.84m2(圖5)。寺院倚山而建,寺前龍眼坪壩、山門(天王殿)及彌勒殿、大雄寶殿、法堂、后山形成五級臺階式中軸線,兩進三重殿,12 個天井(其中3 個天井建筑已損毀,僅存建筑基礎),左右?guī)浚w呈中軸線對稱布局。建筑構架為木結構,屋面為小青瓦,合攏瓦屋面。灰塑屋脊極具南方寺廟特色,脊飾有寶瓶式中堆、龍吻、卷草紋等紋式;正脊、垂脊和戧脊用青瓦堆砌,微微向上翹起,形成輕揚的弧線,豐富了建筑的輪廓線。

圖5 銀杏堂總平面圖
3.3 大雄寶殿現(xiàn)狀分析
大雄寶殿為銀杏堂的主要建筑,位于中軸線第三級臺基上,臺基高1.67m,共9 級臺階。大殿明間為抬梁式木構架,次間兩側為穿斗式排架,殿內(nèi)為徹上露明造,建筑通高13.61m(至正脊上皮),重檐歇山屋頂,青瓦屋面,建筑面積318.97m2。
3.3.1 平面布置
大雄寶殿面闊五間,進深五間。通面闊20.6m,其中明間面闊6.2m,左右次間面闊5.5m,兩側廊道面闊1.7m。通進深14.57m,前檐廊深2.6m,后檐廊深2.1m,中部梁架深9.57m。由明間十根、次間十八根、廊道八根共三十六根柱子構成。通過現(xiàn)狀勘察,大殿階條石、角柱石、柱礎石和條石擋墻均保存較好,未見后期人為改動痕跡。從現(xiàn)狀遺存分析,平面布置應為清晚期形式。
3.3.2 梁架結構
大雄寶殿構架由明間兩榀木抬梁和次間兩榀穿斗式排架組成,因明間為抬梁式構架,跨度大,支撐點少,木柱直徑略大于其它柱子,為410mm。明間前后檐采用雙步梁支撐結構,雙步梁上設駝峰支撐下金檁,上有單步梁連接金柱和瓜柱,使結構更加穩(wěn)定;中間為穿斗抬梁結合式構架,五架梁插于前后石金柱上;下有隨梁枋,上立瓜柱支撐三架梁。穿斗抬梁結合式構架贏得了較大的使用空間,兩側次間為穿斗式木構架,柱距1.8~2.0m。前檐廊柱為石質(zhì),明間柱礎為石質(zhì)圓雕獅子吼,廊柱四周刻有清光緒時期重建銀杏堂捐款人名。兩側山墻、后墻均有方型漏窗。
在2015 年修繕前及修繕過程中,筆者對大殿進行了詳細的勘察測繪,發(fā)現(xiàn)其大木構架有明顯的改動痕跡。如圖6 所示,該位置為明間北側內(nèi)金柱,柱徑420mm,該柱所示位置切口明顯,其上直接放置Φ250 木柱連接,無任何墩接措施,可見后期改造較為隨意。同樣,圖7 木柱均有切口。圖8 和圖9 分別為大殿西北側和西南側重檐角金柱,同樣存在切口且高低一致,老角梁與重檐角金柱連接僅用扒釘固定,并未開鑿榫口。圖10、圖11 為北側次間木穿斗排架,可見排架木柱上有明顯切口,切口高度由中間向兩側遞減,將所有切口連接起來,正好形成“人”字形,如此有規(guī)律的斷面切口,說明大殿前期受到過降低處理,為人為改建的有力佐證。通過上述勘察結果發(fā)現(xiàn),銀杏堂大雄寶殿在2015 年之前受到過較大改動。

圖6 明間北側內(nèi)金柱

圖7 北側山墻面木排架拼接

圖8 大殿西北側重檐角金柱

圖9 大殿西南側重檐角金柱

圖10 大殿北次間排架切口局部

圖11 大殿北次間排架圖
3.3.3 屋頂形式
大雄寶殿屋頂為重檐歇山頂,小青瓦屋面。正脊、垂脊、戧脊和中堆均為水泥砂漿制作,而傳統(tǒng)工藝為灰塑屋脊,可見屋脊為后期制作,屋脊樣式改動較大。
4 與重慶地區(qū)同時期、同類型建筑特征對比分析
關于銀杏堂大雄寶殿三重檐的建筑結構形式,通過查閱史料、文獻、碑刻、傳記,發(fā)現(xiàn)均無記載和描述。根據(jù)建筑復原“同一地域、同一時期、同一類型”的原則,本文選擇與銀杏堂合稱為“川東二堂”的雙桂堂大雄寶殿作為參考,進行對比分析,原因有三:一是銀杏堂與雙桂堂相距較近,直線距離約68km;二是兩者同屬禪宗曹溪派臨濟宗,在建筑文化、建筑技術和建筑藝術等方面應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三是兩者在歷史形成過程中淵源深厚。據(jù)銀杏堂清乾隆木質(zhì)碑文載:“……即如石邑銀杏寺者,明末初建古南賓之遺剎也。……乾隆三年間,陳秦二姓并闔郡紳士耆再三禮請梁邑雙桂堂上透下月老和尚,主院擁錫,來慈慨然以……”(圖12)《嘉慶年重修碑記》載:“……八年間,于雙桂謹迎緒輝飛錫,接居和尚位。”(圖13)這兩處碑記雖未明確銀杏堂大雄寶殿的制式,但給出了兩條信息:一是乾隆三年透月和尚從梁平雙桂堂來銀杏堂當過住持;二是嘉慶時期的住持緒輝也來自雙桂堂。可見清中晚期在渝東南區(qū)域兩寺交流頻繁。而雙桂堂始建于清順治十年(1653 年),由禪宗破山大師創(chuàng)建,破山大師在創(chuàng)建雙桂堂之前,正好在蟠龍寺(現(xiàn)銀杏堂)。據(jù)《破山海明禪師語錄》記載:“師蟠龍解制,與徐公說法,以酬為法懇求之愿也,蟠龍則有牟吏部尚書郎秉素,奉差金陵,遇朝宗和尚告以天童衣缽,正在破山。……闔放講武,累世談兵,雖當大亂之際,無敢侵梁萬之疆,安居在陣,云闡化亦如治世。末后雙桂……”[2]1642 年破山禪師受明吏、兵部之請,入寺(銀杏堂)兼任第三十五世方丈八年。南明永歷六年(1648 年)寺院遭遇兵變,兵部尚書呂大器從石柱取道入黔,請大師隨同前往云南,大師未從,入梁平,而后建福國寺(今雙桂堂)。因此,參考梁平雙桂堂大雄寶殿進行分析研究,總結出二者建筑形制上的共同特征,為銀杏堂大雄寶殿三重檐的復原提供依據(jù)。

圖12 清乾隆木質(zhì)碑文

圖13 嘉慶年重修碑記
4.1 特征對比分析
對銀杏堂大雄寶殿與雙桂堂大雄寶殿建筑特征進行對比分析,總結如表1 所示。

表1 建筑特征對比
通過對銀杏堂大雄寶殿現(xiàn)狀與雙桂堂大雄寶殿的對比分析,得出以下共同點:
(1)在重建時期上,兩殿年代較近。銀杏堂大殿重建于清光緒十九年(1893 年),雙桂堂大殿重建于清光緒十五年(1889 年),重建時間相差4 年。而雙桂堂大雄寶殿重建歷時5 年,正好能接上銀杏堂大殿的重建時間,鑒于兩地相距較近且交流甚深,筆者大膽推測,銀杏堂大殿重建時的石作、木作、瓦作、灰塑或有參與重建雙桂堂大殿的工人參與;
(2)在建筑用材上,兩殿均大量使用石柱。雙桂堂大雄寶殿一層檐柱金柱全為石質(zhì),共計46 根,而銀杏堂大殿回廊亦全為石柱,共計10 根;
(3)在建筑風格上,屋面均為小青瓦,灰塑屋脊貼瓷片做法。
4.2 制式對比分析
銀杏堂與雙桂堂大雄寶殿平立剖面對比如圖14—圖16 所示。

圖14 一層平面圖

圖15 正立面圖

圖16 明間剖面圖
通過對比可知,銀杏堂大殿為三開間五進深帶回廊兩重檐歇山頂建筑,正立面二層檐口通過廊步架童柱出挑。而雙桂堂大殿為五開間六進深帶回廊三重檐建筑,每層檐口通過檐柱、外金柱、內(nèi)金柱挑出,形成三重檐。若銀杏堂大殿為兩重檐建筑,二層檐口通過外金柱出挑,結構更為合理。而重慶地區(qū)的三重檐建筑淶灘二佛寺下殿和南岸區(qū)大佛寺五佛殿亦是通過童柱出挑形成三重檐,如圖17、圖18 所示。

圖17 淶灘二佛寺下殿明間剖面圖

圖18 南岸區(qū)大佛寺五佛殿明間剖面圖
5 大雄寶殿復原分析
5.1 平面分析
古建筑面寬與進深,在清代以前并無明確規(guī)定,清《工程做法則例》規(guī)定,“凡面寬、進深以斗科攢數(shù)而定”[3]。而銀杏堂大殿并無斗栱,且南方地區(qū)并未完全按照清《工程做法則例》實施,川東地區(qū)做法隨意性較強。通過現(xiàn)場踏勘及雙桂堂大雄寶殿關于面寬與進深的對比(表2),筆者認為在解放后的降層處理中,并未對原大雄寶殿的面寬與進深進行改變,因此,大雄寶殿的三重檐將在原柱網(wǎng)的基礎上進行。

表2 面闊進深對比
5.2 結構分析
對于銀杏堂大雄寶殿的三重檐結構的復原,現(xiàn)有建筑遺存及同類型建筑特征對比,可以作為復原其建筑結構構成形態(tài)的依據(jù)。古建筑結構主要由三大要素組成:一是結構尺寸。包括構成梁架結構的總尺寸,如開間、進深、柱高、舉架等;二是結構形式。重慶地區(qū)古建筑大木結構包括穿斗式、抬梁式以及兩種結構混合而成的插梁式;三是屋頂形式。屋頂形式也是決定大木結構形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歇山建筑的收山、廡殿建筑的推山等[4]。因此,各構件的細部尺寸不在復原的范圍之內(nèi)。
5.2.1 建筑高度與舉架
在建筑開間、進深已經(jīng)確定的情況下,房屋總高度取決于建筑的檐柱高度和屋面舉架,而檐柱的高度一般又取決于房屋明間面闊寬度。古建筑柱子(檐柱)的高度與明間面寬具有一定比例關系,清工部《工程做法則例》規(guī)定:“凡檐柱以面闊十分之八定高,以十分之七定徑寸。如面闊一丈一尺,得柱高八尺八寸,徑七寸七分。”可見,檐柱柱高與明間面寬比例為8:10,而川東地區(qū)的大式建筑檐柱柱高與明間面寬比例在8:10~9.5:10 之間。通過對比,銀杏堂大雄寶殿柱高與面寬的比值為0.87,雙桂堂大雄寶殿柱高與面寬的比值為0.88,兩殿極為接近(表3)。再結合圍廊石檐柱并無改動后的榫口,筆者推測,現(xiàn)銀杏堂大殿廊步架及一層檐口高度保留了大殿降層前的形制及高度,在復原研究過程中,對此不做改動。在對兩殿的各層檐高對比過程中可看出:銀杏堂大雄寶殿(現(xiàn)狀)與雙桂堂大雄寶殿的一二層檐比值非常接近,三層檐呈逐步減小的趨勢。若參照雙桂堂大雄寶殿各層檐口高度的比例關系,則銀杏堂大雄寶殿的各檐口高度為一層檐高:二層檐高:三層檐高=5:2.25:1.9(表4)。

表3 柱高面寬對比

表4 各層檐高對比
關于舉架,通過兩殿對比分析(表5、表6)可知,銀杏堂大殿與雙桂堂大殿一層檐舉架相當,而銀杏堂大殿頂層舉架則大于雙桂堂大殿,可見在后期修繕過程中,銀杏堂為改善大殿在前期降層上帶來的視覺效果而局部提高了建筑高度。

表5 銀杏堂大殿舉架

表6 雙桂堂大殿舉架
5.2.2 大木結構
在銀杏堂大殿的降層過程中,保留了主要的大木結構形式。建筑明間為抬梁式木構架,次間山墻出則為穿斗式木構架,而大殿廊步架則采用了插梁式構造方式,以便承接二層出挑童柱。所以,銀杏堂大殿在木構架形式上為“抬梁+穿斗+插梁”混合式形制。
從前述建筑高度分析中可以得出,一層檐口及廊步架形式保持不變,利用廊步架童柱與外金柱和內(nèi)金柱之間插梁上置童柱形成二層檐,檐高取2.25m,舉架參照雙桂堂大殿二層檐舉架取0.59。這樣,原大殿頂層由十五檁變?yōu)槭粰_。兩內(nèi)金柱間抬梁保留原有形制,參考雙桂堂三層舉架數(shù)據(jù),檐步舉架、下金步舉架、中金步舉架、上金步舉架、脊步舉架分別取0.58、0.59、0.59、0.59、0.60。結構復原如圖19、圖20 所示。

圖19 大殿明間橫剖面復原示意圖

圖20 大殿明間縱剖面復原示意圖
5.2.3 建筑外觀
(1)外檐柱
通過前文分析,銀杏堂大雄寶殿檐柱及一重檐檐口未作改變,本次復原研究中沿用原有樣式。
(2)墻體及門窗
通過現(xiàn)狀勘察,銀杏堂大雄寶殿一層山墻和后檐墻為青磚墻,以上則為竹編墻白灰抹面。本次復原過程中,一層墻體保持不變,其余均按竹編墻白灰抹面恢復。關于門窗,繼續(xù)沿用現(xiàn)有花格門窗。
(3)屋頂
寺院大殿屋頂多采用歇山形式,如前文所提及的淶灘二佛寺下殿、南岸區(qū)大佛寺五佛殿均為三重檐歇山頂屋面。根據(jù)現(xiàn)狀勘察及口述歷史的調(diào)研,在降層改造過程中并未對屋頂形式進行改變。所以,在復原銀杏堂大殿建筑外觀時,仍采用重檐歇山頂形式。
(4)屋頂裝飾
通過銀杏堂大殿與雙桂堂大殿的外觀對比,兩殿在屋頂裝飾的形制、工藝和用材上基本相同,如小青瓦屋面、貼瓷片的脊飾,木質(zhì)封檐板、博封板等。
綜上所述,銀杏堂大殿外觀復原如圖21所示。

圖21 大殿正立面復原示意圖
6 結語
銀杏堂作為重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寺院建筑群歷史悠久,建筑保存完好,是重慶市宗教建筑、文物、藝術方面重要的文化遺產(chǎn),具有較大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和旅游價值。對銀杏堂大雄寶殿的復原研究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其成果可為后期大雄寶殿的復原提供圖文資料和研究思路,呈現(xiàn)大殿在降層改造前的原貌,重現(xiàn)其清晚期的原貌。在本次復原研究過程中,由于缺乏直接的數(shù)據(jù)支撐,而只是根據(jù)現(xiàn)有建筑柱網(wǎng)、開間、進深、檐柱高及建筑遺存木構架遺留下來的痕跡,并結合梁平雙桂堂大雄寶殿的對比分析進行復原嘗試,難免存在疏漏之處,后續(xù)研究可結合相關數(shù)據(jù)進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