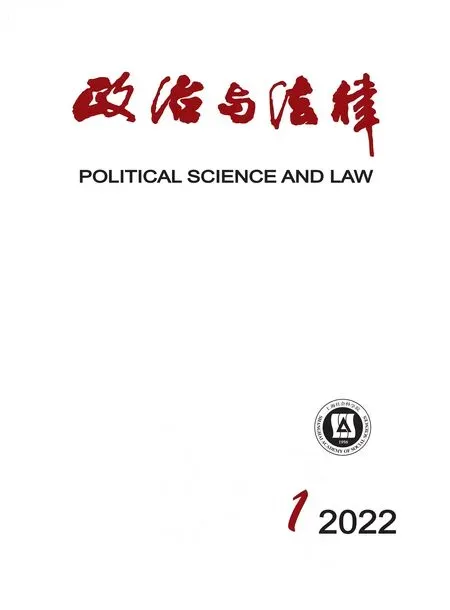論微罪體系的構建*
——以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研究為切入點
李 翔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 200044)
自1997 年我國《刑法》全面修訂以來,除了一個單行刑法外,我國《刑法》共經歷了11 次修訂,新增209 個條文,其中新增法定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輕罪”共計28 個。據此,有學者認為,我國刑事立法在整體上表現為“‘輕重并進,重罪為主’,輕罪制度并未成為立法主線”〔1〕冀洋:《我國輕罪化社會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與批評》,載《東方法學》2021 年第3 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輕重并進”的立法進程中,以《刑法修正案(八)》醉駕入刑為標志,截至《刑法修正案(十一)》,立法者先后設立了多個法定最高刑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包括拘役)的罪名,包括危險駕駛罪、妨害安全駕駛罪、危險作業罪、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代替考試罪、高空拋物罪,加上原有的侵犯通信自由罪和偷越國(邊)境罪,現行刑法中法定最高刑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罪名共有八個。如果說法定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是“輕罪”,那么這些法定最高刑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罪名可以被稱為“微罪”。以這些罪名為基礎,我國刑事立法正在形成一個有別于傳統輕罪體系的“微罪體系”,這些微罪的罪名數量雖然不多,但是適用量很大,微罪入刑逐漸成為我國刑事立法的新趨勢。
當前的八個微罪中,最具爭議的當屬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主張廢除者有之,主張修改者(提高入罪門檻)亦有之。隨著《刑法修正案(十一)》又增設數個微罪,關于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的存改廢之爭,逐漸上升為對微罪入刑的不同立場。一方面,勞教制度廢除后,原屬勞教規制的微罪行為面臨著向刑法或行政法的分流;另一方面,隨著“技術風險的日益擴散”〔2〕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載《中國社會科學》2007 年第3 期。,眾多新生危險源也不斷催生新的微罪行為。不少學者或是基于刑法的價值理念和制度功能〔3〕參見袁林、姚萬勤:《用刑法替代勞教制度的合理性質疑》,載《法商研究》2014 年第6 期。,或是基于對刑法一般預防功能的質疑〔4〕參見冀洋:《我國輕罪化社會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與批評》,載《東方法學》2021 年第3 期。,反對微罪入刑的正當性,進而主張多元社會治理。然而,事實上,提倡多元社會治理與微罪入刑并不沖突。微罪入刑并非“無原則、無標準”〔5〕陰建峰、袁慧:《后勞教時代微罪入刑問題探析》,載趙秉志主編:《刑事法治發展研究報告》(2016—2017 年卷),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第72 頁。,而是將部分確有必要納入刑法規制范圍的法益侵害行為予以入罪。有鑒于此,筆者于本文中旨在通過對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的分析,回應關于微罪入刑正當性的質疑,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微罪體系構建的方案。
一、微罪入刑的正當化根據
理論層面上,批判微罪入刑的核心論點就是刑法謙抑性。這一概念由國外學者提出,德國刑法理論則將其表述為“輔助性的法益保護”,即“在全部手段中,刑法甚至只是應當最后予以考慮的保護手段”〔6〕Roxin/Greco,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5.Aufl.,§ 2 Rn.97.。刑法的謙抑性主要從兩個層面對刑事立法進行限制:第一,刑法只能針對侵犯法益的行為,法益概念具有立法批判的功能〔7〕參見張明楷:《論實質的法益概念——對法益概念的立法批判機能的肯定》,載《法學家》2021 年第1 期。;第二,即便確認行為侵犯了法益,也只有當輕緩手段不能提供充分的保護時,才允許動用刑法。前者強調的是刑法的法益保護原則,后者則是強調刑事立法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以此為依托,有學者提出一種“微罪非犯罪化思維”〔8〕賈學勝:《非犯罪化與中國刑法》,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21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版,第512 頁。。然而,在筆者看來,微罪入刑與法益保護原則和比例原則并不沖突。
(一)微罪入刑并不違反法益保護原則
1.微罪入刑符合自由主義的法益概念
拋開關于法益立法批判功能的種種爭論,微罪入刑與自由主義的法益概念也不沖突。根據法益理論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羅克辛的表述,所謂法益,指的是“對于個體的自由發展、基本權利的實現、以及以此為目標所構建的國家制度的正常運轉所必須的全部事實情況和目標設定”〔9〕Roxin/Greco,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5.Aufl.,§ 2 Rn.7.,這種法益概念意在維護刑法的自由保障機能。就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而言,本罪意在保護道路交通安全,并借此反射性地保護了“其他道路交通參與者免受不適格的司機的影響”〔10〕MüKoStGB/Pegel,3.Aufl.2019,StGB § 316 Rn.1.。道路交通安全對于現代社會中的每個公民的自由發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它無疑是合格的法益。
除了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以外,其他微罪從法益保護的視角來看也無可指摘。現行刑法的另外7 個微罪中,妨害安全駕駛罪和危險作業罪所保護的法益分別是道路交通領域和安全生產領域的公共安全,這種公共安全最終可以歸結為對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和財產的保護;侵犯通信自由罪的保護法益是通信自由,這恰恰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之一;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和代替考試罪的保護法益分別為身份證件的管理秩序和公平的考試選拔秩序,這兩種制度都是當前我國社會所必須的,與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均為合法的法益。高空拋物罪相對特殊,《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一審稿將其規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但二審稿卻將本罪移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并由具體危險犯改為情節犯。因此當前本罪的保護法益為“社會管理秩序中的公共秩序”〔11〕彭文華:《〈刑法修正案(十一)〉關于高空拋物規定的理解與適用》,載《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1 期。,具體而言,是禁止從高空拋擲物品的公共秩序。由于這一公共秩序最終服務于對公眾生命、健康、財產以及安全感的保障,因此也不違背自由主義的法益概念。
2.法益保護原則不排斥抽象危險犯
法益保護原則并不要求只有在侵犯法益的情況下才產生刑事責任,在抽象危險犯中,只要以法益保護作為刑事立法的動機就足夠了。法益理論反對的是一種與法益無關的對行為價值和思想價值的保護。〔12〕Vgl.Roxin/Greco,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5.Aufl.,§ 2 Rn.68.不僅如此,以自由主義為思想淵源的法益理論,其實本身就具有“不自由”的一面,“與貫徹法益保護的關切相應的,就是讓刑事構成要件盡可能地擴大和沒有漏洞,不僅是法益受損的情況,而是要將發生危險和所有的在前階段都納入其中”〔13〕Roxin/Greco,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5.Aufl.,§ 2 Rn.12a.,因為“法益的問題就是刑法的任務問題。任務意味著一種好處、一種利益;換句話說,法益所關涉的是動用刑法對于潛在的受害人或者說全體公民的好處。從這種視角來看,在發生導致災難性后果的嚴重行為的場合,等待就顯得不合理、輕率”。〔14〕Roxin/Greco,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5.Aufl.,§ 2 Rn.12b.
當前主張廢除或修改(提高入罪門檻)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的主要理由是該罪已經成為所有犯罪中的“頭號”罪名,數量之大,已經不能被容忍,周光權教授認為,其“每年將30 萬余人打上罪犯的烙印,使數萬家庭陷入窘境”。〔15〕劉嫚:《危險駕駛罪排刑案首位,人大代表建議適時強制安裝酒精檢測裝置》,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39578251804098 7&wfr=spider&for=pc,2021 年5 月16 日訪問。然而,犯罪數量多,不是廢除或提高入罪門檻的理由。本罪案件數量多,主要是由于立法上將其設計為抽象危險犯,不要求對道路交通安全造成具體危險即可構成本罪。這一立法設計有其刑事政策意義。眾所周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一審稿和二審稿規定:“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或者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處拘役,并處罰金”。這種情節犯的設計卻遭到普遍質疑,“讓對‘從眾治醉’普遍支持的公眾感到一絲困惑”,因為它“留下了一個模糊地帶”,“可能被某些特殊人群惡意鉆空子,出現‘因人而異’的判定”〔16〕王松苗:《醉駕入刑要杜絕“模糊上路”》,載《人民日報》2011 年5 月12 日,第9 版。。正是為了避免出現司法不公的現象,最后的定稿才將其設置為抽象危險犯。當前理論和實踐通過“情節顯著輕微”或所謂的“抽象危險犯的實質考察”給醉駕“松綁”的做法,均不符合抽象危險犯的基本原理,其本質是試圖將本罪變為具體危險犯或情節犯,從而提高“入罪門檻”、減少醉駕案件。這種做法不僅置立法目的于不顧,而且置“公共安全”于不顧,法益保護原則也從來不曾為這種做法提供過正當性。
3.保護社會公眾的安全感并不違反法益保護原則
長期以來,我國“醉酒駕車犯罪呈多發、高發態勢,嚴重危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17〕白龍:《醉酒駕車罪當幾何》,載《人民日報》2009 年9 月9 日,第6 版。,因醉駕而引發的重大交通事故頻頻見諸報端,例如“南京張明寶醉酒駕車案”“成都孫偉銘醉酒駕車案”“廣東黎景全醉酒駕車案”等等。這些因醉酒駕車所引發的惡性案件,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引發了醉駕入刑的呼聲。
在此背景下,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的立法設計反映了刑事立法的宣示或者象征意義,在不安社會狀態下為公眾提供象征性的安全感和情感歸宿感。法益理論雖然反對將感情作為刑法的保護對象,但承認在個人的安全感受到某些行為損害時,可以動用刑法。理由在于,“不害怕他人或者不受他人的歧視是一種自由和平的共同生活的前提條件”,這體現在,對安全感的損害會導致“那些不得不擔心自己安全的人,放棄一些他們本來可以無憂無慮地從事的活動”〔18〕Roxin/Greco,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5.Aufl.,§ 2 Rn.27.。刑法分則的多個罪名都體現了對公眾安全感的保護,例如侮辱罪、誹謗罪,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盜竊、侮辱、故意毀壞尸體、尸骨、骨灰罪等。當醉酒駕駛行為已經嚴重到損害社會公眾對道路交通安全的信心,以至于社會公眾必須付出額外的成本,或者投入額外的小心,才敢于參與道路交通時,保護公眾的安全感,重建公眾對道路交通安全的信心,就是一個法治國家的合法任務。對此,法益保護理論并不構成障礙。
4.微罪入刑不等于象征性立法
象征性立法是現代刑事立法的一個痛點,因為其并不發揮具體的保護作用,而是為了“表達立法者的某種姿態與情緒、態度與立場”〔19〕劉艷紅:《象征性立法對刑法功能的損害——二十年來中國刑事立法總評》,載《政治與法律》2017 年第3 期。,象征性立法“通過可預見的無效率的法律,來制造一種印象,即正在采取行動來打擊不受歡迎的狀況和行為”〔20〕Roxin/Greco,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5.Aufl.,§ 2 Rn.37.。象征性刑法是對法益保護原則的背離,但微罪入刑有所不同。象征性立法的一大特點就是相關罪名在司法實務中適用率極低,但微罪并非如此。以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為例,本罪的司法適用率極高,甚至成為“頭號”罪名,無論如何都談不上“象征性”,而是極具“實用性”。除此之外,其他微罪的適用率也不低。反而沿襲自1979 年《刑法》的侵犯通信自由罪適用率極低。〔21〕筆者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庫中檢索到,除了危險作業罪、高空拋物罪和妨害安全駕駛罪因入罪時間尚短而案件數量少之外,截至2021 年5 月14 日:標題中包含“代替考試罪”字樣的判決書有285 份,標題中包含“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字樣的判決書有422 份、標題中包含“偷越國(邊境)罪”字樣的判決書有2925 份,這些微罪的適用率遠高于“幫助恐怖活動罪”等典型的象征性立法,而侵犯通信自由罪僅5 份判決書。這反映出,我國近幾年入刑的微罪,并不是象征性立法的產物,而是服務于真實的實踐需求。
(二)微罪入刑并不違反比例原則
法益理論本身具有“不自由”的一面,它只能說明刑事立法的目的正當,單憑法益無法完整地劃定刑事立法的界限〔22〕參見陳璇:《法益概念與刑事立法正當性檢驗》,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3 期。,因此,反對微罪入刑的學者不得不援引憲法上的比例原則。比例原則起源于德國公法領域,因其立足于法治國原則和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因此效力輻射到所有法律領域〔23〕Klatt/Meister,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JuS 2014,193.。根據德國通說,比例原則的審查分為五個步驟〔24〕Vo?kuhle,Grundwissen -?ffentliches Recht: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JuS 2007,429(430).:第一,確定相關措施所追求的目的;第二,審查該目的是否合法,在法律上能否被允許;第三,審查所使用的手段是否能夠實現預期的目的(有用性);第四,審查是否不存在其他損害更輕微的手段(必要性);第五,審查所使用的手段與目的是否相稱(相稱性,或稱狹義的比例原則)。其中,前兩個步驟僅僅涉及抽象層面對目的正當性的審查,反映到微罪入刑中,通常很快可以得到肯定。困難集中在后三個步驟。當前部分學者所提出的:刑法治理“易導致出現高成本和低效益”〔25〕袁林、姚萬勤:《用刑法替代勞教制度的合理性質疑》,載《法商研究》2014 年第6 期。,“刑法的一般預防只是一種‘靠天收’的最原始農耕模式”〔26〕冀洋:《我國輕罪化社會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與批評》,載《東方法學》2021 年第3 期。,以及過度犯罪化造成案件數量激增、耗費大量資源、罪犯改造效果不佳等〔27〕參見齊文遠:《修訂刑法應避免過度犯罪化傾向》,載《法商研究》2016 年第3 期。,歸根結底是認為刑罰不僅本身就是一種“惡”,而且在社會治理方面顯得無效率,實質上都是借由有用性、必要性或相稱性來批判犯罪化。這些批評有其合理性,對于理性把握微罪入刑、避免刑法萬能主義具有重大意義,但是,如果因此就全盤否定微罪入刑的正當性,則未免因噎廢食。
1.有用性:實現預期的社會治理效果
討論微罪入刑是否能夠實現預期目的,必須立足于微罪入刑的實踐效果,任何不顧實踐效果而主張“刑法無用論”的,都是不負責任的表現。那么,微罪入刑的實踐效果如何呢?以最為典型的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為例,據統計,醉駕入刑僅三年,我國機動車年均遞增1500 萬輛、駕駛人年均遞增2000 萬人、道路里程年均遞增12 萬公里,但全國發生涉及酒駕、醉駕導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起數和死亡人數較醉駕入刑前同比分別下降25%和39.3%〔28〕張洋:《醉駕入刑有效果法治入心顯力量》,載《人民日報》2014 年10 月20 日,第11 版。;到2020 年,每排查百輛車的醉駕比例比醉駕入刑前減少70%以上。醉駕入刑十年,在機動車、駕駛人數量保持年均1800 萬輛、2600 萬人的高速增長情況下,全國交通安全形勢總體穩定,酒駕醉駕肇事導致的傷亡事故相比上一個十年減少了2 萬余起〔29〕程林杰、劉哲、黃亦程:《“醉駕入刑”十年間減少兩萬余起傷亡事故》,載《人民公安報》2021 年4 月29 日,第2 版。。除此之外,十年來,“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的觀念深入人心,拒絕酒后駕車成為社會共識。以上統計數據和可以感受到的社會觀念的轉變,都充分證明了醉駕入刑能夠維護道路交通安全。醉駕入刑的例子說明,微罪入刑對于社會治理有其積極意義。在理性把握的前提下,微罪入刑可以起到良好的社會治理效果,不應不加甄別地全盤否定微罪入刑的有用性。
2.必要性:不存在能夠達到相同效果的輕微手段
審查比例原則中的必要性,需要先假設若干個同樣能夠實現目的的替代手段(這些手段實際上未被采用),然后去判斷:第一,所采用的手段是否能夠達到替代手段的同樣效果,這要求比較替代手段和所采用的手段對于目的的實現所具有的效果;第二,在此基礎上,所采用的手段造成的損害是否小于(至少要求不超過)替代手段所造成的損害,這要求確定所采用的手段和替代手段各自對憲法原則所造成的損害,并對它們進行比較。〔30〕Vgl.Klatt/Meister,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JuS 2014,193(195).以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為例,在此,所采用的手段即為當前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的刑事條款,而可能的替代手段主要有:(1)廢除本罪,完全以行政處罰進行規制(例如罰款、扣留或吊銷駕照、行政拘留等);(2)提高入罪門檻,主要是增加“不能安全駕駛”的要求。
(1)刑罰與行政處罰的比較
單論所造成的損害而言,與刑罰相比,行政處罰的確更為輕緩。然而,損害大小的比較只是必要性審查的一個方面,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不同手段的效果的比較。如前所述,就醉酒駕駛而言,“入刑”的效果是顯著的,可謂立竿見影,那么相對輕微的行政處罰是否具有同樣效果呢?筆者對此持否定態度。理由在于:從我國的社會治理實踐來看,醉駕入刑前,行政處罰在打擊酒后駕車方面的效果并不好,每年因酒后駕車引發的交通事故達數萬起,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均超過數萬人,造成死亡的交通事故中,50%以上都與酒后駕車有關〔31〕參見張海燕:《尊重生命維護交通安全莫讓酒駕猛于虎》,http://www.chinanews.com/auto/2011/05-24/3062925.shtml,2021 年5 月15日訪問。。
醉駕應當適用行政罰或是刑罰的爭議并非我國獨有,德國在醉駕入刑過程中也發生過類似的討論。1961 年前,根據當時的德國《道路交通許可條例》(StVZO)第71 條結合第2 條,醉酒駕車僅僅是一種違法行為,可以被處以罰款或者拘留。德國聯邦議會交通委員會第一次建議增設醉酒駕駛罪時,該議案在聯邦議會未獲通過。然而,在此之后,與酒精有關的交通事故大量增加,在涉及死亡或受傷的事故中,駕駛人員受酒精影響的案件數量的比例增加了50%以上。因此,德國在1957 年第四次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議,“因飲酒而不適合駕駛機動車的,應以輕罪論處”,并于1959年第五次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議再次重申:“會議非常關切地注意到,酒精作為嚴重事故原因的比例高得令人不安。有必要向公眾提供有關這些危險的持續信息。”〔32〕BT-Drs III/2368,Entwurf eines Zweiten Gesetzes zur Sicherung des Stra?enverkehrs,S.23.有鑒于此,德國在1961 年的第二部《道路交通安全法》草案中再次提出增設醉酒駕駛罪,并獲得通過。
此外,事實上,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目前醉駕的法定刑配置并不高,入罪門檻也不算低。醉駕入刑所造成的影響之所以為人詬病,主要是因為未能合理地構建微罪的處遇措施(例如犯罪附隨后果),導致醉駕者被打上犯罪人標簽后,就會遭受超出刑罰本身嚴厲程度的后果〔33〕參見黃云波:《微罪犯罪附隨后果有待科學化》,載《檢察日報》2017 年7 月12 日,第3 版。。這種情況完全可以通過科學構建微罪處遇措施而得到改善。
綜上,一方面,行政處罰對于醉駕這一世界性難題的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在機動車高度普及的現代社會,單憑行政處罰難以遏制醉駕蔓延;另一方面,當前醉駕入刑的影響可以通過構建合理的微罪處遇措施而得到緩解。因此,不能簡單地因為存在更為輕緩的行政處罰手段,就得出醉駕入刑不具有必要性的結論。
(2)抽象危險犯與具體危險犯的比較
除廢除論外,還有學者主張在本罪的成立條件上增加“不能安全駕駛”要素,即將本罪修改為“醉酒后,在道路上不能安全駕駛機動車的”〔34〕周光權:《建議修改“醉駕”犯罪標準,有效減少社會對立面》,https://news.tsinghua.edu.cn/info/1578/85038.htm?ivk_sa=1023197a,2021 年5 月16 日訪問。,從而使本罪從抽象危險犯變為具體危險犯。令人費解的是,增加了“不能安全駕駛”之后,本罪就成了具體危險犯嗎?德國刑法中關于醉駕的條款存在“不能安全駕駛”的表述,但本罪在德國被認為是抽象危險犯,“不能安全駕駛”是對行為人狀態的限定,以呼氣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作為判斷標準〔35〕參見林東茂:《交通犯罪》,載《酒醉駕車刑法問題研析》,元照出版公司2016 年版,第6-7 頁。,而不要求行為造成具體危險。因此,上述的修改方案似乎也不是最佳方案。假如真要改成具體危險犯,不如直接增加“危及道路交通安全的”。
然而,改為具體危險犯至少帶來兩個現實問題:第一,不具有可操作性,對具體危險的要求將極大地增加執法成本;第二,產生模糊地帶,導致公眾對執法公正的質疑。因此,將本罪改為具體危險犯,所產生的損害并不明顯小于抽象危險犯;并且就治理醉酒駕駛的效果而言,具體危險犯的效果肯定不如抽象危險犯。故而,這一替代手段也不能否定當前所采用手段的必要性。
3.相稱性:目的重要性足以將干涉正當化
比例原則的審查的最后一個步驟是相稱性。作為比例原則審查中的核心,相稱性審查的核心在于權衡,即利益平衡,它需要“對眾多對立的憲法價值進行權衡。”〔36〕Klatt/Meister,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JuS 2014,193(196).權衡的目的在于“確保因國家干預而產生的負擔不會與所追求的目標不相稱。對基本權利的干涉越嚴重,對干涉之正當性的憲法上的要求就越高。更確切地說:對基本權利的干涉越嚴重,對所追求的目的的重要性要求就越高。”〔37〕Klatt/Meister,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JuS 2014,193(197).為此,相稱性的審查共有三個步驟:首先,確定具體情況中的干涉強度;其次,討論干涉所追求的目的在具體情況中的重要性;最后,通過分析干涉強度和目的重要性的關系,審查目的的重要性是否能夠將干涉的強度正當化。為了使得審查有說服力,可以將目的重要性分為“輕微”“中等”“重大”三個等級,干涉的強度同樣如此。〔38〕Klatt/Meister,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JuS 2014,193(197).
以醉酒駕駛為例,首先,數據表明,醉酒駕車是引發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現代社會的一個重大危險源。醉駕的普遍性、后果的嚴重性以及發生后果的現實危險性,決定了預防醉駕、減少醉駕發生這一目的的重要性屬于“重大”。
其次,醉駕入刑的干涉主要表現為:一個月到六個月的拘役和罰金,以及相應的犯罪附隨后果。就刑罰內容本身而言,與國外相比,我國為本罪配置的法定刑絕不算嚴厲。醉駕入刑的干涉嚴重性主要體現在犯罪的附隨后果,例如,“醉駕將納入個人信用記錄,貸款、消費受到限制”“不能得到保險公司理賠”“吊銷駕駛證、不得重新取得駕駛證”“特定職業資格被吊銷,個人不能報考國家公務員,當兵或報考軍校無法通過政治審查,被用人單位開除勞動合同,公職人員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等”〔39〕劉嫚:《危險駕駛罪排刑案首位,人大代表建議適時強制安裝酒精檢測裝置》,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395782518040987&wfr=spider&for=pc,2021 年5 月16 日訪問。。個人貸款消費受到影響,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醉駕入刑,而在于醉駕所反映出來的行為人的社會誠信缺失;不能獲得保險理賠,本質上也不是由于醉駕,而是由于行為人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使得保險公司負擔了過多的義務,醉駕入刑導致保險公司免賠,恰好平衡了雙方的合同義務;參軍、報考公務員無法通過政審,實質原因也不在于醉駕入刑,而是醉駕反映出行為人不具有從事相應職業的政治素養和道德品質。因此,醉駕入刑的干涉程度遠遠達不到“重大”的程度,最多屬于“中等”。
故而,在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中,重要性屬于“重大”的目的,完全可以將最多達到“中等”的干涉正當化,符合相稱性的要求。退一步說,即便真的認為醉駕入刑的干涉達到了“重大”的程度,也可以通過前述優化微罪處遇措施的方式,對這種干涉予以緩和,使之達到能夠被正當化的程度。
綜上所述,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既不違反法益保護原則,也不違反比例原則,符合刑法的謙抑性,這一微罪具有正當性。同理,微罪入刑只要符合法益保護原則和比例原則,也將具有正當性。全盤否定微罪入刑的正當性,是一種忽略現實的片面觀點。
二、微罪體系的立法設計
“一個有良知的立法者必須意識到,通過刑罰,他對人進行了一種特別的干涉”〔40〕Roxin/Greco,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5.Aufl.,§ 2 Rn.2.,肯定微罪入刑的正當性,并不意味著立法可以動輒對危害社會的行為發動刑罰,否則便陷入了反對論者所憂慮的“刑法萬能主義”。“微罪入刑的正當性”的實現,依賴于理性的立法設計。如前所述,認定微罪行為應當經過法益保護原則和比例原則的雙重審查,而這一準則反映在立法上就是:微罪的成立條件應嚴守明確性;微罪的法律后果應呈現系統性。
(一)微罪的成立
為維護微罪體系的構建正當性,必須明確劃定輕微社會危害性行為的犯罪化邊界。以現有的八個微罪為觀察樣本,結合微罪體系應然的價值展開,筆者認為,應當嚴守微罪屬于“非實害犯”的界定,并且把握只有故意犯罪才能構成微罪的原則。
1.微罪的類型為“非實害犯”
“理論與實務在解讀刑法分則具體罪名構成要件時,習慣于貼上行為犯、結果犯、舉動犯、實害犯、危險犯(包括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的標簽。”〔41〕陳洪兵:《中國式刑法立法模式下的結果犯與實害犯》,載《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5 期。界定某個或一類罪名的犯罪類型的意義在于,犯罪類型能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罪名的成立條件、處罰范圍等。微罪應當嚴守“非實害犯”的犯罪類型。
(1)微罪的刑罰配置決定了其不能包攝實害犯
“犯罪因為所侵犯的社會利益不同而存在由重到輕的次序排列階梯,因此,立法者應該將刑罰也按由重到輕的次序排列階梯,并將重刑分配于重罪,輕刑分配于輕罪,使刑序與罪序相結合。”〔42〕[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 年版,第66 頁。貝卡利亞的這一論斷對現代刑法的展開仍然很有意義:首先是刑事不法性應形成梯度;其次是犯罪梯度與刑罰梯度應當形成對稱。從法定刑配置來看,微罪被置于刑罰梯度的底端,則可以推知微罪行為的刑事不法性也最低。體現在犯罪成立條件上就是,微罪不能包攝實害犯這一犯罪類型。原因是,對法益造成現實侵損的行為才構成實害犯,刑事可非難性較強,因此自然也會配備較高的刑事處罰,而這就與微罪的犯罪內涵及其體系地位形成壁壘,不可能互通。
簡言之,微罪是在風險社會背景下誕生的、以完成特定刑法任務為價值追求的一類罪名。通過“非實害犯”的這一界定,以“法定最高刑低于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為標志的微罪滿足了犯罪梯度與刑罰梯度的對稱性,才符合罪刑均衡原則。
(2)微罪以同一法益的“上一位階犯罪”為參照物
至2021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出臺,我國刑法已形成“刑法、補充規定以及刑法修正案”的規模體系。有學者認為,“刑事立法上懲治犯罪行為環節的前移,是對風險社會的立法回應,危險犯是其中的重要立法形式”〔43〕涂龍科:《經濟刑法中危險犯的立法問題研究》,載《法學雜志》2012 年第8 期。。筆者認為,我國刑法的修正趨勢是,對同一法益的保護設計了“抽象危險犯、具體危險犯、實害犯”的階梯式犯罪類型體系。在微罪成立的立法設計方面,保護同一法益的“上一位階犯罪”可以作為其上限之參照物。
以道路交通安全領域為例,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設立促成了“抽象危險犯、具體危險犯、實害犯”的罪刑體系維度的充實性。首先,筆者認為醉駕型危險駕駛罪屬于抽象危險犯。特定的行為(醉酒狀態下駕駛機動車)出現,危險伴生,血液中或者呼氣中酒精含量達到或者超過一定標準而駕駛機動車,立法即推定為危險狀態出現。進言之,危險駕駛罪規制的抽象危險“尚無具體危及的對象、尚未達到具體危險,距離實害結果則更是相對較遠”〔44〕劉軍:《危險駕駛罪的法理辨析》,載《法律科學》2012 年第5 期。。由此,我國《刑法》通過第133 條交通肇事罪與第115條第2 款過失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33 條之一危險駕駛罪、第114 條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險犯)以及第115 條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實害犯)這五個罪名,形成了從危險到實害、層層遞進的道路交通安全領域規制體系。
那么,該領域的立法是否已經在各個維度上達成完滿了呢?筆者認為不能這樣說。因為“與醉酒(在法益侵害程度上)相當的還有吸毒駕駛,醉酒駕駛與吸毒駕駛在罪與非罪的區別在法理上沒有任何依據,之所以在實踐中出現這樣的差別,則主要是受制于現實中該行為的多發性與立法的急切必要性。”〔45〕參見高銘暄:《風險社會中刑事立法正當性理論研究》,載《法學論壇》2011 年第4 期。在未來,立法者仍有可能通過設置新的微罪以保護道路交通安全這一集體法益,但對構成要件的設計仍是要以“對于同一法益的上階犯罪”為參照。
對于具體危險犯、情節犯同樣如此。微罪體系中,我國《刑法》第133 條之二妨害安全駕駛罪是典型的具體危險犯,保護法益是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其相對應的具體危險犯是我國《刑法》第114 條。具體危險犯的成立,是要求危害行為有危險現實化的高度可能性,介于抽象危險與實害之間。〔46〕參見王永茜:《論現代刑法擴張的新手段——法益保護的提前化和刑事處罰的前置化》,載《法學雜志》2013 年第6 期。簡言之,同樣是處罰道路交通安全法益的具體危險犯,根據罪刑相當原則應當,妨害安全駕駛罪中行為實現的“危險”應當比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險犯)中的“危險”較輕緩。還可以展開類比的是我國《刑法》第134 條之一危險作業罪與第134 條重大責任事故罪形成的具體危險犯與實害犯的階梯關系。在觀察情節犯時,可以以高空拋物罪為代表。該罪中的“嚴重的情節”與我國《刑法》第115條規定的“實害”相比應當更輕緩。具言之,可以從行為人的動機、拋物場所、拋擲物的情況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層面呈現行為危害程度的梯度。此外,此種“情節嚴重”還應當與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形成壁壘。
2.微罪的主觀罪過只能是故意
根據本文對微罪體系的觀察,發現八個罪名無一例外都屬于“故意犯罪”。那么,這是立法偶然的形式巧合,還是微罪實質的體現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后者。微罪體系只能由故意犯罪構成,不能設置主觀罪過為過失的微罪。
(1)濫設過失犯是對刑法人權保障機能的損害
過失犯罪處罰范圍的擴大意味著人類行為自由界域的限縮,刑法保障人權的機能被刑法保衛社會的功利需要不斷蠶食。面對人類社會撲面而來的各種信息,人類受自身認識局限性的制約,不可能像機器那樣永遠保持精神的專注和行動的審慎,人類自身具有的局限性決定了其行動時疏忽在所難免。尤其是,“刑法的任務是保護人類社會的共同生活秩序。沒有一個人能夠永遠與世隔絕地生活,相反,所有的人均基于其生存條件的要求,需要生活在一個彼此交往、合作和相互信任的社會里。”〔47〕[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上)》,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7 年版,第1 頁。換言之,刑法作為社會治理中的后置手段,不能濫行犯罪化的功能。若刑法可以動輒將對法益造成輕微損害的過失行為納入犯罪圈,則人們在開展社會生活的過程中將毫無安全感,因為不知道自己的哪一個未加防范的輕微行為會被認定為犯罪。過失論發展至今,已經形成了“以對預見可能性的抽象判斷取代預見可能性的具體判斷”的新新過失論,〔48〕參見陳興良:《過失犯論的法理展開》,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2 年第4 期。因此更不能將此種依托于抽象認定的“過失”納入微罪的主觀罪過范圍內,否則將不當擴大微罪的處罰范圍、損害其犯罪化的正當性。
以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為例,有學者曾以危險犯也是結果犯為立論的基點,通過論證危險駕駛罪的主觀方面為故意具有不恰當性,主張危險駕駛罪為過失危險犯。〔49〕劉憲權、周舟:《危險駕駛罪主觀方面的刑法分析》,載《東方法學》2013 年第1 期。甚至持“過失說”的觀點不在少數。〔50〕參見馮軍:《論〈刑法〉第133 條之1 的規范目的及其適用》,載《中國法學》2011 年第5 期;付曉雅:《危險駕駛罪的主觀要件研究》,載《當代法學》2014 年第5 期;梁根林:《〈刑法〉第133 條之一第2 款的法教義學分析——兼與張明楷教授、馮軍教授商榷》,載《法學》2015 年第3 期,等等。筆者不認同“過失說”的觀點。危險駕駛罪的主觀方面應是故意,其內容表現為行為人對危險駕駛行為有認識并放任或希望危險駕駛行為的抽象危險發生。首先,如果認為該罪是過失犯罪,那么對于以“結果預見可能性”為中心的過失犯罪理論而言,就只能將預見的對象定位于虛無縹緲的抽象危險,這顯然是有害于刑法人權保障機能的。進言之,從實務角度看,設若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主觀罪過是過失,將引起危害行為入罪的司法便利性、甚至是恣意性。其次,將危險駕駛罪的主觀方面認定為過失將導致罪名體系混亂,不利于形成“過失實害犯、故意抽象危險犯、故意具體危險犯、故意實害犯”的罪刑體系。畢竟,這是刑法在道路交通安全領域十分精巧的罪刑維度設計。
那么,上述罪刑體系內是否還有“過失危險犯”維度的空間呢?筆者認為不然,在我國刑法體系中沒有過失危險犯存在的空間,〔51〕對上述觀點的具體反駁以及筆者觀點的展開,具體可參見李翔:《危險駕駛罪主觀方面新論》,載《法商研究》2013 年第6 期。因為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過失犯罪都是實害犯,也就是說“過失行為只有當造成了危害結果時,才能構成犯罪”。〔52〕王作富:《中國刑法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 年版,第168 頁。過失危險犯是一個有害的概念,是對罪刑法定原則與罪刑均衡原則的威脅。
(2)嚴守故意犯罪是限縮微罪處罰范圍的進路
有學者認為,“刑法修正案(十一)在第134 條之后增設第134 條之一危險作業罪,本罪是前置于重大責任事故罪(基本犯)的危險犯,責任人實施‘篡改、隱瞞、銷毀其相關數據、信息’‘依法責令停產停業而拒不執行’‘未經依法批準或者許可,擅自從事礦山開采’等行為對引發重大傷亡事故及其可能性的主觀罪過同樣是過失,因而屬于業務過失危險犯。”〔53〕冀洋:《我國輕罪化社會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與批評》,載《東方法學》2021 年第3 期。并且該學者借此對構建微罪體系開展了質疑與批判。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存在偏失,進而前述論者對微罪體系的批判似亦有所偏頗。首先,無論是依據法條之表述還是從法理上分析,危險作業罪的主觀都應該是故意。該學者基于危險作業罪與重大責任事故罪的法條表述相似性就得出主觀罪過的同一性,是未加深思的結論。實際上,“第xx 條之一”的立法設計本就不能說明前后兩個罪名在主觀罪過上的一致性。例如,我國《刑法》第133 條交通肇事罪屬于過失實害犯,而第133 條之一醉駕型危險駕駛罪就是故意抽象危險犯。前述兩個罪名的關系可以類比于醉駕型危險駕駛罪與交通肇事罪的關系,即前者是故意危險犯,而后者是過失實害犯。其次,建立在不當結論上的對微罪體系的批評同樣是不可取的,原因是嚴守故意犯罪正是限縮微罪處罰范圍的關鍵進路。筆者于本文中已經論述了構建微罪體系的正當性,此處不再贅述,且在微罪的立法設計層面,恰恰要通過對犯罪故意的嚴守完成微罪的“自我約束”——即犯罪化正當性的維持。
(3)嚴守故意的主觀罪過標準體現行刑銜接
微罪體系因其體系定位而直面行法與刑法銜接的課題。整體來看,微罪體系因其“中間性”而獲得了前置法與刑法的雙重支持。理由是,首先,微罪所保護的集體法益在受實害時將引起相應的刑事不法認定;其次,此種集體法益在未受到抽象危險侵損時同樣為行政法所不能容忍。因此在立法設計上,實害犯為微罪提供上限參照的同時,微罪亦受到銜接行政法的考驗。與自然犯主要致力于個人法益保護不同,法定犯側重于對社會秩序即集體法益的維護,大都基于保護秩序的需要而設定。”〔54〕孫國祥:《集體法益的刑法保護及其邊界》,載《法學研究》2018 年第6 期。微罪體系正是法定犯的集合,一般起于對行政違法的犯罪化。堅持故意的主觀罪過能夠體現行刑邊界。
“行政處罰責任與刑事責任同屬公法責任,而且在違法行為的責任上具有遞進性。”〔55〕參見楊小君:《行政處罰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第53-54 頁。轉引自解志勇、雷雨薇:《基于“醉駕刑”的“行政罰”之正當性反思與重構》,載《比較法研究》2020 年第6 期。行政違法側重于行為客觀上的危害性,一般不考慮違法行為人的主觀狀態。這一點恰與微罪的不法形成鮮明的邊界,因為刑事歸責要求主客觀的統一,認定行為人構成微罪必須經過對其主觀罪過的把握。進言之,部分行政違法行為,因其主觀上的“惡”而獲得刑法的否定性評價,進而其“不法性”發生躍遷,被劃入犯罪圈。這是微罪的主要來源,可以被稱為“質”的不法躍遷。〔56〕微罪的另一來源是,部分行政違法行為在不法的“量”上發生躍遷而被劃入犯罪圈,亦即前文所述的情節犯,筆者認為可以通過“非實害犯”的界定加以約束。對于這類“質”的不法躍遷,應受到主觀故意的限制,才不至于引起犯罪圈的無限放大,亦銜接了行政違法與刑事不法。有反對論者批判微罪的設置降低了刑法犯罪構成刑事違法性的要求,實則不然,微罪體系恰恰鮮明反映出了“犯罪階梯與刑罰階梯”的對稱性。因為“越是距離實害結果近的行為,就越是違法性重的行為,處罰也應該更重”〔57〕王永茜:《論現代刑法擴張的新手段——法益保護的提前化和刑事處罰的前置化》,載《法學雜志》2013 年第6 期。,從行政違法到微罪不法,一種路徑是“質”的不法躍遷,因行為人主觀之故意而致其刑事可非難性更高;另一種是“量”的不法躍遷,行為人從加重了危害行為之情節的角度引起了刑事違法性。
(二)微罪體系法律后果的系統配置
1.微罪輕緩化的法定刑設計
在嚴格把握輕微犯罪化邊界的同時,立法機關應當對微罪體系后果尋求最合理的配置。域外刑法對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大多秉持“根據刑事政策或社會變化及時修改刑法”的態度,對“醉酒”的標準也予以詳盡規定。英國1998 年《道路交通法》第4 條第2 款規定“在不適宜狀態下駕駛或企圖駕駛,可判決3 個月以下的監禁或2500 英鎊以下罰金,或者兩者并處,是否吊銷駕駛執照由法官決定。”在這之前,1991 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對因飲酒或者吸毒而駕駛車輛的,規定“應當被提起公訴被判處2 年以下的監禁刑罰,同時無其他特殊原因的,剝奪駕駛的期限不得少于2 年。”〔58〕參見趙秉志主編:《英美刑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版,第342 頁。德國規定了“酒后駕駛罪”:不論是故意還是過失,駕駛人因飲用酒或者其他麻醉品,導致不能安全駕駛交通工具的,處“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刑”。〔59〕參見《德國刑法典》,徐久生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220-223 頁。日本采取了兩種不同的規制模式,一種是根據駕駛人的實際情況判斷其是否屬于無法正常駕駛狀態的“醉態駕駛罪”,根據日本《道路交通法》第117 條之二第1 款的規定,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百萬日幣以下罰金;另一種是以駕駛人血液或呼氣中酒精含量為標準,當酒精濃度達到血液中每毫升0.3 毫克或者呼氣中每公升0.15 毫克時成立“飲酒駕駛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五十萬日幣以下罰金。〔60〕林東茂等:《酒醉駕車刑事問題研析》,載謝煜偉:《交通犯罪中的危險犯立法與其解釋策略》,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版,第21 頁。我國臺灣地區對醉酒駕駛予以嚴格規制。其“刑法”第185 條之三規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5 毫克以上”〔61〕林東茂等:《酒醉駕車刑事問題研析》,載林東茂:《交通犯罪》,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版,第6 頁。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的,“處2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 萬元以下罰金。”我國法對飲酒后駕駛機動車分為“飲酒駕駛”與“醉酒駕駛”,“飲酒駕駛”是指駕駛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在20mg/100ml 與80mg/100ml 之間,“醉酒駕駛”是駕駛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80mg/100ml。我國法將“醉酒駕駛”作為危險駕駛罪的構成要件,“飲酒駕駛”則按照行政違法行為處理。
從各國對飲酒后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輛的刑事規制可以看出,無論是入罪的酒精含量標準,還是法定刑的設計,我國刑法對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規制較為寬和,且我國“司法判決受傳統報應刑的影響,以彌補被害人損害為要旨,犯罪人積極彌補被害人損失,取得被害人諒解”,〔62〕賈長森:《醉駕刑罰完善之構想——以海峽兩岸比較為中心》,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 年第6 期。可以從輕處罰,司法實踐中宣告刑以三個月以下拘役刑為多數。參考德、日對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刑法規制,提高我國危險駕駛罪的刑罰標準,對整個道路交通安全體系大有裨益。
“輕刑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與當前我國社會民主文明的發展進程相契合。”〔63〕李翔:《論刑法修正與刑罰結構調整》,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 年第4 期。筆者認為,首先,對輕微犯罪行為在立法上依然要規定監禁刑(有期徒刑),與輕罪、重罪相區別,以一年有期徒刑為法定刑較為恰當;其次,還應當增設管制刑和資格刑,充分體現罪刑均衡原則;最后,應當考慮單獨設置罰金刑,其他國家對醉酒后駕駛機動車都是以監禁刑和罰金刑選科適用,我國也應當改革罰金刑適用程序,以更好地發揮罰金刑的作用。
首先,應當保留對微罪的監禁刑(有期徒刑)。雖行為人實施的輕微犯罪行為并非對公民或者公共法益具有緊迫、現實的巨大危險,主觀惡性不大,但也不可直接排除適用監禁刑罰(有期徒刑)。目前刑法擴張對其調整范圍的規制邊界,如果只設置程度較輕的刑罰種類,會導致其與行政處罰之間界限不清,降低刑法對一般人的威懾力。相較于行政拘留,刑法作為窮盡適用前置法之后的最后一道維護公平正義的防線,在手段的強制效果與懲罰效果上應當明顯重于行政處罰行為,所以在立法上對微罪設置一定限期的監禁刑(有期徒刑)是有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其次,考慮拘役刑和管制刑種的多樣選擇適用。“在我國刑罰朝向輕緩化有序發展的過程中,要著重調整輕刑的配置策略和適用方式,使得宣告刑結構進一步多樣化。”〔64〕李翔:《論刑法修正與刑罰結構調整》,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 年第4 期。增加對拘役刑、管制刑的選處設置,更加廣泛地將其適配于危害程度不高、情節輕微的刑事犯罪。拘役作為懲罰程度最輕的監禁刑,其1-6 個月相對較長的刑期在外觀上明顯區別于行政拘留。管制刑作為限制自由刑,使犯罪人在不脫離社會的情形下,對其進行教育改造,這種社會化教育“符合當前刑罰追求功利性價值的主流方向。”〔65〕李翔:《論刑法修正與刑罰結構調整》,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 年第4 期。之前,管制刑在司法實務中鮮少有用武之地,犯罪行為普遍被判處管制刑以上刑罰,“重刑主義”現象十分明顯,甚至當前依然有學者認為“目前刑法新增或修改的大部分條文仍是重罪條文,因而我國刑法呈現的是‘以重為主、輕重并進’的犯罪化趨勢”。〔66〕翼洋:《我國輕罪化社會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與批評》,載《東方法學》2021 年第2 期。事實并非如此,刑罰的輕緩化已經成為當前刑事改革方向,在目前的微罪刑罰結構中,加大對管制刑、拘役刑的適用更加符合寬和的刑事政策導向。
最后,考慮擴大罰金刑的單獨適用范圍。刑法在財產刑適用上主要就是“過于重視罰金刑的并科”〔67〕李翔:《論刑法修正與刑罰結構調整》,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 年第4 期。,雖然罰金刑“可以作為主刑的附加刑適用,也可以單獨適用”,但目前實務界更為重視罰金刑的附加刑地位,這可能“將某些犯罪從輕罪過度地拔高為重罪,從而造成輕罪與重罪的比例進一步失衡”。〔68〕王志祥、韓雪:《我國刑法典的輕罪化改造》,載《蘇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 年第1 期。危險駕駛罪并科適用罰金刑的規定,在導致實踐中刑罰處罰過重的同時,也難免有過分放大罰金刑作用之嫌。〔69〕賈長森:《醉駕刑罰完善之構想——以海峽兩岸比較為中心》,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 年第6 期。在目前輕刑化的導向下,“原本作為短期自由刑的一種有效替代刑,罰金刑可以有效規避自由刑的某些流弊,達到懲罰犯罪的目的”〔70〕李翔:《論刑法修正與刑罰結構調整》,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 年第4 期。,單獨適用罰金刑也足以實現懲治和預防情節輕微的犯罪的效果,“以罰金來替代短期自由刑已經成為法治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71〕趙秉志、金翼翔:《論刑罰輕緩化的世界背景與中國實踐》,載《法律適用》2012 年第6 期。德國與日本監禁刑與罰金刑的選科適用的規制方式,法律效果良好,德國雖然規定了很多并科適用罰金的條款,但是實務中很少有并科罰金的判例。因此,在立法上應考慮完善罰金刑的相關規定,對微罪規定選科適用罰金刑,對其他較重的罪可以規定并科罰金〔72〕李潔:《罰金刑適用若干問題研究》,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0 年第5 期。;在司法上要求審判人員增強單獨適用罰金的意識,統一罰金刑適用標準,“將罰金刑作為推動刑罰輕緩化發展的有力工具。”〔73〕李翔:《論刑法修正與刑罰結構調整》,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6 年第4 期。
2.微罪附隨后果的具體構想
縱然,“醉駕入刑”確有實效,但危險駕駛罪龐大的案件數量背后〔74〕筆者以“醉酒駕駛”為關鍵詞在北大法寶進行檢索,全國共有刑事案件1143402 件。其中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的案件共有628 件,以“交通肇事罪”定罪的案件共有29079 件,約占3%,以“危險駕駛罪”定罪的案件共有1114647 件,約占97%。,依然是短期自由刑的弊端體現,犯罪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處以短期刑罰的嚴峻性,也沒有意識到“犯罪產生的標簽效應,犯罪前科以及犯罪對行為人自身和家庭帶來的負面影響”〔75〕何榮功:《我國輕罪立法的體系思考》,載《中外法學》2018 年第5 期。。在肯定微罪體系構建的同時,司法機關也應當考慮對輕微犯罪行為定罪處刑所帶來的負面效果。筆者認為,可以單獨或并科設定資格刑、設置從業禁止條款以提高刑罰懲治教育效果,同時設計微罪前科封存制度體現刑法的寬宥性。
首先,在刑法中加入資格剝奪刑可以實現有效的懲戒教育效果,預防行為人再犯和預防其他人犯罪的作用都會十分明顯。以“危險駕駛罪”為例,司法實踐中犯罪人通常會以緩刑并科罰金刑被判決。然而,這種刑罰的執行不剝奪人身自由,僅繳納罰金,似乎不足以懲罰危險駕駛的行為人,其再犯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如果在刑法條文中加入“吊銷駕駛證”或者“在一定期限內禁止使用(暫扣)駕駛證”的款項,犯罪人所需要承擔的不僅是限制自由(緩刑)并科罰金,而且需要遵守在一定期限內不能駕駛機動車的要求。目前關于吊銷或暫扣駕駛證的處罰出現在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 條,屬于行政處罰的范疇。筆者認為,比起拘役刑與罰金刑,行為人似乎更為忌憚以后能否繼續駕駛,禁止駕駛的規定對犯罪人的威懾力更為強大,這種取消駕駛資格的處罰被規定在行政處罰中過分嚴峻,不僅導致刑行在處罰內容方面有所交叉,而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出刑罰輕于行政處罰的外觀,對刑法的威懾力會有一定的影響。因此,應當將這類剝奪資格刑的處罰納入刑法規制,對這類刑罰的執行可以規定在相關行政法中。
其次,對微罪體系中具有特定業務的人員,應當附加從業禁止的規定。《刑法修正案(九)》已經在我國《刑法》第37 條后增加第37 條之一的禁業規定,對“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犯罪,或者實施違背職業要求的特定義務的犯罪被判處刑罰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具體案件,禁止犯罪人在一定期限內從事相關職業。該條一般集中適用于非法經營類犯罪,但是這種兼具刑罰性與行政性的處罰也應當適用在微罪體系中,以危險駕駛罪為例,“從事校車運輸業務或者旅客運輸”,嚴重超速超載駕駛,以及“違反危險化學品管理規定運輸危險化學品”,包括醉酒駕駛的職業運輸人員在被提起公訴宣判有罪的,在刑罰執行完畢后應當禁止犯罪人在一定期限甚至終身不得從事相關職業;危險作業罪對遵守安全生產管理規定有嚴格要求,對違反管理規定造成危險的,審判人員在判決有罪的同時可以裁定禁止犯罪人從事相關生產經營工作,從根本上杜絕行為人再犯本罪的可能性。
最后,為避免刑罰負面效果的波及其他而顯得過分苛刻,應當考慮建立微罪前科封存制度。在我國,犯罪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僅及于犯罪人,而且往往會波及其他人(如近親屬等),依照上述刑期和刑種的構建想法,即使不適用緩刑,監禁的刑期也并不漫長。但是在刑罰執行完畢之后,“犯罪人”的標簽依然會貼在身上,終其一生不能消滅。有過刑事處罰經歷的公民,不論其所受刑罰輕重,在求職、求學、入伍抑或在社會評價上都會遭到不一樣的對待,這樣的負面效果甚至波及其近親屬,這種懲罰對觸犯微罪的行為人來說未免太過苛刻。從這一方面來看,似乎違背了罪刑相適應或者罪責自負原則,微罪行為的社會危害輕微,危險性不大,行為人接受刑罰執行后,往往還會承擔彌補一定的損失,甚至消除其產生的危險,但行為人甚至其近親屬還要因自己先前的行為承擔社會上的不平等對待,付出過大代價,有礙于刑法改造功能的實現。目前,日本、瑞典等國對未成年人的前科封存制度都做了一定的規定。〔76〕現行《日本少年法》第60 條規定“少年犯刑期執行完畢或免予執行,適用有關人格法律的規定,在將來得視為未受過刑罰處分。”《瑞士聯邦刑法典(1996 年修訂)》第96 條第4 款規定:“被附條件執行刑罰的少年在考驗期屆滿前經受住考驗的,審判機關命令注銷犯罪記錄。”在刑事立法層面,筆者建議建構微罪前科封存制度,將適用人員從未成年人擴大到輕微犯罪的行為人。在細節方面,可以根據“前科封存的基本條件(時間、刑期等),適用范圍(罪名、次數等)和實現方式(自然消滅、依申請消滅、消滅后的再恢復)等方面進行規范”。〔77〕賈曉文、張美惠:《輕罪治理現代化的基層檢察經驗與立法展望》,載《刑事法學研究》(2021 年第1 輯,總第1 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
3.微罪體系中刑事不法與行政不法的銜接
構建微罪體系不能僅在刑法條文內部斟酌,也應當注意刑法與行政法的銜接問題。“我國對違法行為的處理采取的是二元化的處罰結構,”〔78〕儲槐植、閆雨:《危險駕駛行為入刑:原因、問題與對策》,載《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2 期。刑法的謙抑性允許其在前置法無法發揮效用的時候才予以介入。從法理上講,法益保護并不是刑法的專利,作為公法的行政法也當然服務于保護法益、防止危險的任務,而且如果刑法所規制的范圍已經擴張到了抽象危險,那么當然會出現刑法與行政交疊的地帶。〔79〕參見謝煜偉:《交通犯罪中的危險犯立法與其解釋策略》,載《酒醉駕車刑事問題研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 年版,第26 頁。司法實踐中,對于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行為,無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行政法中也有相應處罰措施(即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 條第1 款之規定)。〔80〕《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 條第1 款規定:“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暫扣六個月機動車駕駛證,并處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因飲酒后駕駛機動車被處罰,再次飲酒后駕駛機動車的,處十日以下拘留,并處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吊銷機動車駕駛證。”除此之外,針對其他社會失范行為的行政處罰措施對行為人人身自由的限制效果甚至高于刑事處罰,模糊了行政法和刑法的邊界,有背離微罪入刑的本意之嫌。
為此,應在整個公法體系內權衡,明確“微罪制裁的核心模式應為刑事制裁模式,而非行政處罰模式”的前提,〔81〕姜瀛:《勞教廢止后“微罪”刑事政策前瞻》,載《學術交流》2015 年第11 期。在限制行政權擴張的同時對行政處罰權進行司法化改造,這“直接牽扯國家權力的結構調整,事關國家和社會治理方式的深刻變革”。〔82〕何榮功:《我國輕罪立法的體系思考》,載《中外法學》2018 年第5 期。“在行政處罰制度的規制上,將行政處罰中‘人身自由罰’司法化是重中之重”。〔83〕李曉明:《行政處罰中“人身自由罰”存在的原因及解決路徑》,載《蘇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4 期。雖然限制或者剝奪人身自由的勞動教養、收容教育制度相繼廢除,但是具有“人身自由罰”色彩的強制戒毒、對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等處罰措施依然被置于行政處罰之下,且具有擴張之勢。筆者認為,應當在嚴格限制行政拘留適用范圍的基礎上,將其他“人身自由罰”的最終裁決權交由法院行使,賦予“人身自由罰”司法屬性,使之區別于行政處罰,明晰行政法與刑法的界限,從而有效防止行政權過度擴張僭越司法權。
三、微罪的司法適用
“在犯罪圈的設定上,實現國家對難以容忍的違法行為進行懲罰的有效方式即是,通過立法者所確定的刑法規范將值得處罰的危害行為規定為犯罪,賦予被告人辯護機會,尊重和保障其各項權利,將處罰納入法治軌道。”〔84〕周光權:《轉型時期刑法立法的思路與方法》,載《中國社會科學》2016 年第3 期。但是,嚴密法網并不意味著納入刑法調整的微罪最終都應當被定罪量刑。為了體現國家對人權的保障以及避免刑法對社會生活的過度干預,司法適用方面應當為微罪提供可行的出罪(輕緩化處理)路徑。那么,我國現有司法制度能否承擔微罪出罪的功能呢?對此有學者表示擔憂,其理由是,“與西方法治國家‘漏斗式’的刑事司法體制相比,我國司法出罪機制不僅種類少,而且實踐效果也不好”。〔85〕何榮功:《我國輕罪立法的體系思考》,載《中外法學》2018 年第5 期。誠然,域外刑事訴訟程序的設計較為豐富、嚴密。在大陸法系國家,普遍采取的是暫緩起訴制度、檢察官自由裁量起訴制度,還包括絕對輕微不起訴制度、相對輕微不起訴制度、追訴適當性制度等。〔86〕參見王志祥、融昊:《對醉駕行為適用不起訴制度的思考》,載《人民檢察》2020 年第20 期;何榮功:《我國輕罪立法的體系思考》,載《中外法學》2018 年第5 期。英美法系國家的司法出罪制度包括警方撤銷案件制度、警察告誡制度、罰款通知程序、緩予宣告制度等。〔87〕參見謝川豫:《危害社會行為的制裁體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 年版,第317 頁。我國有學者提議單獨制定一部輕犯罪法,“對于輕(微)犯罪法中的行為,適用簡易程序或者速裁程序審理;同時,適當修改簡易程序和速裁程序的適用條件”。〔88〕劉傳稿:《犯罪化語境下的輕罪治理》,載《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2 期。有學者提出可以在輕罪體系的司法適用過程中建立與新設大量輕罪相契合的不起訴制度、不開庭審理的刑事速裁程序等制度。〔89〕參見周光權:《積極刑法立法觀在中國的確立》,載《法學研究》2016 年第4 期。還有學者提出“可以借鑒世界先進法治國家的做法,建立專門審理輕罪案件的治安法院,并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廓定治安法庭的受案范圍和職責權限”。〔90〕白岫云:《建立我國輕罪體系的構想》,載《法治日報》2020 年11 月11 日。筆者認為,上述提議為微罪的司法適用提供了新思路,但同時應充分關注我國當前的刑事訴訟體制能夠為微罪的適用提供的司法過濾功能。具體而言,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7 條第2 款規定的相對不起訴制度,“直接契合于微罪的法益侵害程度輕微的罪質特點”,〔91〕參見王志祥、融昊:《對醉駕行為適用不起訴制度的思考》,載《人民檢察》2020 年第20 期。而我國《刑法》第37 條定罪免刑條款也能夠承擔實體法上的緩和制裁功能,從而“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在法律規范范圍內正確定罪量刑,以對沖案件查處的過度剛性”。〔92〕參見解永照、黎汝志:《醉駕犯罪化的問題與省思》,載《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17 年第5 期。
“將屬于行政管轄的違法行為納入司法范圍,從而落實尊重和保障人權”,〔93〕參見劉仁文:《后勞教時代的法治再出發》,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5 年第2 期。這是我國微罪制度建構的一個重要出發點,但是“機械地執行法律規定將可能造成司法的不公”。〔94〕任志中、周蔚:《醉酒駕駛行為“出罪”問題探討》,載《法律適用》2014 年第8 期。因此,筆者認為,在微罪體系的司法適用過程中,公檢法需要發揮不同的功能。首先,公安機關的執法需嚴密,積極的執法有助于實現微罪的一般預防作用,“防止社會從嚴重不法行為走向失序狀態,增強人們對社會的認同感和安全感”。〔95〕參見儲槐植、李夢:《刑事一體化視域下的微罪研究》,載《刑事法評論》2018 年第2 期。其次,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應當充分考慮適用相對不起訴制度進行司法過濾,而“微罪一律起訴”的觀念則不可取。最后,進入到法院審判階段,不宜“一刀切”地定罪處罰,而應當在滿足條件時積極適用定罪免刑條款,以達成個案公正。
(一)相對不起訴制度的適用
在大陸法系國家刑事訴訟程序中,微罪是起訴階段較為常見的出罪事由。在德國,其刑事訴訟法典第153-154e 條規定了對微罪、輕罪甚至中等程度的犯罪適用起訴便宜主義原則。〔96〕參見[德]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事訴訟程序》,岳禮玲、溫小潔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44 頁。法國的刑事訴訟法典則明確了追訴適當性制度,其通過強調追訴的適當性為微罪不訴保留了不予立案與公訴替代措施的通路。〔97〕參見[法]貝爾納·布洛克:《法國刑事訴訟法》,羅結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329 頁。日本主要通過適用檢察機關的不起訴(起訴猶豫)制度,以實現微罪不舉的效果。〔98〕參見[日]田口守一:《刑事訴訟法》,張凌、于秀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120 頁。“(這些)制度運行的背后,是以行為罪質輕微而否定犯罪化處理必要性的功利主義考量為支撐的。”〔99〕王志祥、融昊:《對醉駕行為適用不起訴制度的思考》,載《人民檢察》2020 年第20 期。這里的功利主義在我國刑事訴訟法范疇內對應的就是相對不起訴制度,需進一步明確的是,微罪案件與相對不起訴制度的契合性及其適用條件。
1.制度契合
有學者指出,“我國司法實踐中存在著在起訴環節未能充分發揮相對不起訴制度的起訴裁量功能的現象”。〔100〕陳興良:《施某某等聚眾斗毆案:在入罪與出罪之間的法理把握與政策拿捏——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導性案例的個案研究》,載《法學論壇》2014 年第5 期。對符合條件的微罪案件適用相對不起訴,能夠為相對不起訴制度注入活力。
其一,相對不起訴制度的核心是起訴便宜主義,與微罪案件數量之多形成匹配。在當今世界各國的刑事訴訟理論中,為了避免過分追求整齊劃一的追訴制度,訴訟經濟原則、訴訟效率原則被普遍重視,在有罪必罰的法定起訴原則之上產生了起訴便宜主義。林山田教授認為,起訴便宜主義是對公訴一方的授權,令其基于刑事懲誡的目的權衡各種利益。〔101〕參見林山田:《論刑事程序原則》,載《政大法律評論》1999 年第3 期。以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為例,“在全國刑事案件總數中,‘醉酒駕車型’危險駕駛罪大約占1/3 的比例,發案率已高于盜竊罪。”〔102〕周光權:《建議修改“醉駕”犯罪標準,有效減少社會對立面》,https://news.tsinghua.edu.cn/info/1578/85038.htm?ivk_sa=1023197a,2021 年5 月29 日訪問。大量“醉駕”案件擠占了基層司法機關有限的司法資源,給基層司法人員帶來了沉重的辦案負擔,而對符合條件的微罪案件適用相對不起訴制度,可以充分發揮制度的訴訟效率價值。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在“輕(微)罪訴訟制度的討論中,效率一直居于核心地位”。〔103〕段陸平:《健全我國輕罪訴訟制度體系:實踐背景與理論路徑》,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21 年第2 期。筆者認為,相對不起訴制度中的“訴訟效率價值”不同于其他如簡易程序制度中的“效率”價值。原因是,相對不起訴是對行為人作出的“有罪不訴”的評價,直接終止了訴訟程序,不同于以標準化、格式化為目標的簡易程序等快速結案模式,〔104〕參見王敏遠:《“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綜合治理的實證研究——以浙江省司法實踐為研究樣本》,載《法學》2020 年第3 期。更注重個案公正的實現。
其二,相對不起訴制度也能夠有效發揮犯罪的宣示性機能,符合微罪的立法初衷。相對不起訴在法理上仍然宣示了被不起訴人行為的犯罪性,而“強調犯罪的明示性,就是告知國民行為合法與違法的邊界以及國家法律對違法行為的否定性”。〔105〕程龍:《再評陸勇案:在法定不起訴與酌定不起訴之間——兼與勞東燕教授商榷》,載《河北法學》2019 年第1 期。有學者提出,“先在刑法中增設大量輕罪,后在程序法上增加簡化過濾程序,如此大費周章、輾轉迂回,等于重返問題原點”。〔106〕冀洋:《我國輕罪化社會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與批評》,載《東方法學》2021 年第3 期。實則不然,首先,相對不起訴制度不屬于“增設程序”,其次,設立微罪與過濾微罪體現的是立法與司法的層次性,其核心仍在于明確法律對微罪行為的否定性評價。
2.適用條件
針對相對不起訴制度中的“犯罪情節輕微”,司法實踐中一般以三年有期徒刑為分界線,〔107〕王志祥:《醉駕犯罪司法爭議問題新論——浙江最新醉駕司法文件六大變化述評》,載《河北法學》2020 年第3 期。據此,“最高法定刑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微罪可以落入相對不起訴制度的適用范圍,但為了避免起訴裁量的恣意性與地域差異性,仍然需要明確相對不起訴制度適用的條件。
以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為例,各地司法機關就醉駕行為如何適用相對不起訴制度作出了若干細則規定。在這些細則中,最具實務可操作性的考察因素就是劃定可以適用相對不起訴制度的醉駕者血液酒精含量上限,但是關于血液中酒精含量幅度空間的規定卻呈現出地域差異性。北京市、上海市一般嚴格按照80mg/100ml 的標準執行;浙江省將酒精含量上限設為170mg/100ml;其他地方如湖北省和天津市為100mg/100ml,四川省、安徽省、重慶市和呼和浩特市為130mg/100ml,湖南省為150mg/100ml;對于短距離挪動車位、非因檢查原因自動停止駕駛、隔夜醉駕等情形,各地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血液酒精含量規定;而沒有出臺規范性文件的省份,檢察機關的不起訴標準也不統一。〔108〕參見寇凈磊:《關于危險駕駛(醉駕)犯罪案件不起訴參考標準的論證》,載《山東法官培訓學院學報》2020 年第4 期。應當肯定,一系列精細化、具體化的相對不起訴制度適用辦法體現了輕輕重重刑事政策的貫徹,但各地的標準有待統一。筆者認為,可以結合各地實施細則及最高人民檢察院院提出的量刑意見,采取“定性+定量”的模式確定相對不起訴制度的適用門檻。首先是定性,嚴守“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實質要素,要求做出相對不起訴的檢察人員展開充分的說理;其次是定量,應當出臺具有全國性效力的規范性司法文件,從形式要素上統一規定適用相對不起訴制度的血液中酒精含量幅度,對各地檢察機關處理醉駕案件的起訴裁量權加以規范。〔109〕參見王志祥、融昊:《對醉駕行為適用不起訴制度的思考》,載《人民檢察》2020 年第20 期。實質與形式因素相結合,既能夠鼓勵檢察機關積極行使不起訴裁量權,又可以避免案件處理結果的地域差異過大。
(二)“定罪免刑”條款的激活
1.定罪免刑對于微罪治理的積極意義
對于符合實體法上犯罪成立條件的微罪行為,可能的處理方式包括:第一,通過相對不起訴制度進行審前分流;第二,依據我國《刑法》第37 條或其他免除刑罰情節,對被告人定罪免刑;第三,定罪處刑,但適用緩刑;第四,定罪處刑,并執行刑罰。其中,定罪免刑制度在許多國家的刑法中均有所規定,例如,《法國刑法典》第132—58 條規定:“在輕罪方面,或者除第132—63 條及第132—65 條規定之場合外,在違警罪方面,法院在宣告被告有罪并在必要時作出沒收有害物或危險物的判決后,得免除被告其他任何刑罰”;〔110〕參見梁根林:《非刑罰化——當代刑法改革的主題》,載《現代法學》2000 年第6 期。《德國刑法典》第60 條規定:“如果行為人遭受的行為后果嚴重,判處其刑罰明顯不當的,法庭可免除其刑。但行為人因其行為被判處一年以上自由刑的,不適用本規定。”〔111〕徐久生譯:《德國刑法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32 頁。與審前分流和緩刑的適用相比,法院通過定罪免刑能夠充分平衡法規范的呼吁機能和個案的妥當性,從而實現刑事制裁的多元化。〔112〕參見曾文科:《免除刑罰制度的比較考察》,載《法學研究》2017 年第6 期。
首先,通過宣告行為人有罪,以及在必要時施加非刑罰處罰措施,在有些案件中能夠達到與刑罰相同的效果。一般認為,現代社會中,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犯罪。〔113〕參見張明楷:《刑法學》(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510 頁。然而,在微罪案件中,犯罪行為的預防需要性本就較低,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有時甚至單純宣告行為人有罪,就足以實現預防犯罪目的,并對社會公眾起到教育、指引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其一,有罪宣告作為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之一,本身就意味著對行為人的否定評價,〔114〕參見杜雪晶:《中國刑事制裁框架的梳理與擴展——以犯罪學的視角重新審視》,載《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 年第1 期。并且具有向社會公眾宣示法秩序的價值取向的功能;其二,通過有罪宣告,行為人將被貼上犯罪人的標簽,從而帶來附帶性的不利后果;〔115〕參見姜濤:《從定罪免刑到免刑免罪:論刑罰對犯罪認定的制約》,載《政治與法律》2019 年第4 期。其三,宣告有罪回應了被害人的報應情感,有利于平息案件導致的社會矛盾和不良影響。
其次,定罪免刑制度可以彌補形式裁判的不足。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80 條的規定,對于人民檢察院作出的不起訴決定,被害人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人民檢察院維持不起訴決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被害人也可以不經申訴,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當被害人向法院起訴時,法院就應當對不起訴決定進行審查,視審查結果,決定不予受理、駁回請求或者強制起訴等,這是法院行使形式裁判權的表現。〔116〕參見李昌林:《論刑事訴訟中的權力制約——以賦予法院形式裁判權為核心》,載《甘肅社會科學》2007 年第1 期。可是,問題在于,對于某些輕微案件,判處刑罰失之過重,形式裁判又無法對案件進行全面評價,此時,定罪免刑制度便能有效發揮作用:一方面,與以形式裁判來終止程序相比,定罪免刑由于認定行為人構成犯罪,制裁效果更強;另一方面,與定罪處刑相比,其又具有緩和制裁的功能。〔117〕參見曾文科:《免除刑罰制度的比較考察》,載《法學研究》2017 年第6 期。
最后,定罪免刑能夠避免對行為的重復評價。在我國行政法與刑法的二元規制模式下,微罪行為不僅面臨刑罰威脅,而且往往還會受到行政處罰。以醉酒駕駛為例,根據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 條的規定,醉酒駕駛機動車的,吊銷機動車駕駛證,并且五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吊銷機動車駕駛證雖然不屬于刑罰,但無疑是對行為人的重大限制。對于情節輕微的微罪案件,考慮到行為人已受過“行政前置處罰”,〔118〕賀洪波:《危險駕駛罪免刑實證研究》,載《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4 期。定罪免刑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對行為的重復評價,從而防止違反比例原則。
2.我國《刑法》第37 條在微罪中的具體運用
我國刑法理論上通常認為,我國《刑法》第37 條是我國刑法關于定罪免刑及適用非刑罰處罰措施的一般性規定,具有獨立的免刑功能。〔119〕參見賀洪波:《優化定罪免刑實踐的法治路徑研究》,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 年第6 期。然而,如何解釋我國《刑法》第37 條中的“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刑法卻并未提供明確的標準,只能交由法官自由裁量。〔120〕鄭超:《無刑罰的犯罪——體系化分析我國〈刑法〉第37 條》,載《政治與法律》2017 年第7 期。因而,必須對該條中“犯罪情節輕微”這一表述進行解釋。為此,一方面需要結合刑罰目的對第37 條的規范本質進行分析;另一方面,需要結合微罪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探明第37 條在微罪領域中的具體考量因素。
從刑罰的預防目的出發,刑罰的輕重取決于行為的預防需要性。沿著這一思路,如果原本需要動用刑罰才能實現的預防目的,在具體案件中不需要動用刑罰也能夠實現,那么就可以免除刑罰;〔121〕Vgl.Gabriele Kett-Straub,Das Absehen von Strafe gem?? § 60 StGB,JA 2009,53.換言之,就可以將其歸入“犯罪情節輕微”之列。尤其是在微罪領域中,行為的罪責程度本就較低,刑罰的施加與否及其輕重主要取決于行為的預防需要性。因此,對微罪“情節輕微”的考察,應當以刑罰的預防目的為基礎,漸次考量個案中微罪行為的特殊預防需要和一般預防需要。例如,就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而言,如果行為人醉酒駕車的行為,導致行為人自身受到嚴重傷害甚至喪失駕駛能力,這種重大不利后果本身就阻遏了一般公眾對此類行為的效仿,并且事實上剝奪了行為人的再犯可能性,此時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需要都大大降低了;又如,行政機關已經依據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剝奪了行為人的駕駛資格,那么借由這一行政前置處罰,特殊預防目的就已經得以實現;再如,具體案情表明行為人的醉駕行為明顯不會給其他道路交通參與人造成危險,此時通過宣告行為人有罪,并通過行政處罰剝奪行為人一定期限的駕駛資格,就足以滿足輕微的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的需求。
上述標準是立足于刑罰的預防目的,對“犯罪情節輕微”所進行的規范本質分析,以此為基礎,司法實踐在適用我國《刑法》第37 條時仍需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進行判定。除了前述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考量之外,還應當考慮一般性的量刑因素,〔122〕Vgl.MüKoStGB/Gro?/Kulhanek,4.Aufl.2020 Rn.22,StGB § 60 Rn.22.包括事后的悔罪表現、采取的補救措施、是否初犯、犯罪動機和目的,以及行為人的“年齡、生理狀況、行為的正當性、犯罪的停止形態、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自首或立功表現等情形”。〔123〕參見鄭超:《無刑罰的犯罪——體系化分析我國〈刑法〉第37 條》,載《政治與法律》2017 年第7 期。以醉酒駕駛型危險駕駛罪為例,可以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為主,輔以前述量刑情節,包括有無事故后果、人員受傷及程度、財產損失數量、有無快速路行駛過程、是否沖卡等等,綜合構筑危險駕駛罪免刑適用的標準。〔124〕參見賀洪波:《危險駕駛罪免刑實證研究》,載《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4 期。
四、結 語
誠然,刑法只是社會治理方式的一種,但卻是最為特殊的一種方式。這種特殊性體現在:一方面,基于制裁手段的嚴厲性,刑法對其他社會治理手段具有兜底功能,當其他社會手段無法滿足法益保護的需求時,刑法必須積極介入;另一方面,基于法治原則,刑法的適用受到嚴格的程序約束,刑法在保障程序正義、發現實體真實方面具有其他治理手段所不具有的效果。有鑒于此,如何理性運用刑法對輕微的社會失范行為進行規制,成為風險社會背景下的重要命題。對此,我們既不應該陷入對“重刑主義”的盲目崇拜,也不應該走向“刑法無用論”的片面立場,而應當在堅守法益保護和比例原則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刑法在社會治理上的兜底功能。在此基礎上,還應建立與微罪的輕微社會危害性相配套的處遇機制,嘗試建立微罪前科封存制度,構建科學的微罪體系,正確把握刑法在多元社會治理中的應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