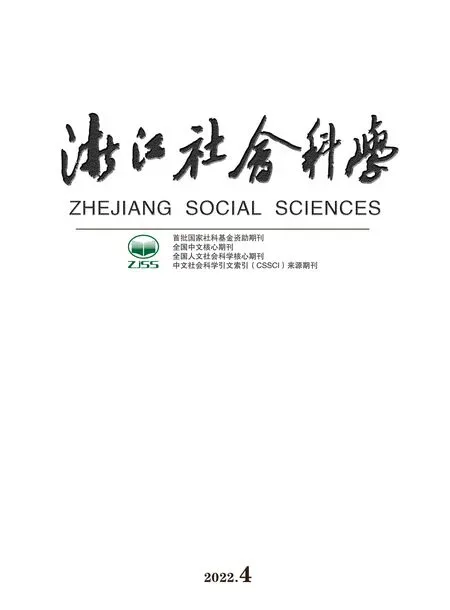以“局”論局:中國近代企業早期歷史研究的一個視角
□ 李志茗
內容提要 晚清幕府中出現了大量以“局”立名的機構,其中有一類是洋務企業。它們是中國第一批近代企業,開啟了至今還在路上的中國現代化進程,長期成為學界關注和研究的熱門話題,被幾代人一遍遍地反復書寫,成果蔚為大觀。然而,已有研究多把它們經營上的不成功歸咎于國家的干預及由此帶來的種種腐敗等,不少學者還利用西方經濟學理論或所處時代的歷史認知從不同側面進行論證,強化和固化了上述論調。其實,作為幕府機構的晚清早期洋務企業,從一開始便發端于地方且依附于地方,對其研究也應該從地方的立場或“局”的視角出發,這樣才合乎邏輯和事實。以輪船招商局為例,它是李鴻章事先籌辦、事后奏請并始終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幕府洋務機構。他為之肩負許多責任,當然擁有支配權,為自己服務。因此,早期招商局出現的種種怪象和營私舞弊問題,主要與李鴻章采取的幕府管理方法有關。同理,從“局”的視角入手,研究其他洋務企業的早期歷史,也不失為一條可行的取徑。
19世紀60年代,歷經內憂外患的接連打擊之后,自強成為很多國人的共識。于是,在求強、求富觀念的引領下,當時的地方督撫相繼創辦許多以“局”命名的軍工企業和民用企業。這些“局”是中國第一批近代企業,開啟了至今還在路上的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所以長期成為學界關注和研究的熱門話題,被幾代人一遍遍地反復書寫,成果蔚為大觀。然而,已有研究多把它們經營上的不成功歸咎于國家的干預及由此帶來的種種腐敗等,不少還利用西方經濟學理論或所處時代的歷史認知從不同側面進行論證,強化和固化了上述論調。其實,中國近代企業的形式或制度不是自生的,而是從西方移來的,這種移來難免要建立在中國既有條件基礎上,便不能不發生走樣變異,既非西方原形,又與中國傳統有別。因此,研究中國近代企業特別是它們的早期歷史,不能簡單套用西方理論,也不能一味夸大國家的宰制作用,應回到歷史現場,置身于具體的情境中,追問這些企業為何設立、受什么條件影響、到底是誰主導等等,惟有如此才能對它們的歷史形成整體的認識,從而予以具體的、有針對性的評判研究。
一、晚清的“局”
晚清時期涌現出很多以“局”立名的機構。①梁元生先生注意及此,率先撰《體制內的變革:清末上海的“局”》一文進行論述,發人所未發,富有創見。但他認為,“作為政府設立的組織,‘局’雖然在19世紀以前就出現了,但卻并沒有被視為官僚體制的一個部分”②。其實不然,“局”作為官僚機構起源很早,與軍隊行陣之禮有關。《禮記·曲禮》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意思是說左右各有軍陣,各軍陣自有統領,因而進退都有法度。鄭玄注:“局,部分也。”后“局”被引申為政府的部門,徐珂作《“局”考》一文說:“官吏所居曰局,始于六朝。梁分門下二局,北齊有左龍、右龍、尚藥等局,其取義殆原于《禮記》之‘左右有局’。”③至清代,以局為名的官僚機構有寶泉局、寶源局、官錢局、司經局、鑄印局、織造局、五城米局、管理火藥局等,它們附屬于不同的國家機關,涉及財政、民生、軍事、文化等方方面面,內部組織、人員構成、具體職掌等一應俱全,有的常設,伴隨清朝始終;有的中途被裁撤;有的臨時而設,事后即裁,不一而足。由此可見,在清中葉以前“局”主要是中央的正規官僚機構,它負責某個具體事務,規模不大,級別中等,但針對性強,地位較為重要,可設可裁,靈活方便。
正因為上述特點,“局” 在晚清時期被地方大員從中央借鑒、引入。當時,百年盛世已經過去,很多本來隱伏的問題都逐漸凸顯,露出千瘡百孔,社會問題和矛盾積弊相沿,極重難返,加上內憂外患頻仍,傳統的官僚體制難以應付,清廷又不能適時做出調整,于是地方大員根據實際需要而臨時設“局”。“考設局原委,不自近年始,始于道光年間前兩江督臣陶澍。……軍興以后,前湖北巡撫臣胡林翼、前兩江督臣曾國藩,皆師其意而踵行之。”④可見,地方設“局”有個過程,陶澍開其端,至太平軍興時胡林翼、曾國藩等“踵行之”。由此“局”重新被發現,大量設立,十分盛行。本來的一時權宜也逐漸常態化、制度化。各“局”“規模大小,人數多寡,甚至有否衙署,俱無定制”,但一般采用“辦委”體制:辦有總辦、會辦、幫辦等,是管理階層;委即“委員”,是局中辦事人員。無論是“辦”還是“委”,主要由候補官員充任。⑤由于“局”取便一時,“積久遂成為故事”⑥,各地越設越多,引起清朝監察部門的注意。光緒十年,御史吳壽齡以各省設局太多造成濫支冗費為由,奏請裁撤。戶部和吏部奉命核查,發現僅在朝廷報備的“局”就為數不少,非常可觀。調查結果如下:
查各省散置各局,已報部者,于軍需則有善后總局、善后分局、軍需總局、報銷總局、籌防總局、防營支應總局、軍裝制辦總局、造制藥鉛總局、收發軍械火藥局、防軍支應局、查辦銷算局、軍械轉運局、練餉局、團防局、支發局、收放局、轉運局、采運局、軍械局、軍火局、軍裝局、軍器所、軍需局等項名目;于洋務則有洋務局、機器局、機器制造局、電報局、電線局、輪船支應局、輪船操練局等項名目;于地方則有清查藩庫局、營田局、招墾局、官荒局、交代局、清源局、發審局、候審所、清訟局、課吏局、保甲局、收養幼孩公局、普濟堂、廣仁堂、鐵絹局、桑線局、戒煙局、刊刻刷印書局、采訪所、采訪忠節局、采訪忠義局等項名目;其鹽務則有各處鹽局、運局、督銷局;其厘卡除牙厘局外,則有百貨厘金局、洋藥厘捐局,暨兩項各處分局更不勝枚舉。⑦
盡管這些局各式各樣,五花八門,但遠非全部,此次調查發現,“其未經報部者尚不知凡幾”。不過即以報部各局而論,已令清廷大為震驚和不滿,認為“各局林立,限制毫無,究其實事,一無成效”,“種種消耗,何所底止”,飭令各省督撫破除情面,予以裁并,“實力整頓”⑧。然“局”已成為各省督撫用慣和慣用的東西,不愿也不肯放手,所以他們陽奉陰違,聽之藐藐,直至清朝滅亡,依然沒有全部裁并,所謂整頓成效有限。因此“局”自太平軍興以后,便一直保留下去,難以消除,“儼然成為地方官場及城市文化之特色”⑨。
二、洋務之局:晚清幕府下屬機構⑩
晚清地方設“局”的始作俑者是陶澍。道光五年,為籌辦清朝第一次漕糧海運,他在上海設立江蘇海運總局,“以川沙廳同知臣李景嶧、蘇州府督糧同知俞德淵董之,與道府各臣共襄其事”?。可見,陶澍設“局”關乎國計民生,是國家大事,并且局務均由在職官員兼任。清代設官定職甚嚴,禁止濫設官吏,陶澍所為中規中矩,沒有違制。然而20多年后的咸豐年間,胡林翼、曾國藩等仿效陶澍設“局”,所面臨的時代環境完全不一樣了。其時太平軍如虎兕出柙,席卷千里,清政府疲于奔命,不僅兵弱將寡,難以抵御,而且羅掘俱窮,庫儲一空,不得不將用兵、籌餉等權力下放給地方領兵大員。在此之前,凡興大兵役,皆是戶部撥餉、兵部調兵,“至今日則兵無可調,惟有募勇;餉無可請,惟有自籌”?。募勇、籌餉均非一兩個人可以勝任,必須在軍幕中設立相關機構來辦理。最典型的莫過于曾國藩,他率湘軍出師東征時,就奏報幕中“設立八所,條綜眾務:曰文案所、內銀錢所、外銀錢所、軍械所、火器所、偵探所、發審所、采編所,皆委員司之”?。這八所涵蓋政治、財政、軍事、司法等方面,猶如一個小政府,一方面反映軍務繁雜,涉及方方面面,須設立專門機構各負其責;另一方面,因為清政府無可指望,曾國藩要自募兵勇,自籌糧餉,自造軍械,只能在幕中大量設“局”,委派自己的幕僚主持其事。
面對這些明顯的違制之舉,清廷權衡利弊,唯有做出讓步,予以默認。于是,“局”經曾國藩的創造性利用,性質發生變化,成為晚清幕府的辦事機構。作為一種戰時應變之舉,這情有可原,無可厚非。因為幕府本來產生于軍營中,唐人顏師古說:“莫府者,以軍幕為義。”?軍幕是個具有高度自主權的組織,可便宜行事。孰料曾國藩幕中設“局”的創新舉措立即引發示范效應,迅速推廣開來,被其他領兵大員所仿行,并且隨著這些大員先后就任督撫,他們也用這種辦法管理地方。梁啟超曾論此過程及現象說:“同治中興之役,胡、曾、左諸公,以封疆吏任練兵籌餉之事,因本省之屬員,才不足用,必須調用平日親信之人,而實缺各官,又不能舉而易之也,于是乎廣設諸局,以善后、厘金等局,代藩司之事,以保甲等局,代臬司之事,其余各事,莫不設專局以辦之。下至各府州縣,皆有分局,故當軍興之時,全省之脈絡,系于各局。”?清代的督撫下不設屬官,也沒有輔佐機構,此時其幕府中的幕僚和“局”剛好提供了人員和機構保證,使他能夠自主有效地處理日益紛繁的地方事務。就此說來,晚清的“局”盡管是一時權宜,不在清政府的官僚體制之內,但它們是晚清幕府機構,為地方大員所創置,不僅便于其支配操控,而且可以用來統轄地方,疏通全省脈絡,這就是清末“局”長期保留、屢禁不止、越裁越多的原因所在。
晚清時期的“局”林林總總,名目繁多,其中有一類是洋務企業。梁元生說晚清“現代化的兩個重要范疇——即對外開放及交涉和興辦各種現代企業,都以‘局’為制度性的基礎”。的確如此,最早在幕府中設立現代意義企業的是曾國藩。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他在安慶“設內軍械所,制造洋槍洋炮,廣儲軍實”。后來,他上奏朝廷,追述這段往事說:“同治元、二年間駐扎安慶,設局試造洋器,全用漢人,未雇洋匠。……二年冬間,派令候補同知容閎出洋購買機器,漸有擴充之意。”?可見,曾國藩是比照上述設立八所前例,自行設局制造洋器,事后奏報。在他看來,這也只是其幕府事務之一而已。據容閎回憶,他奉命購買機器所需“款銀六萬八千兩”是憑曾國藩的“公文兩通”,“半領于上海道,半領于廣東藩司”?,顯然出于曾國藩自籌。與此同時,李鴻章“亦自購機器,設局上海”。他后來奏報朝廷說:“同治初年,臣鴻章孤軍入滬,進規蘇浙,輒以湘淮紀律參用西洋火器,利賴頗多。念購器甚難,得其用而昧其體,終屬挾持無具,因就軍需節省項下籌辦機器,選雇員匠,仿造前膛兵槍、開花銅炮之屬,上海之有制造局自此始。”?不難看出,與曾國藩一樣,李鴻章也是自行設局,自籌經費,用西法制造槍炮的。中國近代企業的創辦和現代化的啟動沒有隆重熱鬧的開場,也沒有所謂的頂層設計,就是這樣從地方大吏與晚清幕府中不經意地開始了。
然而,就自強的本義而言,近代企業應當由國家出面創辦,但在19世紀的中國,“這一類師夷之長技的事業于古無征,很難從板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里自然分蘗出來,而富有張力的幕府制度則提供了一個茬口,使它們能夠與中國社會接起來”,“在后來的三十年里,這些官局一個一個地成了炙手可熱的洋務衙門”,“成為時政中的要目”。不過,由于它們是從晚清幕府里分娩出來的,所以其事務“天然是一種幕府事務”,督撫大員也“沿用管理幕府的方法”?管理近代企業。這成為晚清最后三十多年里的常態。
三、以輪船招商局早期歷史為個案的考察
晚清的洋務企業既是“以‘局’為制度性的基礎”,“從一開始便明顯不僅發端于地方而且依附于地方”?,那么對其研究也應該從地方的立場或“局”的視角出發,這樣才合乎邏輯和事實。但或許如學者強調的那樣,“中國作為一個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在開始實行工業化時,……政府的制度安排比西方自由發展起來的工業化更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既有的海量研究成果大都將洋務企業視為 “早期的國有企業”,“大政全由官府一手包攬”?。這種先入為主之見,不可避免地會使研究者戴著有色眼鏡去觀察、思考和解釋問題,將中國近代企業的所作所為都等同于清朝中央政府行為。其實際情況究竟如何,下面試以輪船招商局早期歷史的研究為案例,作番歸納和辨析。?
首先,許多研究者套用西方公司理論,認為輪船招商局是一家特許股份公司。因為股份公司“并非在中國自發形成,而主要是制度引進的結果”。在西方,公司制度先后經歷特許和準則兩個階段,“直到西方國家一般公司法產生以前”,公司的成立“都以得到政府特許為前提”。也就是說,在缺少相應法律法規的情況下,公司能否獲準成立“需要政府采取一事一議的方式決定”?。以此比照,學者們認為“就中國公司而言,特許階段是指中國近代第一家公司經政府特許產生到一般公司法《公司律》產生為止,……時限大致為1872~1903年”。在此期間,“清政府對于新式企業成立并沒有相應的準則,公司的成立與否,主要根據朝廷采取‘一事一議’的方式,即采取特許的方式”。于是,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72年12月26日)經清政府批準正式設立的近代中國第一家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便被視作 “經過政府特許”的“中國近代第一家公司制企業”?。實際上輪船招商局的創辦經歷一年多的醞釀過程,剛開始是紙上談兵,地方和中央、地方和地方之間函電交馳,反復商議辯駁,未有成局。李鴻章認為與其空談,不如付諸行動,乃“于海運通商、留心時事各員中,博訪周密”,查有浙江候補知府朱其昂兄弟二人精明穩練,“習知洋船蹊徑”,“熟悉南北各口岸情形”,遂趁同治十一年七月他們在天津兌漕期間,與之“反復議論”他倆所擬輪船招商章程二十條,并令他們回上海后,與江海關道沈秉成、江南制造局總辦馮焌光共同商量。九月初,朱其昂復至天津向李鴻章面陳節略,李鴻章命他再與津海關道陳欽、天津道丁壽昌籌議。陳、丁二道皆以朱其昂所論為然,“求其準行”。李鴻章允其所請,借撥練錢20 萬串,令朱其昂設局試辦。?十月三十日,輪船招商局開始營業,第一號輪船“伊敦”號裝貨從上海開往汕頭,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它已第四次由滬啟行。?兩天后,李鴻章分別向總理衙門和同治皇帝匯報“試辦輪船招商”情況,稱“現已購集堅捷輪船三只,所有津滬應需棧房碼頭”等“均辦有頭緒”。二十六日,軍機大臣奉旨:“該衙門知道”,意味著通過向朝廷報備,輪船招商局取得合法的身份。?可見,輪船招商局是李鴻章自行設立在先,事后予以奏報,清政府順水推舟,責成李鴻章全權辦理,“招商局由李鴻章奏設,局務應由李鴻章主政,……該大臣責無旁貸,凡有關利弊各事,自應隨時實力整頓,維持大局”?。就此而言,輪船招商局的成立并非清政府特許,采取一事一議方式決定的,而是李鴻章自行創立,由其主政,顯然是其幕府洋務機構。至于設局動機,在不同的場合他有不同的表述,都很冠冕堂皇,即分洋商之利,有裨海防、洋務、國計民生等,但實際他是想整合華商財力、物力為其洋務事業提供便利。所以該局“是繼承歷代政府的‘招商’政策而來的”,其名字“即師歷史上招商之義”?,從根本上說它仍是本國土壤和環境的產物,主要秉承歷史經驗和習慣做法。因此,盡管輪船招商局被許多學者視為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其實徒有虛名,李鴻章自言“輪船招商局本仿西國公司之意”,“原系仿照西商貿易章程集股辦理”?,充其量只是借用西方公司集股的功能而已,并未移植其整套制度。在這個意義上,用西方公司理論來對之進行研究已很勉強,其他的如當代經濟學的產權制度、組織依附、預算約束軟化等理論更不太合適,很可能出現削足適履的毛病。?
其次,不少研究者認為“招商局的方案、籌建均由清廷一手控制”,“清政府始終保持著對招商局的控制”?。這里的清廷、清政府應指清朝中央政府。上文已論及招商局乃李鴻章自行籌辦,事后奏報,朝廷僅表示“知道”而已,并無實質性的控制手段,以致招商局成立14年后,戶部抱怨:“輪船招商局之設,始創于同治十一年。當時如何招商集股,有無借撥官款,部中無案可稽。光緒二年,前兩江總督沈葆楨奏:美國旗昌公司歸并招商局,請撥浙江等省官款,通力合作,是為招商局報部之案。此后行之十年,官本之盈虧,商情之衰旺,該局從未報部,部中均無從查悉”?。戶部掌管全國財政,卻無從查悉招商局的經營情況,則可見它確實只是在清朝中央政府備案而已,朝廷沒有把它當作一件要事來抓,更別提扶持和保護了。那么學界言之鑿鑿的清政府為招商局提供漕糧及輪運壟斷權等扶持保護措施,事實是怎樣的呢? 就前者而言,本是李鴻章為吸引商人投資附股以及與外國輪船公司競爭的手段,清朝政府當然也允準招商局兼運漕糧,然并無具體的分配方案,如運多少,運哪些地方的漕糧,因為當時沙船還有能力從事漕運,與招商局形成競爭關系,所以盡管李鴻章奏請招商局每年“協運江、浙漕米”四五成,但“承辦漕務人員往往自便私圖,不肯加撥”,“分撥不及二成”。于是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來應對:其一,致函總理衙門“請加撥漕糧”,“蘇、浙海運漕米必須照四五成一律加撥,不準再有短少”,取得合法性。其二,鑒于江蘇“漕數最多,分撥不及二成”,親自寫信給江蘇地方官員,“言商船承運過少,能否加撥若干”,請求給予支持。?其三是擴大運漕省份范圍,責成主持招商局漕運業務的兩會辦盛宣懷、朱其昂“規復江楚漕運”?,爭取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漕運承辦權。據上述,漕運成為招商局的主營收入,與其說是清政府賦予專利的結果,不如說是李鴻章及其幕僚通過一系列努力得來的。結果因此欠了人情,“漕務各員薦人,該局不敢堅拒,自有苦衷”?。而就后者來說,“1872年招商局成立時,李鴻章并沒有給它獨占輪船航運之權,這大約是因為既不能禁止外商輪船公司存在,也就不便明文規定不準華商輪船公司設立”。但有人援引兩條材料認為李鴻章阻止華商設立輪船公司:一是“滬商葉成忠(澄衷)稟置造輪船,另立廣運局經直督李鴻章批飭不準獨樹一幟”;二是“臺灣的巡撫為著幫助該島發展貿易,曾購置了兩只火輪船,而招商局的保護者們反對這兩只船到北方貿易,認為對招商局商場的侵犯”。經學者考證,這兩條材料都是道聽途說,經不起推敲,根本不可信,招商局“不存在壓抑或阻撓新式航運企業出現的問題”,也沒有享有近代中國輪運的獨家經營權。?上述這些從側面說明清政府并未控制招商局,如果真的控制了,應該千方百計加以保護,主動給予特殊待遇,想招商局之所想,急招商局之所急,而不是被動地、原則性地應付來自招商局或其他官員的訴求,毫無章法。?
再次,與清廷形成鮮明對比,招商局從籌備到開辦營運,始終是李鴻章在關愛呵護,為之保駕護航。第一,在創辦過程中,李鴻章親自與他指派的招商局經辦人朱其昂反復議論輪船招商局章程,還派其幕僚與之籌議,因此其意志體現在章程里,如招商局官督商辦,實行總辦負責制,而總辦由李鴻章委派;所發行股票印有“奉直隸爵閣督部堂李奏準設局招商”字樣等。第二,他用人不疑,對朱其昂很信任,朱不時稟報招商局籌辦順利,已“會集素習商業殷富正派之道員胡光墉、李振玉等公同籌商,意見相同,各幫商人紛紛入股”。因此,李鴻章在奏辦招商局時,特地提到這個細節,意在表明設局很有必要,籌辦也非常成功,華商入股踴躍。于是他錦上添花,“準該商等借領20 萬串以作設局商本,而示信于眾商”。?然而事實是,朱其昂除了自己投資外,僅募得6 萬兩現銀,原先認股10余萬兩的各商均未交款,結果他所借的20 萬串官款成為招商局初期的最主要資本,也就是說招商局實際是靠李鴻章撥借的官款才辦起來的。?第三,因朱其昂對新式航運業務不熟悉,既招募不到商股,經營又乏善可陳,“在半年左右的時間,輪船招商局便虧損了四萬二千兩”,李鴻章不得不進行改組,“于阛阓中破格求才,得唐景星、徐雨之兩觀察肩任艱巨。當斯時也,風氣未開,招徠不易,二君慘淡經營,力圖振作,兼并旗昌公司,增船至三十余號,縱橫江海,無遠勿屆”?。可見在招商局開辦半年即陷入困境之時,又是李鴻章出面,尋找替人,力挽狂瀾,使招商局得到發展。第四,招商局起步極為艱難,不僅外受西方輪船公司跌價競爭,而且內為一些官員所彈劾抨擊。對于前者,李鴻章盡量提供經濟上的支持和援助,除了籌撥官款外,還動員地方“閑款”撥存招商局,以求“于公有益,于眾商有裨”。鑒于商股觀望,生意清淡,他于光緒三年奏請將各地歷年撥存商局的“官帑銀一百九十萬八千兩,均予緩息三年”,至光緒六年起緩利撥本,分五年歸還,“以紓商力”。?至于后者,面對京師士大夫“訟言船政之非”,朝廷“淟涊依違”,聽之任之,李鴻章則逐一辯駁,承認招商局創辦伊始,“英商力與傾擠,商股遂多觀望”,導致“貲本尚薄,船數寥寥,經理亦未盡得訣”,但“賴同志互相幫助”,招商局務日有起色,取得一定成績,“統計九年以來,華商運貨水腳,少入洋人之手者,約二三千萬兩”。因此他告誡說:“經理商局與別項官事稍有不同,只能綜其大綱,略其細故,頭緒既繁,豈能處處盡善! 交涉既廣,豈能人人愜意! 若必吹毛求疵,朝令暮改,則凡事牽掣,商情渙散,已成之局,終致決裂。”?不難看出李鴻章極力為招商局開脫,營造寬松的外部環境,護犢之情昭然可見。第五,除了招商局本身業務,李鴻章還采取激勵機制,積極為招商局的員紳、司事列保、請恤。同治十三年,他以運解南漕出力為由,開保案保舉招商局總辦唐廷樞,會辦朱其昂、盛宣懷、徐潤、朱其詔,各分局商董陳樹棠、宋縉、劉紹宗等,當吏部對其未與其他漕運出力員弁并案請獎,而另開一案表示異議后,他再上《輪船招商請獎折》,強調招商局“實為海防、洋務一大關鍵,所裨于國計民生殊非淺鮮”,“創辦輪船招商,勞績非尋常局務等項可比”,“該員紳等不無微勞足錄”,自應單獨獎敘,及時鼓勵,得到清廷支持。光緒元年二月,招商局的“福星”號輪船失事沉沒,65 人溺水身亡,李鴻章奏請照陣亡例,“從優議恤”,并建專祠“春秋致祭”;光緒四年五月,朱其昂病死,李鴻章則上請恤折,請求“從優議恤,以慰藎魂而示激勸”,清廷均照準。?晚清大吏慣用請獎手段來為其幕府帶來好處,李鴻章一面聲稱招商局務與官事不同,不能用官事來看待招商局,另一方面卻為招商局爭取官事里的利祿,顯見他是用國家名器作為激勵措施,以拉攏人心,收獲個人的知遇之恩。“地方政府的基礎是與中央政府不同的, 其間的差別必須被注意到。”?上文不厭其煩地羅列李鴻章護持招商局的具體表現,就是為了說明招商局是李鴻章主政的,必須對之負責,并且他也有這個責任和義務,但畢竟他掌握的資源有限,必要時只得爭取清廷支持,尋求幫助,這就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差別。遺憾的是多數研究者未能注意到這種區別,把地方政府行為與中央政府行為混為一談,甚至無視前者,認為招商局是清廷一手控制的,這樣陳言立論難免與事實有偏差。
復次,既然輪船招商局為李鴻章所控制,那他是如何經營管理的呢? 很多研究者引用李鴻章的兩句話“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所有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就斷言他采取的是以這兩條為基本原則的官督商辦體制,進而批評在該體制下,官主導一切,“官督” 變成實際上的“官員管理”,“商辦”變成實際上的“商人只是出資無權管事”,“招商局形成事實上官督凌駕于商辦管理系統之上的格局,由官府操縱招商局的權益分配”?。實際上述兩句話分別出自招商局試營業期間李鴻章向總理衙門和同治皇帝上呈“試辦輪船招商”的奏報中,一方面有夸大官權之嫌,以取悅朝廷,希望一舉得到首肯,另一方面這個所謂體制只是一種紙面設想,未經實踐檢驗,并不能當真。事實就是如此,李鴻章創辦招商局是想借此融洽官商關系,利用華商資本,“以濟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朱其昂順從其意,迎合說:“若由官設立商局招徠,則各商所有輪船股本必漸歸并官局。”?李鴻章遂委派他開辦輪船招商公局,但因官氣過于濃厚,華商冷眼旁觀,不愿投資附股。無奈之下,李鴻章只好改弦更張,重組招商局,凸顯商辦性質。其做法有二:一是招羅殷商入局,二是商事商辦,由商總主持局務。此舉立竿見影,李鴻章興奮地致函友人論述其事說:“現復專派粵商唐廷樞為該局商總,并令分舉各口董事,廣為招勸”,“兩月間入股近百萬,此局似可恢張”?。嘗到這個甜頭后,李鴻章明確表示“商務應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輪船商務牽涉洋務,更不便由官任之也”,支持唐廷樞等“照買賣常規”,按商辦原則進行經營,由商總主政,以專責成,“刪去繁文,以歸簡易”,“除去文案、書寫、聽差等名目,以節糜費”[51]。此外,李鴻章還盡量替招商局排除來自官方的各種干擾,如同治十二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要求招商局租領官輪,被李鴻章以官輪機器費煤等理由婉拒;光緒六年有人奏請徹底清查招商局賬目,李鴻章專折上奏,指出“局外猜疑之言,殊難憑信”,如果照辦,“殊于中國商務大局有礙”; 次年兩江總督劉坤一提出招商局收歸國有建議,李鴻章據理力爭,強烈反對,不惜上奏朝廷,以自己不再過問并“責成劉坤一一手經理”相威脅,迫使朝廷公開承認招商局由他主政。[52]因為招商局是其洋務體系的樞紐,“無事時可運官糧客貨,有事時裝載援兵軍火,借紓商民之困而作自強之氣”[53],所以他當然要控制在自己手里,方便自己調遣使用。而對于招商局的盈虧,他也是很在意的,盡量創造條件予以大力扶持,促其穩步發展。也正基于此,他對于自己物色、委派的總、會辦并不苛求,明知他們“大抵皆射利之徒”,“各有私意”[54],仍非常信任,給予他們一定的經營自主權,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使得“招商局在應付維艱的環境中表現出色”,不僅持續盈利,資本擴充兩倍,而且許多商人還被吸引去投資李鴻章創辦的其他洋務企業,達到其裕餉以自強的預期目的。[55]
綜上所述,輪船招商局是李鴻章事先籌辦,事后奏請,并始終控制在自己手里的幕府洋務機構。為了發展局務,他多方延攬高級經營管理人才,給予相當大的自主經營權,還極力保護這些人才,為他們遮風擋雨,并盡可能多地提供政策和資金上的扶持,減輕他們的負擔和壓力,便利他們開展工作。因此,招商局會辦鄭觀應由衷地說:“謂上臺措置不周、體恤不至,可乎?”他甚至致函總辦唐廷樞,擔心萬一李鴻章不在其位,他們也飯碗難保,“查招商局乃官督商辦,各總、會、幫辦俱由北洋大臣札委,雖然我公現蒙李傅相器重,恐將來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誤聽排擠者讒言,不問是非,不念昔日辦事者之勞,任意黜陟,調劑私人,我輩只知辦公,不知避嫌,平日既不鉆營,安有奧援為之助力”[56]。由此可知招商局是屬于地方的,不歸清政府控制。作為創辦者的李鴻章,肩負許多責任,“比起今天人們所能想象到的要艱巨得多”[57],所以應該站在他設局的角度,研究招商局的早期歷史,這樣才能更客觀,更有說服力。
四、結論
晚清時期,中國進入多事之秋,地方事務紛繁,原來由朝廷設立專辦某事的“局”便被地方大員引進幕府中,用來辦理各種臨時性事務。尤其從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起,地方大員大量設“局”,包羅廣泛。其中有一類是洋務企業,因為需要擴大規模、投入巨資以及現代技術、西式管理等,不得不引進洋務人才、華商資本,于是出現新變化,“大憲開辦之公司,雖商民集股,亦謂之局”。始作俑者就是李鴻章,“輪船招商局之原起, 中堂鑒于中國官商不能如外國官商相聯一氣,是以創官督商辦之局,為天下開風氣之先”[58]。“創官督商辦之局”是李鴻章對幕府洋務機構所采取的一種制度創新,按他自己的說法是“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59],意在兼取官、商兩方的優勢,合作共贏,相互獲利。對于如何設局及起步,李鴻章提出了具體的方案:“由上海辦起”,“須華商自立公司”,物色“熟悉商情、公廉明干、為眾商所深信之員,為之領袖擔當”,從直隸借撥練餉“錢二十萬串以為倡導”,“咨準江、浙,分運明年漕米二十萬石”[60]。可見,招商局是李鴻章精心籌劃、盡己所能創建的。
然而,招商局開辦后,究竟要如何運營,發展目標是什么,李鴻章并沒有確切的想法和要求,而是聽任自己物色的總、會辦等“自立條議”,只有當他們中有不能勝任其職者及招商局岌岌難支時,他才出面干預,或另外物色人選,或“多方設法以扶助之”[61]。以前者言,從1872年至1884年,他先后任命的總、會辦有朱其昂、唐廷樞、盛宣懷、徐潤、葉廷眷、張鴻祿、鄭觀應七位,其中首任總辦朱其昂因經營無方而被李鴻章新招致入幕的唐廷樞取代;會辦葉廷眷因主張將招商局收歸國有,引起李鴻章不滿,將其撤職,又延聘鄭觀應代之。就后者來說,盡管李鴻章說過招商局“所有盈虧全歸商認,與官無涉”,但實際在他的呵護照拂下,商認虧損的機會很少。光緒八年,唐廷樞動情地對股東憶及五六年前招商局陷入困境時李鴻章大力扶助的情形,“當斯時也,內欠二百余萬之多,外有奉旨查賬之件,或將全局傾頹,幸賴李爵相洞燭無遺,力扶危局,奏請添撥漕米,以固其根;暫停繳息,以紓其力。由此根固力紓,連年得利。今日官款可以按期撥還,諸君股資能得厚利者,莫非爵相之力”[62]。不難看出李鴻章對招商局的支持幫助是全方位、多方面的,非常周到,顯然是把招商局視為自己的私有企業。
正因如此,他也經常動用招商局資源為自己服務。其一是運兵、運賑糧。光緒七年,李鴻章奏稱“直、晉、豫等省旱災之時,該局船承運賑糧,源源接濟,救活無數災民。往歲臺灣、煙臺之役,近日山海關洋河口之役,該局船運送兵勇迅赴機宜,均無貽誤”[63],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其二是為自己的洋務事業提供資金。光緒八年,挪用該局資金銀27 多萬兩用于創辦湖北荊門煤礦和開平礦務局;次年,從該局撥銀25 萬兩借給朝鮮國政府,助其開埠通商,時間長達26年,至宣統元年,朝鮮才還清最后欠款23 萬兩。[64]有學者就此認為李鴻章對招商局的扶持幫助,不是“博愛行為”,而是另有所圖,上述兩方面即是他從該局撈回的好處,有利于鞏固和增強“他在華北的政治地位”[65]。實際不是這樣,李鴻章曾多次說過招商局事關海防根本、洋務樞紐,而這些基本是他主導的,他創辦該局也是為了自己方便調遣。在他看來,招商局只是其幕府機構,由他開設,他有監護的責任,當然也有支配的權力。至于該局前景如何,他沒有過多考慮和規劃。后來該局取得較大成功,李鴻章大感意外,奏稱“竊惟招商一局,自臣經始,不過因運漕之便小試其端,事勢所趨,逐漸擴充,亦賴同志互相幫助,現既占江海生意之大半,此非臣力量所能,亦非臣意料所及”[66]。“自臣經始”“同志幫助”,李鴻章的這些說辭不正是向朝廷表明招商局是他一手創辦的,在與其幕府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現在“占江海生意之大半”的巨大成就嗎?
就此而言,創辦初期的招商局并非所謂國有企業,受清朝中央政府控制,而是李鴻章的幕府洋務機構。與其他幕府機構一樣,招商局系李鴻章因事而設。他提供條件,派人辦理,既是為了某種目的,更是要為其所用,但他一般不干涉局中經營活動,也沒有具體的績效要求,更無長遠規劃,所以招商局才會出現戶部指摘的“計存本則日虧”“問子母則無著”“生之者寡,食之者眾,取之無度,用之無節”等各種奇怪現象和營私舞弊問題。[67]基于此,如果從李鴻章這種粗放式的幕府管理入手,研究招商局的早期歷史,不僅有解釋力,而且具針對性,不失為一條可行的取徑,這就是本文所論的以“局”論局視角。同理,其他洋務企業早期歷史的研究也可以循此路徑,兼用這種視角。與招商局一樣的其他民用企業自不必說,就是被公認為國營的軍用企業也可從“局”入手研究。如江南制造局是李鴻章自籌資金,“設局創議于前”,顯然是其幕府洋務機構,而后曾國藩為之“奏請專款”,撥留洋稅一成,才成為受清政府控制的國有企業。[68]而這些國有企業所存在的重復建設、產品結構單一等毛病,也與晚清幕府大量存在、各幕府設局成風有關,因此,以“局”論局的視角仍然適用。
注釋:
①當時除了以“局”立名的機構,還有很多以“所”立名的機構,即所謂局所,因兩者只是命名有別,其他基本相同,都是地方大員設立的臨時機構,為了論述方便,本文統稱為“局”。
②梁元生:《晚清上海: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9頁。《體制內的變革:清末上海的“局”》原載張仲禮等主編的《中國近代城市發展與社會經濟》(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一書,在收入梁先生上述著作中,有所修改,所以本文引用梁先生后出著作,特此說明。
③徐珂:《康居筆記匯函》,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2頁。
④《曾國荃全集》第2 冊,岳麓書社2006年版,第529頁。
⑤⑨梁元生:《晚清上海: 一個城市的歷史記憶》,第194~195頁。
⑥《度支部奏各省財政統歸藩司綜核折》,《政治官報》宣統元年四月初八日第565 號,第12頁。
⑦⑧朱壽朋編:《光緒朝東華錄》,中華書局1984年版,總第1879頁。
⑩關于“晚清幕府”的概念及其制度特征等,詳見李志茗《晚清幕府:變動社會中的非正式制度》,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版。
?《魏源集》,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415頁。
?《胡林翼集》(二),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587頁。
?黎庶昌:《曾國藩年譜》,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37頁。
?班固:《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5頁。
?梁啟超:《變法通議》,《梁啟超全集》第1 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頁。
?黎庶昌:《曾國藩年譜》,第142頁;《曾國藩全集·奏稿十》,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6091頁。
?容閎:《西學東漸》,岳麓書社1985年版,第113頁。
?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岳麓書社1989年版,第13頁;《李鴻章全集》第6 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12頁。
?楊國強:《百年嬗蛻》,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100、101頁。
?楊國強:《衰世與西法·晚清中國的舊邦新命和社會脫榫》,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8頁。
?王玉茹等:《制度變遷與中國近代工業化——以政府的行為分析為中心》,陜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頁。
?劉佛丁、王玉茹:《中國近代工廠制度的產生及其產權運作的特征》,《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 期;張忠民:《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頁。
?本文所謂輪船招商局早期歷史主要指它從1872年籌辦起至1884年唐廷樞、徐潤離局止的發展歷程。
?楊在軍:《晚清公司與公司治理》,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31、11、10頁。
?楊在軍:《晚清公司與公司治理》,第13、140、68~69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海防檔》甲《購買船炮》(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57年版,第910頁;《李鴻章全集》第30 冊,第477頁。
?徐元基:《輪船招商局創設過程考》,載易惠莉、胡政主編《招商局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87頁。
?《李鴻章全集》第30 冊,第484頁;第5 冊,第258頁。
?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六),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頁。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 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443頁。
?《李鴻章全集》第10 冊,第512頁;第34 冊,第449頁。
?輪船招商局是在現代公司法誕生10年后成立的,但當時的中國不僅未引進公司法,而且對公司制度也認識粗淺,不甚了了。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輪船招商局“除了在股份配置方面具有完整的公司性特征(股份均一)外,在賬目公布、股息分配、股權運作和經營管理方面,與近代公司制的要求尚有較大差距”,參見李玉《晚清公司制度建設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頁。所以,用西方公司制度及當代經濟學理論研究輪船招商局看似很有新意,但實際是以今衡古,用今天的眼光和認識去裁斷、評判,忽略了時空的變異和當時的歷史情境,可能方鑿圓枘,與歷史事實不相符。這類著述很多,恕不舉例。
?羅蘇文:《輪船招商局官督商辦經營體制形成的原因及影響》,《史林》2008年第2 期;狄金華、黃偉民:《組織依附、雙邊預算約束軟化與清末輪船招商局的發展——基于輪船招商局與清政府關系的分析》,《開放時代》2017年第6 期。
?[62][67]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 第1 輯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5、824、828頁。
?《李鴻章全集》第32 冊,第147頁;王爾敏、吳倫霓霞合編:《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中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1346頁。
?王爾敏、吳倫霓霞合編:《盛宣懷實業函電稿》上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8頁。
?《李鴻章全集》第32 冊,第151頁。很多學者將招商局這種因人情往來而導致的用人太濫,說成是招商局“內部人”控制下的腐敗現象,有失偏頗。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 第2卷,第455頁;李時岳、胡濱:《從閉關到開放——晚清洋務熱透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148頁。
?如攬載漕糧原為李鴻章奏請,但加撥漕糧是太常寺卿陳蘭彬率先提出,浙江巡撫梅啟照也有此議,而承運官物則是御史董儁翰建議的。清廷不明所以,寄諭李鴻章等詢問“中國官商應需輪船運載貨物,能否統歸該局攬載? 各省漕糧能否再予加成歸該局輪船載運,并著該大臣等體察情形,妥善辦理”。參見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六),第26頁。這得來全不費功夫的好事,李鴻章豈能放棄,當然高度贊成上述各位的提議,并力稱多多益善,招商局有能力也應該承運更多官商貨物,清廷這才一一諭允。由此可見,清廷不懂招商局業務和需求,如何能控制它? 清廷給予招商局的一些政策,并非它主動作為,而是聽取各方意見的結果。
?《李鴻章全集》第5 冊,第258頁。
?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786~787頁。6 萬兩現銀由兩部分組成:天津李氏股份銀5萬兩,上海沙船商郁熙繩股份銀1 萬兩。20 萬串官款,扣除預繳的1.2 萬串利息,實收18.8 萬串,折合銀12.3 萬兩。
?李時岳、胡濱:《從閉關到開放——晚清洋務熱透視》,第139頁;虞和平編:《經元善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頁。
?《李鴻章全集》第30 冊,第615頁;第7 冊,第498頁。
?《李鴻章全集》第30 冊,第505頁;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六),第24、57、60頁。
?《李鴻章全集》 第6 冊,第130、257~258、281~282頁;第8 冊,第84~85頁。
?科大衛:《公司法與近代商號的出現》,陳春聲譯,《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3 期。
?《李鴻章全集》第30 冊,第485頁;第5 冊,第258頁。
?仲繼銀:《中國的公司之難:理不清的官商民關系》,《中國新時代》2014年3月號;羅蘇文:《輪船招商局官督商辦經營體制形成的原因及影響》,《史林》2008年第2 期。
?《李鴻章全集》第6 冊,第257頁;第5 冊,第258頁。
?《李鴻章全集》第30 冊,第524、547頁。在朱其昂時期招商局的性質學界有爭議,有說官辦的,有主張官商合辦的。有學者不同意上述說法,進行一番論證,認為“定性為官督商辦性質更客觀些”,參見楊在軍《晚清公司與公司治理》,第171頁。其實從招商局改組為商辦性質后成效明顯來看,不管在朱其昂時期招商局是什么性質,官氣太濃、商辦不足是毫無疑問的,因此難以調動商人,激發他們投資的興趣。
[51]《李鴻章全集》第9 冊,第48頁;聶寶璋編:《中國近代航運史資料》第1 輯下冊,第847頁。
[52]《李鴻章全集》第31 冊,第30頁;第9 冊,第48、316頁。
[53]《李鴻章全集》第6 冊,第257頁。
[54]陳秉仁整理:《李鴻章致李瀚章書札》,載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11 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頁。
[55]劉廣京、朱昌崚編:《李鴻章評傳》,陳絳譯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287頁。
[56]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3、780頁。
[57]劉廣京、朱昌崚編:《李鴻章評傳》,陳絳譯校,第316頁。
[58]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2頁; 陳旭麓等主編:《湖北開采煤鐵總局·荊門礦務總局——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2頁。
[59]《李鴻章全集》第30 冊,第485頁。
[60]《李鴻章全集》第30 冊,第428頁;第5 冊,第109頁;第30 冊,第484、485頁。
[61][63][66]《李鴻章全集》第9 冊,第314、315、315頁。
[64]朱蔭貴:《論清季輪船招商局的資金外流》,《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2 期。
[65]費維愷:《中國早期工業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14頁。
[68]中國史學會主編:《洋務運動》(四),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