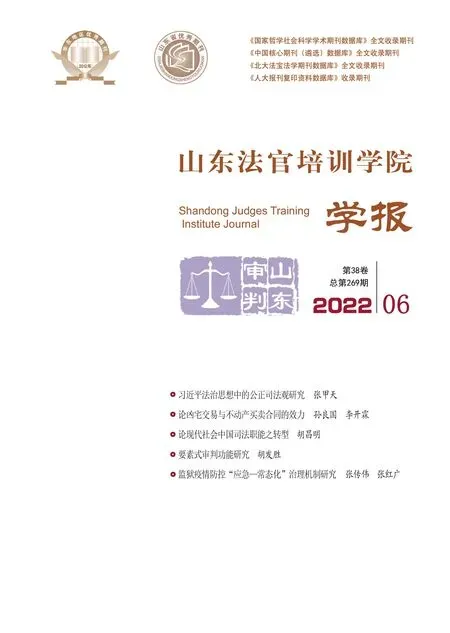論現代社會中國司法職能之轉型
胡昌明
“定分止爭”與“規則指引”是司法制度的兩項主要職能。定分止爭功能著眼于當下,追求案件的實質公平,以雙方當事人滿意、案結事了為旨,在司法實踐中往往表現為通過調解等手段著力解決當事人的一事一案的爭議;規則指引功能則更強調對法律規范的適用,主張通過訴訟向社會宣示一個行為的準則,主要表現為法官適用法律作出裁判。在中國長期的司法實踐中,法院的這兩項職能并不平衡,往往更加偏重定分止爭,而輕視甚至無視司法的規則指引功能。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有必要引導司法規則指引功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國法院傳統上抑制規則指引功能的原因以及現代司法強調發揮規則指引功能的理由和做法亟待理論梳理。
一、應然與實然中司法的職能定位
(一)司法職能定位的文獻梳理
法學家是法律發展的先導者,法學家眼中的法院也就是應然層面的法院。這一層面上,法院抑或法官具有什么樣的職能呢?①司法的職能主要是通過法官審理案件實現的,因此法官是司法職能的主要體現者和承擔者。蘇力教授認為,法院的基本職能有解決糾紛、規則確定及中國司法的一種特殊職能,即民族國家的建立。②參見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3、176頁。胡玉鴻教授認為法官角色的三個主要方面即糾紛裁決的主持者、訴訟活動的指揮者、終局結果的判定者。③參見胡玉鴻:《在政治、法律與社會之間——經典作家論法官的角色定位》,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蔣銀華教授則認為,“司法具有政治功能,其是國家意志的表達方式;司法具有民主功能,是維護民主體制的重要力量;司法的法律功能則表現為其對法律之統一適用上。司法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三者不可偏廢其一”④蔣銀華:《論司法的功能體系及其優化》,載《法學論壇》2017年第3期。。
由此可見,學界對司法職能的看法各不相同,其中論及最多的兩個主要功能:一是著眼于當下糾紛的解決;二是通過確定原被告雙方的權利義務,為社會提供一個普適性的規則,即規則指引。有時候司法的這兩種功能是統一的,能夠相輔相成,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既解決了糾紛,又確認了社會規則。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可能存在沖突,法官傾向于定分止爭還是規則指引,可能會采取不同的審判策略,甚至會導致不同的審判結果。因此有學者提出:“法院的基本職能究竟是落實及形成規則(普遍性地解決問題),還是解決糾紛(具體解決問題)?或者兩者在不可偏廢的情況下以何為重,并將向哪個方向發展?”⑤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頁。但是,這一沖突沒有引起法學界的廣泛重視,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對此主題的研究都不夠深入。
(二)司法職能的現實表達
從新中國成立到21世紀初,從法律的規定到媒體輿論的導向,再到司法機關自身的績效考核都可以看出,中國司法在實踐中更加偏重定分止爭功能,而不太重視發揮其規范確認的功能。
1.法律、規范性文件的規定
《憲法》第128條寬泛地規定了法院的職能,“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組織法》第2條規定:“人民法院通過審判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以及法律規定的其他案件……解決民事、行政糾紛……”
上述法條對法院的功能要么語焉不詳,要么只是強調了其解決糾紛功能,而考察革命根據地時期以來的法律發現,雖然中國民事訴訟的原則變動不居,但是在相當長時間內,都始終存在著重視糾紛化解,強調調解的傾向。一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馬錫五審判方式”和“楓橋經驗”一直備受司法機關高度推崇,此后又將“依靠群眾、調查研究、調解為主、就地解決”十六字方針作為民事審判的根本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二是1982年試行的《民事訴訟法》以“著重調解”作為民事訴訟的原則;1991年《民事訴訟法》雖然將“調解應自愿合法”代替了“著重調解”原則,但在司法實踐中仍然鼓勵調解,將各地法院的調解率作為績效考核的內容之一,并將善于做調解工作作為法官充分做群眾工作的一種體現;2012年《民事訴訟法》第122條還規定了普通一審民事糾紛的先行調解制度。三是各種司法政策也對以司法的定分止爭情有獨鐘。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要求充分發揮人民法院調解工作的積極作用。
2.輿論場的導向
在媒體和社會輿論場中,法院也主要扮演一個解決糾紛、定分止爭的角色。在各種媒體中,作為正面典型報道的法官形象大都是法官走下法臺,深入民眾,促成糾紛化解,實現案結事了。與此同時,法官主持正義,做出正確裁判這樣的報道卻鳳毛麟角。
以《人民法院報》為例,通過對刊載文章標題關鍵詞的搜索發現,近十年來,“調解”為關鍵詞的文章1192篇,以“判決”為關鍵詞的文章僅406篇,前者的數量是后者的2.9倍。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時,《人民法院報》特別刊發了《中國司法濃墨重彩之筆》一文,作者認為“調解成為當代中國最具有本土特征的糾紛解決途徑……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生命力……突破了單一司法解決的局限性,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成為現代中國司法濃墨重彩的一筆,是值得珍視的寶貴司法經驗與制度財富”①張建偉:《中國司法濃墨重彩之筆》,載《人民法院報》2019年10月1日,第19版。。另外,在一則有關調解解決糾紛的通訊報道后,作者對法官在解決糾紛中所體現出來的知識與智慧表示欣賞,稱贊“法官是在用自己的心靈與行為為社會追尋正義之規則,且也以其善言善行在影響和感染他人”②王建慧、景永利:《規則之治與非規則之治的博弈》,載《人民法院報》2004年8月5日,第4版。。
主流媒體大張旗鼓贊美的事例也大都是法院以解決糾紛為己任、追求案結事了,或者法官放下架子,深入人民群眾解決糾紛,對一份推理精妙的判決書、一次精彩庭審主持過程的報道和頌揚則難得一見。
3.法院的價值追求
法院內部的績效考核、總結和表彰,也非常突出調解等解決糾紛方式。
一方面,從法院的工作報告中我們可以管窺一二。十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的工作報告中還經常提及“加強訴訟調解”或者“調解優先”“充分發揮調解解決糾紛的職能作用”等內容,并將調解率高、調解結案作為法院的一項良好業績。“堅持調解優先、調判結合,提高調解質量……一審民商事案件調解與撤訴結案率達到64.6%。”①《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另一方面,在法院先進個人事跡的宣傳材料中,往往側重介紹其注重調解、化解糾紛的經驗方法。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授予金桂蘭同志“全國模范法官”的榮譽稱號的決定》中提到:調解是消除雙方積怨、化解矛盾糾紛的有效辦案方式,金桂蘭同志對每一起案件都依法耐心細致進行調解……在金桂蘭同志審結的案件中,90%都是以調解方式結案。②參見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教育局等編:《百姓的好法官金桂蘭》,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以第二屆“中國法官十杰”評選活動為例,十位杰出法官中,有七名的先進事跡材料中都提及“耐心為當事人做調解工作”“化解群眾糾紛”等內容。可見,法院自身的評判體系中,善做調解、定分止爭相當重要,是衡量法官優秀與否的標準之一。
二、中國司法實踐偏重“定分止爭”的原因探析
雖然學者認為司法具有定分止爭和規則指引兩項職能,然而在傳統司法實踐中,法院卻往往偏重定分止爭。究其原因,可以從社會環境和法院自身條件兩方面予以分析。
(一)社會環境的制約
第一,全國各地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中國的城市與農村、沿海與內地之間,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然而,法律作為一種社會規范,要求在規則面前一視同仁,這與中國的城鄉差別和地區差異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張力。一千元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人們只不過一頓飯錢;而在中西部的農村地區,則有可能是農民一年的生活費,因此,同樣盜竊一千元錢造成的社會危害存在天壤之別。這時候法律應該一視同仁還是區別對待?這種經濟水平的差異會讓法律的規則性、普適性無所適從,如果一味強調規則,就會出現《秋菊打官司》里秋菊的訴求與法律產品之間那樣的隔膜。③參見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
第二,社會尚未完全規則化。“真正要實現規則之治,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條件是規則之治的治理對象本身要具有一定程度的規則性。”①蘇力:《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頁。但是,中國的糾紛本身類型多樣,既有涉及現代商業活動的公司、股權類糾紛,也有大量涉及家長里短、雞毛蒜皮的鄰里糾紛,而這類糾紛通過訴訟來解決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在立案登記制改革后,大量的社會矛盾涌向法院,司法的規則指引功能對于這些糾紛很難有用武之地。例如,在一起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中,甲家的孩子上了乙家的房,踩碎了瓦。乙家便把甲家告上法庭,索賠32塊瓦。②參見潘劍鋒、齊華英:《試論小額訴訟制度》,載《法學雜志》2001年第1期。又如,筆者從前辦理的張某某訴北京某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損害賠償案中,經紀公司在未告知租戶原告張某某的情況下,強行更換門鎖,并將張某某的個人物品全部扣押。張某某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歸還其個人物品及身份證,但張某某無法提供物品損失清單。這些案件的處理難度不在于法律疑難,而在于根據現有證據法官難以復原案件的客觀事實,司法對此往往無能為力。這類糾紛進入訴訟程序后,在當事人沒有留存書面證據的情況下,法官不易查清事實,只能優先選擇調解方式結案。
第三,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在改革開放之后,直至上世紀末,中國的人口流動在不斷增長,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廣大農村地區乃至縣城大體上仍然是一個熟人社會。在日常生活中,規范村民言行的不是國家法律,而是由傳統維系的禮俗以及維持家族、鄉里之間感情關系的人情。③參見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8頁。現代司法提供的工具往往不足以解決熟人社會的矛盾。這不僅因為人們的關系越緊密,介入他們之間事務的法律越少,④參見[美]布萊克:《社會學視野中的司法》,郭星華等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而且因為親密關系妨害法律的應用,熟人間的交往通常不需要書面的文字材料,就像沒有人問自己父親、兄妹借錢還會打借條一樣,如果是普通朋友,就很可能要打借條,如果向關系更遠的人借,則必須打借條了。因此,一旦熟人之間發生糾紛,法院就很難查清事實,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調解化解糾紛更現實,也更便利。
(二)中國司法的現實局限
中國司法存在的一些現實局限性也使得法官更傾向于采用定分止爭的方式。
首先,中國的司法機關職責多元。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法官地位崇高,職責明確。“法院專司裁判職能以及由裁判職能而衍生的相關職能,原則上不承擔與裁判職能無關的日常性‘事務’工作。”⑤丁以升、孫麗娟:《論我國法院糾紛裁判功能的理性建構》,載《法商研究》2005年第2期。一個權威性強、地位崇高的法官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負責審理與裁判。但是,在中國的實踐中,司法機關除了審判、調查取證、案件執行等司法職能外還要承擔諸多其他司法之外的工作,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參與信訪化解、社會維穩,參加公益性社會活動,甚至包括招商引資和“創建文明城市”等等。①十八大以來的本輪司法改革加強司法人員的履職保障,要求司法人員不應從事與司法職能無關的其他事務。為此,2016年7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頒布了《保護司法人員依法履行法定職責規定》,其中第3條規定:“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要求法官、檢察官從事超出法定職責范圍的事務。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有權拒絕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安排法官、檢察官從事超出法定職責范圍事務的要求。”但是,就在這個規定頒布實施后不久,徐州市創建全國文明城市指揮中心要求包括司法機關在內的全市機關上街協助交警執勤,引發社會輿情。《人民法院組織法》中法院的職能除了懲罰犯罪、解決糾紛外還包括“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和權威,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進行”。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司法職能不僅僅是審判,法官只注重規則指引和審理裁判是沒有大局觀、政治不成熟的體現,這意味著法院必須以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為重,努力化解社會發展帶來的各種糾紛。因此,能夠利用各種方式化解解紛,讓當事人息訴服判,特別是不要形成涉訴信訪和涉訴輿情。
其次,法官隊伍素質參差不齊。法院能夠確認法律規則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法官必須具有專業的法學功底和法律思維。近年來,雖然中國法官的素質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與法治發達國家相比,法官整體素質和法律素養仍存在提升空間,②一份調研報告發現雖然大多數法官具有本科以上學歷(97.85%),但是其中35.79%的法官是在職學歷。參見胡昌明:《中國法官職業滿意度考察——以2660份問卷為樣本的分析》,載《中國法律評論》2015年第4期。特別是在一些偏遠的山區、農村地區的人民法庭,還有不少非科班出身,沒有經過法學專業學習的法官。讓沒有經過法律專業思維訓練的法官行使“規則指引”的職能就有點勉為其難,他們很自然地更傾向于做群眾工作,用調解來化解糾紛。
(三)法官趨利避害的心理
法官的趨利避害心理也會使得定分止爭更加符合法官的利益訴求。許多國家為法官制定了完善的身份保障制度,非因法定事由,不得將法官免職,法官有長期、穩定的任期,有些國家的法官甚至終身任職。③在英國,高等法院法官的任職是終身的,或者任職到法定退休年齡為止。美國聯邦法院法官除非因違法犯罪受彈劾或者自動辭職,其職務是終身的,工作也是終身的。澳大利亞法官實行終身制,除非由于行為不端,可一直任職到退休年齡。法國的憲法和法院組織法均規定,法官實行終身制,法官在任期內,非因可彈劾之罪,并經法定程序不得被免職、撤換或強令退休。參見胡昌明:《中國法官保障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141頁。這種制度安排下,法官沒有后顧之憂。但是從中國法律的具體規定來看,《法官法》規定的法官懲戒與免職條款較多,法官在任職期內只需“經考核確定為不稱職的”等理由,與公務員一樣可以隨意任免。現實中,法官因正當履行職務而被錯誤免職、調離法院,甚至受到刑罰追究的案例時有發生。由此可見,中國法官身份保障的制度尚不完善,法官身份保障不力往往導致其在判案謹小慎微、反復斟酌。如果他們通過調解方式結案,不僅解決了糾紛,不會出現上訴,更不會發生發回重審、改判等“錯案”,也可以消除當事人信訪的后顧之憂。此外,法院普遍追求高調解率,甚至將調解率作為考核法官業績的指標之一,更是推動了法官傾向于以調解方式結案。
三、均衡發展兩種司法職能的必要性
雖然,中國司法突出定分止爭的功能有其社會、法律和法官心理基礎,但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過分偏重這一功能定位,忽視法律具有指引性的面向,則有可能產生一些負面影響,甚至可能會損害當事人訴訟利益,特別是過分注重調解無法適應現代法治社會規則治理的要求,無法為人們的行為提供更加明確的指引,從而增加因社會“失范”引發的矛盾糾紛。因此,未來規則治理功能將在司法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
(一)向陌生人社會轉型之必要性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隨著城市化的不斷發展,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7.92%一路攀升至2021年的64.72%,人口城鎮化水平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時間內提升了46.8個百分點。“在中國傳統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認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統一規則。”①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頁。但現在,這個熟人社會被逐步打破,漸漸向重視規則、有規則意識的陌生人社會轉型,實現了梅因所說“從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這為司法的規則之治提供了巨大的適用空間。因為,規則之治的一個前提是社會生活本身具有較高的規則化,社會現代化將每一個人在一定程度上標準化了,將我們的生活環境、行為方式,甚至是在某種程度上的思想感情都標準化、規則化了,只有這時,作為規則的法律才可能有效地起作用。由此可見,中國社會幾十年來城鎮化、現代化的轉型成為中國司法需要規則之治的社會背景。
(二)有助于為社會確定行為規范
法律規范較之于地域差別較強的道德、宗教、習慣等社會規范,具有較強的普適性和確定性。法律的這一性質決定了司法不能囿于解決糾紛,充分行使規則指引職能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法律作為普適規則,給人提供的就是一種內心的確信,在確定的規則下,每個人對該做哪些,不該做哪些,做哪些違法,侵權、違約、不法行為會導致什么樣的法律后果都一清二楚,而且一旦發生違法行為就必然受法律的懲戒,那么違法行為就會減少。司法作為法律規則適用的過程,就是將抽象的法律規范具化,成為民眾看得懂、理解得了的行為準則的過程。法院作為司法權的實施機構,為社會提供是非判斷的標準是其重要的職責之一。霍姆斯甚至認為:“法律就是法院事實上將做什么的預測。”也就是說,司法機關在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同時,應當發揮為今后的類似糾紛確定有效的法律規則和行為準則的功能。由此可見,司法不僅僅要解決眼前的、單個的矛盾糾紛,更為重要的是在解決一個個糾紛的同時宣示法律,解釋法律在現實生活中的運作方式,為社會提供一個確定且一致的行為規范。
(三)有助于消弭未來糾紛
法院通過判決確認規則,還有助于發揮規則指引的功能,使得諸多的矛盾糾紛消弭于訴訟之前,避免當事人陷入訴累的同時,也有助于減輕法院“案多人少”的壓力。通過法律經濟分析的方法可以清晰地揭示裁判消弭糾紛過程的機理。
基于“理性人”的假設,我們相信在訴訟中能夠獲益是絕大多數民事訴訟原告起訴的前提條件。假設原告的訴訟請求是J,他認為勝訴的可能性是P,而訴訟成本為C,那么,原告認為J×P>C時,才會采取訴訟方式解決糾紛,此時原告的收益為J×P-C。如果在法律規則確定,預期的裁判結果明確的情況下,被告贊同原告的訴訟請求是(J),被告也認可原告勝訴的可能性是(P),而被告的訴訟成本為(c),那么原告提出的訴訟請求使得被告在訴訟中面臨J×P+c的損失。如果在訴訟前被告同意給付原告的賠償額是A,當A≥J×P-C時,原告就不會再行起訴,而被告之所以會給原告賠償,則需滿足A≤J×P+c。所以雙方在訴訟前就調解或者說自行解決的條件便是J×P-C≤A≤J×P+c。①參見胡昌明:《民事案件調撤率的實證分析及規律適用》,載徐昕主編:《司法》(第二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那么,為什么不是所有的糾紛都有在訴訟前就雙方自行和解呢?原因在于現實中原、被告的P和J往往是不同的,若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重新假設:被告認為法院可能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是(j),而被告認為原告勝訴的可能性是(p),一般情況下j<J,而p<P,所以在j與J,p與P差距過大時就會出現被告愿意償付的數額小于原告的訴訟期望值,A<J×P-C,而A的大小則是由j×p+c來決定的,所以當j×p+c<J×P-C雙方就難以達成一致意見。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糾紛能否形成訴訟的關鍵在于J與j以及P與p之間的差距,如果PJ-pj<C+c,則雙方可能達成訴前和解(或者訴訟中的調解),如果雙方對于判決結果預期的差距過大,PJ-pj>C+c,則雙方永遠也無法自愿地解決糾紛。
由此,法官的裁判之所以能夠消解社會矛盾的原因便一目了然了。司法的確定性要求法院遵循“同案同判”原則,確定的裁判能夠使雙方當事人的期望值接近最終的判決結果,原告降低自己的訴訟請求,被告也能更客觀地評價自己的預期損失,P×J與p×j的數值越接近,PJ-pj<C+c出現的可能性越大,當事人在訴訟前自行和解的機會大幅增加,糾紛成訟的可能性就降低,訴訟便可能在訴前化解。因此,通過確定性的裁判,法院在化解糾紛同時,也起到了減少矛盾糾紛成訴的作用。
四、中國司法職能轉型的價值追求
司法的性質、現代社會的城市化以及陌生人化特征都要求中國司法逐漸從偏重定分止爭的職能轉變為平衡司法的兩種職能,甚至側重規則指引功能。具體而言,在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國司法從單一側重定分止爭向兼顧兩種司法職能轉變具有如下價值。
(一)更易確立法官超然地位
在追求司法調解結案時,法官為了促進雙方達成一致意見,通常需要與原、被告單方溝通,要么加入原告一方說服被告履行義務,要么加入被告一方勸說原告降低訴訟請求。一旦法官加入這種“說服”,被說服者自然會認為法官站在了對方的立場上,從而對法官的中立立場產生動搖。此外,法官在說服一方當事人接受對方意見時,往往會積極介入案件的道德評價,對一方或雙方進行道德上的評判或教育。在主持調解過程中,法官也會制定具體的調解方案,基于調解方案“做雙方當事人的勸說工作”,如此以來法庭如同市場,可能動搖法官的超然立場。在司法體制改革背景下,“審理者裁判,裁判者負責”的改革原則賦予了法官更大的裁判權。因此,強調司法規則指引功能,需要法官作為社會公平正義的化身和是非的裁決者,應當具備更為嚴格的中立性,“這既是對司法者社會地位的一種理想要求,又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性”①謝暉:《價值重建與規范選擇》,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頁。。此外,法官還必須與雙方當事人都保持一定的距離,超然于訴訟雙方,如果法官一味追求定分止爭,法官之中立地位將受到損害,其超然中立地位也無法體現。
(二)為糾紛提供更明確的規則指引
近年來,由于受經濟發展與立案登記制等的影響,法院案件迅猛增長,法官審判壓力巨大。雖然,調解較之于判決具有節約法官撰寫裁判文書時間、提升案件息訴服判率等特征,本身有助于緩解審判壓力。然而,調解只是解決了眼前的個別糾紛,對社會行為較難產生指導意義和規范性,因此也就無法面向未來,無法預防矛盾糾紛的發生乃至形成訴訟。社會的飛速發展往往會出現新的矛盾糾紛,使原有的社會規范難以發揮指引作用,新的法律規范尚未建立健全,因此,一定程度上會出現法律規范空白的窗口期,這也是近年來“訴訟爆炸”的原因之一。調解可以妥善解決眼下的矛盾,卻難以為社會確立一個是非曲直的標準。用個別化的定分止爭去應對由于社會變遷和規范缺位造成的“案件潮”,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訴訟案件過快增長的問題。因此,亟待法院通過裁判文書,以司法確認的方式為一些新矛盾、新類型糾紛提供明確的裁判規則,確立人們行為規范的法律指引。
(三)更有利于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在訴訟中,任何一方都有其合法權益。法官通常會居中保證雙方享有同等訴權。但是,一旦法官受到“調解率”“服判息訴率”等影響,不同的結案方式會對自身的利益產生積極或者消極的影響,那么法官在庭審中就有了自身獨立的利益訴求,也就無可避免地會為了自身利益提升調解率,加快結案速度,減少撰寫裁判文書的勞動付出,降低案件發回改判、被認定錯案、上訴信訪的風險等,甚至不惜“強制”雙方調解。因此,雖然通常認為在調解過程中,訴訟雙方都進行了妥協讓步,但其實由于法官調解偏好的介入,最后達成的讓步大多數是單方的,往往以權利人放棄部分權利為代價。在法庭上,法官裁判者與調解者的角色混同,當事人會產生不接受法官調解,判決結果可能對自己不利的顧慮,從而違心地接受調解。這時,當事人之所以做出讓步,其實隱含了對法官審判權的一種屈從。所以,調解中的讓步并不一定完全是由當事人自愿做出的,也可能不是雙方同步、對等地退讓,這使得有的調解之所以能夠達成是以損害了部分權利人權益為前提的。因此,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調解的本質特征即在于當事人部分地放棄自己的合法權利,這種解決方式違背了權利是受國家強制力保護的利益的本質。調解的結果雖然使爭議解決,但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當事人的合法權利,這違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①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124頁。因此,如果平衡法院糾紛解決和規則指引的功能,降低法院和法官對“調解率”的偏好,鼓勵法官“能調則調、當判則判”,把調解和裁判作為兩種并行的結案方式,那么法官就會在法律關系明晰時敢于裁判,如此也就更有利于保障守法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公義。
(四)拓寬多元解紛途徑
司法并不是糾紛解決唯一的途徑,對于大多數糾紛來說,通過訴訟來解決的成本太高了。一方面是當事人的訴訟成本高。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不僅只有訴訟費,還包括圍繞訴訟而搜集、保存證據、聘請律師、參與訴訟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時間成本。另一方面,用訴訟方式解決糾紛司法成本高昂。司法成本既包括案件辦理所需花費的陪審員、證人的誤工費、電話費、文印費、調查取證、保全、查封、執行等差旅費等直接成本,也包括法官辦公、開庭的場所和設備、司法機構的日常管理和運行、法官、司法輔助人員的工資、遴選、培養法官等間接成本。此外,訴訟遵循嚴格的程序,從立案、答辯到審理、一審、二審都有一定的期限,有些訴訟甚至拖延數年。國家為此承擔著巨大的訴訟支出,司法是一種昂貴的解決糾紛方式。
既然司法成本高昂,訴訟不應作為社會主要,乃至唯一的糾紛解決途徑。應當在保證訴訟渠道暢通的同時,擴大多元糾紛解決路徑,引導大量瑣碎的、重復的、不適合司法解決的糾紛分流到訴訟程序外,由相對快捷和低成本的行政機關、行業組織、仲裁機構、基層調解組織等來加以調處和解決。讓法院將更多的精力用于審理、裁判疑難復雜的有典型意義的糾紛,為社會確立行為規則,用確定的規范來指引日常行為。
結 語
目前,法院之所以片面側重定分止爭的功能,是由社會經濟和法院自身條件決定的,而且相當多的案子也能夠通過這種方式得以解決,甚至比裁判更能夠贏得當事人的好評和媒體的贊譽。但是司法不應當僅僅考慮現在和過去,中國社會也在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之中,各種現代社會的信息通過廣播、電視、手機等媒介,也能夠傳播至最偏遠的山區,那里的村民也可以和北大教授同時觀看《法治進行時》,接受現代法律和規則的熏陶。隨著社會不斷現代化和規則化,中國法院在化解社會當下矛盾和糾紛的同時,應當慢慢地抬起頭,面對未來更加規則的社會,逐步承擔起規則指引的重任。如果說司法就是解決糾紛,那么它的目標就是向后看——恢復原狀。但由于要考慮規則之治,司法就得更多地面對未來的問題。只有這樣,法院才能夠更加從容地面對“案件潮”,為化解糾紛與社會治理做出更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