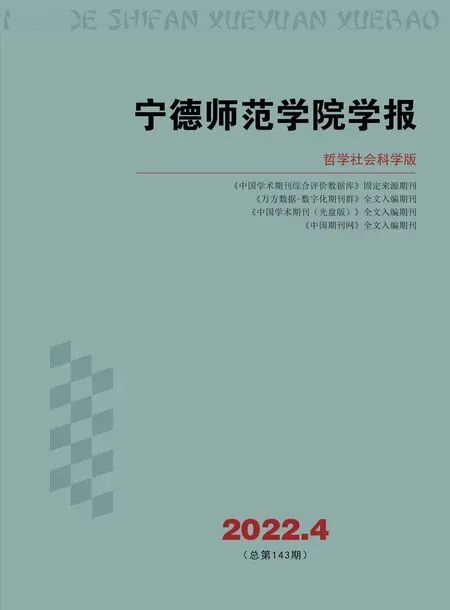高管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影響程度的研究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經驗數據
陳艷聲 林 瀅
一、引言
自上個世紀80 年代末以來,股權激勵計劃在美國企業中的盛行程度不斷上升。[1]我國于21 世紀初期才開始推行企業的股權激勵計劃,彼時正值我國上市企業高速發展的階段。2006年,有關部門頒布了《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管理辦法》及《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推動了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2]
股權激勵是隨著高管與股東之間不斷在博弈中尋找共同訴求而誕生的一種產物。[3]它讓高管扮演了股東的角色,激發了管理層經營管理公司的潛力,有效地緩解企業因兩權分離導致的代理成本與股東財富最大化之間的矛盾。同時,股權激勵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提高管理者的風險承擔水平,進而為企業獲得較好的業績。因此,股權激勵可通過降低代理沖突、減少管理層風險規避行為等方面來提升公司績效水平。
國內外文獻有關股權激勵計劃的研究范圍廣泛,然而,在提升公司績效水平方面股權激勵是否真的在其中起到促進作用的問題上,大家說法不一。當前學術界中存在4種主流的觀點,即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不相關、正相關、倒U 型、負相關。且對于不同行業、不同所有權性質以及不同發展期的企業來說,股權激勵是否會對企業績效產生不同程度的差異影響,現還沒有大量的研究數據支撐。
二、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有關研究高管股權激勵影響公司績效的研究方向主要可包括以下三點:
(一)股權激勵與公司績效的相關關系
在早期股權激勵的研究中,以Jensen[4](1976)為代表的學者得出了股權激勵計劃有利于激勵高管提高公司績效水平的研究結果。在股權激勵計劃剛開始在美國推行的時期里,Demsetz 和Lehn[5]認為股權的所有權制度對公司績效起不到激勵作用。同理,我國學者鄒靖[6]發現我國500多家國有公司的績效水平與高管股權激勵之間不存在太大的相關關系。
而早在學者鄒靖之前,相關專家得出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并非呈現比例關系的結論,而是呈現非線性關系,包括倒U 型(范合君、初梓豪[7],2013)、函數型(李曉玲[8],2008)、提升型(周云波和張敬文[9],2020;張敬文和田柳[10],2020;萬里霜[11],2021)。
(二)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差異
在研究公司績效初期,高管股權激勵大多被專家們看作一個單獨的解釋變量。[12]隨后很多專家逐漸將研究重點轉移到高管股權激勵在不同條件(或環境)下對提升公司績效管理水平的影響程度上的差異。包括任職時間、學歷和年齡的環境影響(白潔[13],2013),研發投入的促進作用(齊秀輝等[14],2016)。周軍、張欣然(2019)則發現在國有企業中,高管股權激勵計劃在高度制衡公司里的表現效果并不如在低股權制衡公司里的表現效果好。[15]且相較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可能設置更嚴格的行權業績條件來實施高管股權激勵計劃(顧秀敏[16],2020)。
除此之外,高管股權激勵的激勵物類型可能也是導致股權激勵計劃出現激勵效果不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當前,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權這兩種股權激勵計劃是全球企業普遍推行的主流股權激勵計劃,[17]有關專家大多用這兩種股權激勵機制來實證分析激勵物類型對公司績效的激勵效果差異,國外學者大多更加肯定股權期權對公司績效的激勵作用,而國內學者大多支持限制性股票。此外,有相關文獻表明,企業性質、發展階段、以及行業特性等不同因素都可能使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產生不同程度上的激勵差異。
(三)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負面影響
盡管大量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企業高管股權激勵計劃對公司績效的影響都是正向促進的,股權激勵計劃依然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股權激勵會造成盈余管理現象,損害公司價值,影響企業績效。[18]王家美(2020)指出真實盈余操縱在實施高管股權激勵計劃時會對未來經營業績造成不利影響。[19]
綜上所述,國內外文獻有關股權激勵計劃的研究范圍廣泛,然而,在提升公司績效水平方面股權激勵是否真的在其中起到促進作用的問題上,大家說法不一。且對于不同行業、不同所有權性質以及不同發展期的企業來說,股權激勵是否會對企業績效產生不同程度的差異影響,現還沒有大量的研究數據支撐。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假設股權激勵可以提高公司績效
與股權激勵相關的理論有以下三類——分別是委托代理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20]委托代理關系使得管理層與經營層之間存在一定的利益沖突。即便是在有高管監督機制的情況下,高管也可能傾向于在職為自己謀求更多的利益,其工作的積極性可能沒有得到更大程度上的調動從而不利于公司長遠經營發展的意識,提高了公司的代理成本,從而不能更有效地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的企業目標。股權激勵讓高管向股東的利益訴求看齊,當高管的利益訴求與股東能有較大重合的地方時,高管的主觀能動性將可能更大程度地被激發出來,從而使得高管為雙方“共同擁有的公司”創造出更大的企業價值。
H1:股權激勵促使高管更加努力地提高公司績效水平。
(二)假設上市初期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影響更顯著
由于企業存在生命周期,所以股權激勵對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公司的績效的提升效果有所不同。由于高管對企業初創期或成長期的發展前景有一個較好的預期,所以在此期間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激勵效果可能會更好;對處在成熟期亦或者衰退期的企業實施股權激勵,由于企業此時發展穩定或走下坡路,這可能影響著高管對公司發展前景的信心,股權激勵可能收效不佳。由上面的分析假設對臨近IPO時實施股權激勵的公司來說,股權激勵計劃對企業高管的激勵效果更加明顯。
H2:股權激勵對處在上市初期的企業高管的激勵效果更好。
(三)假設股權激勵對非國有企業績效的激勵效果更好
由于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在所有權性質上的不同而導致它們在股權分布、社會責任、以及經濟效益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由此可以推測,在相同股權激勵強度的前提下,股權激勵效果在國企與非國企之間仍存在一定的差異。
H3:非國企股權激勵比國企股權激勵的效果更好。
(四)假設限制性股票股權激勵比股票期權的效果更顯著
當前,我國資本市場上主要使用的股權激勵計劃有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權以及股票增值權。研究表明,高管股權激勵物的不同種類在公司績效的影響方面存在差異。就提高公司績效管理水平而言,限制性股票可以起到正向促進的作用,但股權期權對其的影響呈“倒U型”變化。[21]
股權激勵機制中有關限制性股票的設計原理如下:在獲得股東們同意授予的一定數量的股票之后,高管需要在其工作崗位上更加勤勉盡責地提高任職期內的業績水平,以便于在達到約定的績效范圍時套現股票;但如果高管沒有實現套現股票的條件,企業就會以“激勵價格加同期定期存款利息”的方式回購高管持有的股票。[22]股票期權激勵計劃會授予高管一種權利:在未來某個行權期內選擇以約定好的價格購買上市公司股票或選擇放棄購買該公司股票的權利,這樣做可以使得高管更加努力地為企業創造價值,以便其在未來可以利用更大的價差收獲到更大的經濟利益。與股權期權激勵計劃相類似,股票增值權激勵計劃也允許高管在不支付資金的情況下對其進行股權激勵。因此,相較而言,限制性股票可能需要高管為公司的發展投入更多的精力,因為股票價格的漲跌與高管的利益息息相關,并且一旦未達到業績要求,高管就無法解鎖,而股票期權和股票增值權是一種權利而非義務,且需要高管支付的資金較少,其前期投入成本較小。
綜上,限制性股票計劃可能比其他兩種類型更能起到激勵導向作用。
使用單一的“股票期權”或單一的“限制性股票”是我國資本市場上股權激勵物類型的主流。很多企業也會使用“股票增值權”來作為公司的股權激勵計劃,然而,“股票期權混合股票增值權”或者“股票期權混合限制性股票”等其他股權激勵機制相互組合的方式幾乎沒有公司采用。因而,本文決定采用“只使用一種主流的股權激勵的激勵物類型”的企業樣本的數據:即分別對只使用“限制性股票”和只使用“股票期權”的公司的激勵效果進行研究分析,并提出假設4。但為了進一步驗證這個假設的可信度,本研究在此假設的基礎上還增設了“股權期權+限制性股票”的實驗對照組。
H4:限制性股票對高管的激勵導向作用比股票期權顯著。
四、變量與模型設計
(一)樣本數據說明
為了使研究結論更具有說服力、時效性,本研究使用了CSMAR 數據庫中有關2012 年—2019 年A 股上市公司的樣本資料,并去除了金融保險行業、房地產行業、ST類上市公司、公司性質出現變化的公司以及剔除了樣本期內有關變量的數據不全的公司樣本,最后收集了372 家A 股上市企業的2976 個非平衡面板數據,樣本行業和年度分布見表2。
(二)變量設計
1.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
通過查閱相關文獻資料和參照現行的通用做法,本研究決定分別用資產收益率(ROA)和高管持股比例來作為被解釋變量公司績效[23]和解釋變量高管股權激勵的替代變量。
2.控制變量
根據大量現有的相關文獻研究情況,決定將企業成長性(Growth)、兩職合一情況(Pos)、公司規模(Size)、上市年限(Ln(1+age))、資本結構(Lev)、以及企業所有權性質(State)作為本研究的控制變量。各研究變量的定義見表1所示。

表1 變量含義
(三)計量模型
本研究主要使用橫截面OLS 回歸模型和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來構建以下4 個回歸模型,其中,橫截面OLS的回歸模型(模型1)如下:
模型1:

面板數據固定效應回歸模型(模型2)如下:
模型2:

模型3:
研究不同所有權性質下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差異時,將樣本分成2個子樣本——國企組和非國企組,并分別對它們應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

模型4:
在研究不同股權激勵物方式對公司績效的有利差異時,依據本文決定采用的兩種股權激勵方式對已選樣本進行進一步的分類和數據剔除,分別是只使用股票期權組(O)、只使用限制性股票組(R)以及使用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票組(O+R),并分別對它們應用面板數據的固定效應。

五、模型檢驗與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從表2和表3可以得出:

表2 本行業和年度分布

表3 模型1和模型2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1)研究結果的資產收益率的均值為0.038,表明所選取的樣本公司的總體業績不太突出;
(2)高管持股比例的中位數為0.019,均值為0.119,最小值為0,說明A股的股權激勵強度比較小;
(3)上市年限的最小值約為1.609,最大值為3.367,這表明A股的上市年限存在較大的差異;
(4)從其他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可以看出,企業成長性的標準差較大,表明所選企業之間的發展水平存在較大的差距,即它們可能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此外,資本結構的差距也比較大。
通過表4可知,國企中Equity高管持股比例的均值、中位數和最大值都低于非國企,而且國企公司績效的均值低于非國企績效,說明所選的國企樣本對高管進行股權激勵的積極性并不太高,初步驗證了假設3。

表4 模型3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模型3和模型4的描述性統計見表4和表5所示。

表5 模型4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二)相關性檢驗
各研究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如下表6所示。在1%的水平下大多研究變量的相關系數均表現顯著。并且ROA 與Equity、Pos 顯著正相關,與Size、Age、Lev 顯著負相關,粗略證明了假設1 和假設2。另外,控制變量之間以及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并不是很大,這表明本研究的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可能沒有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表6 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

續表6
(三)回歸分析
回歸結果分別見表7、表8所示。F檢驗結果顯示,固定效應模型比隨機效應模型更適用于所選樣本數據的表現情況。Hausman 檢驗發現固定效應模型要更為穩健。故決定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來回歸分析本研究的四個假設。

表7 模型1、模型2、模型3回歸結果

續表7

表8 模型4回歸結果

續表8
由表7可知,高管股權激勵這一變量在橫截面估計模型的回歸系數為0.058,且在10%水平下顯著可靠,其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里的回歸系數為0.053,且在1%水平下顯著可靠。兩個模型的回歸結果證實了假設1的結論,即實施高管股權激勵計劃與沒有實施的相比,更能提升公司績效水平。之所以股權激勵計劃能較為有效地提升公司績效,是因為接受股權激勵計劃的高管多了一重“股東”的身份,這使得高管可能更加勤勉盡責地為公司的長遠發展而服務,從而提升了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公司的績效水平。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之所以只將“高管”的持股比例作為研究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關系的替代變量而不考慮如技術研發人員等員工的股權激勵的持股比例,也是因為考慮到高管的管理決策對公司經營成果的影響更大一些。
此外,Age可能起到抑制提升公司績效的作用,這表明上市公司的上市年份越長,其公司績效的表現越差,同時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激勵效果也呈遞減的趨勢。這可能源于公司在企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發展階段的主要表現,因而上市年份越長,股權激勵效果越差,即公司績效的增長程度較之前相比會更小一些。因此,本研究的假設2是可以成立的。
模型1和模型2的研究結果見表7所示。
由表7,國有企業股權激勵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而非國有企業股權激勵的回歸系數顯著,驗證了假設3 即對非國企實施高管股權激勵機制的效果更好。這大概是由于政府在很多國有企業里扮演著大股東的角色。由于國企承擔著比民企更大的社會責任,其最終目標里包括社會責任(如,追求環保效益等),所以國企里的很多項目并非以凈現值最大為目標,而非國有企業大多以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或企業價值最大化為公司目標。兩者的所有制差異可能就造成了股權激勵促進作用的差異。此外,國企高管的獎金薪酬通常不與公司績效掛鉤,而非國企高管的獎金薪酬則與公司績效息息相關。
綜上可知,由于國企與非國企在股權結構、公司目標以及高管薪酬來源等方面的不同,導致股權激勵計劃的激勵效果不同。
由表8,“股票期權(R)”樣本組下的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影響顯著,而“使用股票期權(O)”樣本組以及“使用股票期權+限制性股票(O+R)”樣本組對公司績效的激勵作用不顯著。這說明股票期權的激勵效果低于限制性股票。證明了假設4 成立的可信度。這一方面可能源于股票期權套利無需支付額外資金,降低了高管經營公司的沉沒成本,對高管勤勉盡責的督促作用較低;另一方面,股票期權的收益源于二級市場的增值收益,被授予股票期權激勵計劃的高管會重點關注二級市場的股價,但其并不總是與公司的真實價值掛鉤,從而降低了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與經營者的業績的關聯度。此外,到了行權期,高管可能只顧對股票期權進行套利而不顧公司長遠發展,長期來看不利于高管為企業的發展創造更大的價值。而限制性股票具有“達到一定的解鎖條件方能套現”的特點,這可以使高管在任職期里擺正“職業經理人”和“股東”的雙重身份,從而有利于解決高管的身份矛盾問題。綜上,盡管股票期權在提高公司績效水平上具有一定的長期性和激勵性,但是股票期權對高管的約束力還是要比限制性股票來得弱一些。
(四)穩健型檢驗
將原模型中的解釋變量Equity“高管持股比例”用“高管激勵標的物數量占激勵標的物總數量的比例”代替進行再次檢驗。結果顯示,回歸分析系數的顯著性與原模型基本一致,從而驗證了本文模型的穩健性。(表9)

表9 模型1多元回歸和穩健性回歸結果

續表9
六、結論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果,并結合我國A 股上市公司的特點和股權激勵方式的特征,由此得出的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對高管實施股權激勵計劃有助于促進公司績效管理水平的提高,可能是由于有效的績效管理需要較長期的激勵機制來約束。這是因為委托代理關系導致了高管與股東的利益不一致,而實施股權激勵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高管的道德風險,調動高管的主觀能動性,從而激發其管理決策的潛力,提高工作執行力,努力工作,克服困難,恪盡職守,為企業的利益盡更大努力。
第二,在企業不同發展階段中,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促進作用是不同的,成長期需要更多的股權激勵。這說明股權激勵對企業高管來說不一定是長期有效的,它的激勵作用可能存在一定的邊際遞減效應,它的激勵效果也許要依賴于公司當時的發展潛力,因為這可能影響高管對公司未來前景的信心,進而在一定程度上上影響高管對提升績效水平的努力程度。
第三,在非國企里實施股權激勵計劃要比在國企里實施的激勵效果更好。這可能是因為國企與非國企的所有權性質和公司目標的不同所致,國企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即使面臨虧損也還有相關政府進行大力扶持和補助,而非國企大多沒有太強的政府背景,它的企業目標是尋求股東財富最大化,所以在面臨績效評價時,它比國企可能更加重視一個項目的盈利能力,從而對高管提升公司績效的水平的管理決策能力尤為看重。此外,非國企高管的薪酬一般與公司績效掛鉤,股權激勵對非國企的高管的激勵作用更大。
第四,就正向激勵高管的效果而言,只使用“股票期權”或使用“股票期權+限制性股票”的激勵方式不如只使用“限制性股票”激勵機制的效果好。股票期權和限制性股票同樣都能對高管起到激勵作用,但與限制性股票不同的是,股票期權更容易讓高管獲得激勵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票期權的激勵效果,說明不同的股權激勵機制設計產生的激勵效果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除了應該具有激勵功能之外,股權激勵機制還應具有監督與約束的功能,以便更好地對高管發揮激勵作用。
七、啟示與建議
根據本文研究結論得到的啟示,筆者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一)結合企業所有權性質類型來決定是否對公司高管進行股權激勵
國企高管股權激勵與非國企的相比,后者激勵效果更明顯。因此,鑒于國企與一般企業的不同,國有企業可考慮對高管采用其他形式的激勵方式,而不僅僅采用股權激勵來促使高管努力工作。而對于非國企來說,可適當地實施股權激勵計劃,以便更好地激發高管的主觀能動性,從而讓公司的盈利業績更上一層樓。
(二)依據企業的不同發展階段,適度調整股權激勵強度
高管股權激勵計劃的激勵效果會受到企業不同時期發展情況的影響。因此,企業可結合自身的戰略布局和當前行業的發展形勢等具體情況,適度地調整高管股權激勵強度,防止出現高管在“行權期”里扎堆套現、減持股票的“股權激勵陷阱”。
(三)設計適宜的股權激勵機制
設計一種考慮了公司發展狀況并有助于其更好地成長的股權激勵機制。從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來看,這樣做可以用較小的成本取得較大的激勵效果。結合上述研究結論和不同的股權激勵方式的特點可知,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更能實現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促進效果。因此,企業可結合所處行業類型的特點、公司的具體情況以及不同激勵物類型的優缺點等方面來綜合考慮建立一套科學合理的股權激勵計劃。例如,企業可建立適當加大限制性股票比重的股權激勵機制,以防止高管做出太多只顧短期內快速提升公司績效而不顧公司長遠發展的管理決策行為。
本文研究的政策啟示在于:高管股權激勵在公司的發展上有著較為重要的影響,它的存在可以幫助企業進一步實現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企業應結合自身情況,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股權激勵機制緩解因兩權分離帶來的管理層與經營層之間的矛盾;有效的股權激勵機制可以更好地激發高管的工作積極性,以便其盡最大程度地發揮其領導和決策才能,從而為企業創造更大的價值。
注釋:
[1]王棟、吳德勝:《股權激勵與風險承擔——來自中國上市公司的證據》,《南開管理評論》2016年第3期。
[2]扶青、謝作為:《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影響實證研究——基于限制性股票與股票期權視角》,《財務管理研究》2020年第2期。
[3]閆雪菲:《高新技術企業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的影響》,《商場現代化》2021年第5期。
[4]Jensen,M.C.&M.William.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1976,3(4):5-50.
[5]Harold,Demsetz.&K.Lehn.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Causes and Consequences,1985,93(6):1155.
[6]鄒靖:《股權激勵政策提升了公司績效嗎?——來自國有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財會通訊》2016年第6期。
[7]范合君、初梓豪:《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倒U型影響》,《經濟與管理研究》2013年第2期。
[8]衡金金:《股權激勵對企業績效影響研究綜述》,《廣西質量監督導報》2019年第7期。
[9]周云波、張敬文:《經理人股權激勵可以提升企業價值嗎?——來自中國A股上市公司的證據》,《消費經濟》2020年第1期。
[10]張敬文、田柳:《股權激勵與上市公司經營績效關系研究——基于分析師關注的視角》,《南開經濟研究》2020年第5期。
[11]萬里霜:《上市公司股權激勵、代理成本與企業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預測》2021年第2期。
[12]鐘潤偉:《我國創業板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績效的影響因素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20年。
[13]白潔:《上市公司高管特征與股權激勵對企業績效的交互影響研究》,《財會通訊》2013年第30期。
[14]齊秀輝、王維、武志勇:《高管激勵調節下研發投入與企業績效關系研究》,《科技進步與對策》2016年第15期。
[15]周軍、張欽然:《中國國有上市公司股權制衡度、管理層激勵與公司績效的實證分析》,《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9年第3期。
[16]顧秀敏:《公司治理結構與股權激勵行權業績條件設定》,《江蘇商論》2020年第12期。
[17]肖淑芳、石琦、王婷、易肅:《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方式選擇偏好——基于激勵對象視角的研究》,《會計研究》2016年第6期。
[18]林大龐、蘇冬蔚:《股權激勵與公司業績——基于盈余管理視角的新研究》,《金融研究》2011年第9期。
[19]王家美:《股權激勵是否會影響企業的盈余管理行為》,《中國集體經濟》2021年第10期。
[20]陳笑雪:《管理層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經濟管理》2009年第2期。
[21]孫錦濤:《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影響的研究文獻綜述》,《現代經濟信息》2019年第14期。
[22]孫偉艷、劉家媛:《上市公司管理層股權激勵對公司績效影響分析》,《中外企業家》2019年第31期。
[23]葉紅雨、聞新于:《管理層股權激勵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風險承擔的中介作用》,《山東財經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