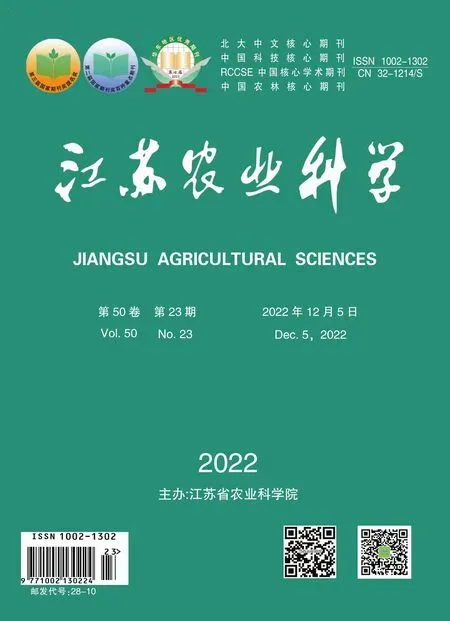江蘇省奶牛養殖結構與成本收益變遷研究
還紅華, 程金花, 王慧利
(江蘇省農業科學院,江蘇南京 210014)
奶業是我國畜牧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產值占畜牧業總產值約3.8%[1]。自2018年,我國提出奶業振興戰略以來,奶業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奶牛養殖規模化、標準化和現代化水平不斷提升,生產效率大幅提升,滿足了人們對不同類型動物蛋白的消費需求。然而,受資源環境制約,國內奶牛養殖成本始終居高不下,比奶業發達國家高約50%[2],直接影響了產業鏈底端養殖環節的利潤。
國內學者在不同規模或地區奶牛養殖成本效益比較分析方面已有比較成熟的研究。楊利等在對養殖場深入調研和數據分析的基礎上分析比較了北京市規模化奶牛養殖場的成本收益情況,通過計量經濟學模型對影響成本收益的因素進行了分析[3]。尹春洋利用2004—2011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以牛奶單位質量為基礎,對不同養殖規模奶牛的成本效益進行了分析,表明散養和小規模養殖更具有成本優勢,提出要提高奶農組織化程度,逐步推進奶牛規模養殖的發展[4]。張曼玉等采用成本收益法和數據包絡分析研究了不同規模下我國奶牛養殖效益及生產效率,表明規模化養殖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是我國奶牛養殖的重點發展方向[5]。郭策和馬長海對比了河北省、奶牛生產優勢地區和全國小規模奶牛養殖的成本效益,結果表明,2004—2013年間河北省小規模養殖成本呈逐年遞增趨勢,其平均成本利潤率達最高水平,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6]。楊曉彤等對比了中荷兩國奶牛養殖在原料奶價格、單產水平、養殖成本和養殖效益方面的差異,提出我國原料奶價格長期高于荷蘭和國際水平,存在單產水平較低、飼料成本和人工成本較高、規模經濟效益尚未凸顯等問題[7]。
已有研究主要基于成本效益比較,且主要分析全國或優勢產區的奶業競爭力,鮮有針對非重點或優勢地區奶牛養殖成本收益的分析。江蘇地區經濟發達、城鎮化率高,歷來不是全國奶業發展的重點區域,為確保穩定的奶源自給率,江蘇明確了奶業現代化、高質量發展走在前列的目標定位[8],在中大型規模養殖比例、牛奶產量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成效。奶牛養殖處于產業鏈的最低端,承受著巨大的市場風險,其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直接影響著產業鏈的各個環節[9]。本研究通過數據分析,闡述近10年來江蘇奶牛養殖業的發展特征,分析江蘇奶牛養殖業的成本收益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為建設高質量奶源基地、提高江蘇地區奶牛養殖收益提供數據支撐,并對落實奶業振興戰略、提高江蘇奶業競爭力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1 數據來源及其說明
本研究生產數據分別來源于《江蘇統計年鑒(2011—2020)》和《江蘇省農村統計年鑒(2011—2020)》,成本收益數據來源于《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11—2020)》,規模養殖數據來源于行業主管部門統計數據。按年末存欄量將不同規模養殖場界定為:≤49頭為散戶和小規模,50~499頭為中規模,≥500頭為大規模[10]。根據江蘇省的實際情況,散戶和小規模養殖場的年末存欄比例不足1%,因此在進行成本收益對比分析時只考慮中規模和大規模養殖場。
2 江蘇省奶牛養殖業發展特征與變遷
2.1 奶牛養殖量和生產水平總體平穩
由圖1可知,近10年,江蘇省奶牛養殖量和產奶量總體保持平穩,2016年養殖量和產奶量數據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是由于第三次農業普查數據接軌調整所致[11],在奶牛養殖量總體未變的情況下,產奶量在2019年出現大幅度提升。從發展趨勢觀察,全省的養殖量和產奶量總體趨勢與全國一致,養殖量和產奶量占全國的比重在2%以下,產奶量的占比高于存欄量占比,表明江蘇地區的奶牛生產水平相對較高(圖2)。而從不同規模的生產水平衡量,除個別年份,江蘇地區中規模養殖場的牛奶單產均低于全國水平;而大規模養殖場的單產遠高于全國水平(圖3)。


2.2 養殖方式逐步轉變,規模養殖比例不斷提高
隨著規模養殖的發展,全省奶牛養殖場的數量不斷下降,出現了2個斷崖式下降階段。第1個階段發生在2015年,與2010—2014年的平均水平相比,2015年的養殖場數量下降了58.9%;第2個階段發生在2017年,與2015年相比下降了53.4%(圖4)。


從不同規模養殖場的分布觀察,散戶和小規模養殖戶的數量占比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其年末存欄量、牛奶產量的比重也逐年降低。2010—2014年,散戶和小規模養殖戶數量占比約80%,其存欄量占比10%以上,產奶量占比從14.11%降至9.64%;2017年,散戶和小規模養殖戶的占比降至51.07%,存欄量占比2.20%,產奶量占比降至1.86%;2019年,散戶和小規模養殖戶的占比為20.59%,其存欄量和產奶量占比不足1%。這期間,年存欄100頭以上的中大規模養殖戶發展迅速,從初期約10%迅速發展至2019年的70%以上。奶牛的養殖主體和生產主體為年末存欄200頭以上的中大規模養殖戶,其中,尤以年存欄1 000頭以上的大型養殖場為主導,其養殖量和牛奶產量占全省的70%以上(圖5)。
2.3 養殖布局逐步變化,主產區優勢明顯
從全省的產業布局看,養殖量比較大的地區有徐州、蘇州、鹽城、宿遷和南京,這5個地區的奶牛養殖量和牛奶產量占全省比重60%以上,部分年份產奶量比重達70%以上。

2018年以前徐州的養殖量一直居于全省首位,2019年出現大幅下降;2010—2016年期間,蘇州的年末存欄量一直維持在2萬頭以上,從2017年開始出現下降;鹽城的養殖量逐年上升,并從2015年開始逐漸超過蘇州;宿遷養殖量一直穩定維持在2萬頭以上;2016年以前,南京年末存欄量維持在1萬頭以上,而從2017年開始銳減至約3 100頭(表1)。

表1 2010—2019年全省13市奶牛養殖年末存欄量
2017年之前,徐州的牛奶產量一直穩居第一,2018年有所下降;蘇州的牛奶產量在2014年略升高后又于2017年開始出現回落;南京的牛奶產量從2014年開始下降,并在2017年后降至較低水平;鹽城的牛奶產量除2018年出現短暫回落外,一直處于穩步上升趨勢,并從2018年開始取代徐州躍居全省第一;宿遷牛奶產量在2018年出現大幅提升。此外,連云港、泰州兩地在近年的奶牛養殖量保持逐年增加的趨勢,其奶牛產奶量也出現大幅度增長,未來可能會加入優勢產區行列。值得關注的是,宿遷地區奶牛養殖量總體保持穩定,但其牛奶產量卻在近2年出現大幅度增加(表2)。

表2 2010—2019年全省13市牛奶產量
全省范圍內,年末存欄1 000頭以上的大規模養殖場是生產的主體;但從近5年的牛奶產量觀察,各主產區的生產結構又特征各異。分析2015—2019年南京、徐州、蘇州、鹽城和宿遷5個地區生產主體的結構特征發現,徐州地區在各個年份年末存欄1 000頭以下的規模養殖場和散戶的產能優勢明顯;2016年之前蘇州地區年末存欄50~999頭的中大規模養殖場產能優勢明顯,隨后這種優勢逐漸削弱;鹽城地區年存欄1 000頭以上的大規模養殖場有持續的產能優勢;而宿遷地區年末存欄500頭以上的大規模養殖場產能優勢明顯(表3)。

表3 2015—2019年5個優勢產區不同規模養殖場戶牛奶產量分布
3 中大規模養殖場成本收益變遷分析
3.1 不同年份成本構成比較
奶牛養殖成本由生產成本和土地成本2個部分構成;生產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在98%以上,包括飼料原料及其加工費、水電煤費、醫療和死亡損失費、技術服務費、設備材料費、維修管理費等直接費用,固定資產折舊費、保險費、管理費和財務費等間接費用及人工成本;中大規模養殖場人工成本主要為雇工費。
從成本的變化(表4)觀察,不同規模養殖場單頭奶牛的總成本均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其中,人工成本的增加幅度最大;飼料原料成本也有增加的趨勢,但受原料價格變動的影響,呈起伏變化的趨勢;中規模養殖場的死亡損失費呈下降趨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理水平的提升,而大規模養殖場的死亡損失費變動較大,說明大規模養殖場的管理水平穩定性還有待提升。
從各項成本的構成(表5)觀察,飼料原料及其加工成本比例最高,其次是固定資產折舊成本和人工成本;中規模養殖場飼料原料及其加工成本比例總體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這一比例在2017年之前高于大規模養殖場,而近2年又略低于大規模養殖場;中規模養殖場人工成本的比例逐年提高,固定資產折舊成本比例除個別年份外基本保持穩定;大規模養殖場人工成本比例總體表現出先升后降的趨勢,而固定資產折舊成本比例總體呈下降趨勢。
3.2 江蘇地區中大規模養殖場單位成本、成本利潤率及其與全國的比較
從不同規模養殖場單位產奶量的成本觀察,由圖6可知,2010—2013年江蘇中規模養殖場的單位成本先升后降,同期全國中規模養殖場單位成本升降起伏明顯并呈相反的變化趨勢,2014年開始總體保持先降后升的趨勢,且全國和江蘇趨勢一致;大規模養殖場的單位成本總體表現先升后降的趨勢,但江蘇地區變化趨勢起伏較為明顯,且單位成本明顯高于全國。而在2019年江蘇和全國不同規模養殖場的單位成本趨于一致。

表4 2010—2019年全省中大規模養殖場成本變動趨勢 元/頭

表5 2010—2019年中大規模養殖場成本構成比例變化趨勢 %

對比江蘇地區與全國不同規模養殖場成本利潤率發現,由圖7可知,2010—2013年間,江蘇地區中規模養殖場的成本利潤率遠低于全國,從2014年開始出現強勁上升并遠高于全國水平,但又在2019年失去這種優勢;江蘇地區大規模養殖場的成本利潤率始終低于全國水平,甚至在部分年份出現虧損現象。而從規模比較發現,中規模養殖場的成本利潤率高于大規模養殖場的成本利潤率,且在江蘇地區表現更為明顯。從成本利潤率變化趨勢看,江蘇地區起伏明顯,而全國則保持相對穩定。該結果與單位成本變化反映出的結果一致。
10年間,2012、2013年江蘇大規模養殖場的單產水平處于谷底,而單位產奶量的飼料成本處于最高位(圖8),這也可能是造成虧損的主要原因。

4 結論與討論
近10年,江蘇省奶牛生產總體保持穩定,規模養殖比例不斷提高,大規模養殖場逐漸成為全省牛奶產量的主力,優勢產區主要分布在徐州、鹽城、宿遷等地。從成本效益看,盡管大規模養殖場的產能占比高,但中規模養殖場的成本優勢更為明顯,且生產效益穩定。因此,為進一步提升江蘇地區奶牛養殖的效率和產業的競爭力,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優化規模養殖場成本控制體系,降低養殖綜合成本。首先,養殖場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片面追求高投入、高產量在一定時間內可能會獲取豐厚的利潤,但奶牛養殖是一個經年的持續過程,過分追求高產量可能會對奶牛的健康、牛奶品質造成一定的影響。分析大規模養殖場的成本構成發現,多數年份單頭奶牛的死亡損失費遠高于中等規模養殖場。其次,飼料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在60%以上,大規模養殖場的資金實力雄厚、易于智能化設備的應用,應大力推廣精量飼喂、精細管理技術,提高飼料利用率和降低單位產奶量的飼料成本。最后,隨著勞動力的稀缺、勞動力工價的增加,勞動力成本越來越高,這在中等規模養殖場表現更為明顯。而從大規模養殖場的成本構成比例看,養殖設備機械化、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的提升盡管在一定范圍內增加了設備投入、能耗費用,但更能降低人工成本的投入。因此,應鼓勵和扶持中等規模養殖場設備的升級換代,降低人工成本,進一步提高中等規模養殖場的生產效率。

二、優化大規模養殖場內部管理,提升產出效益。從江蘇的生產實際看,大規模養殖場養殖量占比高、單產水平遠高于中等規模養殖場,但其單位成本高、成本利潤率相對低下。如何將大規模養殖場“量”的優勢進一步轉化為“質”和“效”的優勢是當前面臨的重要課題。應引導大規模養殖場在擴量生產的同時更加注重內部管理水平和技術效率的提升,要充分利用好省內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資源,為其奶牛養殖提供技術支持,通過專題培訓班提高養殖場人員的管理水平和技術水平,發揮出我省奶牛養殖的規模優勢。
三、優化奶牛養殖組織方式,提高原料奶產量和質量。從江蘇奶牛養殖結構的發展看,部分地區奶牛存欄量優勢并不明顯,但其產奶量卻在近年出現大幅度增加,這提示可能會存在“跨區域”的“公司+基地(或合作社或農戶)”的組織方式。“公司+基地(或合作社或農戶)”的組織方式對提高生產的組織化程度、避免盲目化生產和穩定市場價格有積極的作用,但也對奶源質量造成一定的隱患。應鼓勵和引導企業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通過品種、投入品、生產技術和產品收購的多方面“統一”加強對合作基地(合作社或農戶)的管理,保證原料奶的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