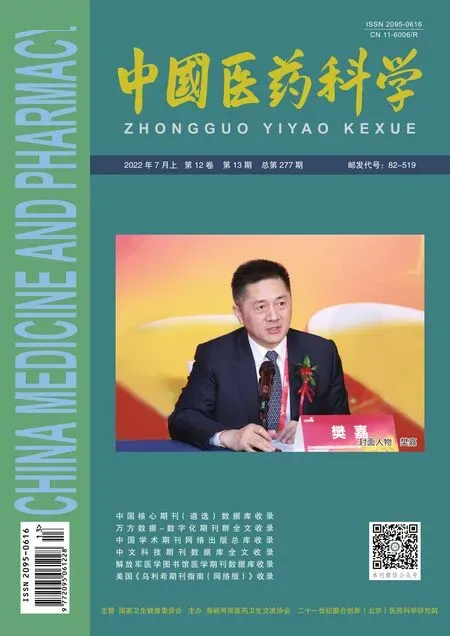膀胱癌的診療研究進展
盧文斌 王 尉 聶海波 張小明 呂 軍▲
1.廣東醫科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廣東湛江 524023;2.解放軍南部戰區總醫院泌尿外科,廣東廣州 510010
膀胱癌(bladder cancer,BC)是最常見的泌尿系統惡性腫瘤之一,全世界每年約有43萬新發病例和16.5萬死亡病例[1]。有研究[2]表明,BC是我國新發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泌尿系腫瘤。2015年,BC在中國全身性惡性腫瘤的發病率為580/1000,排名第13位。其中男性發病率為883/1000,排名第7位,女性發病率為261/1000,排名第17位[3]。同年,其在中國的病死率為每10萬人死亡2.37人,并且男性的發病率和病死率遠高于女性,約為女性的3倍[4]。BC的危險因素眾多,吸煙和職業接觸化學品是眾所周知的環境危險因素,盆腔器官其他惡性腫瘤的放射治療和慢性尿路感染也與BC的發生密切相關。BC具有發病率及病死率高的特點,早發現、早診斷及早治療對BC的預后極其重要。因此,文章就BC目前的診斷和治療展開綜述。
1 BC的分型
在組織學類型上,BC主要分為尿路上皮(移行細胞)癌、鱗狀細胞癌和腺癌等,尿路上皮癌占90%以上。根據TNM分期可分為非肌層浸潤性 膀 胱 癌(non-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NMIBC),為T1期及原位癌(tumor in situ,Tis),和肌層浸潤性膀胱癌(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MIBC),為T2~T4期[5]。NMIBC可逐漸發展成MIBC,兩者的治療方式及預后有極大差別,MIBC具有高復發率、整體預后差的特點,術前對于準確判斷BC是否存在肌層浸潤,對患者的治療決策和預后十分重要[6-7]。
2 BC的診斷
2.1 膀胱鏡檢查
目前,膀胱鏡檢查結合病理活檢仍是診斷BC的金標準。當前應用最廣泛的為普通白光成像膀胱鏡(white light cystoscopy,WLC),但隨著科技的發展,窄帶光成像膀胱鏡、熒光膀胱鏡(fluorescence cystoscopy,FC)已逐漸應用于臨床。WLC無需使用熒光劑,無熒光顯色效應,相對于FC來說,更易分辨腫瘤與非腫瘤性病變,假陽性率相對較低,特異性較高,但其對于扁平型尿路上皮病變、微小病變敏感性差,尤其是對于Tis,其檢測率低于T1腫瘤,容易漏診或術后殘留導致復發[8-9]。
窄帶光成像膀胱鏡通過光學濾鏡過濾紅色光譜,產生藍色(415 nm)和綠色(540 nm)光譜,可以差異性穿透黏膜,以增強黏膜中的血管系統顯像,使尿路上皮腫瘤的新血管可視化。研究[10]表明,窄帶光成像膀胱鏡的敏感度及在降低BC的復發率方面均優于WLC。而FC又稱為藍光膀胱鏡,通過腫瘤對光敏劑的選擇性吸收,在藍光背景下,腫瘤組織可呈現出紅色熒光,從而區別出腫瘤組織與正常組織。FC的敏感度、檢出率與窄帶光成像膀胱鏡相似,二者常作為WLC輔助手段,聯合應用可以提高BC的診斷率及降低復發率[8,10]。
雖然目前膀胱鏡應用廣泛,但其存在一定局限性:①對Tis靈敏度低,有可能遺漏癌變部位,檢查有效性取決于操作者;②屬有創操作,部分患者膀胱鏡檢查后可出現相關癥狀:排尿疼痛、尿頻、偶見血尿和感染[11]。
2.2 尿液細胞學檢查
尿液細胞學檢查是臨床上一種非侵入性的診斷方法,主要檢查患者尿液中是否存在脫落的癌細胞或相關標志物。尿液細胞學檢查對高級別腫瘤具有高敏感性,但對低級別腫瘤的敏感性較低[12]。尿液細胞學檢查的作用是肯定的,尤其是當患者存在高級別惡性腫瘤時,可作為膀胱鏡檢查的輔助手段。目前FDA批準的生物標志物包括核基質蛋白22(NMP22)、膀胱腫瘤抗原(BTA)、UroVysion?熒光原位雜交(FISH)探針等。
NMP22在BC患者的尿液中經常升高,其陽性提示尿路上皮細胞死亡,常作為BC的生物標志物。BTA檢測的原理是通過免疫測定法檢測在BC細胞系中發現的補體因子H相關蛋白,也被稱為人補體因子H相關蛋白(hCFHrp)[13]。FISH檢查通過對尿液樣本進行分析,尋找在載玻片上雜交的去角質尿路上皮細胞,進一步檢查在BC中觀察到的染色體畸變,包括染色體3,7和17的非整倍性,以及位點9p21的丟失[14]。大多數測試的敏感度隨著腫瘤分期或等級的升高而增加[15]。目前關于BC的非侵入性蛋白質生物標志物敏感度和特異度均存在局限性。為了改善BC的診斷,目前正在開展廣泛的研究,以發現敏感度和特異度更高的生物標志物。白介素-2(IL-2)、IL-6、IL-8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等炎癥因子已被獨立驗證為對膀胱內卡介苗治療反應有希望的預測因子,但目前還無直接證據證明其與BC的關系,需要通過多個機構的前瞻性臨床試驗進一步驗證[13]。
2.3 影像學檢查
BC常見的影像學檢查包括CT檢查、MRI檢查、靜脈腎盂造影、超聲檢查等。臨床上對于疑似BC患者,建議進行腹部和骨盆CT檢查,以評估膀胱、淋巴結、潛在轉移和任何并發的上尿路疾病。CT尿路造影的敏感度、特異度均較高,而MRI可在出現造影劑過敏或存在禁忌證的情況下作其替代方法。MR尿路造影較適用于低GFR或碘造影劑過敏且無急性腎功能衰竭的患者,當不允許進行造影劑,也可以利用T2序列評估尿路的非造影劑MRI[16]。
3 BC的治療
NMIBC和MIBC在管理、治療目標以及生存率和復發率方面存在很大差異。對于NMIBC,其治療目標主要是預防腫瘤進展以及限制復發。而對于MIBC,主要考慮的問題是根據患者的個體情況,決定治療方式,包括膀胱保留或切除、單獨局部膀胱治療還是需要全身治療等[17]。
3.1 NMIBC的治療
經尿道膀胱腫瘤電切(transurethral resection of bladder tumor,TRUBT)是NMIBC最常用的治療手段,一般的NMIBC可通過TURBT達到完全切除。但TURBT并發癥的發生率為4%~6%,其中尿路感染和明顯的血尿最常見。特別是對位于膀胱外壁的腫瘤,電流可能會刺激閉孔神經并導致肌肉收縮即閉孔神經反射(obturator nerve reflex,ONR),影響術中操作,甚至導致膀胱穿孔[18]。
與上述等離子電切比較,激光切除術具有更優異的止血性能,能改善術中視野。因其未產生電流,可以有效避免ONR出現,較傳統的TURBT更安全,圍手術期并發癥更少,近年來得到廣泛應用。目前經尿道膀胱腫瘤激光切除術中常用激光包括鈥激光[19]、綠激光[20]、銩激光等。經尿道銩激光膀胱腫瘤切除術中應用的銩激光波長為2 μm,具有良好的汽化效果,暴露的組織在加熱到90~100℃后汽化。汽化部分附近的組織則在60~80℃下凝固,凝固的組織層能更有效地止血[21]。銩激光的另一個優點是其穿透深度淺,可以降低膀胱穿孔的風險[22]。熟練掌握技術能實現完全去除腫瘤且避免腫瘤碎片化,可以減少潛在的漂浮腫瘤細胞的數量并降低種植轉移的風險[23]。
NMIBC術后復發率高,而且有10%左右的患者會進一步發展為MIBC,術后需進一步隨訪行規范的膀胱灌注化療。目前主要的膀胱灌注藥物有兩大類,一類為抗腫瘤化療藥物,包括吡柔比星、多柔比星、絲裂霉素等。另一類為免疫調節劑,包括卡介苗、干擾素、白介素等,還有一些新的藥物,包括多西他賽、吉西他濱等[24]。
3.2 MIBC的治療
對于MIBC,根治性膀胱切除術(radical cystectomy,RC)聯合盆腔淋巴結清掃術(pelvic lymph node dissection,PLND)和尿流改道目前被認為是標準治療術式。BC主要的轉移途徑為淋巴轉移,因為淋巴回流的雙側性,對側淋巴結受累很常見,41%的單側腫瘤患者出現對側淋巴結陽性,因此,在根治性膀胱切除術時建議進行盆腔淋巴結清掃術,至少應包括雙側髂外、髂內淋巴結和閉孔淋巴結[25-26]。雖然手術作為浸潤性膀胱癌的主要治療手段,但有50%患者在術后2年可出現復發轉移[27]。術前新輔助化療旨在控制局部病變和遠處小腫瘤轉移,降低手術難度,提高患者術后長期生存率[27-29]。術前新輔助治療包括全身新輔助治療、局部新輔助治療。全身新輔助治療主要采用靜脈化療方式,而局部新輔助治療主要為動脈灌注化療。靜脈化療最常用的為MVAC方案和GC方案,其他還有ddMVAC方案、CMV方案等。研究表明,MVAC方案與GC方案療效相當,但GC方案的毒副作用更小,安全性更高[29]。
盡管目前手術技術和圍手術期患者護理已趨于完善,但開放性RC即使在最有經驗的術者手中,圍手術期并發癥和病死率仍然很高[30]。微創手術被認為在術后恢復和減少圍手術期并發癥方面更有優勢,且不會影響遠期腫瘤治療效果。有研究表明,微創RC與開放性RC治療BC的效果是一致的,該研究還對BC的圍手術期變量和并發癥進行了評估,結果表明與開放手術相比,微創手術需要更長的手術時間,但患者失血量及輸血率更低,恢復常規飲食的時間以及住院時間更短,并發癥發生率也更低[31]。
此外,微創手術還可通過機器人手術系統進行,與普通腹腔鏡手術相比,機器人手術系統具有機械臂穩定、腔內無死角的特點,無論是在分離還是止血上,都可以調整至最佳角度。在其高清三維視覺系統下,可以良好顯示出解剖結構和血管方向,有效避免術中副損傷[32]。機器人輔助根治性膀胱切除術同時也具備患者失血量少,術后恢復快的優點,與開放術式在癌癥相關預后或生存率方面無顯著差異[33]。
還有許多MIBC患者存在與年齡相關的并發癥,如腎功能損害及心血管或呼吸系統疾病,對于這一部分患者,當評估其身體基礎情況不能耐受根治性膀胱切除術時,建議進行保留膀胱的TMT三聯療法,最大限度地經尿道膀胱腫瘤切除術結合外放療和同步化療[34]。
4 總結
目前對于BC的治療沒有絕對的標準,隨著研究深入和技術的成熟,患者的個體化診療正在逐步完善。相信在日后的研究中,會出現更為精準的腫瘤分期、更加優化個體化治療策略,為眾多BC患者帶來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