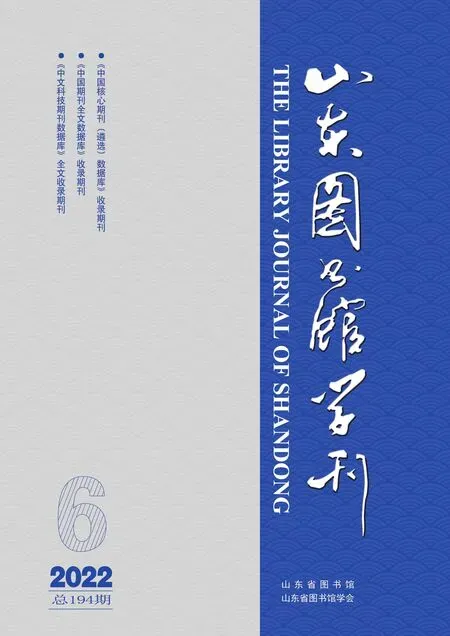消費文化視域下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建構研究
龔雨璐
(上海圖書館(上海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 上海 200031)
全球知識經濟和體驗經濟的快速發展使人們的消費需求提升,物質消費不再滿足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人們的消費逐漸轉向符號化的物品,即以物品為載體、追求文化需求滿足的符號消費[1]。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文化建設高度重視,習總書記也指出謀劃“十四五”時期發展,要高度重視發展文化產業。圖書館作為文化產業的關鍵組成,承載著社會知識、信息和文化的記憶,也肩負著“培育社會文明、傳承與傳播文化的歷史使命與時代使命”[2]。依托于圖書館的豐厚館藏,圖書館文創產品是“讓文化活起來”從而弘揚優秀文化、增強文化認同與文化自信的新興方式。目前,圖書館文創產品的種類和功能日趨同質化,只有建構特色符號,增強文創產品文化元素的共鳴,才能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
通過文獻梳理,目前對于圖書館文創的研究集中于國外圖書館文創產品開發的經驗總結、圖書館文創產品開發與模式探究、國內圖書館文創工作經驗、圖書館文創產品IP與品牌建設、博物館文創與圖書館文創的比較和對圖書館特色資源的文創產品開發研究等,尚未對目前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建構進行研究。因此,本文主要以符號消費理論為切入點,對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的符號建構現狀進行分析,探索更個性化、更符合消費需求的發展方向,更好地發揮圖書館文創的文化價值。此外,本文研究的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是指狹義的有形文化產品,不包括服務類產品。
1 符號消費與作為文化符號的文創產品
隨著經濟與科技的發展,物質的極豐富使人們對生產過程和商品的要求轉入文化的意識形態范疇。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在著作《消費社會》中提出,現代社會的消費已超過了生存需求的滿足,轉為了對物品象征性“意義”的消費。在物的時代,物品不僅僅以有用性而存在,它們集中渲染了一種情景,顯示了某種價值,成為了某種符號[3]。符號消費中,被消費的是理念,消費所涉及的是文化符號及符號間的交互關系[4]。因此,消費者購買文化產品主要關注作為文化符號的產品所象征的美感、情調、意義和內涵。
鮑德里亞還著重指出消費社會中存在“個性化”的特征,而個性的獲取在于消費的“差異性”[5]。符號消費中,產品和服務的同質化迫使企業賦予產品更多文化內涵作為符號價值,從而體現與同類產品的差異性。例如,可口可樂將傳遞“快樂”的文化理念融入其產品包裝的標志性飄帶。可見,作為符號消費的一種,文化產品的消費也需要重視差異性,沒有獨特的、區別于其他產品的文化符號,文化產品就會缺乏競爭力[6]。
作為文化產品的重要組成,公共圖書館開發的文創產品在開發時除了以“保護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深入挖掘文化文物資源的精神內涵”[7]作為導向,更應該重視如何將這些文化進行符號化建構并凝聚于產品中。一方面,公共圖書館在設計開發文創產品的過程中應該充分挖掘圖書館特色館藏與地域性文化特征,選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元素進行符號化,將文化的精髓融入到產品中,引發消費者對這些文化符號的情感認同,實現符號對文創產品的賦能。另一方面,符號消費強調了產品的“差異性”,因此公共圖書館在建構符號系統時不能夠忽略消費者的主體性。圖書館文創產品開發應根據大眾個性與共性需求特征,通過創新性的符號表達,讓文創產品更有生命力,也讓文化的傳播更加多元。
2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建構研究
文化軟實力提升、文化產業發展及文化強國建設的目標確立以來,國家多次制定相關政策,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自2016年制定并發布《關于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的若干意見》,各地緊隨其后,制定了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意見。2021年,包括文化和旅游部、中宣部等在內的8個部門再次發布《關于進一步推動文化文物單位文化創意產品開發的若干措施》。在一系列政策的驅動下,文創產品開發成為公共圖書館業務實踐領域的重點,在近年來得到快速發展,由簡單的產品變為提取文化元素進行設計的創意產品。
2.1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建構方式
此前對圖書館文創產品的研究中,已有學者對圖書館文創產品的設計方式進行了歸納。《圖書館文創產品開發的創新思路研究》一文中將國外圖書館文創產品的設計方式概括為:直接提取法、抽象變形法、寓意法和概括歸納法[8]。《公共圖書館古籍文創產品開發研究》一文中則將古籍類文創產品的古籍元素提取手法歸納為外觀仿制、內容提取與元素組合三類[9]。這些對館藏與地域文化中文化元素的提取與設計方法雖在命名方式上不相一致,但實際手法類似:均在設計時對文化元素進行提取、歸納、解讀與重構從而形成符號化注入產品中。
消費社會中,“消費的前提是物必須成為符號”[10]。因此,本文主要以符號的外延意義與內涵意義,對圖書館文創產品的符號化設計方式進行概括(表1)。符號的外延意義是指符號與物體間的直接關系,通常由視覺符號建構;內涵意義為該符號與指代或表述的對象所具有的特征的關系,即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表1 公共圖書館符號建構方式
在外延性符號的建構方式中,基于圖書館館藏的形態提取對符號進行編碼是最為直觀、形象地還原文化載體的方式,消費者通過產品的造型特征直觀了解文化。色彩提取的編碼方式則是通過色彩刺激人們的感官,喚醒對色彩所象征的文化隱喻的聯想。
在內涵性符號的建構方式中,內容挖掘是將書籍等豐富館藏中的名言警句、精美插畫、傳統紋樣等內容挖掘提煉,將經典轉移到文創產品中,形成新的文化符號,賦予文創產品更深層的內涵。故事內涵的編碼是將文創產品自圖書館館藏與地域文化中繼承而來的歷史故事、文化風韻、思想精神融入文創產品的符號中。群體認同則是在文創產品中建構的符號能夠激發某一群體對文化身份的認同從而激發的消費欲望。
2.2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建構現狀
筆者通過網絡調查的方式,對2017年成立的“全國圖書館文化創意產品開發聯盟”的37家聯盟發起館進行調查,選取其中開設線上商店的3家公共圖書館與其余7家在官方公眾號內對其文創產品有詳細介紹的公共圖書館作為統計對象,共計442件文創產品。隨后通過銷量、閱讀量排名方式,篩選最具代表性的產品共120件,并針對這些文創產品數據樣本進行研究,探究了目前國內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中符號建構方式的選取與整體情況。表2列舉了10家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建構方式的占比。

表2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建構方式占比
由表2可知,以上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中最具代表性的120件商品中,符號系統建構時運用形態提取進行編碼的占15.83%、色彩提取占2.08%、內容挖掘占54.59%、故事內涵占23.33%、群體認同占4.17%。整體而言,外延性符號系統占17.92%,內涵性符號系統占82.08%。
2.3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建構存在的問題
2.3.1 整體符號建構方式單一,缺乏美感
圖書館作為文獻收藏機構,精于對館藏文獻內容進行挖掘,這也使得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化的方式更偏重于內涵性符號系統的建構。在五種不同符號編碼的方式中,排名前兩位的就是內容挖掘與故事內涵。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的“故事化”特征尤為明顯,在產品的詳細信息與宣傳推廣中,該產品所包含的歷史故事、文化內涵都予以突出描繪,通過營造敘事空間,增強人們對文創產品中文化符號的理解和對文化價值的認同。
相對的是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對外延性符號系統建構的忽視,尤其對于色彩隱喻符號系統的運用寥寥無幾。然而,在對文創產品消費的研究中,有學者通過對國內外10家文博機構暢銷文創產品的研究表明:文創產品須滿足人們的“審美”需求,而這種對“美”的需求通常表現為外觀設計引發消費者的愉悅、興趣[11]。
因此,目前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系統建構中存在過度重視內涵性符號而忽視外延性符號的現象,這導致文創產品往往意蘊有余、而美感不足,缺乏吸睛元素。
2.3.2 內涵性符號建構淺層,缺乏差異性
作為目前被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運用最多的內涵性符號建構,在其建構過程中超過70%的圖書館偏向于挖掘內容。多數文創產品局限于挖掘館藏文獻中的圖像元素和名言佳句,并將它們直接運用于產品再賦予新的解讀,鮮有圖書館會在內容挖掘后進行重構與再創。這種淺層的內涵性符號建構導致圖書館的文創產品符號同質化嚴重,如重慶圖書館的“良友系列筆記本”與南京圖書館的“良友工作日歷”均為簡單呈現《良友》畫報的封面元素與畫報中的精彩之處,雖然產品載體不同,但實質挖掘成果相似,使得二者文化產品的文化符號雷同。
此外,群體認同這一深層次的內涵性符號建構也未被多數公共圖書館運用。然而,個體的文化消費選擇與消費者的身份是互相影響的。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認為文化消費一方面滿足了個人對文化等符號意義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在重構消費者的社會地位[12]。消費者往往出于對符號所代表的內涵的肯定引發文化消費的行為,而經由消費文化產品上附加的“意義”,進一步增強對文化和身份的認同。群體認同的編碼方式也更能體現消費者在文化產品消費中的“主體性”,只有滿足其個性化追求和文化、身份認同的產品才能獲得青睞。
3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建構的發展方向
3.1 注重差異,豐富符號建構思路
消費文化中,符號消費在某種程度上是差異性消費[13]。因此,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的符號建構應當注重符號編碼方式的多樣性。不僅需要加強對外延性符號系統建構的重視,更要加強對內涵性符號建構的深度挖掘。圖書館應從館藏資源、地域文化中選取具有美感的造型外觀、色彩色調,注重文創產品的視覺符號建構,使文創產品美學特征鮮明。然而,開發富含審美趣味的文創產品并不意味著產品承載的文化內涵、意義讓位于產品的美感。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仍應注重對內容的深層挖掘,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解構與重塑,將人文故事、群體認同融入所挖掘的內容中,形成獨屬于文創產品的文化符號。
由于外延意義的符號是文化元素的表現層,內涵意義的符號是文化元素的內在層,二者關系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因此,圖書館文創產品在建構符號系統時,既要注重外延視覺形象,更要將擁有共鳴的文化故事融入文創產品中。外延性符號系統的建構與內涵性符號系統的建構可以相互融合,在形態、色彩中呈現傳統文化,聯想歷史故事,喚醒群體文化自信與文化認同。
此外,在數字時代,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還可結合當前的AR、VR、3D打印等技術,打造圖書館文創的數字化符號。例如,國家圖書館與阿里合作開發的“翰香書墨”書法文具盒,運用AR和人工智能技術展示館藏碑帖[14]。在提升圖書館文創產品體驗感的同時,將科技符號與文化符號同時納入文創產品符號建構中,創新融合,使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符號建構多元化。
3.2 以人為本,發揮消費者的主體性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除了通過符號建構作為文化載體,發揮文化傳播的職能外,作為商品,其符號建構還需接受市場的考驗。目前,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的符號建構通常是以圖書館為主導的,由負責文創的館員進行選題策劃、內容挖掘、設計開發等環節,而忽視了其受眾作為消費者的主體性。以專業經驗主導文創產品開發的方式無法在符號建構與消費者之間建立全面的認知,以此生產的文創產品可能無法真正滿足消費者的文化需求。
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的符號建構需要“以人為本”,以受眾為中心,積極結合其他學科領域的技術或研究方法,獲取消費者對文化的感知、消費心理與偏好,從而增強消費者對文創產品及背后文化的認同感。例如,將感性工程運用到公共圖書館文創符號建構環節。澳門學者就如何從澳門歷史建筑中有效提取文化元素進而轉換為文創產品的符號進行了研究[15],通過感性工程理論與語義微分法,在澳門當地居民中進行調查,有效地提取受眾對澳門歷史建筑最具有情感訴求和深刻認同的元素并將之融入文創產品的符號設計中。
3.3 符號傳播,強化文創產品文化意蘊
在符號建構方面,具有傳播力的文化符號是一種有效傳播方式[16]。文化消費作為符號消費的一種,其在傳播與推廣中的符號也尤其重要。
因而,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的符號系統建設不止拘泥于對蘊含的文化元素的符號化,還要考慮文創產品整體及品牌的符號建構。圖書館文創品牌的符號建構中故事敘述是必不可少的。創作符合圖書館文創產品整體并吸引消費者的故事能夠快速生動地建構品牌形象與文創產品的文化基調,讓產品在傳播過程中逐步完善關于品牌核心訴求的文化符號[17]。
亦或利用大眾媒介助力圖書館文創產品品牌的符號建構,通過新媒體的多渠道、多手段的表現方式,讓文創產品的符號動態、立體地與消費者互動,讓人們沉浸式體驗文創產品符號所包含的文化意蘊。
4 結語
消費社會中,文化消費正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創產品作通過符號建構將無形、抽象的文化變為有形、具象的符號,通過符號所包含的美感、內涵和意義滿足人們的文化消費需求,同時通過對“意義”的消費,傳播與構建文化認同、文化自信。公共圖書館文創產品在文創產品的符號建構中既應發揮圖書館文獻內容挖掘的優勢,還應重視對外延性符號和內涵性符號建設的融合。通過文創產品多元化的符號建構與品牌符號傳播,在個性化的文創產品消費中體悟文化之美,傳播民族優秀文化,讓“詩、遠方與文化”觸手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