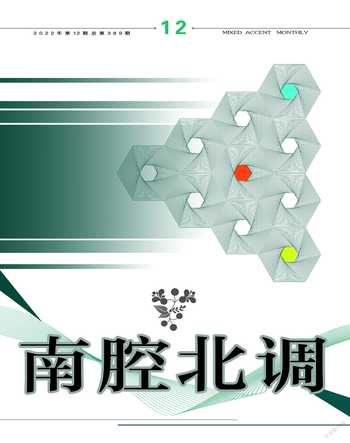陳眾議:回歸理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原會長陳眾議對拉美文學的研究頗為深入,尤其撰寫過很多關于加西亞·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的很多作品的評論。為了以特殊的方式致敬大師,陳眾議也出版了一部融合懸疑、魔幻、荒誕等多種創作手法的現實主義小說《如是我聞》。
陳眾議既是國內外文學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同時在文學翻譯和文學批評領域有較高的社會知名度,此次跨界創作的小說,他蘊積十余載,抨擊封建迷信蠱惑人心的積弊,用一種新穎的表達,在營造出極強藝術感染力的同時,表達了作者對于當代社會的獨特認知和敏銳反應。
一、你要看,而且要看見。陳眾議說,在《如是我聞》中,他努力一層層發掘魔幻如迷信、玄奧背后的真實。
舒晉瑜:您愿意如何概括《如是我聞》?魔幻現實主義?神秘的文化現象比較多,您的文學創作受誰的影響比較多?
陳眾議:我的文學創作是在潛移默化中受到影響的,除非有意模仿某個作家或某些流派。《如是我聞》首先是一部反迷信小說,最初的動因來自一腔憤懣。十年前我太太受人蠱惑,輕信“大仙”“大師”,最后離家出走,至今杳無音訊。而當時那些人都用難以稽查的網絡和手機信息與她聯系,他們鉆了虛擬空間的空子。這也是我緣何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后呼吁網絡和手機實名制的直接原因。導致各種迷信沉渣泛起固然原因眾多,但人們信仰的闕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心理落差和心理壓力等都是客觀因素,但起決定作用的始終是主觀因素。我太太身體不好,剛四十出頭就提前退休了。像我太太這樣的人最易被蠱惑。
小說有魔幻因素,因為生活忽然變得魔幻起來。就像莫言讀了拉美當代小說,尤其是馬爾克斯的作品,認為這不就是高密東北鄉嗎?不過我的小說是反其道而行之,關鍵在于如何一層層發掘魔幻如迷信、玄奧背后的真實。
舒晉瑜:小說透露出作者作為知識分子的憂思:我國從事人文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同仁何止千萬,卻始終未能阻止邪教和迷信的泛而濫之。您希望通過寫作傳達什么?作品完成了,能幫助您、幫助讀者獲得一些啟發吧?
陳眾議:我特別希望人們回歸理性。文明浩蕩,怎么能讓這些滋生于數千年前莽荒時期的神神鬼鬼、巫不巫儺不儺的東西再度復活呢?遺憾的是邪教尚未被肅清,不少人包括青少年依然跌入八字算命、風水運勢的陷阱,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我想從心理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巧妙地、潤物無聲地將它們解剖、打倒。當然,我不指望畢其功于一役,但總得有人先吃螃蟹。
舒晉瑜:我想《如是我聞》大概是一部學院派的小說,知識點很多,對當下社會的一些問題,如教育、技術等皆有關注,并且在寫作中不斷提出思考和反省。您覺得知識分子的寫作有何特點?
陳眾議:學者的毛病之一是好為人師,但我已經盡量克制了。問題是大量的迷信故事讓我不得不對其背后的故事和產生的土壤有所還原和開掘。這就免不了會借用心理學、社會學等有效武器。雖然我盡可能不動聲色,但難免還是會露出馬腳。這是兩難的選擇。
舒晉瑜:小說中“我”看到女孩關小露有一番辯白,用“由甲感官挪移至乙感官的純粹游移,具體說來是將過去生活中某種重要情感由甲目的物向乙目的物遷移的過程”解釋“這是移情卻并非別戀”,形容關小露是“理所當然的目的物”。這既是“心理學概念,也是量子糾纏,更是人之常情”——在閱讀的過程中,感覺可以獲取到知識點,但對于多數讀者來說,有沒有掉書袋的嫌疑?您這么用心寫作,也可能被讀者一晃而過,會不會有些失落?
陳眾議:一定會有很多類似的細節被忽略。不過問題不大,我堅信段子是一時的精神自慰,而迷信是一生的精神迷醉。只要這一個目的達到了,那么也算是開卷有益了。
舒晉瑜:您是全國政協委員,履職期間曾多次提交有關教育的建議和提案,這一身份對于創作是不是也有很多幫助?有心的讀者會發現教育在小說中有所體現。
陳眾議:開始構思這部小說,適逢校外培訓如火如荼。它的問題已為世人所公認。校內放羊,校外廝殺,不僅使億萬孩子及其父母身心俱疲,關鍵是國家教育體系和意識形態被嚴重破壞。我這一代,包括我孩子這一代,基本沒有擇校的概念,大家都是就近上學,公平競爭。之所以造成“雙減”前的亂象,我認為原因很復雜,除了資本侵入,有沒有優質教育資源權力尋租?總之,問題很復雜,但受害最甚的無疑是孩子。因此我從2015年起開始大聲疾呼“救救孩子”。不減負,不切切實實地減負,誰敢要孩子,別說二胎三胎了!念茲于茲,此乃真正國之大者!
小說中有個人物叫夏琴,她命途多舛,與主人公“我”的關系十分曖昧。她便是從事校外培訓的,我借她之口道出了一些奧秘。
舒晉瑜:笑話和段子在《如是我聞》中比比皆是。是人物塑造、情節構造所需,還是敘事節奏的需要,或提振閱讀的興趣?您如何看待幽默(段子)在小說中的作用?生活中您很幽默嗎?
陳眾議:其實我在生活中過于正經,也過于矜持,而且既不抽煙,也不喝酒,屬于比較乏味的那種。但與人為善是我的本性,在中國社科院工作期間,從副所長到所長20多年,我基本充當了“和善家長”的角色。
至于作品中的大量段子,我用來與迷信對位,就像我前面說的,“段子是一時的精神自慰,迷信是一生的精神麻醉”。段子是極端世俗化的表征,而迷信只有在極端世俗的土壤中才如魚得水、游刃有余。失去了崇高和理想,等待的就只能是金錢至上和醉生夢死。
舒晉瑜:小說中石頭講的笑話都是從《笑林》或者百度、知乎、抖音之類的網站上撿來的;老白在精神病院縱火后逃逸,電臺、報紙、微信公眾號到處懸賞通緝;師尊不僅有通靈術,而且對現代通信技術也運用自如,他寫微博,還是最早的網紅;“我”無從斷定朝露姐妹是克隆還是整容或者人工智能加基因工程的產物——您的創作受到新媒體的影響比較多?
陳眾議:是的。虛擬空間已經全方位浸潤現實生活。在《如是我聞》的姐妹篇《冥合天人》中,批判迷信和邪教依然是主題,但虛擬空間的描寫有大幅度提升。像劇本殺、元宇宙等從一開始便有被帶偏的危險,而克隆術及其相關的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也完全有可能被資本和邪教利用,因此我斗膽提前敲幾下警鐘,說科幻也好,謂杞人憂天也罷。
舒晉瑜: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種(新媒體)的挑戰?
陳眾議:新媒體不是法外之地,但新媒體也確實易受資本和各種不法利益入侵。我們除了加強法制建設、嚴格管理,恐怕還有賴于國民素質的提高。畢竟在虛虛實實、似是而非的海量信息面前,誰都有被淹沒的危險。反過來說,別有用心的人也可能乘虛而入。
二、談讀書,陳眾議始終有一個觀點:任何時代偉大的文學都是鳳毛麟角。
舒晉瑜:小說中為了多少給朝露一點提醒,“我準備將枕邊的《儒林外史》送給她”,能否談談您的枕邊書有哪些?有什么閱讀習慣嗎?
陳眾議:枕邊書會經常更新。學者最自由,但也最辛苦,幾乎沒有一個不是五加二、白加黑,也沒有一篇文章、一部著作不是一次重新開始,否則會被當作自我“抄襲”。但閱讀中總有一些是“常客”。我的“常客”中有《老子》《莊子》,也有唐詩宋詞和《紅樓夢》、元曲和《本草綱目》。后者這些年有點被束之高閣,原因是網絡太方便了,圖文并茂,而且還可能有視頻作參照。
我讀書向來挑剔,因此買得多,讀得進去的少。主要習慣大概有兩個,一是工作需要,剛性,沒什么可說的,必須讀;二是真正入目入心的,就像看到心儀的人、碰到會心的事,只消翻兩頁就知道這書是為我寫的。隨著閱歷的增加、年齡的增長,這樣的書越來越少,有點可遇而不可求了。可能是越來越珍惜時間,覺得時間最寶貴、不容浪費,或者是老了!覺得“學焉未能,老之已至”!可心里還有一大堆事想做,豈不既犯難又犯愁?
舒晉瑜:《如是我聞》中“我”博覽群書,對古今中外不同領域的書皆有涉獵,談談您本人的讀書情況吧,留學期間,讀得最多的書是什么?您最喜歡的文學類型有哪些?有什么不為人知的趣味?
陳眾議:留學期間讀得最多的自然是外國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在西方文學中又以西班牙語文學為甚,同時兼修西方歷史和哲學,后來又擴展到心理學和社會學。要說最喜歡的文學類型倒是有過幾次變化,開始是近代文學,尤其是19世紀西方文學,包括俄羅斯文學,而后是拉美當代文學,再而后是西班牙古典文學。對于題材和風格就沒有那么挑剔了,但大抵比較喜歡空靈一些的,比如古今玄幻或魔幻小說。
至于不為人知的趣味,大概是委婉地問我對西方女孩的認知吧?雖然骨子里東海西海,心理攸同,或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區別還是有的。比如五服之外我們大概率不會喜歡西方女孩,但隨著中外交流的日益頻繁,尤其是中蘇友好關系的建立和好萊塢夢工廠的影響日漸擴大,別說現在,就是我們的上兩代也已經與西方審美漸漸趨同了,如今更甚。但夏日炎炎,且不說體味不同,即使稍有不慎觸碰到了胳膊,你也會發現她們固然金發碧眼,但具有幾近膚色、不易覺察卻頗為扎人的汗毛,還有不同的體味。悄悄地告訴你,我還是更喜歡細膩溫婉的中國女孩。
舒晉瑜:很開心分享秘密,謝謝您的坦率!在《說不盡的經典》(作家出版社)中,您對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均有精辟地剖析,而且很多作家不止一篇。您經常重讀作品?重讀哪些?
陳眾議:我讀書向來挑剔,這可能是比較的結果。但矛盾的是文學藝術可以自立邏輯,它是文藝賴以永恒的不二法門。幾年前有人對《高玉寶》提出批評,認為它邏輯有問題,半夜雞叫,誰會相信?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是自成邏輯的,因為雇農們沒有鐘表,雞鳴便意味著天要亮了,何況背后有周扒皮這個混世魔王。因此,從文學作品本身的邏輯來看,“半夜雞叫”的可信性是成立的。類似的情況非常普遍,這歸咎于“艱深乍覺詩如讖,消散方知道是虛”。于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能讓我重讀甚至不斷重讀的書往往有幾個特征:一是讓我不忍立刻讀完的,它們就像孫猴子吃人參果,是需要慢慢地品嘗的,而且樂于慢慢地品嘗,以至于生怕它們被吃相難看的豬八戒囫圇吞了;二是可以入夢的,它們會一直縈繞在我的無意識中,無論是人物還是情景,非空非色,卻能隨時撩撥方寸神機;三是經得起理智判斷的,譬如我會將不同的文藝作品或其他書籍分門別類。言情的肯定以《紅樓夢》為最;言志的肯定以唐詩宋詞為先;載道的如諸子、古來演義和紅色經典就難分伯仲了。當然,言情和言志在很多人眼里是同一回事,但在我看來還是有區別的。我反倒覺得古來爭論不休的載道和言志是可以雜糅的。誰說二十四史、《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等許多名著不是既載道又言志的呢?也許只有《紅樓夢》是反道統的。
上面提到的基本都是我經常重讀的作品,除了《高玉寶》《西游記》《水滸傳》,因為它們入眼即化,無須重讀。
舒晉瑜:您有一個觀點:任何時代偉大的文學都是鳳毛麟角,少數作品幸免于難的原因,要歸功于學院派(哪怕是廣義學院派)的發現和守護,才完成和持續其經典化過程。可否簡單概括一下這一觀點的依據?是否所有經典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或必然性?
陳眾議:是的。至少迄今為止是這樣的。首先不是每個時代都能創造經典的,也不是所有時代的經典都能流芳百世。這可以有兩大指向,一為縱,二為橫。從縱向看,不少作品的經典化過程并不一帆風順,《紅樓夢》是最好的例子。如果沒有“百日維新”和“五四”運動,它的命運可想而知。也許被“誨淫誨盜”之類的唾沫永遠埋入歷史塵埃也未可知啊!結果是書生或謂學院派如梁啟超、王國維、蔡元培、胡適之等人一點點地將它從煙塵中搶救出來,并一步步將它推為“四大名著”之首,以至于毛澤東當年說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時,還不忘加上“半部《紅樓夢》”。其中就有一定的偶然性。所謂滄海桑田,世風日新,很多中外名著都是在數十乃至數百年之后才被重新發現的,有的甚至是“出口轉內銷”的結果,譬如《堂吉訶德》,將它定于一尊的是在塞萬提斯去世兩百余年后的德國浪漫派。當然,文學作品的內在肌理是決定因素。這是基本的辯證法。
誠然,從橫向看,當下和可以預見的未來,資本的作用將大為增強,這幾乎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此,我對當代經典的形成機制頗為悲觀。好在最終由時間老人說了算。“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也是未來史;一切文學亦然。
三、學外語或從事外國文學翻譯、研究,最終都是為了強健母語和母體文學文化的拿來。
舒晉瑜:創作、評論、學術研究……您多方兼顧,皆頗有成就。可否先談談您的小說創作,如長篇小說《玻璃之死》《風醉月迷》及很多短篇小說,在小說創作中您有怎樣的體會?和寫評論比,狀態有何不同?
陳眾議:作為外國文學學者,我是叛逆者。我始終認為學外語或從事外國文學翻譯、研究,最終都是為了強健母語和母體文學文化的拿來。借用許淵沖先生關于三民主義的譯法——“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我們何嘗不應該是of the Chinese, by the Chinese, for the Chinese?歸根結底,我們的工作終究是為了強健中文母語和中華文化的拿來及中外互鑒的送去!背離了這個初衷,一切也就無從談起,至少是舍本求末。因此,我間或從事文學創作便是為了貼心地擁抱中文,同時緊密與母體文學文化的血脈聯系。
至于《玻璃之死》,那是一部抽屜小說,始作于20世紀80年代初那個遍地書香的時代。后來一不小心拿出來示人,心里充滿了遺憾,于是又追加了《風醉月迷》。雖然后者起筆于90年代,但明顯較前者成熟穩重一些,雖然標題有點花哨。那些短篇小說是隨機寫下的,有朋友看到就拿去發表了。當時不像現在,既不論家門,也無所謂名利,畢竟主業是外國文學,總覺得寫小說是離經叛道,有時甚至不得不化名發表。
這多少受了老先生們的影響。雖然我所在的單位有一大批“雙槍將”,如馮至、錢鐘書(后被借調至文學所)、楊絳、卞之琳、李健吾、袁可嘉等,但他們從事文學創作大抵是在青年時期,后來基本都潛心問學了。何況,時移世易,分工越來越細。創作和研究有點兒不相雜廁,甚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味道。不過我還算是比較執拗的,一直堅持了下來,因此抽屜或電腦儲存了不少殘編斷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如是我聞》的初稿其實是七八年前草就的,另一部剛剛刪減削剔好的《冥合天人》算是前者的姐妹篇,同樣起手于七八年前。寫寫停停,停停寫寫,以此接續對母語的親切感和親密感。
當然,從事研究與投入創作的心態確實不太一樣。研究要盡可能既有我又有他(她),創作卻是非常自我的一個活計。行當所行,止當所止,海闊天空,全憑個人興趣。
四、作為評論家的陳眾議,每年保持二三十部國內原創長篇小說的閱讀量,其他中短篇小說和詩歌難以計數。
舒晉瑜:您的評論文章鞭辟入里,即便是批評,也是善意的。比如在莫言獲諾獎后您寫的評論文章中,就有一篇《莫言的五根軟肋》。莫言看到過這篇文章嗎?您會和作家交流觀點嗎?
陳眾議:在我這個不大不小的圈子里——30余萬外國語言文學從業人員,相當于解放戰爭渡江戰役粟裕麾下的主力隊伍——我可能是同中國作家圈保持往來的極少數之一。我每年保持二三十部國內原創長篇小說的閱讀量。其他中短篇小說和詩歌難以計數。由此,我會應約寫一些關于國內作家的評論。
做文學批評難免吹毛求疵。因此,當莫言摘取諾獎桂冠以后,我除了替他高興,第一件事便是寫一篇自以為中肯的批評。我列數了莫言的五個過人之處,同時又認為這些過人之處或許恰恰也是他的“軟肋”,譬如狂放的想象力、旺盛的生命力,以及不拘小節甚或蝌蚪效應等。我這不僅僅是為了批評的批評,而是想說明諾貝爾文學獎不是評判文學的標準,遑論唯一。
舒晉瑜:早在2002年您就寫過《文學理論到了該清理的時候》,20年過去了,您對當下的文學理論批評有何評價?對于批評的重建您有何建議?
陳眾議:我認為這方面的清算還不夠徹底。至少對西方現當代理論的盲從依然存在,批評的武器遠未轉向武器的批判。而文學批評實踐也尚未擺脫阿諛和惡搞現象。如何有禮有節、進退中繩尚需同道努力,“四個自信”和“三大體系”建設任重道遠。我的建議之一是重溫李健吾對巴金、傅雷對張愛玲的批評。
舒晉瑜:對于拉美文學您的研究頗為深入,您如何評價魔幻現實主義對您、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影響?
陳眾議:拉美現當代文學的確是一座富礦。當然,在“冷戰”時期對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的文學的推崇和推介也是不可否認的客觀原因。拉美文學左右逢源,加之后發的優勢,不僅對我國,而且對全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魔幻現實主義對我本人的影響毋庸置疑,我曾借用“集體無意識”概而括之。
我想,受拉美文學影響最甚的莫過于“尋根派”和“先鋒派”作家,前者得益于馬爾克斯(這是國人對他的簡稱,在此隨俗,譬如有人告訴你達·芬奇應該叫列奧納多),后者受惠于博爾赫斯。這是千真萬確的。但究其原因,也許前者基于我國五千年文明積淀的集體無意識和一代人對前現代的反叛沖動,后者則更加取法同現實生活的間離效果。這只是一概而論,具體情況要復雜得多,何況每個作家也在不斷地發生窯變。
舒晉瑜:關于加西亞·馬爾克斯,您寫過很多作品,比如《〈百年孤獨〉何以暢銷》《二十年后談孤獨》,2022年5月是《百年孤獨》出版55周年,您有什么要表達的嗎?
陳眾議:《百年孤獨》在20世紀80年代被中國作家奉為“圣經”,但在2013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的抽樣調查中,卻成了“死活讀不下去”的作品,而且位列外國文學作品榜首,就像《紅樓夢》位居“死活讀不下去”的中國文學作品之首一樣。馬爾克斯尚在世,他若聽到這個消息,又當作何感想?我覺得他會高興。畢竟他的作品可以同我國的第一名著對位并列了,哈哈!話又說回來,以范曄譯本《百年孤獨》的銷量看,讀它的人依然不少。它和《紅樓夢》一樣,是可以從任何一頁開始閱讀的。我對兒童和青少年朋友的忠告是多讀文學作品,倘使你連文學經典都不肯多讀,那么也就錯過了許多“美夢”和“艷遇”、“深潛”和“飛翔”的機會嘍。
舒晉瑜:您的譯著多嗎?能否談談當下文學翻譯有哪些新的問題?
陳眾議:我年輕時譯過一些文學作品,但主要是零敲碎打,譬如博爾赫斯、卡彭鐵爾、富恩特斯等人的作品,同時還翻譯過一些古今詩歌。如果說文學是遺憾的藝術,那么翻譯尤其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活計。首先是閱讀趣味的變化,其次是研究領域的發現,再次是語言習慣的移易,這些都可能決定譯本的命運和不斷被重譯的必然,加上錯譯在所難免,因此不可能沒有遺憾。馬爾克斯就曾表示《百年孤獨》中有二十幾個錯漏,有些已被研究界零星發現,我自己也發現過一兩個。可惜其他“馬腳”被他永遠地帶走了。自然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趣和使命,我的遺憾是后來退卻了:當有人約我翻譯馬爾克斯時,我婉言謝絕了。
現在翻譯有網絡的幫助是一件好事,但同時也因為有了網絡和翻譯軟件,問題越來越多。但守望和專注于譯德的青年人依然不在少數。寄希望于他們吧!
舒晉瑜:您曾著有《帕慕克在十字路口》,您和帕慕克有過深入交流?能否談談對他的印象?
陳眾議:我擔任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所長期間先后邀請過七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慕克是其中一位。他是很有個性的作家,率真而不失睿智,這不僅體現于他的作品,同樣表現在他的為人。很多與他打過交道的人覺得他太任性,而我卻喜歡他的這種性情。做事直來直去,講話有一說一。除了在北京幾天,我還帶他去了我的老家紹興。他很喜歡那里的風景和黃酒,結果有一次喝多了。我老家有一句箴言:“紹興老酒后反堂”,意思是它后勁兒足。酒香又不沖,不知不覺幾杯下去便可能被醉倒。同去的許金龍先生也不免多喝幾杯,結果連皮夾子都丟了。
五、閱讀就是蜘蛛織網的感覺:從一點開始,不斷延伸,往返穿梭,這也是一般西方高等教育的取法:凡事都講個學術史視野。
舒晉瑜:記得您好像提到自己最早的閱讀是“聽書”,那么閱讀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可否談談童年“閱讀”對您的影響?
陳眾議:我上學比較早,當時未滿5歲,在這之前一直在街頭和茶館酒店門前聽人說書。此外,江南夏天悶熱,于是家家戶戶都攤一張涼席、搬幾把竹椅在街頭消夏,街邊總有清渠。太熱了,孩子們就會跳到水里涼快一會兒,順便摸魚捉蟹玩兒。但凡有人講故事,就會豎著耳朵傾聽,也就顧不得玩水了。聽得最多的是《三國演義》《水滸傳》,其次是《北宋楊家將》《說岳全傳》,再次是《聊齋志異》《徐文長傳奇》。后者屬于少兒不宜,一般情況下大人會有所避諱,盡管我等偶爾側耳聽說一二也是有的。我開始閱讀大概是在7歲那年,因為可以磕磕絆絆連猜帶蒙地看書了,就開始大撒把,只要是文學作品,便逮著什么看什么。一直到“文革”和知青年代,閱讀便成了習慣。
過去以為“三歲看大”“七歲見老”是一種迷信,如今卻被科學證明是有道理的。就閱讀習慣而言,我稱之為童年的味蕾。由于讀得最多的是演義類作品,從隋唐演義到明演義,其中當然還有《楊家將》《岳飛傳》《七俠五義》《小五義》等。外國文學最先入目的是《基督山伯爵》《福爾摩斯探案大全集》之類。同時蘇聯和國內的紅色經典也一股腦兒地入目入心了。因此,“義”字早于儒釋道進入我們那一代孩子的心志。這個“義”既是古來我國文化四要素之一的俠義,也包含了現代紅色經典的正義凜然。
舒晉瑜:作為政協委員,您一向關注教育,不知您是否關注當下孩子們的閱讀?可否在閱讀方面提一些建議?
陳眾議:目下孩子們的閱讀情況令人擔憂。究其原因,一是手機剝奪了孩子們閱讀的興趣,從小沉溺于游戲的不在少數;二是課業的壓力過大,我曾多年就中小學義務教育階段的校外培訓提出批評,認為這是資本挺進基礎教育、中小學校舉手投降的結果。“雙減”政策出臺以后情況有所好轉,但正所謂“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從根本上解決教育內卷的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孩子們如果不能從小養成閱讀習慣,很難想象他們走上社會后還有時間和興趣沾染書香。
因此,我認為當務之急是從小學開始規定閱讀綱目,而且必須同語文、思政和素質教育結合起來,同課業考核結合起來,甚至同中考和高考這兩大杠桿結合起來。非如此,很難改變目前的狀況。
說到閱讀,我不免想起兩位前輩來。首先是錢鐘書先生,圍繞其一生的最大公案之一,便是他1949年緣何謝絕民國要員之約,堅定地留在大陸。關于這樁公案,當然也是私案,坊間曾有過許多揣測。最終楊絳先生在晚年用最簡單也最溫婉的方式了卻這樁公私案:她說,“為了中文”。原來事情居然這么簡單!其次,我的故友柏楊先生畢生致力于探究國民性,尤其是國民性的美與丑。他不像辜鴻銘先生那么樂觀,用一個“gentle(溫良)”簡單概括國人的心性;但也不像錢玄同先生那么悲觀,后者幾乎偏激到了否定一切、橫掃一切傳統的地步。柏楊在鞭笞丑陋的中國人和褒獎美麗的中國人的同時,編修了《中國人史綱》,并雄辯地論證了國人何以對外平和、對內嚴苛的根本原因:幾千年一畝三分地,以鄉土為本的小農經濟。他甚至認為這也是中華文化的穩定性之所在。而我曾斗膽替他的這個穩定性附加了另一個關鍵因素:中文。如果沒有中文,我們的文化也許早就被遼化、金化、蒙化、滿化,甚至完全西化(或拉丁化)了。而守護中文、強健中文的最好方法無疑是文學,其中閱讀與書寫尤為重要。還是那句話,如果連文學名著都讀不進去,那還能指望什么?好,不說文學家,看看錢學森、蘇步青、楊政寧、李政道、丁肇中等一干科學家吧,居然也都個個飽讀詩書、文采飛揚!
舒晉瑜:您在1977年考入復旦大學,師從于哪些名家,他們對您有怎樣的影響?在閱讀方面,會給您具體的指導嗎?
陳眾議:我于1977年考入復旦大學,但半年后就被選拔為“文革”后第一批留學生了。因此,我的本科、碩士、博士都是在國外完成的。要說受誰的影響最大,那肯定是時任校長的蘇步青。他既是著名的數學家,又是詩人。而且選派留學生的動議還是他率先提出來的。
由于外語水平太差,我的洋插隊比土插隊還苦,尤其是開始一兩年,那真個兒是兩眼一抹黑,兩耳成擺設。但我曾經的口頭禪是:“活都不怕,還怕那個苦嗎?”(另一個版本是:“活都不怕,還怕那個死嗎?”)因為成分不好,當兵報國的愿望未能實現,爾后只能硬著頭皮讀洋文,但心里一直有一個夢想:成為作家甚至學者型作家,這可以無限伸展理想的翅膀,也可以盡情潛入別人的生活,無論古人今人、文臣武將。
為此,閱讀就是蜘蛛織網的感覺:從一點開始,不斷延伸,往返穿梭,這也是一般西方高等教育的取法:凡事都講個學術史視野。這樣由點及面,縱橫捭闔,庶乎既見樹木也見森林便成了一種閱讀習慣。
舒晉瑜:如果您有機會見到一位作家,您想見到誰?希望從他那里知道什么?
陳眾議:這我得想想。也許是巴爾加斯·略薩吧!他一生風流倜儻,可以說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唯一的遺憾可能是競選總統未果。我曾于2011年6月邀請過他,他來了。當時他還是新科諾獎得主,可謂意氣風發。我當時最想知道的是他70年代中后期緣何與加西亞·馬爾克斯拳腳相向,以至于分道揚鑣,連文風都為之一變,寫起了艷情小說。可出于禮貌,最終我還是沒好意思張口。我想現在舊事重提應該沒什么忌諱了吧?2011年以后,老馬和老略似乎漸漸言歸于好了,何況人家馬爾克斯已經去了天堂。與其謠言滿天飛,倒不如說開了來個痛快。謠言之一是馬爾克斯看上了略薩(這是國人對他的簡稱,我也一并隨俗)的前妻加舅姨胡莉婭,又說馬爾克斯鐘情于略薩的第二任妻子加表妹帕特里西婭,總之都是桃色的。問題是他老人家80多歲了,如今又因為菲律賓名媛鬧得滿城風雨。呵呵,真想問問他如何打理文學與生活。
舒晉瑜:如果您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陳眾議:我可能會帶三本最實用的:為了自救的《本草綱目》、為了生存的《魯濱遜漂流記》和為了跟自己說話的《現代漢語詞典》,當然我會把漢語兩個字改成中文。
舒晉瑜:假設您正在策劃一場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會邀請誰?
陳眾議:我會邀請馬爾克斯,在他有生之年,我與他有過幾面之緣;同時我把略薩也請上。我還會邀請亞歷山大大帝,他像個任性的孩子,篤愛聽故事。但我最想邀請的是薩福,她是古希臘詩人,據說才貌雙全,還男女通吃。俗話說,“三女一男是三娘教子”,那么三男一女呢?
舒晉瑜:如果您可以成為任意文學作品中的主角,您想變成誰?
陳眾議:我想成為笛福筆下的魯濱遜或者圖尼埃筆下的禮拜五,反正要去無人島了。
作者單位:《中華讀書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