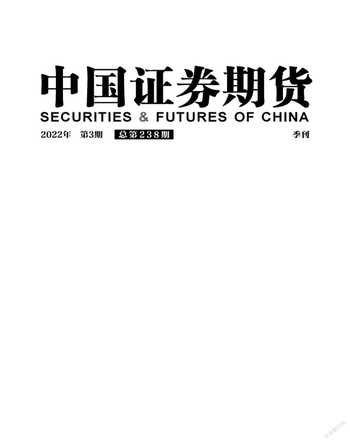我國商品互換場內集中清算趨勢與路徑分析



摘 要:2009年G20匹茲堡會議后,世界各國對場外衍生品場內集中清算的相關監管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推動場外衍生品進行集中交易和清算已經成為國際上的發展趨勢。由于場外衍生品具有明顯的定制化特性,場外衍生品如何進行中央對手方集中清算一直是近年來監管部門和清算機構考慮的主要問題。相關研究表明,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實際上就是個性化產品全部或部分標準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并非適用于所有的場外衍生品交易。本文結合國內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實際和業務實踐的經驗,指出我國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存在的找交易對手難、機構發展不均衡、實體企業參與不足和風險處置難等問題,對我國商品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標準化建議,特別是對于違約風險的處置措施,提出中央對手方并不完全適用終止凈額結算機制,建議參考場內期貨市場建立強行平倉等違約風險快速處置機制。
關鍵詞:場外衍生品;中央對手方;集中清算;商品互換
一、前言
互換、遠期、期權是場外衍生品的三種主要形式。場外衍生品的主要特點是定制化。交易雙方經過協商后確定合適的風險對沖工具,可以滿足企業的個性化需求。與交易所場內期貨和期權相比,這種個性化體現在標的范圍更廣、到期日和結算方式更加靈活等方面。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上半年全球場外衍生品存量名義本金610萬億美元,其中利率類為4881萬億美元,外匯類為1025萬億美元,權益類為75萬億美元,商品類為25萬億美元,信用類為91萬億美元。商品類衍生品中,遠期和互換為159萬億美元,占比最高,場外期權為087萬億美元(見圖1)。
場外衍生品的定制化特點確實滿足了許多企業和機構的風險管理需求和產品創新需求,但是,隨著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場外衍生品的風險隱患也逐漸顯現。2008年信用違約掉期產品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后,各國監管機構開始反思過度金融創新與監管缺失的關系,出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如G20在2009年匹茲堡會議上提出的場外衍生品改革措施。
(1)所有標準化的場外衍生品合約都應該在交易所或電子交易平臺交易。
(2)所有標準化的場外衍生品合約都應該通過中央對手方進行清算。
(3)場外衍生品合約應當向交易報告庫報送。
(4)提高非集中清算的場外衍生品的保證金要求。
(1)和(2)明確提出,可以標準化的場外衍生品應在受監管的交易設施進行交易,并進行中央對手方清算。
G20匹茲堡會議后,美國出臺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其中包括強化互換衍生品監管,對利率互換和信用互換進行重點監管。2012年12月,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的最終規則生效后,符合要求的互換產品大部分轉向在交易所或者互換執行設施(SEF)進行公開、透明交易,并由中央對手方進行清算。《美國商品交易法》(CEA)自2011年至2021年持續地對SEF的準入、交易、報告、合規等相關問題制定相應的規則,2021年2月完成了SEF監管規則的最終版。2014年通過SEF達成的掉期產品的交易金額為5.9萬億美元,2020年已經達到10萬億美元。
2012年,歐盟發布了場外衍生品監管規則《歐洲市場基礎設施條例》(EMIR),旨在促使標準化的場外衍生品通過中央對手方進行清算。《歐盟金融工具市場指導Ⅱ》(MiFID II)對EMIR的規定進行了詳細的補充,強制場外衍生品在有組織的交易設施或衍生品交易所交易。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和國際證監會組織在2012年發布的雙邊保證金要求文件中提出,在場外衍生品交易中采用初始保證金和變動保證金制度。當時變動保證金已被普遍使用,但初始保證金尚未普及,要求非集中清算場外衍生品繳納初始保證金將縮小非集中清算和集中清算場外衍生品之間的差距,對于推動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有著重要意義。
二、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的相關研究
場外衍生品通過中央對手方集中清算,已經成為近年來場外衍生品市場的發展趨勢。通過中央對手方清算能夠提高交易和清算效率,通過中央對手方的風險共擔機制能夠大大降低對手方違約風險。
但是,由于場外衍生品個性化和集中清算標準化之間的差異,并非所有的場外衍生品都適合中央對手方集中清算。
境外學者按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的難易程度,將場外衍生品分為四類:①有標準到期日的簡單結構的衍生品;②沒有標準到期日的簡單結構的衍生品;③能夠清晰定價的非標準化衍生品;④高度結構化的衍生品。
有學界認為第一類衍生品能夠根據市場交易進行估值,是中央對手方清算機構最容易處理的,也最容易轉化為場內交易產品。第二類衍生品可以通過插值方法,根據到期日相近的類似產品進行估值,如期權波動率可以使用已知的相鄰行權價和到期日的波動率進行估計。前兩類衍生品的特點是可以根據市場上已知的同類產品進行估值。而清算機構很難對所有的產品進行定價,對于需要集中清算的第三類衍生品,可以由市場參與者向清算機構提供合理的估值模型和工具,雖然不能強制要求市場參與者把各自的模型都提供給清算機構,但是可以要求這些參與者接受標準模型和參數對產品進行估值。第四類衍生品由于結構和估值比較復雜,如果要進行集中清算,應當由交易雙方向清算機構提供公認的估值模型和工具或者由指定的第三方進行估值。
可以看出,這四類產品雖然都可以通過中央對手方進行清算,但是清算難度差異較大。第一類和第二類容易被清算機構接受成為主要的清算產品;第三類和第四類則需要市場參與者提供估值模型和工具才能進行集中清算,產品估值和流動性是清算機構需要考慮的主要因素,在實際操作上這兩類產品集中清算有較大難度。
對于實體企業用戶,則可以豁免中央對手方集中清算,主要是因為這些企業與金融機構進行交易時,一般不需要繳納保證金,而是用信用交易。但可以通過提供雙邊清算服務讓這些交易在清算平臺進行登記,以方便監管機構分析和管理。
綜上可見,場外衍生品能否被準確估值(定價)是決定其能否參與集中清算的重要因素。除此以外,還需要考慮市場流動性、術語是否統一、交易流程是否統一等。
歐洲證券監管委員會(CESR)對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的標準進行了研究。CESR認為場外衍生品要進行中央對手方集中清算需要從以下3個方面進行一定的標準化。
1.規則的標準化
與場外主協議類似,規則的標準化包括規定和協議的統一,需要相關術語的定義和標準協議模板。
2.交易過程的標準化
交易過程的標準化主要指通過統一的電子交易平臺(STP)完成交易的配對、確認、結算和風險處置等過程的處理。
3.產品的標準化
產品方面,需要基礎交易要素、標準估值方法和統一結算模式等;同時也要保留一定程度的靈活性,允許市場參與者按照需要定制產品。
三、境外衍生品交易所在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方面的經驗
(一)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提供的場外衍生品交易和清算服務
CME Direct是CME提供的一個網頁形式的交易工具,具有前端交易、訂單保護等功能,可以瀏覽CME市場的實時數據,支持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通過Direct達成的場外衍生品交易可以通過場外清算平臺ClearPort參與CME的中央對手方清算服務(見圖2)。
CME Clear Port是一個面向全球場外市場的綜合清算服務平臺。目前已推出覆蓋利率、外匯、大宗商品等大類資產的超過1800個合約的清算服務。每天清算超過30萬筆交易,客戶超過17000家,包括實體企業、銀行、對沖基金、期貨經紀商和清算服務公司等。
(二)洲際交易所(ICE)的場外清算業務
ICE在北美、歐洲、新加坡等設有清算機構。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后,為滿足監管需求,ICE上線了ICE Clear Credit平臺,成為首家推出信用違約掉期(CDS)清算的清算所。
ICE清算所同時為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提供清算服務。場外清算產品包括CDS、其他互換交易以及天然氣等能源產品現貨交易。
ICE提供的集成交易終端WebICE提供了場內期貨和場外市場的交易功能。場外交易達成后,自動進入確認環節,ICE eCONFIRM為場外交易提供了快速、準確并具有法律效力的電子確認服務,以代替過去人工的、紙質的確認形式。經過電子確認后,交易進入清算環節(見圖3)。
四、國內商品互換現狀
(一)我國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持續高速增長
隨著場內期貨市場的持續發展,我國大宗商品場外衍生品在服務實體經濟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大宗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規模在2013年發展初期僅有0.73億元。根據中國期貨業協會統計,2021年全年,我國期貨公司風險管理公司開展的商品場外期權和商品互換名義本金已接近1.2萬億元,其中商品互換1819億元,同比增長4.4倍。
目前,在我國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中,主要是期貨風險管理公司、券商、銀行等機構為企業提供風險管理服務。
(二)我國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風險隱患增加,企業對場外衍生品的認知亟待提高
2019年中拓系企業利用場內市場和場外衍生品工具過度投機,引發了場外期權的違約事件,導致多家風險管理公司遭受重大損失。事件反映出來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幾點:一是對客戶授信過高,且缺少合適的抵押品和擔保措施;二是企業客戶參與數量不多,風險管理公司通過高授信等方式爭奪客戶的現象明顯;三是信息不透明,客戶違約風險識別難;四是保證金追保和風險處置措施不到位等。
上述問題表明,我國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仍然處在發展初期,許多企業對如何運用場外衍生品管理風險認識不足。特別是前幾年發生的中航油事件和航空公司場外衍生品巨虧事件等,導致許多企業對場外衍生品持有一定的偏見,不愿使用這類工具管理企業的經營風險。
(三)各類機構發展不均衡的矛盾日漸突出
近幾年,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加劇,商品價格的大漲大跌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許多實體企業所面臨的經營風險愈加突出。面對價格的持續上漲,一些通過期貨市場對賣出套保的企業需要不斷追加保證金來維持期貨套保持倉,企業的流動資金壓力較大。這種情況下,少量企業轉向銀行尋求幫助,更多的企業暫停甚至退出期貨套保業務。部分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使用商品互換等工具從套保時間、價格、數量等方面設計出滿足企業需求的個性化套保方案。同時,在該企業的授信范圍內免收保證金,既幫助企業實現套期保值,又極大地減少了企業經營壓力。
但是,由于監管限制,銀行不能直接參與國內除貴金屬外的其他期貨品種。因此,銀行只能將這類產品放在境外的期貨市場進行對沖,或者與券商、風險管理公司進行對沖。由于銀行對簽署場外衍生品主協議的對手方的資質要求較嚴格,較高的準入門檻和履約保證金要求導致許多對沖交易實際上難以達成。
風險管理公司普遍注冊資本較低,券商的產業資源較少,以及銀行準入門檻高等因素,導致我國難以形成境外成熟市場的機構間商品場外市場,這種“交易鴻溝”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的發展。
(四)國內已有的經驗和探索
為促進證券期貨市場場外衍生品交易業務發展,2013年,中國證券業協會起草并發布了《中國證券市場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協議(2013年版)》。2014年,中國證券業協會、中國期貨業協會、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在此協議的基礎上發布了《中國證券期貨市場場外衍生品交易主協議(2014年版)》及補充協議,形成了我國證券期貨場外交易的單一主協議,助推了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的發展。
2018年12月27日,為促進證券期貨市場衍生品交易業務發展,進一步完善證券期貨市場衍生品交易主協議,中國證券業協會、中國期貨業協會、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調整了《中國證券期貨市場場外衍生品交易主協議(2014年版)》名稱,修改為《中國證券期貨市場衍生品交易主協議》,協議內容保持不變。
中國期貨市場監控中心在證監會的指導下,于2018年建立了場外衍生品交易報告庫。作為重要的金融基礎數據庫,該報告庫有助于監管部門深入了解場外衍生品市場情況,進行場內場外聯動分析,提高風險識別和風險防范能力。
大商所于2018年年底推出商品互換交易業務,交易雙方按需定制產品,交易所提供雙邊清算,大商所的商品互換業務對國內商品互換市場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2021年大商所商品互換名義本金達到110.9億元,同比增長超過1倍。
上海清算所于2014年在國內首次推出鐵礦石和動力煤互換的中央對手方清算服務,上海清算所采用了標準化合約模式,雙方登記后參與中央對手方清算,截至2021年12月,已清算的大宗商品場外互換和現貨名義本金達9246億元。
上述實踐對我國商品互換市場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仍然存在幾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是機構間交易難、找對手方難;二是標準化合約限制多、標的對沖難;三是雙邊清算沒有解決對手方信用不對等的問題。
五、我國商品互換集中清算路徑建議
從國際經驗來看,2008年金融危機是場外衍生品過度創新而引發的一次金融系統的系統性風險。因此,G20匹茲堡會議的場外衍生品監管改革措施中明確提出場外衍生品應當實現標準化、平臺交易和中央對手方清算。
雖然我國的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發展時間較短,但市場規模已經超過萬億美元。基于我國商品場外衍生品市場處于發展初期階段的基本判斷,以及現階段市場需求與機構發展不均衡等突出問題的分析,筆者從產品、交易和結算等方面對我國商品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的路徑進行了研究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標準化過程:產品的標準化、規則的標準化、交易的標準化、結算的標準化以及風險處置流程的標準化。
(一)產品的標準化體現在產品可以準確估值、市場流動性好
場外衍生品交易的個性化特征明顯,不同交易之間的差異較大,如果要進行集中清算,必須對定價與估值相關的關鍵要素提出一定的標準化要求。
但是應當注意,在鼓勵產品創新的同時,需要平衡個性化與風險管理的關系。場外衍生品的標準化不能簡單地參考或者復制場內期貨和期權的做法,提供完全標準化的合約來交易和清算,這樣會失去場外衍生品的本質。應當兼顧市場參與者的個性化需求和集中清算的風險管理要求,使用市場接受的估值模型和工具進行定價,同時對相關要素提供一些選擇,以滿足不同參與者的需求,讓這些產品具有一定的市場流動性,有利于市場參與者進行風險對沖或風險處置。
(二)規則的標準化體現在建立統一的交易規則和入市協議
場外衍生品交易中,主協議的作用在于統一術語、明確違約情形和爭議解決方式等,這樣可以降低交易雙方的溝通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場外衍生品集中清算同樣需要解決集中清算過程中的交易要素、結算方式、違約爭議解決方式等問題,對相關的術語、流程等進行詳細的定義,制定相應的規范和規則,以降低參與者的溝通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市場流動性。
(三)交易的標準化體現在建設統一的電子交易平臺,提高市場透明度
場外衍生品交易一般都是一對一交易或者通過經紀商撮合成交,市場不透明且交易數據分散。
建立統一的電子交易平臺有利于減少交易雙方的溝通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同時,統一的電子交易平臺對產品信息、交易數據進行統一存儲、管理和發布,有利于提高市場透明度,有利于監管部門防范和管理系統風險。
此外,電子交易平臺應當兼顧雙邊清算和集中清算的需求,在產品設計上支持合約要素和產品結構的定制化。
(四)結算的標準化體現在建立統一的中央對手方清算制度體系
逐日盯市和分級清算等制度是期貨市場多年以來積累的有效防范違約風險的結算制度。
采用保證金交易的場外衍生品同樣適用上述制度,只是在線下交易過程中,信用交易較為普遍,特別是交易中強勢的一方往往只收取保證金或者不繳納保證金,導致對手方信用風險的管理存在一定的難度。
建立中央對手方清算制度,主要是解決雙方信用不對等導致的對手方信用風險管理難等問題,提高市場的公平性和透明度。
中央對手方清算制度的核心是合約替換,通過合約替換,原有交易被替換成兩筆交易,中央對手方清算機構成為原交易買方的賣方、賣方的買方。
建立分級清算制度,主要是將中央對手方的對手方違約風險轉化為清算會員的違約風險。清算會員可以通過對不同資信水平的客戶施行差異化的保證金政策,降低客戶交易成本的同時,防范和降低客戶違約風險。
為應對清算會員的違約風險,中央對手方應建立風險共擔機制,向清算會員收取一定比例的清算基金,同時從自有資金或手續費中提取一部分資金作為風險準備金。基于上述資金池,建立違約風險處置瀑布,明確清算會員違約時的資金使用順序和處置流程。
(五)風險處置流程的標準化與終止凈額機制
場外衍生品主協議的三大基石包括單一協議、瑕疵資產原則和終止凈額。其中,終止凈額結算是主協議處理對手方違約風險時的重要措施。在一對一的場外交易中,這種制度可以提前終止買賣雙方所有的場外衍生品協議,有利于保護守約方。
但是,對于清算機構來說,合約替換后,清算機構成為所有參與者的對手方。一個清算會員或者交易者出現違約,并不表示其名下的所有交易都存在盯市虧損,在強行平倉措施無法全部平倉的情況下,如果采用終止凈額機制,將使其他未虧損的持倉加速到期,可能引起更大的虧損。為避免上述情況的發生,一些清算機構采用拍賣制度,通過市場化手段處理違約者的虧損持倉,但由于拍賣處置的流程復雜,實際操作難度較大。
筆者認為,建立交易平臺的另一個優點就是為強行平倉等風險處置提供了一個高效的通道,對于規定時間內無法強行平倉的持倉,可以借鑒期貨市場強行減倉措施,將違約者的虧損頭寸盡快了結,有利于快速處理違約風險。
參考文獻
[1]The G20 Research Group.G20 Leaders Statement:The Pittsburgh Summit[EB/OL].http://www.g20.utoronto.ca/2009/2009 communique 0925.html.
[2]CFTC.Swap Execution Facilities[Z].Federal Register,2021.
[3]BCBS-IOSCO.Margin requirements for non-centrally-cleared derivatives[R].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2012.
[4]HULL J.OTC derivatives and central clearing:can all transactions be cleared?[J].Financial Stability Review,2010(14):71-79.
[5]Committee of European Securities Regulators.Standardisation and exchange trading of OTC derivatives[R].Consultation Paper,2010.
[6]王霄曼,李澤海.“中拓系”場外風險事件對期貨市場影響分析及相關啟示[Z].2019.
[7]《期貨市場典型案例研究》課題組.期貨市場典型案例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