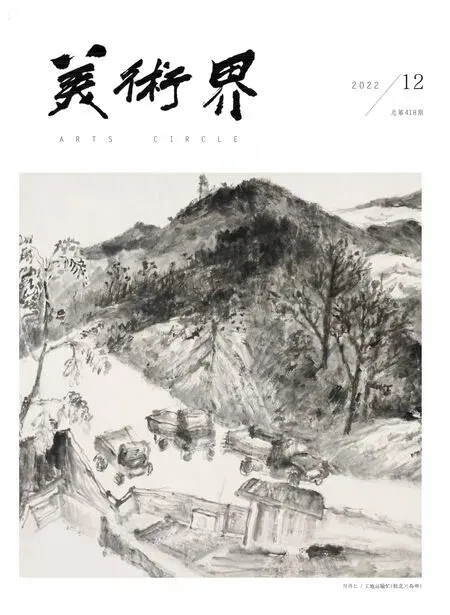關于山水畫寫生的思考與探究
文/陳水興

陳水興/彩虹橋夕照95cm×60cm 2021年
20世紀伊始,山水畫寫生便成了畫者開啟實踐探索且一直不斷討論的一個話題。現當下的山水畫寫生已是畫者直面大自然體現生活、搜集素材、激發靈感的一項重要藝術探索活動,也是現當下畫者通過寫生探尋個人藝術語言或繪畫風格的一種方式,山水畫寫生更是目前各大藝術院校必修的一門專業訓練課程。全國各地對于如何寫生的理解和解讀實際上是各有側重,而在寫生熱潮不斷發展之下,全國各地相互影響以及名人效應的導向下,寫生面貌趨同現象越加明顯。我們該如何看待寫生以及新形勢下山水畫發展的方向,都是我們必須要面對和需要反復思考的一個問題。
就本人而言,隨著山水畫寫生時間量的不斷積累,對于寫生的思考以及寫生的發展方向問題越加重視,每次外出寫生不管時間長短都或多或少給自己提出一定的要求,甚至有針對性地著重解決什么問題。藝術之路因每個人的認知和理解不同,寫生探求的方法方式亦各有差異,往往想法越多,樣式樣貌越加不明確,伴隨探知的欲望引發許多偶然性或不可預知性效果自然有之,而與此同時,過多的想法和嘗試同時也會帶來更多的困惑和不斷的自我否定。這種不確定性一定程度上根源于一定時間內對于如何審視傳統以及如何觀看西方觀念引入所導致的“新樣式”。這時往往是通過寫生實踐在觀望中尋求認知的確切答案。有的人在實踐和觀望中很快選擇并確立自身的追求方向,而有的人則可能會終其一生在摸索中前行。
任何藝術門類的發展探索都不存在著既定的模式或者確定的藝術法則,山水畫寫生也一樣。寫生探索就是在既有認知基礎上通過一次次的寫生實踐去積累和豐富藝術經驗,然后將自身置于大環境中不斷去檢驗和審視自我,從而獲得對有關藝術和有關寫生的新認知,并逐漸將所有的問題和困惑明朗化。因此,山水畫寫生,不管采取什么方式,總的來說始終回避不了以下的幾方面問題。
一、觀察方法

陳水興/大足石刻136cm×34cm 2020年

陳水興/北海漁港一角136cm×34cm 2019年

陳水興/春江水暖136cm×34cm 2020年

陳水興/青巖古鎮一角95cm×60cm 2021年
山水畫寫生,觀察方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寫生時景物在畫面的分布以及空間的營造等都是因觀察方式的不同而產生相應不同的藝術效果。中國傳統山水畫一直以“三遠法”的造景方式沿用至今。對于何謂“三遠法”,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已有表述,在此不作贅述。傳統山水畫通過“三遠法”的構圖法則營造了“可居、可游、可行、可望”的空間關系,讓人仿佛有置身其中并有身臨其境之感。近代以來,為了區別西方繪畫“焦點透視”的觀察法而提出了“散點透視”法。“散點透視”與“焦點透視”觀察法有著本質的區別,簡單來說,一種是“在其中”,而另一種是“在畫外”,觀看方式不同,實質上就是中國“山水畫”與西方“風景畫”所呈現的本質區別。然而,由于近代西方繪畫的引入和沖擊影響,在觀察方式上可以說已有一部分人接納了西方繪畫的觀察方式,從而導致有“山水畫”等同于“風景畫”的認知誤差。實際上,這個話題在20世紀已有爭論,至今仍存分歧。中國傳統的“散點透視”法以“游觀”的方式將不同對象通過虛實的處理進行空間關系的銜接,主觀營造一個理想的畫面,而西方“焦點透視”法所遵循的是一個以眼中所見的直觀視覺空間,是客觀近似于眼觀真實的視覺畫面。顯而易見,就是不同觀察方式形成不同畫面的展示結果。
二、取景構圖
構圖,中國傳統繪畫稱之為“經營位置”。構圖可以說是一幅畫好壞成因的一個重要因素。山水畫寫生時,如何取景構圖往往又取決于觀察方式。上文中已提到觀察方式有“散點透視”與“焦點透視”。在寫生過程中,若采用“散點透視”實際上就形成了對景創作的一種方式,這是中國傳統山水畫追求意境和營造畫面空間“可居、可游、可行、可望”的必然結果。因此,在寫生時往往需要對景進行取舍、提煉或者搬移而形成一個合理的畫面空間。即是將客觀對象進行主觀經營組合的畫面。那么,雖是對景寫生亦可畫出《溪山行旅圖》《萬壑松風圖》《溪山清遠圖》《富春山居圖》式的鴻篇巨制。而若采取“焦點透視”的觀察方式寫生,特別是處于山林之中時,則只能以“馬一角夏半邊”式的裁剪法表現眼前的“半壁山水”。實際上,在繪畫多元發展的當下,“中西融合”同樣也體現在了山水畫寫生構圖之中,普遍以裁剪式的構圖法表現鳥瞰或縱深發展的畫面空間,從而形成平面化或形式化的視覺體現。可見,不同的取景構圖方式同樣形成不同的畫面效果。

↑陳水興/云山屯瑞雪136cm×34cm 2019年

↓陳水興/郎木寺之晨136cm×34cm 2020年

↑陳水興/嵐山山麓人家46cm×68cm 2017年

↓陳水興/李家山46cm×68cm 2015年
三、筆墨應用
筆墨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繪畫的核心。物象造型、意境營造等都依靠筆墨來傳遞。用筆的輕、重、緩、疾,墨色的干、濕、濃、淡無不反映畫者作畫時心性的抒發,這是筆墨的魅力所在。那么,在山水畫寫生中解決筆墨問題也同樣重要。筆墨作為繪畫表現手段,在中國傳統繪畫中體現了它的獨特性。但是,在繪畫多元發展的當下,筆墨所承載的內容也應當更加廣泛,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西方繪畫審美體系對中國傳統繪畫審美體系的不斷沖擊和作用下的結果。中國傳統的審美經驗和審美標準也同樣走向了多樣化,從而凸顯了筆墨在當下表現力的局限性,諸如以傳統筆墨表現異域風光,表現廣闊的草原或是一望無際的沙漠,甚至表現某種具體對象的光感或質感時,那么,以意象表現為主旨的傳統筆墨很明顯就失去了它自身魅力。社會的發展始終是向前的。因此,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發展中的一切事物,傳統筆墨也同樣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之賦予它新的內容。那么,在山水畫寫生時,不應是為了筆墨而筆墨,而是根據不同的作用和要求,以不同的“筆墨”予以應對。
景色之美、物象之靈動、自然之生機等皆有其自然法則。我們在自然中寫生就要明白寫生的目的,領會其中的藝術意義,對傳統的“不離不棄”或者是對西方觀念的機械的套用、盲從同樣有悖于藝術規律的發展。實踐出真知,實踐經驗的積累是我們不斷得以向前發展和進步的重要途徑。一次次的山水畫寫生既是實踐的檢驗,也是經驗的總結,同時也是新一次實踐檢驗的開啟;每一次寫生的思考都是認知的深化,更是不斷否定再否定的自我思想修正歷程。只有不斷探索才能開拓藝術更多可能性。正所謂“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因人而異而各結其果。

陳水興/唐昭提寺一角68cm×46cm 2017年
陳水興

1975年出生,廣東人。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博士畢業。現為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講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中國畫學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