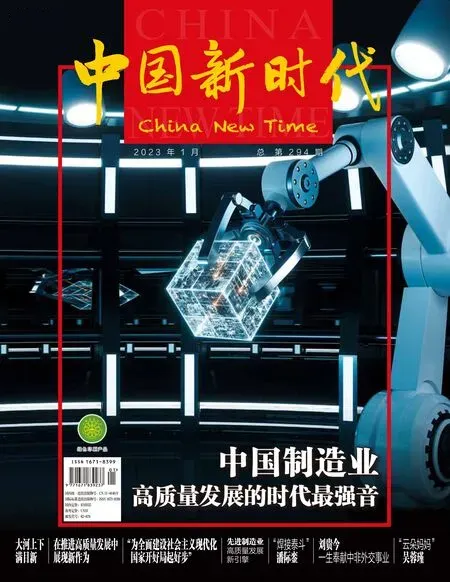“焊接泰斗”潘際鑾
|文·聶容止
一個又一個關鍵焊點,潘際鑾始終把初心與使命扛在肩上,“我們每個人都要奮發而為,為國家、為人民做事,錯不了”!

2017 年11 月1 日,北京大學,潘際鑾在西南聯合大學建校80 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言
他曾說,自己這一輩子主要做了3 件事:在中國建立起了焊接專業;把南昌大學建了起來;一生為中國工業經濟做了很多工作。
他的科研成果產值巨大,但自我總結起來卻如此輕描淡寫。
他被譽為“中國焊接泰斗”,他的青春、事業,乃至一生都與祖國的需要緊緊地焊接在一起:中國第一個焊接專業由他籌建,中國第一臺電子束焊機由他研制,中國第一條高鐵、第一座自行建設的核電站由他擔任焊接顧問……
一個又一個關鍵焊點,他始終把初心與使命扛在肩上,“我們每個人都要奮發而為,為國家、為人民做事,錯不了”。
他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南昌大學原校長、國際著名焊接工程教育家和焊接工程專家、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潘際鑾。
2022 年4 月19 日,95 歲的潘際鑾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潘際鑾院士為我國焊接科技和教育事業奮斗一生。”清華大學在訃告中如是說。
“要自己學,自己鉆研”
1927 年12 月24 日,潘際鑾出生在江西瑞昌的一個書香門第。他的父親潘鳳林14 歲中秀才,科舉廢止后,進了鐵路學堂,畢業后在南潯鐵路做職員,后任九江站站長、段長。
“10 歲的時候,日本人向我家鄉進攻,父親就帶著我們一家逃出了江西,像難民一樣顛沛流離。”生前回憶起這段歲月,潘際鑾總是難掩傷感,“飛機飛得很低,時常用機槍向人群掃射,有時3 架,有時9 架,有時27 架,晝夜都來。”
1938 年,潘際鑾的父親下決心帶著全家人逃難,一路上數次遭遇日機。潘際鑾和表哥又同時得了傷寒病,高燒昏迷不醒,“如何到桂林已不知,只感覺父親背著走”,到了柳州高燒才退。
他們用了3 個月才逃難到了云南昆明。為了謀生,父親四處尋找工作。潘際鑾回憶說:“父親到哪兒工作我就跟到哪兒,換了四五個中學,因為家里實在貧窮,有時候不得不輟學打工。”
在那顛沛流離的歲月,潘際鑾一度無法上學。但他從小就知道讀書會改變一個人的命運,甚至一個國家的命運。
“我中小學念了不到6 年,都在逃難,中間還做小工、臨時工。大家說我從小就是學霸,我想了想,我們家兄弟姐妹5 個,其實基本都是這個類型。我分析(原因),第一,父母的表現和影響。抗戰時,全家老小10口人,走到哪逃到哪,維持生活就很難了。但他們非常勤勞也非常正直。我父母從來沒跟我說,你好好念書將來要如何如何,就是說勤奮是很重要的。第二,我們家境很困難,沒飯吃,挖野菜(吃)。我們非常團結,都是大的帶小的。我跟哥哥漫山遍野去摘蘑菇、采竹筍,搞吃的。我每天下午去山上砍柴,背回家生火燒飯,新鮮樹枝燒得滿屋子都是煙。我14 歲從鄉下挑水果走很遠去賣,要走幾十公里,家里車費都出不起。這很辛苦啊,就體驗了人生的苦。那時就自覺地自己要學。”潘際鑾生前回憶。
1944 年,潘際鑾以云南省會考第一名的成績保送西南聯大,入讀機械工程系。
然而,潘際鑾在西南聯大的第一次期中考試居然有門功課不及格。為什么?課上講的內容明明都搞懂了。潘際鑾仔細研究了一下,發現考了很多課堂外的內容。從此,他懂得了一個道理:學習要有自主性,自己要去拓展、融匯、鉆研。
于是,每節課后,潘際鑾都去圖書館借很多書,結合老師講的,一個個專題鉆下去,鉆深鉆透。事實證明,這樣的學習方法非常有效。“我大學念書念得很好,門門課考第一。中學小學也是。這是第一次考不及格,給了我很重要的教訓。原來在中學學習很死板,老師講什么學什么。這一棒子把我打醒了,要自己學,自己鉆研,‘師傅引進門,修行在自己’。”
這是西南聯大真正給潘際鑾上的第一課。
潘際鑾在西南聯大真正上的“第二課”是在物理實驗上。“按照學校要求,我先用英文寫了實驗的預備報告,通過之后就進實驗室操作。但反反復復幾次下來,實驗結果仍與預期的標準相差甚遠。(我)匆忙之下就抄了一套數據,遞交了正式報告。但這沒有瞞過老師的眼睛,我受到了嚴肅的批評,被要求重新實驗。”這件事也給了潘際鑾很大的觸動,令他從此養成了認真細致、一絲不茍的嚴謹學風。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學校很快就結課了。“當時學校提出,未畢業的學生可以自由選擇清華、北大、南開3 所大學,我選擇了清華。”潘際鑾說。
于是,潘際鑾離開西南聯大轉入清華大學機械系繼續學習。
“中國最缺的是焊接”
1948 年,潘際鑾從清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畢業并留校擔任助教。1950年,潘際鑾進入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攻讀研究生。
“當時中國最缺的是焊接,沒人懂。機床有人懂,刀具有人懂,機械加工都有人懂,中國老的工業都有。唯獨焊接,中國老工業沒有,可以說一無所知。1950 年我從清華被選派去哈爾濱學習,蘇聯派的導師是焊接權威,我翻了翻他的著作,覺得很有興趣,就報了他的名。”
他報名攻讀了普羅霍洛夫教授的焊接學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世界焊接技術中的前沿課題之一——熱裂紋問題。潘際鑾說:“國家需要什么,什么難,我就干什么。當時選擇焊接,也是這個考慮。”
有人笑話潘際鑾:“學焊接?焊洋鐵壺、修自行車嗎?”潘際鑾說:“這個有用!”他的信念非常堅定,他認為在國家未來的建設中,一定能用到這項技術。
1953 年,潘際鑾研究生畢業后,留校擔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機械系教師,參與創建了哈爾濱工業大學的焊接專業,也是全國第一個焊接專業。
1955 年,他再次回到清華大學機械系,從規劃設計實驗樓、訂購實驗設備做起,正式開始組建焊接教研組。1956 年,焊接教研組開出了6 門專業課,但很多學生不愿意報這個專業。
為了鼓勵學生們積極學習,摒棄對焊接的誤解和偏見,潘際鑾專門在校報《新清華》上發表了一段話:“焊接是一門新興的先進技術,是衡量一個國家工業發展的標志。焊接能節省原材料,堅固美觀,簡化工序,并能改善勞動條件。世界上約有一半的鋼材需要焊接才能成為可用的產品,一輛轎車約有7000 個焊點,一架飛機約有25 萬個焊點和250 米焊縫,一個焊接的鍋爐要比鉚接的鍋爐節省金屬25%。想一想,焊接是多么重要而有意義的工作啊!”
潘際鑾一邊鼓勵廣大師生,一邊緊抓教學,一邊開展科學研究,讓學生們通過親身參與項目,去感受國家工業發展對焊接專業的需求。
20 世紀60 年代初,潘際鑾帶領團隊先后成功研制了重型軋鋼機架的電渣焊技術、大型錘鍛模堆焊技術和我國第一臺真空電子束焊機,完成了清華大學核反應堆焊接工程的研究及生產任務,成為我國第一個自己生產的核反應堆焊接工程。
在當時艱苦的環境下,這些課題的成功,讓學生們感受到了焊接的重要價值。此后,哈爾濱工業大學和清華大學為中國工業建設培養了大批焊接專業人才和師資,為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而潘際鑾功不可沒。

2017 年4 月21 日,潘際鑾在家中接受采訪
1987 年,潘際鑾接受國務院委托,擔任秦山核電站工程的焊接技術顧問。秦山核電站是國內第一座自主研發、設計和建造的核電站。“焊接,對建核電站來說,太重要了。這不僅是中國的事,也是全世界的事。一旦發生福島那樣的事,怎么交代?”他多年后回憶。
他一面制定嚴格標準——每項焊接都要做工藝評定,不合格的不準上去;一面培養優秀焊工——從100 多名焊工里通過考試選拔出24 名優秀員工,集中培訓、考核合格后分組開展焊接工作。
1991 年年底,秦山核電站并網發電,運轉至今。潘際鑾生前對此很是驕傲:“秦山核電站發電至今,主要焊接結構從來都沒有出過問題。”
進入新世紀,中國開始建設世界上最龐大的高鐵工程,但是一根鋼軌,鋼鐵廠只能生產100 米長,如何運用先進的技術將這些鋼軌連接起來是個大問題,也是高鐵成敗的關鍵一環。2005 年,鐵道部邀請潘際鑾做焊接顧問。在他的指導下,中國高鐵鋼軌完成了80 多萬個焊頭,做到了真正的天衣無縫,高鐵上立著的硬幣能始終豎立不倒的傳說曾驚艷全球。

2017 年4 月21 日,潘際鑾在家中接受采訪
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高鐵大國,運營里程最長、運營速度最快、高鐵運量最多、高鐵等級最高……中國高鐵不僅遍布全國,更開始走向世界。潘際鑾說:“過去鋼軌是有接頭的,現在1 小時走300 公里,焊得不好,一斷,車子就都翻了,現在我們中國鋼軌焊接的水平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看著焊工們經常爬得很高,被強光傷眼睛,被煙塵傷肺,潘際鑾又著急又心疼。于是,經過多年研究,潘際鑾團隊終于研制出無軌導全位置爬行焊接機器人,并申請獲得了美國專利。2003 年11 月,國內焊接行業全部院士和數名頂尖專家對項目進行了鑒定,一致認為“其成果的技術集成與創新處于國際領先水平”。
為了爭取機器人盡早投產,2016年開始,潘際鑾依舊像個精力旺盛的大小伙子那樣,每個月出差三四次,去有合作意向的企業,協助他們對機器人的技術進行深化。
有人問他:“參與無軌導全位置爬行焊接機器人的產業化,是不是為了賺點錢改善生活?”
潘際鑾一笑哂之:“根本沒想過錢的問題。用機器人替代人工焊大型結構,這是一塊硬骨頭,我已經啃了30 年。現在還要抓緊時間,和年輕人一起,真正把這塊硬骨頭啃下來。”
2017 年,90 歲的潘際鑾還在為中國100 萬千瓦的核電站如何運轉尋求突破;2018 年,在潘際鑾的帶領下,我國又成功研究出了能承受620 多攝氏度高溫的焊點……
回顧歷史,如果沒有焊接,中國高鐵就不能實現快速、安全、平穩;如果沒有焊接,中國核電站就不能實現絕對密封、絕對可靠;如果沒有焊接,中國第一艘航母便無法如期誕生。建造一艘航母需要2000 余名頂級焊工,這些人基本都是潘際鑾的學生,同時,需要炸不穿、高強度的鋼,而鍛造這些鋼,離不開的依然是無縫焊接技術……
潘際鑾突破了普通人對焊接的想象,讓一個個“國之重器”留下他和中國焊接的功勛。
為黨育人、為國育才
1993 年,66 歲的潘際鑾應邀回到江西省,受命擔任新組建的南昌大學校長。就任后,潘際鑾發現學校風氣很差。“校園里打球、談戀愛、跳舞的學生很多,跟我們上大學時候的氣氛完全不一樣。大家經過高考進了大學,就如同進了保險箱,認為肯定能畢業。”
“抓投入不如抓學風,抓學風是最好的投入”,為黨育人、為國育才,一向隨和的潘際鑾展現出了改革者“鐵腕”的一面。
為了辦好大學,培育人才,潘際鑾把西南聯大的辦校理念和方式帶到了南昌大學。“當年在西南聯大,淘汰率很高,而且很自然。我就結合實際,學習聯大的制度,實行‘三制’——一是學分制,修滿學分可以提前畢業,未按時修滿但努力學習的可以延長年限;二是滾動競爭制,把獎學金從落后的公費生轉給優秀的自費生;三是淘汰制,評審不及格的學生要被淘汰。”
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壓力,但南昌大學的“三制”改革始終沒有動搖,南昌大學的學風很快有了好轉,教育質量有了大幅度提高。
潘際鑾為提升江西省科研能力,一邊當校長一邊當導師帶教學生。他反復告誡在校任教的學生:“你就默默無聞地干,自己去爭取課題,別指望在學校拿錢。”
“人才不一樣,教育要根據個人的特點。我老講像游泳一樣游到對岸去,姿勢可以不一樣,快慢可以不一樣,因為人不一樣啊。有人耐力好,有人爆發力強,有人擅長蛙式,有人喜歡自由式,但都可以游過去成才,也才會有不同方面需要的各種人才。強國時代需要更多這種教育,才會有更強大的原始創新。”潘際鑾說。
在潘際鑾的帶領下,2002 年,南昌大學成為江西省唯一一所“211工程”大學。而對于一個個鮮活的學生,在校學習時被錘煉過的學風,則變成了走工作崗位后的作風。
2002 年,75 歲的潘際鑾離任,回歸清華大學,成為南昌大學的名譽校長。
南昌大學一位1994 級的學生在工作20 年后感嘆:“當年被潛移默化深植于心的那些理念——實干、勤懇、認真、拼搏……一路幫我走了很遠。”如今,在南昌大學校園內,隨處可見與潘際鑾有關的元素,如際鑾路、際鑾書院……
潘際鑾身上有太多重量級的科研成果,價值高達千億元,成果斐然,榮譽等身。但他對這些卻毫不在意,他在乎的,只是做事。
“國家需要堅決上馬、知難而進、敢于攀登、團結友好、共同戰斗、只求奉獻、淡泊名利。”生前,潘際鑾如是闡述自己的人生觀,“我總覺得一個人,一輩子,活這么幾十年,做點對人類有意義的事情,才是我們生活的目的。我在活著的時候,做了一些對人類有益的事,對我來講是很大的欣慰。如果我平平淡淡過去了,就關心拿了多少錢、做了多大官,我就不欣賞那個。”
斯人已逝,其志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