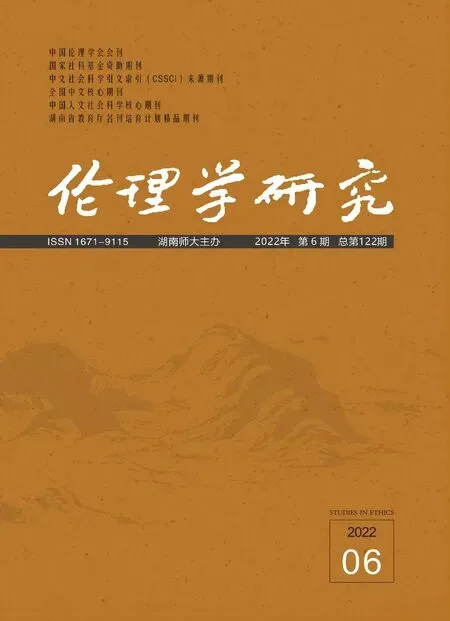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規范理論的新發展
李家蓮
在安斯庫姆(G.E.M.Anscombe)的《現代道德哲學》(Modern Moral Philosophy)于1958 年發表前,西方規范倫理學主要由道義論和后果主義平分天下,前者以康德倫理學為典型代表,后者則以邊沁(Jeremy Bentham)、密爾(John Stuart Mill)和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為代表。《現代道德哲學》指出,當上帝作為道德權威或神圣立法者被排除在倫理學之外后,后果主義和道義論所提出的“道德應該”、“道德義務”和“道德正當”等概念隨即失去了合法基礎,有鑒于此,安斯庫姆呼吁基于道德心理學為這些概念確立新的理論支撐。20 世紀60 年代以降,作為對后果主義和道義論所提出的規范理論的替代品,一種不以神圣立法者為預制理論前提且以確立道德規范為己任的美德倫理學正式登上了西方倫理學的歷史舞臺,抒寫了濃墨重彩的理論新篇章。為了完成為道德確立規范的理論使命,以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多元論美德倫理學和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為代表的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分別采取了理性、情感以及理性與情感兼具的不同路徑進行建構。本文認為,以情感主義為代表的美德倫理學表現最佳。
一、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發展現狀
20 世紀的規范倫理學圍繞善行(good action)展開對規范問題的討論,后果論從行動的后果出發為之確立規范,而道義論則試圖從義務出發而達到相同目的。不過,美德倫理學認為規范的基礎既非行動的后果,也非義務,而是被稱為行動者的主體,主體自身的美德才是規范得以確立的基礎。換言之,通過聚焦善行的主體,美德倫理學認為,要為善行確立規范,既不能走后果主義之路,也不能走道義論之路,而只能走美德之路,是美德而非義務或后果才使善行真正得以為善。以美德為基本概念對“正當”、“應當”和“善”等概念進行解釋并確立可與道義論和后果主義相抗衡的規范理論①是否試圖基于美德來確立規范,這是美德理論(Virtue Theory)和美德倫理學(Virtue Ethics)的差別所在,美德理論雖研究美德的本質及其與其他道德概念的關系,但卻并非規范理論,而美德倫理學是一種規范理論而非單純以美德為對象的理論研究。在此意義上,道義論和后果主義雖然也討論美德以及美德與其他道德概念的關系,但卻從未試圖基于美德建立道德規范理論,因此,它們是美德理論,但不是美德倫理學。,構成了美德倫理學的基本特征。總體看來,20 世紀60 年代以降,西方先后出現了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以及多元論美德倫理學,從而使當代西方倫理學舞臺呈三足鼎立之發展態勢。
1.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
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是20 世紀后半葉最早出現的美德倫理學,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約翰·麥克道維爾(John McDowell)、阿拉斯戴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lntyre)以及羅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等。該派美德倫理學深受亞里士多德哲學影響,反對道德義務,呼吁過一種有美德的生活,倡導回到重視美德的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哲學傳統。無論是對美德的理解還是對基本哲學立場的確立或對幸福與美德之關系的闡釋,該派美德倫理學均展現了濃厚的亞氏哲學特征。
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基于亞氏哲學闡釋美德概念。《尼各馬科倫理學》把美德理解為卓越(Excellence),認為單憑美德即可造就善人或卓越之人,此處所謂的美德并非僅指道德領域內的美德,而是在人之為人的整體意義上所言的綜合性美德。秉承亞里士多德哲學精神,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家赫斯特豪斯和茱莉亞·安娜斯(Julia Annas)也把美德理解為卓越,認為美德即可以使我們過上好生活的品性。亞氏的美德概念是一個具有綜合性特征的概念,同理,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所理解的美德也是如此,它并不認為美德可以使人成為善人,這種美德所關心的是諸如“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1](101)一類更宏大的人生問題。就此言之,赫斯特豪斯認為,要成為有美德的人,須滿足多種要求。首先,須有一種行事可靠的氣質。其次,須使自身性格中的情感活動和理智活動展現出美德的特征。安娜斯認為,美德不僅展現于行為中,而且以某種方式展現于感情和推理活動中。例如,當我們看到一個做家務的孩子時,我們不能僅僅基于該行為而認為這是一個體貼父母的孩子,因為孩子可能會因為幼年所受的教育而養成了做家務的習慣,也可能因為害怕母親的苛責而被動做家務,要知道該孩子是否真正體貼,我們不能僅僅基于行為進行判斷,還需深入到孩子的性格內部進行考察。就此而言,美德可被視為受優良情感推動的行為傾向或氣質。
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基于亞氏之理性主義哲學立場理解理性、情感與美德的關系,認為理性在人身上居核心地位。該派美德倫理學對情感持認知主義態度,認為情感并非對世界的物理性回應,可用理性予以認知并教導。基于此,該派倫理學所討論的美德是一種要求理智(intelligence)或智慧為之保駕護航的美德。有美德的人之所以關心正確的事情且能對正確之事產生正確的欲望,原因在于該人能用理智對真正正確或重要的事作出判斷,這種判斷并非生而有之,而是所有未喪失德性能力的人學習并實踐倫理學邏各斯的結果[2](50-51),因此,實踐智慧是美德得以生成的必要條件,而要獲得實踐智慧,首先則須有理智。就此言之,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所討論的美德雖同時具有情感和理智雙重特征,但該派美德倫理學歸根結底還是秉承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理性精神而認為是理智而非情感才能為行動提供動機。不僅如此,理智還是價值判斷的來源,唯有理智能告訴行動者何謂值得做的事情。因此,勇敢的人之所以作出勇敢的行為,不是因為該人從情感上擁有勇敢的動機,而是因為該人的性格過去曾以一種可使該人作出勇敢行為的方式得到過鍛煉[3](9-10)。亞里士多德認為真正有美德的人在作出有美德的行為時會感到快樂。同理,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家也認為,真正有美德的孩子在做家務時會感到快樂,一如真正慷慨的人作出慷慨的行為時會感到快樂。不過,安娜斯強調說,快樂不是美德的伴隨物,而是行動者克服了種種阻礙——“克服內在阻力不遺余力地作出了正確的事”[4](517)——而作出有美德的行動時所經歷的一種內在情感體驗,同理,赫斯特豪斯也認為,快樂并非美德的伴隨物,而是“理性與欲望在美德之人身上處于和諧狀態”[1](104)。
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基于亞氏思想理解美德與幸福的關系。亞里士多德主義倫理學把美德與幸福緊密聯系起來,相信美德會使其擁有者受益,認為有美德的人即為有能力過幸福生活的人。同理,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家們在討論美德的過程中也十分重視幸福問題,在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中,該派美德倫理一般來說被視為最重視幸福的一派美德倫理學。不過,在幸福與美德的關系問題上,絕大多數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家都追隨亞里士多德,認為盡管美德為幸福所必需,但卻不是充分條件,為了成為一個幸福的有德之人,還需輔以財富、榮譽、朋友以及社會地位等“外在善”(external good)。一個人之所以能過上幸福生活,是因為該人擁有可以被稱為美德的性格特征,而使一種性格特征成為美德的原因在于它能使其擁有者過上幸福生活。換句話說,美德這種性格是幸福的必備條件。在此意義上,對于真正有美德的人來說,理論上的確可過幸福的生活。可是,如果實際上卻無法過幸福的生活,那么,在赫斯特豪斯看來,原因不在美德,而在于運氣不佳。
2.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
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被視為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的替代品,其古典思想來源是斯多亞主義哲學,近代思想來源則是18 世紀英國道德情感主義哲學,當代西方主要代表人物是邁克爾·斯洛特(Michael Slote)。美德被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視為核心概念,但卻不被理解為基礎性存在,因為這種美德倫理學并不把美德視為一切道德價值的來源。這一方面體現為,這種倫理學寓于亞里士多德哲學之理性主義哲學立場的影響,把理性視為美德的內核;另一方面體現為,這種倫理學把美德僅僅視為幸福所必需的某種性格特征。在美德的功能與作用等問題上,以斯洛特為代表的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比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更純粹。斯洛特認為,美德是一切道德價值的來源,擁有美德即擁有令人欽佩的性格特征,而唯有行動者內在具有某種情感或心理才能使這一切得以可能,好的動機是美德得以成為美德的充分必要條件。
較之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有兩個獨特特征。其一,就美德與后果的關系而言,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認為美德通常會產生好或善的后果(good consequence),但好的后果并非美德的特征所在,也不會賦予美德以道德價值,因為后果隸屬于運氣。道德上的贊許或譴責應該處于我們能控制的范圍。既然我們無法控制運氣,那么我們就不會基于后果而贊許或譴責行動。但我們可以控制自身行動的情感動機,因此,我們可以基于對情感動機的評價而給予它道德評價。總之,對行動的評價和對行動后果的評價不可混同,美德與行動者的幸福之間并無緊密關聯,因此,人們甚至有可能過一種并不幸福但卻有道德尊嚴的生活。其二,就情感與動機的關系而言,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并不把情感視為美德的動機與保障,而是認為理智或實踐理性才是美德的動機與保障;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則認為,單憑情感本身,美德即可成立,更確切地說,理智或實踐理性并不是美德的動力,唯有情感才是美德得以生成的初始因,正是基于此,諸如關心、關懷或同情等情感被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理解為美德所必需的情感。簡言之,我們因自身的情感而獲得以贊許或責備為情感表現形式的道德價值。美德由情感構成,有美德的人擁有令人欽佩的情感,而邪惡的人則擁有令人厭惡的情感,我們之所以對一種情感表達欽佩或厭惡,根本上是因為該情感可令我們或旁觀者產生溫暖感或心寒感。因此,要獲得美德,道德主體須擁有令人感到溫暖的情感,而要避免惡行,道德主體則須避免令人感到心寒的情感。在美德或惡行得以生成的過程中,為亞里士多德哲學或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所看重的理性始終處于次要地位,被視為情感用以實現自身目標的工具或手段。
由斯洛特創立的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以主體為基礎的美德(agent-based virtue)以及情感主義者的美德(sentimentalist’s virtue),前者是其早期發展階段,后者則是其晚期發展階段。從早期到晚期的轉變表明,斯洛特所討論的美德逐步從關注主體轉移到關注主體的情感,而且也表明,斯洛特在闡述其理論進路的過程中,表現得越來越重視移情(empathy)。正是通過闡述移情的內在機制,該派倫理學基于情感為美德確立了一種可與道義論以及后果主義相抗衡的規范理論。總體看來,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不僅第一次在美德倫理學中提出了較為完備的規范理論,而且在道德情感主義道德判斷的問題上也展現了較強的理論創新。例如,這種倫理學認為,道德判斷以贊同或譴責為前提,伴隨著贊同或譴責的情感感受不是苦樂感,而是令人溫暖與否[5](34-35)。
3.多元論美德倫理學
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和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均可被視為單一論美德倫理學,它們均認為美德的基礎具有單一性。不過,以克里斯廷·斯旺頓(Christine Swanton)為代表的多元論美德倫理學并不贊同這種觀點。響應安斯庫姆認為道德心理學在倫理學研究中應該具有優先性的呼吁,斯旺頓認為,美德是一種“優良的內在狀態”(Fine inner state)[6](6)。不過,在解釋優良的內在狀態時,斯旺頓采取了一種既不同于亞里士多德主義哲學傳統也不同于道德情感主義哲學傳統的全新做法。與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或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不同的是,斯旺頓反對用自然主義或理性主義解釋構成美德基礎的內在狀態,而是試圖用多元論進行解釋。另外,與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不同的是,多元論美德倫理學雖承認所有美德均暗示著某種優良的內在狀態,但并不同意把某種單一類型的情感(如仁愛)或優良內在狀態視為美德的動機,美德須以不同方式對不同回應對象作出有效道德回應。斯旺頓主張,唯有美德才能使某種單一類型的情感或優良內在狀態具有優良性或合宜性。斯旺頓把實踐理性和情感均視為一種內在狀態,認為并非日常生活領域內的美德都需要實踐理性,實踐理性并不為每種美德所需。在反對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和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的同時,斯旺頓從尼采的道德心理學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據此把美德定義為“以一種足夠卓越的方式對一個或多個領域內的復雜因素作出回應或給予認可的心理傾向”[6](19)。更確切地說,多元論美德倫理學認為,盡管善的行為源于美德,但美德卻形成于對實際生活處境所產生的不同要求的不同回應之中。要求不同,美德也會相應不同,美德的形成從來不會僅僅只受某種單一因素的影響;相反,唯有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有可能形成美德。同理,善的行為之所以形成,也是受多種因素推動所致。較之一元論美德倫理學,多元論美德倫理學的典型特征體現為“多”,這種“多”不僅表現為主體的回應類型,也表現為主體的回應對象。
就主體的回應類型而言,多元論美德倫理學主張,諸美德共同具有的特征是它們均能對世界的各種要求作出合適回應。然而,由于每一種美德均有各自不同的領域,而各種不同的領域會對我們作出各種不同要求,故所謂美德,即對這些差別各異的要求分別作出合適回應。例如,勇氣即為對危險處境作出合適回應。斯旺頓的美德理論之所以被稱為多元論,還因為該理論認為,當我們對各種不同處境給予道德回應時,我們的回應方式也是多種多樣的。例如,仁愛的美德使我們對他人的需求產生回應并著手改善他人的善,此種類型的回應可被視為主動回應,此外,我們還會以一種被動或不具目的性的方式對我們面臨的處境作出回應,即被動回應。例如,欣賞藝術品時產生的回應就是被動回應。
基于主體的不同回應對象,主體會基于對不同對象的回應而培養不同類型的美德,多元論美德倫理學據此把美德分為四種類型:以價值為基礎的美德(value-based virtue)、以興旺為基礎的美德(flourishing-based virtue)、以個體狀態為基礎的美德(status of individual based virtue)以及以關系為基礎的美德(relationship-based virtue)。所謂以價值為基礎的美德,指的是該美德能對有價值的物或人給予合適回應,就此而言,此種類型的美德會維持或提升有價值的物或人。例如,保護自然不受污染或破壞的環境美德(environment virtue)即為以價值為基礎的美德,一旦應受珍視的自然價值得到了保護,該自然價值就會給人帶來好的后果。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斯旺頓認為,好的后果并非該美德成為美德的原因,對有價值的事物的珍視才是該美德成為美德的原因。所謂以興旺為基礎的美德,即以提升或改進有感生物的善為目標的美德。此種美德不以自身為善(good in itself)的事物為目標,而是著眼于增進對有感生物而言的善的事物(good for sentient beings)。為了有效提升這種善,必須基于對有感生物的了解并基于這種了解而形成某種知識。就此而言,知識在這種類型的美德中占據至關重要的地位。所謂以個體狀態為基礎的美德,指的是基于對個體之不同狀態(孩童、成年、老年、已婚、為人父母、學生、科研、商場工作、政治活動等)的回應而生成不同的美德。所謂以關系為基礎的美德,指的是基于情感紐帶而產生的美德,諸如同情(compassion)、友誼、關愛、父母之愛等就屬于這種類型。基于關系而生的美德不同于以價值為基礎的美德,前者的理論基礎是關系,而后者的理論基礎是價值。以哀悼為例,這是一種以關系為基礎的美德,因此,哀悼得以發生的基礎或原因不是被哀悼者的價值,而是哀悼者與被哀悼者的關系[6](42-43)。
二、理論使命與路徑抉擇
作為一種具有獨立理論身份與地位的倫理學,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承載著重要的理論使命,即成為一種能與道義論和后果主義相抗衡的道德規范理論。那么,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是如何進行的呢?斯旺頓認為,美德倫理學研究尚處“嬰兒期”[7](32)。我們認為,若不能正確處理好美德與規范的關系,不能正確處理好美德或規范與道德心理學的關系并找到恰當的心理學研究路徑,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就不能在規范問題上提出有深度與說服力的哲學觀點。簡言之,若要通過討論美德而讓美德倫理學為道德確立規范,既需找到恰當的理論路徑理解美德與規范的關系,也需找到恰當的理論路徑理解美德或規范與道德心理學的關系。
通過聚焦主體探討美德與規范的關系,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區分為激進進路和溫和進路。激進進路認為,只要行為者真正擁有美德或好的品質,行為就會自然而然變得正當起來,規范問題也會隨之迎刃而解。因此,美德倫理學需高度關注的問題不是規范本身,而是好的或有美德的主體本身。以赫斯特豪斯為代表的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認為,好人的品性或好的行為主體才是美德的本質或內核,美德倫理學并不關心也不會告訴我們應該做什么,也不會討論行為正當與否的標準問題。基于這種思路,赫斯特豪斯認為,只要有美德,人們在合適的情景就會作出正當之事[8](54-55)。總之,較之單純討論規范問題,道德主體是否擁有美德或好的品性顯得更加重要。一些美德倫理學家還以更激進的方式看待美德倫理學中的規范問題,不僅認為以拜爾、麥金泰爾、納斯鮑姆和麥克道威爾等為代表的美德倫理學家批評道義論和后果主義時所提出的規范理論是一種不可被應用于所有道德語境的僵化規則,而且認為倫理學主題具有不可法典性(uncodifiablility of ethics thesis),因此,倫理學不可被囊括在某一個或幾個剛性法典或規范理論之內。與激進進路不同的是,溫和進路認為,美德倫理學不僅要關心“是”(being),更要關心“做”(doing),不僅要關心“我應成為什么樣的人”,更應討論“我應做什么”,因此,為了闡明“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等問題,美德倫理學需為行為提供規范。以斯洛特為代表的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一派是溫和進路的典型代表。與激進進路不同,溫和進路的美德倫理學并不認為規范之于美德倫理學可有可無,這派美德倫理學家自覺擔當了為美德倫理學確立規范的理論使命,把當代美德倫理學之規范理論建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關于美德或規范與道德心理學的關系,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有三種不同的理解范式。安斯庫姆曾指出,由于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并未明確解釋美德概念,因此,唯有深入理解諸如意圖、快樂、行動等概念后,才能知道何謂美德。簡言之,唯有深入研究道德心理學,才能探究美德的本質,也才能做倫理學。那么,如何研究道德心理學?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有三條理論進路。幸福主義美德倫理學基于亞里士多德之理性主義哲學立場,從理性出發研究道德心理學,通過把情感置于理性的支配下,讓美德染上了濃厚的理性色彩;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秉承18 世紀英國情感主義哲學傳統,把情感視為道德心理的基本構成元素和美德的本質,讓美德被注入了濃厚的情感元素;多元論美德倫理學通過聚焦主體在不同處境中的反應討論美德,在理性與情感問題上表現出了中立性的綜合立場,它既不屬于理性主義,也不屬于自然主義,而是讓美德表現出多元性。
就三種類型的美德倫理學對道德心理學的不同理解范式來說,以情感為基礎的研究路徑最具可取性。就美德倫理學試圖完成的理論使命——取代道義論和后果主義而成為一種新的規范倫理學——來說,要使美德能為道德提供有效規范,首先須對作為美德之基礎的道德心理學的理論本性進行定位,那么,道德心理狀態的本性到底是理性還是情感呢?在三種類型的美德倫理學中,唯有斯洛特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十分明確且可信的回答。斯洛特指出,西方哲學存在著一種源遠流長、根深蒂固且十分強勢的錯誤觀念,即認為心靈(mind)活動可以在沒有任何情感參與的情況下發揮功能。這種觀念之所以從根本上說是錯的,理由有二。其一,一切心靈功能都必然包含或涉及相信(believing),如果用“P”代表相信的內容,那么,當一個人相信某物(P)時,就可以說是相信P,而相信P 時必然會包含肯定或否定的認知態度。比如,展開推論時,必須相信推論的結果來自推論的基礎,如果連這點都無法相信,那么,推論將無法進行。這樣,當一個人批評或贊成某觀點時,首先也必須以相信什么東西為前提。以妻子對丈夫不忠為例,不希望妻子不忠的丈夫聽到“妻子不忠”時會感到非常憤怒乃至無法相信或接受該命題,而如果對于自己身陷婚外戀且想娶另一位女子的丈夫來說,聽到“妻子不忠”這一命題時不僅不會憤怒,而且會較容易就相信并接受該命題并巧妙加以利用。這充分說明,當一個人相信P 時,必然伴隨著情感,也即必然伴隨著肯定或否定認知態度。因此,“相信”這一行為不是純理智的,它內在地包含著情感。其二,信念本身也是情感之物,正是如此,信念不像西方主流哲學思想所認為的那樣是惰性的。以饑腸轆轆的人在房間尋找食物為例,當該人確立了“屋里沒有食物”這一信念后,如果按照把心靈視為理性之物并把信念視為惰性之物的西方主流哲學思想所述,該信念只含有純理論性或認知性特征且在因果上不具有主動性,那么持有該信念的人就不會走出房屋去外面尋找食物。然而,這顯然不符合事實。一旦確信屋里沒有食物,該人就會走出房屋,去外面尋找食物。如果信念是惰性的,那么,為什么持有該信念的人會走出房屋尋找食物呢?斯洛特指出,休謨、戴維森和其他行動哲學家都無法回答該問題。要對該問題作出有效回答,首先要從根本上否定信念是惰性的這一看法。斯洛特認為,信念不是惰性的,信念內在地含有情感性的動機,正是在情感動機的推動下,該人才走出房屋去外面尋找食物。這充分證明,信念不是純理智之物,也非惰性之物,它內在地包含著與情感有關的動機。基于從上述兩個視角作出的論證,斯洛特得出結論,“信念、推理及其類似之物本質上都包含某種感情,實際上并不存在所謂純理性之說”[9](2)。進一步說,一切功能良好的心智功能都離不開情感。就此而言,當美德倫理學聚焦于美德以及道德主體討論美德時,較之對美德給予理性闡釋的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無疑更符合心靈的情感本性,也更具理論優先性,而以此為基礎確立的道德規范理論也更具說服力。有鑒于此,較之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和多元論美德倫理學,由于較好地處理了美德與道德心理的關系,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在西方當代美德倫理學中似乎是最富前景也最有可能提出恰當規范理論的美德倫理學。因此,迄今為止,唯有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基于情感為道德提供了較系統的、可與道義論和后果主義相抗衡的規范理論。
三、理論探索與新成就
自2010 年出版《道德情感主義》以來,隨著《從啟蒙到承應》《完美的不可能性》《陰陽的哲學》《陰陽哲學大觀:從心靈和諧到宇宙和諧》《無處不在的情感:以陰陽觀之》等作品的相繼面世,以斯洛特為代表的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聚焦于移情(empathy)概念在道德規范問題上作出了卓有成就的理論探索。繼承18 世紀英國道德情感主義哲學提出的道德感官(Moral Sense)和同情(sympathy)概念,借鑒當代西方心理學針對鏡像神經元的研究,以斯洛特為代表的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試圖基于移情機制構建并闡述道德規范理論。總體看來,該理論有三個方面的新成就。
第一,就道德規范的情感表達而言,情感主義美德倫理論圍繞不以理性或任何既定道德判斷原則為預制前提的贊許和譴責討論道德判斷,認為伴隨著贊許或譴責的情感是溫暖感或心寒感。該觀點的創新在于,斯洛特之前很多討論情感或性格的倫理學家并不把溫暖感或心寒感而是把苦樂感視為贊許或譴責的情感表達形式,理由有二。其一,相信美德使人快樂而惡行則使人痛苦[10](40)。通過把苦樂感視為某種既定習慣或性格的試金石,《尼各馬科倫理學》第二卷指明,美德以各種方式與苦樂感相連,人們在苦樂感的幫助下形成各種性格。美德在苦樂感問題上不會保持中立,相反,道德美德需借助苦樂感的幫助才能臻于完美[10](38-39)。其二,相信美德和美可進行類比,二者同屬感官感受,一如美可令人愉悅,美德也使人愉悅。以此為基礎,近代英國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家們據此用苦樂感討論道德判斷。例如,哈奇森就認為,美德會給人帶來最持久、最高的快樂,而惡行則會給人帶來持續時間最長、最痛徹心扉的痛苦。然而,斯洛特認為,這種做法存在局限。援引《人性論》第三章第三節論述過的我們被慈愛感動得熱淚盈眶的現象,斯洛特認為,伴隨著美德的情感狀態并非快樂,而是令人溫暖的感覺,而伴隨著惡行的情感狀態也不是痛苦,而是令人心寒的感覺。當斯洛特主張把溫暖感或心寒感視為美德或惡行引起的情感感受時,這意味著他從根本上顛覆了亞里士多德對美德或惡行的看法。就此而言,當代西方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基于情感或性格所構建的道德規范學說無疑具有劃時代的創新價值。
第二,就規范賴以建立的基礎即情感機制而言,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并沒有停留于基于移情闡述該機制的階段,而是進一步深入剖析該機制的深層結構并基于該結構構建規范理論。當移情機制基于令人溫暖或心寒的情感感受作出道德判斷并為行為提供道德規范時,其內在運行機制將由內而外分別具有兩種表現形式。斯洛特借用中國哲學中的陰陽概念論述其內在表現形式。所謂陰,指的是對他人的情感產生承應(receptive/receptivity);所謂陽,指的是與承應緊密相連的理性控制(rational control)、定向沖力或目的(directed impulsion/purpose)。以仁愛為例,當旁觀者看到當事人展現仁愛之情并因此而贊許該情感時,該旁觀者就會把前者稱為陽,把后者稱為陰,一如陰陽彼此具有十分緊密的互補性關系,移情機制主導下的道德判斷過程也是如此。旁觀者一見到他人身上的仁愛之情,就會自動承應該情感并產生令人溫暖的感覺,其過程既是天然的、即時的,就其與他人身上的仁愛的關系來說,二者具有不可分割性。不過,單憑運行在移情機制內部的陰陽機制,我們無法生成以贊同和譴責為表現形式的情感主義道德判斷,也無法為道德確立規范,因為移情機制還須具有某種外在表現形式。斯洛特認為,用以建立道德規范的移情機制的外在表現即為當事人與旁觀者的二階情感關系。再以仁愛為例,當旁觀者見到當事人的仁愛之情而感知該情感并感到溫暖時,這種溫暖感并不能成為道德判斷或道德規范的情感來源,斯洛特將這種溫暖感稱為“一階移情”(first-order empathy),真正能成為道德判斷或規范之情感來源的是“二階移情”(second-order empathy),即旁觀者從當事人身上感知到的仁愛和令人溫暖的感受需再次被另一個旁觀者所感知,唯有二階移情才能為道德判斷或規范提供有效情感基礎。至此,在以陰陽為工作原理、以二階移情為表現形式的移情機制的作用下,令人溫暖的情感感受才真正得以成為道德判斷或規范的情感表達形式。
第三,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借助移情機制的先天性為規范確立強制性。通過改造克里普克(Saul Kripke)的指稱固定(reference-fixing)理論,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賦予了移情機制以先天性,從而使令人溫暖或心寒的情感感受從實然轉變成了應然。當克里普克在《命名與必然性》中使用指稱對不可進行分析定義的自然類詞項如“紅”等的指稱進行固定時,該理論并未試圖以同樣的方式處理道德詞項。斯洛特認為克里普克的這種做法無疑十分明智,因為他認為原汁原味的純克氏指稱固定理論無法用來固定道德詞項的指稱。以“紅色”為例,純粹的克氏指稱固定理論認為,“紅色”雖無法進行分析定義,但其指稱卻可通過我們對紅性的主觀體驗——對紅色波長的反射——被固定。雖然在相當抽象的意義上,還需輔以邏輯上的先天可能性才能使“紅色”的指稱被徹底固定,然而,克里普克的指稱固定并不重視也不需要從因果邏輯意義上的先天性入手對“紅色”的指稱進行固定。斯洛特指出,如果我們用這種類型的指稱固定理論解釋“道德善”,那么,這將意味著我們僅僅只能根據某種類似于對紅性的主觀性后驗經驗(如對紅色波長的反射)來固定其指稱。在此意義上,“以仁愛的方式而行動在道德上為善”這一判斷將失去先天基礎,而這與我們的道德直觀感受不吻合。因此,斯洛特認為我們需要對克氏指稱固定理論進行改造,以使其可用于固定道德詞項的指稱。斯洛特對克氏指稱固定理論給予的關鍵性改造在于,用潛在地存在于用以固定“紅色”一詞中的邏輯先天性取代后驗性經驗事實(如對紅色波長的反射)并用它固定“紅色”的指稱。經此改造,當我們對“紅色”的指稱進行固定時,就意味著在因果上為我們的紅色經驗負責的事物最終是客觀意義上(也即在一切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可能世界)的紅色,這一事實具有且保留了先天性,更確切地說,能使我們產生紅色主觀經驗的“紅性”源于先天事實。當我們把這種改造后的指稱固定理論用于固定“道德善”的指稱時,這意味著在移情機制的作用下產生的溫暖感或寒心感便能以先天的方式進行道德判斷并為道德提供規范。至此,經過對克氏指稱固定理論的改造,當我們在移情機制的作用下憑借溫暖感或心寒感理解道德善時,這種道德善也就相應具有了先天性,由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提供的道德規范理論也因此具有了先天基礎與理論合法性,從而擁有了真正可與道義論和后果主義道德規范理論相抗衡的可能性。
基于對三種不同類型的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在發展過程中共同面對的理論難題及其解決方案的描述與分析,我們發現,不管是對美德問題的討論,還是對規范問題的探索,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不僅超越了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和多元論美德倫理學,而且把當代西方美德倫理學推向了新的發展高度。就此言之,有兩點啟示:
其一,關于美德研究的啟示。要使基于性格討論的美德真正成為美德,正如安斯庫姆所言,道德哲學必須關注并研究道德心理,就此而言,道德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無疑是最關心道德心理的美德倫理學。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和多元論美德倫理學將使自身的美德理論面臨較嚴重的身份問題。如果說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是當代西方流行的三種美德倫理學中最靠近道德心理的美德倫理學而言,那么這是不是意味著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和多元論美德倫理學在其發展過程中要進一步向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靠攏?如果說是,這是否意味著亞里士多德主義美德倫理學和多元論美德倫理學將在美德、情感、動機、幸福以及道德行為等諸問題上放棄自身的理論立場?更確切地說,以美德與情感的關系為例,這是不是意味著這兩種美德倫理學將放棄自身的理性立場而轉向情感立場?很顯然,這都是有待研究的問題。
其二,關于規范的啟示。前文的分析顯示,當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基于移情機制在被改造后的克氏指稱固定理論的幫助下為道德提供規范時,這既意味著蘊含在指稱固定中的內在邏輯能以先天的方式為道德行為提供規范,也意味著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規范理論也會隨之擁有先天合法性。不過,需注意的是,美德倫理學在指稱固定的幫助下基于移情而建立起來的規范雖以先天為其合法性之來源,但此處所言的先天性與西方傳統理性主義哲學所討論的先天性卻有著本質不同。雖然美德倫理學基于移情和指稱固定理論為道德確立了具有先天特征的規范原則,但這并不意味著當代西方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因此可被納入西方傳統理性主義哲學的陣營之內。美德倫理學的這種新發展表明,作為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之理論基礎和哲學立場的經驗主義在當代呈現了與理性主義相融合的趨勢,但即便如此,也絕不意味著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可被劃入或等同于理性主義。毋寧說,為了使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真正建立起自身的規范理論,斯洛特并未把經驗主義視為一種綜合性的哲學思想,承認經驗主義的非綜合性,這意味著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相信我們除了能通過感官感知的途徑獲取知識外,還能通過先天的方式獲取知識。就此而言,由情感主義美德倫理學確立起來的規范不僅有效推動了當代美德倫理學的發展,而且也把18 世紀以來的情感主義倫理學推向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