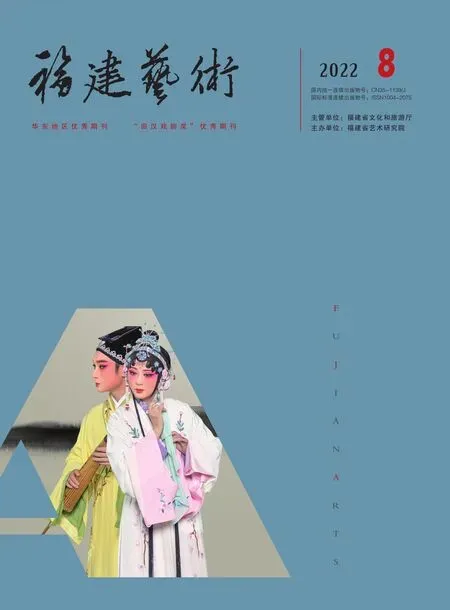徐曉鐘導(dǎo)演“梅花版”《雷雨》回眸
◎ 栗 征
一
在徐曉鐘先生堪稱(chēng)輝煌燦爛的導(dǎo)演生涯中,2003年執(zhí)導(dǎo)的《雷雨》顯得有些不起眼。除發(fā)表過(guò)一篇《實(shí)現(xiàn)老師夙愿 再讀〈雷雨〉詩(shī)情——〈雷雨〉導(dǎo)演闡述》[1]外,徐曉鐘本人日后很少提起此版《雷雨》的創(chuàng)作。而這篇導(dǎo)演闡述,相比他所寫(xiě)的《〈春秋魂〉導(dǎo)演闡述》《歌劇〈圖蘭朵〉導(dǎo)演闡述》,無(wú)論篇幅還是深度都有所不及,更不要說(shuō)像《培爾·金特》和《桑樹(shù)坪紀(jì)事》那樣,把極為詳盡的導(dǎo)演構(gòu)思公之于眾。學(xué)術(shù)界對(duì)此版《雷雨》也缺乏足夠的興趣,雖然2003年演出時(shí)舉辦了研討會(huì),但之后將此版《雷雨》納入研究范圍并做重點(diǎn)討論的理論批評(píng)文章寥寥無(wú)幾。
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當(dāng)然是有原因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們認(rèn)為,這是一次“慶典性”演出,因而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嚴(yán)肅性方面打了折扣,也就缺乏深入研究的必要。此版《雷雨》確實(shí)是一次“慶典性”演出,演出的首要目的是紀(jì)念中國(guó)戲劇梅花獎(jiǎng)創(chuàng)建20周年。將劇目選定為《雷雨》,既是因?yàn)椤独子辍吩谥袊?guó)話(huà)劇史上不可動(dòng)搖的標(biāo)志性地位,也有紀(jì)念《雷雨》誕生70周年之意(《雷雨》寫(xiě)作于1933年)。此版《雷雨》最為人津津樂(lè)道的是演出的完整性,即演出了序幕和尾聲。但這樣做很難說(shuō)是出自藝術(shù)家個(gè)人的創(chuàng)作意志還是出自向曹禺致敬的考慮,徐曉鐘在導(dǎo)演闡述中的說(shuō)法是:“我們想圓曹禺老師多年的愿望,努力按他自己的情感、哲思與藝術(shù)面貌,加上他自己在原稿中寫(xiě)的‘序’和‘尾聲’。”[2]為了更好地展示梅花獎(jiǎng)得主的風(fēng)采,此版《雷雨》由23位獲得過(guò)梅花獎(jiǎng)的演員聯(lián)袂主演,8個(gè)主要角色在不同的幕次由不同的演員分飾。排演時(shí)間只有12天,6位導(dǎo)演組成員分別負(fù)責(zé)四幕正戲和序幕、尾聲,分頭排練,最后合成。[3]這些事實(shí)加在一起,的確會(huì)讓人覺(jué)得,此版《雷雨》的慶典性和展示性超過(guò)創(chuàng)造性和學(xué)術(shù)性。
2003年演出期間召開(kāi)的研討會(huì)上,主持人廖奔做開(kāi)場(chǎng)白時(shí)說(shuō):“這次《雷雨》的演出,我認(rèn)為值得探討的有兩點(diǎn):一、集眾多的‘梅花獎(jiǎng)’演員、不同的演員來(lái)演繹同一人物,場(chǎng)次之間就有一種轉(zhuǎn)換,一種變動(dòng);二、演出加上了序幕、尾聲。”[4]根據(jù)研討會(huì)紀(jì)要,發(fā)言者關(guān)于演出本身的評(píng)論,大多是圍繞這兩點(diǎn)來(lái)談的。如果只聚焦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尤其是導(dǎo)演創(chuàng)作,這兩點(diǎn)究竟有多大意義呢?于前者,固然徐曉鐘利用若干演員分飾同一角色的特殊情況創(chuàng)造出一些精彩絕倫的戲劇場(chǎng)面(后文詳述),但這種情況在話(huà)劇演出中實(shí)屬罕見(jiàn),只能作為特例看待。于后者,研討會(huì)上已有專(zhuān)家指出,序幕和尾聲的演出效果并不理想,至少?zèng)]有達(dá)到曹禺理想中讓觀眾“可以‘帶著哀靜的心理回家’的效果”[5]。近年又有話(huà)劇史研究者考證,此版《雷雨》并非《雷雨》首次帶有序幕和尾聲的完整演出[6],看來(lái)“梅花版”《雷雨》的演出史意義也不如人們以為的那樣重大。
既然如此,“梅花版”《雷雨》是否已無(wú)再做細(xì)致回顧之必要?這樣判斷恐怕過(guò)于武斷。首先,無(wú)論是曹禺還是《雷雨》,徐曉鐘都不陌生。很難想象,2003年時(shí)將近75歲的徐曉鐘不曾對(duì)《雷雨》這部中國(guó)現(xiàn)代話(huà)劇的扛鼎之作產(chǎn)生過(guò)自己的心得體會(huì)。這和上世紀(jì)80年代初他導(dǎo)演《培爾·金特》時(shí)需要很長(zhǎng)時(shí)間做各方面準(zhǔn)備的情形殊為不同。[7]況且,盡管“梅花版”《雷雨》創(chuàng)作時(shí)間十分緊張,徐曉鐘還是把大量時(shí)間用于案頭工作,真正“落地”只占了3天,他有理由稱(chēng)“梅花版”《雷雨》的排演“是一次嚴(yán)肅的學(xué)術(shù)性創(chuàng)作活動(dòng)。”[8]其次,此次《雷雨》創(chuàng)作固然倉(cāng)促,但正是特殊的創(chuàng)作過(guò)程賦予其特殊的研究?jī)r(jià)值。徐曉鐘不僅是一位導(dǎo)演藝術(shù)家,還是一位導(dǎo)演理論家和教育家。他最重要的導(dǎo)演學(xué)論著之一《導(dǎo)演構(gòu)思論》[9]既是他對(duì)自己導(dǎo)演實(shí)踐的理論總結(jié),又是一套可用于教學(xué)、具有高度實(shí)用性和廣泛適用性的導(dǎo)演工作方法。在很短的時(shí)間內(nèi)排演《雷雨》,一方面,徐曉鐘理所當(dāng)然會(huì)調(diào)動(dòng)他多年以來(lái)對(duì)《雷雨》和曹禺的既有認(rèn)識(shí),另一方面,想必他會(huì)下意識(shí)地踐行他最熟悉的導(dǎo)演理念、運(yùn)用他最習(xí)慣的導(dǎo)演手法。從這個(gè)角度來(lái)說(shuō),“梅花版”《雷雨》的某些導(dǎo)演手法、某些“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或許能讓我們最直觀地透視徐曉鐘導(dǎo)演藝術(shù)的核心特征。本文即以此思路切入“梅花版”《雷雨》的導(dǎo)演創(chuàng)作。
二
在導(dǎo)演闡述中,徐曉鐘非常強(qiáng)調(diào)開(kāi)掘《雷雨》劇作本身所具有的詩(shī)情。他的想法是:
這一次《雷雨》演出的詩(shī)情、表現(xiàn)美學(xué)的特征,體現(xiàn)在努力對(duì)人物的主觀感受,對(duì)人物的意識(shí)與潛意識(shí)的開(kāi)掘上。對(duì)劇作者的情感與哲思,力圖用詩(shī)化的語(yǔ)匯予以外化。
總的來(lái)說(shuō),努力用詩(shī)情激蕩的基調(diào)來(lái)處理這臺(tái)戲。
努力剖析人物心靈,揭示曹禺筆下人物的豐富和深邃的人的精神生活。導(dǎo)演創(chuàng)作將會(huì)擴(kuò)展心理時(shí)空,努力創(chuàng)造人的精神生活;尋找體現(xiàn)人物情感激蕩的詩(shī)情濃郁的主觀幻化的語(yǔ)匯。[10]
徐曉鐘的導(dǎo)演創(chuàng)作是如何達(dá)成上述目標(biāo)的?“梅花版”《雷雨》的舞臺(tái)呈現(xiàn)體現(xiàn)了徐曉鐘怎樣的劇作解讀?要回答這些問(wèn)題,不妨從“梅花版”《雷雨》的“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入手。
在《導(dǎo)演構(gòu)思論》中,徐曉鐘把“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描述為導(dǎo)演的邏輯重音,指出“導(dǎo)演排戲,并不是所有戲都‘同等重要’地抓,而‘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是他要著力描繪的戲”;“導(dǎo)演處理一臺(tái)戲的風(fēng)格流派的原則和表現(xiàn)形式的特征,要在‘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處用最精彩的形式予以體現(xiàn)”;“導(dǎo)演創(chuàng)作的‘解釋’和‘立意’往往是從‘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的確定反映出來(lái)”。[11]考慮到《雷雨》創(chuàng)作時(shí)間的緊迫,徐曉鐘恐怕更會(huì)把導(dǎo)演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集中于“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的組織呈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無(wú)疑為我們辨察徐曉鐘導(dǎo)演構(gòu)思的藝術(shù)個(gè)性以及他對(duì)《雷雨》人物精神世界的把握提供了一條捷徑。
在筆者看來(lái),“梅花版”《雷雨》中,徐曉鐘“著力描繪”的“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有以下幾處。
第一幕,周樸園逼蘩漪喝藥。這場(chǎng)戲歷來(lái)被當(dāng)做重頭戲,不僅因?yàn)橹堋⑥蓝说闹苯記_突奪人眼球,更因?yàn)檫@次沖突鮮明地凸顯出人物性格且造成人物關(guān)系的急劇變化。在“階級(jí)論”的闡釋框架中,逼蘩漪喝藥被視為周樸園封建壓迫的一大罪狀。很長(zhǎng)時(shí)間里,演出這場(chǎng)戲的重心要放在周樸園身上,其次是蘩漪。比如北京人藝的《雷雨》經(jīng)典版本(1979年版),舞臺(tái)調(diào)度在周樸園和蘩漪等人之間形成逐漸強(qiáng)烈的對(duì)抗關(guān)系——周樸園位于舞臺(tái)一側(cè),其他四人(蘩漪、四鳳、周萍、周沖)位于舞臺(tái)另一側(cè),“導(dǎo)演要求周樸園要以自己的威嚴(yán)懾服所有的人”[12]。“梅花版”《雷雨》中,這場(chǎng)戲開(kāi)端時(shí)(即周樸園問(wèn)四鳳“叫你給太太煎的藥呢”),端坐于沙發(fā)上的周樸園占據(jù)著舞臺(tái)的中心位置。戲劇沖突展開(kāi)的過(guò)程中,雖然周萍并未移動(dòng)到蘩漪、四鳳、周沖身旁,但舞臺(tái)調(diào)度的思路仍是強(qiáng)調(diào)其他四人與周樸園之間的對(duì)抗。然而當(dāng)周樸園要求周萍跪下勸蘩漪時(shí),徐曉鐘別出心裁地將舞臺(tái)的焦點(diǎn)轉(zhuǎn)移到周萍身上。周樸園向周萍吼道“叫你跪下”后,舞臺(tái)上出現(xiàn)了較長(zhǎng)時(shí)間的停頓。此時(shí),周樸園和蘩漪從舞臺(tái)兩側(cè)各自回頭看向周萍,臺(tái)上臺(tái)下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周萍那里。隨著周萍走到舞臺(tái)中心(調(diào)度的依據(jù)是周萍向蘩漪移動(dòng)),燈光變化,轉(zhuǎn)臺(tái)把沙發(fā)轉(zhuǎn)離周萍,舞臺(tái)中心(即轉(zhuǎn)臺(tái)區(qū)域)進(jìn)入到周萍的心理時(shí)空。在“喝藥”這場(chǎng)戲來(lái)到高潮時(shí)轉(zhuǎn)而去突出表現(xiàn)周萍的心理震蕩,說(shuō)明徐曉鐘認(rèn)為,相比于周樸園和蘩漪,此時(shí)更需被優(yōu)先注意的是周萍的處境——一邊是周樸園的威嚴(yán),一邊是蘩漪的糾纏。“喝藥”并非只與周樸園和蘩漪相關(guān),周樸園有教子之意,蘩漪屈服的直接原因是避免周萍受辱。而周萍直勾勾盯著周樸園,又好像在驚恐地揣度,父親如此震怒是不是因?yàn)樗懒诵┦裁础_@就把第一幕最后周樸園訓(xùn)誡周萍的戲和“喝藥”一場(chǎng)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lái),使周萍的心理線(xiàn)獲得更清晰連貫的呈現(xiàn)。
第二幕,蘩漪與周萍談話(huà)后的獨(dú)白。“喝藥”的軒然大波過(guò)后,蘩漪找到周萍,想和他開(kāi)誠(chéng)布公地談?wù)劊f(shuō)服他不要離家。他們的對(duì)手戲?yàn)榫o隨其后的蘩漪獨(dú)白做足了情感鋪墊。從蘩漪披露周萍是私生子到蘩漪質(zhì)問(wèn)周萍“你怎么肯一個(gè)人走”,二人始終沒(méi)有離開(kāi)樓梯這一局促的空間。他們?cè)跇翘萆系倪M(jìn)退閃躲增添了舞臺(tái)調(diào)度的立體感,與斑駁灰墻的貼近放大了他們的掙扎與無(wú)奈。談話(huà)不歡而散,蘩漪挽留周萍的努力失敗了,徐曉鐘跳過(guò)魯貴上場(chǎng)的一段戲,直接轉(zhuǎn)入蘩漪的獨(dú)白:
熱極了,悶極了,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變成火山的口,熱烈烈地冒一次,什么我都燒個(gè)干凈,那時(shí)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凍成死灰,一生只熱烈地?zé)淮危簿退銐蛄恕N疫^(guò)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的。哼,什么我都預(yù)備好了,來(lái)吧,恨我的人,來(lái)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來(lái)吧,我在等候著你們。[13]
曹禺在1951年“開(kāi)明版”《雷雨》中把此段獨(dú)白簡(jiǎn)化為“熱極了,悶極了,這日子真過(guò)不下去了!”[14]。北京人藝1979版《雷雨》演出的即是這句簡(jiǎn)化后的臺(tái)詞,2004版干脆連簡(jiǎn)化后的臺(tái)詞也刪掉了。“梅花版”《雷雨》演出了蘩漪的完整獨(dú)白,濃墨重彩地渲染蘩漪的渴望、激情與生命意志。這是蘩漪如火似電的“雷雨”式性格的詩(shī)化展示,是她熾熱情感的集中爆發(fā)。當(dāng)蘩漪重復(fù)著“恨我的人,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來(lái)吧”時(shí),轉(zhuǎn)臺(tái)轉(zhuǎn)出三組周樸園、周萍、四鳳,顯然他們就是蘩漪所指的人。徐曉鐘對(duì)不同演員分飾同一角色這一客觀條件的巧妙運(yùn)用帶來(lái)了奇特的舞臺(tái)效果。獨(dú)白往往被認(rèn)為游離于戲劇情境之外,延緩甚或中斷戲劇情節(jié)的發(fā)展。如狄德羅認(rèn)為:“獨(dú)白對(duì)劇情來(lái)說(shuō)是一個(gè)停頓的時(shí)刻……如果獨(dú)白太長(zhǎng),就會(huì)傷害劇情的自然性,使它停頓得過(guò)久。”[15]徐曉鐘的處理則把蘩漪的獨(dú)白拉回到《雷雨》情節(jié)的上下文中。這些形象的突然出現(xiàn)提醒觀眾不要過(guò)分沉浸于舞臺(tái)上充沛的情感激蕩而忽視蘩漪臺(tái)詞的具體指向,蘩漪不是在空洞地抒情,而是在絕望的控訴。觀眾也許會(huì)因此而思考,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蘩漪的命運(yùn)悲劇?
第二幕的另一個(gè)“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出現(xiàn)在侍萍開(kāi)始意識(shí)到周公館似曾相識(shí)時(shí)。伴隨著滴水聲,侍萍疑惑著觀察著四周,轉(zhuǎn)臺(tái)把沙發(fā)轉(zhuǎn)向臺(tái)后、把樹(shù)叢轉(zhuǎn)向臺(tái)前。侍萍一邊說(shuō)著“我的魂兒來(lái)過(guò)這兒”一邊在樹(shù)叢中穿梭,似乎樹(shù)叢更能勾起她久遠(yuǎn)的記憶。她叫四鳳去看柜子里有沒(méi)有繡花虎頭鞋,由于她邁步的方向與轉(zhuǎn)臺(tái)轉(zhuǎn)動(dòng)的方向相反,事實(shí)上她在原地踏步,這恰好對(duì)應(yīng)了她的臺(tái)詞“我心里有點(diǎn)怯,我有點(diǎn)走不動(dòng)”。徐曉鐘又一次借轉(zhuǎn)臺(tái)實(shí)現(xiàn)劇情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與人物心理時(shí)空的滲透和轉(zhuǎn)換。
第三幕有兩處“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一是周沖的獨(dú)白,二是蘩漪關(guān)窗的瞬間。在《導(dǎo)演構(gòu)思論》中,徐曉鐘特別指出:“高潮肯定是‘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但‘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并不只是高潮。高潮的戲我們會(huì)注意,而非高潮處的‘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常常被忽略。”[16]周沖的獨(dú)白是在向四鳳描繪夢(mèng)幻中的理想世界,當(dāng)然不是高潮,但這段堪稱(chēng)《雷雨》中最具詩(shī)情畫(huà)意的臺(tái)詞,對(duì)于理解周沖的精神世界、涂畫(huà)周沖那一抹明麗色彩,卻是十分關(guān)鍵的。徐曉鐘此處對(duì)轉(zhuǎn)臺(tái)的使用與上一幕侍萍的“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相仿,所不同的是,樹(shù)叢之于侍萍猶如舊日夢(mèng)魘的化身,而在暖色調(diào)的燈光下,周沖拉著四鳳在樹(shù)叢間奔跑,舞臺(tái)上洋溢著青春的美好夢(mèng)幻,哪怕那是不切實(shí)際的空想。
“蘩漪關(guān)窗”是《雷雨》第三幕的高潮。關(guān)于這一場(chǎng)面及此前周萍來(lái)魯家與四鳳幽會(huì)的段落,徐曉鐘在導(dǎo)演闡述中做了比較詳細(xì)的說(shuō)明:
第三幕,四鳳家的小窗實(shí)際上是展現(xiàn)人物心靈的小窗,在寫(xiě)實(shí)原則下,這扇窗戶(hù)只能在臺(tái)后的深處。根據(jù)現(xiàn)在舞臺(tái)時(shí)空處理的表現(xiàn)美學(xué)特征,我們可以把它搬到臺(tái)口樂(lè)池的升降臺(tái)前,把曹禺同志放在窗口呈現(xiàn)的場(chǎng)面,其中包括蘩漪在雷電中在窗外的閃現(xiàn),都呈現(xiàn)在觀眾的面前。當(dāng)蘩漪在雷電閃耀中在窗口出現(xiàn)的那一瞬間,我們“疊印”三個(gè)蘩漪:一個(gè)因忌妒而憤怒的蘩漪;一個(gè)苦苦哀求周萍不要忘卻舊情的蘩漪;最后從樂(lè)池升上來(lái)的,是曹禺同志在劇本中描寫(xiě)的蘩漪,她“像個(gè)死尸……痙攣地不出聲地苦笑,淚水流到眼角下”。[17]
三個(gè)蘩漪的“疊印”,強(qiáng)調(diào)了作為個(gè)體的人的多面性。人是復(fù)雜的,三個(gè)蘩漪都是真實(shí)存在的。只有把性格和經(jīng)歷的各個(gè)側(cè)面疊加起來(lái),才是完整的蘩漪。“關(guān)窗”固然是瞬間行為,但這一舉動(dòng)背后蘊(yùn)藏的豐富情感以及蘩漪此時(shí)如同鬼魅的形象,必須要在她全部的生命歷程中獲得理解。
第四幕,從周樸園當(dāng)眾說(shuō)出魯媽就是周萍的生母直至此幕落幕。得知魯媽就是三十年前死了的侍萍,周萍、蘩漪、四鳳、周沖,每個(gè)人都受到劇烈的心理震動(dòng)。在他們之中,徐曉鐘最突出表現(xiàn)的是周萍。命運(yùn)和周萍開(kāi)了一個(gè)巨大的玩笑,他發(fā)出一陣怪笑:“轉(zhuǎn)臺(tái)轉(zhuǎn)出三個(gè)‘侍萍’:一個(gè)正在哺育嬰兒,一個(gè)在給幼兒縫補(bǔ),第三個(gè)正在給少年教讀”[18]。三十年前侍萍被驅(qū)逐出周家時(shí),周萍剛剛一歲,轉(zhuǎn)臺(tái)中出現(xiàn)的場(chǎng)景只可能出自周萍想象。一方面,想象的溫馨與現(xiàn)實(shí)的殘酷形成強(qiáng)烈對(duì)比,讓人更覺(jué)悲涼。另一方面,與上一幕“關(guān)窗”時(shí)“疊印”不同蘩漪的思路一致,兒童形象把我們的思緒引向周萍完整的生命歷程。
緊接著,慘劇發(fā)生,四鳳、周沖、周萍接連喪命。徐曉鐘把四鳳和周沖觸電身亡的暗場(chǎng)戲放到了明場(chǎng):
在全劇結(jié)束前四鳳觸電及周沖也不幸觸電雙雙死亡的場(chǎng)面,在我們的情感中視同一場(chǎng)莊嚴(yán)的“青春祭”,覺(jué)得有必要推到觀眾面前。借助舞臺(tái)的假定性原則,我們讓四鳳跑向后花園,周沖緊緊跟上,同時(shí)樂(lè)池升上,一座高平臺(tái)呈現(xiàn)在觀眾面前,四鳳與周沖先后跳上這座平臺(tái)——雷電炸裂,兩個(gè)年輕人在特寫(xiě)燈的頻閃中,慢慢倒下,滾滾雷聲,為他們哀鳴……[19]
三
根據(jù)以上對(duì)“梅花版”《雷雨》“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的分析,我們可以做出如下總結(jié)。
第一,《雷雨》中8個(gè)主要角色,出現(xiàn)在“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最多的是蘩漪和周萍。可以說(shuō),在蘩漪和周萍身上,徐曉鐘花的心思最多、下的功夫最狠。重視蘩漪并不稀奇,北京人藝2004版《雷雨》也把蘩漪定位為第一主角。這既是因?yàn)檗冷羯砩辖豢椫摹白顨埧岬膼?ài)和最不忍的恨”賦予她高度的藝術(shù)魅力,也是因?yàn)榉变粼凇独子辍穭∽鹘Y(jié)構(gòu)中的重要作用。一旦意識(shí)到繁漪是《雷雨》劇情發(fā)展的驅(qū)動(dòng)力,就會(huì)順理成章地重視起周萍,因?yàn)榉变粼趧≈械呢灤┬袆?dòng)就是挽留周萍,重獲周萍的愛(ài)情以實(shí)現(xiàn)自我拯救。在這個(gè)意義上,繁漪和周萍是《雷雨》中最關(guān)鍵的一組人物關(guān)系。“梅花版”《雷雨》的“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第一幕“喝藥”、第二幕“繁漪獨(dú)白”、第三幕“關(guān)窗”、第四幕“認(rèn)母”,均與繁漪和周萍直接相關(guān)。徐曉鐘緊緊抓住繁漪和周萍之間的沖突作為“梅花版”《雷雨》的主線(xiàn),從一個(gè)側(cè)面反映出他對(duì)《雷雨》劇作的認(rèn)識(shí)水平,無(wú)論這是參考相關(guān)研究的結(jié)果,還是純粹藝術(shù)直覺(jué)的創(chuàng)造。
第二,徐曉鐘在開(kāi)掘人物心靈世界的基礎(chǔ)上力圖透視人物完整的生命歷程。在《導(dǎo)演構(gòu)思論》中,徐曉鐘把“人學(xué)開(kāi)掘的加深”列為“導(dǎo)演構(gòu)思”應(yīng)有品格的組成部分。所謂“人學(xué)開(kāi)掘的加深”,即加強(qiáng)“對(duì)于人的心理、情感、靈魂和內(nèi)在生命的開(kāi)掘和研究”[20]。進(jìn)入新時(shí)期后,“人學(xué)戲劇”的觀念迅速轉(zhuǎn)變了戲劇的政治化和社會(huì)化傾向,戲劇的“人學(xué)”定位——關(guān)注人的尊嚴(yán)和價(jià)值、思索人的靈魂和本質(zhì)、探尋人性的復(fù)雜和多面,是導(dǎo)演主體意識(shí)覺(jué)醒的重要原因。如徐曉鐘所說(shuō):“新時(shí)期戲劇結(jié)構(gòu)、表現(xiàn)手法所發(fā)生的巨大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學(xué)的研究,由于人的心靈與深層意識(shí)開(kāi)掘的需要。”[21]徐曉鐘本人上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和理論探索,正是“人學(xué)”內(nèi)涵在導(dǎo)演藝術(shù)領(lǐng)域不斷深化拓展的杰出代表。“梅花版”《雷雨》的“人學(xué)”開(kāi)掘,突出表現(xiàn)為注重人的完整性。其一是注重人的復(fù)雜性,人的性格及對(duì)他人的情感時(shí)常會(huì)存在多個(gè)側(cè)面,這些側(cè)面可能彼此矛盾,但又是辯證統(tǒng)一的;其二是注重人的歷史性,人的當(dāng)下無(wú)法與過(guò)去割裂。徐曉鐘在特定時(shí)刻用導(dǎo)演手段為戲劇人物的多面性和歷史性找到了相應(yīng)的外化形式。其三,除四鳳、周沖、周萍相繼死亡外,《雷雨》四幕正戲并未交代其他5個(gè)主要人物的結(jié)局,“梅花版”《雷雨》完整演出序幕和尾聲,客觀上起到補(bǔ)足人物完整生命歷程的作用。
第三,徐曉鐘偏愛(ài)且擅長(zhǎng)使用轉(zhuǎn)臺(tái)。“梅花版”《雷雨》“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的營(yíng)造,大多離不開(kāi)轉(zhuǎn)臺(tái)的功勞。王曉鷹把“使用轉(zhuǎn)臺(tái)”視為“徐曉鐘處理舞臺(tái)空間的最明顯的特點(diǎn)”,徐曉鐘“眾多的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精彩處理幾乎都是在舞臺(tái)的轉(zhuǎn)動(dòng)之中展開(kāi)的”[22]。使用轉(zhuǎn)臺(tái)當(dāng)然不是徐曉鐘的專(zhuān)利,但徐曉鐘使用轉(zhuǎn)臺(tái)的目的和思路有著明確的美學(xué)傾向。不妨以其他習(xí)慣使用轉(zhuǎn)臺(tái)的導(dǎo)演做參照。在德國(guó)導(dǎo)演烏爾里希·拉舍(Ulrich Rasche)的多部作品中,一直旋轉(zhuǎn)著的轉(zhuǎn)臺(tái)(更確切地說(shuō)是轉(zhuǎn)盤(pán))是演出最重要的舞臺(tái)裝置和功能元素。拉舍的“機(jī)器劇場(chǎng)”強(qiáng)調(diào)人和機(jī)器之間的對(duì)抗與張力,通過(guò)演員在轉(zhuǎn)臺(tái)上耗費(fèi)大量體力的不間斷運(yùn)動(dòng),凸顯演員的身體存現(xiàn)。徐曉鐘的美學(xué)趣味與拉舍大相徑庭。徐曉鐘為何如此鐘愛(ài)甚至迷戀轉(zhuǎn)臺(tái),王曉鷹做過(guò)十分到位地總結(jié):“由于轉(zhuǎn)臺(tái)轉(zhuǎn)動(dòng)時(shí)產(chǎn)生的空間流動(dòng)感具有高度假定的性質(zhì),使得演出中的現(xiàn)實(shí)空間與心理空間、客觀空間和主觀空間的有機(jī)滲透和自如轉(zhuǎn)換成為可能,而且轉(zhuǎn)臺(tái)的舒展、流暢、平緩的旋轉(zhuǎn)感覺(jué),更有利于抒發(fā)深沉的情感、渲染濃郁的氣氛。徐曉鐘顯然明確意識(shí)到了轉(zhuǎn)臺(tái)的這些特征,他正是要利用這些實(shí)現(xiàn)自己的‘結(jié)合再現(xiàn)和表現(xiàn)兩種美學(xué)原則,在破除生活幻覺(jué)的同時(shí)創(chuàng)造詩(shī)化的意象’的藝術(shù)追求,這也就是徐曉鐘執(zhí)意要重復(fù)使用轉(zhuǎn)臺(tái)的根本原因。”[23]“梅花版”《雷雨》中,轉(zhuǎn)臺(tái)最主要的作用是,借由場(chǎng)景的變化實(shí)現(xiàn)劇情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與人物心理時(shí)空之間的轉(zhuǎn)換。具體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是“聚焦”,把觀眾的注意力“框定”到特定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如在“喝藥”一場(chǎng)開(kāi)辟出周萍的心理時(shí)空;第二種是“解釋說(shuō)明”,轉(zhuǎn)臺(tái)區(qū)域進(jìn)入非劇情空間,但又與轉(zhuǎn)臺(tái)之外的劇情空間保持緊密聯(lián)系,因?yàn)檗D(zhuǎn)臺(tái)上出現(xiàn)的場(chǎng)景或形象,構(gòu)成對(duì)轉(zhuǎn)臺(tái)外劇情(特別是人物情感)的補(bǔ)充性解釋說(shuō)明。“梅花版”《雷雨》對(duì)轉(zhuǎn)臺(tái)的使用首先是為了“人學(xué)開(kāi)掘”,在“人學(xué)開(kāi)掘”的過(guò)程中自然生發(fā)出深沉濃郁的詩(shī)情。
四
《雷雨》演出史上,“梅花版”《雷雨》外,還有兩版《雷雨》與徐曉鐘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1993年,尚在跟隨徐曉鐘攻讀博士學(xué)位的王曉鷹為中國(guó)青年藝術(shù)劇院導(dǎo)演了“沒(méi)有魯大海”的《雷雨》。多年之后,王曉鷹談及此版《雷雨》,總會(huì)深情回憶起導(dǎo)師徐曉鐘帶他看望曹禺先生并向先生征求意見(jiàn)的場(chǎng)景。2011年,福建人藝推出實(shí)驗(yàn)版敘述體《雷雨》,導(dǎo)演陳大聯(lián)曾在中央戲劇學(xué)院“戲劇創(chuàng)作高級(jí)研修班”受教于徐曉鐘,他還是“梅花版”《雷雨》的導(dǎo)演組成員之一。三版《雷雨》的樣貌各異其趣,但基本思路均是在“人學(xué)戲劇”的定位下對(duì)《雷雨》進(jìn)行去歷史化的人學(xué)解讀。陳大聯(lián)認(rèn)為:“怎樣將‘人’還原為曹禺戲劇的‘主體’,回歸到‘人’的本質(zhì),是曹禺戲劇作品當(dāng)代性的存在核心。”[24]王曉鷹刪去魯大海,“一方面是為了減去‘罷工’這條與矛盾沖突主線(xiàn)關(guān)系不那么密切的線(xiàn)索以縮短篇幅,但更重要、更具本質(zhì)性的意義卻在于試圖變一個(gè)思路、換一種眼光來(lái)解讀《雷雨》。”他想“穿越人物之間社會(huì)階層差別帶來(lái)的對(duì)立沖突的表面,進(jìn)入那些人物復(fù)雜隱秘的情感世界,力圖開(kāi)掘人物更深的生命體驗(yàn),從而開(kāi)掘出《雷雨》超越時(shí)代的深層意蘊(yùn)”[25]。
本文回顧2003年“梅花版”《雷雨》的導(dǎo)演創(chuàng)作,試圖通過(guò)分析徐曉鐘在特殊的創(chuàng)作條件下如何處理“關(guān)節(jié)時(shí)刻”管窺其導(dǎo)演藝術(shù)。筆者想強(qiáng)調(diào)的是,徐曉鐘導(dǎo)演藝術(shù)思維模式與美學(xué)風(fēng)格的形成與他對(duì)戲劇人學(xué)內(nèi)涵的注重密不可分。如果說(shuō)“導(dǎo)演構(gòu)思論”是徐曉鐘導(dǎo)演藝術(shù)的方法論,“人學(xué)戲劇”就是方法論背后的世界觀。在梳理總結(jié)徐曉鐘導(dǎo)演藝術(shù)的源流脈絡(luò)時(shí),著眼于他的教育背景(留學(xué)蘇聯(lián)的經(jīng)歷)、中國(guó)藝術(shù)傳統(tǒng)的影響和他個(gè)人的文化修養(yǎng)外,也不能忽視徐曉鐘導(dǎo)演創(chuàng)作黃金時(shí)期[26]“人學(xué)戲劇”的時(shí)代語(yǔ)境。在“人學(xué)戲劇”背景下考察徐曉鐘的導(dǎo)演藝術(shù),一方面有助于我們深入認(rèn)識(shí)支撐其藝術(shù)追求的哲學(xué)基礎(chǔ),另一方面促使我們思考徐曉鐘與其他戲劇家(包括戲劇藝術(shù)家和戲劇理論家)同時(shí)期藝術(shù)實(shí)踐與理論探索的互文性關(guān)系。
注釋?zhuān)?/p>
[1][2]徐曉鐘《導(dǎo)演藝術(shù)論》,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252頁(yè),第246頁(yè)。該文原載于《中國(guó)戲劇》,2003年第7期。
[3]徐曉鐘為此次《雷雨》演出總導(dǎo)演,鮑黔明、酈子柏、陳大林、夏波、陳大聯(lián)、王紹軍擔(dān)任分幕導(dǎo)演。
[4][5]鄒紅語(yǔ)《永遠(yuǎn)的〈雷雨〉——全本〈雷雨〉研討會(huì)紀(jì)要》,中國(guó)戲劇家協(xié)會(huì)主編《中國(guó)戲劇梅花獎(jiǎng)20周年文集》,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頁(yè),第327頁(yè)。
[6]參見(jiàn)侯抗《中國(guó)戲劇學(xué)會(huì)與〈雷雨〉的首次完整演出考論》,《文學(xué)研究》第7卷第2輯,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
[7]徐曉鐘導(dǎo)演《培爾·金特》時(shí),“從分析劇本,辯論演劇觀念,建立導(dǎo)演構(gòu)思,直到體現(xiàn)構(gòu)思,先后經(jīng)歷了一年的時(shí)間”。見(jiàn)宮曉東《徐曉鐘在〈培爾·金特〉排練中》,林蔭宇編《徐曉鐘導(dǎo)演藝術(shù)研究》,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1991年版,第267頁(yè)。
[8][9][10][11][16][17][18][19][20][21]徐曉鐘《導(dǎo)演藝術(shù)論》,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17年版,第243頁(yè),第3-73頁(yè),第247頁(yè),第66-71頁(yè),第66頁(yè),第248-249頁(yè),第248頁(yè),第249頁(yè),第10頁(yè),第13頁(yè)。
[12]蘇民等編《〈雷雨〉的舞臺(tái)藝術(shù)》,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頁(yè)。“喝藥”一場(chǎng)的舞臺(tái)調(diào)度,詳見(jiàn)本書(shū)第79-105頁(yè)。
[13][14]曹禺《雷雨》,《曹禺全集》第一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82-83頁(yè),第63頁(yè)。《曹禺全集》收錄的《雷雨》據(jù)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雷雨》單行本校訂。
[15](法)狄德羅《論戲劇詩(shī)》,徐繼曾、陸達(dá)成譯,《狄德羅美學(xué)論文選》,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4年版,第203頁(yè)。
[22][23]王曉鷹《試析“徐曉鐘模式”》,《戲劇思考——王曉鷹戲劇文集》,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頁(yè),第181頁(yè)。
[24]陳大聯(lián)《〈雷雨〉的當(dāng)代性 實(shí)驗(yàn)戲劇〈雷雨〉創(chuàng)作談》,《劇本》2013年第12期。
[25]王曉鷹《曹禺與一出沒(méi)有魯大海的〈雷雨〉》,《戲劇思考——王曉鷹戲劇文集》,中國(guó)戲劇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頁(yè)。
[26]上世紀(jì)80年代可以說(shuō)是徐曉鐘導(dǎo)演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shí)期,他最重要的3部作品《馬克白斯》(1980年)、《培爾·金特》(1983年)、《桑樹(shù)坪紀(jì)事》(1988年)均創(chuàng)作于這一時(sh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