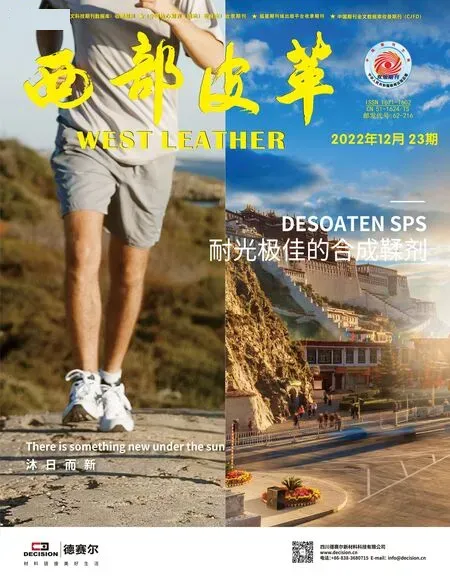人工智能時代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與技術關系新思考
王蘊杰
(廣東工業(yè)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0)
引言
近年來,我國經(jīng)濟、技術的高速發(fā)展推動著社會文化的全面進步,作為新興產(chǎn)業(yè)的代表,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呈現(xiàn)出蓬勃發(fā)展之勢,這使得人民物質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的同時,對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的需求也越來越豐富,居民的消費結構逐漸呈現(xiàn)出由原先的以物質消費為主向以精神消費為主的轉變與升級,這樣的變化又反過來激發(fā)了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進一步發(fā)展。人工智能時代,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以技術創(chuàng)新為動力、以文化創(chuàng)意為價值核心,同時,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對文化生活的前沿需求又不斷為技術創(chuàng)新和產(chǎn)業(yè)升級提供了強大的驅動力。
1 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現(xiàn)狀與問題
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作為新興產(chǎn)業(yè)之一,是推動文化產(chǎn)業(yè)整體發(fā)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其發(fā)展的關鍵點和支撐點[1]。作為具有深厚文化傳統(tǒng)的文化大國,中國非常重視現(xiàn)代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近幾年,國內許多地區(qū)和城市充分利用其地域、經(jīng)濟和人才等多方優(yōu)勢,支持和推動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各地政府聯(lián)合企業(yè)為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創(chuàng)造優(yōu)良的市場環(huán)境,在城市內成立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園區(qū),并不斷完善相關基礎配套設施以進一步擴大人才的引進[2]。在各地逐漸形成規(guī)模化的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集群的過程中,我國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的競爭優(yōu)勢也逐步體現(xiàn)出來。2016 年震驚世界的人工智能阿爾法狗戰(zhàn)勝韓國棋手李世石事件,也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人工智能的實力以及未來在各個領域發(fā)展應用的無限可能性。國家對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的大力支持和人工智能技術在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應用讓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邁入了全新的階段。
然而,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在發(fā)展的過程中仍然出現(xiàn)了一些問題。雖然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在前期發(fā)展中一直呈現(xiàn)向好趨勢,但內部仍然存在著市場主體競爭不充分的現(xiàn)象[3],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的企業(yè)推動力不足,而市場規(guī)則和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缺失長時間也會阻礙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未來的整體發(fā)展。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主要包括傳媒、藝術設計、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廣告、廣播影視、計算機服務等方面的創(chuàng)意內容,其中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作為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中極為重要內容同時也最具大眾滲透力。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是具有創(chuàng)意的經(jīng)過設計的文化內容產(chǎn)品,既包含文化意涵又具有實用功能,它以傳統(tǒng)文化內容為土壤,對其中所蘊含的美好精神、情感和形象等核心價值進行二次創(chuàng)意創(chuàng)作與表達,通過對文化內容的創(chuàng)新設計人們可以感知并領悟文化與創(chuàng)意的內涵[4]。因此,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更強調“文化”與“創(chuàng)新”二者的良好結合,區(qū)別于其他一般產(chǎn)品,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特殊性在于其文化創(chuàng)意的內容,這也是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核心價值[5]。在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的快速發(fā)展下,文創(chuàng)市場出現(xiàn)了一個普遍的問題,即企業(yè)在一味的追求文創(chuàng)潮流,卻沒有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消費市場千篇一律的審美和山寨產(chǎn)品的頻發(fā)已成普遍現(xiàn)象,在創(chuàng)意和設計方面也只一味的挖掘“文”的內容,而忽視了“創(chuàng)”的部分,在推新機制和創(chuàng)新創(chuàng)意上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表現(xiàn)出較為明顯的后勁不足傾向[6]。
2 人工智能時代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發(fā)展新范式
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為社會發(fā)展提供了新的發(fā)展方向,高新技術在文學、藝術等領域展現(xiàn)出廣闊的應用前景,文化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也呈現(xiàn)出獨具創(chuàng)新意義的跨越式趨勢。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等新興技術形態(tài)的深度推廣與應用,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也逐漸呈現(xiàn)出富含體驗與內涵的數(shù)字化、場景化發(fā)展態(tài)勢,這種在文化創(chuàng)意領域呈現(xiàn)出的全新發(fā)展形態(tài)正是托馬斯·庫恩(Thomas Samuel Kuhn)所說的“范式轉移”①(Paradigm Shift)。在人工智能時代,已然改變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范式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全新的文化生產(chǎn)方式,不僅體現(xiàn)在技術對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的促進作用中,同時也在其發(fā)展模式和價值追求的轉變中表現(xiàn)出來,原有的生產(chǎn)理念、方法和價值觀已不再適應新的時代特點與發(fā)展模型,因此無論是行業(yè)內的從業(yè)者還是享受消費的公眾都必須做出相應的改變[7]。
新興技術在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應用,為文化創(chuàng)意內容的生產(chǎn)與分發(fā)提供了先進的技術方法與工具,為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產(chǎn)品帶來了豐富的內涵、創(chuàng)新的表現(xiàn)形式和多元的消費終端。首先,以智能化為代表的技術為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的內容生成、分層、推薦等環(huán)節(jié)帶來了變革性的改變,使文化內容的創(chuàng)作效率提升,生產(chǎn)運營成本下降。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在技術的介入下將更加深入的挖掘IP 內容背后的文化內涵,以文化內核支撐并延展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鏈,進而打破各類產(chǎn)業(yè)之間的壁壘[8]。特別是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的創(chuàng)作領域,以文化創(chuàng)意和文化價值作為核心考量標準,在產(chǎn)品內容創(chuàng)作中不斷激發(fā)衍生產(chǎn)品的創(chuàng)新,通過設計對品牌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進行激活,使其一系列衍生創(chuàng)意產(chǎn)品既具備了趣味性,也不失知識性和實用性;在對產(chǎn)品進行推廣的過程中,一方面充分利用大數(shù)據(jù)等技術手段挖掘社會公眾可能存在的物質和精神需求,另一方面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渠道擴大品牌影響力,從而達到提升自身價值的目的。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不斷深入應用,文化創(chuàng)意領域在內容創(chuàng)作與美學觀念上都獲得了一定的更新和提升,二者的融合發(fā)展催生出新的藝術體驗與欣賞形態(tài)以及文化形態(tài)。同時,通過全新的數(shù)字化媒介,人工智能技術使人腦中審美意象的轉化變得更加方便快捷,區(qū)別于原有的文化內容生產(chǎn)模式,技術的應用在最大程度上對復雜、深層的文化要素進行整合,通過對相關數(shù)據(jù)信息的挖掘,可以不斷為內容生產(chǎn)提供創(chuàng)意元素。在這一過程中,文化內容生產(chǎn)、表達以及文化產(chǎn)品與信息接收狀態(tài)都隨之改變,平臺及分發(fā)渠道的工作變得更有效率,而文化內容也得到更廣泛的傳播,智能文化的定制式生產(chǎn)也更加貼合用戶的需求。另一方面,作為文化內容接收端的公眾也在互聯(lián)網(wǎng)和智能技術介入文化產(chǎn)業(yè)的過程中獲得了更加精準的服務。文化創(chuàng)意企業(y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平臺對內容進行智能分發(fā)與傳播,首先通過大數(shù)據(jù)深度挖掘受眾偏好、心理和行為以及個人文化習慣等來實現(xiàn)用戶需求的精準定位和分類,再進一步收集和挖掘受眾反饋與評論,經(jīng)過多次迭代最終將定制性內容傳遞到不同用戶手中[9]。
在人工智能主導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鏈重塑的過程中,AI 深度學習可以為內容生產(chǎn)和傳播提供精準的用戶相關信息,為生產(chǎn)者創(chuàng)造智能化的想象與創(chuàng)作空間;在運營端,愈發(fā)具有針對性的智能識別能力和大數(shù)據(jù)深度挖掘技術的應用也讓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的設計更加個性化、優(yōu)質化,并進一步推動了智能化的精準傳播[10]。智能算法和大數(shù)據(jù)一邊不斷了解和學習消費者的文化偏好、行為模式和生活習慣,一邊為人類提供更加多元的個性化定制內容,在提高消費者文化生活質量和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也讓智能平臺不斷更新改進,進行更加快捷、精準的高質量創(chuàng)作,在徹底改變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生產(chǎn)、運營和營銷模式的同時形成了三者的良性循環(huán)。
3 人工智能時代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挑戰(zhàn)與問題
雖然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人工智能等技術的介入讓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從范式到方法都得到了更新,然而在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向著虛擬化、數(shù)字化、智能化方向發(fā)展的進程中,依然暴露出了一些潛在的風險[11]。在經(jīng)濟利益的推動下,文化創(chuàng)意企業(yè)對產(chǎn)出量和收益率的過分追求可能會忽視文創(chuàng)產(chǎn)品的內容質量與價值,同時對智能化工具的過度依賴將會引發(fā)部分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思想內容混亂、文化內容創(chuàng)作的情感感知和文化藝術創(chuàng)造能力弱化的現(xiàn)象,以及文化產(chǎn)品的原創(chuàng)性和優(yōu)質性降低甚至抄襲的亂象,而產(chǎn)品所傳達的價值觀、審美觀的扭曲也體現(xiàn)出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意識形態(tài)的混亂[12]。人工智能在提高網(wǎng)絡文學、文化信息、影視傳媒等文化創(chuàng)意領域的生產(chǎn)能力和效率的同時,也引發(fā)了原創(chuàng)內容缺失、創(chuàng)作質量和深度不夠、創(chuàng)新積極性下降等問題,長此以往必然會導致文化內容單一的后果。
另一方面,雖然人工智能平臺可以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實現(xiàn)內容的智能傳播與分發(fā),以深度挖掘用戶需求來實現(xiàn)不同內容的實時傳遞,但是,AI 平臺對用戶數(shù)據(jù)進行實時觀測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對用戶的文化習慣和需求進行引導的過程[13]。基于智能算法推薦的文化生產(chǎn)和傳播會完全以用戶的需求和興趣來推薦文化產(chǎn)品,用戶在不斷獲取與其心理取向同質化的文化產(chǎn)品和信息的過程中,會逐漸被這種“個性化”的智能推薦所捆綁。在智能化信息時代,互聯(lián)網(wǎng)使人類變得更加浮躁,當人們只關注自己感興趣、與他們有關的話題的時候,雖然獲得了他們認為的“高效生活”,但也無形中陷入了人工智能所帶給人類的“信息繭房”②(Information Cocoons)。同時,由于網(wǎng)絡信息來源冗余龐雜,如果對于相關信息不能做出及時的判斷和甄別,很容易被錯誤信息誤導從而失去應有的判斷能力[14]。
英國學者安吉拉·默克羅比(Angela McRobbie)曾提出關于大眾傳播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問題,她認為后現(xiàn)代社會人們生活在由大眾傳播所引發(fā)的“道德恐慌”中,在其中會有大量不曾被注意的社會文化問題被放大凸顯。隨著人工智能時代全新的文化創(chuàng)意生產(chǎn)模式和傳播空間的形成,由于AI 在不斷的自動生產(chǎn)圖像、信息、文化產(chǎn)品等內容,因此相應的“道德恐慌”問題也會加劇,即由智能文化產(chǎn)品構成的智能社會正在向人們灌輸一種危機感,甚至會導致人們回避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復雜社會問題,進而造成“城堡式心態(tài)”。
4 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與技術關系的演化與思考
當今社會,科學技術為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和技術支撐,并極大的拓展了相應的傳播媒介,傳統(tǒng)文創(chuàng)企業(yè)借力于高新技術,以創(chuàng)新為動力,在與信息技術融合發(fā)展的過程中將碎片化需求重新整合,打破了固有的文化生產(chǎn)和消費方式,并培養(yǎng)出一群完全不同的文化消費群體。新興技術在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應用不僅為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平臺,也讓傳統(tǒng)文創(chuàng)企業(yè)獲得了更高的利潤。在文化創(chuàng)意與技術創(chuàng)新不斷融合發(fā)展的過程中,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逐漸走向智能化,而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品也體現(xiàn)出技術性和新穎性,文化創(chuàng)意被可視化,同時可視化的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又不斷催生出新的業(yè)態(tài),成為經(jīng)濟發(fā)展的新增長點。
不可否認人工智能產(chǎn)業(yè)在未來可以滿足人類各方面物質需求的生產(chǎn),但作為更加注重人類精神文明需要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在其發(fā)展的過程中則更需要強調人類的智慧。正如上文所述,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技術創(chuàng)作的文化創(chuàng)意內容及其生產(chǎn)模式將會引發(fā)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除卻技術發(fā)展所帶來的非創(chuàng)意性工種的替代和失業(yè)問題,以及互聯(lián)網(wǎng)大數(shù)據(jù)隱含的數(shù)據(jù)安全和信息偏差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大量網(wǎng)絡內容與信息的迸發(fā)和自動傳播可能引起的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矛盾和價值分化,而這些問題會進一步導致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和安全隱患。
事實上,技術在不斷推動現(xiàn)代社會各方面發(fā)展的同時,人類社會原有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都在悄然發(fā)生著變化。雖然人工智能驅動的文化創(chuàng)意創(chuàng)作和審美角度能夠推動人類的自主創(chuàng)新以及創(chuàng)意的產(chǎn)生和高效實現(xiàn),但這一過程也給人類帶來了關于技術倫理的思辨,尤其是對于創(chuàng)意領域,AI 的過度介入和使用可能會導致創(chuàng)意主體參與度的降低,從而引起創(chuàng)意端和消費端的創(chuàng)新水平、認知能力和審美能力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長期對文化內容和用戶信息進行自動化處理與輸出,從而引發(fā)的人類認知能力削弱也必然會導致人類思維方式的固化。
人工智能技術的發(fā)展是人類社會理性活動的結果,技術的應用體現(xiàn)著人類的需求,從對人類身體的延展向思想的延伸演化,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工具的智能技術也逐漸顯現(xiàn)出對人類本身異化的危機。人工智能時代,技術應用為人類提供了更高質量的生活水平和豐富的精神享受,人們在與各種智能技術對象互動溝通、享受文化產(chǎn)品與服務的過程中,其生活方式、思維模式乃至倫理觀念都在無形中被重塑,整個社會文化的價值觀念也都將迎來挑戰(zhàn)[15]。人工智能時代社會技術與人類的相處模式逐漸表明,技術的應用使人們在許多方面可以進行自動的、無意識的感知,而智能技術在文化創(chuàng)意領域的應用使得大眾逐漸失去了對文化內容進行個人判斷和思考的能力[16]。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技術在重塑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鏈時引發(fā)的人文倫理問題,以及人工智能未來自我認同思想系統(tǒng)的形成都將挑戰(zhàn)現(xiàn)實意義上人的存在。
5 結束語
從工業(yè)技術時代到數(shù)字技術、智能信息技術時代,人類對于文化內容的傳承與發(fā)展都面臨著技術介入與滲透的難題。新興技術的應用雖然帶給文化創(chuàng)意領域以改變和革新,但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不是簡單的內容與技術的疊加,在精準把握用戶需求的基礎上對傳統(tǒng)文化內容進行有意義的創(chuàng)新才是其發(fā)展的不竭動力。我們要把握的是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中技術介入和應用的界限,并以相應的科技、人文倫理為底線進行文化內容與制度的創(chuàng)新,樹立以人為本、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價值觀,對人工智能進入文創(chuàng)產(chǎn)業(yè)的邊界和范疇做出明確的規(guī)定,推動人文價值與人工智能系統(tǒng)的良好融合,實現(xiàn)多元主體參與的人工智能倫理治理[17]。
注釋:
①范式轉移:認知模式、思維模式的轉變,用來描述某一領域對于基本理論做出的根本性修正,由托馬斯·庫恩于1962 年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
②信息繭房:指人們的日常關注的領域受到自己的興趣和習慣所引導,長此以往會將自己之故于信息的牢籠之中,由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桑斯坦于2006《信息烏托邦》中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