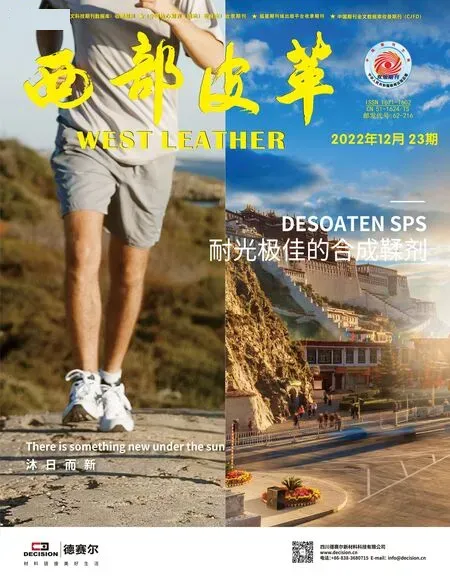體驗經濟下消費者體驗層次的探討
——以苗族蠟染為例
王筱
(云南民族大學藝術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引言
體驗經濟時代的到來是物質生活水平快速發展的必然趨勢。早在1999 年,約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爾摩就在《體驗經濟》一書中指出,所謂體驗經濟,就是一種以商品為道具,以服務為舞臺,為滿足人們的體驗而產生的經濟形態,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浪潮[1]。具體來說,這種經濟行為已不僅只出于基本實用性的需求,其本身還包含著對于情感價值的追求,即關注發展、身份地位與藝術品位等,形成以符號化為特征的消費新風尚。至此階段,審美逐漸演變為一種文化資本,影響著消費者的觀念,而充滿趣味性的苗族蠟染,也自然成為其選擇的對象。在這一過程之中,人們所獲得的精神快感,可大致分為感官體驗、審美體驗以及情感體驗三重層次。
1 苗族蠟染消費者的感官體驗
隨著旅游業的繁榮發展,體驗式項目現逐漸成為一種常見的活動,消費者在其游玩過程之中,以親身的參與來獲得有關身體上的直觀感受。而這種體驗往往是借視、聽、嗅、味、觸等多種感官渠道來接收信息,從而進一步引發主體的情感[2]。作為當下商業開發較為成熟的體驗型技藝,同樣苗族蠟染也以一種創新的形式,在視覺、嗅覺、觸覺等多種感官上,給予消費者強烈的刺激,也就是感知的第一步——感官體驗。
1.1 視覺體驗
1.1.1 色彩
苗族蠟染的色彩呈現通常以藍、白兩大顏色為主,所制作出的成品也大多為藍底白花或白底藍花樣式。從色彩心理學的角度來看,藍色深沉、白色淡雅,二者相互襯托明快清新的視覺沖擊力,會帶給觀者一種古樸自然的心理感受。而這樣的色彩特征與苗族自身樸素的文化生活是分不開的,并且其也受到了地理環境的影響,貴州山林眾多、氣候潮濕,非常適合蠟染原材料——藍靛草的生長。這種染料上色后,不僅可使布料耐洗、不褪色,而且還能依據藍白色彩比例分辨出當地女性的身份,由此進一步傳達苗族人民崇尚自然、簡單樸實的思想。當然,這一觀念與當下消費市場的趨勢也較為契合,現有大量群體將傳統復古的風尚作為自身的審美追求。因此,西江地區的蠟染商品,通常在保留本真藍白特征的基礎上,進行元素的添加,來確保產品與所表達之美的一致性,使消費者獲得別樣的精神滿足。
1.1.2 造型
對于苗蠟蠟染來說,其最大的造型特點就是均衡對稱。整體來看,蠟染畫面雖圖案復雜、紋飾繁多,但構圖時卻表現出一種極為規整的感覺,充分展現出視覺上的裝飾之美。當然,這種呈現形式與苗族人民追求圓滿的思想息息相關,以滿和全為創作理念的蠟染,將不同時空的多種物象巧妙融合在一起,使其彰顯出獨特的韻味。不過,這一特征與現代繪畫相比也存在些許不同,其物象大小不僅不受自然比例的限制,構圖時也完全依照主次關系來決定位置,但這并不影響整體視覺效果的表達。因為藝人們以多年創作的經驗,可將線條、紋樣進行有序的組合,完成協調工整的“程式化”造型。這一傳承苗族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在作為商品時,以一種生動的感染力,賦予了消費者和諧規整的感官體驗。
1.2 嗅覺體驗
1.2.1 蠟材
蠟材是蠟染工藝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又分為植物蠟、動物蠟等多種類型,是天然的一種防染劑[3]。苗族蠟染傳統所用的一般為蜂蜜蠟,由純蜂蜜熬制而成,為黃色或棕色半透明固體,味道香、黏性強,上色不易擴散,特別適合于精細線條的描繪。不過,這種蠟材通常制作繁瑣、成本較高,不適宜體驗項目中的大規模使用,因此在實際經營時,現多將石蠟與其以1:2 比例混合在一起。當然,這種綜合蠟材在燃燒時會散發出特殊的氣味,直接刺激消費者的嗅覺,從而達到“以味傳物”的互動體驗,引起人們的注意。
1.2.2 染料
染料所用的原材料,一般會選用當地種植的草藥——馬藍(又稱板藍根、藍靛草),其是提煉藍靛的重要原料,也是多種植物染料中應用最早、最廣的一種,在貴州地區極為常見[4]。通常情況下,馬藍會在春天開始種植,并于每年的8、9 月份進行收割,加工制成藍靛,其制作方法分為浸泡藍草、加入石灰或草堿水發酵、攪拌過濾、沉淀成泥幾大步驟。而這一過程往往需要十幾天到半個月才能完成,因此經過漚制的黑藍色染料水會散發出酸臭氣味,帶給消費者極為特殊的感官印象。
1.3 觸覺體驗
1.3.1 布料
苗族蠟染所用的布料通常會選用白棉麻布,這種面料不僅平整厚實,上蠟時不易擴散,而且還能更好地吸收染料,提升染色效果。在以前,這種布料往往由家庭手動自紡自織,雖結實耐用但生產效率較低,現多被淘汰掉。如今,工業生產的白棉布取代了其地位,這點在體驗項目與產品的開發中表現的尤為明顯,通常制作者會對購買來的T 恤、連衣裙、帆布包等白色成品服飾進行二次加工,省去紡織步驟。不過在實際操作時,其仍會注意選用棉、麻、絲等材質,傳遞給消費者簡單質樸的感知體驗。
1.3.2 蠟刀
蠟刀,是蠟染制作過程中最為重要的工具之一,其刀片一般采用紅銅或黃銅,手柄則由木頭或金屬制成而成,小巧堅硬。在日常生活中,苗族人民所用的蠟刀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三角形蠟刀,二是弧形蠟刀。三角形蠟刀刀頭為三角狀,內部夾有2-4片重疊的小銅片,外部包裹兩片對稱且連接的三角,側面呈尖角形態。而弧形蠟刀刀頭則呈圓弧狀,其由兩片對稱的弧形銅片夾一片略小的銅片并列組成[5]。這二者都存在不同型號,可依據圖案進行相應的選擇,畫出所需的線條。不可否認,這種繪制工具對于消費者來說是極為新穎的,它以區別于傳統畫法的堅硬溫熱觸感激發其體驗的欲望。
2 苗族蠟染消費者的審美體驗
審美體驗是體驗過程中的又一重要內容。這種經驗往往建立在感官體驗的基礎之上,是主體對直接知覺的進一步深化,以來感受審美對象的工藝之美,并獲得身心愉悅。實際上,審美本身就是一種天性,當游客進入到旅游環境之中,就會通過親身的參與,來獲得新穎的體驗。此時,消費者往往會舍棄實用價值,轉而去關注審美價值,由此美學也隨之與消費行為產生深刻的聯結[6]。當然,作為體驗過程中的中心環節,生產者在設計時往往也會將消費者的審美偏好納入考慮范圍之內,但由于大眾審美品位的不定性,產品樣式也在不斷發生改變,而這種現象在苗族蠟染的商業開發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
2.1 圖案的選擇
通常情況下,普通的消費體驗者在繪蠟時,需提前設計好圖案樣式,即使用鉛筆確定出輪廓造型,再蘸蠟涂于該樣稿表面。由此,這里隨之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消費者對于圖案的選擇,以及其所體現出的審美偏好。從傳統視角來看,苗族蠟染的繪畫是基于苗族人民對于生活的觀察,它題材豐富、類型多樣,內容與形式高度統一,富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常見的傳統蠟染主要分為兩大類——自然紋與幾何紋,其線條繁多、規整秩序,顯示出平衡雅致的獨特美感[7]。而這一美學意蘊極為適配中老年受眾的需求,因此在實際體驗時其往往會選擇傳統化的圖案,來滿足他們崇尚古樸的價值觀。當然,現代的審美偏好是極為多樣的,對于年輕的消費者來說,他們更偏向于追求一種簡潔直白的風格,所以該群體在體驗時往往會進行圖案樣式的創新,將傳統內容轉化為卡通人物、數字字母、潮牌商標等現代化形象,獲得審美與創造力的愉悅滿足。如此,蠟染圖案的選擇,在迎合當下市場發展趨勢的基礎上,進一步展示出消費者的多樣審美取向。
2.2 操作的樂趣
蠟染圖案選擇完成之后,就要進行實際的繪制,而這一步所涉及的畫面比例構圖和線條技法的運用,都在體現消費者的實踐樂趣與品位追求。首先,由于商家所提供的杯墊、方巾、T 恤等原始物品,在形狀與尺寸上是各異的,所以此時體驗者需要對所選物品進行構思,考慮圖案的位置大小問題。由此這里也就出現兩種傾向:第一是消費者面對像杯墊等方正小型物品時,將圖案放置于畫面中心,基本占滿整個畫幅所體現的平衡對稱審美意識;第二則是面對T 恤等不規則大型物品時,圖案位置隨機多樣,所體現的留白寫意審美意識。這兩種帶有消費性質的審美,都呈現出當下人們個性化的價值新取向。不過,構圖僅是蠟染體驗中最簡單的一道步驟,接著線條的描繪才是最為困難的事項。由于工具的特殊性,操作者在作畫時通常需要使用反手拿筆,利用尖角斜立勾畫,這樣隨蠟液流出的線條才能平順自如。但此技法對于初次體驗的消費者來說,是頗具難度的,而生疏的操作必然致使其線條歪扭斷連、粗細不一。如此,體驗群體就會追求一種細致順滑的線條表現,以及嚴謹精細的審美偏好。不過無論是構圖還是線條,實際上它們都在反映消費者的品位與情感,而這種感覺又折返引導人們審美意識的表達。
2.3 成品的不定
隨著工藝流程的推進,上蠟后便要進行接續的染色,雖說這一步驟不存在太多方法技巧,但其仍以完全打破往常產品程式化約束的隨機性,在整個工序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通常在染色之前,消費者會對所染面積和顏色深淺進行大致的構思,根據個人喜好選擇局部浸染或整體浸染,深藍色或淺藍色。但這種規劃并不能按照最初設想百分百還原,染料的好壞、染色的時長、捆扎的方式、人工的操作等各種因素都會影響最后的呈現效果。因此,即便是同時間同批次的蠟染成品,也不一定能夠完全相同,細節的不可控致使其充滿著神秘感。然而也正是因為此特性,才賦予蠟染一種與眾不同的表現形式,并以其別樣新穎的范式激發人們的體驗欲望。當然,這種成品的不確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消費者的好奇心,每個人都會擁有屬于自己獨一無二的作品,并由此獲得一種精神愉悅,而這種選擇偏好,也在顯現當今群體追求與眾不同的審美新取向。
3 苗族蠟染消費者的情感體驗
從外在形式的直接感官體驗到獲得感性認知的審美愉悅,消費者的思想意識不斷深入,逐步走向抽象空間,其關注對象也由客體轉為自身,隨之進入感知過程的情感體驗階段[8]。在這一環節中,物品價值丟棄了功能性,只存在于精神層面,消費者占有某一物,實際上是在實現自身的向往與追求,找尋情感的寄托。而作為當下商業化的代表,苗族蠟染也以一種承載著民族精神的符號形象,滿足人們對于異文化的好奇心以及展示個性的自由。
3.1 異文化的好奇
在旅游開發的背景下,原本傳統的苗族蠟染出現了文化狀態的改變,其內容同步創新,工藝逐步簡化,由家庭生活場域走向生產消費場域。當前,苗族蠟染已不再是一種單純的手工藝,其憑借自身的特殊性,演變成當地的文化符號標識。而這種公眾不常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又以反傳統的方式,扮演著“異文化”角色,進而吸引消費者的關注與行動。
現下,苗族蠟染主要以一種體驗化的形式來呈現,消費者不但關注產品的表現如何,還更加注重怎樣去得到這一產品,其體驗過程成為時下最新興的賣點。于是這就要求商家在經營時,不斷去塑造產品形象,加深新奇感受,保持自身的差異性,使客體不自覺去對比其日常生活和當下所見,從而產生消費欲望,為個人認知增加新內容。由此,通過“體驗”的橋梁,消費者便與蠟染產生緊密的聯系,并以一種空間位移的方式獲得新鮮感,成為跨文化情感體驗最直接的創造者。而從該角度出發,這一消費實際即是追求樂趣的過程,這種建立在人本基礎之上,通過移情實現對于未知探索的欲望,最終滿足了個體的好奇心,使之獲得獨特的情感經歷。如此,作為文化產品的苗族蠟染,就以一種情緒上的專屬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體驗,使人超越物質世界,完成自我精神價值的提升[9]。
3.2 個性化的追求
隨著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越發關注情感上的需求,這就致使當下消費行為呈現出一種符號化的特質,追逐個性成為時尚潮流。具體來說,個性化作為一種反傳統、流動化的形式,其本質就是要證明自己與眾不同,并在群體中展現個人魅力,以期與他者區分開來。此時,普通產品已無法激發人們的消費欲望,小眾風尚開始興起,由此那些大量展現自我意識的感性商品逐漸發展為熱門項目,個性化表現也隨之提升。而作為當下帶有較強稀缺性與參與性的苗族蠟染,也自然成為其中一員,在該過程之中,消費者更為在意的是充分發揮創造力,主動加入產品的設計與制作,從而展現的自我意識。
從該意義上來講,對于苗族蠟染的消費并不完全源于物質實用性的需求,它實際是一種形式的追尋,因為擁有這一文化符號即代表著擁有了某種優雅的品味[10]。消費者往往會利用它來引人注意,進行特性的展示,并炫耀自身的階級層次,獲得心理的滿足。具體來說,人們大多會以拍照、錄像、發朋友圈的方式,顯示自己占有這一物,從而進一步凸顯自我形象,將自己與他人區隔。由此,這一象征身份、財富以及品味的消費,便以創新的工藝、陌生的實踐,引導人們全方位了解該事物面貌,進而實現個性化的自由。
4 結論
苗族蠟染文化產品的流行,是體驗經濟時代下消費者自主意識不斷提高,精神需求愈發增強,以期通過金錢交易來獲得愉悅感的結果。而這一情感欲望的滿足,可大致概括為感官體驗、審美體驗和情感體驗三個層次,其中感官體驗是整個過程的起點,審美體驗和情感體驗則是對感官體驗的升華[11]。具體來說,隨著主體認識的不斷深入,其各個環節自然生成聯結,因為沒有直接的感官感受就不會有審美的認知,之后也更不可能產生情感的共鳴,這三者以一種循序漸進的順序緊密嵌套,不可分割,從而為消費者建立起完整的產品認知流程。總之,在當今體驗經濟的環境下,作為地方文化資源的苗族蠟染,通過雙向溝通的方式,使消費者獲得以上三種由淺入深的感知體驗。